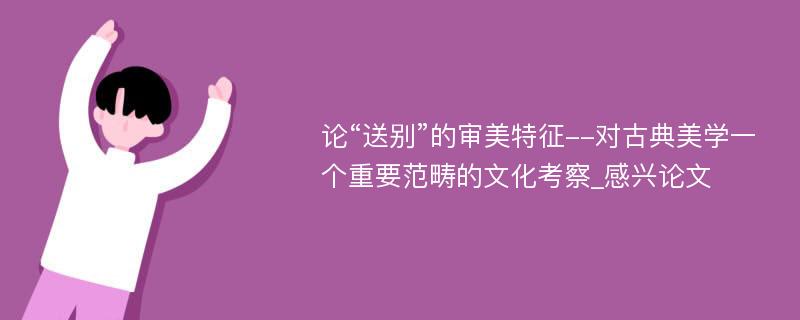
论“寄”的审美特征——关于一个古典美学重要范畴的文化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范畴论文,特征论文,古典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古典美学的研究里,从“感”到“兴”到会都不同程度地引起过学者们的兴趣。如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里,“感物”、“感兴”被列入创造编,“兴会”被列入接受编。皆是将其列为了文艺学中的典型范畴。“兴”之所以能贯彻于创造与接受,完成“感”的范畴向“会”的范畴的审美延伸,事实上是有中介的,从美学的体系上说,这个中介也应当属于美学范畴,它就是“寄”。
一
在“寄”作为一个古典美学范畴被明确提出之前,与“寄”相近的艺术化行为就已经存在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倡。曹魏时期,三曹身上已出现了一些与传统文人很不相同的成分,一方面,他们追逐着事功;另一方面,公务之暇,则又表现出艺文情趣化的向往与沉溺。《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云:“(操)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又引《曹瞒传》云:“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列,常以日达夕。”明人袁小修《铜雀观歌为黄观察赋》亦云:“魏武当年愁寂寞,半谋征战半行乐。自言朝霞去时多,高筑三台结绮阁。西园才子唱新诗,南国佳人藏绣阁。”歌咏其“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的文武并行,非尽为言史实,实乃后人以此风流雅逸的人生当作了自己的模范。曹植《魏德论》言曹丕:“既游精于万机,探幽洞深;复逍遥乎六艺,兼览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场囿,容与乎道术之疆畔。”谢灵运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具体形容其与邺下文人之闲逸,虽不乏个人心中理想色彩,但也可得其环中仿佛。曹植本人,一生有宏图大志,而诗酒逍遥有甚于父兄者。他们父子三人,在事与道的关系上,事不避,道亦求之,此道非大道玄理,正是颐养性命精神的闲情之道,在事外闲暇之中情兴的寄托之道。也就是以曹魏时期为一个基本起点,中国文人在寄托之路上的探索以个性化艺术化的面目开始了。
魏晋玄学兴起,其“应物而无累于物”的思想推动了“寄”在贵族文人中的成熟。王弼云:“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注:《三国志·钟会传》注引。)倡导应物,一方面自然在人生出处上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文人艺术化生命追寻中也具有实践品格,这就是把自我生命与客观世界沟通。这里的客观世界所包容的范围极广,如自然山水、艺术手段、自我之外平常之外的群体生活方式、新异生活内容的投入等等。它们是情感投射的对象,而非改造利用的对象。这个观点在后来的玄学学者那里演化为了“凭乎外资”。此观点见于裴頠《崇有论》,其文云:“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只要入乎品类者,即难免有偏,不能自足,欲心体圆融,则需假物、凭乎外资。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裴頠认为这还是情理之中之“情实”:“是以生(性)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之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这是从普遍的人不可能不凭假外资而言的。这个观点表面看与庄子所推崇的无待是抵触的,但却符合魏晋玄学应物不累于物的新解,因而实亦是情当有所寄的一个基础。而之所以能有这种观念,主要在于中古文人因玄学的洗礼在主体性升扬、个体自觉的延续之中对彼此、物我的区分已经达到相当的哲学高度。如此区分的意义,在于使自我被进一步从与宇宙社会诸关系的混融状态、牵系状态中分离出来,原先笼统的物我彼此关系如今被亮明了归属,自我在清晰中又表现了巨大的局限,远没了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之类思想下的通天达地。因此延伸生命空间与延伸生命时间,便大致一起被文人们当作了追求的理想。而延伸空间之方法,最主要的就是把自我的空间,扩展到他物之上,使他物中闪烁出“我”的生命,这就是生命的空间拓展或扩张,它就需要凭乎外资,需要“寄”。
六朝烟水,江南金粉,使偏安呈现出祚永运隆的假象;从学理化向生活化转变的玄学使玄意人生的追求成为时髦,而这种人生的核心特征就是贵族文人们以种种艺术化的手段、形式的探索,摆脱太平无为下的庸常与凡俗。“寄”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六朝时期逐步确立起来。陶渊明《九日闲居》序云:“寄怀于此。”《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寄事外即是委怀于琴书,“寄”与委意相近。《古诗笺》引郑氏仪礼注云:“委,安也。”此“寄”即是托付而求安,侧重在琴书等遣兴娱情手段。在一些崇尚道家思想倾心于清谈的文人那里,“寄”则往往与山水自然相关,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云:“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王凝之《兰亭诗》:“庄浪濠津,巢步颖湄。冥合真寄,千载同归。”王徽之《兰亭诗》:“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秀薄灿颖,疏松笼崖。游羽扇宵,鳞跃清池。归目寄欢,心冥二奇。”等等。至《梁书·徐勉传》引其尺牍云:“中年聊于东田间营小园者,非在播艺,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寄”与情的关系在此已经被揭出,而江总《游摄山栖霞寺》则明确提出了“从情所寄”。
“寄”在六朝之际常常被表达为托。谢脁《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云:“上春初吉,亦留渊寄。”《说文》:“寄,托也。”王羲之所云:“因寄所托”亦明寄、托二义之相通。江淹《杂体诗》云:“灵芝望三秀,孤筠情所托。”即为以竹之审美投入为情兴所寄。《梁书·文学传》引伏挺致徐勉书云:“怀抱不可直置,情虑不能无托。”《南齐书·徐孝嗣传》云:“孝嗣爱好文学,赏托清胜。”《刘则传》云:“畅余阴于山泽,托暮情于鱼鸟。”沈约《郊居赋》云:“时复托情鱼鸟,归闲蓬荜。”沈约《七贤论》亦云:“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托,慰悦当年,萧散怀抱。”作为一种美学范畴,“从情所寄”、“情虑不能无托”、“情性宜有所托”等明确而热切的呼唤与提倡,正是其已成熟的表现。
二
综合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概括:“寄”是一个涵盖艺术化生命追寻与艺术创作的古典美学范畴,它是通过对客观对象或某种情感形式的选择、沉浸而实现情感托付转移驻留,从而使身心获得安适的一个审美过程。从这个意义理解,“寄”就是使生命有意义而无功利的一种形式选择与形式创造。它表现为以下四个特征:兴寄,审美流程的必然;遣寄,偶然外的主动;显象与含蓄;物我统一的期待。
一,有兴则有“寄”,审美流程的必然。
感兴赏会,是艺术创作、文人艺术化生命状态中的语码,感凭直觉获取了对象或对象的一个侧面;兴,即开始了对锁定之象的内在诸般底蕴与主体性情所钟的对应关系的情感选择。兴是维持主体对此象热情的动力。所谓维持,就是一种具有时间意义的持续,只有这种时间得以维持、愿意维持、且可以维持,美的出现才能成为一种实在的生命状态。而这种维持,不可能凭期望、意志来完成,只能靠兴的转移,在转移的过程里使之与生活相融,由此得以驻留。遣兴即由此而来,但遣兴非是因为“兴”之丰厚而厌之,故才排遣——而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冲动;兴不能移,则心中的热情、诗情就面临着转瞬即逝的遗憾。这种转移,不是说将情兴的关注点从一物转到另一物,而是将情感倾心托付于兴所锁定的物象或情感形式,其中包括以艺术形式将其凝定下来。这就是“寄”。有兴必有寄,乃兴与物统一特性的具体体现:
支遁《咏怀诗》云:“感物思所托,萧条逸韵上。”此处的感就是感兴。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赞语中将兴的运用比作“拟容取心”,二者都是强调兴的运用在于提炼心象,熔铸意蕴,说明兴之中的意蕴寄托的内涵。
释慧远《与隐士刘遗民等书》中称:“徒积怀远之兴,而乏因藉之资,以此永年,岂所以励其宿心哉!意谓六斋日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若染翰缀文,可托兴于此。虽言生于不足,然非言无以畅一诣之感。因骥之喻,亦何必远寄古人。”亦兴在寄前,有兴则必有寄。慧远以“染翰缀文”为“怀远之兴”的“因藉之资”,是寄高兴于文义。又寄津相连,标为“津寄”,更可见在当时文人名僧眼中,“寄”非一种结果,乃是与下面的情感流程相关联的桥梁。
罗大经《鹤林玉露》:“盖兴者,因物感遇,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李俊民《锦唐赋诗序》:“士大夫咏情性,写物状,不托之诗,则托之面,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得之心,应之口,可以夺造化,寓高兴也。”托,即是寄。其意正是以兴之高而思有所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夫人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这里的感也是感兴之意。
由“兴”而至“寄”并不一定都表现为这样明确的理论概括,更多的是从审美实践的流程中显示出来。如高适《白湖寺后溪宿云门》:“毕竟有余兴,到家调玉琴。”此兴之所激起的,正是超越自我的局限,欲寻对象寄托宣泄,借以沟通主客、摆脱自我孤独的冲动。此外,“兴”作为一种情感冲动,它对于主体之具体的情感、行为以及选择具有强化功能,因而使“兴”又表现为种种内容上的差异。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东阁官梅动诗兴”,此诗兴。《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得心字》:“野兴每难尽,江楼延赏心”,此野兴。白居易诗有《清夜琴兴》。他如归兴、游兴、酒兴等等,不仅成为对主体某种情感与相应行为的支撑,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其由此深化进文人诗意的心灵,从而使其在一种艺术化生命状态中悬浮、流连,与理智、现实拉开距离,兴之所至,“乘兴”而为,最著名的例证,即是《世说新语》所载王子猷之雪夜访戴安道,乘兴而往,兴尽而还,何必见戴的风流;又嵇康吕安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张翰因秋风起而归帆。而乘兴而为的整体过程就是“寄”,它兼包着“兴”,兼包着主体的情感与客体的交融,包含着主体的情感形式表达、选择。
关于“兴”与“寄”的这种内在关系,袁济喜先生在《论兴的审美世界》一文中也有所揭示,他认为:“循着这种对兴的认识深化,人们对兴之中的寄托含义也有了新的掌握……魏晋以来的文士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兴’,可以寄托深邈浩博的心灵活动,可以将内心无法言传的想法与情感,通过‘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寄兴来表达,而这种表达是一种‘前表达’,也就是说不同于常规的语言表达,它借助于原始思维中的触类相长与观物取象的思维方法,而相对黜退了文明社会惯用的一套语言符号系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兴”而至“寄”,就是主体对客体在模糊把握中的最终落实的指令形式——用以统领、规束、深化这一情感流程的指令形式。这个过程,苏珊·朗格以音乐家创作给予了形象的说明:“音乐家可能坐在钢琴前弹奏着各种主题,在一个松弛的幻想曲中把它们掺合在一起,直到一个乐思或一个结构从这种遐想的声音中浮现出来。他仿佛忽然听到了整个音乐形象……从此,他的心思不能再随心所欲地从这个主题到那个主题,从这个调式到那个调式,从这种情绪到那种情绪地任意漫游了……人们可以把最初的概念称为作品的指令形式(Commendingform)”(注:《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140页、142页。)。此指令形式,即是兴的寄托。这种指令形式一旦在艺术观照中出现,心思与情感便不能再随心所欲,而是表现为一种艺术化生命状态下的皈依。它是完全在情愿统摄下的投入与对其他的放弃。此种情感愉悦之坚持、之专著于一体,即是已进入“寄”之境界的象征。而不再旁及其它的情趣选择的限定,不仅没有窒息美的活力,恰恰为审美观照、寄托开拓出丰厚自由的美质创造了条件:“指令形式从根本上讲不是限制的,而是丰富多彩的。一个完全自由的想象正是苦于缺少某种圈定,从而处在一种先于总体形式概念的不明确的摸索阶段”(注:《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140页、142页。)。而“兴”的本原形态里,主要包含着类似于类比想象的引类譬喻,其间升腾着难以指实的纷杂信息。可见,“兴”之指令形式的获得,正是对“寄”之对象的选定与情感投射,从而获得情感的驻留、深化,继而放飞。
二,兴寄外的遣寄:偶然外的主动。
前面论述里,已说明了因兴而“寄”的纯美学品位,它乃属一种审美偶然。但经常又存在这样的情形,心绪郁陶,烦累萦怀。而此时文人们所开出的药方,也是“寄”。陈眉公《小窗幽记》云:“眉上几分愁,且去观棋酌酒;心中多少乐,只来种竹浇花。”后者即是兴寄、移情,它使生命激情得以延展;前者则属遣寄,以寄寻遣,以期生命情感的平复,其重要的手段就是前面提到的凭乎外资的假物。假物表示主体对客体的选择,不是偶然的无意,而是略有被动的不得已;而“寄”则代表着贯通赏会的一种物我两忘的审美情境。嵇康《琴赋》云:“顾兹梧而兴虑,思假物以托心。”此处之假物,即上述之选择意,而“托心”,才是代表美学意义的“寄”。超越了情当有所托,而进入已经托付的过程,至乎“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这才是“寄”的境界。
假物与“寄”的关系,关键在于主体借物而可迁想妙得,这是玄学对主体提升所带给文人的心法。这其中的理路是:先假此物入人耳目,经善想妙思的美学联想而将物提升;提升的结果是创造出了经主观情感改造的物的第二自然。进入这一阶段的情感,才属于“寄”的阶段——超越了假物而进入物我一体之赏会。
从上述意义看,假物与“寄”之关系,就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具体到艺术境界上,实即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变迁。王国维《人间词话》,将意境分为有我、无我二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我对峙;无我之境,以物观物,物我两忘。如果要在六朝文人艺术化追寻中寻求二者的对应,当以谢灵运的山水参玄诗与陶渊明的田园诗最有代表性。玄言诗是以诗化之玄理,追求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情与理的统一,在若有若无扑朔迷离中获得精神境界的超逸与人格的升扬。玄言诗发展至于晋宋之际,出现以山水悟道的趋势:以言寄意之外又引入以名象寄意。唯其假山水而体玄,功利目的很强,故其山水诗的山水与主体之间往往被玄理阻隔,显出明显的二者并列、对峙,难以融为一体。这就是有我之境,是假物。当然,这只是诗歌外形的呈现,而就大谢本身的情感获得而言,他同样达到了“寄”的目的,即心灵的赏会。陶渊明于田园诗酒,无一非“寄”,《诸本评陶汇集》引张尔公洁生曰:“渊明无之非寄,凡获稻饮酒乞食读书皆寄耳。诗又寄之寄也。岂必铢铢两两与余人校工拙论喜憎哉?”此寄,也含有假物的成分,但在假这一手段的展开过程中,陶渊明率先发现了假于物这一手段、这一过程本身亦是一个美不可言的与物统一、吸纳生机的过程。手段与目的统一,原先的功利心反而被遗落、淡化。目的手段的区分没有了,我自然已丧失了在此境中的位置,无我之境,即由此而生。假物至此即升华为“寄”。
人生于世,悲戚多于欢娱,不如意事常八九,所以这凭借假物的遣寄一途便得以光大,从而渐渐具备可操作的品格。袁中郎说:“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什么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注:《袁中郎尺牍·李子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袁中郎全集》本。) 强调的也是情当有所寄的假物,属于遣寄一途。尽管从功利的遣置入手,有官能消遣的求“用”痕迹,但即使是遣寄的非偶然性之“寄”中,仍能通过在假物与投入执着中获得兴发,从而使假物转化为高级之寄,达到物我一体的赏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寄”就是以假物为开端进而达乎赏会审美状态的得意忘言的一个过程。“寄”与遣的这种关系,是以主体的有意识选择寄托对象开始的,亦是对生理快感满足基础的肯定。既然人生实难,所谓高兴盈怀的激动并不是人生的常态,因此,从选择所假之对象入手,先通过初级的假物凝聚心神,在此基础上通过消遣掉或遮蔽掉心中的愁郁而进入审美之境,也是更近情更真实的对“寄”的理解与应用。六朝及其前后的文学创作,在兴寄之余,多有遣寄色彩,《文心雕龙·序志》云:“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分析这节文字,可以品出在刘勰的意识里,诗文可为情之所寄含以下理由:一是生也有涯的深刻反省,使有与无这一对范畴间的落差在文人心中造成了巨大的鸿沟,而要填充、消弭二者之间的这种距离,凭对外物、欲望的追逐难以完成,只能通过顺性情而为。二是傲岸泉石与咀嚼文义,在文人眼里,即是性情所嗜者,二者是相等的,无价值上的差异,山水泉石可寄,诗文研、创自然也可寄。可寄的原因就是文可载心。仔细品味,其因人生之无奈而引发的欲使此心此情有所托付、从而获得消遣的心态很明显。文既可承载文人之心之情,自然文人可以将情寄于创作甚至其他著述,从而使之获得安顿。这是对遣寄较早的理论阐释。刘铁云《老残游记》自叙云:“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所谓哭泣,正是心中积聚的浓烈情感,而寄哭泣于艺术创作,也正是以创作为寄,寻求情怀的转移与平复。
三,“寄”的显象与含蓄。
“寄”的显象特征,就是主体在客体中能发现主体精神的同态对应物,即本质力量可以达到对象化的显现。一种审美意境的落实,最终皆以一种诗化的情感形式选择表现出来。此表现或为对第二自然的观照,或为情感固态物的创作与鉴赏。这个过程中所包含的用于表达以上意境的符号核心就是形或象,这就是“寄”之显象。其理论依据就是玄学的寄象出意。
宗炳《画山水序》云:“神本无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栖,即寄之意。所谓栖形,即将神寄于有形,将无寄于有。山水以形媚道,此道正是山水之神。主体之神——情趣性灵,对山水之神的追觅,可使二者达到际会,从而使心之期待、目之搜求在山水之具象中发现。山水仍系同一山水,但其与心契合,存在着主体迁想之变;虽变,然象却未变;此未变之象中包含着对所有迁想的开放。因而,它就是“寄”的具象或显象。何劭《游仙诗》中云:“吉士怀贞心,悟物思远托。扬志玄云际,流目瞩岩石。”心有远思,远即是玄理之所逐,而玄云际与岩石,正是扬志、流目所寄的对象。二者并为远的显象,但又并非是远的本身,它只是一种远的姿态的展示,但又不可能涵盖远的阔大与飘缈。尽管如此,正因为这种显象如上所言与主体兴发之际所有的迁想对应,所以具体之象中实际上有着无限的情感空间与可能,这就是玄学以有而达无的现实表现。最贴切的解释是雷简夫的一段话:“余偶画卧,闻江涨瀑声,想其波涛翻翻,迅駃掀摇,高下蹙逐奔去之状,无物可以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在笺下矣。”(注:《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31页、144页。) 显象,将心中无法彻底具体化的情以具体的象作一个见证,同时又实现了将瞬间永恒化。所显之象、心中之象在这个创作过程中统一为浑然之境。这一特点,实际上是与“兴”的托物为喻一致的,因为“寄”是在感兴赏会的链条上实现对“兴”的超越而出现的审美状态与情趣,所以它身上具备“兴”的特征很正常,同时甚至可以认为,这就是“兴”的托物为喻特征的延伸。古代文人艺术化生命状态追求中的种种因兴而寄的淋漓表达——诗、词、曲、赋、小说、书、画等等的即兴创作与无为色彩极重的酬应,都是“寄”的显象功能的具体显现,这些作品就是对文人高兴的见证与记录。
“寄”的显象与短暂往往是一体的,因为靠显象来表示其存在本身,就说明其存在对各种外因的依赖以及自身的飘移与无自性。因寄托而显示驻留,在驻留中显示这片刻的也是片面的“自性”。“寄”的短暂性,是与美的短暂、审美感觉的短暂一致的。先秦典籍中言“寄”者不多,大致集中于一意:暂寓而时间短促。魏晋文人自觉,承此二义,于“寄”的暂寓一意敷演颇多,基调即是源于人的自觉的人生如寄。曹丕《善哉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陆机《豫章行》:“寄世将几何,日冥无停阴。”张华《轻薄篇》:“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陶渊明《荣木》:“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谢安与支道林书》云:“生如寄耳。”这种意识在中古扩散,使美学意义之“寄”中,宿命般地难逃这种苦涩味道。中古文人,对人生如寄的道理悟之极彻,“寄”中所含的这种客居流浪的内容,是其短暂的根本源泉,虽经美学洗礼,此意却难以脱尽。但恰是对这种短暂性的深刻体认,六朝文人才更深刻地领会和珍惜由“寄”而带来的当下性的美的陶醉。方东树评陶渊明《形影神》三诗云:“形影神三诗,用庄子之理,见人生贤愚贵贱,穷通寿夭,莫非天定。人当委运任化,无为欣戚喜惧于其中,以作庸人无益之扰。即有意于醉酒立善,皆非达道之自然。后来佛学,实地如是,此诚足解拘牵役形之累,然似不如屈子九歌司命之有下落。至于康乐,见亦如此,而一归于寄情山水,尤为没下梢。于圣人大中至正尽人理之学,皆未有达。此洛、闽以前人,其学识到此而止。”(注:《昭昧詹言》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方东树之观点,主要是以下两点:汉魏儒学不振,文人基本操守遗落,无道义可言;理学未兴,见道不彻,人生追求茫然无措,只凭有意于酒、寄情山水消磨。方的此观点,实是混淆了美学与理学、审美与见道、情与理的关系,忽略了正是因为所行“没下梢”,才见出“寄”的重要特征——只重当下,瞬间即逝,更无种因待果之功利。
“寄”之短暂,是其本体的特征,非是主体审美寄托的感受。相反,“寄”的实际感受与文人对它的期待恰恰是长久。《宋书·隐逸传》引雷次宗《与子侄书》云:“日月不处,忽复十年,犬马之齿,已逾知命。崦嵫将迫,前途几何?实远想尚子五岳之举,近谢居室琐琐之勤。及今耄未至昏,衰不及顿,尚可厉志于所期,纵心于所托。栖诚来生之津梁,专气暮年之摄养,玩岁日于良辰,偷余乐于将除。在心所期,尽于此矣。”书中列及所托,含未引录之山水之好,晤言之欢,又及幽栖、专气、玩良辰、偷余乐。将有限的人生,托付于这些无目的的兴趣里,单调由此丰富,而有限之人生亦由此被拆解,使短暂被丰富所延长,“寄”所给主体的感受,正在于此。
含蓄实际上是对“寄”的显象特征的另一种理解路径。从“寄”的情实而言,《周易·系辞传》开其先河:“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玄学学者在象和意、言和意之间拈出的关系即是寄言出意、寄象出意;寄言出意又言不尽意,寄象出意又象不尽意,等等。也就是说,“寄”之显象,一方面可以使混融的情感意境具象化,便于情感意境的言说表达,但另一方面,此有中含无,象中又具不尽之意义,本是具体的象却向着丰富敞开,这就是“寄”的含蓄。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论词之寄托的“出”:“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羡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文中推崇的正是这种与直白相反的混容与含蓄,而这种含蓄则来源于寄托。蒲松龄《聊斋自志》云:“盖有漏根因,未结天人之果;而随风荡堕,竟结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其无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磋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作者在此是心有孤愤而无法明言,故寄于狐仙鬼怪,青林黑塞,其迂曲含蓄也因“寄”而见。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中云:“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其意正是假“寄”为途径,达到意境的婉曲,是“寄”的含蓄特征的表现。
四,物我统一的期待。
概而言之的话,可以说“寄”即是寻求物我统一的努力与期待。“寄”之物我统一的特点,可从两个维度理解:一是“寄”之中形神俱冥;二是“寄”之中达于忘境。
所谓形神俱冥,就是主体与外物在神理之上达到契和。形即主体,神则指自然之理与自我的本体性的真性情。形神欲达契合,需要有一个通过寄托使形入于神——使自我之精神合于物之精神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消弭物我界限,打通沟通之路的过程。《鹤林玉露》丙编卷六云:“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迈愈精。余尝问其有所传乎。无疑笑曰:是岂有法可传哉?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寄于草虫而融入草虫。《绘事微言》之《山水性情》云:“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得其性情,山便得环抱起伏之势,如跳如坐,如俯仰,如挂脚,自然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而落笔不软矣;水便得涛浪潆回之势,如绮如云,如奔如怒,如鬼面,自然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而落笔不板呆矣。”此寄山水而融于山水。二者皆在物象之中,因痴迷的投入发现了自我情感、性情的同态对应,在第一自然之中看到了潜在的第二自然,物我难分难解。徐勉《诫子书》中称自己聚石移果,杂以花卉,其目的就是“以娱休沐,用托性灵”。花木石果之所以能托主体之性灵,其原因正在于主体性灵之爱、情趣之尚、赏心之处,与“寄”之对象的“风、趣、韵”等有契合之处,所谓托于此,正是借对象将心中这种性灵、趣味唤发出来表现出来。此间之我与物,是一体化的。所以:“什么物之神、己之神,古人根本不注意这样的区分,或者说正是要取消这样的区分。无论从物之神出发,还是从己之神出发,最后都是要达到二者的统一。只有达到了二者的统一,才算达到了美”(注:成复旺《神与物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版,52页。)。
另一条统一之途即是在“寄”中的忘却,忘却的对象就是“寄”的对象,这是玄学得意忘言之旨在审美中的渗透。郭象《庄子·大宗师注》中有云:“宜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则夫游外弘内之道坦然自明,而庄子一书,故是超俗盖世之谈矣。”此倡忘其所寄之言、事、象以求意。东晋李轨注《法言》云:“妙旨非见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统,故每遗其妙寄,而去其粗迹。”倡遗其妙寄。僧叡《十二门论序》云:“表我在乎落筌,筌忘存乎遗寄。”此在倡忘寄之外,又专门强调“筌我”兼忘——即忘所寄之对象,所假之中介,又忘寄象假物之主体。忘中即没有了分别与差异,所有的就是一体。以上是玄学对物我关系中“寄”的中介之用“忘”的强调。在具体的诗文里,中古文人们还表达了另一种忘的路径,这就是因执着于所寄托而实现对其它的暂时忘却。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中云:“(其)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寄”,在这两处即是托情于众事、于酒,而其意又皆不在此,无非假此以忘俗情。
“寄”在“忘”中达到统一,实则与美学上讲的“隔绝的力量”有些近似。主体在浸入主客所营造的情境氛围之际,“寄”的对象起到了一种隔绝作用。凭这种隔绝,主体形成了一个暂时与社会、与理性世界不相贯通的自由王国,在这里,自由得益于时空有限的封闭。
三
作为一种玄化的审美状态,“寄”的体验系偶然性与目的性的统一。当其得意之际,自我与所寄的对象呈现为难解难分的浑融,自我放弃了任何的判断与品评。这一唯美生命状态在物我一体的境界中表现了充分的当下的沉浸,没有此外的顾及与功利。宗白华评王徽之嗜竹时即称,他“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量和充实,不为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注:《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31页、144页。)。这是人生一种忘怀一切的身心自在,其间有着从心为适的自足,是人生具有终极情调的境界,它因为褪去了世俗氛埃的沾染、现实人生的心力交瘁征逐无涯而一朝清真透朗,自由解放。
这样一个范畴的确立有着重要的美学意义,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文人艺术化生命状态追求因此实现了由志到情的落实;二是在古典文艺学或诗学当中从此确立了寄托这种艺术手法。
庄子设定的人生境界,任自然、与道冥、玄游坐忘、逍遥是纯哲学的境界,不是人的境界。但这种境界作为人生理想,在汉末之后,仍然以其神秘的魅力,吸引着众多文人的目光。蔡邕《琴歌》、仲长统《述志诗》、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等,都表现了对这一道境的心仪和渴望,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停留在“志”的阶段——文中所描绘的境界,往往或心向往之而未践行;或只是道境的再现;或要表达一种高远的姿态与不得已与现实的疏离,一如阮籍《咏怀》、《大人先生传》,与神游相似,又时时取鸿鹄玄鹤等以为载体,驮着自己的梦翱游。
但“寄”的审美范畴基本成熟之后,这种状态发生了变化。以嵇康为例,在他的作品中,开始广泛涉及到艺术化生命状态的追求手段,且作品中开始出现玄境、实境相融合的境界。如《赠秀才入军诗》中云:“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此诗中间,有着高逸玄妙画也画不出的境界,同时又皆将其融入了人间生活的场景与手段。其间有伦常之色彩、有日常性所寓的对崇高的淡化。但又让人品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人伦情味十足的闲适生活与玄味十足的对人生的玄悟,一志与一情,在此是一体的。形而下的情的真心投入——即“寄”的实现,就是形而上之志的现实表达;而这个过程,就是志寄于情或者说就是玄境寄于实境的过程。至此,魏晋文人追求艺术化生命状态的志终于因为“寄”的成熟而有了落脚点,那就是志向情的落实。而情与志的差别在于,志未践行,而情则需要向外发抒、表现;志玄虚无端,情则需回归现实人生。文人们因为这个落脚点的落实,才得以将理想的追寻假种种艺术创作、艺术化行为以及其他丰富多彩的范式而表现出来,由此而实现移情,实现以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饮酒、雅集、清谈、登山临水、田园耕读、诗文流连等等范式,就这样在贵族闲逸人生追求的实践中与“寄”的观念同时发展、成熟起来的,它们是历史的积淀与主观情感的整合,是艺术化生命状态在现实人生中展开的重要形式,也是主要内容。文人艺术化生命状态的追寻,也就是这些情感寄托范式的继承、丰富、表现、创造与享受的过程。
尤其是诗歌、文章、赋以及随后的词、曲、小说、笔记等的创作、交流,因为“寄”的审美范畴在六朝的确立而与先秦两汉的一定程度的功利拉开距离,而以之为审美寄托手段,消释心中抑郁幽愤、抒发自我兴会情赏,逐步形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而文学创作也由此成为历代文人艺术化生命状态得以实践的最重要的形式。艺术范畴的文学的内涵也由此愈发丰满起来。
在生命情感的寄托之外,经过长期文学实践的探索与文艺理论的总结,寄托又演化为了艺术创作的一种手法。如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况周颐《蕙风词话》:“词贵有寄托。可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沈祥龙《论词随笔》:“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这些论述,强调的都是在词可以为情怀之寄托的基础之上,在词当中将自己深远、飘缈的情感托付其中。这对深化文学作品的意境显然有着重要意义,而这种手法所依托的手段就是意象或兴象的摄取或塑造,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寄托艺术手段的实际应用要远远早于寄托理论的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