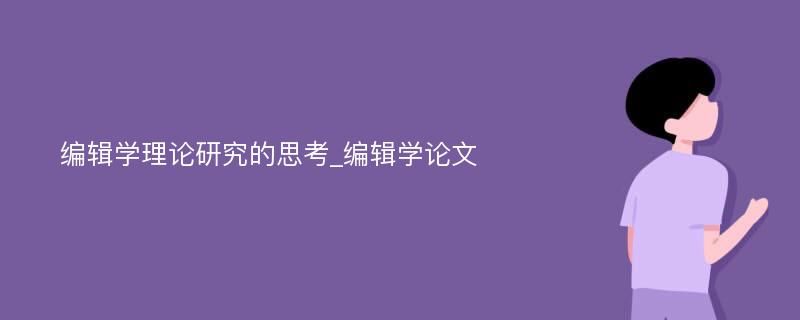
编辑学理论研究之非是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非是”,即“不是什么”。本文题旨所在,是要对那些与编辑学理论研究相悖的形式与方法进行一番检视与思考。
三年前,笔者曾为《编辑之友》杂志草拟过一则《征稿启事》,登载在1991年第6期上,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编辑学理论研究已走过了它的草创时期,目前,若想最终建立起这门学科的大厦,似应注重于从具体的、微观的角度入手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对于仍然将论题停留在诸如有学无学、有多少分支学科、如何研究这门学科之类的只打外围不攻坚层次的文章,本刊将敬而远之。”“论文,应当‘论’、应当‘证’,而忌‘议’。”现在再来翻检这段文字,这只是笔者当时在读稿过程中的一些断续、零散的感受,表述未必准确和周全。然而,自那以后至今,《征稿启事》里边指出的有关来稿当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于是,笔者将担任《编辑之友》杂志编辑工作的九年当中,在阅读和编选有关编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稿件时所发现和感觉到的一些问题加以梳理,对那些未予采用的稿件做了一个大致的分类,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文中或有失之偏颇之处,望方家学者不吝赐教,给予指正。
1.编辑学不是臆想的分支学科的罗列
围绕编辑学到底有多少分支学科,并由此繁衍成文,罗列成表,这样的文章我们称之为“罗列分支学科型编辑学文章”。
罗列型的来稿有不少数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它们的情况各有不同。有的稿件认为编辑学有若干分支学科,然后对各分支学科、研究对象等略加阐述,似乎还有些内容;有的稿件前边有几百字、上千字的引言和简短叙述,主要内容则集中在后边罗列的图表上,诸如母本学科包括哪些子系学科,各子系学科又包括哪些孙辈学科,等等。从罗列的学科数量上来讲,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因此,这样的图表有时往往也很大,甚至是另找来大开张的白纸誊写而成。
面对这样的来稿,往往令人感到很茫然。这就好比一座要建的大厦尚处于奠基之时,却有方案提出要先从高层盖起……
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李一安先生曾和笔者谈起过他的一段失败的治学经历:
80年代中期,在发表了几篇关于编辑理论探讨的文章之后,李一安萌发了撰写一部有关“编辑美学”方面的著作的想法。为此,他翻阅书籍,收集资料,编写提纲。其后,他们拟写的这部书稿的选题计划也被一家出版社所接受和批准。但是,当他开始进一步深钻细研、进入撰写阶段的时候,他的思维则逐渐地被美学的种种概念和原理所完全占据,他感到实际情况并非如当初所想。他这样对笔者说:“越是深入研究就越是感到,只有美学,哪里有什么单独的编辑的美学。”于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写作计划。
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并不是要否认“编辑美学”的存在,况且一门学问的确认与否也不可能由某个孤立的研究个案来决定。但李一安先生的这个例证至少说明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一门学科的确立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由此我们再反观那些仅仅是在“我认为”之类的话语之后就罗列了十几门甚至几十门的编辑学分支学科的名称的文章,其罗列的根据是什么?其学术价值又在哪里?
应该说,学科门类的划分,各个具体分支学科名称的确定,这样的问题也属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但讨论这样问题的文章必须有科学的分析和论证作为其必要的基础,而不是简单的罗列和没有根据的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并不是一概地否定罗列型编辑学文章,但毫无疑义的是,我们反对这种缺乏认真态度和严谨学风的撰写学术论文的方法。
一门分支学科的名称,写在稿纸上也就四五个字,倘若这个分支学科是以著作的形式出现,那它至少也应当有15~20万字的篇幅,而十几万字的一部学术著作又至少是数倍于此篇幅的著作材料(包括著作者个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关的资料和参考文献等)的结晶。我们所开展的编辑学理论研究,最终是要使那些一门门由四五个字构成名称的分支学科树立于学科之林,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所要花费的功夫和气力大约还不在那十几万字篇幅的著作上,因为至少从逻辑上讲,所有的有关编辑学基础理论和概念系统方面的问题,都应解决在学科学术著作形成之前,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篇幅,肯定会远远超过著作本身。这大约就是学科名称与编撰学科著作之间、与理论研究所必须解决的种种问题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
结论1 “罗列分支学科型编辑学文章”以罗列编辑学的分支学科为其主要特征。这样的罗列,特别是在缺乏理论依据情况下的罗列,犹如空中楼阁,对编辑学理论研究可以说毫无助益。这是由于,任何一门学科,包括分支学科,要想立于学科之林,都必须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概念系统,而单凭构想学科的名称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从文章的形式和撰写意图来看,罗列型文章似乎是要探讨编辑学所包括的研究范围的,这题目不可谓不大。但若要真正攻克编辑学理论研究这座堡垒,现在似乎应当注重一下从微观着眼的问题,论题不妨小些、具体些,而且要扎实严谨,以求实实在在地解决具体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目标。
2.编辑学不是对其他学科理论的诠释
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来研究编辑学,实质上则是以编辑实践活动作为实例,对其他学科的理论加以诠释和验证,这样的文章我们称之为“诠释其他理论型编辑学文章”。
诠释型文章多采用的是“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一类的语言。在《编辑之友》杂志的来稿当中,以“三论”一类理论来研究编辑学的文章占有相当多的数量,其中的情况并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有的仅是在文章中借用了“三论”的一些概念术语或基本原理,在新学科不断涌现、各学科之间不断交叉融合的现时代,这本是正常的现象,而且也应当大力提倡。但其中还有一类稿件的情况比较突出,无论是从论述角度还是从撰写形式方面来看,都是值得商榷的,其所采用的方式大致是这样的:
将所运用的学科理论的内容,按一定的逻辑层次关系或叙述方式(比如:性质、原理、作用、意义之类)划分为若干部分或节、段,在每一部分或节、段之首,先是对所采用的学科理论的叙述或讲解,然后以编辑工作的具体环节或有关内容作为例证,对有关部分或节、段所述学科理论内容加以阐释和说明。
对于这种类型的文章,笔者曾做过两步修改试验。下面,就将这两步修改试验的方法、结果及分析简要地叙述一下。
试验第一步:对诠释型文章施行固定位置的内容删节。即将其每一部分或节、段后边的例证部分统统用红笔涂掉。经过这样的删节,文章会出现一种奇异的变化;从内容上看,它已不再是一篇有关“编辑学”的文章,因为此时它通篇之中再也找不到“编辑”这两个字及相关的语汇;但与此同时,这一经过固定位置删节后所形成的却又依然是一篇结构完整的文章,只不过是篇幅短小了些,而且它需要重新更换一个题目,因为此时它已完全成为一篇介绍和阐释作者原本藉助的那一学科理论的文章。
试验第一步的原则方法有二:(1)在固定位置上删节文字;(2)只删不改。结果有三:1)文章篇幅有所减少;2)文章结构没有改变;3)文章内容面目全非。
试验第二步:再对诠释型文章施行固定位置的内容填充。即选用除编辑实践活动之外的其他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譬如说,工业企业的生产实践活动、公共交通管理的实践活动,或者是学校教育的实践活动等等——的内容,将其按照一定的运作程式分解成若干环节,然后用文字表述出来,再分别填充于试验第一步已删除文字的位置上。经过这番填充,又会使它变成“探讨”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或者其他什么学的文章。
试验第二步的原则方法亦有二:(1)在固定位置上填充文字;(2)只填不改。结果亦有三:1)文章篇幅又有所增大;2)文章结构依然未变;3)文章内容再次面目全非。
上述两步修改试验所显示的现象,尚不得知从写作学的角度应当给予什么样的解释,但从编辑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以客代主、反客为主的结果,即研究的立足点不在于“编辑”方面,而是把叙述“三论”等学科理论作为文章的主体。同时,两步修改试验的原则方法和试验结果向我们表明:诠释型文章可以一文多用,具有万能的特点。
那么,诠释型文章的这种“万能”的特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被称作“三论”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可以用来分析与研究任何的“以人为主要组成单元的系统和以人的社会活动为内容的系统”①,以及“各类系统控制的规律”②*。各个系统的性质、结构、机制及其控制规律,固然都有各自的特殊性,但“三论”已由共性的角度从中抽象出一般,并由此而形成自己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自然也就可以用来解释任何不同的系统及其控制规律。因此,只要研究问题的立足点是在“三论”上,那么,采用任何一种系统的情况作例证都是可以行得通的。
这也就是诠释型文章所具有的万能性的根由所在*。由此,它从反面角度提示我们,如果要研究任何一种系统的特殊性,包括它的基本理论和概念系统,首先需要摆正的就是研究问题的立足点。
以下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包括笔者与有关人士的通信内容,涉及不同的观点。
有一位作者提出了一种叫作“时空质连续统”的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撰写了一篇长达一两万字的论述编辑实践活动的文章,笔者以为这篇文章和上边所讲到的情况基本属于一类,于是作了退稿处理。作者为此写来一封信,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一个简要解释,并依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经过几个阶段:(1)人类之初,认为万物均是神造的;(2)后来演进为对事物孤立的、静止的认识,如石头就是石头,树就是树;(3)认识到事物是发展变化的;(4)认识到事物之间有联系;(5)认识到事物有空间(规模、结构、联系)、有时间(速度、节奏、变化),还有性质的差别,从而深入了一步;(6)到今天则认识到事物是时空质连续统的过程,这是当代人类认识的一个最高层次。但这一认识尚未普及,非常必要用它来分析研究各种具体的事物。这就是演绎法,就像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问题,用全面质量管理来研究出版管理,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相反,用时空质连续统认识编辑过程也是为了解决编辑过程而不是相反。”笔者的复信是这样的:
“作为刊物编辑,我们不反对用各种新的理论去研究编辑学,而事实上我们也刊发过一些这样的文章,但这里应当有一个尺度,就是以谁为主的问题:以编辑学研究为主,引入其他理论,并使其为编辑学研究服务,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能起到建设学科大厦的作用;以各种新的理论为主,以编辑过程中的种种现象来验证某种新的理论,这样的文章似乎应该投到其他刊物上去发表。
“您的文章属于后一种情况。第一,如果将您文章中的有关‘时空质连续统’的论述去掉,您再看看剩下的是些什么;第二,如果采用您这样的研究方法,那么,可以用这一理论写出无数篇分别反映人类社会活动各个侧面的有关的规律、过程的文章,然后再将它们分投相关的刊物。但我以为,理论研究不应当是这个样子。”
以上两封信均写于1992年5月下旬。此后,争论未再继续下去。在这里,谨抄录如上,一任有意于此的方家同仁就这尚未完全展开的不同观点予以评说。
强调编辑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问题,并不是要排斥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鉴。正相反,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在摆正立足点基础上的借鉴。事实上,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就有一些是在立足于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理论而取得的。比如,冯国祥先生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编辑学,并提出了“编辑力”的概念③;刘光裕先生和王华良先生的一些文章借鉴了信息学、传播学的理论和概念④;欧阳维诚先生则利用几何学知识来分析和探讨问题⑤;等等。由此,我们又联想到编辑学理论研究队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各不相同,有的是文史哲,有的是理工医农,这样,从整体上看,就包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众多学科领域,这大约是其他学科理论研究队伍中不多具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这种独具的优势,利用研究者各自所拥有的不同的专业知识结构,参与编辑学的理论研究,不仅使研究工作本身色彩纷呈,更使研究的内容丰富充实,在学科的借鉴和交融之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结论2 “诠释其他理论型编辑学文章”以一种非编辑学的理论作为文章的主体加以陈述,以编辑实践活动的内容对其进行说明,论证的是这一非编辑学理论的正确,而文章本身所具有的编辑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则基本等于零。
任何学科理论,不论其理论价值有多大,影响有多深,适用面有多广,它都不能涵盖或替代编辑学本身的研究;如果能涵盖,或者能替代,那说明编辑学已丧失了存在的价值。编辑学只要能够得以立足于学科之林,哪怕它再微不足道,它也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语言——包括它的基础理论和它的概念系统。
3.编辑学不是远离理论研究题旨的漫议
对编辑学的理论研究采取清谈漫议的形式,这样的文章我们称之为“漫议型编辑学文章”。
漫议型文章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我们大致地归一下类,那么,从其内容的表现方式上分析,它可以分为四类;
(1)围绕编辑实践活动的漫议
具体又有两种情况:1)编辑活动的叙谈。这样的文章一般先从中国古代最初的编辑活动谈起,诸如孔子编“六经”之类,然后再蜻蜓点水一般地叙述一番其他朝代的某些编辑大家的编辑事略。从所采用的史料情况来看,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材料零打碎敲,没有章法;二是材料多是别人的文章已多次采用过或人们所习见的,不像是个人深入挖掘出来的东西。2)编辑过程的复述。这种文章主要是将现代编辑工作当中的各个环节,诸如选题、组稿、审读、加工、发稿、读样等编辑程序照本宣科般的复述一遍。以上这两种情况,不论是采用历史材料,还是运用现代材料,或者是堆砌材料,或者是材料选用不当,大多使文章停留在“议”的层次,而缺乏思想,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结尾也难以得出有价值的理论。
(2)围绕编辑学理论问题的漫议
有的稿件的内容已涉及到编辑学的基本理论或有关的概念问题,但其内容从整体上看,或者只议不论,致使文章深入不下去,缺乏理论的层次;或者篇幅冗长,枝蔓较多,水份较大,致使文章显得散漫;或者缺乏得力的论据,以致难以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一类的文章稿件,有一个比喻,即“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谓“鸡肋”是也。
(3)围绕建立编辑学的重要性的漫议
一门新兴学科在创建之初,谈论建立的重要性是必要的呼吁,编辑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这种谈论重要性的文章出现在80年代的初、中期,它是必不可少的舆论准备,但倘若进入90年代后,仍然去大谈“编辑有学”、应当建立这门学科等类的问题,这样的议题就显得很陈旧,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4)围绕如何研究编辑学的漫议
对于谈论怎样研究编辑学的文章,不可一概而论。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应当在科学研究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就所接触到的这类稿件而言,其中有一部分基本停留在一种泛泛而言的老的套路之中,诸如以什么什么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什么什么具体实践之类,内容显得很空洞,实际上等于没说。
在漫议型文章的四种类型当中,比较而言,前两类大致还属于编辑学理论研究范畴之内的漫议,而后两类则属于研究范畴之外的漫议。假如我们把编辑学理论研究比作一场攻坚战,那么,前两类的漫议型文章就像是击鼓摇旗,但却围而不打;而后两类则好比南辕北辙,根本就跟攻城不搭界。
结论3 “漫议型编辑学文章”以远离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题旨和范畴为其主要特征,它或者以“议”代“论”,或者只“议”不“论”,是文风不正的表现,也是理论研究之大忌。如果让此风蔓延,势必误学,影响编辑学学科大厦的构建。
漫议型文章的形成,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对编辑学理论研究的现状缺乏较为全面的了解,以致造成论题平庸,甚至过时;二是缺乏对材料的了解掌握和深入挖掘,以至于论述空洞,导致漫议;三是写作本身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能正确选择与恰当地运用材料,文章的逻辑关系不明晰,缺乏理论色彩,等等。
各种漫议型文章的出现,反映的是编辑学理论研究领域里的一种低效劳动的现象,由此提示我们,编辑学理论研究存在着一个如何深入下去的问题。
在科学发展史的册页上,铭刻着牛顿的一句名言:“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背上。”⑥为了不断提高编辑学理论研究的质量,我们应当随时了解和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使自己总是处于学术的前沿,这是防止文章流于漫议的一个有效途径。
4.结语:编辑学理论文章的类型应该是什么
尽管世间对于编辑学持不屑者大有人在,但此道中人却未有敢等闲视之者。如果说我国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兴起于80年代初⑦,那么,在这方小小的学术园地里所经历的十数载风风雨雨表明,通往编辑学科峰巅的是布满荆棘的崎岖小路。而今又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编辑学研究深入不下去”⑧的局面。当此之时,编辑学理论研究更应当求精求深,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文归纳总结了罗列型、诠释型、漫议型这样三种偏离编辑学理论研究方向、徘徊于理论研究外围的文章类型,但愿能为攀登这座理论山峰的人们提供一个参考。
从总体上讲,编辑学是一门应用学科,这大约在研究者当中已形成共识。但是,我们所开展的编辑学理论研究,主要的着眼点却是它的基本理论和概念系统,而不是一般性的工作研究,更不是经验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讲,编辑学是理论色彩、思辨色彩都比较浓的一种纯理论性研究。对此,这里需要强调两点:其一,纯理论性的研究可以不直接回答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但这并不等于理论研究本身可以脱离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其二,“纯”理论绝不等于“玄”理论,即纯理论性的研究应当防止玄奥虚幻的倾向。比如说,有人把编辑的历史无限度地向前延长,甚至认为编辑活动比文字的产生还要早;还有人把编辑的思维无限度地左右扩展,认为人的大脑即具有编辑机能;等等。这些观点恐怕都已大大超出了科学设想所允许的范围。
那么,在探讨了编辑学理论研究之非是的同时,什么又是编辑学理论文章应有的类型呢?
概略地说,有三种:(1)阐述型。主要是针对编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论述。(2)论证型。偏重于对于编辑学有关的基本概念的阐释与证明。(3)评述型。包括对有关编辑学的专门性的学术讨论情况的综述;对编辑学界阶段性的理论研究状况(或整体,或局部,或专题)的述评。
相比而言,前两种类型是攻坚者,处在战斗的前沿;第三种类型类似于参谋人员,处在后方的观察所中,但又绝对有别于我们在前边所提到的“只打外围不攻坚”的三种“非是”的类型。而本文,如果做一番自我评价,当可忝列评述型之中。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初稿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日二稿
注释:
①吴岱明:《科学研究方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441页。
②金哲等:《世界新学科总览》,重庆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27页。
*此处须略加说明的是,“三论”的研究对象绝不仅仅限于人工的系统及其控制,只是由于这个问题与本题无涉,因此不做更多的叙述。——笔者注
**只有立足于“三论”一类的理论体系,才能写出这种万能性的文章来。假如利用其他学科理论,比如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数学、物理学等等,是绝对做不出这样的文章来的。——笔者注
③参见《图书编辑力浅论》,载《编辑之友》1985年第4期。
④参见《编辑的社会本质》、《编辑的信息观念与信息功能》、《编辑在传播中的作用》、《编辑与传播场》等文。均见刘光裕、王华良:《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版。
⑤参见《从几何图型看编辑学研究模式》,载《编辑之友》1989年第6期。
⑥转引自申漳:《简明科学技术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173页。
⑦参见胡光清:《编辑学研究10年概观》,载《编辑学刊》1991年第2期。
⑧胡光清:《深化编辑学研究必经之途》,载《出版科学》199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