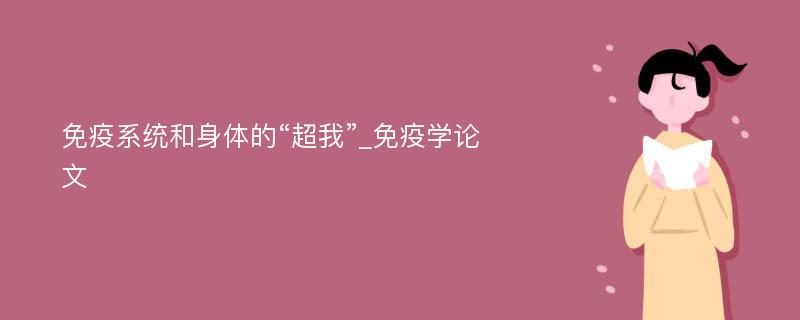
免疫系统和身体的“超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免疫系统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指出:在加强对心的哲学这一领域的研究的同时,不应忽视对身的哲学的研究。免疫系统是人体中可与遗传系统、神经系统“相提并论”的第三个巨大信息系统,它的基本功能是识别身体的自己和非己。本文指出:身的自我(或曰我身)的根本特性是其特异性乃至唯一性,身的自我有:身体的本我、身体的超我和对“身体的超我”的再超越。免疫系统就其本质而言乃是身体的“超我”。
1 在很大程度上被哲学遗忘的角落——身体的哲学
在学习西方哲学史时,大概很少有人不因“认识你自己”这个格言而感到心灵的震动。据说,这是德尔菲神庙墙上的一条铭文。第欧根尼·拉修斯说是泰勒斯首先提出了这个思想。〔1〕可是, 真正使这个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则仍应首推苏格拉底。
何谓“你自己”?何谓“我自己”?何谓“自我”?“我”是什么?这真是一个永恒的“宇宙之谜”。
当代哲学家在分析“自我”一词的含义时认为:“在其最一般的含义上,自我(self)意味着在变化之中保持的唯一性和持续性,由此性质每个人称他自己为我并且导致诸如我自己、你自己、他自己等等的词汇所指的诸自我(selves)之间有了区别。”〔2〕
人类很早就认识到:“我”既有“我的身”,又有“我的心”。在哲学诞生之后,心身关系很快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引起了许多哲学家的关注,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学说。〔3〕
在回顾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对心身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时,我们不难看出: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格外倾心于研究“心的哲学”而不太重视研究“身的哲学”。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到了本世纪则简直可说是“登峰造极”了。目前,在英语文献中关于心的哲学的各种著作和论文多得已经让人目不暇接了;而心的哲学在整个哲学界中的“地位”的变化更要让一些人莫名惊诧。这种情况也许以在英国哲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和典型。最近,冯俊在《当代英国哲学的研究取向及其特点》一文中指出:“综观当今英国哲学……自80年代以来心灵哲学(引者按:philosophy ofmind又被译为心智哲学、心的哲学、精神哲学等,比较起来似还是以译为“心的哲学”较好,因为中文“心智”一词范围过于狭窄,“心灵”一词用在哲学术语中难免会带有某种唯心主义色彩,只有“心”这个单词含义广泛且属于一个“中性”词汇)日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如果把当代英美哲学笼统地称作分析哲学思潮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走过了从逻辑分析,语言分析到心灵分析的路径。从出版的著作和论文、国际论坛和学术讲座来看,心灵哲学确实是英语哲学的热点。”〔4〕我们看到,传统西方哲学中心身(mind-body )问题研究中对身的哲学的研究一直受到严重的轻视,而在当代英语哲学中心身问题更被许多人“归结”为“心的哲学”,于是“身的哲学”日甚一日地成了一个被哲学遗忘的角落。
必须申明:我绝对无意于否定对心的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相反,十余年前我就对此领域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有了某种强烈的感受。特别是对于中国哲学界目前的现状来说,对于心的哲学的研究目前仍是注意不够、“热度”不够的问题,需要大力加强对于心的哲学的研究。可是,对于心的哲学的重视和加强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对于身的哲学的研究,不应以“遗忘”对身的哲学的研究为代价。
在开展对身的哲学的研究时,两个误解是必须消除与避免的。误解之一是认为“身的现象与心的现象相比太简单”;误解之二是认为“身不象心那样有许多哲学问题需要研究”。
消除这两个误解是十分困难的,决非一朝一夕可以收效的。在这里,有两件哲学史上的事实是值得顺便一提的。一是在西方哲学史上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个口号和被公认为开创西方哲学史一个新时代的笛卡尔竟然认为“心灵比形体更容易认识”,〔5〕这是耐人导味的。 二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身这个范畴受到了更大的重视。杜维明指出:“身体这个名词相当于英文的body。今天我们在行文中用‘身体’就好象用英文的body,直指‘躯壳’,了无深意。可是身体,或‘身’,‘体’,在儒家传统中是极丰富而庄严的符号,非body可以代表,当然更不是佛语所谓的‘臭皮囊’。修身和修己是同义语,因此身和己有时可以互用,身等于自身的简称。”〔6〕《论语》中所述曾子之语“吾日三省吾身”,这个“身”字也很难准确地译为外语。在身的哲学的研究中如何兼顾与融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两个不同的传统也是一个大问题和大难题。
身的哲学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本文将仅根据免疫学的研究成果而谈谈本人在这方面的一些初步哲学思考,以求正于大方之家,并希望能有更多的同道关注对于身的哲学的研究。
2 免疫学发展中的峰回路转
当代学者认为:“免疫学是研究自身防御,机体如何识别异物并与之发生反应的一门基础医学,所谓‘免疫’原由拉丁字‘immunis ’而来,其原意为‘免除税收’(exception from charges),也包含着‘免于疫患’之意。这门学科在生长、遗传、衰老、感染、肿瘤以及自身免疫的发生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免疫学最早是研究抗感染问题,为微生物学的分科。然而自60年代后,免疫学有了迅猛的发展,已冲出了抗感染免疫的范畴”。〔7〕
免疫学历史的开端应追溯到我国宋朝接种人痘苗预防天花的实践。1798年詹纳发明用牛痘苗人工接种以预防天花更是一项卓越成就。此后,免疫学的发展停滞了将近一个世纪。到19世纪末,巴斯德用减毒活疫苗预防传染病(如炭疽病、狂犬病)成功,奠定了免疫学的基础。在其后免疫学的发展中出现了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两大学派的长期论争。前者以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俄国动物学家梅契尼科夫为首,认为免疫是体内的吞噬细胞同病原菌斗争的结果;后者以德国科赫研究所的埃尔利希为首,认为机体的免疫主要来自体液因子,如抗体、补体等。这两个学派本来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可是,争论双方却各执一端,争论不休。“这场争论是以体液免疫学派完全压倒细胞免疫学派而告终的。这个结果大大推迟了对免疫功能的细胞基础的认识,对免疫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8〕于是,在理论上, 免疫学的生物学研究变成了对抗原、抗体的化学结构的研究;在应用上,免疫学被局限在抗感染的狭小范围内。
1945年,R.D.欧文提出了免疫识别问题。50年代末、60年代初,淋巴细胞的功能和胸腺的功能得以阐明。F.M.伯内特提出了细胞克隆选择学说,这一学说使得免疫学的根本问题——免疫识别有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于是,免疫学的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向,免疫学的发展再次“峰回路转”了。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免疫学发展中的这一再次峰回路转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揭开了人类认识身体的自我的新的一页。
3 免疫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本性
人体的免疫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括了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体液免疫因子(特异性抗体及淋巴因子等)。
免疫器官根据发生和作用的不同可分为中枢免疫器官和外周免疫器官两大类,都属于造血—淋巴—上皮组织。
中枢免疫器官在体现免疫应答中处于第一位的作用,它们在胚胎的早期发生,是造血干细胞增殖、发育、分化为T细胞和B细胞的场所。胸腺、骨髓和类囊器官均属中枢免疫器官。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世人尚不知胸腺对于人体有何等重要的作用。60年代以来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研究证明胸腺乃是一个对于动物个体生死攸关的器官,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器官。外周免疫器官由二级淋巴组织构成,包括脾脏、淋巴结及淋巴小结等。
免疫细胞是泛指所有参与免疫反应的细胞及其前身,包括造血干细胞、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粒细胞等。许多证据表明血液中的红细胞也是一类免疫细胞。T 淋巴细胞在细胞免疫中起着关键性作用。B淋巴细胞在体液免液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淋巴细胞是机体内最复杂的一个细胞系,每天以10[9]的高速度从一级淋巴器官产生,大多数新生细胞在几天内死亡,也有一些通过循环进入二级淋巴组织。长命细胞将在免疫系统中保持数周、数月,甚至终生。淋巴细胞约占血循环中白细胞总数的20%。〔9〕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各种免疫活性细胞及其产生的许多免疫效应分子能非常准确地识别数以万计的不同抗原异物和病原体,而这些不同抗原异物和病原体又是神经系统及其支配的感觉器官所不能辨认的,所以有人称免疫系统是体内”最精确的特殊感觉器官”。由于免疫细胞具有免疫记忆能力,且在体内四处流动,有人又将其称为“游离飘浮的神经细胞”。〔10〕
免疫系统的功能,直接而集中地表现为对“非己”物质的抵抗力,所谓“非己”物质,既可以是外源性的细菌、病毒,也可以是内源性的肿瘤细胞、异常代谢产物等。无怪乎有的人要把免疫系统比喻为人体中的“国防军”了。这支“国防军”的任务就是既要消灭和驱逐外来的“入侵者”——细菌和病毒,又要消灭体内由于“突变”而新生的“坏份子”——肿瘤细胞。
免疫细胞之所以能发挥如此的功能,其“基础”和根本原因在于它能高度特异地识别自己和非己,更准确地说是高度特异地识别自己的身体成份和非己的身体成份。识别自己和识别非己其实是“一个事情”的两个不可分离的侧面。一支“国防军”在执行任务时,既不能把“自己人”误认为“非己”,也不能把“非己”误认为“自己人”。“我”的免疫系统的本质就是在正确识别“身体的自己”和“身体的非己”的基础上,消灭和驱除非己的身体成份,保持自己的身体成份的稳定性。于是就有了“免疫监控”这种说法。免疫系统起着对自我的身体成分进行“监控”的作用,这就是免疫系统的本质。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人格由本我(id)、 自我(ego)和超我(superrego)三部分组成。本我是人的无意识的本能欲望; 自我是意识结构部分;超我是道德化、理想化的自我,超我的主要职能是以社会道德指导自我,限制本我的盲目冲动。本文无意于评价弗洛伊德这些观点的得失。本文之所以在这里提及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是因为这些观点有助于启发我们去认识免疫系统在身体的自我中的“地位”。
如果说,医学的长期发展已使人们对人的身体结构和成份的复杂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那末,在免疫系统的理论建立之前,对于人的身体还具有高度特异性这一点大概是所有人都缺乏“思想准备”的,那时的人们简直无法想像“我的皮肤”、“你的皮肤”同“他的皮肤”有何等巨大的差异,也无法想像“我的心脏”、“你的心脏”同“他的心脏”是可以被人的免疫系统所“精确”地“识别”出来的。
当代免疫学理论知识告诉我们:“我”的身体——我的皮肤、我的肌肉、我的心脏等等——是具有高度特异性,极而言之是具有唯一性的。如果我们把处于免疫系统监控下的身体成分称为身体的本我(为了叙述的方便,以下有时也将这个意义上的“身体的本我”泛称的“身体的自我”),那么,我们也有理由把免疫系统称为身体的超我了。
乍看起来有点令人出乎意外,细想起来决非偶然的一个事实是: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有着特殊的关系,神经系统具有免疫特免性,即神经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处于免疫监控之下或曰“超越”免疫系统的。从而,我们可以说,神经系统既不属于身体的本我,亦不属于身体的超我。关于这个问题本文第五部分将有进一步的讨论。
4 身体的自我和非我识别中的几个“特殊”问题
在正常情况,机体的免疫系统对身体的自我和非我有正确而敏锐的辨识能力。免疫系统只攻击和排斥异己的抗原,而不对“身体的自我”发动“免疫攻击”。这就是所谓的自身耐受现象,即身体的自我不会受到自身免疫系统的排斥。
正象社会现象中一个国家的国防军可能“叛变”一样,人体的“国防军”——免疫系统也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敌我不分”或者有时简直是“以我为敌”起来,这时的免疫系统向自身中属于“自我”成分的细胞和组织发起了免疫攻击。自身的组织成分由于受自身免疫系统的攻击而产生的疾病就是所谓自身免疫病。结缔组织病中的类风湿关节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神经肌肉疾病中的多发性硬化症和重症肌无力、消化系统疾病中的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等都是自身免疫病。
医学和免疫学的实践与理论的进展告诉我们:识别身体的自我和非我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想像。
如何识别和区分身体的自我和身体的非我,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例如,外来的病毒是非我,人体“自有的”组织是自我。可是,人体中的肿瘤是身体的自我还是非我呢?从肿瘤不是来自外部的“入侵者”而言,似乎应说肿瘤是身体的自我。另一方面,就肿瘤细胞不是“正常细胞”而言又应说肿瘤细胞属于身体的异己成份。实际上,现代免疫学已发现肿瘤细胞表面存在着肿瘤特异性抗原,从而可以被免疫系统识别出来并被免疫系统所“消灭”掉。这也正是虽然人体中经常而不断地有许多肿瘤细胞“自发”或被诱导而产生,但许多人并没有患癌症的原因——癌变细胞刚一出现就被免疫系统识别出它们是异己成份而被消灭了。
可是,肿瘤细胞毕竟是有生命的活细胞,肿瘤细胞有可能通过多种途径逃脱免疫系统的监控而恶性发展起来,甚至最终导致肿瘤这个身体的异己成份(我们也许可以把肿瘤称为“异化的”身体)战胜身体的自我。
肿瘤特异性抗原的发现引起了许多人的极大兴趣。有人希望免疫治疗能成为继外科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化学治疗之外的第四种对付癌症的治疗方法。手术和放疗只在癌变局部化时有效。如癌细胞已全身扩散,则只能用化疗了。可是化疗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亦难免不在某种程度上伤害正常细胞,这就限制了化疗的最终效果。而免疫治疗却具有放疗、化疗所无法企及的特异性。从理论上说免疫治疗有可能只攻击有特异性标记的癌细胞而不攻击没有这些抗原的正常细胞,这就是癌症免疫疗法的特殊诱人之处。可惜这种设想还远未成为现实。目前,世界各国有许多实验室都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器官移植的梦想可追溯至遥远的古代。托名列子而今人多认为成书于晋代的《列子·汤问篇》中记载了一个扁鹊为鲁公扈和赵齐婴二人换心的故事:扁鹊在让二人饮下毒酒后,“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此事自然只能是虚构的故事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器官移植之从幻想变成现实是本世纪的事情。本世纪初,奥地利眼科医生最早成功地进行了角膜移植,50年代成功进行了孪生同胞的肾移植。而在舆论界和社会上引起最大轰动的器官移植事件也许要首推南非医生所首先进行的心脏移植手术。
在这里值得顺便一提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在本世纪初开始研究肿瘤免疫学时,有人将小鼠肿瘤移植到其他小鼠体内时,起初瘤块开始生长,然后在受移植小鼠免疫系统攻击下又缩小和消失。人们曾错误地认为这就是针对肿瘤特异性抗原的免疫反应。随后发现即使移植物是正常组织而不是肿瘤组织,外来的植入物也是要受到被植入动物的免疫系统的排斥的。这就是所谓的移植免疫。
器官移植是医疗实践提出的需要。有些病人的某些器官由于严重病变而无法正常完成其功能,于是就提出了进行器官移植的需要和设想。如果把人体的器官比喻为机器零件的话,那么所谓器官移植就是给人体这部机器进行“换零件”操作(在英文中,手术和操作恰好是一个词——operation)。但人体毕竟不同于机器,因为机器没有“自我”, 所以工人可以很顺利地把同型号机器的同部位零件进行互换(这里不考虑由于制造误差过大和设计公差所产生的特殊问题)。可是,在把张三的心脏移植到李四的身上时,如单纯从物理学、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移植可说是没有什么问题;但从免疫学的角度来看,当张三的心脏植入李四的身体时,李四的免疫系统能够很敏锐地识别出这不是“自己的身体成份”,它是身体的异己成份。由于免疫系统的“天职”就是保护自己的身体,排斥身体中的异己,所以,李四的免疫系统也就理所当然地要攻击和排斥一切被植入的他人器官了。
移植免疫再一次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象心的自我(或曰我的心)有个体特异性一样,身的自我(或曰我的身)也有其个体特异性。
为了使植入的器官能在体内存活,现代医学和免疫学进行了许多研究,采取了许多措施。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采用高效免疫抑制剂。而抑制免疫系统即抑制人体的“超我”的结果虽然可带来使移植器官在体内长期存活的结果,同时也难免不带来降低人体对其他疾病的抵抗力的不良后果。
早在1890年,冯·伯林发现了在用白喉抗毒素治疗病人时,会导致个别病人休克死亡。1902年李克奈特把由于反复注射异种蛋白引起的反应称为过敏反应。
过敏反应曾是一个使人谈虎色变的术语,它至今仍使许多人感到烦恼和头痛。过敏反应也被称为变态反应,超敏反应。对于过敏反应的分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过敏反应分为四种类型。过敏反应的症状可轻可重,轻的仅有皮疹,重则出现哮喘、吐泻、休克,甚至导致死亡。
过敏反应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果说防御反应是免疫系统对抗原物质的正常生理反应,那么,过敏反应就是免疫系统对抗原物质的病理变态反应,是免疫系统功能紊乱的表现。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人体——更准确地说是身体的自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免疫系统是身体的超我。人体不可能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系统,身体的自我中不但有属于自己的成分,也不可避免地有非己的成分,前者我们可以称为身体的本我,后者可以称为身体的非我。身体的超我对身体的本我和非我进行监控。如此看来,所谓身体的自我就是身体的超我、身体的本我、身体的非我所组成的一个三者互相联系又互相作用的复杂系统了。当然从另一种分类和含义上,我们又不应把“非我”包括在身体的自我这一范畴之内,从而这里所述的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实际上,“我身”的含义问题要更加复杂得多,那么,应怎样解释身体的自我呢?
5 三个层次和三个含义的“我身”
人体中有三个极其复杂、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信息系统:遗传系统、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在这里需要强调和加以特别说明的是:尽管许多人可能对于免疫系统的极其复杂性少有所知和少有耳闻,但现代免疫学关于免疫识别、免疫应答等许多问题的精细研究已证明免疫系统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与遗传信息系统,神经信息系统“相提并论”的第三大信息系统。
有人在为免疫系统下“定义”时说,免疫系统是“由具有免疫功能的器官、组织、细胞、免疫效应分子及有关的基因组成”〔11〕的,在这个“定义”中,“有关的基因”已成为免疫系统的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免疫系统同遗传系统的密切联系已可由此窥见一斑。限于篇幅本文以下不拟再涉及免疫系统与遗传系统相互关系方面的问题,以下只就免疫系统与神经系统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免疫系统同神经系统相比,既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又有重要的不同之处。
二者的相似之处是:①在解剖和结构上,两个系统均由中枢和远隔的周围两部分组成,均由细胞和递质两部分组成,递质最后通过效应器官和或细胞发挥作用;②在功能上,二者均能接受刺激,而后呈现兴奋或抑制;二者都有识别能力:免疫系统能识别身体的自己和非己,神经系统能识别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刺激;两个系统都有应答反应:免疫系统有细胞和体液免疫应答,神经系统有神经和内分泌输出的应答;两个系统的细胞都有其表面标志或受体;两个系统都有记忆功能,而且以核糖核酸为记忆的共同物质基础;两个系统内的不同细胞各有分工。〔12〕
二者的不同之处,从最根本之点来说,神经系统——尤其是人脑——是“人心”(mind,即精神活动)的“载体”,而免疫系统虽然是人体之内的一个堪与神经系统“比美”的信息系统,可是,免疫系统中的“信息流”却是不带有“意识性”的信息活动。两个系统都有记忆能力,但比较起来,神经系统的记忆(特别是短时记忆)较短暂,而免疫记忆则较持久。另外,免疫系统除有非特异性免疫应答外,还有高度特异的免疫应答,这取决于抗体分子的Fab 端和免疫活性细胞表面受体的特异性,而神经系统缺乏此高度特异的接合部位。如此等等。
在上个世纪,埃利希用各种染料作静脉注射,发现除脑外全身均染色。1900年列万道斯基根据普鲁士蓝不能由血入脑而提出“血-脑屏障”的概念。血-脑屏障的存在表明人体在大脑和免疫系统之间是存在着某种“隔离”机制的。血脑屏障的重要生理学意义是在发生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系统的全身性激活时不致影响神经系统的功能。如果作一比喻就是:当由于细菌、病毒等“敌人”大量侵入体内,免疫系统全面动员奋起抗敌,因而全身其他部位皆成为“战区”时,血-脑屏障能使大脑成为一个“战火”之外的区域,尽力保证大脑在“全身战争”的情况下仍能正常工作。
本世纪的许多实验工作都提示一个结论:神经系统是免疫特免部位。虽然进一步的研究已证明神经系统的免疫特免性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世界上又有何事物之间的区别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呢?
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之间存在着多种形式、多种途径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些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既表现为整体水平上精神因素对免疫力的影响,免疫反应对精神因素的影响,表现为整体水平上神经系统对免疫功能的调控及后者对前者的反馈影响,又表现为在分子水平上两个系统有“共同”的起传递信息作用的分子。某一系统的细胞不仅产生其本系统的递质,而且产生其它系统的递质;另一方面,某一系统的细胞表面不仅有本系统递质的受体,而且有针对其它系统递质的受体。为了深入研究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的相互关系,研究精神病学、神经病学和免疫学之间的交叉性问题,已“诞生”了一门新学科——神经免疫学。〔13〕1987年还正式成立了国际神经免疫学协会。
可是,承认免疫系统与神经系统之间有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决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混为一谈,决不意味着可以否认二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本文在前几节的分析和阐述中已经指出:由于免疫系统的基本功能是识别身体的自己和非己,我们有理由把在免疫监控下的身体部分称为身体的本我,把免疫系统称为身体的超我。
在本节的阐述中我们又看到:由于血—脑屏障和神经系统免疫特免性的存在又向我们提示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对免疫系统的再次超越。
在同免疫系统的关系上,神经系统体现和标志着对免疫系统这一“身体超我”的再次超越;在功能上,神经系统成为精神(mind)活动的载体。这“两件事”也许实在应该看成“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
显然,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又都是“完整的”身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免疫系统既是身体的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标志着对身体的本我的一次超越;而神经系统也是身体的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同时又标志着对“身体的超我”的再超越。
于是,我们就区分出了身体的自我(或曰“我身”)中的三个层次和三个不同含义:第一层次的身体自我是身体的本我;第二层次的身体自我是身体的超我,即免疫系统;第三层次的身体自我是对身体的超我的再超越,这就是神经系统。
自我是一个含义很多的术语,人们不可能为自我下一个唯一的定义并在唯一的含义上来使用它。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出:所谓身体的自我至少可有以下三个不同的释义,一是以身体的本我或者还应包括“体内”的“非己”成分为“我身”;二是以身体的本我和身体的“超我”的“统一体”为“我身”;三是以第二义的“我身”和神经系统的“统一体”为“我身”。
笛卡尔在研究心身关系时以广延性为身体的基本性质,完全是不得要领,误导了对身的问题的哲学研究(当然,这里不是要“责难”笛卡尔,而只是不得不进行的一个历史事实描述)。身的哲学的核心问题是“身体”的层次性和“我身”的特异性乃至唯一性问题。
身的哲学是一个复杂、重要而饶有趣味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但有独立的意义而且还会有力地促进对心的哲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