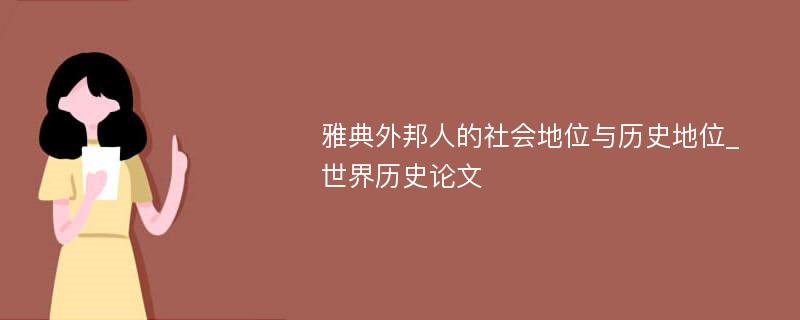
雅典外邦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典论文,社会地位论文,作用论文,外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6-0013-07
古典时代规模庞大的外邦人①的存在,是雅典城邦在古希腊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独特历史现象。作为雅典城邦的一个基本社会阶层,外邦人是来自于雅典以外城邦和国家②,在雅典居住一个月以上而在德莫注册的外来定居居民。他们在雅典城邦拥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在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外邦人扮演着一种局外人的角色,而在经济文化领域却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作为有自由之身却无政治权利的社会群体,外邦人在雅典城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异于公民和奴隶的特殊历史作用。本文在分析雅典外邦人存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基础上,主要就外邦人在城邦军事、经济、文化方面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发挥的历史作用加以探讨。
一、古典时代外邦人的兴盛
公元前6世纪末.以希腊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已经定型,希腊城邦制度,经过长期演变,到此时也已最后形成,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就是在这个根基上成长起来的③。雅典外邦人阶层的兴起即是城邦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外邦人之所以在雅典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社会阶层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与雅典独特的城邦体制和自身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分不开。
第一,雅典城邦的开放性。雅典城邦三面环海,是东西之间通商的天然中介,这就方便了雅典人与外界的联系和交流,从而有助于培养雅典人的开放意识。雅典城邦的开放不仅表现于向广大的外来者敞开城门,还表现在公民权的相对开放性方面。向外邦人开放大门的首先是雅典改革家梭伦。公元前6世纪初,为了发展雅典当时并不发达的手工业,加强工商业者在政治生活中的比重,进而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梭伦曾经将公民权授予那些被本邦永久流放或者举家迁往雅典的从事商业贸易的人④。而其后继者克里斯提尼为了打破旧部落的血缘纽带,获得新的政治支持,亦吸纳了一些外邦移民和奴隶⑤。雅典城邦的这些举措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同时,亦使得一些外邦人获得了雅典的公民权。于是外邦人随着雅典民主制度的日益完善和城邦的兴盛繁荣而逐渐壮大起来。
自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由于公民人数不断攀升,虽然雅典人不再积极主动地授予外邦人以公民权,但是仍旧执行向外来人开放的政策。伯里克利为了促进雅典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进行城市建设以及扩大商业,继续大规模吸纳外邦人。伯里克利曾经说:“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并且从未有任何排外法令阻止任何人学习。”⑥于是,到伯里克利时代外邦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总数一度达到雅典自由居民的一半⑦。但是由于雅典公民权的泛滥,雅典人意识到外邦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对自身生存形成了威胁,因此公元前451- 450年伯里克利颁布了公民权法令,规定只有父母双方均为雅典公民者才拥有公民权,也就是说雅典公民与外邦妇女所生的后代不再被视为雅典公民。这就阻塞了外邦人获得雅典公民权、融入雅典社会的道路。至此,雅典外邦人获得雅典公民权的梦想完全破灭。尽管如此,外邦人仍旧对雅典趋之若鹜。
第二,雅典城邦具备吸纳外邦人的有利条件。希波战争后,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政治霸主。希腊诸城邦都归于雅典帝国治下,这就为航海安全创造了必需的条件,并使得雅典具备了足够强大的力量保护境内的工商业、海外贸易活动。希波战争亦把经济的轴心从东方移向了西方,即从小亚细亚诸城邦移向了巴尔干半岛及西西里,这就为雅典在希腊世界中经济地位的提升带来了契机。战后雅典人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重新修筑了被波斯人毁掉的城墙,完成了战前已经开始的比里尤斯港的建设工程,并建筑长城将雅典与比里尤斯港连接在一起,从此雅典拥有了牢固的海军基地和希腊世界最大的商港,取代米利都和科林斯成为希腊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
西方学者克勒克认为,大多数外邦人之所以选择侨居雅典,不在于外邦人社会地位对他们的吸引,而在于雅典的财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雅典是一个可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大都市和主要港口。传统上讲,外邦人阶层在雅典的最终形成要归因于公元前5世纪初比里尤斯港的修建⑧。一方面由于港口的修建吸引了大批外邦的自由劳工和艺匠;另一方面由于比里尤斯港是交通运输的中转站以及往返东西之间形形色色商品的必经之路,这就为世界各地商人云集雅典提供了其他城邦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比里尤斯港的建成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显著的社会效应就在于促进了雅典人口的急剧增长,以至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由一个半农村的城市一跃而为一个人口云集的世界大都市。在那里,拥有当时爱琴海世界最大最稳定的市场,有良好的港口设施、金融环境以及规范市场秩序的监察官⑨。比如,储藏商品的巨大仓库、造船厂、作坊、银行办事处、公证人办事所和招待客商的旅店宿站⑩。古典作家色诺芬曾论述:从海上贸易和航海事业来看,雅典是最使人向往的,最有利可图的城市。首先,它拥有优越而安全的商港,遇到风暴,可以在那里泊船。其次,大多数别的城市每次都必须带回新的珍宝,因为这些城市的货币出了国境便不通用,但是雅典有许多物品可以载满船,假如商人售出了自己的货而不载回新货的话,他可运载最纯粹的商品,因为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出卖雅典的白银,都可以得到更好的价钱(11)。雅典的繁荣为外邦人从事工商业活动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为他们带来了无限商机。发达的文化与繁荣的经济总是结伴而生的,雅典经济的繁荣、政治上的强大亦使雅典成为当时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雅典文化上的优势、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吸引并造就出一大批来自外邦的学者。对于外邦人来说雅典城邦就是一个“黄金之国”、“理想之都”。因此,外邦人受雅典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优越条件的吸引而群趋至此,并在古典时代发展成颇具规模的社会阶层。但是,外邦人来到雅典城邦之后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地位又如何呢?
二、外邦人的社会地位
雅典的外邦人在社会地位上介于雅典公民与奴隶之间。作为一类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外邦人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发展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在雅典城邦制度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外邦人的社会地位受到城邦特征的严格制约。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论述:“一般来说,城邦就是为了生活的目的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体。”(12)雅典城邦是一个渐次实现了民主的公民集体,这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它决定了雅典城邦的一切事务必然围绕着公民的利益而展开,公民集体的利益就是城邦精神的所在。城邦本质上是全权公民联合起来压迫奴隶和外邦人以及调整内部关系保证集体福利的机器(13)。在此体制下,一切非公民皆是城邦奴役的对象,皆被严格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尽管雅典人与外邦人并未划分彼此的居住界线,但是在雅典人的思想意识中外邦人仍然是外人。因此,即使某些外邦人获得了雅典公民权,他们也不可能拥有全权公民权,只是拥有有限的民事权利而已。外邦人不能担任公职,甚至无权参加公民大会,也就不能参加选举与投票。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外邦人系无缘于荣誉者,而公民则为享受荣誉者(14)。此处,“荣誉”指的是政治权利以及财产所有权,诸如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公职以及拥有土地和房屋等权利。在古希腊,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是两个互为因果的条件。由于雅典外邦人没有公民权,故而无权占有土地,也因此无权自己建造房屋,除非是那些对城邦贡献巨大者方有可能获得建造房屋的特许权。雅典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城邦(15),农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的居民分成了五类,第一类就是占城邦绝大多数人口的生产粮食的农民(16)。在雅典人的思想意识里,工商业是贱民所从事的职业,只有农业耕作才是公民可以从事的体面的、稳妥的职业(17)。因此,雅典外邦人无缘农业耕作和城邦政治事务的参与。
但是,雅典外邦人的人身是自由的,受到雅典法律的保护,这是雅典奴隶和一般的外来人所不具备的基本权利。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乞援女》对此有相关的描述。埃斯库罗斯借逃婚到阿哥斯的女性外邦人之口写道:“我们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外邦人,自由并且受到保护,没有男人的暴力。任何居民或者外来人都不能囚禁我们。如果有人对我们使用暴力,任何不救助的庇护者(18)将被剥夺政治权利并被公众流放。”(19)这说明在理论上城邦应为外邦人之基本人身自由提供保障。虽然这种保障是有限度的、相对的,但亦表明外邦人是拥有城邦有效身份的自由人。在不侵犯雅典公民利益的前提下,外邦人可以谋求自身的自由发展。
事实上,在雅典的工商业与文化领域,外邦人拥有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在雅典工商业的许多部门外邦人都占据主导地位。例如,雅典早期的陶制品工业和陶器的出口贸易基本上为外邦人所垄断;在金属制造业方面外邦人也占据主要位置;外邦人还控制着雅典的金融业,银行业巨头多为外邦人,著名的外邦人银行家为公元前5世纪的帕西昂和佛尔米昂,据说帕西昂拥有资产60塔兰特;在雅典,手工业作坊的主人往往都是外邦人,其最大的工场主是公元前4世纪来自叙拉古的外邦人凯法鲁斯及其子。据说凯法鲁斯因为富有而受伯里克利之邀定居在比里尤斯港,并且开办了一家由120个奴隶所组成的军械制造工场;除此而外,在雅典的工业建筑领域外邦人的数量也颇为可观。例如,参加雅典卫城埃莱克泰乌姆神庙竣工的一份公共名单上86位已经知道身份的工人中,公民有24位,奴隶有20位,而外邦人竟达42位之多(20)。外邦人在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一开始就相当重要,以后一代一代的加强,到了希腊史的晚期,在外邦人和被释奴当中就有不少富豪、作家、演说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职业中的佼佼者(21)。在雅典城邦体制下,外邦人拥有一定的思想、言论、创作的自由,因此,在古希腊辉煌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涌现了许多外邦人出身的学者、名家。例如,来自爱琴海西北部希腊殖民城市卡尔西狄克地区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创立的吕西昂学园是一个外邦人聚集的主要公共场所;小亚细亚哈里卡纳尔苏斯城的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世纪8位著名演说家之一的吕西亚斯、伊萨埃乌斯和阿提卡最后一位伟大的演说家戴纳库斯;智者学派的普罗塔高拉、高吉亚斯和阿那克萨高拉;被誉为欧洲“医学之父”的科斯的希波克拉底等。由此可见,外邦人虽然在雅典的政治领域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但在工商业及文化方面却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并占据相对较为重要的位置。外邦人独特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历史作用的独特性。
三、外邦人的历史作用
外邦人在雅典城邦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邦人是雅典公民有力的辅助军。外邦人作为雅典社会的一个基本社会阶层必须履行军事义务,必须与公民共同保卫城邦的安全。这项义务在外邦人注册成为外邦人的同时即已附加在他们身上。一般来说招募外邦人主要是用来保卫城邦,比如城邦被围困时的紧急调援。古希腊演说家德摩斯提尼曾记载,当不幸的消息传来时,雅典人就动员外邦人参加保卫城邦的军事行动(22)。但当公民兵人数不足或来不及调遣的时候,外邦人也代替公民参加军事远征,公元前 4世纪为数众多的外邦人曾被雇佣做国外远征军(23)。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外邦人只有在城邦的非常时期才被征召,不能参加和平时期的军事组织。大多数外邦人担任预备队或者卫兵,除非是在城邦危急时刻才被派往前线。
雅典城邦的公民集体性质决定了外邦人在雅典军队中不可能扮演与雅典公民同等重要的军事角色。外邦人没有公民权,只能参加没有资格限制的步兵或水军,而不能参加骑兵,因为骑兵是一种荣誉和身份的象征,只有那些出身高贵、家庭殷实的公民才能参加。公元前5世纪成年男性外邦人估计约有2.4万人,其中足够富有的8000人可以参加重装步兵,其余的则作水勇或轻装步兵(24)。在雅典水师中,外邦人是基本的组成部分,危急时刻外邦人与公民比肩作战,成为雅典水军的主力。通常情况下,公民为雅典水师的领航者和统帅,外邦人充当水勇,而奴隶则充当桨手。如果“提米斯托克利法令(25)”可信的话,那么从希波战争起外邦人即已成为雅典人武装战船的重要兵力来源。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西西里远征时外邦人曾扮演雅典水师主力军的角色。
最早关于外邦人参加陆战的记载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因希腊世界两大盟主之邦作战规模之巨,历时之长导致了城邦对兵源需求的急剧增长。修昔底德说在狄里乌姆战役中 3000名雅典的外邦人曾经代替同数量的公民兵侵略马加里德,因为当时3000名公民重装步兵远在波提狄亚无法返回。修昔底德又记载在公元前428年,由于雅典舰队正在远征莱斯波斯途中无法返回,外邦人才参加了征服伯罗奔尼撒的军事行动(26)。在伯里克利演说中描述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的军事力量时,修昔底德给出的公民与外邦人重装步兵总数为2.9万人。其中公民兵野战军为1.3万人,其余的1.6万人包括未成年和年老体衰的公民重装步兵以及登记为重装步兵的外邦人负责驻守城堡和守卫雅典长城(27)。杜肯·琼斯认为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装步兵中公民与外邦人之比约为3:2(28)。外邦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军事辅助作用,补充了雅典的兵源。而外邦人在陆军中的大量使用,表明雅典公民兵制出现了危机。
外来人一旦决定在雅典长期居住,就已经将雅典视作与自己命运息息相关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就有责任保护城邦的安全。在排除生计的威胁方面外邦人与公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外邦人参军是履行作为雅典城邦人口的职责,虽然不排除有赚取薪饷的动机,但是比之那些纯粹为了利益受雇的职业化的外邦雇佣军,外邦人对城邦有更多的责任感。外邦人在雅典城邦的非常时期维护了城邦的安宁与稳定,一则他们有义务维护城邦的安全,另一则他们还有可能因为立下军功而获得被授予公民权的机会,因此,外邦人是公民兵的忠实后盾,发挥了重要的军事辅助作用。古典作家色诺芬曾经强调外邦人是雅典舰队的必需力量,还关注到外邦人对雅典的另一重要作用,即雅典多样性的工业亦需要外邦人的存在(29)。
第二,外邦人是雅典工商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虽然古典时代的雅典也有一些公民从事工商业活动,但是主体是外邦人。外邦人所从事的职业大多是雅典人不屑为之或者自己无力经营的需要大批技术人才以及带有风险性的工作。外邦人可以是工场主、贸易商、批发商、零售商、包工头,亦可以从事扫除垃圾、贩运木材、加工原木、制作衣服、泥瓦匠、理发、搓澡、染织、镀金等工作(30)。在雅典,富有的公民通常提供贷款给外邦人,或者将自己的奴隶租给外邦人收取租金,而他们自己并不亲自经营,事实上从事商贸活动的多是那些外邦人或外来人。
在采矿业,外邦人由于没有土地,原则上不能拥有矿山的开采权。但是,由于工作的危险和艰苦,雅典城邦亦允许外邦人与政府签订承包合同进行开采。例如,色雷斯人索西亚斯从雅典公民尼奇亚斯手中雇佣了1000多名奴隶开发劳里乌姆银矿并从中牟利。由于古典时代雅典粮食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口,而粮食海外贸易是一种带有风险性的行业,雅典人一般很少从事这方面的经营,在雅典以及雅典最为繁荣的港口比里尤斯港,从事大宗粮食海外贸易的大多是外邦人以及外来人。这些外邦的粮食贸易商从意大利、西西里、埃及和黑海进口粮食,载往比里尤斯港,再从那里转口希腊各地。外邦粮商的贸易活动确保了雅典的粮食供应,满足了城邦人口基本的生活所需。这是外邦人在维持雅典人的生计方面最大的贡献。
银行业在公元前4世纪初一直由那些拥有特殊才能以及经验丰富的外邦人所控制,古希腊早期的银行业世家都是外邦人出身。银行家帕西昂继承了雅典最古老的由安提斯泰奈斯和阿尔凯斯特拉图斯所建的银行,并不断扩展其规模。从公元前394年以来他与许多市场都有贸易往来,尤其是拜占庭和黑海。外邦银行家在管理金融以及银行贷款方面首屈一指,这是雅典人所不能及的。银行贷款要依赖稳定的政府,而雅典政府也一定需要筹措资金。这些外邦银行家们在资金上支持了城邦,城邦便授予他们公民权,在这一过程中城邦与外邦人彼此受益,互为消长。例如,银行家帕西昂曾经向城邦捐献了1000面青铜盾,还无偿借钱给将军提摩修斯。帕西昂与佛尔米昂由于对城邦的巨大贡献而完成了由奴隶到外邦人再到公民的飞跃。银行业的创立是外邦人对古典时代雅典的最大贡献,因为雅典的银行方便了工商业领域的钱币兑换,并成为必不可少的贸易媒介,这就促进了公元前5世纪以来雅典商业的迅速发展,雅典也因此成为古希腊主要的货币市场(31)。
总之,大多数外邦人从事着雅典公民所不愿或不善于从事的工作,他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雅典公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迎合了城邦的发展需求,扮演着相对次要却必不可少的社会角色。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论及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的社会成分时说:“毫无疑问,城邦必须包括大量的奴隶、外邦人以及外来人。”(32)雅典外邦人促进了自梭伦时代以来雅典工商业的发展。雅典经济的繁荣和在城邦史中后期所呈现的发达的工商业特征与外邦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第三,外邦人是雅典城邦的财政来源之一。关于外邦人在雅典财政中的作用,古典作家早有论述。色诺芬认为外邦人是雅典政府最为可观的收入来源之一,如果雅典政府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好外邦人,那么雅典的收入会大大增加(33)。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面对雅典城邦的衰落,马其顿的威胁,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亦曾指出如果雅典继续大力吸引从事商业活动的外邦人以及外乡人,那么雅典就会得到现在两倍的收入(34)。古典作家这些描述表明雅典外邦人在城邦财政中占据不容忽视的地位。
古典时代雅典城邦的固定收入除了法庭诉讼费外,内部收入主要来自于港口和市场的税收、外邦人头税以及矿山租赁金;外部收入在公元前5世纪,主要来自同盟贡赋,但是自公元前405年同盟贡赋被取消后,城邦就更多的依靠盘剥外邦人与奴隶(35)。
那么雅典城邦以何种方式剥削外邦人呢?首先,外邦人必须缴纳人头税,通常情况下每个男性每月缴纳1德拉克马,不与丈夫或儿子居住的女性每月缴纳半个德拉克马(36)。其次,雅典人规定进出比里尤斯港的货物要征收2%的关税。由于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大多是外邦人以及短期居住的外来人,而雅典公民只是把资金或者运货船租借给他们以获取利润,自己并不亲自进行贸易活动,因此这项税收的制定主要还是针对外邦人以及外来人。再次,外邦人要想在市场上买卖还必须交纳市场税,尽管未有外邦人交纳市场税的确定数额记载,但这也是雅典城邦必征的税收之一。除了以上这些固定征收的税项而外,在战争等危急情况下外邦人还要与公民一起交纳不定期的战争税,据说外邦人整体要交纳1/6的战争税。此种税收是依据外邦人的经济能力征收的,富者多征,贫者少征,有时还视战争情况临时加重征收税额。此外,外邦人还要与富有的1200个公民一起负担特殊的“社会义务” (liturgy)。这项义务包括为歌队、火炬接力赛以及圣餐仪式提供基金。
雅典城邦将这些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支付公职人员的津贴、战争经费(包括支付军饷、督造战船和武器)以及城市建设的费用方面。因此,公元前5世纪,在城邦繁荣时期,外邦人从财力上一定程度地支持了城邦的民主建设。A.兹门认为,如果没有外邦人在劳动力和资金上的支持,雅典就难以建立起曾经辉煌一时的海上霸权(37)。尤其是在公元前4世纪城邦危机时代,外邦人除了积极履行必需的义务外,一些富有的外邦人还自愿慷慨捐助。阿提卡铭文记载的60个由于对城邦的特殊贡献而被授予占有土地与房屋特权的外邦人中,过半以上来自于公元前4世纪,这表明公元前4世纪外邦人在城邦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比如,来自伊里昂的外邦人尼坎德罗斯以及以弗所的外邦人波里泽罗斯从347/6年直到323/2年,每年都自愿定期交纳建造码头以及武器督造厂的特别税收;在拉米亚战争中还在财政上支持雅典水师;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另一场战争中,又捐给雅典百姓1000德拉克马;公元前 306/5年,还负责出资修缮了雅典长城的一部分。城邦有战事时,他们还自备武装在雅典陆军和水师中服役(38)。由此可见,外邦人不论是在城邦繁荣时期还是在城邦危机时代都在财政上一定程度地支持了雅典城邦。
第四,外邦人促进了古希腊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关于外邦人在古希腊文化中的作用问题,古典作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亦没有明确区分哪些是雅典人,哪些是雅典的外邦人。但是,现代一些研究外邦人的西方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英国古典史家D.怀特海德认为雅典的许多非公民雕刻家、画家、陶工、医生、科学家、智者、哲学家、演说家以及其他学者,都对雅典做出了巨大的创造性贡献,虽然在古代雅典人不愿将他们称之为外邦人,但是只要他们在雅典居住时间足够长,理论上就应该是外邦人,而不是一般的外来者(39)。这些外邦学者大多在雅典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伯里克利时代修建的大量公共建筑,包括雅典娜大庙、忒修斯大庙以及豪华富丽的、装饰有巨大柱廊的雅典卫城正门皆融合了多里亚和爱奥尼亚的风格,是现在世界各国建筑艺术的典范。而主持这些建筑的建筑师、雕刻家、画家大多是来自希腊世界各地的外邦人。另外,在雅典的雕刻家中,还有塞浦路斯人、派罗斯人以及西多尼亚人等非希腊人。希腊第一流的外邦人雕刻家,帕特农神庙艺术雕刻的监制人和制作者斐狄亚斯以及杰出的建筑学家——著名的帕特农神庙和伊利特昂神庙的设计者卡利克拉特和伊克丁等,都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艺术做出过重大贡献。
外邦人促进了古希腊各个城邦间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使古希腊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古希腊文化中所含有的诸多东方、埃及与西亚因素,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人的经商以及征服行为,但是不能否认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外邦人以及外来人亦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传播作用。有些古希腊著名学者和文人,为求知识游历到东方,然后又回到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雅典,他们把在外地学习到的知识带到雅典并将其发扬光大,这就使古代东西文化直接融合,从而创造了璀璨的古希腊文明。譬如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他边游历,边行医,曾到过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埃及等地,后来到达雅典,取得了巨大的医学成就;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雅典发表他的著作《历史》之前曾经游历了腓尼基、巴比伦、波斯、埃及等地。他把古代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介绍给了希腊人,从他所写的历史巨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方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这些都离不开他对那些城市的实地考察。
雅典在希波战争后成为“全希腊的学校”,文化上高度繁荣。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40)来自于雅典以外世界的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在雅典主要集中居住在比里尤斯港周围以及考埃莱与麦利特的长城之间;另外,有些居住在考里图斯、区达泰奈乌姆、斯卡姆邦尼德与郊区某些地方以及阿提卡的边远地区,比如埃莱乌西斯、萨拉米和劳里乌姆银矿等矿山地区;只有很少一部分居住在北部和东部的以农业为主的德莫(41)。外邦人分散居住于雅典各个德莫和地区的居住方式有利于与雅典人全面接触和交流。色诺芬曾经说,由于雅典人控制了海洋,因此雅典人与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混杂在一起并且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美食,以及西西里、意大利、埃及、吕底亚、黑海、塞浦路斯等其他地区的土特产。他们听到和了解世界各地的方言,并且从所有的希腊人和非希腊人那里融合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衣着打扮(42)。不难看出外邦人对雅典人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促进了雅典人饮食文化与服饰文化向多样化发展。由于与外邦人接触,雅典人的语言、服饰和社会生活必不可免地会融入许多新的因素,从而产生新的式样。例如,在语言方面,雅典本地的方言和外邦人的方言混在一起,就产生了许多不纯粹的雅典话;在装束方面,从前那些高贵的雅典人所穿的伊奥尼亚式的麻制的长贴身衣被多里亚式的办事人所穿的短贴身衣所代替;雅典人的头发也剪短了,从前用“金蟋蟀”束着的高傲的卷发再也看不见了(43)。说各种语言的外邦人与雅典人杂居一处,在价值观、世界观、宗教信仰、知识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各方面彼此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促进了古希腊人的种族融合,并造就了古代雅典辉煌灿烂的文化。
综上所述,外邦人以其独特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在古代雅典城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他们促进了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雅典城邦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为雅典城邦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贡献。外邦人的存在迎合了城邦的发展需求,为构建稳定、和谐、发展的社会共同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外邦人在城邦史中后期经济重要性的明显增强,他们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这就制约了其历史作用的发挥,并最终加重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城邦危机。由此可见,弱势群体社会认同感的形成对于社会的长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外邦人”(Me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Metoikoi”,词源学含义为“同住之人”或“改变家园之人”,国内学界大多将之称为“外邦人”。自19世纪以来国外学界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雅典外邦人的论著,例如:U.Wilamowitz-Moellendorff,'Demotika der attischen Metoeken',Hermes,1887(22); M.Clerc,Les mé tèques athéniens,Paris,1893; D.Whitehead,The Ideology of the Athenian Metic,Cambridge,1977。就雅典外邦人的研究现状而言,西方学界对外邦人社会地位的探讨较多,而对于外邦人历史作用的研究相对薄弱;国内学界虽然在论及雅典城邦社会形态时谈到外邦人的一些情况,但目前尚未见比较系统的研究。
②雅典的外邦人最初主要是亚洲与欧洲的希腊人,后来才有弗里吉亚人、色雷斯人、帕弗拉哥尼亚人、加拉提亚人、吕底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甚至阿拉伯人等。
③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
④Plutarch,Solon,24.4.
⑤Aristotle,Politics,1275b34-38.
⑥Thucydides,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2.39.
⑦R.P.Duncan-Jones,'Metic numbers in Periclean Athens',Chiron 10,1980,P102。据估计公元前431年雅典成年男性公民为5万人,外邦人为2.5万人,奴隶为10万人;公元前317年成年男性公民为 2.1万人,外邦人为1万人,奴隶为5万人(Joint 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Teacher's,The World of Athens,Cambridge,1985,P157);芬利则认为雅典男性外邦人和男性公民数量之比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可能在1/6到1/1.25之间(M.I.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1985,P48)。
⑧A.Diller,Race Mixture among the Greeks before Alexander,Greenwood Press,1971,P18、116.
⑨为了确保进口的粮食三分之二能够进入雅典城,雅典人抽签选举出10位专门负责粮食供应的官员,他们主要负责监察比里尤斯港与雅典城的粮食交易价格与斤两。雅典人还选出10位贸易专员管理商业贸易,后来这一官职又增加到20人 (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51)。
⑩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266页。
(11)Xenophon,Ways and Means,III.1-3.
(12)(14)(16)Aristotle,Politics,1275、1278a、1291ab.
(13)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15)关于古代雅典经济性质的探讨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导言第3页。他阐述:“希腊文明不是一个商业文明,而是一个以农业为其主要社会与经济基础的古代文明”。
(17)公民对工商业的偏见,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邦危机的加深,受利益的驱使以及为了谋生而逐渐削弱,到了公元前4世纪很多雅典公民开始从事工商业活动,富有公民投资工商业并不亲自经营,贫穷者像外邦人一样在市场上或在比里尤斯港进行买卖活动。
(18)外邦人取得合法身份必须到雅典人的德莫注册,而注册前必须首先选择一个雅典公民作为庇护人,如若不选则被视为对公民权的亵渎,将被卖为奴。庇护人负有保护开代替外邦人进行法庭诉讼的义务。
(19)Aeschylus,Suppliant Maidens,P607-614.
(20)M.I.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Penguin Books,1992,P79-80.
(21)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第265页。
(22)Demosthenes,Private Orations,4.36.
(23)A.H.M.Jones,Athenian Democracy,The Jone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164.
(24)A.Zimmern,The Greek Commonwealth: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177.
(25)在伯罗奔尼撒的特洛真(Troizen)发现了一则公元前3世纪的法令铭文。该铭文描述了希波战争前提米斯托克利动员所有的雅典人、外邦人抵抗波斯入侵的事件。记载是这样的:“将军应该在告示板上逐船登记其他人的数量,雅典人依据德莫的记录,外来人与军事执政官登记在一起(笔者认为这里的“外来人”即为外邦人,因为梭伦时代用“外来人”即“Xenos”来指代所有来自外乡的人,包括已注册的外邦人和未注册的外来人,外邦人并不称作“Metics”;阿里斯托芬时代两个词才分别用于指代不同的人群,外邦人称作“Metics”,而未注册的外来人称作“Xenos”)。他们应当把他们列到名单上,然后分配到以每组一百人划分的二百个组中去,记下每组战船的名字以及指挥官和船长的名字,这样每一组就知道该登上哪一艘三层桨战船了。”(M.Dillon & L.Garland,Ancient Greece,Rouledge,London,1994,7.31.)
(26)Thucydides,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2.31.1-2;3.16.1.
(27)Thucydides,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2.13.6-7.
(28)R.P.Duncan-Jones,'Metic numbers in Periclean Athens' Chiron 10,1980,P102.
(29)Ps.Xenphon,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as,I.12.
(30)G.Glotz,Ancient Greece at Work:an Economic History of Greece,London,1926,P180.
(31)M.Grant,The Classical Greeks,Michael Grant Publications Ltd,1989,P283.
(32)Aristotle,Politics,1326a.
(33)Xenophon,Ways and Means,II.1; II.7.
(34)Isocrates,On the Peace,6.21.
(35)Joint 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Teacher' s,The World of Athe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227.
(36)Isocrates,8.21.
(37)A.Zimmern,The Greek Commonwealth: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178.
(38)J.Pecirka,'A Note on Aristotle' s Conception of Citizenship and 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fourth century Athens',Eirene 6,1967,P25.
(39)D.Whitehead,The Ideology of the Athenian Metic,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1977,P18.
(40)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41)A.Diller,Race Mixture among the Greeks before Alexander,Greenwood Press,1971,P120.
(42)Ps.Xenophon,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II.7-8.
(43)《罗念生全集》第4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2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