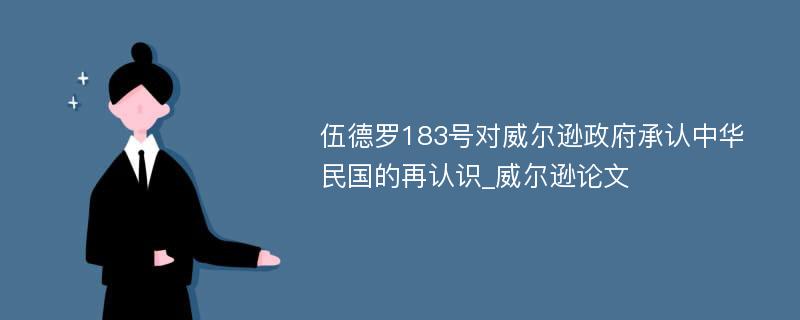
伍德罗#183;威尔逊政府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民国论文,威尔论文,伍德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4)06-0142-07
关于威尔逊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策的动机,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中国史学界基本上把威尔逊的行为视为一种政治权术或外交智谋,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在华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这种说法当然并非毫无道理,威尔逊政府的对外政策当然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但是,塔夫脱政府的政策也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那么,既然目的是一致的,为什么采取的政策截然不同?笔者认为,仅仅用“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来解释威尔逊的承认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很显然,面对同样的问题,塔夫脱和威尔逊对如何回应中国的形势和如何维护美国利益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并因此导致截然不同的政策。其根本原因在于威尔逊和塔夫脱是透过不同的认知透镜来观察中国局势的,并对什么是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美国在华外交目标的优先秩序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有着不同的理解。总体而言,塔夫脱作为一个倡导“金元外交”的现实主义者更加注重美国在华经济与战略利益,而威尔逊作为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典型理想主义者则更加关注美国在中国的道德影响与意识形态利益,把扩大对中国的精神与文化影响置于经济与战略利益之上。本文试图应用美国外交决策理论中的意识形态透镜模式和跷跷板模式对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动机重新进行研究。
一、威尔逊的信仰体系及其对美中关系的认知
所谓意识形态透镜模式(Ideological Lens Model)是指一个人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知体系、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提供了个人认知外部世界的机制。意识形态好比一个透镜,个人通过这一透镜来观察外部世界,外部世界的信息通过透镜的过滤和折射进入个人的意义框架得以被个人所认知。换言之,人们通过意识形态提供的模板和意义框架来感知、认识、理解和判断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只有在意识形态框架内才有意义。如美国学者詹姆斯·伯恩斯所言:“意识形态价值观为我们提供了借以观察政治的透镜。……一种意识形态可能是对现实的精确或不精确的描述,但它却是我们思考人、权力和社会的一种方式。”[1](P243)就美国外交政策领域而言,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人看待国际事务的方式、界定了什么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而这些反过来又指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估价和不同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一模式,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取决于意识形态。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布拉福德·帕金斯(Bradford Perkins)曾言:“无论哪一个国家,决策者都不仅受到他们得到信息的影响,还要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价值观被用来理解信息。”[2](P9-10)
关于威尔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尽管支持和反对他的人对威尔逊的个性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但都承认威尔逊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的理想主义者。威尔逊出生在一个虔诚的长老会家庭,对基督教具有使徒般的信仰,笃信基督教徒应该用基督教的原则来改造社会。著名史学家、威尔逊的传记作者阿瑟·林克(Arthur Link)称威尔逊在基督教信仰方面像一个孩童,从不怀疑《圣经》的内容,总是从阅读《圣经》、教堂礼拜和祷告中获取精神的力量。在神学方面,威尔逊是一个典型的加尔文主义者,相信上帝具有绝对的权威,主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律法也应该主宰国家之间的关系,《圣经》是生活的准则。他还是一个预定论者,坚信上帝主宰历史的进程,而人和国家被上帝用来展示其目的与计划的工具[3](P12)。威尔逊特别强调基督的精神就是爱与服务,他在1889年写道:“基督教的真正精神不是出于以拯救为目的的爱,而是出于以爱为目的的服务”,“爱是行为的唯一动机”[4](P273)。在他的一次演讲中短短的几段话中竟出现六七次“服务”(service)这个词汇。威尔逊从基督教传统和他的长老会神学中继承的宗教与道德信仰和价值观构成威尔逊政治思想的基础,深刻塑造了他对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看法。威尔逊对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看法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他认为国家同个人一样也应该坚持崇高的伦理和道德标准,“在外交行为中,眼前的目标和物质的利益应服从于更高尚的伦理标准以及道德和精神目标的提高”[3](P13)。这不是说他无视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作用和扩展美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事实上,威尔逊在任内也曾为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市场和投资而奔走,但是在他看来,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能主宰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外交必须关心更高远的道德目标,即扩展美国的文化影响,为世界树立自由和正义的典范,而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利益。威尔逊说道:“美国的力量是道德原则的力量……只有道德的力量是它所热爱的……和为之战斗的”[5](P84)。其二,坚信民主制度是最人道的、最符合基督教道德的政治制度,是立宪政体最进步的形式。威尔逊在从政前作为一个学者曾对政治体制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对英美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传统大为赞赏。这使其把在国外促进民主视为美国的责任,相信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将带来世界和平。其三,认为美国由于它在政治、社会和道德与精神方面的成就和美德,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承担特殊的使命,这种使命不是聚集财富和权力,而是通过服务于人类完成上帝交给的任务,向世界输出民主以及建立一个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新秩序。美国学者哈利·诺特(Harley Notter)这样概括威尔逊的使命思想:在威尔逊的眼里,美国的使命就是“实现自由的理想,提供民主的样板,支持道德原则,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树立政府行为和政治理想的典范以及树立正义,巩固人权,为人道和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幸福而奋斗.领导世界的思想以及促进和平,——简言之,为人类和进步服务。”[6](P653)这一概括虽然有溢美的成分,但确实道出了威尔逊对发挥美国道义影响的重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威尔逊被誉为“世俗的福音传教士”。
正是从其个人意识形态信仰出发,威尔逊相信美国在中国的最大利益是保持美国对中国独一无二的道义影响,并以此为中国提供一个民主的样板,实现输出民主的国家理想,为此可以牺牲在当时微不足道的经济与战略利益。
威尔逊在当选总统之前就通过教育与传教的纽带与中国有一定的联系。其父亲是著名的长老会的牧师,是海外传教事业,包括在华传教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威尔逊每年都极力鼓动学校录取赴美的庚款留学生,同时也非常关注普林斯顿大学在北京的项目和活动。这些纽带使威尔逊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并特别关注美国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认为中国是一个东方新觉醒的巨人[8](P15)。威尔逊在1912年11月27日的一封信中称他正在研究中国的形势,对中国的命运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兴趣”[6](P202)。威尔逊在1912年大选中获胜后,孙中山曾写信表示祝贺。威尔逊在回信中说:“我一直以极大所兴趣关注中国最近事态的发展,对每一个有望为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人民带来自由的运动表示最强烈的同情”。[9](P576)威尔逊曾对他的密友豪斯上校表示他“对中国人民具有深切的同情,希望做一切可能的事情帮助中国人民”[10](P62)。
威尔逊挑选驻华使节过程集中反映出威尔逊的对华政策思想,即对美国文化影响的重视远远超过对经济与战略利益的关注。在新政府遴选派驻海外的外交官时,威尔逊对职业外交官极不信任,而更倾向于从教育界和学术界选拔外交人才。他在给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W.Eliot)的信中说:美国目前占据公使馆和大使馆职务的人“头脑中考虑最多的是美国个人物质利益而不是道德和公众利益,这一点我们有责任去控制”。在1913年1月16日给布赖安的信中,威尔逊称驻华使节应“具有显著的基督的品格”,并称中国“在我的思想中非常重要”,美国应该给予中国“某些特殊的服务”,而只有具有基督品格的人才能最好地服务于中国[10](P58)。
威尔逊最初曾瞩目埃利奥特,认为埃利典特这样的人是帮助中国的合适人选。他在给埃利奥特的信中说,“我相信可能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在东方发生的一切更能接近触动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而这些事情就我们影响所及应该在最好的可能的指导下发生”[10](P65)。
埃利奥特拒绝接受任命后,威尔逊转向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的总干事约翰·穆德(John W.Mott)。他在给国务卿布赖恩(William J.Bryan)的信中说:“在我的心中最令人瞩目事情是,在建立新政府和中国新政权过程中最活跃的人中有很多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很多人也曾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基督教的影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在中国政治的第一线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不用说,这种影响应该继续保持。”而穆德在他看来“为中国的改革作了很多贡献”,“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受到最有影响的那些人物的信赖”[10](P124),因而是合适的人选。威尔逊称穆德的任命“非常密切地关系到中国和基督教世界的利益”[10](P190)。
但穆德同样拒绝接受任命,这使威尔逊感到非常失望,称穆德的决定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表示他“从未这样失望过”[10](P263)。威尔逊后来在谈论驻华公使的人选时说:“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大部分是以传教活动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的公使应该是一位传播福音的基督徒。”[8](P38)最后威尔逊任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芮恩施(Paul S.Reinsch)出任驻华公使,这不仅是因为芮恩施是研究世界政治特别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著名学者,而且还因为芮恩施的宗教立场和进步主义观点。芮恩施离美赴任前,威尔逊对他说,“美国应该独立地完成她应尽的义务,给予中国以特殊的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援助”。芮恩施回忆说:“我从总统那里得到了他将对我在中国的建设性工作给予积极支持的保证,在谈话中,他着重谈到了教育、政治榜样和道义支持三方面的问题,而在财政和商务方面则不怎么热心。”[11](P63)
芮恩施的回忆印证了威尔逊在对华关系上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威尔逊从其个人信仰出发,把用美国政治榜样和道德力量来影响世界,在全世界促进民主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国家目标。威尔逊对外交与国际问题的这一看法深刻地影响了威尔逊政府的对华政策。
二、威尔逊承认政策的动机:意识形态战胜现实政治
决策理论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既追求安全与经济利益等现实的目标,同时也追求价值观和理想等意识形态目标,美国外交决策过程是两大目标之间相互竞争对外交政策影响力的过程。如果二者是重合和一致的,那么有利于物质性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也会有利于其意识形态利益,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大体上可以说二者共同决定了一项对外政策,如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既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也符合其捍卫自由的意识形态利益。但是两大目标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经常表现出国际性利益与其国内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美国外交中存在“以国家利益和权力为一方,以政治道德和原则为一方的拔河”[12](P246)。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外交决策过程是意识形态目标与利益目标之间博弈的过程,一项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由安全与经济等物质性国家利益驱动还是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驱动取决于二者相容的程度和相对强度的大小,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外交决策者需要在意识形态利益、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找平衡。意识形态与安全和经济利益好比跷跷板的两端,决策者试图寻找二者的平衡,哪一端份量较重,哪一端就会在影响政策的形成与制定方面占据上风。这就是解释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的跷跷板模式(See-saw Model)。
威尔逊之所以改变塔夫脱政府与大国一致的政策,率先承认中华民国,并非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而是出于扩大美国对中国的道义影响。如果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审视威尔逊的政策,大体可以说,在战略、经济与意识形态三大国家利益范畴中,威尔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所追求的主要是意识形态利益。若用当代美国外交政策语言来说,在安全、繁荣和民主三大目标中,威尔逊认为在国外促进民主最为重要。威尔逊实际上“把增进美国文化影响的愿望置于塔夫脱提出的经济计划之上”[13](P2)。
从跷跷板模式来看,承认政策所牵涉的战略与经济利益的强度相对较低,而关乎美国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利益的强度较高。所谓的意识形态利益是指扩大美国的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以及支持中国的共和运动。反映这种意识形态利益强度的是传教士的游说活动和美国国内支持中国共和运动的压倒性舆论以及威尔逊对美国在华道义影响的重视。相较而言,商人阶层在承认问题上意见不一,缺乏对美国舆论的影响力。
20世纪前20年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的所谓“黄金时代”。在这20年中,尤其以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的第二年即1906年到美国加入一战的前一年即1916年间来华传教士增长最快。1912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共2038人,教堂1016座[4](P440)。通过对在华事业捐款,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不同程度地关注在华传教事业。据美国学者詹姆斯·里德(James Reed)统计,当时美国人口大约有1亿人,其中经常到教堂礼拜的成人教徒大约有4200万人,除去其中1600万天主教徒外,大约有2500万新教徒。而在这2500万新教徒中约500万是黑人,另有500万属于小教派,且多为穷人,对海外传教事业不感兴趣。在余下的1500万白人成年教徒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也就是500万人经常为传教事业捐款。如果加上主日学校孩子们的捐助,这个数字要达到1000万人。这样,通过捐款和与教会的联系,在美国1亿人口中,大约有1500万美国出生的白人成年新教徒关注在华传教事业,如果考虑到当时美国平均每个家庭的子女超过两人的话,那么关注中国传教事业的公众群体(China-missions public)的人数大约有3000万以上。这些人大多来自中西部基督教气氛极为浓厚,仍然过着质朴的村镇生活的城镇、农场和乡村[15](P19-23)。
此外,传教士还建立了有效和庞大的通讯网络。传教士是各种场合中国传教事业的宣传家。传教士出版了大量著作,很多传教士的著作成为美国国内的畅销书。传教士还为传教杂志、教会报纸和全国性的报刊撰写了成千上万的文章。而且所有传教士都定期与美国的差会、家乡的教会、家人、亲戚、朋友通信,介绍和讨论中国传教的情况,这些信件经常在教堂礼拜时向教徒宣读。除此之外,传教士还是优秀的演说家。传教士在回国休假时经常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播放从中国带回的幻灯片。卫三畏(S.W.Williams)在1945-1846年间回国休假时,作了一百多次演讲[13](P43)。柏锡福(James Bashford)在1912年回国度假的一周里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镇演讲6次。据保守的估计,在1912年前后,每年大约有300位传教士回国度假,即使每个人每周只演讲两次,那么每年以中国为主题的传教士演讲大约就有30000次[15](P24-25)。
在传教士的号召下,数以百万计的美国草根阶层的普通民众把他们节省下来的从一美分到一美元的硬币拿出来捐助在华传教事业,通过这些纽带,他们的感情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传教运动的巨大影响使众多的本来对外国和国际事务不甚关心的美国民众在1913年前后非常关注中国的命运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对承认中华民国如此充满感情。他们把中国的“觉醒”和进步归功于传教事业的贡献,看作是他们所关注的基督教的道德和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延伸。
辛亥革命爆发后,传教团体中压倒性的舆论是对辛亥革命的欢迎和赞扬,传教团体把中国的革命视为传教运动影响的结果,是中国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获得进步的证明。1913年1月,美以美会北京教区会督柏锡福曾给威尔逊写了一封长信,希望威尔逊就职后”第一个官方行动就是承认中华民国”。“如果给予承认,无论是在财政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对中国的帮助”[10](P27-28)。威尔逊称柏锡福的这封信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0](P58)。1913年3月,美国基督教教会联邦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政府尽早承认中华民国,威尔逊表示这一决议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义[10](P231)。
在传教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国内舆论也表现出同样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收到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几乎所有的信函都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反对美国政府为了华尔街财团的利益而拖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当时著名的中国通、长期在中国生活的英国人蒲兰德(John O.P.Bland)正在美国旅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美国听到一些极重要的人物表示支持立即承认,不要拖延,但是这些人提出这一建议更多是从感情而不是从理智出发的”。而这种感情的产生应由“传教士阶层负主要责任”。1913年元旦,蒲兰德还拜会了当时美国总统塔夫脱,他强烈感受到传教士对塔夫脱对华政策的压力。塔夫脱曾对他说,他很难制止传教士领导对中国的多情(sentimentalism),他们巴不得立即承认中华民国[15](P148)。
与在华巨大的宗教与文化利益相比,承认政策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当时由于中国的动乱和贫穷,美国在华经济利益一直较少,无论是对华贸易还是在华投资在美国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总额中都占有极低的比重。无论一些商人如何试图游说美国政府把中国的市场前景作为美国制定东亚政策的依据,但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市场一直是美国海外市场最缺乏吸引力的一部分。用保罗·瓦格(Paul Varg)的话说,由于中国交通不便,内乱频仍和中国民众的普遍贫困,中国市场始终是一个“迷思”(myth)[16]。1913年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出口只有7900万美元,约占美国对外出口总额的5%,其中对华出口只有2100万美元[15](P42)。当时美国在华投资总额是5900万美元,其中有1000万是传教差会的财产,4200万是商业投资,另700万是债券和国债[8](P41)。商业投资主要来自于极少数大的跨国公司,如美孚、英美烟草公司、国际金融公司、通用电器公司等。华尔街的四家银行,即摩根公司、昆洛公司、第一国民银行和花旗银行之所以在1909年6月组成美国银行团,加入承揽湖广铁路贷款的争夺并组成后来的六国银行团并非纯粹出于商业动机,而是应国务院要求来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爱国行为而并非纯粹的商业行为。因此当1913年威尔逊政府宣布不再支持美国银行团加入六国银行团时,银行家们并没有表现出过分失望。美国商人对中国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与传教士阶层相反,关注利益的商人对中国没有传教士的那种感情。商人最初对中国革命采取反对的态度。武昌起义之初,代表商人利益的《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抱怨武昌起义导致的全国混乱形势“破坏了铁路特许权,危害了货币改革,干扰了贸易,威胁着在华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15](P121)。除因为革命不利于商业活动开展外,商人阶层对中国革命缺乏同情还在于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反帝目标心存疑虑,对中国民族主义缺乏理解。当时代表商人利益的美国亚洲协会(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反对美国退出银行团,反对美国放弃与大国的合作,单独承认中华民国。但是,与传教士相比,商人缺乏传教团体那种庞大、有效的通讯网络来影响美国的民众。同时美国正处在进步主义运动的高潮,进步主义运动的主题之一就是反对托拉斯的垄断行为,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则是反对金元外交。商人观点难以影响普通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当时一些舆论曾指责塔夫脱政府之所以拖延承认中国的共和政府,是为了维护加入六国银行团的华尔街银行家的利益。
一般说来,商入主要是从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和情感出发来看待中国革命的,一旦发现共和政府的建立并不妨碍他们做生意,就不会反对美国的承认。况且承认政策本身基本上与美国的商业利益无关,如果尽早承认民国政府可以加强袁世凯政府的地位从而有助于稳定的话,一些商人甚至可能愿意支持威尔逊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而就战略利益而言,威尔逊单独承认民国政府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塔夫脱政府在武昌起义之初提出的大国协商一致的原则,势必损害美国与日、英、俄等国的关系,特别不利于通过协商与合作机制来约束日本,因此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但是,拖延承认的危害可能更大,正如1913年3月18日美国驻华临时代办卫理(E.T.Williams)在给国务院的长篇报告所说的那样,“继续恪守与列强的合作政策,在所有列强达成一致之前拒不承认中华民国,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而且是在纵容其它国家的侵略企图”[17]。
对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威尔逊在对华关系中重视的是宗教与文化影响和对中国共和事业的支持,而非经济利益,同时他并不认为美国的单独行动会严重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
威尔逊上任伊始就于3月18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不再支持美国财团留在当时正与袁世凯政府谈判善后借款的六国银行团,因为“贷款的条件几乎触犯了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甚至会导致美国政府“强制干涉那个伟大东方国家的金融甚至政治事务,而现在中国已经觉醒,深知自己的权力和对人民的义务”[18](P170-171)。在此情况下美国继续留在银行团只会损害美国在中国的道义地位。
在此前内阁讨论银行团问题的会议上,据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日记记载,内阁的这次讨论几乎没有考虑贷款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和战略意义。国务卿布赖恩和其他内阁成员考虑的主要是贷款的垄断性、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和对美国行动独立性的约束。布赖恩明确反对美国参与六国银行团对华贷款,因为六国贷款的安排赋予少数几个美国银行家垄断性的特权,赋予国际银行家对中国财政事务的控制权,而这种控制权可能会导致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同时六国贷款安排也会剥夺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的独立性。内政部长富兰克林·莱恩(Flanklin K.Lane)对中国事务曾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认为在中国新的形势下美国赞同这种旧式的偏袒某些银行家的做法将是一个错误,美国不应该参与建立在这种条件下的对华贷款。丹尼尔斯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找到与承认中华民国结合在一起的某种方式帮助中国”。而威尔逊总统坚信美国政府不能要求美国的银行托拉斯来参与这项贷款,美国“应以更好的方式帮助中国”[10](P174-175)。
在承认问题上,俄国曾以墨西哥问题向美国施加压力,即如果美国率先承认民国政府,俄国可能也率先承认当时美国尚未承认的墨西哥胡尔塔政权,但这也未能说动威尔逊。在4月1日讨论承认问题的内阁会议上,威尔逊决定准备承认中华民国,而不管其它列强是否采取同样的立场。当时司法部长麦克雷诺兹(McReynolds)认为在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上最好能邀请其它列强与美国合作,威尔逊不同意这一主张,称他不愿意把承认行动搞成一个各国在一起的协商或者让美国受其它国家行动的约束。威尔逊说他希望其他国家能明白,美国将在中国国会召开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日子里承认中华民国,美国当然也会建议其它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是美国不会让自己的行动受制于其它国家[10](P249)。这说明威尔逊并不担心美国独立行动会产生损害美国与其他大国战略关系的后果。
4月17日,北京政府发布官方公告呼吁全国各省的基督教团体在4月22日这天为全国祈祷日,为新选出的国会和民国的总统,为新政府和新宪法,为争取各国对民国的承认而祈祷。《华盛顿邮报》对此专门作了报道,称这是“革命以来这个国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显著标志”。在4月18日的内阁会议上,国务卿布赖恩特别宣读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并认为中国政府的公告是“这一代最引入瞩目的官方文件”[10](P328)。威尔逊总统说,他在当天早上从报纸上读到这条消息的时候非常兴奋和激动,他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威尔逊称“尽管我没有权利发布一个通告,要求全美的所有教会在那一天也加入到中国的教会中一起为已经感受到基督徒祈祷必要性的共和国的成功而祈祷”,但他在想是否要求全国这样做。同时威尔逊再一次提到尽快承认民国政府的问题。他说,人们会问:既然我们祈祷中国成为一个和平和进步的共和国,为什么这个国家不通过立即承认中国而回应我们自己的祈祷者呢[10](P330)?
5月2日,美国驻华临时代办卫理向袁世凯政府递交承认国书,“欢迎一个新的中国加入世界大家庭”,并表示希望“中国人民通过完善共和政府,能够实现最高程度的发展和幸福”[18](P110)。
美国承认中华民国后,烟台人民为表示对美国的感谢曾送给威尔逊丝绸制品作为礼物。威尔逊在感谢信中说:“我的脑海中经常想到这个正在为作为一个自觉和自治的民族站立起来而奋斗的伟大国家。我非常骄傲他们在完成他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时把美国视为朋友和典范。”他请美国驻烟台(芝罘)领事朱利安·阿诺德(Julean Herbert Arnold)不仅要转达他对烟台人民的感谢,还包括他“对他们的幸福和繁荣的最良好的祝愿”,威尔逊还表示“最真诚地希望,不仅在承认和最先祝福中华民国这一次,而是在将来能有许多次,美国这个国家能有机会表达其对中国和所有那些为中国的永久利益而工作的人的真挚的友谊”[10](P465-466)。
简言之,在威尔逊看来,美国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利益比经济与战略利益要重要得多。美国要保持对中国独一无二的道义影响,为中国的发展树立榜样,通过美国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的力量来影响和改造中国,这是美国在中国的伟大使命和国家理想,美国不能为了少数银行家的利益而牺牲更重要的促进美国价值观与理想的利益。这是威尔逊单独承认中华民国的最深层的原因。费正清曾评论说:“传教士在美国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无论是对中东还是对中国,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威尔逊总统任期内都达到顶点。这个时代的政治人物经常受传教士宣称的道德责任和行善动机所驱使,而不是受国家利益观念和谋取商业利润的希望所驱使。”[15](forwordp9)
正因为如此,威尔逊政府的外交被一些学者称为“传教士外交”(missionary diplomacy)[7]。这一外交与罗斯福的“现实主义”政策、塔夫脱的“金元外交”形成鲜明对比,打上威尔逊鲜明的个人色彩,即强调美国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对输出美国价值观的重视远甚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威尔逊对中华民国的承认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影响战胜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或者说是理想政治(Idealpolitik)战胜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一个典型个案。
收稿日期:2004-0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