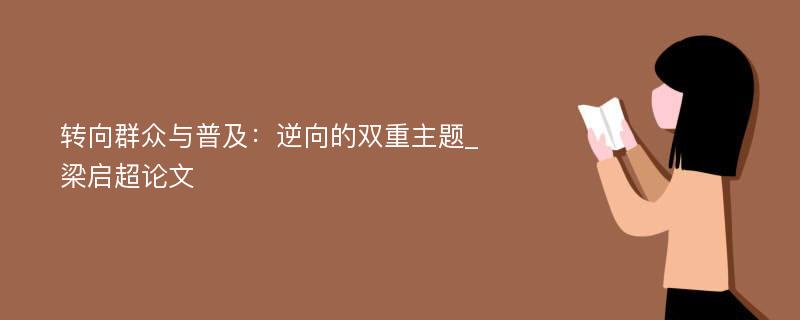
化大众与大众化:逆向的孪生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知识者的一个重要人生追求是做“帝王师”,直到上一个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为知识者圆了一百零三天的“帝王师”梦。但是,西太后的宫廷政变,却将康梁的美梦变成了一场充满血腥气的恶梦。不过,这场恶梦却促成了知识者的一个划时代的转变:由追求做“帝王师”到追求做“大众师”的转变。自此以降,中国知识者便开始了各式各样的“化大众”(即启蒙大众)的努力,同时,为了他们的“化大众”话语被大众接受,他们又不得不对他们的话语甚至他们自身实施“大众化”的改造。萌生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百年中国文学,从一开始便踏上了由“化大众”和“大众化”这对孪生主题共同导引的轨道……
一、化大众与大众化主题的浮出
鸦片战争的炮火在物质的层面上击碎了封建统治者的“天朝大国”梦,但并未使统治阶层从阿Q式的“精神第一”的幻想中醒来。直到在甲午战争中被一个一向为自己所看不起的日本击败,统治阶层及其知识者才开始从精神层面上寻找原因。严复首先得出结论:“民力已隳,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所以,当务之急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最关键者是“开民智”〔1〕。这可以说是近代意义上的“化大众”命题的正式提出。但是,此时,知识者们大多正追随着康有为、梁启超做“帝王师”之梦,所以,“开民智”的问题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维新运动被慈禧太后扼杀在血泊中之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才决心“从长计议”,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开民智”的宣传中,自此,“开民智”这一“化大众”的命题才逐渐引起知识者的广泛关注。
但是,“开民智”的利器何在?梁启超的回答是:文艺。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宣称以“开发民智为主义”,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将小说对大众的影响之力做了充分的强调,欧洲仁人志士的小说一出版,“于是彼中缀学之子……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梁氏还援引康有为的话,点出小说在开发民智方面的特殊功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2〕”在戊戌维新前的一八九七年,严复、夏曾佑曾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言:“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3〕,但是,象梁氏这样将小说的功能抬到无所不能的水平,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小说的“开民智”(梁氏后来正式将其定格为“新民”)功能,梁启超一九零二年十一月又在横滨创办了《新小说》月刊。在创刊号上,梁氏发表了其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该文开篇第一段就直接点明了其利用小说以新民的主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接着,梁氏具体论述了小说的诸种社会作用,并阐释了小说的四种力:熏、浸、刺、提。文末则进一步断言:“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在这里,梁氏将小说牢牢地拴在了“新民”的战车上。此后,其他一些小说评论家沿着梁氏的思路做了许多新的阐发,进一步强调了小说的工具功能,如陶*曾在其《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中亦做了梁启超式的断言:“欲革新支那一切腐败之现象,盍开小说界之幕乎?欲扩张政治,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5〕
在维新受挫、救国无路、救民无着的境遇中,粱启超等忧国忧民的知识者突然在绝望的大海中发现了小说这一小舟,于是,他们便把这一小舟视为了救民于苦海的“挪亚方舟”,将希望置于“方舟”之中,这是有着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的。
随着梁启超们的振臂一呼,许多科举路断、抱国无门的知识者一起将目光转向小说这一“希望之舟”,他们放下士大夫的架子,竞相著译小说,小说遂呈一时之盛。吴沃尧在《月月小说序》中曾对此进行了如卞的描述:“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所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6〕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孕育和萌发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从一开始就势所必然地肩负起了以“新民”为核心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历史使命……
维新派的诗文理论中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的成份较之于小说,要稍为少一些,并且也较少极端、偏面之论,在此不再赘论。
维新派在倡导文学内容上“化大众”即发挥“开民智”、“新民”的社会功用的同时,为了使其“新民”的内容顺利“化”入大众之中从而达到“化大众”的目的,他们同时甚至更早进行了切实的在文学形式上“大众化”的努力。
其实,在“化大众”的“新民”理论尚未形成之时,“大众化”的问题就被明确地提出来了。早在一八六一年,黄遵宪就借其诗作《杂感》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牢?即今流欲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7〕诗中的“我手写吾口”,实际上就是“言文合一”,这是倡导“白话”的先声;而诗中的“流俗语”问题的提出,则更是一种诗歌语言“大众化”的变向倡议。一八八七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中对其主张进行了更具体而明确的阐发:“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周、秦以下,文体屡变……。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此文中,不但“语言与文字合”被正式提出,而且作者将其视为实现“通行于俗”、“令天下之农、工、商、贾……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简易之法”,这就不但为文学昭示了“农、工、商、贾……皆能通文字之用”的“大众化”取向,而且为这种取向明确了“语言与文字合”的走向“白话”的途径。
黄遵宪之后,《无锡白话报》的主编裘廷粱又推出了堪称提倡白话文的纲领性文章《论白话为维新之本》。 裘氏其文发表于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当时戊戌变法正处于高潮中,所以裘氏从“维新之本”的角度立论。该文首先明确宣布了“言文分离”的弊端:“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继而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矣?”在批判了文言的诸多弊害之后,袭氏列举了白话的八大益处:
一曰省日力:读文言日尽一卷者,白话可十之,少亦五之三之,博极群书,夫人而能。二曰除骄气:文人陋习,尊己轻人,流毒天下,夺其所恃,人人气沮,必将进实求学。三曰负枉读:善读书者,略糟粕而取菁英;不善读书者,昧菁英而矜糟粕。买椟还珠,虽多奚益?改用白话,决无此病。四曰保圣教:《学》、《庸》、《论》、《孟》,皆二千年来古书,语简理丰,非卓识高才,未易领悟。译以白话,间附今义,发明精奥,庶人人知圣教之大略。五曰便幼学: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日魁儒耆宿,殆将过之。六曰练心力:华人读书,偏重记性。今用白话,不恃熟读,而恃精思,脑力愈浚愈灵,奇异之才,将必迭出,为天下用。七曰少弃才:圆头方趾,才性不齐;优于艺者或短于文,违性施教,决无成就。今改用白话,庶几各精一艺,游惰可免。八曰便贫民:农书商书工艺书,用白话辑译,乡僻童子,各就其业,受读一二年,终身受用不尽。〔8〕
从裘氏列举的白话的八大益处中,可以见出其倡言白话的动机集中于“启民智”,因为,八大益处中的每一点都与“民智”有关,甚至第四点“保圣教”,也是维新派心目中的“启民智”的一个方面(“庶人人知圣教之大略”)。虽然如此,但从语言形式的“大众化”取向而言,能早于五四白话文运动二十年提出系统的白话主张,裘氏其文不啻为一篇极具“语言革命”意义的“白话宣言”。
在语言实践中,梁启超首创的散文“新文体”的出现,可以说是显示了文学形式“大众化”的实绩。梁启超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任《时务报》主笔时,“新文体”已具雏形,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言《时务报》,“文章的格式是介乎于仅为少数学者所懂的古文和劳动者所能明了理解的俗语之间,是如此的雅洁,因而得到每个学者的赞美,可是又如此的明畅,使得每个地方的读者都能够了解。”〔9〕可以说是对初期“新文体”的概括。这里的“介乎于”古文和“劳动者所能明了理解的俗语”之间,已显示出了其对“劳动者”、“俗语”的贴近。戊戌之后,梁氏流亡日本,在各式报章上力倡“文界革命”,而其“新文体”亦更显通俗晓畅。梁氏在其《小说丛话》中曾言:“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是也。”〔10〕而其“新文体”的首倡及实践,则可称为走向“俗语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收获。当时,“新文体”曾风行诸多报章杂志,文坛风气为之一变。这其中不能不说有着梁氏相当大的功劳。
上文谈到小说时,曾言及维新派将小说的社会功用夸大到无所不能的水平,而维新派倡言“小说界革命”的目的在于发掘和利用小说这种无所不能的力量,以达到“化大众”即“新民”的目的。其实,“小说界革命”本身,还有着其文学形式上的“大众化”的意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诗、文为正宗,《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列于九流十家之末,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虽然《汉书》中的“小说”与近代小说有异,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至少在正统文士心目中尚未发生大的变化,仍然是文学之“末”,仍然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仍然为正统的士大夫文人所不齿。而梁启超们却一反陈规,大呼“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将小说这种“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的文学体载抬到了诗、文之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体裁“大众化”之举—一将不入流的属于下层民众的文学体裁抬到正宗的文学体裁而属的殿堂,可谓增加了文学殿堂中“大众化”的成份。尤其是梁启超们将小说的功用夸大到神乎其神并且身体力行参与创作,更将白话、俗语运用其中,从而使小说为更多的人接受、阅读,这就将本来就相当“大众化”的小说推向了更广泛的大众。
在用较多的篇幅谈了维新派的文学理论及实践之后,我们不妨也谈一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学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执著地将力量投入现实的革命实践,因此,在文学上的参与反而逊于维新派。在文学主张上,革命派基本沿袭了维新派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传统,只是他们往往更进一步,将维新派注重助思想上的“新民”宣传推进到政治上的“革命”鼓动,将“化大众”推进到了不但“化大众”而且“救大众”。如柳亚子在《复报发刊辞》中曾言要用文学“鼓动一世风潮”,“打破这五浊世界,救出我这庄严祖国来”。而陈去病在其《大汉报发刊词》中则要用文学“张吾民族之气而助民国之成……获共和之幸福”。王钟麒在其《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则云:“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11〕
为了使政治上的“革命”鼓动行之有效,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文学要面向“贩夫走卒”、“屠夫牧子”。这显示出了他们在文学“大众化”方向上的努力。〔12〕另外,革命派还着力提高戏曲等通俗文艺的地位。维新派曾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供入了文学的圣殿,但更低一等的通俗戏曲尚未引起他们的注目,于是,更加激进的革命派便肩起了提高通俗戏曲地位的使命,他们不但理论上提倡,〔13〕而且投入创作实践。如秋瑾的《精卫石》就是用绍兴地方曲艺“弹词”的形式写成的。据此,可以说,在文学形式“大众化”的方向上,革命派较维新派走得更远。
辛亥革命之后,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国建立,维新派被甩到了历史的后台,有的转向(如梁启超成了民国要人),有的退隐,而革命派则大多以革命功臣的身份厕身政界,或投入新的斗争。被鼓吹为具有洗心革面、改天换地之力量的文学,也被认为完成了她的工具功能,由大紫大红坠入了“门前冷落”的窘境。但是,文学本身好象也不太“争气”,她忍受不了“门前冷落”的寂寞,开始浓妆艳抹,走街串巷去招揽“顾客”,由高高在上的“化大众”转向了低姿态的迎合市民阶层大众之趣味的“大众化”作为其具体表现,就是以写“言情小说”著称的鸳鸯蝴蝶派的崛起。
其实,中国本来可算得上“言情小说”大国,(《红楼梦》就是一部言情巨著),但近代以来的生死存亡的严肃历史课题使有着忧国优民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暇顾及这种小说品种,即使有人偶尔创作一两部言情小说,不待别人指责,作者个人便已羞羞答答。如吴沃尧在其自称为“写情小说”的《恨海》(1906年)中就曾做过做贼心虚式的辩解:
我素常立过一个讨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大抵婴儿一啼一笑都是情,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开”那个“情”字。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写情,真是笔端罪过。我今叙这一段故事,虽未便先叙明是那一种情,却是断不犯这写魔的罪过。〔14〕
但是,通读《恨海》全篇之后,我们却不能不说,棣华对伯和之情,已陷入了“魔”的境界。
从吴沃尧的辩白的背后,我们也可以见出当时“言情小说”声誉之不良了。不过,即使需附上辩解也仍然写,这也从反向说明了言情小说的植根于“大众”的生命力。
辛亥以后,小说既然无需再负起救国救民的使命,写言情小说也就无需羞羞答答了,鸳蝴小说遂得以兴盛。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盛,在某种意义上也得力于它们内容上的“大众化”因素,以前人们批判鸳蝴小说时常言其“投合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如果换一种说法,则可说: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追求,与当时的城市大众阶层的审美趣味相契合,遂被这一部分“大众”所认同和接受。只是由于鸳蝴小说内容上的“大众化”只化到了“市民”而末至“农民”,且显示出了“迎合”“媚悦”之态,遂为坚持文学之“审美品格”和主张文学彻底“大众化”的双方所共同厌恶。
不应忽视的是,鸳蝴派小说家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在文学形式上也做了一些“大众化”的努力,他们的有些小说已基本上采用了比较地道的大众口头语——白话,我们不妨摘引周瘦鹃发表于一九一四年的《真假爱情》中的一段以作印证:
这位豪气不可一世的郑亮,也犯了这一个“情”字。原来他和一个女学校里的女学生唤做陈秀英的有了爱情,并且已订了婚约,两下里十分缠绵。现在既要去从军,须得和意中人说一声。当下他便写了一封信去,约在城外一个幽静的花园里相见。〔15〕
虽然“白话”而不彻底,但若思及必较彻底“白话”化的小说四年后方出现,我们就不能不赞佩周瘦鹃所做的努力了。
另外,鸳蝴派作家包天笑与钱病鹤一九一七年一月在上海创办《小说画报》,在《例言》中即正式声明:“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16〕不但要求“全用白话”,而且宣称“小说以白话为正宗”,这已是一种必较彻底的“大众化”方向了。《小说画报》月刊至当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十二期,所载全为白话小说;而《新青年》上的白话小说次年五月才出现。简直可以说在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取向上,鸳蝴派的有些小说家甚至比五四新文学作家先行了一步。——当然《小说画报》中的白话小说之“白话”仍非纯现代意义上的白话。
二、化大众与大众化主题的深化与泛化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执著于以文学“化大众”的宣传与实践,强调的是文学的教化功能;辛亥革命后兴起的鸳鸯蝴蝶派,则热衷于将文学“降格以求”“大众化”到市民社会,强调的是文学的娱乐功能。一九一七年,五四新文学兴起后,中国文学又有了全新的追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本质上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由其促生、并成为其重要一翼的新文学,必然地承荷起思想上“化大众”的使命。一九一六年八月,李大钊就曾指称:“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17〕恰如李氏所言,正是陈独秀等“哲人”“发挥其思想”的《新青年》“惊破”了“当时有众之沉梦”,“新文艺之勃兴”才指日可待,李氏心目中的“新文明”也将紧随作为“先声”的“新文艺”而进入国人的精神界域。在这里,李氏言“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已昭示出:即将萌发的五四新文学,已被先驱者们设定为“新文明”的催生剂,亦即,已被预置上了思想上“化大众”的使命。
但是, 在五四新文学的倡导和具体实践中,新文学家“化大众”时所“化”对象的内涵、“化”的方式及“化大众”时所采用的策略,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化大众”全然不同。首先,就所“化”对象而言,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维新派、革命派注重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而五四时期所侧重的是个体意义上的“人”;前者注重的是“民”之“智”的改变,而后者侧重的是“人”之“德性”的重铸(此点只是就其主导倾向而言)。早在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所“陈”的“六义”的第一义即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并在对此义的阐释中大力强调“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指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而鲁迅则更是在一九零七年就强调“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8〕到一九一八年十月,鲁迅在其《随感录三十八》中,仍然极力抨击中国固有的“合群的自大”,而大力提倡“个人的自大”〔19〕。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人的文学”要以“人道主义为本”,而他“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从今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20〕当然,不可否认,五四一代知识者的终极目的仍有于整体“国民性”之改造,但在具体操作中,他们“化大众”的切入点却选择了“个人”、“个性”培植。
其次,就五四新文学“化大众”的方式及其所采用的策略而言,五四一代作家也不再象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之维新派或革命派那样,直接将文学视为“新民”的工具或直接以文学去鼓动大众的革命激情,他们是在保证文学之独立性的前提下,发挥其思想上“化大众”的潜在功能。譬如,文学研究会是主张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团体,但其“宣言”却着力强调了文学的“独立性”:“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21〕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回忆其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时,曾言:“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虽然鲁迅强调“启蒙”,强调“为人生”,甚至强调用文学“改良这人生”,但仍然是通过“取材”上的选择,“揭出病苦”,“引起”“注意”,而非象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小说)那样为了“新民”而在两万字的篇幅内加入了近一万六千字的政治论辩,搞得小说不象小说,“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22〕当然,五四时期也有一些强调文学的直接的社会作用的言论,如言文艺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23〕,等等,但就全局而言,无论是理论倡导,还是创作实践,思想上“化大众”的努力都是在重视文学”独立性”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五四文学中思想上“化大众”的主潮之外,也出现了知识者在思想、情感上“大众化”的趋向。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同时刊载了胡适和沈尹默的同题新诗《人力车夫》, 二诗中皆透出了知识者对下层劳动者的同情,也显示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者“自审”、“忏悔”的开始与“原罪感”的萌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蔡元培在天安门前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宣称:“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24〕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口号中的“劳工”,是一个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较宽泛的概念,但是,随着“劳工神圣”口号的广泛传播,作为传播者的知识者却逐渐将自己从“劳工”中剔除出来,使“劳工”只剩下了“体力劳动者”这单一的内涵。所以“劳工神圣”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下层劳动者的讨论,也因此而引起了更多的新文学作家对劳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即使一贯不爱趋时的鲁迅,也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劳动专号》上发表了《一件小事》, 表达了对下层劳动者高尚品格的崇敬,亦深化了胡适、沈尹默之《人力车失》中透露出的知识者的“自审”与“忏悔”。另外,还出现了许多其他描写下层劳动者的作品,并有不少亦透出作者的敬佩之情,如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等。而这一切,都可以称之为知识者的“化自我”即使自我“大众化”的趋向。
当然,五四文学中更不能忽视的是文学语言上的“大众化”,其集中体现就是白话文学的提倡与实践。本章第一小节曾提及,在一八九八年,裘廷梁就积极提倡过白话文,此后的几年内白话也一度较为流行,但是,就倡导白话文的主张之系统、态度之坚决及运用白话之执著而言,五四文学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标志着五四文学发难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在这里,虽然胡适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将以白话从事文学创作的主张置在了较温和的“不避俗字俗语”的遮蔽之下,并且将这一点列为“八事”的最后一“事”,但胡适内心所真正重视、最为强调的恰恰是这最后一“事”,而其极力主张的也恰恰是较“不避俗字俗语”更明确的“用白话作文作诗”。胡适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说:“我们在国外讨论的结果,早巳使我认清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说来,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最基本的”。〔25〕虽然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采用了隐蔽主要目标的策略,但在第八“事”中言及“白话文学”时,仍未掩饰住其态度之坚决:“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得到了陈独秀的激赏,于是,在次月刊行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陈氏即登载了他“声援”胡适的《文学革命论》。 其实,胡适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既曾在致陈独秀的信中以“文学革命”称其拟想中的文学变革〔26〕,但在《新青年》上正式将其主张公之于众时,却改为《文学改良刍议》中的“文学改良”;而陈独秀却不善要弄胡适这种“内无武器”的玄虚,而是以“内皆武器”(鲁迅语)式的策略大张声势,直呼“文学革命”。陈独秀态度更加明朗,其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虽然其所要建设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并未被赋于明晰的内涵,但从其所用的“平易的”、“新鲜的”、“明了的”、“通俗的”等修饰语中即可以见出明确的要求文学语言形式“大众化”(即白话化)的取向。胡适、陈独秀其文相继刊出后,“白话文学”的倡议遂成了新文化界普遍关注的话题,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先后介入讨论,胡适、陈独秀也进一步切磋,“白话是文学的正宗”不久便成了不争的事实。在创作中,新文学家进行了切实的以白话入诗入文的尝试,并很快获得了白话文学的第一批实绩:胡适等人之于白话诗,鲁迅之于白话小说,……
从总体取向而言,“白话化”与“大众化”是一致的,因为“白话”不但包涵着对贵族化的“文言”的否定,而且其本身也确实是一种极为“大众化”的语言交流工具。不过,若细致考察五四文学“白话化”的具体进程,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对“大众化”的“偏离”。一九一九年,傅斯年在其《怎样做白话文》中提出,“我们仅仅做成代语的白话文,乞灵说话就够了,要是想成独到的白话文,超于说话的白活文,有创造精神的白话文,与西洋文同流的白话文,还要在乞灵说话以外,再找出一宗高等凭藉物。这高等凭藉物是什么,照我回答,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种欧化国语的文学。”〔27〕新文学的发展确实与傅氏的设想相一致,从“说话”与“欧化”两个方面汲取所需,从而形成了一种被后人指责为过于“欧化”的新文学语言系统。不过,在五四一代作家的心目中,这种“欧化”正是他们在实现文学语言“大众化”之时,为避免语言的单调化而做的一种“化大众”式的矫正。
在文学形式的其他方面,五四一代作家也未忽视“化大众”意义上的改造,如对传统的较合大众欣赏习惯的“情节结构”的突破,对与大众的接受心态相契合的“大团圆”结局的摒弃甚至“戏杀”(如《阿Q正传》)、对传统戏曲改造甚至以话剧取代传统戏曲的努力,等。这一切也反证了五四一代作家实现了为其前及其后的许多主张思想上“化大众”的作家所不及的文体意义上的“自觉”。
另外,五四文学还显示出了题材上的引人注目的“大众化”取向。胡适在其《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要将文学的取材范围扩展到“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28〕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也强调:“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男女是大多数,……所以其事更为普遍。”〔29〕而五四时期的创作,更是将题材扩展到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的各个阶层尤其是下层劳动大众,让粗手大脚的工人、农民,各式各样的普通男女,走进了以往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的文学画廊。
(作者补白:如果将百年中国文学初期维新派、革命派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视为“正题”,那么鸳鸯蝴蝶派对文学的娱乐作用的刻意追求就可以视为“反题”;而五四新文学强调在保证文学之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发挥文学潜在的思想启悟与审美娱乐功能,则可以称为“合题”。至五四时期,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化大众与大众化主题已完成了其正、反、合的第一个阶段,并为此后文学史展开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现象埋下了伏笔。限于篇幅,在此只将对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化大众与大众化主题演进历程的第一个阶段的考察公诸于此,以就正于方家。)
注释:
〔1〕严复:《原强修订稿》,见《严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2〕《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P302-303,上海书店1995年版。
〔3〕《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P248。
〔4〕《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P303。
〔5〕《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P388。
〔6〕《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P260。
〔7〕《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一》,P636,上海书店1994年版。
〔8〕《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一》,P84-85。
〔9〕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纪》,《戊戌变法》第3册,神州国光社出版。
〔10〕《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P308。
〔11〕《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P378。
〔12〕柳亚子在其《我与朱鸳雏的公案》,中曾明确介议写“布衣之诗”。
〔13〕参见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
〔14〕《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六》,P249,上海书店1991年版。
〔15〕《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七》,P376,上海书店1992年版。
〔16〕转引自范伯群:《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17〕李大钊:《“晨钟”之使命》,载1916年8年15日《晨钟报》创刊号。
〔18〕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19〕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20〕载《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
〔21〕《文学研究会宣言》,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
〔22〕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四》,收《饮冰室丛著小说零简》。
〔23〕《民众戏剧社宣言》,载1921年5月,《戏剧》第一卷第一期。
〔24〕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同时刊载于《北京大学日刊》第260号。
〔25〕胡适:《逼上梁山》,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印行。
〔26〕参见胡适:《寄陈独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27〕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
〔28〕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29〕1919年1月《每周评论》第五号。
标签:梁启超论文; 文学改良刍议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新青年论文; 胡适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