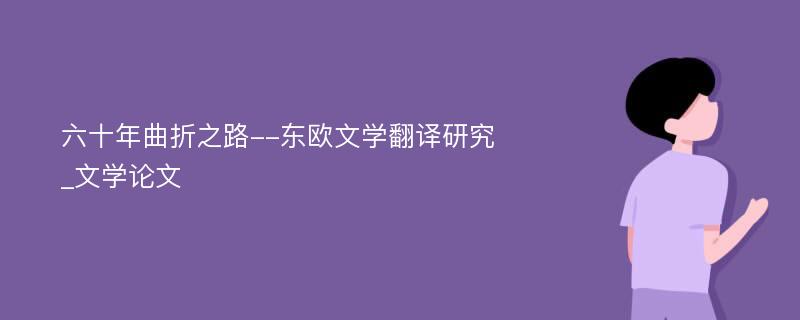
六十年曲折的道路——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曲折论文,六十年论文,道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特殊时期:开拓·重启·停滞
早在20世纪初,中国读者就读到了显克微奇、密茨凯维奇、斯沃瓦斯基、裴多菲、约卡依·莫尔、崛古立克等东欧作家的作品。李石曾、鲁迅、周作人、周瘦鹃等都是东欧文学翻译和介绍的先驱,鲁迅的功绩尤为突出。在《摩罗诗力说》中,除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英国和俄国诗人外,鲁迅着重介绍了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论及《先人祭》、《克里米亚十四行诗》、《格拉席娜》、《康拉德·华伦洛德》、《塔杜什先生》等多部作品。对于密茨凯维奇,鲁迅大加赞赏。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文学翻译和介绍事业。在此情形下,东欧文学翻译和介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茅盾、郑振铎、沈泽民、胡愈之、王鲁彦、冯雪峰、楼适夷、巴金等都译介过东欧文学作品。茅盾、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除大力译介东欧文学作品外,还组织翻译过《近代波兰文学概观》、《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塞尔维亚文学概观》等重要文章,为中国读者了解和研究东欧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茅盾更是常常亲自撰文,介绍和报道东欧文学。莱蒙特、普鲁斯、聂鲁达、萨多维亚努、伐佐夫、参卡尔等更多东欧作家被译介到了中国。甚至还有为数可观的东欧文学作品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其中包括显克维奇的《你往何处去》、莱蒙特的《农民》(4卷)这样恢弘的杰作。
鲁迅等先辈倾心译介东欧文学有着明确的意图:声援弱小民族,鼓舞同胞精神。鲁迅本人就说过:“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特别多。”应该说,在国家苦难深重的时刻,这些东欧文学作品的确成为了许多中国民众和斗士的精神食粮,在特殊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得到了重视。那是又一个特殊时期。中国正好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关系密切,往来频繁。东欧文学译介也就享受到了特别的待遇。自1950年至1959年,东欧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被译成了汉语,掀起了东欧文学翻译的又一个高潮。仅罗马尼亚小说就翻译出版了26部。时隔几十年,一些中国老作家依然记得萨多维亚努的《泥棚户》、《漂来的磨房》、《斧头》等小说。当时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东欧作家还有罗马尼亚作家格林内斯库、爱明内斯库、阿列克山德里、谢别良努,波兰作家奥若什科娃、柯诺普尼茨卡,南斯拉夫作家乔比奇、普列舍伦,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狄尔、聂姆曹娃、马哈、爱尔本等。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译介的作品良莠不齐,不少作品的艺术价值值得怀疑,政治性大于艺术性,充满说教色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读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想象一下,1950年代,当中国读者读到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阿喀曼草原》时,会产生怎样的美学和情感感动:
我航行在没有水的大海之上,
我的车子像一只船,摇荡着前去,
乘着青草的波浪,花朵的潮头,
经过了红红的山茱萸的岛屿。
黑夜下来了。没有路,也没有山——
我要寻出那指引水手们的星星。
那远远的云,闪耀的第聂斯特尔,
那颗星,阿喀曼的早晨的明灯。①
再比如罗马尼亚剧作家扬·路卡·卡拉迦列的代表剧作《失去的信》。曲折多变的情节,辛辣尖锐的笔锋,妙趣横生的语言,滑稽可笑的人物,所有这些确保了《失去的信》的艺术性、思想性和战斗性。一百多年来,该剧始终是罗马尼亚各大剧院的保留剧目,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已成为罗马尼亚戏剧中的经典。当这部剧作于1953年同中国读者见面时,同样受到了热烈欢迎。五年后,它还被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搬上了舞台。
此外,罗马尼亚小说家萨多维亚努的《斧头》、捷克小说家狄尔的《吹风笛的人》、捷克诗人爱尔本的《花束集》、捷克女作家聂姆曹娃的《外祖母》、捷克小说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捷克诗人马哈的《五月》、波兰作家显克维奇、普鲁斯的不少小说和散文等也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不愧为东欧文学中的经典。我们还要在此特别提一下“三套丛书”。那是一项宏伟的工程,而且目标明确,就是要让中国读者分享到外国的优秀文学成果,提高中国作家的艺术修养,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冯至、卞之琳、罗大冈、戈宝权等专家学者参与制定选题。
在此之前,东欧文学作品都由日语、德语、英语、法语、俄语等语言转译成汉语,基本上都绕了一个弯,有些还绕了几个弯。介绍和研究文章也都是根据二手或三手材料而写成的。艺术性和准确性都有可能遭到损害。这自然只是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根本没有通晓东欧国家语言的人才。建国后,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国家先后多次选派留学生到东欧各国,学习它们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这就意味着一批专门从事东欧文学教学、翻译和研究的人才即将诞生。后来,这些人才主要集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文学研究室也应运而生。最鼎盛时,它几乎拥有东欧各语种的专家学者:波兰文的林洪亮和张振辉;捷克文的蒋承俊;匈牙利文的兴万生、冯植生和李孝凤;保加利亚文的樊石和陈九瑛;罗马尼亚文的王敏生;南斯拉夫文和阿尔巴尼亚文的高韧和郑恩波。此外,世界文学编辑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等单位还涌现出了杨乐云、易丽君、冯志臣、陆象淦、李家渔等优秀的翻译家和学者。从1950年代末开始,人们就从《译文》(1959年后改名为《世界文学》)上陆续读到一些直接译自东欧语言的文学作品。一些介绍文章也都出自第一手材料。
但令人遗憾的是,进入19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国和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也因此日趋冷淡。
“文革”期间,整个国家都处于非正常状态,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也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在近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读不到什么东欧文学作品,只看到一些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电影。《伏击战》、《第八个铜像》、《多瑙河之波》、《勇敢的米哈伊》、《齐波里安·波隆佩斯库》、《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让我们了解到那些国家的历史和状况,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伴随了一代中国人的成长。
二、改革开放:机遇·发展·兴盛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总体来说,我们读的大多是外国文学。不能否认外国文学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也不能否认外国文学对当时中国文学创作所发挥的引导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外国文学引领着一批中国作家逐步走上了创作之路。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也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呈现出翻译和研究齐头并进的勃勃生机。
1980年代初,社科院外文所东欧文学研究室开始酝酿和筹备《东欧文学史》的撰写工作。这是项艰巨而庞大的工程,填补了东欧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有关专家和学者们经过艰苦努力,于1980年代中期完稿。1990年,这部50多万字的著作作为“东欧文学丛书”的一种,由重庆出版社推出。全书按年代顺序分为四编,囊括了东欧所有国家的文学史,而且根据具体情形,主次分明,重点突出,既有宏观概括,也有微观描绘,既涉及基本历史和文艺思潮,也兼顾作家论述和文本细读,还关注到其他艺术种类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撰写者都是通晓东欧有关国家语言的学者,所依据的全部是第一手材料,基本上是东欧文学研究室成立后学术上的一次集体亮相。林洪亮和张振辉负责波兰文学;蒋承俊和徐耀宗(唯一外单位的作者)负责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兴万生、冯植生和李孝风负责匈牙利文学;王敏生负责罗马尼亚文学;陈九瑛和樊石负责保加利亚文学;高韧负责南斯拉夫文学;郑恩波和高韧负责阿尔巴尼亚文学。这是我国第一部《东欧文学史》,简明扼要,脉络特别清晰,只要一册在手,读者便能了解到东欧各国文学的基本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依然是最全面、最权威的东欧文学史方面的著作。
到了1990年代,冯植生、林洪亮、蒋承俊、陈九瑛、高韧、高兴等部分东欧文学学者趁热打铁,又参加了吴元迈主编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东欧文学部分的撰写工作,将东欧文学史写到了1990年代。至此,东欧文学从古至今的基本面貌,在我国学者的笔下得到了初步呈现。规模巨大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历时多年,分成五大卷,最终由译林出版社于2004年隆重推出。这套外国文学史,凭借其宏伟的规模、实力整齐的作者队伍、扎实的第一手资料、规范的编辑加工以及精致的装帧印制,获得了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与此同时,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利用自身优势,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1999年前后推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作者大多是北外的教师,活跃在外语教学第一线。丛书中,我们读到了《保加利亚文学》(杨燕杰)、《波兰文学》(易丽君)、《捷克文学》(李梅、杨春)和《罗马尼亚文学》(冯志臣)。这套丛书以大学生为读者对象,注重通俗性、概括性、生动性、便捷性,每本都在十万字左右,属于文学简史,是不错的外国文学史入门书,对普及外国文学知识,提供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线索,都有一定的作用。易丽君、冯志臣等长期在东欧语系工作,有着深厚的外文和中文功底,教学之余,从事翻译和研究,成就斐然。
东欧文学史方面,还有《东欧文学简史》(上下册,张振辉等著,海南出版社,1993)、《东欧戏剧史》(杨敏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东欧当代文学史》(林洪亮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二十世纪波兰文学史》(张振辉著,青岛出版社,1998)、《波兰战后文学史》(易丽君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捷克文学史》(蒋承俊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等著作先后问世。这些表明东欧文学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新时期,东欧文学翻译一刻也没有停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经典重译。我们终于读到了从捷克文直接翻译的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星灿译)、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蒋承俊译),马哈的《五月》(蒋承俊译),从波兰文直接翻译的显克维奇《你往何处去》(林洪亮和张振辉均译过),从罗马尼亚文直接翻译的卡拉迦列的《卡拉迦列讽刺文集》(冯志臣、张志鹏译)、《一封遗失的信》(马里安·米兹德里亚、李家渔译)等。显克维奇的《十字军骑士》(张振辉、易丽君译)、莱蒙特的《福地》(张振辉、杨德友译)、普鲁斯的《玩偶》(张振辉译)、普列达的《呓语》(罗友译)、《世上最亲爱的人》(冯志臣、陆象淦、李家渔译)、安德里奇的《桥·小姐》、塞弗尔特的诗选《紫罗兰》(星灿、劳白译)等从原文直译的东欧文学作品都在中国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阅读记忆。而且这些译本大都有长篇论文作为序言,对作家、对作品都有精当和深入的研究和评析。兴万生的研究专著《裴多菲评传》是我们认识和理解裴多菲的权威读本。1996年,他几十年呕心沥血完成的六卷本译著《裴多菲文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刊物中,《世界文学》杂志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译介东欧文学作品。它先后推出的《斯特内斯库小辑》、《鲁齐安·布拉加诗选》、《塞弗尔特作品小辑》、《米沃什诗选》、《赫拉巴尔作品小辑》、《米兰·昆德拉作品小辑》、《希姆博斯卡作品小辑》、《凯尔泰斯·伊姆雷作品小辑》、《贡布罗维奇作品小辑》、《埃里亚德作品小辑》、《齐奥朗随笔选》、《霍朗诗选》、《克里玛小说选》等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具有一定的分量。有些作品甚至引起了读书界、评论界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和热情呼应。比如赫拉巴尔、齐奥朗。
《世界文学》1993年第2期重点推出《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作品小辑》,收入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短篇小说《中魔的人们》和《露倩卡和巴芙琳娜》以及创作谈。赫拉巴尔,一个真正有捷克味的小说家。说到赫拉巴尔,我总会想到哈谢克。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十分亲切的形象。赫拉巴尔也确实受到过哈谢克的影响。但他比哈谢克更精致、更深沉,语言上也更独特和讲究。在我看来,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是其最有代表性的小说,篇幅不长,译成中文也就八万多字。小说讲述了一位废纸打包工的故事。一个爱书的人却不得不每天将大量的书当作废纸处理。这已不仅仅是书的命运了,而是整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同样遭遇过这样的命运。小说通篇都是主人公的对白,绵长,密集,却能扣人心弦,语言鲜活,时常闪烁着一些动人的细节,整体上又有一股异常忧伤的气息。因此,我称这部小说为“一首忧伤的叙事曲”。这种忧伤的气息,甚至让读者忘记了作者的存在,忘记了任何文学手法和技巧之类的东西。这是文学的美妙境界。
《赫拉巴尔小辑》出版后,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龙冬在读到赫拉巴尔作品后,顿时被吸引住了,不久便开始考虑出版赫拉巴尔作品。版权、翻译等事宜费了一番周折。终于,从2003年起,《赫拉巴尔作品集》陆陆续续与中国读者见面了。作品集包含了《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我是谁》、《传记三部曲:林中小屋》、《传记三部曲:婚宴》、《传记三部曲:新生活》、《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巴比代尔》等。星灿、杨乐云和万世荣参加了翻译。译者都是捷克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对作品的把握准确、可信。星灿的序言也为读者提供了不少信息,大致勾勒了赫拉巴尔的创作景象。读者的反响出乎出版社的意料,既产生了社会影响,又带来了经济效益。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惊喜。
齐奥朗可以算是20世纪世界文坛的一大怪杰,一辈子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在孤独中写下了大量哲学和文学作品。他从罗马尼亚移居法国后,一直用法语写作,文笔清晰、简洁、优雅,字里行间不时地会流露出黑色幽默的色彩。他的大量箴言很有特色和深度,各种话题都涉及。他还写有不少有关当今一些大作家的文字。他的文字与其说在叙述、在评论,不如说在剖析、在挖掘,独特,无情,直抵本质。齐奥朗在欧美文坛早就出名,但国内却一直没有介绍过他的作品。《世界文学》1999第6期刊登了“齐奥朗散文六篇”,其中既有箴言,也有笔记,也有一些评论。小辑出来后,立即引起了一些读者的注意。诗人寒烟在《值得人活下去的成长》一文中表达了对这位作家的喜爱:“终于,我也能读到带来‘终结’意义的齐奥朗了。”
《世界文学》之所以一直关注东欧文学,与它几十年的传统有关,与中国和东欧国家共同的经历有关,自然,更主要的还是与东欧文学丰富的资源有关。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世界文学》更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和经典性,将文学价值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如此,我们便通过这个窗口,目睹了一大批真正有价值的外国作家的文学风采。
1980年代后期,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参考丛书”的名义,接连出版了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景凯旋、徐乃健译,1987)、《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韩刚译,1987)、《生活在别处》(景凯旋、景黎明译,1989)等长篇小说,说是“内部参考丛书”,实际上完全是公开发行的。与此同时,《中外文学》等杂志也在连续发表昆德拉的短篇小说、谈话录和一些有关小说艺术的文章。很快,中国读者牢牢记住了米兰·昆德拉这个名字。“轻与重”、“永劫回归”、“媚俗”等昆德拉词典中的词汇,作为时髦词汇,开始出现在中国评论者的各类文章中。昆德拉在中国迅速走红。一股名副其实的“昆德拉热”也随之出现,并且持续了几十年。这显然已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昆德拉是一位有智慧的作家,他将文学、政治和性融为一体,而重心又落在了文学上。这样就有可能让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读他的作品。昆德拉,同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福克纳等外国作家一样,吸引并影响了一大批中国读者、作家和学者。
三、时代变迁:困境·沉淀·反思
1989年底,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共产党政府纷纷垮台,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抛弃。这一剧变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东欧国家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这种影响和改变自然会波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学。
东欧剧变后,我国东欧文学研究者再一次面临困境:学术交流机会锐减,资料交换机制中断。看不到报刊,看不到图书,看不到必要的资料,没有出访机会,这对于文学研究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年,到后来才逐渐得到改观。而此时,不少东欧文学研究者已进入老年。翻译和研究队伍已青黄不接。曾经人丁兴旺的东欧文学研究室,也随着最后一位研究者的退休而不复存在。
和以往不同,这一回,困境并没有导致停滞,而是某种沉淀。沉淀有助于走向深入,进行反思。事实上,尽管艰难,翻译和研究依然在进行。只是节奏放慢了一些。粗略统计一下,除了前面已经说到的一些成果,还是有不少成果值得一提。翻译方面:《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东欧五卷,重庆出版社,1992)、《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东欧卷》(林洪亮、蒋承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我曾在那个世界里》(蒋承俊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东欧卷》(张振辉、陈九瑛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东欧卷》(冯植生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呼唤雪人》(林洪亮译,漓江出版社,2000)、《诗人与世界: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诗文选》(张振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无命运的人生》(许衍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星灿、高兴主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高兴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东欧国家经典散文》(林洪亮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世界美如斯》(杨乐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塔杜施·鲁热维奇诗选》(张振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河畔小城》(杨乐云、刘星灿、万世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一个女人》(余泽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等。这段时间,诺贝尔文学奖这盏聚光灯照亮了希姆博尔斯卡、凯尔泰斯两位东欧作家,让读者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致。此外,由于中国青年出版社成功地出版了赫拉巴尔、塞弗尔特的作品,一股小小的捷克文学热在中国读书界悄然掀起。
这一时期,《密茨凯维奇评传》(张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裴多菲传》(冯植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东欧文学大花园》(高兴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中罗文学关系史探》(丁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等研究专著先后问世。
《东欧文学大花园》力图重新打量和梳理东欧文学。出于种种缘由,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一些作家和作品被夸大了,另一些作家和作品又被低估了,还有一些作家和作品根本就被埋没了。时代变了,目光肯定就不一样。因而,重新阅读、重新评价、重新梳理,成为一件必须的事。例如,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不刻意要表达什么思想意义或达到什么艺术效果。他也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已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这时,小说于他就成了一个无边的天地,想象和游戏的天地,宣泄的天地,就让帅克折腾吧,折腾得越欢越好。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统统都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而这一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理想藏书》的编著者皮沃和蓬塞纳说:“士兵帅克不仅是捷克人精神和抗敌意志的永恒象征,而且还是对荒诞不经的权势的痛彻揭露。这位反英雄是幽默的化身,而这幽默是对我们千变万化时代的唯一可行的应答。”②
我愿意重点介绍一下丁超的《中罗文学关系史探》。这是一本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专著。说实在的,读到这本书时,我的心里充满欣喜。这同我的专业有关。作为中罗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罗文学关系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而且旁涉政治、历史、哲学、外交等诸多领域,值得研究。但长期以来,一直无人问津这一课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资料匮乏,考证难度大,学术时机和政治形势不够成熟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此外,这一课题对研究者本身的素质和条件也有特殊的要求:既要通晓罗马尼亚语、法语、英语等外语,能够阅读和领会外文资料,发掘线索,理清脉络,以求细节和整体上的全面把握;又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文学修养,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并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来探讨问题、分析问题;还要有严谨、踏实、不畏艰难的治学态度。丁超显然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和素质,在恰当的时机完成了一个冷僻、艰难但又极有意义的课题。这一成果至少有以下意义和价值:(一)首次对中罗两国文学互相接受的历程进行了双向梳理和现代诠释,以客观、适当的方法勾勒了中罗文学关系的全貌,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为小国文学研究树立了一个范例,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发掘出了中罗文学关系中一些原先不为人知的珍贵资料,澄清了不少长期以来一直模糊不清的史实,解决了许多悬而不决的问题。比如,澄清了米列斯库的真实身份和访华的具体背景、细节和过程,全面、客观介绍和评价了他的有关中国的著作;通过考证,推翻了“鲁迅为翻译罗马尼亚文学第一人”的说法;用新的眼光重新评估了中罗文学交流中的一些事件和作品。(三)为中罗文学,乃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个案和参考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和丰富了中罗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四)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和外交意义,可以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份有说服力的参照和依据。
近几年,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又开始受到中国读者的注意。他的《破碎的四月》(孙淑慧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亡军的将领》(郑恩波译)也再次出版。其实,1990年代初,此书曾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但当时并没有受到特别关注。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时隔近20年,人们终于将热情和欣赏的目光投向了卡达莱的这部作品。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梦幻宫殿》(高兴译)也已同中国读者见面。高兴等人已开始发表论述卡达莱的研究文章,将来会有更多的文章出现。
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依然有着丰富的空间和无限的前景,就连经典作家翻译和研究都还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一一填补。而赫拉巴尔、塞弗尔特、齐奥朗、埃里亚德、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凯尔泰斯、卡达莱这些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的东欧作家也值得翻译和研究。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关键在人,关键在一支翻译和研究队伍,关键在一种事业的传承。但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目前恰恰就面临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商品时代,文学日益边缘化,加上待遇等种种问题,甘愿献身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更是如此。由于东欧国家都是一些弱小国家,经济上也不太发达,从事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面临着人们难以想象的困境:机会少,受重视程度低,出版艰难。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这项事业已处于濒危状态。期望国家能高度重视这一严重问题,期望有关部门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扶持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
注释:
①孙用译,载于《译文》1953年12月号。
②见余中先译《理想藏书》第8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标签:文学论文; 世界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