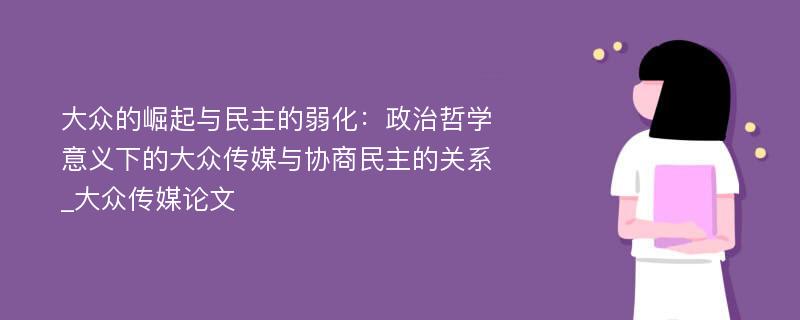
大众的崛起与民主的衰弱——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大众传媒与商议民主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大众论文,衰弱论文,大众传媒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7 对于许多人来说,民主就是大众(public)民主,就是赢得大众支持的民主。然而,如果大众是受到操纵的大众,特别是被现代网络媒体操纵的大众,那么在被操纵的大众之中还有民主吗?笔者认为,民主就是要通过协商找出适用于社会的正当的法律、规则和政策,这就需要借助于具有理性精神的公民的讨论,而大众民主制度却无法达致这一目标。事实上,大众的崛起恰恰正在削弱协商民主的精神。这是当下值得我们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 大众与公众的差别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是无法被明确地区分为公众(mass)和大众这两个类别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政治哲学意义上也无法区分公众和大众。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产生初期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分时,曾经把人区分为“公人”和“私人”①。一个人作为国家的公民应该是“公人”,是超越私人利益而关注普遍利益的国家公民。而在市民社会中,只关注个人利益的人就是“私人”。私人的集合体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大众。然而,当许多个人只是从私人的角度出发来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这些个人就构成了“大众”。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曾经作过类似的分析。她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认为这两个领域分别类似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和家庭。直至古罗马时代,家庭的衰弱和社会的兴起同时发生了,社会是带有家庭特征的组织,它把私人领域中的许多要求带入公共领域中。由此,她把由这些个人构成的组织称为“社会”。她指出:“随着社会的兴起,随着家庭和家务活动进入公共领域,古老的政治和私人领域以及更晚近建立的私密空间不可抗拒地被吞噬的倾向,已经变成了社会这个新领域的典型特征之一。”②阿伦特还把这些由私人构成的社会称为“大众社会”③。按照她的思路,只有古希腊“政治动物”意义上的人才具有公众的意义;而那些带着私人倾向进入公共领域的人不过是大众的一员,他们构成的社会就是大众社会。 卢梭则从“公民政治意志表达的质量”的角度,把公众和大众从政治意义上区分开来。卢梭把公民的政治意志区分为“公意”和“众意”。在他看来,“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④。对于卢梭来说,人民的意见可能会受到私人意愿的左右从而产生“不好的东西”。他说:“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人们总是意愿自己的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人民是绝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唯有在这个时候,人民才好像意愿要不好的东西。”⑤当人民受到欺骗的时候,人民的意志可能就不是公意,而是众意了。也就是说,如果人民受到了欺骗,被某种舆论所操纵,那么此时的人民就成为“大众”。而只有形成公意的人民才是“公众”。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引用了许多资料来说明公众和大众的区分,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米尔斯所做的区分。“正如我们对公众一词所理解的那样,在公众当中,(1)事实上有许多人既表达意见又接受意见。(2)公众交流是这样组织起来的,以至于公众所表达的任何一种意见都有机会立即得到有效的回应。(3)由这种讨论所形成的意见在有效的行动中,甚至在反对(如果必要的话)主导性权威系统时,随时可以找到一条发泄的途径。(4)权威机构并不对公众进行渗透,因此公众在其行动中或多或少是自主的。”⑥而大众则不同:“在大众中,(1)实际上,表达意见的人比接受意见的人少得多,因为公众群体变成了受大众传媒影响的个人的抽象结合。(2)占主导地位的交流过程是这样组织起来的,以至于个人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立即或有效地作出回应。(3)运转着的意见能否实现是掌握在那些组织并且控制这一运转渠道的权威人士手中。(4)大众无法从机构中获得自主性,相反权威机构的行动者渗透到大众中,从而削弱了大众通过讨论形成意见时的任何自主性。”⑦显然,米尔斯对大众和公众的区分也是从相互交流的角度来进行的。在米尔斯所提出的区分大众和公众的四个标准中,最核心的就是:人们之间是否通过传媒而进行了深入的意见交流和讨论。 从米尔斯所提出的经验标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组织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更有可能进行程序化的讨论。比如,在西方的议会组织中,议员作为公民的代表可以不受权力限制,自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这些意见能够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回应。再比如,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控辩双方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而有效的讨论,也可以得到及时的回应。又比如,在学术会议中,这种自由的、无束缚的、充分的讨论也是可能的。上述个案都可以被理解为公众意义上的讨论。但是,在一般大众传媒中,比如在电视或报纸等媒介的辩论中,意见的接受者往往比表达者多得多。当然,这种状况在现代网络传媒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我们能不能由此而简单地说,围绕着大众传媒而结合起来的人群都是大众?比如,一个人正在观看电视辩论,而在电视辩论中人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或者阐述的理由,都曾是他本人思考过或正在思考的,甚至超出了他本人所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于是他对所讨论的议题没有进一步的疑问或者理由需要补充。也就是说,他赞同其中的某些观点。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没有直接交流而简单地判定他属于大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米尔斯的经验标准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补充。 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采取了一个非经验的标准,或者说采取了一个价值标准。他认为,一个群体是大众还是公众,取决于这个群体是否按照一定的非强制的方式而对于有关自己的问题进行了高质量的讨论。这就是说,哈贝马斯是从讨论的方式和讨论的质量来区分公众和大众的。他指出:“在公共领域中,所表达的意见被按照议题和肯定/否定观点而进行分拣;信息和理由被加工为成为焦点的观点。使这种成束的意见成为公共意见或舆论的,是它的形成方式,以及它所‘携带’的广泛的赞同。公共意见并不是某种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它并不是单个地被问、单个地回答的个人意见的总和;就此而言,切不可把它与民意调查研究的结果混为一谈。”⑧在公共领域中,即在公众中,人们之间的讨论是没有被强制的,他们能够通过相互讨论而形成一致意见;而在大众中,人们之间没有什么讨论,甚至只有单个人之间的问答,比如民意调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把“公共性”(publicity)和“大众性”(popularity)区别开来。按照他的分析,公共性就是要把公共政策、法律等交给公众来自由讨论,并通过这种讨论而形成共识。公共性是政府行为、公共政策的正当性的标准。而大众性则不同,大众性是单个人意见的总和,是民意调查中所显示的支持度。因此,哈贝马斯说:“大众性是一把尺子,政府用它来衡量对民众的非公共舆论的控制程度。衡量领导班子还必须另外争取多少可以转化为大众性的公共性。”⑨在这里,非公共舆论就是大众舆论,是“众意”,它类似于影视明星的粉丝数量。某些政府所采取的公共政策所关注的主要是民意的支持度,而不是它的公共性(正当性)。正因为如此,在谈到公共性和大众性之间的区分的时候,哈贝马斯指出:“大众性并不等于公共性;但是没有公共性,大众性也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⑩ 概而言之,对于公众和大众、公共性和大众性的区分不是无足轻重的,这涉及我们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本质的理解。 二 公众与民主 如果公众和大众是可以被区分开来的话,那么民主制度也同样可以被区分为大众民主制度和公众民主制度。大众民主制度是自由主义导向的民主制度,而公众民主制度则是共和主义导向的民主制度。自由主义导向的民主制度强调个人的权利,而不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共和主义导向的民主制度则把国家理解为由公民结合起来的共同体,主张通过所有的公民之间的共同协商来解决那些涉及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问题。 这两种不同的民主制度涉及对于民主的本质的理解。自由主义的大众民主模式强调大众对于政府的监督,注重政府的主张是否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是否被大多数人所赞同,它所忽视的恰恰是公众的参与和自主管理。而对于共和主义来说,国家就是公众自主管理的共同体。大众民主模式所面临的难题是:一个受多数人赞同的政府或者公共政策为什么是正当的?或者说,如果一个政府或者一种政策满足了大多数人的需要,那么少数人的需要为什么应该被牺牲呢?大众民主模式无法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哈贝马斯在分析竞争性民主时对这些问题作了非常深刻的回答。他认为,这种竞争性民主是建立在伦理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的,即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平等的个人是价值的最后判定者。规范的有效性恰是建立在个人的主观意志之中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的主观意志应该得到尊重,而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就应该被牺牲呢?可能的回答只能从权力大小的角度来给出,即少数人的政治力量小于多数人的力量。这就是说,多数人的意见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多数人的意见是正当的,而是多数人的力量更大;少数人只能屈服于多数人的力量。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实际原因。既然多数人的意志不一定是正确的,少数人为什么还要服从多数人呢?少数人在这里采取了一种策略性的态度:既然少数人的力量无法对抗多数,那么少数人只能承认多数人的力量,而等待机会努力使自己成为多数人。多数人之所以会保护少数人,是因为多数人害怕自己未来有一天也会成为少数人。那么少数人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多数人呢?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少数人坚持的意见是否正确,而是少数人能够通过策略手段赢得其他人的赞同。这是因为,在多数人和少数人的竞争中,他们之间不是为正当性而竞争,而是为权力而竞争。这种权力的竞争只需要付诸意识形态的诱惑力,而不是真理。通俗地说,只要人们能够通过话语赢得多数人的赞同即可,至于其中的道理是否正确,这并不重要(11)。也就是说,在竞争性民主(大众民主)中,人们最终要诉诸诱惑性的话语来赢得多数人的赞同,而不是用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获得人们的赞同;不是要探索正当性的规范,而是争取权力斗争的胜利。在这里,民主被理解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西方国家所实行的选举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要实现政治权力的和平过渡。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与探索社会中的“真理”无关,而与权力斗争有关。 如果说大众民主是在进行权力斗争的话,那么公众民主就是要为“真理”(正当性)而奋斗。公众民主在本质上是要探索正当性规范或正当性制度,而这只能通过商谈性程序来获得。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商议民主制度就是构建一种商议程序从而建立一个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并克服竞争性民主所带来的困难。他所理解的民主就是把商谈原则法制化,即通过程序化的商谈来探索正当的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等。为此,他强调:“民主原则是商谈原则和法律形式相互交叠的结果。”(12)他所提出的法制化的商谈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是非建制化商谈,一是建制化商谈。非建制化商谈主要是大众传媒以及其他各种大众聚集中的商谈,建制化商谈主要是在议会和法院等制度化的机构中的商谈(13)。 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商议民主制度中的这两个部分是相互作用的。非建制化商谈的主要功能是“提出议题、作出建议、笼统地讲发挥公共影响”(14);而建制化商谈则需进行严格的程序化商谈,从而提出各种政策和法律。建制化商谈和非建制化商谈的关系是,建制化商谈处于中心地位,非建制化商谈处于边缘地位。他说:“对于商谈的民主论的这种社会学转译,意味着有约束力的决策——如果它要具有合法性的话——必须受到交往之流的导控,这种交往之流出发于边缘领域,穿过位于议会组织或法院入口处(必要时还有实施决策的行政部门的入口处)的民主的、法治国的闸门。”(15)这就是说,非建制化商谈,比如各种社会组织、公民组织中的商谈以及大众传媒中的商谈会提出议题,或者作出决议,从而对立法、司法乃至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而立法和司法部门则进行理性的商谈,从而作出正确的决定。当然,哈贝马斯在这里所提出的是形成正确决定的一般程序,它只是形成正确决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他看来,真正的商议民主制度还需要其他许多充分条件,它们包括:非建制化商谈的中立性;参与商谈的人具有交往理性精神;商谈过程中的人们只是用理由来说服人;商谈中的人必须遵循语用学规则;必须把相互交流并得到共同的意见作为自己的目标;等等。如果一个人在涉及公共事务的商谈中具有交往理性精神,如果他总是致力于用理由来说服人,如果他说话总是遵循语用学规则,如此等等,那么他必定把自己作为公众中的一员。从哈贝马斯关于商议民主的社会学转译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民主制度在社会学意义上就是如是设计的,即大众传媒提出问题,政府、议会和法院对此进行认真思考。但是,这种制度性的结构虽然是合法化所必需的,但是却不够充分。也就是说,即使大众传媒所提出的是合理的问题,是所有公民所关注的问题,但是议会中的讨论或者法院中的讨论就一定是中立的吗?人们就一定是从交往理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吗?显然,如果参加议会讨论的人把自己作为大众中的一员,只考虑自己的党派利益,那么他就不是中立的,也不可能遵循语用学规则而真诚地与其他人讨论和交流。在西方社会的议会组织中,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由此,我们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公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商议民主。如果没有商议民主,那么民主制度就只能停留在权力竞争的水平上。 三 大众的崛起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主不仅需要有制度,而且需要公民以商议民主精神来参与公共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有些人天生便具有奴性,比如奴隶必须受制于别人的管束,他们并不是政治动物,因此奴隶在城邦政治中是没有地位的。如果我们把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等级制度观念剔除出去,而把政治动物理解为合格公民的政治要求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公民只有在成为公众的时候,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才是真正的“政治动物”。阿伦特正是从这个角度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由此出发分析现代民主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16)。她从反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成为“政治动物”的话,那么人就会成为“奴隶”。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说,如果人们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不能成为“政治动物”,不能成为公众中的一员,那么人们就会成为“奴隶”,成为“大众”中的一员。 阿伦特把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她是从社会兴起的角度来理解“大众”的。她对社会领域兴起原因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于大众兴起原因的分析。按照阿伦特对于私人领域的理解,私人领域是维持生存的领域,是劳动的领域;在古希腊时代,奴隶只生活在私人领域之中,为生存而斗争。她指出:“在古代人的感情中,‘隐私’这个词本身所表示的私人性质无比重要,它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被剥夺了什么东西,甚至被剥夺了人类能力中最高级的、最属人的东西的状态。一个人过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一样自愿选择不建立这样一个领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17)如果一个不完整的人进入了公开的领域,那么这个公开的领域就是社会领域。阿伦特认为,社会领域的兴起与家庭的衰弱是同时发生的(18)。她此处的意思是说,当人立足于私人利益而与他人结成一个团体的时候,这样的团体就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团体,就属于阿伦特所说的社会领域。这些自治的社会团体是平等成员的集合体。这些团体包括:“代表明确团体利益的那些协会”、“具有明显党派政治目标的那些社团”、“专业协会、作家协会、激进专业人员团体”、“具有一些公共关切的‘政治利益’团体以及教会或慈善组织”(19)。哈贝马斯把这些团体理解为“由大众传媒所支配的公共领域的公民社会基础”(20)。对于阿伦特来说,这些社会团体都有各自的利益,他们还没有获得完全超越家庭的那种公共领域的意义。社会领域中的这些人不过是具有类似利益的人的汇聚,他们不可能具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那种交往理性精神。而公共领域的人们应该是超脱的、不拘泥于个人利益的。正因为如此,阿伦特指出:“社会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在它里面,人们为了生命而非别的什么东西而相互依赖的事实,获得了公共的含义,与纯粹生存相联系的活动被获准现身于公共领域。”(21)社会领域实际上变成了人们争取个人利益的场所,当人们以这样的身份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这些人不可能具有公民的意愿,而是大众的一员。阿伦特承认,最初,这些社会团体还具有类似于家庭的特点,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各种社会群体“用平等的手段和相同的力量吸纳并控制一个既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22)。即使这些团体的成员是平等的,但是这些成员只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平等,而不具有公共领域中的那种卓越个性。阿伦特把这种卓越个性理解为人性,即公共领域中进行活动的人所应该具有的人性心(23)。而在现代大众民主中,这些平等的成员就是按照统计学意义上的人而被理解的,他们不能被看作具有卓越个性的公民(公众)。或者说,这些人没有哈贝马斯所强调的那些构成商议民主所需要的充分条件。 那么,为什么社会领域中的大众不具有公众所需要的那种卓越个性呢?按照阿伦特的理解,他们把与生存相联系的活动带入了公共领域。或者说,他们在公共领域中仍然坚持家庭生活中的那种生存竞争原则,这无疑限制了他们的眼界。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分析,在生存斗争中,人们所运用的是一种工具理性精神。这种工具理性精神使人们像奥德修斯和他的水手一样,要么把自己捆绑了起来,要么堵塞了自己的耳朵(24)。他们在生存斗争中已经牺牲了自己,他们或者失去了自由,或者失去了听觉;他们不再是阿伦特所期待的那种具有卓越个性的人,他们或者只知道用工具理性来征服别人(如奥德修斯),或者就是简单地顺从别人(像奥德修斯的水手)。对于霍克海默来说,这些人不具有客观理性精神。这种客观理性精神在公共领域中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交往理性精神。 卡耐提对于大众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与阿伦特、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思想有诸多交集。卡耐提和阿伦特一样,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可以追溯到大众的兴起(或社会的兴起)这一现象上。在霍耐特看来,卡耐提也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把现代民主制度的困境的根源追溯到自我持存的逻辑中(25)。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没有从自我持存的逻辑中发现大众产生的根源不同,卡耐提则从自我持存的逻辑中探索大众产生的根源。对于卡耐提来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出于自己的本能而相互竞争,这使人们不可能形成相互关怀、相互理解的共同体。大众就是这种孤独存在者的结合体。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出发,人们之间就不可能通过相互交流而达成共识;对达成共识的民主制度的期待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在这里,正如霍耐特所说,卡耐提实际上接受了霍布斯主义的思想传统(26),即人和人之间构成公众是不可能的。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只要人立足在孤独的自我之中,公众的构想无疑便是天方夜谭。 如果人们把生存竞争的原则直接运用到公共领域中,那么公共领域中的人们就不可能相互合作而成为公众,而只能是孤立个人的聚结,是争夺权力的大众。上述的分析实际上告诉我们,不断深化的市场观念已经把人变成了孤立的个人,变成了大众,它在不断地冲击和动摇共同体的传统。在市场体系中,人和人之间虽然也相互联系,但这种联系仅被局限于功能性关系之中,而共同体意义上的相互联系在其中不复存在。市场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时候即已出现,尽管如此,由于那个时代还存在阶级斗争,因此还有大众传媒对社会事务进行真正的讨论。而现代大众传媒的作用加剧了这种大众化趋势。众所周知,在传统意义上,大众传媒是用来传播信息、教化大众、表达情感的,其中的话语承担着语用学的功能。但是,随着大众传媒大规模的生产,导致话语超出了语用学的功能。在大众传媒中,人们说话不是为了传播信息、表达思想、教化大众,而是为了说话而说话,为了表达而表达,表达本身的目的消失了,人们说话只是为了使再说话成为可能;人们进行信息传播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传播消息,而是为了使再传播消息成为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消息如果不能吸引观众或者听众,那么它就会面临再生产的危机。于是大众传媒自身的目的发生了变化:传播不是为了给人们提供真实的消息,而是为了吸引听众或者观众。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便是:大众传媒有时会不顾真实性而仅关注观赏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大众传媒再也不传播真实消息了,而是说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东西超越了真假,在这里真假变得难于区分了。同样的道理,大众传媒的其他语用学功能也消失了。本来,人们要借助于大众传媒的语用学功能使相互之间进行交流,并借助于这种交流结合成为公众。但是,当大众传媒的语用学功能消失之后,大众传媒的目标定位于吸引观众的注意,或只是要引发观众的赞同,于是,围绕大众传媒所凝聚起来的人们就不是共同体意义上的公众,而是大众。 当然,人们或许会提出质疑,难道现代大众传媒没有提供任何真实的内容吗?难道大众传媒没有任何语用学功能吗?笔者的回答是,或许其中包含了真实的内容。如果没有真实的内容的话,那么大众传媒的再生产也没有可能。然而,问题在于真假在这里已经无法区分。从表面上看,现代大众传媒与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大众传媒没有区别,但是,它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按照鲍德里亚的方式,把这种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理解为“仿真”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同样,从表面上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民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虽然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变化,但其功能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民还有各种形式的社会性联系的话,那么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性联系正在消失(27)。当人和人之间的社会性联系已然消失的时候,国家的公民就从公众转换为大众。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大众化趋势日益明显,此时的公众也可以说是“仿真的”公众。在这里,公众和大众已经难于区分了。这并不是说西方社会已经没有公众了,而是说公众在不断地大众化。 四 大众化趋势对民主制度的消解 当社会大众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时候,竞争性民主就会不断强化,而商议民主的趋势就会不断地弱化。哈贝马斯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状况的时候指出,批判的公共性受到操纵的公共性的排挤(28)。本来,在商议民主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大众传媒对于各种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从而共同地、理性地探讨社会的法律、制度、政策等。然而,今天的公共领域带有公民投票的性质(29)。这是因为,人们不再借助于大众传媒进行理性的讨论,而是争取赢得赞同、赢得“粉丝”。在这里,民主制度转变成为一种操纵舆论的竞争。我们知道,如果参与民主讨论的人们具有超越的精神,具有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卓越”特性,或者具有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交往理性”,那么这些理性的公民是不容易受到操纵的,他们会有自己的理性思考。在西方社会,大众传媒大多是私人机构,它们需要相互竞争,需要维持自身的再生产。因此,大众传媒本身已经不再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的平台,而成为赢得观众和听众的媒介。它们不再把思想交流作为自己的目的,并刻意抑制理性的讨论;它们致力于操纵舆论、操纵观众和读者,它们之间展开的更多的是争取观众的权力斗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今天的公共领域根本上具有了公民投票的性质。 从表面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民投票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民投票是一样的。然而,事实上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虽然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也有假消息,但是,那个时代的大众传媒没有像今天这样出现生产过剩。因此,在那个时代的大众传媒中,理性思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理性思考下的公民投票可以代表一定的阶级(在那个时代,阶级冲突是明显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必须操控大众,任何一个候选人要赢得选举就必须利用大众传媒来操控大众。因此,在这个时代的公民选举中,重要的不是候选人的政策主张是否经过理性的讨论,是否得到人们理性的赞同,而是他们口若悬河的演讲是否可以赢得“粉丝”。候选人的宣传不是要表达自己政策主张的正确性,而是要赢得选票,即大众的赞同。正因为如此,鲍德里亚说“普选是第一个大传媒”(30)。也就是说,普选和现代大众传媒一样,就是要操纵选民,操纵观众。普选的性质与传媒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果说大众传媒原初的目的是要传播消息,那么现代传媒已经将这一目标消解殆尽,而以传媒自身的再生产为根本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媒中所有的东西都具有无目的的目的性;或者说,传媒具有了一种审美的特性。由此,现代普选也具有了审美的特性。如果说大众传媒越来越趋向于娱乐观众的话,那么普选也越来越娱乐大众;普选成为一场政治游戏——让人愉悦的政治游戏。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大众民主制度中不存在竞争,而是说这种竞争越来越成为赢得“观众”的斗争,成为赢得大众的斗争。这种民主不是要探索恰当的社会政策,不是要谋求共同的社会福祉,而是要获得权力,它是一场权力斗争。当民主演变成为权力斗争的时候,民主的性质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当西方某些大国在全球各个角落推广其民主制度的时候,他们不是要让人们理性地讨论哪一种制度、法律、政策对自己最有益,从而对整个国家最有益,而是要夺取权力。夺取权力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大众传媒,赢得大众的支持。当民主制度演变成为一场场权力斗争的时候,灾难同时也就降临到这些国家了。在利比亚、乌克兰、叙利亚、伊拉克,这种灾难每天都在上演。我们还看到,在世界许多地区,即使按照所谓的“真民主”进行普选,权力的更替虽然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但是人民并不会因此而获益。因此,没有理性的公民,没有公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黑格尔曾经以大众传媒所出现的缺陷来为极权制度辩护。他强调说,公共领域是以主观自由为原则的(31)。也就是说,在大众舆论中,真假是难以辨别的。这就需要人们有批判意识和追求共识的客观精神。但是,黑格尔对人民颇感失望。他认为,人民在精神本质上是不受欺骗的,但是,人民会欺骗自己(32)。既然人民会欺骗自己,那么探寻真理便是“伟大人物”的事情。由此,黑格尔从公共舆论缺陷的角度来为君主制度辩护(33)。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转换视角来运用他的思想,还是有启示意义的。人民的精神当然是不会受欺骗的,他们(公众)也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本质。但是,大众会自我迷失,他们会把谬误当作真理。如果追求真理的公众沦落为大众,如果他们失去了批判和辨别的精神,那么他们就只能靠某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了。操控舆论的英雄就是他们所谓的“伟大人物”,比如某些网络“大V”,他们正是凭借操纵舆论来获得自己的权力。西方国家那些善于操控舆论的候选人也可以被视为这样所谓的“伟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社会的大众民主制度也就是确立“伟大人物”的制度。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撰写《启蒙辩证法》的理论目标之一就是要分析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他们在研究中剖析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根源,这就是工具理性的胜利。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这种胜利是“主观理性的胜利”:“所谓主观理性的胜利都归属于逻辑形式主义的实在,都以理性的直接顺从为代价。”(34)利用工具理性而取得胜利的人,犹如奥德修斯或者他的水手缺乏批判和反抗精神,只一味地顺从;他们或者捆绑了自己,或者使自己失去了听力。在笔者看来,主观理性的精神恰恰就是大众的精神,一种只有征服和被征服意义上的工具理性精神。 大众传媒本来肩负着培养公民、塑造公众,并努力使人们具有超越的理性精神的历史使命。但是,现代大众传媒却把自身的再生产作为自己的目标,它逃避使命和责任,而以吸引大众为荣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大众传媒不仅不再为民主制度奠定基础,而且正在动摇民主制度的根基。不仅如此,现代大众传媒不但没有催生出真正的民主,而且制造出诸多民主的假象。在这些假象背后所隐匿的一个无法昭然的秘密,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逐渐与“恐怖主义”的勒索联系在一起(35)。它把大众作为人质来勒索社会,从而获取自己的利益。许多网络“大V”即是如此。对此我们必须警醒起来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30页。 ②③(16)(17)(18)(21)(22)(23)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页;第29页;第14~23页;第24页;第25页;第30页;第26页;第31页。部分译文略有改动。 ④⑤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35页;第35页。 ⑥⑦转引自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295页;第295页。部分译文略有改动。 ⑧(11)(12)(13)(14)(15)(19)(20)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448页;第363~366页;第148页;第441~442页;第441页;第442页;第441页;第441页。 ⑨⑩(28)(29)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51页;第251页;第202页;第204页。部分译文略有改动。⑨中的“公众舆论”改为“公共舆论”。 (24)(34)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31页;第23页。西奥多·阿道尔诺也可译为西奥多·阿多诺。 (25)(26)阿克塞尔·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王晓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90页;第194页。 (27)参见王晓升:《社会的大众化与社会性的终结》,《哲学研究》2013年9期;《社会性的终结与现代社会理论面临的挑战》,《南国学术》2014年2期。 (30)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84页。 (31)(32)(3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332页;第333~334页;第334页。 (35)Jean Baudrillard,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y,or the End of the Social and Other Essays,Semiotext(e)and Paul Virilio,1983,p.48.标签:大众传媒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公共领域论文; 政治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正当程序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阿伦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