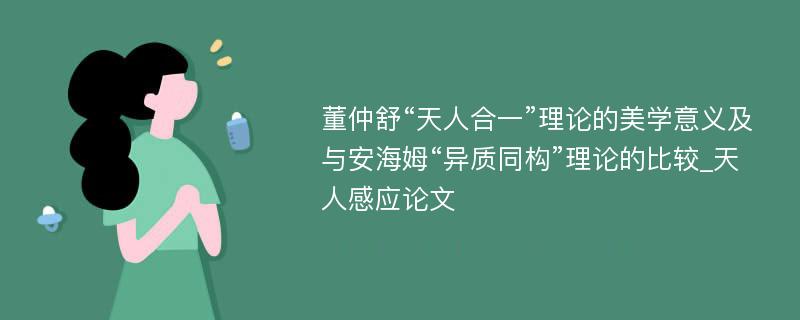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美学意义——兼与阿恩海姆“异质同构”说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同构论文,天人论文,美学论文,感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模式,它不但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同时也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命题和理论基础。“天人合一”说由来已久,从夏商时的“神人以和”始,春秋战国时的百家都有其“天人合一”说,其中最主要的是儒家倡导的道德意义上的“以天合人”说和道家倡导的生命意义上的“以人合天”说。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结合道家、阴阳家各派学说,第一次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此后,经魏晋玄学的继续发展及佛教传入后的影响,至宋明理学,便形成了体系严密,富于思辩色彩的完善的“天人合一”说。可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则为“天人合一”理论的系统化和哲理化确立了基本的理论模式,在其理论的完善化上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以阴阳五行(“天”)与伦理道德、精神情感(“人”)互相一致而彼此影响的“天人感应”作为理论轴心,系统论述了人和自然的合和关系问题。董仲舒认为,人格的天(天志、天意)是依赖自然的天(阴阳、四时、五行)来呈现自己的。具体而言,作为人的生物存在和人的社会存在如何循天意而行,顺应自然,亦即人如何与其赖以存在的客观现实规律相合一。很显然,他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动态结构的天人宇宙图式,其基本精神在于构建一种以道德伦理为基础而又超道德的人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又包含着深刻的审美意蕴,大体说来,其审美意义有如下体现:
第一,合和。“天人”关系其实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是“人”,客体是“天”。董仲舒以“天”作为宇宙人间的最高主宰,“百神之大君也”,但在他的体系中,天并非作为和主体的人相对立的存在,而是一个与其他许多因素相联系相配合的动态结构体系。在这个结构体系中,“天”一方面是整个系统的主宰,但同时又是作为系统中的一个因素,又是结构整体自身。他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注:《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正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基本模式,即不从主客二分的对立关系来探讨天人问题,而是从主客合一的整体思维来认识天人关系。同时,他也明确指出了主体的人在这样一个结构体中的地位。他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注:《春秋繁露·立元神》。)这里他肯定了人与天地同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地一起构成万物,无人则万物无以成。在强调了天人的基本模式后,他认为人和天主要在道德、生命、精神意志等方面合和为一的。
首先是道德上的合一。“天”是至上神,同时又是至善的道德化身。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以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由是可见,作为伦理的“善”,即儒家所倡导的圣人之道也正是取法于天的溥爱无私,是天布德施仁的结果。天道至仁,长养万物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并为人提供善的准则,礼义原则。他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己,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地,取仁于天而仁也。”(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意至仁,生养万物,生生不息,而人之仁德也取法于天。董仲舒在儒家的仁爱思想之上,将仁这样一种作为人的内在的善的道德标准,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人的伦理道德标准,也取法于天,也就是说,在“善”的关系上,主客体是一致的、合和的。
其次是生理构造和情感意志的合一。为了论述天人关系,董仲舒还提出了“人副天数”的主张,认为人的生理构造及情感意志都与天有相同的构成。他说:“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人生于天,所以,人的形体、德行、好恶、喜怒、哀乐等都是化天数而成的。一方面,他认为人的生理构成和天有相同的构成,他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山谷之象也。”(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为天地之精华,人贵于万物,因而人和天最相似。这样,从生理上看,人是天的副本,这里他从外在形式上将天人关系加以沟通合一。他还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和天数相参而命相连,表明了人和天不只是形式上相似,还有内在的联系。他在这里论述人与天的相似,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人能具备天的精神意志,最终达到天人相互感应。所以,另一方面,他强调人的精神意志也来源于天,与天相通,即所谓“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血气即指人的“精气”,人之有精神作用就是因为人有精气,精气是精神的生理基础。董仲舒认为,气本身即具备精神意志的属性。他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注:《春秋繁露·阴阳义》。)气具有喜怒哀乐的属性,人与天同属一气,人之气来源于天,天之喜怒哀乐之气与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是相通的。他说:“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人无夏气,何以盛养而乐生?人无冬气,何以哀死而恤丧?天无喜气,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无怒气,亦何以清而秋就杀?天无乐气,亦何以疏养而夏养长?天无哀气,亦何以激阴而冬闭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气者,合类之谓也。”(注:《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人赋有自然之气,反之天亦具有喜怒哀乐之情,二者完全是合类而相通的,也就是说天具有人的属性,同样人也具有天的属性,从本质上看,二者是和合的同类事物,所以,他强调天人乃“合类”,亦即和合一致。
这样,董仲舒从道德伦理、生理构成、情感意志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其天人合和的宇宙本体论系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董仲舒所构建的这一系统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将人类的道德、情感和外在的自然联系了起来,从而将自然人情化了,赋予了人类的理性、情感色彩。他从根本上认识到,人和自然、社会,即主体和客体可通过各种途径达到合和整一,如他说:“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他强调的合和有自然性的合一,又有道德性的合一,同时还具有情感性的合一,而这样一种合和关系,很显然就具有了审美的意义了。
对于主客体关系,康德从知、意、情三个方面来探讨,即认识性的、功利性的和审美性的关系,从这三个方面都可以达到主客体的统一;但康德认为,无论是认识性的还是功利性的关系,都因牵涉到概念或是利害关系,而不是纯粹的审美关系;只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主体的审美判断力,才因审美意象的生成,而达到主客体的合一,即在人的自由的心灵状态中通过对自然的超功利的审美观照,达到心理的愉悦,主客体的合和。董仲舒也认识到了这样一种自由的天人合和的心灵状态,他认为通过道德的、功利的合一而达到人与自然的情感的彻底交融贯通。这种合和的最高境界他称之为“与天地参”。他说:“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注:《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三者(指天地人)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注:《春秋繁露·立元神》。)只有达到天人合和的境界,人才能够自由地把握自然规律,人才能“与天地参”。而这样一种主客合和的自由境界,正是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核心所在,也是一种纯然的审美境界。
这样一种“与天地参”的合和的审美范畴,直接影响到了艺术家的创作和有关艺术理论的形成。刘勰谈“神思”:“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之并驱矣。”(注:《文心雕龙·神思》。)钟嵘论诗的本质:“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注:《诗品序》。)宗炳论山水画:“山水质有趣灵”,“山水以形媚道。”(注:《画山水序》。)清代画家石涛亦云:“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注:《画语录·山川章》。)不论是刘勰的“神思”,还是石涛的“神遇”,以及钟嵘、 宗炳论诗画, 都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在审美上的合和化一,这种最高的境界当然是“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艺术家的感悟和哲学家的思辩事实上道出一辙。董仲舒所说的“与天地参”的合和境界,既是自然的,又是道德的,更是审美的。
第二,感应。董仲舒强调“天人交感”、“同类相动”,实际上赋予天人合和以动态的内在生命精神,他的感应理论则是以“气”这一概念为基础的。
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他以天人同类证明天人合一,而以同类相动作为天人感应的重要依据。首先,他看到自然界,特别是同类事物之间可以相互感应的现象。他说:“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自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将其亡也,妖孽亦先见。物固以类相召也。”(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这就是一段很明确的审美感应的理论阐述。他认为,之所以音乐能产生共鸣,美丑亦能有相应的感受,关键是“物固以类相召”;“物以类相召”便“以类相动”,互相产生感应,原因是有“使之然者”,这其实就是有其内在的规律。其此,他用气来说明同类相动。气是先秦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董仲舒也谈气,他认为天地阴阳万物和人都是由气构成。如他说:“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所谓天德地德即是指天地以气化物,在他这里,气就是生命、精神的体现,正因为气发挥了作用,万物才会生生不息、富于生命。他说:“天地之化,春气生而百物皆出、夏气养而百物皆长,秋气杀而百物皆死,冬气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气而精,出入无形而物莫不应,实之至,君子法乎其所贵。”(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自然界季节的交替,万物的生长壮老,均是气发挥的作用。同样,他还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然则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注:《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气对于人的重要性、犹如鱼生活于水中,那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正是化育万物,滋养生命的本源。故而,人要善于养气,养正平之和气,他说:“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所以,和气正而平,是最好的气,万物生于和气,养气即养“和气”。这和他的合一理论是相通的,故而他又强调说:“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是故物生皆贵气而迎养之,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者也。”(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董仲舒的这些关于天人感应的论述几乎完全适用于审美。审美活动就是人与物之间的一种感情的交流过程。物以其形象作用于人的感官,在人的心理上引起反应,这种反应由直觉、感悟而上升到审美体验。董仲舒所强调的以气为本源的同类相动,所阐发的感应学说,事实上就包含着一种审美的动态发生过程。正因为天人是合和的,所以才会有以气相通的同类相动,在这种感应过程中,自然也包含着以情感为特征的审美感应。如他说:“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乐之至其时而欲发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时而欲出也,皆天气之然也。”(注:《春秋繁露·如天之为》。)他又强调:“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人的情感的形成完全受外界自然的影响,进而他又阐述了其中的原因。他说:“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者诸春,乐气者诸夏,怒气者诸秋,哀气者诸冬,四气之心也。”(注:《春秋繁露·阴阳尊卑》。)这就是说,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异质同构的关系,在情感上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四时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相联系的,当然人对自然的这种情感关系就是审美意义上的关系。
这一感应理论,表明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情感与外界事物的感应关系,它为审美和艺术创造提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直接影响到了后世的美学理论。刘勰提出:“春秋代序,阴阳舒惨,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徵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注:《文心雕龙·物色》。)钟嵘亦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注:《诗品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指出人对物的感应引起情感激荡,进而形诸于艺术作品。更有些理论直接就是董仲舒感应理论的直接阐发,如北宋郭熙强调“身即山川而取之”,才能感受到“山水之意度”,“春山阴云连绵,人欣欣;夏山佳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注:《林泉高致·山水训》。)沈灏《画尘》云:“山于春如庆,于夏如竞,于秋如病,于冬如定。”恽恪《殴香馆画跋》说:“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在董仲舒的理论基础上,对人和自然的情感有了更丰富、明确的认识,他们的这些论述,都可以看作是天人感应论在艺术的本质和方法上的具体应用。
第三,生命意识。中国古代美学中非常重视生命意识的体现。作为华夏古典美学理论基石之一的《周易》美学,十分强调生的形而上的意义,《系辞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序卦》也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这充满着生命精神的天地之美,构成了美的本体,而人作为天地的生成物,同样具有这种生生不息的审美精神。董仲舒系统地继承了这些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取天地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类的美直接来源于生生不息的天地之美。如前所述,他所建构的以“气”为基础的同类相动、天人感应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动态结构系统。气充溢于天地、万物、人类之间,万物包括人类因气而生,因气而变化发展,这样一个天人感应的动态过程,就是一个充满生命意味的变化不息的过程。在天人合一的感应中,是阴阳二气交感,才有生命的激荡,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注:《春秋繁露·顺命》。)
董仲舒强调生命精神,是和他的哲学理论贯通一气的。我们前面提到,他所建构的人——天的宇宙本体论,是一个以天人为核心的动态平衡结构,是一个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生命构成体;天人合和才会感应,而交感的基本方式则是气,只有生气氤氲其中,才使这一系统充满生命活力,这以人为核心的生命精神正是美学的主题。这一思想在他以后,文人多有论述,如谢赫的“六法”的核心为“气韵生动”,就是强调艺术表现出的一种生气,一种跃然欲出的生命精神。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也说:“阴阳陶蒸,万象错布。”阴阳交感,充满生命,才会有纷繁美妙的境界,乃至于生命意识成为古代美学的核心范畴。石涛说:“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光明。”(注:《画语录·絪缊章》。)山水画要写出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借以表现画家的生命精神。宗白华先生也指出:“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注:《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第四,自然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关系中的天,一方面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存在,但同时又是以具体的方式体现为不同的形象,即“天有十端”,这其中包含着不同的四时(春夏秋冬)和五行(金木水火土)构成的各种自然现象。实际上他的天人关系的基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他主要论述了因自然中的四季更替等变化引起人的情感、情绪的变化,如他所说的:“人有喜怒哀乐,犹天有春夏秋冬也。”这样,自然就形成了人对自然的审美,自然美成为人的审美对象,董仲舒说:“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注:《春秋繁露·阴阳义》。)正因为人与自然都有相通的结构秩序,运动节律,所以人从自然中也体悟到了自身的生命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情绪、情感。
中国古代的美学理论循着这一思想,形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独特的审美关系。如刘勰所说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南梁萧子显《自序》:“风动春湖,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清刘熙载也说:“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注:《艺概·赋概》。)可见,面对自然美所引起的主体心灵的激荡、领悟,而达到天人合和的境界,是华夏审美中的共识。故而在与自然美的关系中,这种脱离审美主体的感悟或心态而对纯客观自然的描摹,在中国古典艺术审美中几难觅得。
同样,受这样一种理论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形成了独特的“怀春”“悲秋”情结,并成为中国古代诗文的永久的主题。因自然季节、时序的循环变化而产生的感悟,早在《诗经》中就有,如《豳风·七月》:“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先民们对季节的变化早有认识,并赋予其审美情感,如《周南·野有死麕》:“有女怀春,吉士诱之。”魏晋以降,对自然的审美(尤其是山水诗)中,已非常成熟地加以表现了。如谢灵运的《登池上楼》即是一首典型的表现因冬去春来季节变迁给人的心态带来的影响和感悟,诗云:“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在他笔下,值此“新阳改故阴”的季节,秋冬一去而春夏来,此时“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万物一派生机,诗人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大自然给人带来的美和享受。同时,也因春夏去而秋冬来,形成了文人的悲秋情结,秋冬将至,万物萧瑟,这种景象也影响到了人的心境,引起了人的悲凉忧伤之情。晋张华的《励志》和唐姚伦的《感秋林》二诗,堪为此类情结的代表作。《励志》诗云:“大仪斡运,天回地游。四气鳞次,寒暑环周。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凉风振落,熠耀宵流。吉士思秋,实感物化。”《感秋林》诗云:“试向东林望,方悲节候殊。乱声千叶下,寒影一巢孤。不蔽秋天雁,惊飞夜月乌。霜风与春日,几度遣荣枯。”至宋欧阳修的《秋声赋》,更是这一情结的艺术化阐释。“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作者除了作了形象的描述后,又从理论上分析其内在的原因,可以看作是董仲舒关于自然审美的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董仲舒所描述的“天人感应”的合和境界,是道德的、伦理的,功利的,更是审美的。正是这样一种以“气”为内在生命,以天人合和为构成,以感应为生机的动态天人宇宙结构模式,典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许多理论范畴莫不源于此。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的模式和西方文化中的“主客二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基本上是重理性思辩,强调科学精神,但在20世纪以降,这种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受到严重挑战,许多学者试图从新的视角认识和解释艺术、美学,阿恩海姆(R.Ambeim)的“异质同构”理论就是试图从整体思维的方法来把握美和艺术,在基本理论的构成上和认识方法上,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十分接近。对于东西方这两种不同的美学范畴,我们作一简要比较。
作为当代著名的格式塔艺术心理学家,阿恩海姆研究美学和艺术,首先批判了西方文化中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理性、轻感性;重逻辑推理,轻觉判断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造成了感性与理性的分裂,知觉与思维的分裂,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直觉与抽象的分裂,所以,为了改变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及人的认识趋向,他认为在基本的理论出发点上,必须要从整体思维和整体感受来把握美和艺术。他认为,一个“格式塔”,虽说是由各种要素和部分组成,但决不是构成它的成分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建立于这种因素基础之上的全新的整体,例如一个曲调不是一串乐音的连续相加,一种心理不是感觉、理解、想象的集结等等。究其实,他的这一认识和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十分接近,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的科学的心理学的阐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同样强调作为天人系统构成的各因素之间的相配合和协调,所形成的也是一个不同于其构成因素相加的全新的格式塔,所以,在这一基本理论出发点上,阿恩海姆的认识和董仲舒的认识是相通的。
阿恩海姆在整体思维的基础上,以“异质同构”说解释艺术表现,他的“异质同构”说和董仲舒的“同类相动”的天人感应说在理论上十分接近,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作为审美对象的物与人的关系。按照阿恩海姆的“同构论”的观点,自然事物和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和人的情感发生关系,主要在于它们二者都存在着一种力的结构同形关系。自然和艺术形式之所以有了人的情感性质,是因为它们内含一种力的式样,这种力的式样则与人类情感生活中包含的力的式样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每当外部事物和艺术形式中体现的力的式样与人类某种情感生活中包含的力的式样达到同形或同构时,我们就觉得这些事物和艺术形式具有人类情感的性质。他所说的力的式样,是指人的大脑力场,他通过很多实验及分析,认为人的大脑存在着一个力场,这种大脑力场包括生物的,有机体的,物理的,神经的和精神的总体,是这种力场使人感受到了外部事物的形状及情感性。故而,正由于这种力的式样的同构性,人才对无生命的自然、艺术等无机物发生情感的同构性,人才能对无生命的自然、艺术等无机物发生情感上的关系。如他认为,一棵垂柳之所以看上去是悲哀的,原因在于垂柳枝条的形状、方向和柔软性传达出被动下垂的表现性,而这种表现性与人的悲哀的心理结构在力的式样上是同构的,所以,人才有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忧伤感,作为艺术品也莫不如此。
董仲舒的“同类相动”说则认为,人与自然之间之所以能合和感应,并具有相同的情感,原因在于人和自然在本质上的同构性;他强调“人副天数”,人不仅在外形上,而且道德、情感意志上都与自然相合,人和自然之所以能产生感应,原因在于人和自然万物都禀受了天地之气,合和的根源在于人和自然之气是相通的。同样,艺术品因具有某种生气和人内在的生命感悟相通,人也感受到了艺术之美;人对自然的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产生了情感交流,因为自然四时之气的特征和人的情感特征是相通的。这种“气”在本质上和阿恩海姆的“力场”有相近的地方,如中国文人的“怀春悲秋”情结,董仲舒认为是气在作用,而用阿恩海姆的理论来看,正因为春天万物景明,气象一新,生机勃勃所表现的力的式样,恰与人的内在的愉快、激动、昂扬等力的式样具有同构性,所以人才从春天的到来中感受到生命的勃发;同样,秋天的萧瑟、悲凄、万物枯萎的肃杀之气,也和人的内在的哀伤、悲凉的情感相通,自然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结。依照他们的阐释,人和自然、艺术的审美关系,都在于情感上的合和,董仲舒认为是阴阳二气化育的结果,而阿恩海姆则认为是力的同形同构引起的。
由此可见,作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两位理论家,阿恩海姆的“异质同构”说和董仲舒的“同类相动”说都思考着同样一个问题,即人和自然、艺术的情感关系问题。在基本思维方法上,他们是相通的,都从整体的、合和的认识方式出发(格式塔强调整体性和完整性,天人合一的核心就是合和),同时,他们都看到了人和自然、艺术形式在情感上的内在相通性,所不同的是,对于这种内在相通性,阿恩海姆建基在西方文化传统上,试图用心理学方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他的解释是具体的;而董仲舒则在中国文化传统下,试图用形而上的哲学方法来解释,他的解释是抽象的。从这一点上,恰恰可以看出中西文化本体上的差异,西方文化强调科学理性精神而中国文化更注重道德情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