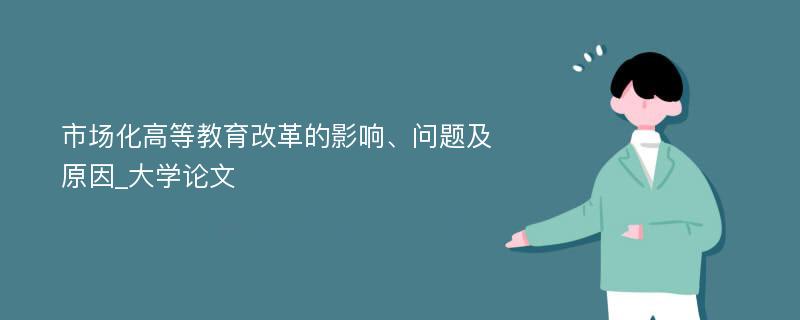
市场取向高教改革的成效、问题及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成效论文,高教论文,原因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在高等教育领域逐渐扩张其力量。欧洲高等教育研究者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高等教育的重要变化是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①;一直以市场力量协调为特征的美国高等教育,市场的触角也不断延伸;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因素开始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作用,并迅速地改变着高等教育中的各种关系。这场市场取向高等教育改革取得的成效、引发的问题及其原因,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市场取向高等教育改革的措施和成效
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同,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取向高等教育改革中却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改革的目标。
1.改变高等教育经费筹措制度,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解决政府财力有限和高等教育社会需求旺盛的矛盾,是这场市场取向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了多渠道筹资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收取学费。
20世纪80-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学费政策和资助制度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读大学生可依社会福利领取的住宿费补助(housing benefits)被取消。从1988-1989学年开始,高校学生依据其家庭经济状况交付学费。自此,英国拉开高等教育收费的序幕。美国高等教育的学费也不断上涨。从1985年到1995年,美国私立大学的学费增加了105%,私立学院增加了108%,公立大学增加了115%,公立两年制学院增加了228%。②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高等教育经费筹措制度的改革。1989年,国家从政策上肯定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制度;1992年开始较大范围地推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扩大招收自费生的比例;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更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国家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教育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1994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均对保证教育经费多渠道来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997年,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普遍“并轨”,开始全面实行收费制度。
多渠道筹措经费,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突破政府财力的局限,利用社会的力量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物质基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就是依靠社会多元筹资来实现的。撇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确实为很多在传统体制下无法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人提供了接受更高程度教育的机会,客观上提高了整个人口的文化和科学素质。
2.促使高等学校进行改革,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拨款的减少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美国各高校不得不进行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以期提高经营管理的成效。美国教育理事会(ACE)1994年对406所院校应对市场化竞争的措施进行了调查(参见表1),可以看出美国高校进行了各种改革,提高学校经营效益。
表1 美国高等学校校园发展趋势调查表(%)
所有院校 公立院校
私立院校
全面减少预算 455332
减少部分部门预算 586546
更严格控制开支808178
改组行政部门 646759
减少行政部门 343926
减少高级行政职务 293322
取消专业 404333
重组院系等学术单位435129
新建或扩大能够增加收入的专业 505149
与企业一起设计专业485149
资料来源: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Campus Trends,1994,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uly 27,1994.
我国1985年以来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也使高等学校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普遍采取各种措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一是教育教学改革,以适应社会和求学者多样化的需求。二是后勤社会化改革,以减轻学校的负担,集中有限的财力资源用于教育教学工作。三是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以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益。
3.改革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模式,提高管理的绩效。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和在公共管理领域的采用推动了这场市场取向的高等教育改革③。强调绩效是该理论的重要特征。英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这主要体现为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的改变。1988年英国的《教育改革法》中,英国政府改变了以前固定的大学拨款方式,大学拨款完全建立在学生数量的基础上。2003年英国政府发布《高等教育的未来》白皮书承诺政府继续承担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部分,但同时指出“政府需要仔细考虑研究资金管理和分配的方式,使之能够以最有效的形式发挥作用”。目前,英国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拨款是以大学在“研究评估活动”和“教学质量评估”中的成绩为依据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从原来的自我控制——资助关系逐步转变为交换关系。政府通过评估、通过结果控制来督促高校改进教学和科研,从而提高政府管理的绩效。
伴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不断改革,总的趋势是:政府角色分化,分权、放权,改变管理手段,试图还高等学校以自主权,以刺激高等学校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同时,政府改变以往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高等学校的做法,运用立法、评估、拨款、规划等多种方式,力图从微观事务中摆脱出来,从控制型向监督型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更加有效地调控高等教育,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市场取向高等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尽管市场取向的高等教育改革已显现出上述成效,也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但是这场改革并没有完全实现改革者的预期目标,出现了新问题。
1.逐利行为对高等学校的侵蚀。
(1)学校的短视和盲目行为。
当政府的财政拨款不断下降、高校不得不寻求外部资金市场的支持时,经济效用成为影响高等学校决策的重要因素,引发高校的短期、盲目行为,危及学校的长远发展。
在美国,“一所大学最为关注的两点,一是申请入学新生的众多,一是慈善基金会捐款的高额”。④办学经费的压力,使一些学校不得不降低自己高标准就读要求,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入学。曾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缺乏学术资格”而拒绝颁予其名誉学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是美国中西部一所备受学术界尊崇的学校。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坚持传统教学的高标准,四年学制中有二年是必修课,包括物理、微积分学以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艰难科目。然而,“在什么都是商业化的形势下,芝加哥大学自恃清高的立场已不可维持”,为了迁就和争取到新生,近年来芝加哥大学已在开始减少两年必修课,而以较为轻松的科目代替。同时,高校为节省开支,削减那些非实用性的学科。“削减费用(临时解雇)的可能性,也是在不同的领域里有所不同。它更可能是发生在不那么显赫的领域里,发生在被认为是远离开‘市场’的领域里——例如,在与自然科学和数学相对的教育、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取向的高等教育改革给高等学校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办学指南,市场上什么“热门”就办什么,一些专业有名无实。市场需求的波动性、变化性与人才培养的长周期性矛盾,盲目跟风造成人力物力浪费。二是利用各种机会,把教育教学服务商品化,利用各种机会创收,高校违规和不规范收费现象比较普遍。⑥三是盲目扩张,甚至举债办学,引发财政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5年底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我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在1500亿到2000亿之间。……由于贷款额数太大,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部分高校已经没有了偿还能力,甚至连利息都还不起,存在巨大贷款风险。⑦
(2)功利主义对师生价值观念的腐蚀
除了上述显性问题外,伴随市场力量侵入而来的更为严重的隐性问题,是经济利益、商场钱物交易规则对高校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价值观念的腐蚀。教育活动不仅承载着社会知识和技能的传递和生产的功能,同时也承担着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递和型塑功能。教育者的立身行事以及学校的整体文化环境是学校发挥上述功能的重要渠道。作为社会知识和文化精英阶层,高校的教师本应具有文化人的品行,具有某种超凡脱俗的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而今当高校在市场化的浪潮中行进时,市场中等价交换原则逐渐成为高校中的重要原则,教师这一传统上有些清高的文化人逐渐变为了功利的世俗人,甚至某些教师变为了纯粹的经济人,现实利益的得失成为其行为取舍的标准。
2.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不公平。
伴随市场在高等教育中作用扩大的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加剧。根据雷斯利、科林曼的研究,学费是影响求学者教育选择的一个因素;学费上涨10%,会有6.2%的中学毕业生做出不上大学的决定。⑧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以来,学费的上涨超出了一些家庭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在社会中处境不利的家庭,无力承担子女的就学费用。根据袁连生的研究,2000年,我国有7个省、自治区90%的农村居民,13个省、自治区50%的城镇居民负担不起高等教育的学费水平。⑨在我国,家庭背景已经成为影响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卢乃桂和许庆豫以父亲的职业为指标,研究了我国90年代以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参见表2)。从表中看出,本科大学生中父亲职业为农民的比例最高,为29.0%,但是农民及其相关职业的从业人口占整个从业人口的比例高达69.3%;机关干部以及企事业负责人在整个从业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2.02%,但是他们的子女在本科大学生中的比例为15%;专业技术人员在整个从业人口中的比例为5.43%,但他们的子女在本科大学生中的比例为13.5%。随着我国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强化,不同教育机会的获得意味着不同的职业地位,意味着未来不同的社会生活处境。教育机会分配中的不平等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机制,反而成为阶层凝固和复制的工具。
表2 不同职业家庭的本科大学生构成(%)
父亲职业占大学生比例 父亲职业 占大学生比例
机关干部15.0工人
17.7
专业技术人员 13.5农民
29.0
大中小学教师
7.9其他8.0
管理人员 8.9
卢乃桂、许庆豫:我国90年代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4):8。
3.教育资源争夺的加剧并未抑制权力寻租。
市场之手的优势本在于市场活动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但伴随着市场迅速侵入高等教育而来的是各种形式的腐败。由于高校之间竞争的加剧,资源占有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高校的生存和发展,资源分配权力的拥有者成为高校不敢怠慢,甚至成为高校攀附的对象;高等教育机会,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在社会成员就业、升迁中的重要性,使得高校特别是层次高的高校也成为某些社会成员不得不求助的对象。制度转型期的各种政策及监管制度的不完善,滋生出高等教育中的各种腐败现象。更令人担忧的是高等教育领域中腐败现象的普遍化、组织化。如2001年,上海某高校方开列的一份供内部讨论的招生参考名单中,一些考生背后都有委托人。“令人担心的不仅是在高校招生中有人‘递条子’‘接条子’,而是这些条子被学校堂而皇之地记录下来,并列成一张表供内部讨论,把不正常的、与高校招生规则相悖的现象‘制度化’。”⑩康宁博士曾在其博士论文中,分析了我国当前在课题申报、评估中的“跑评”现象,一些学术骨干疲于奔命地往返于政府与学校之间,无法安心教学和科研,还滋生出一批专事评估和评审的专家来。(11)在各个高校竞争激烈的情景中,某些权力部门手中的权力对各个高校来说比原有体制下显得更重要,能否得到政府的重点资助,能否申报到课题,能否发表数量多的科研成果,直接关系到高校的生存处境。
三、市场取向高等教育改革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
1.市场本身的固有缺陷。
(1)“经济人”的市场活动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极力主张通过“市场之手”来配置资源的古典经济学,其理论主张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那就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是追求私利的“理性经济人”。该理论学派认为追求私利的微观主体在一种无形力量的作用下会自动地促进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即使他在追求自己的私利,也会比他从公益角度出发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2)然而古典经济学的主张中存在着无法验证的假设,“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会引导市场活动主体在追求私利时自动促进社会公益的实现,斯密没有证明,自1776年以来,任何经济学家都没有证明过。”(13)新古典经济学也从市场活动主体是经济人的假设出发,认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基本动力驱动下,只要存在完全的竞争,借助价格的调节作用,市场可以出现均衡的状态,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该理论也提出了“完全竞争的市场”的四个假设:第一,市场上有无数的买者和卖者,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价格没有任何控制的力量;第二,同一行业中的每一个厂商生产的产品是完全无差别的,即产品是同质的;第三,厂商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是完全自由的;第四,市场中每一个买者和卖者都掌握着与自己的经济决策有关的商品和市场的全部信息。(14)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上述两种认为只有市场配置资源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理论仅仅是一种假设,市场调节社会生产有其优势,也有其局限。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使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神话”市场之力的危害。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经济人存在追求私利最大化的本性,才导致了当前我国市场取向高等教育改革中的诸多弊端。高等教育消费者要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在社会用人制度学历主义盛行时,他们必然过于关注高校颁发的学历的高低;高校面对官方的、非官方的各种量化的评估和排名,为保住自己的社会声誉,实现自己的利益,办学的注意力不得不转向短期见效、看得见拿得出的体现所谓“办学实力”的工作上,忙于学校升格,忙于上多而全的专业,忙于跑硕士点、博士点,忙于引进各种人才,哪怕引入的人才只是名单上的在岗人员;高校教师随着校内分配制度和职称评审制度的变更而调整着自己的工作重点,教师们忙着跑课题、忙着出科研成果。上述现象,我们本不应为怪的,因为这些在高等教育市场中活动的主体本性就是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
(2)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不可避免性。
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的第四个条件——即市场活动中买卖双方对商品信息占有的充分、对等——是在所有的市场中都不存在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因为他们对市场活动中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阿克洛夫在其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的论文中,阐述了因为旧车市场中买卖双方在旧车质量信息占有上的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由于逆向选择的存在,不仅市场通过供求机制总会在一定价位上促成买卖双方成交的理论不成立了,而且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市场通过优胜劣汰来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优的目标也无法实现。
高等教育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在求学者对高校办学信息的不完全了解上,也表现在高校毕业生对就业市场信息以及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信息的不完全了解上,完全的市场调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失灵。
2.高等教育属性决定了市场的非完全适切性。
高等教育的属性决定了其活动不可以像企业一样完全实现市场化的运作。
首先,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市场的供求,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而高等教育服务的价格无法准确确定,主要是因为我们无法完全客观、准确地判定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的高低。人们往往以高校培养的学生质量的高低来推断某所高校教育服务质量的高低。姑且不说学生质量的高低也是无法做出完全客观、正确判断的,即使可以做出这种评判,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双主体互动合作的过程,学生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于高等教育服务提供方——高校的办学条件,更取决于作为高等教育服务消费方——学生原有的基础、先天的资质、后天的投入。单凭培养的学生质量高就说高校的教育服务质量高是难以成立的。现实中,高校中学费高的专业并不意味着此专业提供的教育教学质量高。众所周知,在市场中商品的价格既决定于其质量,也决定于社会的供需状况,同质量的商品在不同的时段价格不同,甚至商品质量改进了而价格却下滑了。某专业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紧俏,可能完全是因为这类毕业生供给的相对稀缺,而并不是因为这类毕业生质量就比其他类毕业生质量高。所以,在高校中高等教育服务的真实价值无法完全获知,价格也就无法准确反映高等教育服务的价值。退一步说,即使高等教育服务的价格可以客观、真实地确定,也不能听凭价格机制来调节高等教育的需求,如此必然带来的不是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是资源的巨大浪费。
其次,市场中的企业是按照“投入—产出”追求利润最大化思路来运行的,而学校组织则不可以营利为目的。学校作为育人机构,其工作无法进行准确的投入—产出计算。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任务,也不允许高校以可以计量的经济收益来调整自己的生产计划。
可见,市场力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引入,增强了市场活动主体的竞争意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益。但市场本身固有的缺陷和高等教育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市场在高等教育领域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如果神化市场的力量,把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适当应用演变为“高等教育的市场化”,那将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灾难性损害。
注释:
①③玛丽·亨克尔和布瑞·达里特主编,谷贤林主译:《国家、高等教育与市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②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1995 (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table 306.
④白雪:《美国大学学府的变质》,《世界教育信息》1999年第4期。
⑤Sheila Slaughter.Retrenchment in the 1980s:the Politics and Prestige of Gender.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64(1993):250~282.
⑥国家审计署:《北大清华等18所高校不规范收费8个多亿》,http://news.sohu.com/20060329/n242528532.shtml
⑦邬大光、陈枭鹰:《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盘点》,《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⑧转引自张民选:《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⑨袁连生:《我国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年第3期。
⑩周春红:《净土不净:高校领域腐败现象透视》,《中国监察》2003年第15期。
(11)康宁:《中国经济转型中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1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页。
(13)P.A.Samuelson.W.D.Nordhaus,Microeconomics.New York:McGrow-Hill Book Company,1989:405.
(14)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