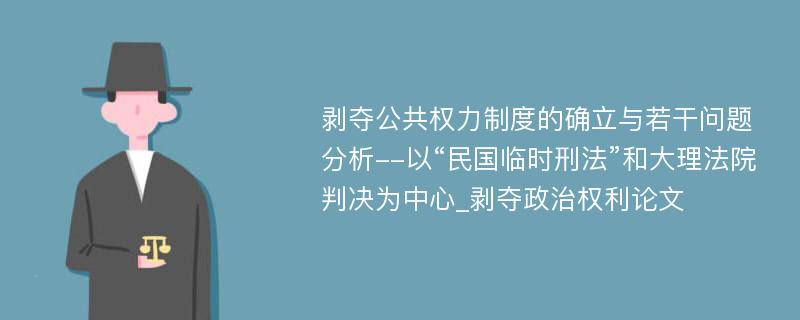
褫夺公权的设立及若干问题探析——以《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和《大理院判决录》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权论文,大理论文,刑律论文,探析论文,中华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6.7
文献标识码:A
一、褫夺公权刑罚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资格刑在中国法制史上由来已久,早在周朝资格刑的适用便有了明确的记载。《周礼·秋官·司圜》:“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礼记·王制》:“不帅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其中“不齿”的含义即是比平民在身份地位上低贱,不可与之相比拟的意思,作为一种资格刑最核心的含义即是不得为官。除“不齿”外,我国古代的“收奴”、“夺爵”、“禁锢”、“除免”、“废”、“逐”等刑罚都作为资格刑真实存在过。
作为一种资格刑,褫夺公权的称谓最早出现在清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公布的《大清新刑律》中。《大清新刑律》由沈家本和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拟定,因此深受德日刑法理论的影响,它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刑名和刑罚体系,将刑罚分为主刑与从刑两种,其中从刑包括褫夺公权和没收。
民国初年,时局未定,因此在立法上基本沿用了清末变法修律的一些现成成果。在刑事法律方面,援用了经过删修的《大清新刑律》,更名为《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以下简称《暂行新刑律》),直至1928年3月《中华民国刑法》颁布,这部《暂行新刑律》使用了十七年。其中,《大清新刑律》中褫夺公权的内容被《暂行新刑律》完全沿用。
《暂行新刑律》中褫夺公权的规定如下:
第三十七条:刑分为主刑及从刑……从刑的种类如左:第一,褫夺公权;第二,没收。
第四十六条:褫夺公权者终身夺其左列资格之全部或一部:(一)为官之资格;(二)为选举人之资格;(三)膺勋章之资格;(四)入军籍之资格;(五)为学堂监督职员教习之资格;(六)为律师之资格。
第四十七条:于分则有得褫夺公权之规定者,得褫夺现在之地位或于一定期限内褫夺前条所列资格之全部或一部,但以应科徒刑以上之刑者为限。
二、褫夺公权适用的若干问题——《大理院判决录》所载案例中的疑惑
本文选取民国二年《大理院判决录》中的几个典型判决,并且碍于篇幅只选取足以说明问题的主文部分。
判决一:大理院刑事判决二年上字第四号
主文
原判撤销
陈显瑯强取之所为处三等有期徒刑三年,终身褫夺公权全部。
判决二:大理院刑事判决二年上字第六号
主文
原判撤销
官知文略诱共犯之所为,处三等有期徒刑三年,窃盗之所为处五等有期徒刑二月,应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又一月。其未判决期内羁押之日数,以二日抵徒刑一日折合计算。并褫夺全部公权六年。
判决三:大理院刑事判决二年上字第十一号
主文
原判撤销
郑海、郑阚氏各诱共犯之所为均予免诉。
郑海杀人共犯之所为处死刑。
郑阚氏杀人共犯之所为处无期徒刑。
判决四:大理院刑事判决二年上字第十号
主文
原判撤销
程喜元杀人之所为处死刑,强取财物之所为处无期徒刑,应执行死刑,终身褫夺公权全部。绸缎褂、缎坎肩各一件,绉腰巾二条没收之。
王开山、赵清奎回复第一审原判之效力。
判决五:大理院刑事判决二年非字第四号
主文
原判撤销
袁冲祥强盗共犯之所为处无期徒刑,终身褫夺公权全部。
判决六:民国八年上字第二一八号
主文
原判及第一审判决均撤销。
洪述祖教唆杀人之所为处死刑,褫夺全部公权三十年。
通过上述判决主文,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即:通常法史学人泛泛地认为褫夺公权就是如今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比如通过判决二就看不出二者区别何在。但是,民国初年的褫夺公权与当今的剥夺政治权利确有诸多不同之处,即本文所提疑问之所在。首先,判决一中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为何被终身褫夺公权?其次,判决三,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为什么判决中没有明确附加褫夺公权?最后,在无期徒刑和死刑判决中,为什么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刑罚的有些案例规定终身褫夺,有些案例规定有期限褫夺?
这些问题说明:虽然褫夺公权制度被视为剥夺政治权利制度的前身,但套用当今剥夺政治权利理论无法完全解释褫夺公权制度,褫夺公权在设立之初必然有着法理上和现实中特殊的考量。
三、问题背后的法理
1.为什么主刑是有期徒刑,附加褫夺公权可以是终身褫夺?
以《暂行新刑律》第三十二章“窃盗及强盗罪”为例,第三百六十八条至第三百七十六条必须褫夺公权,其余实质性规定只剩第三百六十七条和第三百七十七条,相比之下,在犯罪的情节和危害性上,第三百六十七条和第三百七十七条比其余九条要轻一些。因此,可以判断判有期徒刑而附加褫夺公权终身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终身褫夺公权这种方式,使得一些具有较大潜在社会危害可能性的人,在有期徒刑执行完毕之后仍然不能像普通人一样享有行为上完全的自由,而是要有所节制,防止其再次犯罪。
这种对有严重罪行的罪犯终身施以资格刑的做法也源自传统的法律观念。春秋时便有“终身不齿”之说,至秦称为“藉门”,非但罪犯本人终身不可以为官,就连其亲属也在不予录用之列。这种做法不免有滥刑之虞,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刑法预防功能的价值追求。这种利弊并存的刑罚制度及其背后的法律文化观念直接而深远地影响至民国初年。
2.为什么有的无期徒刑、死刑判决中不附加褫夺公权终身,而有的判决中又会附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以下四项权利:(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按照当今刑法理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罪犯必须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内在逻辑在于:如果罪犯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即是对罪犯政治人格的彻底否定,条文中第(1)(3)(4)项权利和“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对被施以生命刑的犯罪分子而言其自然不可能行使,但“言论、出版”的权利却可以在其死后由他人代为行使,因此,死刑犯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目的在于禁止其死后载有其思想的言论、文字被公开表达。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徒刑执行期间为终身,在徒刑执行期间当然被剥夺政治权利,因此在判决中写明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似乎多余,但是,无期徒刑存在被减刑为有期徒刑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最初判决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在减刑时就需要重新启动审判程序做出有期限剥夺政治权利的判决,这样在程序上逻辑不通,而且会增加司法成本。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情况在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时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而民国时候对于褫夺公权的认识是不同于当代的,作为一种从刑,褫夺公权最早被引入中国刑法典是在清末,因此时人对这样一种刑罚的认识比较模糊也在情理之中。当时的一种观点认为:“……然则对于受死刑或无期徒刑之宣告者,宣告褫夺公权,有何实益?……有谓死刑,为绝人生命之刑罚,生命既绝,公权无所依附;无期徒刑,系狱终身,当然不能享有公权,对此宣告褫夺公权,殊堪实益者。”[1]然而这仅仅是一部分学者或者法官的认识,有的无期徒刑和死刑判决中又附加了“终身褫夺全部公权”,对于这样两种矛盾的情形没有资料可以提供确实的答案,只能推测在一个新的制度建立之初,特别是从外国引入的新制度,人们对于它的认识肯定存在模糊之处,这个例子可以看做是立法上的不明确,导致了司法实践之中基于法官的不同认识产生了不同的判决结果。
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我们依然无法据此断言死刑和无期徒刑不附加终身褫夺公权单纯是认识上的模糊所致,立法者有意为之的可能性并不能被彻底排除。在法无明文规定即为许可的通行法理之下,被判处上述两种刑罚的罪犯,只要未被褫夺公权,一旦减刑出狱其各项公权自动恢复,鉴于褫夺公权标准的模糊性,也许有些犯罪人即使被判处极刑,立法者依然认为没有褫夺公权的必要也未可知。或许这就是有些案例中附加“终身褫夺全部公权”的原因,然而也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
3.为什么有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判决中,褫夺公权是有期限的?
从文本出发,就是这类判决所依据的分则条文中规定的是“得褫夺公权”,法官便有权裁量决定是否褫夺且夺权必有期限。这仅仅是表面的解释,背后的立法原意很难猜度,我们还是要从时人的只言片语中进行推测。而时人对此也是持有不同态度的,从对《中华民国刑法》褫夺公权的评论可见一斑。
“有谓对于受死刑无期徒刑宣告之人,可以为褫夺公权之宣告,惟此项宣告,仅以无期褫夺为限,不能想象其有所谓有期褫夺,所以我刑法规定宣告死刑或无期徒刑,其褫夺公权,必为无期者。”[2]
“余以为名誉刑之趣旨,在于剥夺犯罪人之荣誉,加之以耻辱,自剥夺其荣誉加以耻辱之一点言之,是褫夺公权,当然不以受有期徒刑宣告之犯人为限,观刑法对于处死刑与无期徒刑之犯罪,而犹有得褫夺公权之规定(例如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以及第五十七条,明定‘宣告死刑或无期徒刑,得褫夺公权’者,即足以证明。惟刑法中有假释赦免之条,倘受死刑、无期徒刑宣告之人,遇此类事由发生,则有期褫夺,又何尝无实益,我刑法仅规定‘宣告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其褫夺公权为无期’云云,是不可谓非立法上之失当也!”[3]
从上述两种观点来看,对于这一问题即使是在当时也没有明确的官方说法,后者确实道出了前者没有考虑到的情况。其一,这种情况的出现源自法律的明文规定,所以“其褫夺公权,必为无期者”的结论与法律文本冲突;其二,在缓刑和赦免的情况下,有期褫夺确实更加有利于刑罚适当性的实现。但是后者也存在一定缺陷,即对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和终身被执行无期徒刑的罪犯而言,似乎又陷入到前一个问题的矛盾之中。而这一争议之处似乎又可以为上一问题中“有些犯罪人即使被判处极刑,立法者依然认为没有褫夺公权的必要”这一可能性提供具备一定说服力的证明。
4.假释、赦免与无期徒刑、死刑中的褫夺公权期限
《暂行新刑律》第六十六条规定了假释:“受徒刑之执行而有悛悔实据者,无期徒刑于十年之后,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由监狱官申达法部得许假释出狱,但有期徒刑之执行未满三年者不在此限。”
假释是指对于被判处徒刑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一定时间后,根据其表现予以附条件提前释放,如顺利经过考验期则视为刑罚已执行完毕。宏观来讲这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秦瑞玠《暂行新刑律释义》中有对假释的释义:
“自古拘禁人于监狱,谓欲以痛苦惩戒其人,近时则以自由刑之执行,为使犯人得以悔过迁善。刑罚本为一种手段,而非以此为目的。故在刑法执行之时,倘其人既有改悔之情状,无必须对其认为刑之执行,得限刑期中满一定期间后,假许出狱。此深合刑事政策之宗旨。一以使受刑者挟前途之希望,乐于改过自新。一以使受刑者试为狱外之生活,也为确定放免后生计上之准备。用意至善。”
由此可见,假释的用意即在给与确有悔改表现的犯罪分子以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而这种机会的给与对象并不只限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还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褫夺公权的执行是在主刑执行完毕之后开始计算时间的,依据上文《暂行新刑律》中所默许的法意是无期徒刑如果被执行未被假释,则刑罚执行期间犯罪分子的公权当然不能行使;但是当假释出现时,没有褫夺公权可以随之更改的规定,这样一来尽管有悔改表现的犯罪分子得到了一定的自由,但还是终身不能在公权方面享有完整的人格,对其重新融入社会还是制造了一定的隔阂,与立法原意相悖。因此,无期徒刑被假释的情况下,确实需要褫夺公权有明确的期限。
《暂行新刑律》第六十八条规定了赦免:“赦免依赦免条款临时分别行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十四条:“临时大总统得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
秦瑞玠《暂行新刑律释义》中有对赦免的释义:“日本于宪法第十六条,明定天皇命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是即恩赦之制。大赦者,对于某种之罪,消灭其审判之效力,不但消灭其刑之执行权,故虽犯人死亡后,亦仍得有湔雪之利益。特赦者,对于一定之人,免除其刑罚之全部执行,而判决之效力自在。其免除刑之一部执行者,则为减刑,此属于特赦之一种。复权者,谓回复已被褫夺之公权,对于从刑而言之者也。大赦与特赦、减刑之区别:其一、大赦不必由官吏奏请。其二、特赦、减刑,只限判决后刑之消灭前,且只免其刑之执行,而不能消灭其所判决之罪。大赦不然。其三、大赦当然复权。且以后亦不得作为再犯之基础。”
可见大赦时,既免罪又免罚,所以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并附加终身褫夺公权的人在大赦时公权自动恢复;特赦只免罚而不免罪,免除全部刑罚自然包括免除褫夺公权。但是减刑只减部分刑罚的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被判处终身褫夺公权的人同样面临着不能充分享有赦免恩惠的问题。虽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提到了复权的问题,但是没有刑法条文对于复权的程序做出详细规定。
时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今法律规定有期公权之期限,自主刑执行完毕,或免除之日起算,这就是说被褫夺公权的犯人,一出监即当受社会的摈斥,须知目前社会常歧视出监囚犯而摒弃他的行为,若再加以法律之摈斥,则出监囚犯自新机会之缺乏不言可知,其结果未免自暴自弃,而有再入歧途的极大的可能性,岂非违背‘感化’之本旨?故出监人社会之囚犯,不当再科以名誉之刑而绝其自新之路,惟有些人们在某种职业或事业上屡有不名誉,不信用,破廉耻行为,不易立刻改化,则当使改变环境,暂时禁止其有某种资格,至其有改化成效时,立刻恢复。”[4]
四、《中华民国刑法》对“褫夺公权”问题的修正
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总则中涉及褫夺公权的有如下几条:
第五十条:从刑之种类如下:
其一,褫夺公权。
其二,没收。
第五十六条:褫夺公权者,褫夺下列资格:一、为公务员之资格;二、依法律所定之中央及地方选举为选举人及被选举人之资格;三、入军籍之资格;四、为官立、公立学校职员、教员之资格;五、为律师之资格。
第五十七条:褫夺公权分为无期及有期。有期褫夺公权,以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为限。宣告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其褫夺公权为无期。宣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其褫夺公权为无期或有期。宣告六月以上十年未满有期徒刑者,其褫夺公权,不得逾十年。
第五十八条:宣告六月未满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者,不得褫夺公权。因过失犯罪者,不得褫夺公权。
第五十九条:褫夺公权,于裁判时并宣告之。褫夺公权,于裁判确定时发生效力。但有期褫夺公权之期限,自主刑执行完毕或免除之日起算。
《中华民国刑法》相对于《暂行新刑律》而言,在褫夺公权问题上有了较大的改变。其一,没有了法定褫夺与裁量褫夺之分,而是仅有裁量褫夺,没有绝对的法定褫夺。其二,“膺勋章之资格”从褫夺公权条款中删除。其三,废除一部褫夺,凡是褫夺公权,都是褫夺第五十六条所列全部权利。其四,无期徒刑和死刑必须终身褫夺公权。其五,增加主刑免除之后褫夺公权开始执行之规定。
《中华民国刑法》对“褫夺公权”条款的修正使得这一从刑在司法适用上大大简化了,法官无需再对褫夺哪一部分还是全部公权进行裁量,在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时附加终身褫夺公权也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暂行新刑律》中褫夺公权相关问题并没有因《中华民国刑法》的修正而完全消解。例如,既然删除了“膺勋章之资格”这样死后仍可能享有的权利的条款,在判处死刑时附加褫夺公权终身似乎多此一举;再如,在判处有期徒刑的情况下附加终身褫夺公权的条款依然存在。缓刑、假释情况下如何执行褫夺公权和复权问题仍然没有明文规定。另外,以概括制取代选择制的褫夺方式可能出现滥用刑罚的情况,难以充分实现刑法的改造功能。
总之,有关褫夺公权的立法、司法实践,根源于当时褫夺公权理论的发展程度和时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此后的《中华民国刑法》和其他刑法典对褫夺公权和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多有损益,皆源自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褫夺公权制度在不断的争议中日趋完善,为当代剥夺政治权利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宝贵的立法及实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