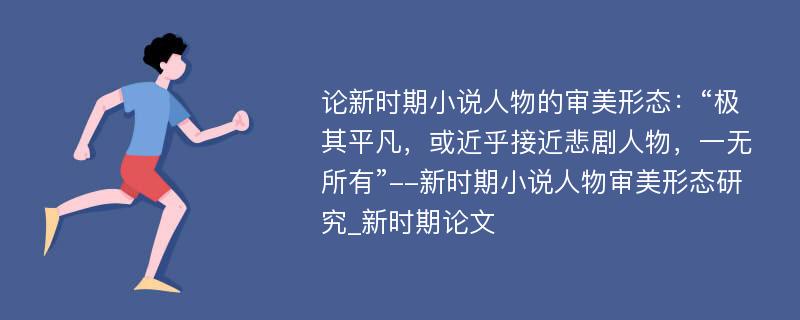
“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新时期”小说人物形象的美感形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美感论文,形态论文,人物形象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13(2002)03-0065-06
一
文学的审美把握方式,包括文学形象的美学与美感形态,既同作家的生存观与美学观 念相关联,也同生活的经验特征有深层的联系。英雄悲剧这一强烈的悲剧美感形态,固 然同新时期作家高扬的人文热情和积极地干预生活的责任感相关,但重要的还是因为生 活中出现了大善大恶、大忠大奸、大美大丑等强烈的对比与冲突的事物。特别是经历了 “文革”这样重大的民族性的创伤性事件,社会在倒退、是非被颠倒、人性遭扭曲,真 善美招致假恶丑的强奸、践踏与破坏,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提,在鲜明、强烈的反衬下, 才有被评论家称为“高尚的圣者与殉道者”、“一尊溢光流彩的铜像”[1]的悲剧英雄 李铜钟的出现。英雄悲剧常常是社会剧烈变动的产物,是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思想矛 盾和情感矛盾严重冲突的结果,是矛盾的双方在不可调和的状态下相互撞击而迸现的灼 目的火花。英雄悲剧,是一种产生于特殊生活状态具有强烈美感的悲剧类型。
但是生活并不永远或经常地呈现为它的反常状态。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更多的时候表 现为非对抗性,并非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而是具有舒缓的性质与状态。就是说,对 于所有真诚、严肃、不肯在假丑恶面前屈服、妥协的人们来说,应该看到生活中大智大 勇、大善大美的英雄遭受毁灭的悲剧,也应该看到不公平、不合理、不理想、不完美带 给普通人的摧残、打击与伤害,这或许是更普通的“平常的”悲剧。狄德罗、拉辛等人 在欧洲中世纪之后,阶级矛盾相对和缓、社会生活相对平静的时候大力提倡市民悲剧, 主张写作以家庭的不幸事件为主题以及大众的灾难为主题的悲剧,这是明智的、适时的 、有道理的。鲁迅曾经说:“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 ,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2](P293),也是真灼地看到了描写“极平常 的”悲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文革”这样重大的民族悲剧和巨大的历史曲折中,出 现了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为真理为人民誓死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英雄, 他们的死是一曲激越高亢的悲歌。而更多的人是在默默之中忍受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的人生苦痛,有的人甚至是在被蒙蔽的情况下既伤害了别人又葬送了自己,他们的悲剧 则是一种欲哭无泪的凄凉与悲怆。作为审美的再现与艺术的把握,新时期的“伤痕小说 ”与“反思小说”中产生了两种美感形象。一种是像李铜钟、罗群(《天云山传奇》)、 王公伯(《神圣的使命》)、葛瓴(《大墙下的红玉兰》)、彭其(《将军吟》)等奋起抗争 的铮铮硬汉和悲剧英雄。另一种则是像王晓华(《伤痕》)、许灵均(《灵与肉》)、钟亦 诚(《布礼》)、冯睛岚(《天云山传奇》)、海云(《蝴蝶》)、李顺大(《李顺大造屋》) 、许秀云(《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胡玉音(《芙蓉镇》)、吴仲义(《啊!》)等众多“ 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普通的“极平常的悲剧者”。
恩格斯从历史辩证法的高度理解悲剧的实质,把悲剧定义为“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 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3](P346),如果不把“历史的必然要求” 作过分狭窄的理解的话,它既应该包括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站在时代前列、推动时代发 展、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人物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也应该内在地包括普通人合 理的生活愿望,对未来正当的期许,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权利等等。换句话说,“历史的 必然要求”应该包括对真善美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合理憧憬与实践行为。所以鲁迅通 俗地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4](P297)。因此,与其把悲剧 的实质看做一种冲突,不如宽泛地看做是一种“否定”,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否定。 因为有些悲剧并不表现为有形的冲突。悲剧者不是表现为对否定性力量的主动性的挑战 或应战,而是被动地出乎意料地受伤害。这种悲剧虽然由于悲剧者力量的弱小、被动, 弱化了冲突的激烈程度,甚至是改变了悲剧的性质(假丑恶成为强势的压倒性力量),但 也正是这种反常、扭曲与颠倒才暴露了加害者、否定性力量的专制、暴戾、反动,显示 出悲剧者的弱小和无辜,使悲剧具有一种令人恐惧的压抑和沉重。以悲剧者的地位与性 质而言,悲剧者越是主动、强悍,冲突就会更加激烈,悲剧美感效果就更加鲜明、强烈 ,而且在道德和文化等形态上越发凸现“正义”的地位,从而奠定它歌颂性的基调。同 它相比,这种弱小者、被动者、无辜者的悲剧的主要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批判性的。
二
在“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等小说思潮中出现的众多的“被污辱与被损害者”、 “无辜者”的悲剧形象,在冲突的性质、美感特征、价值形态等方面都同“十七年”文 学中和新时期文学初期出现的悲剧英雄标示出明显的不同。
就悲剧产生的原因及悲剧冲突的性质与特征而言,“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中的 众多悲剧的产生,既不是由于神秘莫测而又宿命的“命运”,也不是由于悲剧形象的个 人“过失”,甚至也不来自敌对阶级的凶恶与强大,而是来自国家、民族、政权内部的 “精神病变”,加害者、攻讦者可能来自人民内部,来自于一向所信赖的组织、团体、 战友甚至来自受害者的亲人。这一异化的悲剧力量是强大的、无形的,甚至也是宿命的 ,而且常常是以“正义的”、“革命的”名义冠冕堂皇地进行迫害行为。这种悲剧根源 的特殊性,使悲剧冲突的性质与特征具有同样的独特性。
首先,悲剧力量强大而无形,受害者弱小而被动,灾难与悲剧的降临常常是出人意料 的,有时甚至具有几分荒诞无稽的色彩。即表面上看并不具有发生的必然性,导致主人 公命运发展结局的,常常找不到具体的代表人物,找不到具体的对立面;冲突大都没有 那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具有有冤无处诉,有悲无处发 ,有愤无处泄,欲辩无言、欲哭无泪的悲哀气氛。王晓华以“革命”的名义同家庭划清 界线,为表示立场的坚定,有家不归;等到她噩梦既醒,母亲已长眠地下,面对亲人的 骨灰和遗容,她的悲痛向谁申诉?对李顺大、赵镢头、许茂、许秀云、许灵均、钟亦诚 、冯晴岚、吴仲义这些农民与知识分子的悲剧形象,这些被污辱被损害的小人物来说, 谁是他们具体的敌人、仇人呢?没有,或者一时说不清楚。但是他们的悲剧命运又是那 样宿命地无法躲避,让人感到揪心的痛苦。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悲剧或许具有偶然性, 找不到具体的敌人、对立面,但他们生活在一个荒诞不经、是非颠倒的时代,因此他们 的悲剧又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这些悲剧形象是以审美的方式对一个扭曲的、荒诞的 时代的控诉与否定。
其次,悲剧冲突由外部转向内心,由行为转向灵魂,心灵的受审成为这些悲剧人物的 一般特征。就这一点而言,它明显地不同于古希腊的悲剧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文学中 的悲壮而欢乐的英雄形象——他们向来是以外在矛盾冲突的尖锐激烈,英雄外部行为的 大刀阔斧、果敢坚决,来显现精神的神圣,性格的强度,美感形态上的热烈、悲壮的; 倒是同中世纪后期与文艺复兴前期如但丁《神曲》中的法朗赛斯加和保罗以及莎士比亚 戏剧中的某些悲剧形象哈姆莱特、麦克白等在形象特征和美感特征上有些类似,即他们 都以巨大的心理张力表现出灵魂受难、受审时的矛盾状态,悲剧结局主要不是表现为行 为的悲壮,像普罗米修斯、江姐、李铜钟表现的那样,而是呈现为灵魂的深苦。如新时 期小说创作中较早出现的悲剧形象许茂老汉就颇能说明问题。在50年代初,他性格开朗 ,热心集体事业,是农业合作化的积极分子,但50年代后期以来颠三倒四的政治运动严 重地打击和扭曲了他的思想与性格,灵魂屡受创伤,于是他变得沉默、古怪、孤僻、自 私。他常常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想心事,一天难得说上几句话。许茂的悲剧在于他不由自 主地走上了一条违背自己心意的道路:他不能不自私,可又常常为自私而痛苦。这种心 灵深处的矛盾,使他陷入了深深的、令人心酸的忧郁。这种忧郁,人们在李顺大、“漏 斗户”主陈奂生、张铁匠、赵镢头等农民形象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而在许灵均、钟 亦诚、吴仲义等知识分子形象身上,还看到了比忧郁还要令人痛苦的灵魂的无所归依和 张皇失措。灵魂的受苦与受审,是人在现实中的受虐引起的,是人的非人化在文学与审 美中的客观反映。所以,这种同中世纪后期与文艺复兴前期的悲剧形象在美感形态上的 相似性,绝不是偶然出现的,他们都有“人的丧失”这一大的人文背景作为前提。而在 审美上对这些形象进行悲剧性的、心灵化的把握与处理,恰恰表现出对那种“非人”文 化的超越与否定,是人文精神高涨的产物,是在文化上进行人的拯救、人的启蒙的人道 主义精神高扬的必然结果。“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中的大量“极平常的悲剧者” 、“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小人物的悲剧的美感特征与价值形态,也同悲剧英雄标划出明 显的分野。首先,这些悲剧形象不是或主要不是表现为崇高、悲壮等激励性的高昂的美 感特征,而是表现为悲惨、悲苦等压抑性的审美感受。就美感效果而言,主要不是激情 澎湃之后的“净化”与撞击式的动感激励,而是在情感压抑状态下的深沉的反思。朱光 潜在论述到悲剧感同崇高感的相似性时,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两者在体积上或在 强力上超乎寻常。悲剧主角往往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无论善恶都超出一般水平,他的激 情和意志都具有可怕的力量。(二)两者都以宏大、壮观使人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渺小。( 三)两者最终都产生激励和鼓舞等积极的情绪。用这种归纳去验证周文雍、陈铁军、江 姐、刘胡兰、李铜钟等这些悲剧英雄庶几是合适的、准确的,但是就人们对许茂、李顺 大、陈奂生、许灵均、吴仲义、钟亦诚等形象的真实的审美感受而言,却很难将他们的 悲剧、他们的悲剧美感同崇高感相联系。他们不是“非凡的人物”,也没有超出常人的 激情与意志,而是普通的农民或知识分子,是我们身边的人或同我们一样的人,给人以 切近感、平常感,而不是威压感或渺小感;而产生的美感效应与其说是“激励与鼓舞” ,还不如说是压抑和沉重。从价值形态上说,这些悲剧美感形象当然不会把人们导向悲 观主义。但它引起的主要是深切的、理性的、道德的、人性的省察与政治和历史主义的 反思与批判,它在时间上是反向的、回忆性的,而不像“十七年”文学中崇高的悲剧英 雄是一种未来的精神召唤和乌托邦憧憬。其次-这些“极平常的悲剧者”、“受侮辱与 受损害”的小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中还渗进明显的喜剧因素,在形象的审美形态上具有显 著的悲喜剧色彩。从陈奂生、吴仲义、李顺大等形象身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可怜的喜剧 素质,引出的是鲁迅所称的“含泪的笑”的美感效果。“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 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4]“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中 的这些“极平常的悲剧者”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在突如其 来的灾难与困厄面前甚至没有表现出临危不惧、誓死抗争、从容洒脱的英雄气概与刚毅 的精神,但他们的遭难仍然表现出“人”的受辱,“美”的受挫,“有价值的东西”的 遭破坏、被毁灭,从而成为货真价实的悲剧。但是这些形象在逆境中当肉体与心灵遭受 考验时,表现出软弱、奴性十足、依附、乞怜甚至卑怯等的无价值的东西。陈奂生在县 委书记面前表现出的人格的低萎与奴性,在住了五元钱一夜的招待所感到吃了亏之后所 表现出的可怜可笑的精神胜利法,暴露了这一农民形象身上所固有的劣根性、丑的和无 价值的一面,所以这一形象充满了喜剧性的因素。冯骥才的中篇小说《啊!》所描写的 “文革”期间在法西斯恐怖下人人自危、惶惶不安、互相戒备、但求自保的被扭曲的苟 且心态,一方面表现了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迫害的残酷,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知识分子本 身的自私与卑怯。就知识分子的人性、尊严和价值被毁灭殆尽这一面来说,这是包含着 受害者血泪的悲剧,但就他们无价值的阴暗心理被剖析、被显示这一面来说,却不能不 说是一出“怒其不争”的喜剧。这种悲剧与喜剧、崇高与滑稽的结合,使它们的本质特 征彼此制约,而产生一种新的特征、新的美感形态:悲喜剧。就价值形态而言,这些悲 剧形象中喜剧因素的添加与渗透,就使文学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了社会,而且指向了人 性,指向了农民、知识分子这些社会阶层与文化群体自身;这种批判就不仅是政治性的 、社会性的,而且会追根溯源地寻找到文化学这一基本层面上来。具体地说,农民与知 识分子的悲剧一方面是极左政治、社会扭曲造成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农民与知识分 子身上所暴露出的弱点、劣根性和他们的喜剧因素,从深层的文化学与文化心理学的角 度来分析,难道不又是施行极左政策、社会进程逆转的一个原因吗?社会悲剧与人生悲 剧难道又不是互为因果的吗?显然,就形象的价值形态而言,这批悲喜剧色彩的小人物 拓宽了艺术思维与形象塑造的空间,也拓宽了通过艺术形象美感形态达到社会批判、人 性批判的可能性与多向性。
三
“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是当代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批特殊的形象 群体。他们不仅在性格特征上自有相似性,而且在美感形态上也自成一体而且独具特征 。他们的悲剧有共同的根源,即社会的剧烈逆转。就悲剧的性质与对个人命运产生的深 刻影响而言,这已经属于反常的或者说是“特别的”悲剧事件了,我之所以把他们放到 “极平常的悲剧者”这个题目下来论述,一是因为这些悲剧事件孤立地看是“特别的” ,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当时的大多数身临其境的中国人来说,它们又是司空 见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因而是“平常的”。第二个原因是就悲剧冲突的特征 而言,它与那种英雄的“特别的”悲剧显著不同,它的冲突和是非对立是不成比例的, 而是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势打击,悲剧者表现出明显的受虐色彩。应该说,“伤痕 小说”与“反思小说”中的悲剧形象,在美感形态与价值形态上都是相当独特的一个群 体。
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真正体现了鲁迅所说的“极平常的或者简直没有事情的悲剧” 特征的悲剧形象,却大都出现在继“伤痕小说”、“反思小说”之后反映现实生活经验 的作品中,如《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作家钟雨,《人 生》中的高加林、刘巧珍,《远村》中的叶叶与杨万牛,《麦客》中的水香,《心祭》 中的母亲,《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存妮,《挣不断的红丝线》中的傅玉洁,《银杏 树》中的孟莲莲等。稍作观察就可以发现这组作品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就题材来说 ,以反映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爱情与家庭生活为主;二是悲剧主人公大多为女性。对这两 个突出特点的合理解释应该是:在民族性、政治性的大灾难结束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 ,或者说产生个人悲剧的原因就突出为经济贫困、文化落后造成的愚昧,遗留的封建思 想、封建意识对人性的伤害,性别不平等对女性的歧视等非政治性、非全民性和不具有 明显尖锐冲突的文化和观念因素。
在“十七年”文学中,贫困、封闭、落后并不是必然同悲剧联系起来的字眼,相反地 ,它们常常成为产生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土壤,英雄与新人成长的沃土。“困难挡不 住英雄汉,越是艰险越向前”,物质上的贫困、落后成为描绘宏伟蓝图,建设祖国大业 ,实现人生理想的前提条件,环境的艰苦成为砥砺与检验精神与意志的砝码。从《暴风 骤雨》到《创业史》再到“文革”期间的《虹南作战史》,从贫穷的土地上站起了多少 同阶级敌人也同贫困做斗争的高大的农民英雄,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悲剧的影子。同样, 对于那些以共同理想与崇高信念而相爱、结合的男女来说,贫穷也不是爱情与婚姻悲剧 的根源。由经济拮据造成的爱情悲剧只属于富人,属于那些无所事事、精神空虚的资产 阶级的小姐与太太们,而对于革命者与劳动者来说,贫穷也是富有诗意的,能使爱情与 婚姻生活更甜美。当代文学中的这一格局,反映出中国作家在政治激情牵引下脱离现实 的虚假浪漫主义的膨胀与涣漫。
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就表现在对创作中虚假浪漫主义的否定,表现在 开始真实地面对农民的生存,不夸饰、不虚美。在这一语境中,贫困作为对人的压迫性 、打击性、否定性的力量,作为一种必须改造和改变的现实,它的存在显然是悲剧性的 。《远村》、《麦客》、《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桑树坪纪事》等都典型地反映出这 一格局的变动。在这些作品中,贫困被赋予的朴素与诗意洗涤净尽了,露出了它的本来 的狰狞面目。推行极左路线的错误使中国这只巨舰贻误了它的航程,贫穷与落后像魔影 般游荡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尤其是在那些远离城镇的僻远的山村小寨,仿佛是被文明遗 忘的角落,贫穷、封闭、落后、愚昧造成了一幕幕的悲剧。杨万牛与叶叶(《远村》)、 吴顺昌与水香(《麦客》)、小豹子与存妮(《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爱情悲剧,无一不 同贫困以及在贫困基础上滋生的畸形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因素相联系。年轻时的杨万牛与 叶叶相爱,但“豆腐换亲”的恶习——穷得拿不出彩礼的男性用自己的姐妹换娶自己的 老婆,其滋生及存在的根源是贫困——只能使叶叶委身于自己不爱的男子;而杨万牛的 “拉边套”——一种看起来更加野蛮的婚俗,其实不过是两个穷困的男子与一个既不愿 割舍爱情又不愿抛却家庭的女人共同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合作挑起生活的重担。 对于叶叶来说,不是爱情不美好,也不是她不懂或不知珍重爱情,而是面对经济贫困这 一巨大的魔影,爱情不得不收起它纯洁的翅膀,低下它高傲的头。很显然,新时期小说 中对农村爱情、婚姻故事的悲剧式把握与处理,已经表明作家从以往那种闭起眼睛、违 背现实地将生活浪漫化、诗情化的“虚情假意”中回到了现实主义,将冷静的谛视、严 肃的批判与真挚的人文关怀体现于自己的创作中。
如果说,贫困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否定性的物质力量造成人生与爱情悲剧还有 明显的政治、经济等时代与社会特征,还不能完全称之为“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 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2]、“简直没有事情的悲剧”的话(虽然贫困 仅只作为一种潜在的制约与悲剧的因素并没有直接地成为悲剧者的矛盾与对立面),那 么,在新时期小说中,还有一些悲剧来自于无声的、无形的意识与观念。悲剧的发生不 是表现在外在的冲突,而是表现在内心与灵魂内部的矛盾、龃龉;悲剧的制造者常常是 自己的亲人,是以爱的名义实施精神上的虐杀,或者悲剧制造者就是自己,是同自己的 愿望、初衷不符的“另一个自我”。一个落后于时代、沉睡于旧梦的自我观念的“另一 半”,成为自设陷阱,自投罗网。这种悲剧形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磨于极平常的, 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问彬的小说《心祭》写几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成年儿 女同心协力地扼杀了老年母亲的爱情。他们共同认为:年已花甲的母亲儿孙绕膝,而且 都是事业有成,比起过早去世的父亲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因此应当满足,不应该节外 生枝,同乡下的“舅舅”去共同生活。面对儿女的反对,母亲并没有“反抗”,但以后 的日子过得形同死灰,直至抱憾而死。儿女以“爱”的名义扼杀了母亲后半生的爱情与 幸福。这悲剧发生得无声无息,是一出令人沉痛和惋惜的心灵悲剧。《爱,是不能忘记 的》中的女作家钟雨与老干部,一个是由于年轻时的幼稚无知,稀里糊涂地嫁给了己所 不爱的人,后来不得已而离异;另一个则是“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 ”,娶了为掩护自己而牺牲的工人的女儿为妻,两人相敬如宾,但并无爱情与幸福可言 。这两件婚姻本身已是自造的悲剧。在年过半百之后,钟雨却同那个老干部相爱了,爱 得那样如醉如痴,那么刻骨铭心。但是,两人又都固守各自心造的藩篱,障碍于有影无 形的社会道德,不敢跨越雷池半步,而在各自的心中忍受着感情的痛苦与折磨,承担着 对真爱的渴望与对无爱的失望的双重折磨和打击。
在新时期的爱情婚姻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张弦的《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 《银杏树》占有独特的地位。从表面上来看,这几篇作品都有一个类似“大团圆”的结 局,是喜剧性的,但其内核却是地道的悲剧。傅玉洁是一个知识分子,她以“我要走自 己的路”为宣言,一生追求志同道合的爱情与和谐高洁的精神生活。但经历了一次次打 击、波折之后,她违心地投入一位高官的怀抱,以求受到最有力的保护,得到最安宁的 归宿。孟莲莲(《银杏树》)被不爱自己的丈夫抛弃,后来靠了县委书记的威压,丈夫又 同她成婚。然而孟莲莲对这种并无爱情的形式上的婚姻却感到幸福与满足。张弦的爱情 小说对“破镜重圆”等古老的故事原型进行了成功改写,他从“大团圆”这种喜剧形式 中实际上提示出妇女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有名无实或因果相悖的悲剧实质。这种 原地踏步或自缚罗网式的人生怪圈与爱情悲剧,让人们看到悲剧的根源既可能来自政治 、经济等外部的社会因素,也可能来自徘徊盘踞于自己头脑中的封建主义幽灵,自己就 是自己悲剧的制造者。
经济上的贫困以及相关的愚昧落后的遗风旧俗,封建意识以及相关的不健康的心理, 都是人性的否定力量,对于以个性主义和“全面发展的人”为理想和目标的现代人来说 ,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悲剧因素。或者确切地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 否定的今天,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上的贫困与文化上的落后,它们是悲剧的主要根源 ,尤其是思想观念上的落后将成为悲剧的重要因素。在经济贫困的基础上由观念的矛盾 所引发的悲剧,在矛盾的性质、冲突的具体形态方面都同阶级矛盾激化(极端状态则就 是战争)和社会发生畸变(如“文化大革命”)状态时所发生的政治悲剧、战争悲剧和社 会悲剧有所不同。它的突出特征就表现在它的“平常性”。在“英雄悲剧”中,矛盾冲 突的双方表现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尖锐对立,其势如冰炭,似兵戎相对,必激发、撞 击出电光石火般的气势与色彩,而结局往往是“英雄的死亡”。即使在“伤痕小说”与 “反思小说”中出现的那些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悲剧小人物身上,也能看到某些非同寻常 的东西,如命运逆转的突然性,故事的荒谬性,命运与心灵的悲惨与悲苦等等。而在陆 文婷、叶叶、刘巧珍、水香、钟雨等这些悲剧形象身上看到的,是贫困、暂时的不合理 、观念的固步自封和落后等“非特异性”力量。两者并不表现为你死我活的对抗,悲剧 形象的结局也大都不是死亡或毁灭即使写到主人公的死亡与毁灭也不是像那些叱咤风云 的英雄一样突然地、悲壮地赴死,而是以“消磨”为特征,死于、毁灭于日积月累的销 蚀和磨损,如叶叶的死,陆文婷健康的被毁等,都是由日常生活中所潜藏的“极平常的 ”悲剧因素造成的。
这类悲剧形象在美感形态上也具有独特性,它似乎是介于悲剧英雄的崇高、悲壮和“ 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悲惨、悲苦之间的一种美感形态,如果要命名的话,似乎可以 用优美、忧伤等概括。这些形象,尤其是占了大多数的女性形象,常常以朴素、恬静、 温柔、忍耐、柔婉等美感特性打动、吸引读者。她们内在的执著信念,行动的坚韧,对 来自生活的巨大压力、命运的打击和不幸,都显现出处事不惊、从容应对的气度。这是 中国妇女所特有的一种“母亲”的气质,在历经危难与艰辛中给人以冲淡、亲和、温暖 、可依可靠、可信可赖的感受。她们不同于那些壮烈的悲剧英雄,没有可歌可泣的英雄 业绩,没有强烈的戏剧动作和剧烈的心灵冲突,但那种执著、坚韧与从容不迫自有特殊 的魅力和优美的美感。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们的柔弱、朴素、优美却遭受着来自生活的 重压、销蚀与磨损,却不能不唤起人们忧伤与遗憾的感情,如看到暴风雨中弱竹的被摧 折,听到幽室中丝帛的被撕裂,有种遽然惊心的痛感。而对于像傅玉洁、孟莲莲这种作 茧自缚的悲剧者,在感到忧伤的同时,还不能不生出强烈的缺憾感。就价值形态而言, 这些以优美、忧伤为特征的美感形象,除达成社会批判的主题以外,更容易唤起同情、 向善等的伦理情感。事实上,以陆文婷为代表的这批形象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 响并葆有长久的魅力,就足以说明他们在“真”与“善”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就一般 情况而言,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还尤其能在爱的基础上,达到对“生与死”等生存性 命题的探讨,从而使美感形象在“真”“善”“美”的结合上达于至境。而在这一点上 ,这批悲剧形象似有所欠缺,令人稍感遗憾。
收稿日期:2002-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