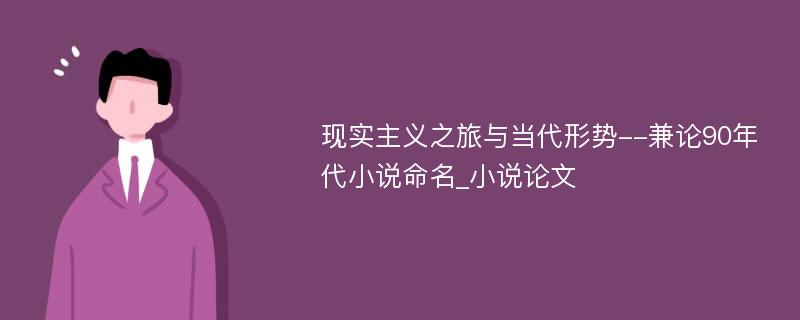
现实主义之旅与当代处境——兼论90年代小说的命名真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旅论文,现实主义论文,处境论文,真相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是一个事件层出与命名不断的文学时代。从新写实、新历史、新体验、新状态、女性文学到晚生代(新生代)、70年代出生作家的翻新推出,无一不具有浓厚的表演色彩。从命名到凸现欲望文本的制作,文学舞台的狂欢性被翻演到一种极致。任何一种关于创作的命名都潜藏着一次性的颠覆快感与翻新欣悦。这情形犹如尼采描述的疯子,大白天打着灯笼满街宣告上帝之死的合谋真相。众声喧哗中,现实主义如一件不合时尚的藏品,似乎在满落尘埃的尴尬中依依作别了时代。这就是我想表述的现实主义在90年代文学中的一幅黄昏图景。其实在80年代,以现代派或“伪现代派”旗帜标举的新潮小说就已经预演着这场合谋的开始。而随着以“马原叙事圈套”为事件的文本出现终于使这种冲动有了实质性的演绎。当这场叙事革命在九十年代初以文学的转型说得到学界的郑重认可,则标示着筹谋中的“后新时期文学”命名的合法性。(注:参见谢冕《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 )以“新”或“后”为界标的命名策略,事实是想宣告一个时代的文学终结。九十年代末“断裂”事件的出现,又使这场蓄谋已久的小说界革命有了一个激进的尾声。这类似于50、60年代美、法批评家们注意到一种声音:小说(写实)的死亡与叙事的再生。
有的批评家聪明地采用了“策略”一词来描述、评介整个合谋事件。这显然是无意从学理上考掘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内在必然因素。现实主义概念的种种衍生,使批评家放弃了指望通过对现实主义本质的认识获得批评共识的努力。他们更乐意移植西方文学理论中闪烁着的最新名词,致力于对一些现象的局部性的描述与演绎,从而作出某种轻灵的调和。而事实是从八十年代后期“现实主义回归”(新现实)到九十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始终幽灵般飘荡在理论界与创作界的视域中,在各种层出不穷的命名的合法性的申请背后,现实主义这块嚼烂的口香糖,并没有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被新口味完全取代。神界的黄昏,有人说上帝死了,甚至宣判了人的死亡。然而思索的人和发笑的上帝至少在米兰·昆德拉的眼中还存活着。现实主义的黄昏场景历来如此充满着喜剧性色彩。现实主义在西方经由卢卡奇发难的“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阵营之争,罗杰·加洛蒂对“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谐调,最终到结构主义从叙事结构功能出发对现实主义成规的肢解,现实主义就一直处在终审判决的险境。中国的九十年代小说同样如此,左冲右突中困陷在现实主义围城。当我们在浮躁中急于命名新的东西的时候,是否疏忽了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新”?这里面有没有一个明晰的目的性?文学总是处在深深的影响的焦虑中,而耽于影响焦虑出走、逃亡乃至谋杀的做法恰恰在另一方面证明了影响着我们令人不安的力量本身的强大,值得探究的,也许应该是明晰它到底涵盖着怎样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背后的规定性又是否决定着文学自身的消长存亡?一方面,我们对现实主义反应情同逃火,避之犹恐不及;另一方面在文学规则的整合中又不时要借助其无所不在的规定性还魂定神。在这其中显然有着值得讨论的价值。本文将借助已经发生的文学运动与现象观照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变异的实质。通过对小说与现实主义与生俱来的关系考察来寻求对小说现实主义合理性的公允认识,在我看来,是一个可以达成的期望。我将选择有关“真实”的哲学认知作为讨论的逻辑起点。
小说:现实主义的合理性寄寓方式
谈论现实主义一般很容易陷于概念本身的纠缠不清。就现实主义谈现实主义无疑是一怪圈。伊恩·P ·瓦特通过对西方十八世纪早期小说兴起的考察讨论小说与现实主义之间与生俱来的关系,也许更能启迪我们洞察到现实主义在小说文体中存在的历史成因与合理性。鉴于现实主义概念的种种衍生,有必要对作为“时代概念”的现实主义与作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术语的现实主义加以区别。前者典型地体现在十九世纪的艺术与文学之中;后者则指对于世界的真实反映立场,具有与时代无关的普遍性意义。显然本文的考察是从后者出发的。因为作为近代小说文体兴起的标志,十八世纪早期小说就已经蕴含着与现实主义的独特关系。
小说作为一个独立文体的兴起,与近代历史大幕的拉开密切相关。伊恩·P·瓦特在考察小说的兴起时特别强调了这种内在的联系。 在他看来,“十七世纪后期兴起了一种更客观的历史研究,因而获得了一种更深刻的对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认识。”(注:伊恩·P ·瓦特《小说的兴起》第一章《现实主义和小说形式》。三联书店,1992年。)笛福的小说反映了这种差别,他的虚构故事最早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个人生活的图景。早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种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的传统作为现实的最权威的仲裁者的趋势已经日益增长,这种转变构成了小说兴起的总体文化背景。这就是笛福与理查逊区别于先前文学最早放弃对神话、历史、传说等情节的使用的事实。显然,近代小说从一开始所禀赋的与历史经验相区别的现实主义的特质与近代人“自我”的觉醒有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显现了“我”与我之外世界之间存在的二元关系。按照弗洛伊德后来的说法,人正是从镜像中第一次发现和认识到自我的。所谓镜像也就是日益被对象化的世界。而导致人从日益对象化的世界分裂出来的事实,发生在近代以后。主体的觉醒开创了新的哲学认知信念,即客体成为主体认知对象。“现实”不再是神话、历史、传奇中的“现实”。它也意味着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社会流程本身。是各种可以为主体所直接把握到的客观事物本身。在这一认知语境中,“真实”的把握通过艺术的反映将在“生活”、“世界”、“现实”、“社会”以及“历史”中得以获取。
古希腊哲学把事物的现象(phenomena)和本质(essence)区别开来,认为不断变化着的是事物现象,而事物的本质恒定不变。后来的哲学讨论都是围绕着对本质接近的可能性与方式来加以展开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代表着“最高的真实”,本来让人们看到了走近本质的希冀,但他把它精神化了,则又把“真实”显现在了遥远不及的彼岸。同样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罗素语)的马克思则把推动进化的力量理解为物质。实证主义与进化论代表了近代小说兴起时代的特定世界观,即科学与进步的人类观与社会观。这为现实主义小说中确立起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奠定了新的认知信念。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与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较为明晰地表达了这种“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世界认知区别。前者的出走寻父与最后回归,表明了神的在场以及留守家园的态度,这是人类与世界分裂前的状态。而后者远离父亲出走游离的成长则表明了一种个人主义的觉醒,是“自我”从“世界”分裂出来后的状态。它意味着人走上了无家可归的情境。个人成长的精神自传不仅由此而成为近现代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同时也通过成长中的“自我”的视角重构了主体与客体之间新的认知与反映关系。十八世纪早期表现个人主义主题的小说,如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理查逊的《克拉丽莎》、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等,与十八世纪后期的启蒙小说,如卢梭的《忏悔录》、《爱弥尔》、伏尔泰的《拉摩的侄儿》、狄德罗的《天真汉》以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近代小说文体在十八世纪的兴起不是偶然,而是人对世界的认知发展到某个阶段的必然结果,人对世界新的认知关系使小说文体应运而生。小说文体区别于戏剧、诗歌与散文的独特性,决定了近代小说与所反映的现实之间新的关系的确立。在这一意义上,小说以及小说与现实之间与生俱来的关系显然是一种近代的产物。
中国小说固然有着它的特殊性。它在一开始也没有获得独立性文体地位,而只是诗赋文章之余志怪志异式的文人闲趣。象《西京杂记》、《酉阳杂俎》、《太平广记》、《夷坚记》等,还只是文人随笔性质的自娱,并没有自觉的文体创作意识。但商业活动的繁荣,特别是当以话本为主体的说书讲史传统形式已经不能满足人口频繁流动的听众要求时,在印刷技术的保障下才有了书面的话本或拟话本的出现。小说文体作为一种自觉的创作形式在明代特别是嘉靖之后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了以冯梦龙、凌蒙初等为代表的作家群。读者群体也相对明确下来。《清平山堂话本》的分集命名,如“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等,从另一个角度形象地表现了小说的阅读功能与读者对象的明晰下来。明代小说在文体意义上获得独立性地位,一方面它摆脱了文人自娱性的随笔闲趣与补正史之阙的参行功能,从而进入到了一个自觉的有明确读者群体的创作时代;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也走出了“志怪”、“说史”的局限,全面进入到对市民社会生活的演绎,这种“当下性”的写作与西方近代小说摆脱神话、历史、传奇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趋势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据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的考证,这与明代“心学”的创立有关。王阳明“心学”的指导思想是要把儒学民间化,后经平民出身的泰州学派开创人王艮的努力,儒学进一步通俗化,王艮提倡顺其自然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而明代另一位思想家李贽的“童心”说进一步发展了王艮的思想,认为“童心”就是人的先天自然本性,饮食男女就是人伦物理,公然把人欲合理化。这种思想给晚明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造化了冯梦龙反映在“三言”中的“情教”思相。“情是天地万物的本性,情始于男女,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注: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240页。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由此市民阶层的情感世界,市民的性格、良知与喜怒哀乐在以“三言”为代表的拟话本中得以体现。
商业的繁荣,儒学的民间化以及印刷术的发达,促成了中国小说文体在明代的兴起。特别是明代思想家所致力的对“人欲”的新阐释,使小说开始具有了开放的民间视角与市民趣味,直接关注、同情和表现社会现象。而“补正史之阙”的史传传统又使小说先天性地禀赋了现实主义的特质。随着晚清民初报业的发达,小说迎来了它的第二次繁荣。如果说冯梦龙时代的小说家还囿于发乎人欲,止乎礼义的局限,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2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提倡“新小说”则赋于了小说启蒙使命。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明确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众、道德、宗教与政治必先新小说的主张。晚清小说或以谴责小说形式表现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或以奇思幻想宣扬西洋技术(如《新石头记》、《新纪元》等),或以“礼拜六”方式表现婚恋爱情,展示出一个形若万花筒般的世界。但真正体现“自我”觉醒意识的还得以民初(1912年)苏曼殊的《孤鸿零雁记》为代表。较之同时代的《老残游记》,该小说已经不同于以往小说表现因果报应、天理循环的思想传统,而表现出“自我”与“自我”之外世界的分离关系。老残的世界还是一个道统的世界,苏曼殊则由于特殊的身世以及在日本的经历,决定了他已经走出外部世界,拥有了一个开放的“自我”世界。《孤鸿零雁记》选择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实际上是开启了现代精神自传的先河,为郁达夫《沉沦》、丁玲《莎菲女士日记》冲破“温柔敦厚”礼教之先声。在这个意义上,它标志着现代个人主义小说的肇始。而中国现代小说与西方文学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契合,实际上是把中国小说纳入西方文学的潮流。新文学在进化论思想的引导下提倡写实主义,更使小说的现实主义态度获取了合法性的存在方式。
纵观中国小说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看出它的三次重要转型。从明代小说受儒学民间化的影响、梁启超对小说启蒙功用的鼓吹到新文学倡导写实主义,小说一直保持着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但也应清醒看到的是,中国小说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与西方的认知传统并不完全相同。明代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特征,更多是源于自身文化的史传传统,崇尚的是史家笔法的客观性。即使是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新文学,倡导者们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也不乏模糊的认识,多停留在文学与社会、政治以及现实生活关系的表层。由于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认知哲学基础,简单地把描写现实生活直接等同于反映真实的做法,不仅削弱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性,也深深影响了现实主义小说在中国的有机发展。五四新文学所反映出来的整体创作水平高下不一的现象,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严重受到机械决定论影响的“革命小说”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更使得现实主义精神受到了猜疑。胡风文艺理论在建国前后的一再受批,恰恰是中国现实主义道路发展的不健康时期。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现实义理论建设步入了误区,在八、九十年代文学中也仍然遗留着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表层认识,导致了现实主义声誉的每况愈下。
如果说二十世纪现代小说家对现实主的质疑还是建立在对真实认知方法的基础上,而在中国则是一种复杂得多了的“多音齐鸣”现状。倘若现实主义存在一个统一的哲学基础,那就是对“真实”的认知,不会再是别的如种种概念、定义所衍生的修饰语。二十世纪小说家其实所作出的努力,也正是围绕对“真实”新的认知方法来展开的,这将使我们更清楚地透视到寄寓在小说文体中的现实主义的实质。
逃避:在奔向“真实”驱使的路上
在近代认知理性之光照亮下,近代小说所蕴含的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信念,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总体精神。十八、十九世纪无可争辨的是小说与现实主义的时代。小说文体对于生活的全部丰富的表现,决定了它在真实反映现实生活方面优越于其它文体。但进入到二十世纪,由于对“真实”认知方式上的差别,小说呈现出各种新的形态,作为十九世纪“时代概念”的现实主义走向了无法界定的困境,从而导致了“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之争。这也是罗杰·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概念的产生背景。
历史的诡谲之处,也许恰恰在于它的不可规范性。近代哲学的发展并没有在理性之山前止步。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是,真实本质是否真的就如进步的科学信念所认为的那样是可以被全部认知的?或而言之,真实本质又是在怎样的一种认知可能中才能为我们所接近?康德在他的认知哲学体系中作出过如下艰涩的讨论。在他看来,世界的存在是主观意识的存在,纯粹的客观并不存在。他著名的“物自体”概念,指的也只能是存在于信仰中的那个不可知的物本身。不可知性提醒着我们人的感性与理性认识的限度。而作为直观的感性与理性所能达到的只是现象界。这就是说,我们以自己的感觉器官与理解结构来认识世界无论感性与理性都只是赋于事物以形式,因而我们知性所能描绘的也只是世界在我们人的眼睛或头脑里的样子,即作为世界存在的表象。
对于知性限度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现代人认知方式的改变。二十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有过这样精确有力的表述:“智力以过去时间的名义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也未必就是那种东西。我们生命中每一小时一经逝去,立刻寄寓并隐匿在某种物质对象之中,就象有些民间传说所说死者的灵魂那种情形一样。生命的一小时被拘禁于一定物质对象之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远寄存其中。我们是通过那个对象认识生命的那个时刻的。我们把它从中招呼出来,它才能从那里得到解放,它所隐藏于其中的对象——我们称之为感觉,因为对象是通过感觉和我们发生联系的——我们很可能不再与之相遇。因此,我们一生中有许多时间可能就此永远不再重现。”(注:普鲁斯特《驳圣伯夫·序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在普鲁斯特沉思迷想的世界里,以回忆方式挽留逝去的时光成为重构世界的方式。如他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展示的“玛德莱娜甜点心”、“马尔丹维尔钟楼”等著名的场景那样,现实只能在回忆的片断中昙花一现。在他看来,即使是最伟大的作家留给这个世界的杰作,“也不过是伟大才智遇难沉船漂散在水上的一些残留物”,他们能做的是把这些残片收集到一起。十九世纪巴尔扎克全景式对于真实的把握方式由此遭到了怀疑。
他的同胞罗伯—格里耶在半个世纪后几乎是以绝望的语气表达着对巴尔扎克时代全能式认知方式的不满。在他看来语言的修饰功能已经完成了对世界的命名,“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他通过对电影画面呈现的“一张空椅子”、“一只手放在肩上”、“窗上的栅栏”情状暗示关于“缺席或者期待”、“友好”、“无法离开”诸意义的分析,反观到相同的场面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为人们所熟视无睹的事实,从而判定“世界既不是富有诗意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仅此而已。”(注:罗伯—格里耶《小说的前途》,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册,第188页,第18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于是他倡导“通过消除文学语言中那些隐蔽或公开地给没有生命的事物的世界赋于人类涵义的修辞用语,从而表现出一种科学的客观世界或中性世界”(注:罗伯—格里耶《小说的前途》,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册,第188 页,第18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的“新小说”革命。 这其实是一次为极具欺骗性与人类自我命名色彩的语言魔力“去魅”的事件,它意味着被先前文学装饰好的那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的土崩瓦解。在“新小说”派看来,“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内心分析、情景描述、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等手段,诱导人们只能通过作者或作者塑造的人物的眼睛去看外在的事物。”(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第114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于是“新小说”所致力的是“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功能意义的世界。让物体和姿态首先以它们的存在去发生作用,让它们的存在继续为人们所感觉到。”(注:罗伯—格里耶《小说的前途》,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册,第188页,第18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从普鲁斯特到罗伯—格里耶,现实主义在经历了十九世纪的高峰之后在二十世纪受到了全面的挑战,但这种质疑并不是以对“真实”把握信念的动摇为代价,而是对“真实”认知方式与“真实”寄寓方式获得了新的认识。康德的批判哲学、存在主义等学说为此提供了全新的认知方法。即使是结构主义理论家从叙事的结构功能出发质疑现实主义,也只是对现实主义根据它所描写现实的真实程度来定义的做法的否定。现实主义以现实生活为判断真实的参照系,而结构主义以想象力为判断真实的参照系。可以这么说,二十世纪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集中体现在对真实存在方式与存在寓所的叩问。普鲁斯特说,真实与逝去的时间一起寄寓在事物中,而且也许永远隐匿在其中不再重现。罗伯—格里耶说,世界存在着,“在我们四周,对我们那套吵吵嚷嚷的万物有灵说的或是保护性的形容词无动于衷。”由此,我们接近“真实”之路变得不可捉摸起来。中国九十年代以“新”或“后”的前缀方式命名的小说,正是在这一语境中获得了接近“真实”的新的可能性。
真实与虚构是当代小说家面对的二元悖论。当王安忆以“我现在终于可以来讲一个故事”的口吻表达一种释然的心情时,“真实与虚构”之间仍隐存着冲突的边界。这在八十年代前期尤为明显。汪曾祺直言,他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认为“故事性太强,我觉得就不大真实”。而宗璞也从中国画与德彪西音乐中发现了一种与现实比例不符的“真实”。这种对虚构的向往,在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对“真实”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的寻求。而“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沟壑也由此获得了有效的弥合。马原的小说《虚构》在对麻风村的叙事行将结束时安排一个梦醒的结尾,无非要强调整个叙事过程的虚构性。形式的消解恰恰赋于了寄寓在文本阅读经验中的另一种真实性。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全面地表达了这种真实的本质,认为它与日常经验无关:“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述的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注:余华《虚伪的作品》,见《余华作品集》第2卷第278页,中国科学出版社。1995年。)这就是《现实一种》与《世事如烟》所呈现的真实。这种真实建立在对使人沦为在缺乏想象的经验常识的怀疑基础上,因为狭隘的经验只能导致我们远离精神本质。发生在九十年代前的对“真实”的另类叩问,其实已经传达出了九十年代小说内在精神变异的实质。以“新”或“后”命名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逃避了真实,而是一直行进在奔向真实驱使的路上。
新写实小说标榜“零度情感”与“原生态”的写作,旨在除去被乌托邦语言遮蔽着的外衣,敞现出一种更为客观或中性的世界。它选择日常生活作为描述的对象,在对“宏大叙事”的消解中显现存在的本真性。新写实这种把生活还原为一种形而下的流动状态的当下性写作态度,与以往现实主义一贯以人道主义立场带着知识人俯视性、同情性的关照现实态度大相径庭。它把本真还原,显现的是一个共存的处境。“真实”就在那里,它存在着,并为我们所共同面对。而新历史小说表现出的是对历史整体性的质疑。它怀疑历史因果方式演绎的可靠,致力于从所谓的历史真相中洞见到存在于时间之流的偶然性与不可知性。格非的《迷舟》、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李晓的《相会在K市》、 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我的帝王生涯》等所表现出的对历史真相的解构,其实旨在期待在另一个地点与“真实”不期而遇或者暗示对“真实”的寻访不遇。
真实不是从狭隘的经验常识中直接获取,它的隐匿性与不可知性显示了我们接近真实之路的诸种可能。同样是对时代的一种眩惑感的表现,贾平凹《废都》的颓废式放逐、张炜《九月寓言》的激愤退守以及格非的《青黄》与鲁羊的《一九九三年的后半夜》中的边缘性独语,都在以自以为更逼近“真实”的方式安妥着灵魂。而在对时代眩惑感中人的伦理关系与道德的表现中,王朔的《我是你爸爸》,韩东的《障碍》、朱文的《我爱美元》等,更象个乐于拆坏父亲手表的孩子,不惜把镜像中的“自我”与温情世界击碎,重构起父子或两性之间的关系。在“自我”华丽外衣褪去之后人更接近一种弗洛依德谓之的“本我”状态。一些在日常经验中熟视无睹或陈规化的事物被一种极具穿透力的命名行为敞现出来,如父子关系、如两性关系。正像《我爱美元》中面对父亲的谆谆教诲,很自豪地说:“你说的这些玩艺,我的性里都有。”
显然,九十年代小说在命名不断翻新的过程中完成的不是对小说现实主义的世纪末判决,只不过是以另种方式表达着对“真实”的认识。它寻求着对世界重新命名的可能,这就是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对“真实”认知驱使下演绎出的一种事实真相。正如马丁·华莱士所言,“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有关现实主义叙事的阐述本身就是一个叙事,说的是世界如何从一个统一的过去到一个分裂的现在,并且也许正走向一个统一的未来。”(注:马丁·华莱士《当代叙事学》第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在这一意义上,小说实际上所做的就是不断构建着一个世界,一个更接近真实本质的认知世界。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自我认识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社会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