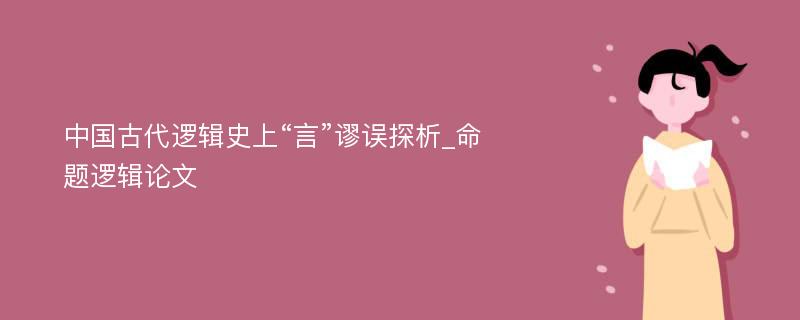
中国古代逻辑史关于“立辞”谬误之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谬误论文,中国古代论文,逻辑论文,立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立辞”在中国古代逻辑中相当于推理论证,其论证要素之论题被称为“辞”,论据被称为“故”,组织论证方式应遵循一定规律被称为“循理”或“知类”,这在《墨辩·大取》中就有明确论述:“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这段话同时也说明“立辞”过程如不遵循一定规律就会发生谬误,其主要表现就是“不明故”、“不明理”或“不明类”等,也即在论据和论证方式这两个论证要素中,用以推论之“故”多是虚妄之“故”,不足为据,以及不循理而推,不察类而论等。显然,“立辞”过程如发生这些谬误,定会使思维陷入困顿和荒诞,故应予以重视和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中较早在这方面予以重视的逻辑学家是墨子。他在《墨子·非儒下》中提出“无故从有故”的要求;在《墨子·非攻下》两次指出他的论敌在论辩中犯了“不明故”和“不察类”的错误,就是提出了要研究和防止在论证或反驳中出现论据或论证方式的谬误问题。后来,后期墨家,即《墨辩》学者也提出要研究因“异故”而产生的谬误问题,并对这类谬误的成因作了探析。再以后,韩非、王充以及其他古代逻辑学家又深入对各种不当之“故”和“不循理”、“不察类”的“立辞”谬误进行揭露探究等。下面我们就对他们的有关揭露和探究作些综合介绍,以启发、丰富今日逻辑科学之内容。
一、关于几种不当之“故”
其一为无验之故。即用未经过验证的理由来作为“立辞”之依据。荀子在《性恶》中指出“孟子曰人之性善”,其“故”即为“无验之故”,因它“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故不能得出孟子所要的结论。这种用“无验之故”来“立辞”的谬误,韩非则称之为“前识”之谬,“前识者,无缘而妄度也”(《解老》)。在韩非的著作中,多处有着对这种无验的“前识”之谬的揭露和批评。如在《显学》中就明确指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而据之者,诬也。”后来王充论“九虚”,其中的“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等也均属对此类谬误的批评。所谓“变虚”,是说不能按星徙定祸福;所谓“异虚”,是说不能据事象占吉凶;所谓“感虚”,是说精诚不能感动天;所谓“福虚”,是说行善天未必赐福;所谓“祸虚”,是说祸亦非天罚;所谓“龙虚”,是说龙不能为神;所谓“雷虚”,是阐明雷是火,并非天怒而杀人示罚;所谓“道虚”,是说所谓得道升天,并非事实。(参见《华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论逻辑谬误》, 李匡武著)王充不仅仅是在以上方面指出“立辞”不能据之以无验虚妄之故,就是他的整部《论衡》,其主题就是“疾虚妄”,也即批判“无验之故”的。
其二为众意之故。此种谬误就是根据众人意见定是非,凡众人赞同者即正确,凡众人反对者即错误,“众意”为“立辞”之唯一根据。韩非在《八经》中把这种谬误描述得很形象:“言之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言乎,千人不可解也。”不然之物,只要说的人多了,也就可信不疑了,这是此种谬误的背理之处。正因如此,故多遭先秦逻辑学家批评。《墨辩·经下》曾就该不该批评的标准说道:“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诽。”《经说下》进一步明确道:“论诽诽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诽,虽多诽,其诽是也。其理不可诽,虽少诽,非也。”《荀子·正名》也指出:“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他们都认为判定是非的标准是“理”,即事物的规律性,不能“动乎众人之非誉”。因为有时众人所赞同者不一定为真理,众人所反对者不一定不为真理,一味以众意为故,作为“立辞”之充足理由,不一定恰当。
其三为圣言之故。此类谬误就是一切迷信圣人言行,或者说是迷信古代典籍中所记述的所谓圣人的言行,唯以此定是非。明代李贽在这方面有精到论述:“前三代,吾夫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把一切唯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讥为“无是非”,这闵是李贽对一切以圣人言行为“立辞”依据这类谬误的实质所作的一针见血的揭露。这表明中国古代逻辑学家也看到了圣人言行不一定都正确,绝对地以其作为“立辞”根据,不一定站得往,而且这种是非观会把人的思想禁锢在所谓圣人的思想框框里,从而丧失根据实际来作出自己是非断定的能力。鉴此,李贽又说:“虽使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同前)其实在东汉的王充也曾有过如此的揭露,如他在《儒增》中就指出儒书中多夸张失实之处,故不可盲目迷信。
其四为传闻之故。此类谬误就是注重是以往传闻而轻视当前之事实。王充在《论衡·齐世篇》中对此谬误是这样描述的:“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杂恶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辩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使当今说道深入孔、墨。名不得与之同;立行崇于曾、颜、声不得与之钧。何则?世俗之性。贱所见贵所闻也。”但所闻的不一定正确,所以王充在《语增》中又指出当时传语中不乏荒诞之谈。如果一概都以传闻为据,不仅使思想遭禁锢,也会使“立辞”之“故”缺乏充足理由。李贽对此类谬误也给予辛辣嘲讽:“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题孔子象于芝佛院》)
其五为强辩而无故。“无故”也即“不明故”。在论辩过程中或者有意,或者无意,不明于别人所言之故就妄加驳难,此即强辩而无故。在《墨子·非攻下》中,墨子就指出他的论敌在“未明其故”和“未察其类”的情况下就非难他的“非攻”主张,把“攻”与“诛”混为一谈。墨子认为这是不妥的,因为论敌的驳难无根据,无理由。王充在《刺孟篇》也指出,孟子在还未知梁惠王所问“将何以利吾国”的意思是什么时,就直接以“何必曰货财之利”而驳之,须知惠王所说之“利”可能还包括“安吉之利”呢。王充进一步认为,“如惠王实问货财,孟子无以效验也;如问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货财之利,失对上之指,违道理之实。”总之,王充认为孟子在此是强辩而无故。
以上为中国古代逻辑史中对与“立辞”有关的一些不当之“故”所作的探析综述。他们都注意到了论证中之论据与论题之间一定要有真正的逻辑联系,如无这种联系或表面似乎有联系而实质无联系,则论证就会发生谬误。这类似我们今天逻辑教科书所讲的不相干谬误。可这些教科书在论到不相干谬误时却忽视了它们所讲的内容在中国古代逻辑中已有过很好探索,没有或不愿提及中国古代逻辑所作的贡献,这是不公平也不应该的。写作此文的目的之一也是想指出这一点。
二、关于几种不循理而“立辞”之谬误
其一为“立辞”中之自相矛盾。中国古代逻辑学家认为,“立辞”过程应遵循的基本之“理”就是要求思维前后一致,否则即产生“立辞”中之自相矛盾。对于此类谬误,中国古代逻辑学家揭露得较多、较充分。如《公孙龙子·迹符篇》中的“先教而后师之者,悖”;及“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等。这里的“悖”即作“自相矛盾”解。因为在公孙龙看来,既承认别人为师,又教之别人放弃之反以为师的条件,这就是“悖”,即自相矛盾。另外,他还认为他的异白马于所谓马的命题与孔子的异楚人于所谓人的命题在形式结构上相类同,而人们却承认后者否定前者,这也是自相矛盾。对此谬误,《墨辩》也有类似揭露,如“以言为尽誖,誖,说在其言”,这里的第二个“誖”,也作自相矛盾解。而最典型最明确的揭露则数韩非那著名的寓言了:“楚人有鬻盾与矛盾,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之盾如何”’其人弗能也。”据此,韩非总结出“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韩非子·难一》)这其中所包含的道理和要求,现已成为逻辑原理中恒久不变的重要内容了。
其二为“立辞”中之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这也是违反“立辞”中思维保持一贯或同一之“理”而产生的谬误。如前所述,墨子指出他的论敌在非难他的“非攻”主张时,就把“攻”和“诛”这两个概念相混淆了,“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是因为对方“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两人所论范围不同,即思维不同一,就妄加非难,自然也就易于混淆概念。类似揭露在《墨子·公盂》中还有:“公盂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是犹倮谓撅者不恭也”。这里,公孟子先以“三年之丧”来偷换“三日之丧”,然后再非难墨子。墨子则把这种作法讥为赤身裸体者反说揭开衣服的人为不恭。可见,“立辞”中的偷换概念是怎样的似是而非。鉴此,后来《墨辩》学者就把此类谬误称之为“巧转”,并要求对之“求其故”(《经上》),因为知其“故”,才能除其害,这是有道理的。
其三为“立辞”中之自我循环。中国古代逻辑学家认为“立辞”过程应遵循之“理”还有一条就是要求能从已知之“故”推出所立之“辞”,切不可以所立之“辞”证所立之“辞”,如此就是自我循环。《墨子·公孟》以例明之:“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应我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以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可见这种自我循环,最终什么也未证明,不能给人以新知识,所以是一种逻辑谬误。
三、关于两种“不察类”之谬误
其一为不知同类相推。此类谬误就是在推论中不知道同一类事物的每个分子也可以具有该类的一般性质,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小不知大,举一隅不会以三隅反。正如墨子在《鲁问》中指出:“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谓也。”就是说,同是侵占别人东西,对于侵占别人的一狗一猪,人们都知为不仁,而对于侵占别人的一国一都,却不知类推也为不仁。这等于少见白知道是白,多见白则不知类推也是白而说成黑一样荒谬。在《公输》中,墨子还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就是说,有的人对于杀少尚知为不义,而对于攻打别国去杀多则不知类推也为不义,这也是不知同类相推。这类谬误,在《墨辩》中也有揭露。如在《小取》中,《墨辩》学者就认为他们的“杀盗非杀人”命题与人们普遍承认的“恶多盗非恶多人”命题在形式结构上是类同的,但人们只知后者的真,而不知类推及前者也为真。《墨辩》学者认为这是人们内心不开窍的表现,“内胶而不解也。”总之,这种谬误,其要点就是不知同类可以相推,或者把同类当作异类,以至出现认识上或行动上的错误还不自觉。
其二为异类间的妄喻或妄推。与上种谬误相反,这种谬误就是在“立辞”中有意或无意反把不同类的事物看作同类而妄作比喻或推断。《墨辩》对此论述得比较详细和集中。如在《经说下》中就有对异类相比谬误所作的质询:“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麋与霍孰高?麋与霍孰霍?蝉与瑟孰瑟?”就是说,木与夜,智与粟,官爵、亲缘、德行、物价、麋与鹤,蝉鸣与瑟音,它们之间均不属同类,故不能把木之长与夜之长,智多与粟多,官爵的贵、德行的贵及物价的贵,蝉鸣的悲与瑟音的悲等妄作比喻,否则就会不伦不类。因此,《经下》提出“异类不比,说在量”的要求,因为衡量的标准不一,异类间就不好妄比。当然,简单的异类相比的谬误还是较易识别的,比较复杂的由于不知类异而妄作推断的谬误就难以识别了,特别是有的推论,相互间各自的前提又似乎有某些相同的语言表现形式或语言结构形式,但实际内容却相去甚远。这时如果也把它们看作是真正同类而从其一真推及另一也真,或从其中之一假推及另一也假,就容易产生谬误了。《墨辩·小取》列举了这方面的四种具体情形:(1 )“是而不然”。它说明的是:有的肯定命题可以通过相当于普通逻辑的附性法,推得一其语言表现形式为人们所公认的新的肯定命题,如“白马,马也”,“获,人也”等,就可通过附性法分别推得“乘白马,乘马也”,“爱获,爱人也”等新命题。这些新命题其语言表现形式人们都是能接受的。但有的肯定命题,尽管在语言形式上也与前述的“白马,马也”,“获,人也”等肯定命题相同,却不能如前照搬附性法也类推得一其语言形式也为人们所公认的新肯定命题。如“车,木也”,“盗,人也”等就不能也分别用附性法类推得“乘车,乘木也”,“多盗,多人也”等肯定命题,只能推得“乘车,非乘木也”,及“多盗,非多人也”等否定命题。如果以为一些肯定命题能用附性法推出新的肯定命题,所有其它语言形式相同的肯定命题也应能类推出新的肯定命题,就错了。这里主要问题在于其附性后所得的语言表达式是否符合社会的约定俗成,符合的则为一类,不符合的自然就为异类,既是异类而再作类推,就产生“立辞”之谬了。(2)“不是而然”。 这说明的是某些语言结构式相同的命题,其中有的可直接导出否定性结论,有的则直接导出肯定性结论;或者有的在附性前可直接导出否定性结论,而附性后却得到肯定性结论。如“且读书”与“好读书”其结构形式相同,但由前者通常可直接导出“非读书”的否定性结论,而由后者通常则可直接导出“好书也”的肯定性结论。又如由“且入井”当然可得否定性的“非入井”,但若附上一“止”后,却由“止且人井”,得出肯定性的“止入井”了。如果以为“且读书”与“爱读书”的语言结构形式相同就一定由前者导出否定性结论因而后者也应导出否定性结论,或由附性前的“且入井”导出否定性结论因而附性后的“止且入井”也应导得否定性结论,就错了。原因在于它们或者是虽结构形式相同,但实际内容并不同,如“且读书”指将要进行的一件事,“好读书”指的是一种品性,这并不为真正之同类;或者是附性前与附性后其命题所指已不是同一方面之性质,如“且入井”指的是将要入井这么一件事,而“止且入井”则是指制止就要入井这么一种动作,这此时所指已不同。既如此,如不加区别地妄作类推,只能是发生谬误。(3)“一周一不周”。这说明的是, 有些结构形式相同的肯定命题或否定命题,有的要涉及其谓项范围的每个分子才能成立,有的则不必涉及其谓项范围的每一个分子即可成立。如果不注意到这点,以为既然结构形式相同,就一定或都要涉及谓项范围的全部分子,或都不涉及谓项范围的全部分子,就要出错。如“爱人”与“乘马”其语言结构形式相同,但“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这里涉及到“人”范围的全部分子;而“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这里就不必涉及“马”范围的全部分子。又如“不爱人”与“不乘马”其语言结构形式也相同,介“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这里不涉及“人”范围的全部分子;而“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这里就要涉及到“马”范围的全部分子。如果以为既然“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能成立,也就可类推出“不乘马,不待周不乘马”,就错了。因为在《墨辩》学者看来,“乘马,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和“不乘马,不待周不乘马”它们成立的条件并不为社会所约定;而“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与“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它们所成立的条件已为墨家有了规定。因此,“爱人”与“乘马”,“不爱人”与“不乘马”它们虽各自结构相同而各自所成立的条件不一样因而所涉及谓项范围分子的多寡也就不同,也即它们实际上并不属于同类,故不能从一周类推另一周。也不能从一不周类推另一也不周,否则就变成异类相推。(4)“一是而一非”。这说明的是,有的推论为什么可以用某种语言形式表达,也纯粹是某一时期社会的约定俗成。如不顾及这点,想绝对地套用这种形式去推及其它推论也可如此表达,则又导致谬误。如“居于国,则为居国”,为什么可以这样表达,完全由人们的一定社会习惯所使然,但如仿此形式也说“有一宅于国,也为有国”则错了,原因在于这种表达并不为人们所公认。一为社会所公认,另一则不然,可见它们实际并不同类,也就不可妄作类推。同理,可以说“桃之实,桃也”,介不能说“棘之实,棘也”,只能是“棘之实非棘也”等等。可见类推只能限于同类或同属性之间,不能扩及异类,按《小取》所言即是“有所至而止”。
以上所介绍的中国古代逻辑对有关“立辞”过程中所易发生的若干谬误情形而作的探究,比起现代逻辑教科书的有关内容来,可以说毫不逊色,这对于我们今天怎样才能避免推论谬误,实现正确思维,以及逻辑学怎样更好地为现实思维作出科学总结和指导等,无疑都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我们应该为我们有着这样一份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感到骄傲,并应继续发扬光大下去。但也应看到,中国古代逻辑所作的探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也难免存在着不够完善之处。如尽管中国古代逻辑学家以批评的态度指出了“立辞”中的“圣言之故”、“传闻之故”等谬误,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仍把圣人或“王制”等看作是非的标准。甚至在《墨辩》中就有这样的言论:“圣,无非”。“圣:若圣有非而不非。言合于圣人者谓之是不合于圣人者谓之非。”《荀子·正论》也说:“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这是中国古代逻辑学家在理论上不够彻底和中国古代逻辑未能完全摆脱政治伦理内容影响的一个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