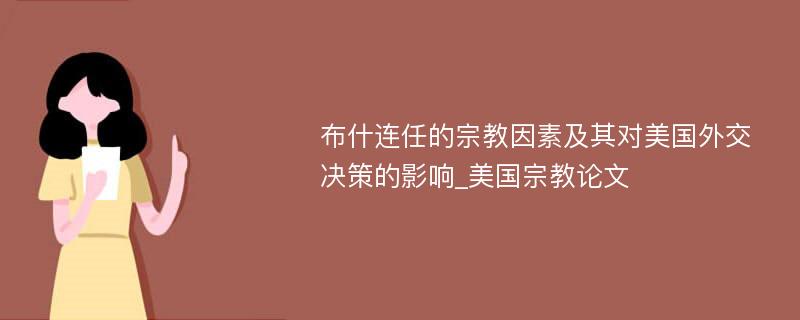
布什竞选连任的宗教因素及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什论文,美国论文,竞选论文,外交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期间,笔者有幸在其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亲历美国这一政 坛盛事,其间耳闻目睹有关宗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令作者颇有感触。如果说 作为社会润滑剂的宗教是对美国政府功能的补充从而服务了国家整体利益,那么它对外 交政策的影响则因导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而备受争议。
一、布什竞选连任战略与宗教议题
布什是以51%的普选票——自1988年他父亲以来的第一次和自1936年弗兰克林·罗斯福 以来第一位——在参众两院同时赢得胜利的总统。支持布什的“红色州”为他带来了高 出克里1.8%的选票,民意调查把这些人称为“带枪的上教堂者”,意指反恐和道德的结 合体。时任布什竞选顾问的卡尔,诺夫(Karl Rove)计划动员400万福音教徒参加投票。 尽管无法计算其中多少人被动员起来,但布什的选票中有一半以上确实来自那些经常参 加宗教活动的选民。事实上,大概有60%每周去教堂一次的选民投票支持布什,支持克 里者只有39%,尽管不去教堂的选民对二者的支持情况完全相反(34%对64%)(注:必须指 出的是,首先多数美国人都有宗教信仰,而且有信仰者往往又是政治上的立场坚定者。 以上引用数字见Alan Cooperman,Liberal Christians Challenge“Values Vote”,
Washington Post,Nov.10,2004.)。所以,布什的胜利被一些福音派基督教组织欢呼为 对诸如同性恋等社会问题持保守立场的强力证据。从这一角度看,宗教已成为美国政治 的分裂力量,把美国分裂为一个相信道德绝对主义的红色国家和一个“我活也让别人活 ”的道德相对主义的蓝色国家。[1]这不仅使不少具有国际眼光的美国人感到不解,也 让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颇为失望。
事实上,布什的总统生涯似乎早已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四年前他就是在奥斯汀的 一座教堂里正式宣布参加竞选并由此很快扭转了初期遇到的不利局面。在四年之后的竞 选连任过程中,布什再次得到宗教力量的鼎立相助。当然,宗教团体的支持并非一厢情 愿的表现,在布什竞选网站与天主教有关的8张照片中,4张是他2004年夏天去梵蒂冈时 与教皇保罗二世的合影,[2]尽管梵蒂冈对布什的外交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布什在强 调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努力争取到信徒选票的同时,还挑拨了克里与宗教尤其是反对堕胎 的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即使传统上的贫富问题与共和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28个低收 入州中布什赢得了26个,而低收入州过去一般支持民主党。所以有人不无夸张地说,如 果不是对同性恋结婚的限制动员了保守派教徒的选票,克里有可能赢得俄亥俄从而在大 选中胜出。[3]尽管这是一个难以验证的假设,但宗教对布什竞选成功的作用是不容置 疑的,有组织的宗教右翼显然比左翼的投票率高得多,二者之比大概是71∶38。[4]大 选后的民意调查显示,选民关注的前4位问题依次为道德观念(22%)、经济(20%)、恐怖 主义(19%)和伊拉克问题(15%)。[3]无论布什的宗教信仰是否真实,最关键的是他的信 仰将如何影响政府政策,尽管他自我标榜宗教信仰使他成为“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 ”。
具有政治投机心理的布什确实利用宗教达到了大选目的。布什的强硬、保守和一贯立 场特别是宗教正统形像,因正好可以迎合一些宗教保守分子的口味而得到其不遗余力的 支持。这就是为何没有什么比大约20%的选民把“道德价值”作为首要考虑更让民主党 觉得布什的重新当选不可思议的了,不少自由派分子已经笼罩在福音教派对布什竞选影 响的恐惧之中。有意思的是,相信小政府的共和党越来越转向将教堂作为建立联盟和赢 得选票的途径,由于这种做法经常逃过了媒体的追踪而成为共和党竞争选票出其不意的 杀手锏。随着布什2004年大选的获胜,美国现在似乎出现了一种世俗事务宗教化倾向, 即使是头脑清醒的自由派对宗教右翼将如何影响美国社会也深表忧虑。[5]许多分析家 认为,布什获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人以道德观为投票的依据,他利用颇具争议的堕 胎和同性恋结婚问题转移人们对伊拉克和经济问题注意力的竞选战略显然取得了成功, 从而把更为紧迫的战争和经济问题置之脑后。至于堕胎是宗教问题还是人权问题显然无 法简单区分,但堕胎是否非法、细胞克隆是否要禁止的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许多“蓝 色州”人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人人认同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大概三分 之二的美国人居然认为创造论应该与进化论一起进入自然科学课堂。[5]
作为对无处不在的宗教势力谙熟的政治家,布什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更多地 使用宗教语言,而且有些用语直接来自福音派本身。对于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而言,诸如 福音派、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这样的价值观不仅是美国的准则,也是上帝的要求。布什 的个人信仰则使他对于承担反对“邪恶轴心”、被召唤担任反恐战争总司令以及自封的 美国“保卫所有人类希望”等责任更加自信。布什不只一次地表示如果他不相信“一个 可以代替所有人类计划的神的计划的话”他就不可能成为总统。就在“9·11”发生以 后,迈克·杜斐(Michael Duffy)在《时代》杂志上撰文称,总统谈到“被仁慈的上帝 选择在此刻承担领导重任”;南方浸信会的理查德·兰德(Richard Land)回忆布什曾经 说“我相信是上帝希望我做总统的”。[6]所以,今天美国神学方面的真正问题不再是 宗教右翼,而是布什政府的民族主义宗教情绪:它把国家认同与教会认同混为一谈,把 上帝的旨意与美帝国的使命相提并论。长期以来就存在某种微妙联系的福音教派和新保 守主义在“9·11”之后关系更趋紧密。特别是作为布什内阁中新保守主义势力平衡力 量的国务卿鲍威尔的辞职,无疑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势力进一步得势,国防部里的强硬派 和新保守主义现在可以联手改造世界了,而一贯崇拜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代表共和党如 今越来越把实力和理念一并使用,企图达到两手抓的目的。
尽管世界舆论对布什当选报以一片反对和失望之声,但是,美国人的总统是由美国人 选举和决定的,其当选被认为最能体现美国利益。然而,正是恐怖袭击使布什能够重新 当选,“9·11”发生后的一周他采取的措施使选民相信布什是更安全的选择。恐怖袭 击使布什成为名副其实的战争总统。正如布什的前任笔杆子戴卫·弗洛姆(David Frum) 在《正确的人》(The Right Man)一书中所作的评论,“战争最终使他成为一个十字军 战士”,[7]入侵伊拉克之前他就恳求“上帝保佑美国兵”。布什不是因为伊战而赢得 竞选,而是尽管有伊拉克这个泥潭依然赢得了选民信任,表明无论对伊战争对错都无关 紧要,关键是美国利益至上。但奉行政教分离的美国目前出现的红蓝分裂局面难免使不 少有识之士担忧。宗教属于不能随意强加于人的个人生活层面,政府领导在公开场合发 表言论时不应宗教和世俗界线不分。
二、宗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自首批欧洲移民定居北美以后,这个国家的公众生活就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督教特征。 林肯说“几乎是被挑选的”美国人将继续为上帝而工作;而一种令人惊愕的论断则是: 《圣经》犹如一颗种子,落在美国这片已经耕耘好的土地上。[8]其实,宗教在美国从 来就是从统治者到一般百姓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工具,即使那些开国元勋也没有一个把宗 教作为自己的一贯信仰。尽管著名美国开国先驱如华盛顿、亚当斯、杰佛逊、富兰克林 和林肯经常援引宗教教义,但谁也没有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也就没有一个传统的基 督教派成为美国革命的先驱,[8]更没有任何一个基督教派始终如一地影响着美国社会 的政治方向。
宗教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孔不入,而美国人对宗教采取的则是实用主义态度。宗 教的作用十分复杂,无论人民日常生活还是国家政治层面都少不了它。二者之间相互异 动、相辅相成,形成完整的统一体。尽管不同的人对宗教在生活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 和解读,但宗教却影响到人生中从摇篮到坟墓的几乎所有重要阶段。人人生而平等的理 念既是独立战争时期人们利用宗教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借口,又是早期移民利用宗教实 现世俗目标的典型案例。尽管美国宗教林立,但各个教派能够做到井水不犯河水,相安 无事,这并不是任何国家都能企及的。这不仅使美国避免了像许多国家那样在宗教问题 上的麻烦,而且充分利用了宗教的社会管理功能。马克斯·韦伯在其《清教道德与资本 主义精神》一书中谈到了工作光荣的宗教道德,认为这种道德强调的不是教堂里的表现 ,而是工作上的成就,这就是为什么新教教义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精神。[9]另外,宗教 与科学在不少美国人身上的和谐体现也使其更加坚信宗教力量,致使个人生活层面亦与 宗教观念息息相关。最近新闻报导披露,现在美国很多药店拒绝出售与计划生育有关的 药品和用具,药店老板居然在避孕药和堕胎之间划等号。事实上,有关药物的关键性政 策和研究目前在美国已成为反堕胎政治的人质(注:前不久作者遇到一个保守组织的工 作人员,她向我们聊起该组织负责人甚至声称每个妇女应该生育30个孩子,表明美国保 守势力不仅反对堕胎,而且鼓励人们提高生育率,以平衡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过快。), 而日常生活中与宗教有关的种种忌讳也使宗教成为政治之外极易树敌的话题。
与许多其他民族国家相比,美国宗教经历着持续不断的演变过程。新教改革催生了20 世纪早期世俗的美国信条。其基本内容如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宪政主义和法治早在19 世纪初期的美国就已形成。但美国人比工业世界的任何其他民族都更乐于自由地改变教 派。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10个最大的衍生教派的成员几乎翻了一番,而6个最 大的主流新教派成员却减少了30%。[8]这表明主流教派的飞速衰退和至多始自20世纪的 福音教派的崛起。如果像一些历史学家推测的那样,衍生教派的快速发展就意味着一次 宗教“大觉醒”,那么美国正在重复一种使其宗教不连贯性更加显著的行为模式。[8] 这就会使教会组织缺乏连贯性,教义缺乏传承性,教徒缺乏历史记忆(尤其是共同的历 史记忆),现在与过去明显脱节,致使美国人正在重复他们上一代(而不是祖先)的行为 ,因为许多福音派运动的新成员都是没有共同美国历史观的新移民的后代。各种现象都 处在由一波又一波移民的加入而引起的动态变化过程中,不断冲淡渐趋形成的主流文化 ,使其永远处于新旧交锋与交融的变动之中,因此,在宗教文化上美国成为历史记忆遭 到不断泯灭和掩埋的没有正宗更没有正统的国家。当然,正是由于美国没有一般意义上 的传统文化,也就没有作为大众遗产从一代传给另一代的纯粹地域联系和传统观念(注 :当然,这种传统的缺失和地域的断层则使美国免除了许多其他国家司空见惯的民族分 离之苦。)。美国宗教的不断演变是为了适应并服务现实,信奉世俗现实主义的美国“ 非宗教化的基督教”便有了可怕的复苏力量,[8]不仅使其成为生活的助手也是精英统 治的工具。
2004年美国发生的大事不能排除反对堕胎问题,这不只是宗教右翼的胜利,在背后起 作用的更深刻动力是延续物种的基本冲动。首先,赢得31州选票而取得连任的布什就是 堕胎的反对者。其次,支持堕胎的参议员之一阿伦·斯派克特被威胁要失去其参院司法 委员会主席职位,除非发誓不阻止提名反堕胎的人选作法官(包括最高法院法官)。再次 ,2004年11月24日国会通过立法给予健康保险提供者拒绝参加堕胎的权利。由于生育率 低者多为白人精英阶层,而少数族裔特别是拉美裔和黑人的生育力旺盛,再加难以遏制 的非欧裔移民的涌入,致使不少人口学者一再提出的美国将于2050年前后成为白人少数 民族国家的警告令人惊醒。为了以宗教为外衣达到增加白人人口的目的,人们骨子里更 自然的方式当然就是提高生育率(注:这里的提高生育率主要指白人生育率,因为黑人 和拉丁人等少数民族的生育率几乎已达到了极限。)。所以,堕胎这个在不少国家司空 见惯的问题,在美国却变得越来越严重,并将成为一种理念渗透到外交实践。对于出生 率低的补救办法之一是增加移民,然而这却具有强烈的争议。难怪有“家庭观念”倾向 并带有限制堕胎冲动的候选人提出的“倾向家庭”政策会深受欢迎。从竞选地图看,“ 红色州”的“倾向家庭”者一般都有更多子女,意味着未来他们比“蓝色州”有更多选 民,尤其在一些保守的中小城市更是如此,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推理:宗教保守→ 反对堕胎→增加人口→减少移民→种族歧视→排外情绪(注:与克里相比,布什显然具 有更多的白人正统观念,所以布什的胜利其实就是美国白人正统压倒一切的表现。)。 但问题在于美国人的立场往往并不限于内政,对于堕胎等与计划生育有关的问题必将成 为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敏感话题。
不少社会学家认为过去20年美国变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即所谓“选择的共和”。[ 10]其特点是法律上的“权利革命”、政治上的“选择自由”、经济上的“消费者至上 ”、立场上的“挑战权威”和意识形态上“赤裸裸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显然就是新 教世俗化的极端表达。但基督教的原罪说与美国人崇尚的自由意志并不协调,所以不符 合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口味,但一旦抛弃了原罪说就必将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老路上 去。正是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自豪感成为无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力之源,即使宗 教也慑于强大的国力而俯首称臣,因为宗教终究是由人创立的。
三、宗教因素对布什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
“9·11”之后布什总统干脆把白宫变成了布道的神坛,他经常就美国的世界作用使用 “召唤”、“使命”和“责任”等宗教词汇。布什想方设法使美国人相信美国正在从事 一场正义与邪恶的道德之战,在这场神圣的冲突中那些不与“我们”在一起的就属于邪 恶的一方。但问题在于“我们”是谁,“我们”中间是否也有邪恶存在?似乎在布什的 词典里,如果不使用邪恶一词就不是什么好神学。但是,把“我们”说成好的、“他们 ”是邪恶的,不与“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逻辑显然也不是什么好神学。但 不幸的是,这就是布什的神学。
回顾美国历史可以发现,布什外交理念中的宗教成分并不新奇。美国历史上的“山巅 之城”、上帝赋予的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天定命运”以及美国民主模式等,无不带 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但在19世纪美国很少有机会把意识形态应用到外交中去,到了20世 纪它突然有了很多机会。20世纪初美国外交中的基督教意识包括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 克林·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如威尔逊似乎相信自己是在执行上帝的意志。有人认为一战 之后美国进入了孤立主义其实是一种错误看法。事实上,美国只是退出了欧洲,而且只 是从安全和军事角度退出。同时美国却在拉美及东亚加紧了渗透。美国之所以退出欧洲 是由于它认为不可能把这些经济发达、军事强大和政治独立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加以 改造。而拉美和东亚(除日本外)则具有被改造的可能性。所以,美国执行的是一种见风 使舵的双重标准:当一国与美国相比国力强大时,美国外交就趋于谨慎,实行现实主义 或“孤立主义”;当一国与美国相比弱小时,理想主义冲动就使美国决定按照自己的形 像来改造它。但对于从威尔逊到罗斯福再到小布什的多数总统而言,机会是必要的条件 。“9·11”袭击无疑是恐怖分子提供给布什推行具有宗教色彩外交政策的机遇。正如 芝加哥大学的基督教学者马丁·马逖所说,“今天福音教派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具有天才 般的活动是其对草根民众的吸引力”,“福音教派随时准备把上帝的旨意称为自己的。 如果上帝召唤我们做‘正义之国’,他们就响应。”[11]
二战之后现实主义对付强大敌人、理想主义对付弱小对手的美国外交实践在美苏争霸 的中间地带得到充分发挥。在西欧和日本,美国推进自由民主但接受那里对自由市场的 限制;在拉美和东南亚,美国接受对自由民主的侵犯却继续推动其自由市场进程。尤其 是苏联的解体、德国和日本资本主义的相对衰退以及近来亚洲国家转向市场经济说明, 所有美国之外的政治经济制度选择都被认为是不可取的,而基督教和商业则是不可分割 的。现在美国可以放开手脚追求普遍人权目标,克林顿政府甚至把人权、自由市场和自 由民主看作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应灵丹。如今布什政府把阿富汗和伊拉克作为理想主义的 试验场。美国信条已增添了普遍人权的概念,或更确切地说美国信条产生了普遍可用的 公共产品。但正如亨廷顿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美国人权观念的普遍性和美国个人主义 模式的至上性在那些有着不同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社会引起了普遍的憎恨和抵制。亨廷 顿把它称为“文明的冲突”,一场“西方与其余世界”的斗争。[12]他认为美国信条在 基督教社会几乎不受抵制,在罗马天主教社会会有一些抵制,但在伊斯兰和佛教社会则 会遭遇强大抵制。尽管这种推理乍一看似乎不无道理,但亨廷顿过于强调文明与宗教引 起的对立和冲突,显然忽视了美国霸权野心所引起的包括盟友在内的普遍反对和抵制。 他的理论在解释美欧围绕伊拉克问题的冲突时就显得苍白无力。
但是并不能由此否定宗教因素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在智囊机构哈得逊研究所 的新保守派霍洛魏茨(Horowitz)先生的领导下,福音派正在以其长期以来的道德狂热追 随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宗教目标。自1998年以来,他们就帮助赢得了联邦立法以对付国外 的宗教迫害,使美国最具孤立主义传统的福音教派给美国外交打上了烙印,尽管一开始 企业组织和公务员反对就国际宗教自由进行立法。[11]近年来,人数上破记录的福音派 教徒被煽动参与全球短期传教活动,2001年就有近350000名美国人通过各主要宗教机构 参与了传教活动,与1996年相比增加了6倍,还不包括个别教会尤其是在美国迅速发展 的“圣灵降临节”所资助的无以数计的传教士,从而使很多教会成为国际人权事务的积 极追随者。[11]宗教组织以公众外交的形式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新的选择,而外交政策上 的公共选择当然就是普遍的人权概念。至少目前而言,福音派在华盛顿终年不断的现实 主义与理想主义外交的竞争中略占上风,前者认为美国改变世界的能力有限而且也不应 该尝试,后者则试图赋予美国外交以道德目的。正如有福音派先锋之称的参院外交关系 委员会成员、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山姆·布朗柏克所说,“我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主 宰地位的国家。我们必须谦卑明智地行事,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而 且是为了在道义上公正。”[11]这里的所谓“公正”无非是美国现实利益的巧妙伪装而 已。
福音派对外交事务日益增长的卷入为海外干预提供了新的支持基础。2004年4月的一份 民意测验发现,那些每周至少上一次教堂的美国人中间有56%支持布什的对伊政策,而 那些很少去教堂的人中持同样观点者则不足45%。[11]对于某些福音教徒而言,当前皈 依穆斯林教徒就成为迫在眉睫的神圣使命,尽管严厉的伊斯兰教规对改信其他宗教者可 能是死亡惩罚。对于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布什总统本人有时也使用“天定命运”概念。 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自由是万能的上帝给予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礼物,当被问及在 对伊政策上是否咨询过父亲时,他说他还有一个必须咨询的更高明的父亲(即上帝)。但 为了通过武力而寻求使古老游牧社会民主化,美国发现这个过程对于入侵者和被入侵者 而言都是十分痛苦的。在伊拉克进行的颇具灾难性的占领向人们提出了在曾经经历过美 国式政治或经济改革的许多其他地方经常听到的问题:美国价值观在美国以外究竟具有 多大的可行性?而且不无讽刺的是,恐怖分子在“9·11”后多次宣称美国所受的袭击是 对其一向信奉的所谓“楷模”、“典范”的攻击,具有自知之明的政府领导一定会深刻 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从“9·11”以来的情况看,布什政府对这样的念头毫无兴趣 。相反,推广民主和宗教自由不仅成为美国的一项道德事业,而且认定它关乎到国家安 全。毫无疑问,一国具有什么世界主导地位是一码事,但把军事胜利和外交政策与什么 宗教使命联系起来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纵观布什政府过去四年的外交思想,由于上台之初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而给其外交报 复行动增加了某种宗教色彩,如布什在一些讲话中甚至使用“十字军讨伐”之极端表达 ,并对拉登的基地组织展开了一场颇具“圣战”色彩的复仇行动。保守派对国际社会的 日益不信任必将驱使政府对外更多使用武力手段,尽管伊拉克的烂摊子可能成为武力冲 动的绊脚石。但组织良好、动机强烈又信心十足的福音派目前正准备在三个外交目标上 施展拳脚:一是试图将穆斯林世界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可能还有乌兹别克)皈依基督教, 二是把未来美国对北朝鲜的任何援助都与人权挂起钩来,三是锁定伊朗作为下一轮实施 宗教“改造”的对象。正如南方浸信会的兰德先生解释宗教作用时所说,如果没有宗教 自由作保证,美国公众对重建这些被入侵国家的支持将会消退。[11]可见,美国外交不 只是先发制人,而是在神学上的胆大妄为;不只是单边主义,而是危险的宗教狂热;不 只是傲慢无理,而是接近偶像崇拜和亵渎神明。这无疑是糟糕的外交与糟糕的神学危险 的结合。
四、简单的结论
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保守”一词并没有什么贬意色彩,而是指希望维持传统生活 方式和价值观的一种心态。但对于多数美国人的信仰而言,还有许多其他更为重要的道 德问题,这就是宗教中间派的立场。[4]毫无疑问,每位基督教徒都希望被上帝召唤以 体现对基督的忠诚。但是,如果一位总统相信国家正在完成上帝给予的正义使命而他本 人正为这一神圣召唤服务的话,则是令人不安的。正如神学家马丁·马狄(Martin
Marty)表达了许多人的担忧:问题不在于布什的信仰是否真诚,而在于他那明显的信念 即认为是在行使上帝的旨意。布什总统更多地使用宗教语言,但糟糕的是以一种歪曲的 方式来引用,即把圣经中有关基督的神力当作美国人的神力。正如他在“9·11”一周 年纪念演讲时说,“美国的理想是所有人类的希望。这一希望仍旧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 。光芒在黑暗中闪烁。黑暗没有压倒光芒。”[13]这最后两句直接出自约翰福音的话讲 的是关于上帝与基督,而不是美国及其价值,所以人们有理由担心布什正在把真诚的信 仰与国家意识形态混为一谈。
美国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它的精力、效率和作为清教改革遗产的组织功能。然而,由于 其普遍性和个人主义信条而试图皈依一切民族国家的宗教狂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世界 发生冲突。正如当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使用宗教征服世界其结果加速了自身解体那样 ,美国的宗教征服也必将面临同样下场。而且,美国仍然在主要是由其独特的地位引起 的一系列威胁和依赖中挣扎: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却不可避免地依赖其他国家取得能源 和贸易;能够轻易地征服却难以对付随之出现的问题。一句话,一个有力量有野心主导 世界的国家最终却不得不只关注自己。所以人们有理由对福音教派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感 到忧虑,如哈佛神学院的戴卫·莱梯尔(David Little)认为,“通过强调一种价值观如 福音教派,你可能不得不疏远这个多宗教、多文明的世界。”[11]而且,如果海外发生 宗教冲突,美国总统可能面临以牺牲美国战略利益为代价而要求援助冲突中的基督教派 的压力。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国内国际上对布什政府过去四年的外交颇有微词,但他的成功连 任尤其是作为对伊战争象征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留任,将使布什对自己外交决策 的“正确性”坚信不移,并予以延续。比如在反恐问题上,可能更多的是进行技术和情 报上的完善,而不是重大战略性转变。连任总统更加“外向”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 尤其是准备留下遗产的布什已跃跃欲试。即使对伊朗动武,美国恐怕不会再采取伊拉克 式的大规模地面入侵,因为既没有如此规模的兵力储备又要吸取伊战后的惨重教训,可 能的情况则是科索沃式的空中打击,尽管策划政变的选择亦不能排除。显然,民主的推 行不是由于大家都是好人,而通常不都是好人的被迫选择。所以,民主提供了一种制度 以制约和平衡任何人得到过多权力。对国家而言是这样,国际关系亦如此。诸如外交、 干预、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大问题最好由国际社会多数国家集体解决,而不是尤其不能让 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垄断。
美国大肆宣扬其宗教理念的做法不无启示:中国学习他人之长固然是对外开放的目的 之一,但绝对不能因丢掉自己优良的文化传统而丧失自我认同。事实上,美国之所以把 实力相差悬殊的中国当对手,就是由于她拥有在文化上能够自成体系的几千年的文明传 承。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源于西方传教士充当过列强侵略中国的鹰犬;今 天在人权和计划生育等问题上美国强行向中国推销自己的标准则是十足的霸权表现。但 对美国实施的宗教攻势亦应采取简单戒绝之外的更聪明策略来回应,因为宗教这种思想 意识影响不是什么简单命令可以消除的。总之,由于中国是不同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佛 教国家,所以被认为在宗教上与西方誓不两立;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不能随意征服或改造 的大国,美国对中国只能实施遏制和对抗。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表明,美国 的遏制或对抗都不奏效。如果中美必将对峙,那么中国既要吸取苏联与美国愚蠢地“硬 拼”的惨痛教训,也不能像俄罗斯那样因试图与西方合穿一条裤子而反遭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