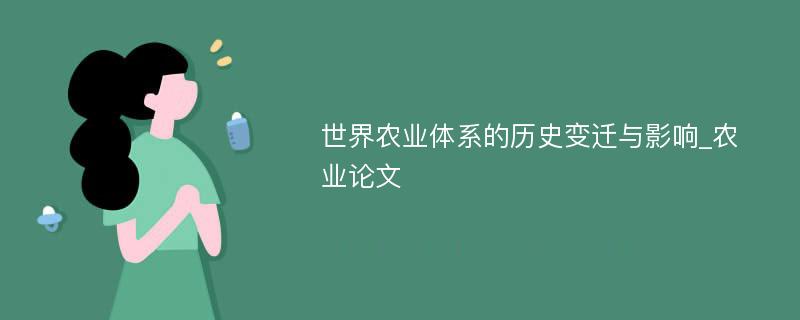
世界农业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功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效论文,制度论文,农业论文,历史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的农业正在面对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农业将如何养活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尽管人口的生育率在世界范围内会持续下降,但世界的总人口却会稳步上升,在2050年的时候将超过90亿人,随后才会开始减少。这一状况意味着世界农业必须生产出比现在多大约50%的粮食,而条件是在比现在更少的土地上,基于更少的水,投入更少的化肥、除草剂、杀虫剂①。当今世界人口的食品消费转向也让问题变得严峻。最近几十年来全球的人均收入都在急剧增加,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导致了人口的食品消费正在从边际收入食品(谷物类和块茎类等)转向弹性收入食品(肉类、奶类制品及其它相似的产品)。而在这一转向中,弹性收入食品所产生每一卡路里热量将比谷类、豆类、块茎类所产生每一卡路里热量耗费更多的资源。
如果纯粹推论,那么全球粮食需求的增长速度可以比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例如,世界的饮食方式也许会向节食方向急剧转变,沿着“素食主义者”(吃鸡蛋和奶制品)到“素菜主义者”(不吃鸡蛋和奶制品)的道路一步步走下去,只需更少的资源。长寿的追求者们为复制那些在实验老鼠身上所做的研究,会减少每日卡路里的摄入量以增进健康和减缓老化过程,因此而减少了人均食物需求量。但是,文化人类学家业已发现,在生活实践中人们的饮食方式和进食习惯很难改变。更可能出现的情形是:随着耕地的减少,粮食作物再分配至能源部门用于生产乙醇、生物柴油等的比重增大(取决于相应的油价),如何养活增长的人口会变得极为严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提高粮食产量和粮食生产的效率极可能会成为全球的一个中心议题。
作为一名研究农业的经济史学家,我想我们可以借鉴历史来思索未来增加粮食产量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对策。我认为人类未来的最佳选择是向一种新型农业制度实行持续的转变。在这新型的农业制度中,转基因甚至克隆将发挥显著的作用。我在本文中将引证历史上农业制度变迁的功效及其所蕴含的意义来说明我的想法。任何预言都会有缺陷,但如果过去1万多年的经验能具有启发性的话,那么总的来看,世界农业制度的历史变迁是有着积极功效的,尽管它也导致了问题及出人意料的后果。
就世界农业制度历史变迁的认识而言,20多年前(1987年),著名的进化主义生物学家贾热德·戴蒙德在《发现》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史上最大的失误》的令人瞩目的短篇文章,批判了“新石器时期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②。所谓“新石器时期革命”,是指在10000-12000年前世界的一些地区独立地并且大致同时地发明了农业。戴蒙德深入地研究了近几十年的学术思潮,向权威的关于新石器时期革命对人类及人类社会产生了成就与影响的著述发起了挑战。戴蒙德对西方的历史发展线性观和进步主义论表示怀疑,对关切人类命运的思想、理性、科学、技术乃至全部的现代主义认识也有疑问。他认为,如果按照“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来考察,农业的发明所导致的是人类福利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净下降,而不是纯粹福音。
戴蒙德有意地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出挑战性。但他的论断,无论有多夸张,是以人体人类学家、经济人类学家、生物考古学家及史前病理学家业已完成且数量日益增长的学术著述为基础的。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学者们一直在拔高农业社会以前采集者与狩猎者经济状态的结论。马歇尔·沙林斯在其1972年的著作《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指出,采猎者们已形成了“原始富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③。科恩与阿姆拉格斯所主编的《农业起源时的史前病理学》一书(1984年)也从人体健康的角度对农业发明前的人群和社会予以了肯定④。在戴蒙德的短文发表后,学术界没有提出不同的观点,相反,大家普遍认为采猎者们在物质生活上过得非常不错。
按照戴蒙德等学者的看法,采集者与狩猎者的社会以丰富的食物供应为特征。采猎者们无须花费过多的劳动就可获得营养平衡的、富含蛋白质的饮食。由于人口密度小、不用与驯养的动物紧密和持续地接触,采猎者们患病情况相对轻微。至少,从现存的人类骨骼分析中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简言之,由于不存在营养不良和传染病,人们可以解释采猎者们已经达到的并且是相对令人印象深刻的身高水平、强壮的体型和相对的长寿。
随着农业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变得糟了,至少从戴蒙德的反进步、反技术、原罪前的镜头里看过去是如此。尽管戴也承认农业的发明和动物驯养提高了能量的利用率和单位土地的卡路里热量输出,但在他看来,新石器时期革命根本不像人们认识的那样伟大。按照戴的观点,农业发明的最终结果是一系列连锁的问题和危害,以致这一发明可被称之为“人类史上最大的失误”。戴认为,在评估由农业和家畜所带来的好处时,人们必须衡量所付出的成本,其中包括更辛苦的日常工作、较不均衡的饮食、较大的食品不安全性。这些成本常常导致健康不良,虽然还不是营养不良或饥饿。但这些只不过是戴蒙德全部理论的开头而已。由于农业导致了人类的群居与动物的集中,流行性传染病变得更加普遍了。繁重劳动、恶劣饮食和高发疾病有力地纠结在了一起,意味着与采猎者相比,耕作者在身高、体型、总体健康状况和寿命方面相对很差。戴还谴责农业的发明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包括不断深化的阶级差别(农业带来了粮食的剩余和粮食仓储的差异,使不平等成为可能),以及妇女地位的持续下降。由于农业制度对劳动力的需求日增,妇女们常发现她们的地位不过是生育的机器。
戴蒙德正确地让我们注意到了农业发明的负面效果,但他的论述更值得批判,因为农业发明更有正面功效。至少对我而言,这些正面功效业已证明为无法衡量的伟大,其影响具有无法触及的深远。如果没有农业,没有它不断增长的产量和利用率,我们将不会处于一个发展的进程中。这一进程在过去1万年里已缓慢地、非均衡地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劳动的高级分工和专业化以及“较次要”的社会与文化的同时发展,如城市、国家、写作、艺术、音乐、文学、数学、宗教、哲学、科学,等等,尽管戴蒙德对这些现象不予考虑并屡加嘲笑。
在戴蒙德看来,当时的游牧者和采猎者的生活比耕作者要差的结论并不准确。例如,卡拉哈里沙漠的丛林人(bushmen)和坦桑尼亚的哈德扎人(Hadza)就吃得很好,有大量闲暇时光,且睡眠充足。可是,我们有谁愿与丛林人和哈德扎人置换我们拥有的一切吗?戴关于新石器时期革命对人类并非是纯粹福音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但他对于农业发明的过度指责和对农业发明功效的批评是可笑的。在后来出版的《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中(1997年),戴对其1987年认识有所修正,但他仍然认为,人类的能动性、创新、物质主义和唯我独尊的结局必然是社会的崩溃,这一崩溃的源头就是10000-12000年前农业的发明。这真是让发明农业的纳图夫人和闪族人、农业文明最早的单粒麦与双粒麦不堪重责。
根据大多数的权威研究,农业最早是在5—9个地区独立出现,随后农耕和畜牧才逐渐传遍整个世界。今天在世界上还残留着少数采猎者的社会,即使它们也可能在不久后就不会再存在。从大跨度时间看,农业社会总的来说在技术与效率方面的变化不大,但在某些特定的时段,有些农业社会经历了超越渐进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些变化归纳为制度变迁的革命。
毫无疑问,比喻性地使用“革命”这个词汇总有着因各种理由所导致的困难。例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Balliol College)讲到英国经济在18—19世纪的变化时,第一次使用了“工业革命”⑤。他认为英国的经济变化正如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政治变化一样具有着深远性,于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了“革命”这个词。但法国大革命通常被视为有着确定的起点与终点,而“工业革命”的时段在英国、欧洲大陆、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难以被界定。就英国而言,即便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认为在18—19世纪的某个时段内确实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变化,但1790-1850年、1800-1860年、1820-1870年这三个时段都有各自有力的支持者。更有许多人依然反对使用“革命”的比喻,认为变化并不剧烈或突然,而是渐进或累积的:没有断然的起点,也没有急剧的失衡,增长的曲线不过是以一束优雅上升的斜线。对于“科学革命”、“消费革命”以及“后新石器时期的农业革命”,学者们也存在着类似的辩论。
无论使用何种词汇,现存证据都已不容置疑地表明,在1800年之前的1000年里,世界上一些地区的农业确实有了一定的发展,期间生产率获得了提高,农产品质量发生了变化。这些成长期标志鲜明,以致我们足可将它们与长时间的模式与趋势清楚地区分开来。世界各地的学者已出版了大量的著作,经常使用“革命”来比喻或描述这些成长期,其中包括阿拉伯农业革命(700-1100年)、中国明末至清初和清中期的农业革命、英国农业革命、苏格兰农业革命、朝鲜农业革命(18世纪)等。
这些农业革命在许多方面不尽相同,但却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作物、耕作和畜牧方面的重大创新;新型农业技术与农产品加工技术的发展(常以机械化为基础);生产要素的合理化应用;专业化与商品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市场的开发;还有农业营销与融资的新方法与手段。显而易见,并非人人都从这些变化中获益,从“革命”中获益的人也并非都是平等地获益。但与戴蒙德不同的是,我在思考农业起源时认为,从平衡的角度看,农业革命的发生是一件极好的事。如果没有农业革命,人类至今仍会如今天某些不幸的农民一样艰难度日、勉强维持生计。这些不幸的农民未能享受到上述农业变化所带来的好处,而那些较幸运的农民和农业群体则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享受过了。英国农业革命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
就在两代人以前,英国农业革命还是每个受过教育的人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每个小学生都学过或至少是听到历史老师讲解过英国封建领主和农民的历史,了解过“平民”、公地、圈地,村民与佃农,苜蓿、豆荚、芜菁,以及“诺福克制度”(Norfolk System,一种饲料作物的轮种制度)和休耕制的知识。人们会对“萝卜”汤申这个名字发笑(“Turnip” Townshend,即查尔斯·汤申子爵,英国17—18世纪政治家,将饲料作物轮种制引入了英国),会对杰思罗·图尔摇滚乐队与英国农业革命先锋人物杰思罗·图尔(Jethro Tull)同名感到欣喜,或许还会带着敬意阅读神秘的斯温队长(Captain Swing)所领导的叛乱。
在今天,随着农业史淡出主流学术舞台,英国农业革命的许多知识已经遗失或被错置。学生们所能学到的大体上只是经过梳理的口号,固定的片段以及打包成段的描述,并且都带有左派与绿党的色彩。这些口号、片段和描述展示出平民地位的下降、圈地运动的恶果、乡村社区的萧条、资本主义农业贪得无厌的剥削和掠夺、农村阶级分化的加剧,还有我们委婉地称之为“改良”的阴暗面以及恶意使用剩余积累。就在前不久,我们还更进一步被提醒:英国农业革命的许多创新实际上一点也不新,不过是其他地区技术发展中玩剩下的遗物,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东方的其他地方。
这些口号、片段和描述并非全然无据。毕竟,英国农业革命是复杂的,涉及了许多方面,充斥着“难以下咽的罪恶”,充满了痛苦。但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更加正面的方式来认识这些论点。平衡地看,英国人,不管其是否是农民,都从农业的革命性变化中获取了重大的好处。
关于英国农业革命研究,当今有些学者追随历史学家艾力克·科瑞杰,对16世纪与17世纪早期给予特别的关注,大部分学者则把重心放在此后的发展⑥。让我们撇开关于英国农业革命的编年和断代来进行认识。在今天,我们越来越把英国农业革命视为“早期近代”(early modern)的一部分,一个从1500年开始直到1800年或1850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英国农业革命不过是发生在农业部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日益以科学为基础,或以系统的经验理性为基础,在时间的推移中导致了产量和生产率的巨大成就。
这些成就来自于各类和各种水平的“改良”,包括圈地、机械化、新的农作物、科学的育种计划、四套作物轮种法(four-field crop rotation)⑦、农业营销和金融方面的创新,或许还可以包括“勤劳”价值观在乡村人口中的传播。“改良”所导致的成就以多种方式支撑起了人口与收入的增长、城市化、工业化,或者说,农业的变化为英国迈入现代经济提供了保证。一些学者将此进程视作为“良性循环”,另一些学者则将其称之为“大转型”。
我们可以特别考察一下英国农业革命培育并支撑起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方式。首先,农业革命使得食品价格相对下降。除了1760-1800年这一段非正常时期外,原先花费在食品上的一部分收入可以空出来用作他途,包括商品消费和投资,这一事实本身就刺激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其次,农业效率的提高导致了农业部门减少了对劳动力需求,让劳动力可以自由地去其他部门寻找工作,尤其是进入制造业和采矿业。无疑,声称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被“释放”了出来不啻是用糖衣来包裹苦涩,因为“释放”对于许多人而言意味着匮乏,假如不是完全的饥馑的话。但任何一种革命,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工业的或农业的,几乎都不会是美丽的。历史上的大人物之一斯大林入木三分地指出:“如果你想做个煎蛋饼,你得打碎几个生鸡蛋”。我本人有幸于20世纪中期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发达地区——芝加哥,但那个地区的制度变迁,特别是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也同样不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今天亚洲一些城市的血汗工厂也可以说明问题。但诚如《纽约时报》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最近提醒我们,比血汗工厂更糟的事情就是连血汗工厂都没有⑧。再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农业所使用的原料与工具越来越多地在远离农地的车间和工厂生产。这种情形刺激了非农业劳动力的雇佣,并促使城镇与乡村、工厂与田野之间产生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最后,英国农场生产率的日益提高,也同样刺激了粮食加工业与纤维加工业对非农业劳动力的雇佣需求。通过以上这些方式,英国农业革命形成了一次农业制度的变迁,它纵然不是英国经济现代化的催化剂,也至少起到了支撑的作用,让英国在18世纪后半叶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
借用马克·吐温的话来说,历史从来不重复自己,但它有时会押韵。在以上提到的例证中,农业革命都促进了各自社会的发展,虽然有着方式的不同。第一个千禧年中阿拉伯世界农业革命的总体效果与18世纪朝鲜农业革命的总体效果有着巨大的差别,但这两次农业革命,按已较为透彻的研究,都平衡地提高了农业的产量与生产率,极大地造福于各自的社会。诚如在英国一样,这两个社会每有一个遭遗弃和剥削的农民,就有更多、更多的人获益。历史是在押韵!
大约从1800年左右开始,世界农业制度的变迁逐渐转向了产业化(industrialization)。我倾向于用一种广义而非狭义的视角来理解农业的产业化的进程。狭义地说,产业化指在一段持续的时间内,一个经济体从其农耕、渔猎和采集的“主要”活动向着制造以及所谓“次要的”经济活动相对转移。但从更广阔视角来看,产业化意味着在经济生活中系统地利用科学知识来促成生产率达到历史性的高度。按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农业的产业化在18世纪里已像一艘“聚满蒸汽”的蒸汽轮,从此便一直加速航行,尤其是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
确切地说,从许多方面来看,农业领域中的全新的、革命化的产业制度和科学制度在20世纪里已变得日益成形。这一成形基于三个独特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产生于1900年前后,第二个始于20世纪60年代,第三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延伸至今。这三个转折点都改变了农业发展的轨迹。每个转折点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产量和生产率,导致了农业的结构与组织发生变化,造成了部分人的痛苦与艰辛(还有恐惧与憎恨)。但平衡地看,每个转折点都为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提供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第一个转折点始于美国科学家“重新发现”孟德尔之后。1900年前后的“发现”孟德尔无疑造就了现代遗传学的兴起,并于20世纪30年代在农作物领域中带动了品种杂交,尤其是玉米。一方面,杂交品种很重要,不同植物品种或品系按规划杂交所产生的后代通常能够提高产量和效率。由于杂交的活力或杂交优势让农民们增了产,同时又相对减少了大批量农作物对土地的需求,于是杂交品种迅速地被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农民所采用。另一方面,或者说更广义的方面,杂交农作物一旦被引进和广泛传播,就显示和标志着科学知识在农业生活中的产业化与制度化的过程开始。这一发展过程既包括机械化方面意义深远的进步,也包括生产、运输、加工、营销和金融服务等领域里增进效率的各种创新。到了20世纪中叶,新的发展在发达国家里已急剧地改造了农业,以致这些国家可以很轻松地养活其全部人口而无须很多农民。例如,在1950年,农民仅占全美国劳动力的11.6%,而1930年他们却占21%,1900年则占整整40%。这一变动对发达国家的一部分人来说是痛苦的,特别是对于经济规模较小、资本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偏低的那些农民,这是一个让他们备受挫折、陷入社会错位的时代,不少人或是破了产,或是利用自己的剩余的劳动能力在科学与资本主义日益主控下的农业世界里谋求生路。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社会中的其他部门则充分享受了农业变化所带来的好处:日益增多的廉价食品、日益增长的实际收入、更多的渴望工作的劳工,以及由城市工厂与农业相关部门所创造出的更多的工作岗位。无疑,这是一种良性的经济循环,虽然不完美。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的、产业的、生物的农业飞快地传播到了欠发达世界,其中美国政府和墨西哥政府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努力、还有洛克菲勒和福特等基金会的努力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些努力导致了20世纪农业产业化的第二个转折点。在资金、理想主义以及冷战意识形态狂热性和自信心的影响下,一批富有才华的植物学家、土壤学家、农艺学家和农业经济学家改革了某些欠发达国家农业部门中的重要领域,启动了一轮迫切需要的农业制度的变迁,即“绿色革命”,重点是在当时被称之为“第三世界”的一些刻意选择的地区,特别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不幸的是,当然也并非令人惊讶,“绿色革命”在今天常沦为嘲笑的对象,虽还不至于是厌恶的对象。嘲笑者中包括老一套的左翼分子、环保主义者、反全球化人士、阿伦达替·罗易等布克尔奖(Booker Prize)的获得者以及好莱坞与宝莱坞的一批过气影星,总之,是一群名人⑨。虽然他们的某些批评不无价值,但大多数的批评是失衡的、文不对题的、缺乏对绿色革命功效的认识,是精英主义的、自以为是的,其效果恰好与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相悖。
按照今天的评判,或借用詹姆斯·斯科特的话来说,绿色革命是一个体现了“高度现代主义”的项目⑩。或者说,在“绿色革命”中,国家、半官方以及基金会的倡导者们采取了一种过度的理性化、以技术为中心、以官僚体制运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科学研究、传播新生产技术、追加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提供杂交品种、提供产品营销渠道以及劝诱目标生产者们接受新价值观念,以实现在食品匮乏地区或接近匮乏的地区提高农业产量和生产率。通过项目提倡者、工作者和官员的努力,绿色革命“礼包”中早先的礼品,包括高产良种品系(HYVs)、商业化肥、拖拉机、灌溉系统、度量器具和最引人注目的大量资金,一一进入了欠发达世界的各个地区,特别是南亚、东南亚、土耳其、墨西哥。这个礼包所导致的成就具有着无可争辩的积极性。诚然,我们不能也不应缩小绿色革命在一些地区造成的环境破坏,或缩小一些群体特别是穷人所遭受的负面经济和社会后果。但平衡地看,绿色革命一旦在足够大的范围内展开之后,就被证明为每个国家带来了净受益。它导致了小麦、水稻、土豆、玉米令人难忘的历史性的高产量与高效率;为农业部门和准农业部门带来了收入的增长;最重要的是它还增强了那些人口高度集中并且人口仍在迅速增长中的国家的能力。那些国家曾饱受食品短缺的威胁,不仅要养活人口,还得不断增加农业设施。对于绿色革命的实践者们,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曼·伯劳格、斯万米纳汗和最近刚去世的吴雷,整个世界应当衷心感谢(11)。不管他们的科研和田野工作是否完美,数十亿人却因此而免遭饥饿之难。绿色革命也争取到了至少20年的时间,容许世界顶尖的农业研究者在绿色革命的一些权宜之计用完之后仍有时间来设计新的农业战略和新的农业工具,以解决日益增长人口的吃饭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业研究者们在现代农业持续不断的和近乎永恒的产业化进程中触发了第三个转折点:转基因研究和转基因农作物的引入。尽管当今存在着许多关于转基因农作物(genetically-modified crops)、转基因有机体(Genetically-Modified Organisms,简写为GMOs)以及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但转基因农作物基本上应被视为是早先育种创新的必然延续,是基于孟德尔学说传统的育种创新。不过,转基因不止是同一物种下不同品系或品种的基因交叉,也不止是近亲物种之间基因交叉,而是可以让相隔遥远的物种之间发生关系,将基因从一个物种插入到另一个物种。这方面工作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将鱼的基因移插入草莓,以使草莓能耐寒。这一案例足以证明发生基因转移的两个物种间距离有多么远。很显然,这一尝试是一项商业上的失败,因为没有几个消费者会嚷嚷着要吃带有沙丁鱼味道的草莓。但须严肃对待的是那些采自于细菌、病毒或不同植物的转基因,虽然这些转移基因业已部分地被证明为有着提高产量与生产率以及改善人类膳食的巨大潜力。通过插入方式所获得的转基因有机体改变了作物的营养成分。例如,2000年1月在稻米的育种过程中插入了贝塔胡萝卜素(即维生素A)后,便有了所谓的“黄金米”。转基因技术同样也可以创造出对除草剂和杀虫剂具有抵抗力的作物,改变作物的成熟期限,造就出能抵御昆虫的作物。转基因技术还能够以多种非常积极的方式影响农业产量、生产率、农产品价格以及田间劳动力的安全。最后再举一例:几年前在中国,当4百万小规模生产的棉农种植了抗虫害的转基因棉花后,他们的棉花产量提高了20%,杀虫剂使用减少了78000吨,棉农因受杀虫剂毒害而死亡的年死亡人数量大幅下降(12)。这个例子可以说是一种小型的良性循环,尽管只是发生在棉花生产领域。
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有机体显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二者距实现它们的潜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转基因技术在一些重要的经济作物生产领域正在占据主导的地位,特别是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一些有关转基因技术对经济、环境和人类健康影响的最全面的研究报告都积极地肯定了这一技术的应用,这一点也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不久前发表的报告所印证(13)。
以上众多的事实至少让我对未来抱有了希望。转基因技术,或许还有克隆技术,可以说是被用来“与时间赛跑”(buy time)。从现在起直至21世纪中叶,在世界人口达到其预测顶峰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必须仰仗这些技术来养活世界持续增长的人口。这种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农业制度不是没有它的负面影响,正像1万年前开始的农业发明和过去1000多年里的农业革命也具有负面效果一样,但重要的是它们的功效。当今的农业制度无论含有多少高度的现代主义设想和情感,它可以说是解决我们迫在眉睫的一系列物质问题的最好的、也许是惟一的答案。
*考克莱尼斯已单独或与人合作出版了《南部、美国和世界:南部经济发展的视野》(Peter Coclanis,The South,the Nation a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on Southern Economic Development,夏洛兹维尔2003年版)等5本著作和多篇论文。目前考克莱尼斯正在撰写一本关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球稻米市场形成的著作——译者注
注释:
①这一估计出自于菲律宾洛斯巴诺斯国际水稻研究院的一位土壤科学家和我在2004年的一次谈话——作者注。
②贾热德·戴蒙德:《人类史上最大的失误》(Jared Diamond,"The Worst Mistak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发现杂志》(Discover Magazine)1987年5月号,第64—66页。戴蒙德后来以《枪炮、细菌和钢铁》和《崩溃》两本书而声名卓著。参见:贾热德·戴蒙德:《枪炮、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Jared Diamond,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纽约1997年版;《崩溃:人类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成功》(Collapse: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纽约2005年版。
③马歇尔·沙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Marshall D.Sahlins,Stone Age Economics),芝加哥1972年版。
④姆·科恩、基·阿姆拉格斯主编:《农业起源时的史前病理学》(M.N.Cohen and G.J.Amelagos,eds.,Paleopathology at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纽约1984年版。还请参见:理查德·斯特可尔、杰罗米·罗斯主编:《历史的脊柱:西半球的健康与营养》(Richard H.Steckel and Jerome C.Rose,eds.,The Backbone of History:Health and Nutri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纽约2002年版。
⑤不是著有《历史研究》一书的著名的阿诺德·汤因比,而是其叔叔。请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工业革命》(Arnold Toynbee,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波士顿1956年版。老汤因比的英国工业革命系列讲座收入在这本书中,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884年。
⑥艾力克·科瑞杰:《农业革命》(Eric Kerridge,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纽约1986年版。如果要概览16世纪初至19世纪中期英国农业的变化,可以阅读:马克·欧维尔通:《英格兰的农业革命:1500-1800年农业经济的转型》(Mark Overton,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剑桥1996年版。
⑦四套作物轮种法是农民在18世纪中在旧有的三套作物轮种法上改进的一种农耕制度,主要是通过一年内在同一块土地上间种豆科植物来增加土壤的养料和巩固土壤的含氮量,以提高土壤的质量和防止昆虫类和菌虫类的病害。轮种的四套作物按时间顺序通常为:芜菁、大麦、苜蓿、小麦——译者注。
⑧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让他们流汗》(Nicholas D.Kristof,"Let Them Sweat"),《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02年6月25日;《赞扬有害的血汗工厂》("In Praise of the Maligned Sweatshop"),《纽约时报》2006年6月6日。
⑨阿伦达替—罗易(Arundhati Roy)生于1961年,是印度小说家,反绿色革命和反全球化活动家——作者注。
⑩请参见詹姆斯·斯科特:《貌似国家:改进人们条件的宏伟规划是如何失败的》,纽黑文1998年版。
(11)诺曼-伯劳格(Norman Borlaug)、斯万米纳汗(M.S.Swaminathan)和吴雷(Ray Wu)是与绿色革命最相关的三位土壤科学家——作者注。
(12)《绿色基因革命》("The Green Gene Revolution"),《科学的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2004年8月号。
(13)请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农业、与农业生物科技的状况:满足了穷人的需求?》(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United Nations,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Poor?),联合国粮农组织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