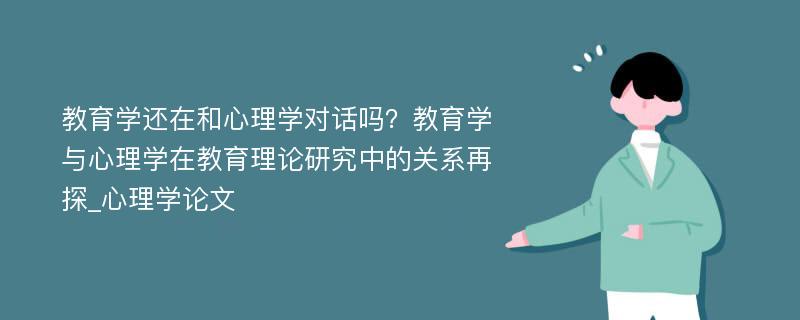
教育学还在与心理学对话吗?——教育理论研究中教育学和心理学关系的再寻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心理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在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心理学是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教育理论研究者说起来似乎都能理解,但在实践中,有教育科学研究机构的场所,就有心理学与教育学并行的轨迹,表面上看起来它们犹如一对双胞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历史之应然,也是逻辑之应然,更是价值所趋。但实质上它们真的是那么亲密,那么如漆似胶地对话、交流和沟通吗?如果说在赫尔巴特、斯金纳、杜威、维果茨基的时代,教育理论研究中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确联姻得很好的话,那么在教育理论发展多元化的今天,教育学与心理学之间实质性的对话越来越少,各行其是,它们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二者面临离异的危机,这对于以人为对象的教育理论研究来说,是好?是坏?教育理论研究是否就是形而上的哲学研究或社会、伦理学等等的研究?教育理论研究中是让心理学退避三舍还是继续与之互动、对话、和好如初?其间的道理似乎很简单、显性,但又似乎很复杂、隐匿,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反思性的梳理。
一、现实的分离:背弃心理学,过分地与哲学等其它学科对话
不管在哪一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中,哲学永远都高高在上,总是处于最高统领层。在教育研究中,哲学的地位也不例外,毫无疑问,哲学对于教育学科的研究“不仅具有提供前提性认识基础的意义,而且具有价值导向的意义,还具有思想方法的指导意义”。(注: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31页。)离开了哲学反思,教育理论研究是盲信且盲动的,并且是肤浅的。因为哲学的特殊价值和地位,教育理论研究中需要与他共鸣、交流,这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回应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科学反思运动的必然。教育理论研究的视野集中于哲学思索主要是近二三十年内的事,如“教育研究的范式”“教育理论的结构”等为题的研究,从教育规律、教育功能、教育价值、教育目的到师生关系、课程改革、德育原理等方面的研究几乎都进行了“×××的哲学思考(意义)”,这些成果我们可称之为“教育研究哲学”或“教育科学哲学”(注:张胜勇:《反思与建构——20世纪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241页。)。教育学与哲学之间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思想对流。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释义学、现象学等等主要哲学流派都渗透到教育的研究对象、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教育观念及教育思想的研究领域,很显然,这些都从客观上刺激了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化。我们喜欢深度、深刻,所以我们喜欢哲学的价值,喜欢用来提高我们自己及理论的深度,所以有的教育研究者提出“恢复人类哲学地探究教育问题的信念,以‘哲人科学家’为目标来培养新一代教育研究工作者”(注:张胜勇:《反思与建构——20世纪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341页。),这些都是无可非议并值得鼓励、提倡的。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教育理论研究哲学化的热潮在促进教育的多元化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哲学和心理学的两大理论基础的天平上,哲学过分超重,心理学已没有说话的席地,哲学用语在教育理论研究中被炒得沸沸扬扬,越来越深奥、玄乎,仿佛不涉及哲学的教育理论就是空洞、肤浅的,毫无价值的。而教育学和心理学虽然睡在同一张床上,却背靠背,他们因为都全力以赴跟哲学拉“关系”,却谁都没有功夫理睬身边最亲密的伙伴,似乎互不认识,互不相干,结果是教心之间越来越陌生,以至产生隔阂,所以现实是,搞教育理论研究就是在搞哲学研究,或社会、文化、伦理等教育实践工作者难以理解的其他跨学科研究,学教育的研究生不懂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及其思维方式,对焦虑、自信、社会化等等心理指标的测量与评定的报告一无所知,对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的教育意义及其教育控制策略等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留于皮毛,整天在形而上的空中楼阁咬文嚼字、杜撰新意。与此同时,学心理学的研究生也不知道教育理论的研究范畴。同在屋檐下,却互不沟通、对话,长此以往,我们会培养出很多哲人教育家,哲人教师,但很难想象是否会培养出像赫尔巴特、杜威、苏霍姆林斯基等一流的能统领、整合哲学与心理学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二是在背弃心理学的前提下过分地与哲学等其它学科对话,导致了一些功利性的教育研究,哲学、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争相抢夺教育学的“地盘”以显自己研究的深刻和新意,尽管这促进了教育理论研究的多元化发展,但却使研究者眼花缭乱寻找不到自己理论的生命“根基”,导致教育理论研究出现虚假的泡沫繁荣,并且使教育理论研究退化而成为哲学等它学科的“附庸”,最终“丧失自己的个性”。(注:陈桂生:《“元教育学”的探索》,福州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78页。)
在近年来有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和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的丛书中,心理学的地位与尊严已丧失殆尽,冠以哲学、系统科学、社会学、自然科学、文化学等学科美名的组装术语俯拾皆是。与心理学联系最紧密的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者论理说是最懂心理学的教育专家,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视野仅孤立地停留于学习、动机、道德等的心理机制、测量及评定等等,对相关的教育策略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当然,他们的研究重心在心理,而不在教育,这有情可原。但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懂心理学或对心理学略知一二却不知怎样迁移到教育研究中来,这是否也可以谅解呢?在教育学科多元化发展、新的教育理论层出不穷的开放式的研究氛围中,我们还需要与心理学民主、平等地对话吗?教育理论研究在选择、借鉴哲学等其它学科的思维模式、理论框架的同时,是否有必要将有关的心理学理论融合、渗透进去?这里我们可以从教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中寻找其与心理学的关系以及心理学在教育理论研究中的贡献与意义。
二、历史的融合:在心理学的呵护下成长、发展
教育理论研究的对象尽管在表述上是教育事实、教育价值、教育行动或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教育规律等,但其核心要素都是人,最终的目的都是使人健康、全面发展,很显然,对作为教育活动要素的人——教师与学生的认识是教育研究必备的前提性知识,这就必须借助于以人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所以教育学还在萌芽阶段,就与心理学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学者,尤其是孔孟学派就在心理知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较完整的教学理论和德育理论,如“学而时习之”“温故知新”“举一反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强调知、情、意、行并重,赞赏“择善而从,闻过则喜”等等。再如在人性与教育的问题的探讨上,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的教育思想就蕴涵有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而荀子提出的教育“化性起伪”的借助外在力量改变人的不良行径的教育思想就与近代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观点相似。
我们知道,真正的教育理论研究始于17世纪的夸美纽斯,而在这以前的教育理论研究尽管也涉及一些心理问题,但一直没有摆脱哲学的束缚,它或者是哲学家在探讨哲学问题时讨论教育问题或者是对自己感兴趣的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总结。但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大教学论》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培根的唯物主义者经验论思想,仍摆脱不了经验哲学的影响,那时的教育学虽然独立,但没有科学化,原因很明显,“教育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是人们对教育的理性的认识的反映,它的构建必须依赖广泛的理论基础,包括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为特点的方法论基础,即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不同层次的学科”。(注:郭芬云:《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研究方法论特征浅探》,《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年第1期。)所以后来的教育工作者不满足于仅从神学和经验主义哲学来建构教育理论,而是将心理学融合进自己的理论基础大厦中,他们注重理性批判,强调心理学的基础作用,如斐斯泰洛齐第一个提出“教育心理学化”的口号,他提出:“教学的原则,必须从人类心智发展的永恒不变时原始形式中得来。”强调以儿童的自然天性为依据来建构教育理论;继后,法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唤起了人们对教育内在规律性及逻辑体系的关注;在前人研究和康德的“自在文物”的基础上,1806年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突破康德理论的局限将教育理论研究扎根在现实的“心理学”土壤中,通过心理学来解释教育因果关系,在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心理学作为教育学理论基础,“完成了教育学和心理学在理论上的结合”,(注:方展画:《教育科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11页。)赫尔巴特明确指出“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以实践哲学与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言明目的,后者指明途径、手段”。(注:转引自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298页。)“我深信,在我们的教育知识领域中大部分缺陷乃是缺乏心理学的结果。我们必须首先建立这一门科学,……然后才能有把握地确定甚至在一堂课中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误的。”(注:戴本博:《外国教育史(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263页。)赫氏正是在其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如统觉团理论等的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较完整的教育理论,如影响较大的四段教学法。至此,经过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的一百多年的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磨合,心理学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教育学也从此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可见,教育学是在哲学和心理学共同推动下独立的,她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心理学融合在一起。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开始缓慢影响心理学和教育,1879年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室的诞生促进了实验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又促进了实验教育学的诞生,实验教育学的先驱梅益曼、赖伊等人就强调用心理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教育,如梅益曼认为,一切教育家、教师都应懂得生理学与心理学,在理解儿童生理、心理规律的基础上来研究教育学。(注: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外国教育史(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51页。)实验教育学采用实验的方法研究教育,无疑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进步。尤其是20世纪初期,瑞士的教育家克拉帕雷特和美国的桑代克,他们始终领导欧洲的“新教育运动”和“教育测量运动”就是建立在其广阔而精湛的心理学造诣的基础之上的,桑代克在动物学习实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学习定律在教育心理学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既促进了教育心理学科的理论体系的建设,又推动了教育理论的研究,其影响力可以和冯特在实验心理学研究中的影响力相媲美。与此同时,渗透于实验教育学中的儿童研究运动也受心理学的影响而于19世纪80年代诞生,儿童研究是现代教育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这一时期儿童研究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霍尔,20世纪初在把心理学的研究与教育结合在教育方法方面,他比其他任何一位美国心理学家都做了更多的工作,霍尔的伟大成就就是他首创的遗传和发展心理学,并把它运用于儿童研究,由此带来儿童观念的重大变化,“与传统教育相比,儿童观念的变革以及据此而带来的教学方法、策略上的革命,是20世纪教育发展最彻底、最深刻的地方之一”。(注:张胜勇:《反思与建构——20世纪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78页。)可见,心理学在实验教育学与儿童研究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到了20世纪上半叶,对世界各国教育理论和实践影响最大,与赫尔巴特教育学形成对峙的首推美国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形成不仅是建立在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生物化的本能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杜威把心理理解为本能的活动,诸如人的情绪、习惯、冲动等生物性的本能是心理的基本内容,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儿童本能生长的不同阶段供给他适当的材料,促进本能的表现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的综合化发展越来越趋于主导地位,教育学也日益与其它学科相互渗透,在理论上逐渐深化,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其中有影响的代表性教育理论是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系统》、布鲁纳的“学科基本结构”和“发现教学”、赞可夫的“教学与发展”理论、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域理论”等,布卢姆、布鲁纳、赞可夫、维果茨基他们不仅是教育家,也都是心理学家,这些理论尽管吸取了系统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营养,但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仍是心理学。
我们关照教育学的产生、发展历史,心理学在教育理论研究中的意义与贡献几乎超过了任何一门学科,丝毫不亚于哲学。教育学在和心理学的交叉缠绵、对话沟通中不断地生成、生长、壮大。如果终止了与心理学有效的实质性的对话,就意味着教育理论研究向夸美纽斯时代的倒退。教育理论研究要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在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对话的同时,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与心理学做有效的交流。
三、未来的对话:用复杂的整合思维与心理学进行深层次地复合
教育学既然注定要与心理学对话下去,那么教育理论研究者至少要学会在两个层面上与心理学进行你来我往的交流:1、直接与心理学平等对话、互通有无。教育理论研究者要掌握教育心理测量和实验方法,学会阅读心理研究报告,及时把握心理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并运用于教育理论分析中。任何一种教育理论诞生后,都要寻找其心理学依据,找到理论支撑点及其与心理学的切合点。教育史上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如前文所指)无不是经过这种横向来回互动和互证的。2、运用复杂科学的思维方式来整合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的基础理论,即与多学科进行“八面玲珑”的交往,兼容并包却彼此都不伤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教育理论研究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注:叶澜:《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3期。),属复杂科学之列,需多学科参与研究。斐斯泰洛齐、赫尔巴特、杜威等里程碑式的教育大家都是在博大精深的宽阔的理论背景下,综合了多学科的知识来进行教育理论研究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就是他巧妙地整合了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主张,从整体上把握教育现象,综合分析教育问题,而不是把教育当作哲学的实验室,他的一个“教育是经验的连续不断地改造”的貌似简单的定义,就将其实用主义哲学和机能主义心理学的见解都融于其中了(注: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末我国教育理论的反思》,《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10期。)。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方式,所以我们要学会将多学科融汇贯通、高屋建瓴。”也只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视野,我们在教育理论研究中才能避免陷入“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