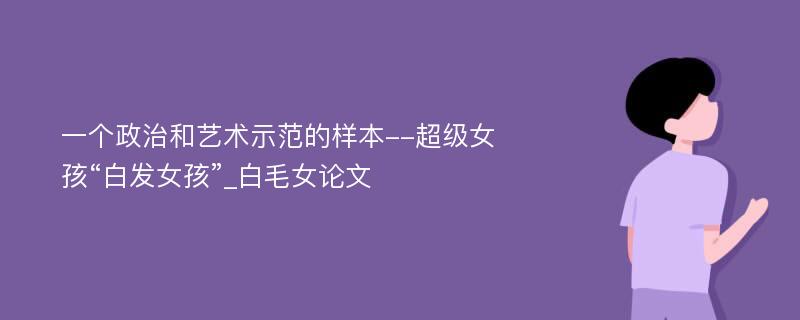
政治和艺术示范的标本——超级女声《白毛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毛女论文,标本论文,女声论文,政治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白毛女”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其内容的确超级悲惨,其影响又的确只能用“超级女声”来形容。原因就在于,《白毛女》及其人物塑造不仅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文艺领域尤其是电影创作方面,具有可供操作的政治示范性,而且在其问世后的几十年间,作为大陆文艺作品的“红色经典”之一,一直对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社会诸领域产生着巨大和广泛的影响。
一般中国大陆观众看到的《白毛女》,或在现在提到《白毛女》,很多人其实指的是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样板戏之一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因为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东北电影制片厂1950年摄制的电影《白毛女》已经不再公映。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政治上清除了以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等人为首的政治集团“四人帮”之后,包括《白毛女》在内的许多被禁国产影片才重新得以公映。许多在1960年代长大的人,也是在那时看到这些电影的。
考察1949年后大陆电影发展历史,我发现,到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确切地说从1960年起,中国大陆电影已经进入到模式化的生产时期,1950年代的许多电影作品包括《白毛女》,已经不适合政治理念新的发展和意识形态新的需求了。实际上,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许多1949年前后摄制的电影(包括译制片)已经被当局禁止公映。据统计,到1968年,被禁映的中外各类影片(故事片、记录片乃至科教片)已经高达400部之多,这些被禁影片分别被冠以“大毒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违背毛泽东思想”等等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罪名,[1](P199~255) 大陆的众多编导和演员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残酷的政治和人身迫害。
作为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样板戏之一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继承和发扬了1950年电影《白毛女》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内核,并进一步提升其政治品质,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诠释和新需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1990年代以后,大陆观众对于《白毛女》以及喜儿、杨白劳、黄世仁这些正面、反面人物形象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微妙的变化”只不过是字面上的修饰,实际上这种变化是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变化。比如,有人认为,黄世仁和其雇工杨白劳的关系是一种被扭曲和颠倒了的劳资和借贷关系。[2] 这种看似另类的认识,表面上看是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艺宣传意识的一种否定,实际上它还蕴涵着另一层合理性认知。
经历了被称为“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已经不局限于“文革”本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1949年之后的大陆文艺作品,包括这里将要展开讨论的《白毛女》(不论是电影版还是芭蕾舞剧版),其所表述和展示的历史有着太多人为的遮蔽、斧凿之处,并且,随着话语权的高度垄断和僵硬,反历史的、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宣教,又逐步掌控、窒息了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正常认知和合理判读。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经典的、发挥强大示范效应的样本作品,《白毛女》在图解和贯彻执政党的政治思想方面,在电影表现模式的建立乃至人物形象塑造等艺术方面,都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电影生产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并且在各个层面都存在着重新解读的空间。
一、政治思想的成熟性和示范性
(一)创作指导思想上的指导性和示范性
一般人提到《白毛女》往往容易忽略一个背景,就是不论是电影还是芭蕾舞剧,《白毛女》最初是一部歌剧,产生于1940年代的延安,换言之,它是中共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1937—1945)时期文艺创作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文艺作品“二为”方针的直接结果。
1942年5月间,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做了一次著名的讲话,史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1943年10月正式发表。这个《讲话》提出一个革命文艺必须“为群众”服务和如何“为群众服务”的“二为”方针,明确指出一切文艺作品只能是政治的诠释者和宣传品。“为群众”中的“群众”在延安时期主要指的是农民和军队(而毛本人曾说当时的军队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如何为群众服务”,指的是文艺作品的创作者要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进而指出文艺作品的宗旨是更好地为政治服务。[3](P459) 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则形成“写工农兵、唱工农兵”的通俗说法。“工农兵”就是工人、农民,“兵”在延安时期叫“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是“解放军”,1949年以后统称为“革命军人”。
歌剧《白毛女》就是在毛泽东延安《讲话》之后创作和搬上舞台的。《讲话》中号召,文艺作品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党的政策路线服务;一切有志气的文学家、艺术家应该深入到民间去。所以一批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就发掘到一个流传于晋察冀(陕西、察哈尔、河北省)一带的“白毛仙姑”的传说,说是一个村里的娘娘庙里的神仙特别神,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根据这一传说,当时写出来的剧本主题仅仅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而已,[3](P622) 而且名字就叫《白毛仙姑》。[4]
但是当这个剧本拿上来以后,延安的文艺主事者发现这个创作品质太低,就组织创作人员重新改写了剧本,并于1945年4月下旬,将新编歌剧《白毛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献礼,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党校礼堂为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做首场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4] 歌剧《白毛女》有一个全新的主题:在共产党来之前,“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共产党来了以后,“新社会把鬼变成人”。[3](P622) 因此,《白毛女》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宣传典范,首先表现在创作指导思想上的成熟。而且,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执政党地位的建立,这种对文艺作品主题在政治维度上的提升和把握,又逐步成为可供操作的示范模式。
(二)阶级关系和阶级属性的示范性
1950年的电影基本上对歌剧《白毛女》没什么大的改动,甚至连主要演员都基本上是原班人马。但在1940、1950、1970年代三个不同时期的《白毛女》版本中,对阶级关系、阶级属性的政治把握和强力定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不需要太多的逻辑推理就会发现,在《白毛女》中,以黄世仁为代表的东家(地主)和以杨白劳、喜儿为代表的佃户(农民),这种雇佣者和被雇佣者、贷款方(债权人)与借贷方(债务人)之间所有的矛盾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阶级关系和阶级属性及其必然的阶级斗争的表现。《白毛女》形象地表明,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存在着鲜明的和天然的阶级和阶级对立: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就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不但是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还是生死对立、你死我活的关系。所以,黄世仁和杨白劳、喜儿之间矛盾冲突及其最后解决,就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了。
在电影《白毛女》中,这种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实际上,在1949年以后的文艺作品尤其是电影中,这种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模式自始至终指向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政治层面,杨白劳、王大春们不仅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还是被压迫者,黄世仁不仅是东家还是县长,这是杨白劳无处伸冤最终自杀的一个直接原因;第二个是经济层面,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就是经营权也是靠东家(地主)施舍的,在经济上是完全的被剥削者,譬如杨白劳辛苦了一年,劳动所得只够还黄世仁高利贷款的利息;第三个就是1949年以后大陆文艺作品,尤其是电影作品中比较尴尬的、不愿面对的性剥削层面,统治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对被统治者(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优良性资源的霸占和榨取,主要是男性针对女性,比如男地主抢夺有姿色的年轻女贫农。
另外,阶级性决定人物的政治、经济乃至道德属性。《白毛女》中以杨白劳、喜儿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和以黄世仁、穆仁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其阶级性就决定了他们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好人和坏人的本性,进而也决定了他们间的关系是天然对立的关系。用1949年以后大陆的流行话语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因此,黄世仁不仅高利盘剥杨白劳,把他逼死,还把喜儿抢去,强暴之后,又要把她卖到窑子(妓院)里去。这样,阶级反抗和阶级斗争就具有了天然性、合法性和正义性。
然而,阶级反抗和阶级斗争及其属性的历史存在不是《白毛女》的解读背景,只有当下意义的现代革命性和党性才是《白毛女》高度的标识,她形象地说明:遭受三重剥削和压迫的农民阶级受苦受难,最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是无力的,是失败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农民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才能找到最终的出路。所以影片安排喜儿的未婚夫王大春投奔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最后大春哥哥回到家乡杨各庄,以革命和新政权名义,亲手把欺负他女朋友的男坏蛋给枪毙了。换言之,就是个人力量只有投入到党的怀抱当中,在这个集体的领导之下,它的斗争才有了价值和意义,最后才能取得胜利,争得个人的权利、自由和解放。反之,一切都是失败的、不可能成功的。就像当初杨白劳、喜儿个人的反抗一样,一个被逼自杀,一个被夺去贞节(肉身权利)。
因此,在培养和灌输阶级意识及其仇恨意识的同时,其对应的阶级斗争方式也就随之形象地进入观众的视野。
(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示范性
《白毛女》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震撼性的真理: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的生存空间几乎等于没有。无论你是妥协还是不妥协,都会被你的天敌欺压到连生存保障都没有的地步。比如同样交不起地租,村里的一个老头儿选择了跳井,杨白劳则被迫用女儿抵债,他觉得对不起女儿,又只有自杀,喜儿要不是逃出黄家,也是难免一死。那么,活下去,不要被欺负死,自己的女朋友不要被坏人抢去,出路只有一条: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种政治的成熟在1940年代延安汇报演出的时候,已经通过其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体现出来了。所以,1949年以后的大陆中国许多影片,主人公绝大多数都是出身底层。出身于社会弱势阶层即农民,都是在被剥夺了起码的生存权、活不下去的时候,才投奔革命队伍。《白毛女》中的王大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再不逃走,他的下场就是要被黄县长干掉。
因此,阶级斗争是必要和不可或缺的,而斗争的方式又必然是暴力的。就像电影《白毛女》所展示的那样,农民阶级在政治、经济、人身权利根本没有生存空间,而道德诉求又是那么苍白无力,面对黄世仁欠债还钱、契约为证的“硬道理”,村里人只能劝喜儿到黄家去(抵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及其对应的革命暴力或日暴力正义就只能成为唯一的方式和选择。就《白毛女》而言,它有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线索:
在1945年歌剧《白毛女》结尾,王大春代表的新政权最终并没有枪决地主黄世仁,但公演后,一位中共领导人就此指出,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新形势下,作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黄世仁作恶多端怎么能不被枪毙?[4] 众所周知,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及时调整了政策,改变了红军时期对地主阶级实施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单一暴力政策。代之以减租减息、团结抗日的新纲领。仔细分析在1950年根据歌剧《白毛女》拍摄的电影,对以黄世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行使的暴力主要指向政治和经济层面,处决黄世仁和穆仁智一个主要原因,在许多观众(我相信也包括那位高层人士)的潜意识里,是因为黄、穆这样的劣绅鱼肉乡里和致人死命,触犯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为富不仁”、“谋财害命”和“逼良为娼”的道德雷区和人伦禁忌;换言之,歌剧和电影《白毛女》的暴力革命是在政治、经济和伦理三个层面上共同展开的。到了1970年的芭蕾舞剧《白毛女》,这种暴力革命已经演化为革命暴力意识,突破了上述三个层面而成为纯粹的阶级暴力意识了;换言之,对阶级敌人(比如地主阶级)的肉体消灭,既是目的,更是手段和方式,政治、经济和道德上的清算和剥夺反倒退居其次。因此,芭蕾舞剧《白毛女》既删除了黄世仁的性剥削痕迹,也淡化了王大春和喜儿的爱情线索,强调阶级斗争的反抗性和暴力革命的必然性。譬如剔除了杨白劳喝卤水自杀的懦弱做法,改成当黄家来抢喜儿时,他操起扁担奋力反抗,结果被打死,直接迎合当时阶级斗争教育和阶级仇恨意识宣传的政治需求。(笔者对芭蕾舞剧《白毛女》另有专文讨论)
1945年的歌剧和1950年的电影《白毛女》的公演和放映,在时间上,前者正值抗日战争行将结束、国共内战(1946~1949年)开始之前,后者则是中共建立全国政权一年后、大陆的土地改革/革命全面铺开的启始之际;就空间上而言,《白毛女》的歌剧和电影的诞生地陕北和东北都是共产党革命活动的根据地,也就是“老解放区”。在1949年之前,陕北、东北是一条红线,共产党军队就是从这里、从关外一直打到关内,进而推翻国民党政府,解放全中国的。在这种情况下,《白毛女》所反映的土地改革/革命、农村的阶级斗争等重大社会问题,就有了直接配合现实政治的实践性和新政权全局意义上的示范性。对待地主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彻底剥夺他们的土地,而且还要在政治上、包括他们的肉体上予以彻底的消灭。否则杨白劳们、喜儿们,这些弱势阶层、群体怎么能够出头翻身、当家做主人呢?《白毛女》告诉你,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才会取得这样翻天覆地的效果。因此,《白毛女》作为斗争标本的示范性在时间上持续到1970年代末,在空间上则由东北而影响至整个大陆范围。
二、影片的艺术模式的成熟性与示范性
1937年8月27日,日本占领军扶持下的伪“满洲国”在“首都”——中国东北的吉林省长春市成立“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之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宣布接收“满映”,改称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制”。但由于苏联红军进驻东北,接收没有实质性完成,“满映”于1945年10月1日成立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4月,苏军撤出东北后,中共派员正式接管东北电影公司。由于国共内战爆发在即,6月1日,中共将公司大部撤至黑龙江省的兴山(今鹤岗),并于10月1日正式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5](P282~283) 1955年2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
1946~1949年国共军队决战,决定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个战役就是发生在东北境内的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11月2日)。1948年底,随着战事上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专门向东北局发出指示,强调“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普遍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利地进行我党的宣传工作”。[5](P401~402) 并先后派遣“东影”领导人分赴北平、南京、上海接收国民党电影机构。同年成立的中央电影管理局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局长为原“延安电影团”和“东影”主要负责人,各地方的电影厂领导也多由“东影”培养的干部充任。[5](P401~402) 1950年,除东北电影制片厂外,大陆主要电影制片厂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已经恢复并批量拍摄影片。因此,在一个极端意义上讲,东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尤其是电影方面的生长点。具体到艺术创作,东北电影制片厂先天性的地缘政治品质,决定了它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直到1980年代中期),都对大陆范围内的电影生产有着强烈的、双重意义上的示范性和指导性,《白毛女》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1949年后,中国大陆电影在制作和艺术表现上的模式化问题开始出现,其源头在于1942年的《讲话》。在1950年代初期,包括《白毛女》在内,就其整体而言,模式化处在形成期间;经过六七年的打磨,到1950年代后期模式基本上全面成熟,到了1960年代就再向前发展;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样板戏”和“样板电影”的出现,在我看来实在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一)电影制作主题和题材比例与审美风格的示范
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东北电影制片厂已经写好8个剧本:《桥》、《回到自己的队伍来》、《无形的战线》、《内蒙春光》(拍摄时改名《内蒙古人民的胜利》)、《赵一曼》、《光芒万丈》、《中华女儿》,[5](P395) 我推测第八个应该就是《白毛女》。这些剧本都在1950年完成拍摄并产生重大影响,其中《赵一曼》、《白毛女》、《内蒙古人民的胜利》分别在1950、1951和1953年获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颁发的电影奖项;[6](P383~394) 《桥》被称作是新中国第一部国产电影;《无形的战线》则是独具大陆特色的第一部反特片(抓捕大陆或海外敌对势力隐藏或潜入大陆内部的间谍特工人员的影片)。按照1949年后大陆通行的文艺题材划分,这8部影片几乎涵盖所有题材领域:工业题材、革命战争题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农村题材(土地革命,或以农村生活为背景)、反特题材和少数民族题材,只有少年儿童题材暂时没有涉及。
仅仅1949~1954年,大陆一共拍摄电影104部,其中农村题材(或以农村生活为背景)73部。东北电影制片厂共投拍34部,其中农村题材(或以农村生活为背景)24部;上海电影制片厂共拍摄25部,其中农村题材(或以农村生活为背景)15部;北京电影制片厂共拍摄14部,其中农村题材(或以农村生活为背景)8部;东北电影制片厂在这5年间,投拍影片数量及其农村题材(或以农村生活为背景)在全国范围内所占比例都超出三分之一(分别达到33%强)。
如果从1949~1959年这11年间更长的时间段来看,大陆一共拍摄275部电影(不包括戏剧戏曲片59部、记录性艺术片35部),其中农村题材(或以农村生活为背景)121部。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在这11年间,投拍影片数量及其农村题材(或以农村生活为背景)在全国范围内所占比例,则分别是48%和49%。[6](P383~384)
显然,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投拍影片数量及其农村题材(或以农村生活为背景)在1949年后电影生产中的超强比例与当时的政治要求和背景有关,也与大陆第一个党营/国营电影制片厂的率先垂范有关。因此,电影《白毛女》在主题思想、题材选择方面都属于开风气、引潮流之列也就顺理成章了。
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许多领导、技术骨干和演员来源于1940年组建的“延安电影团”,随着大陆政治形势的体制性变化,一方面,这些干部和演员以胜利者和领导者的身份接管了其他电影厂(尤其是上海的电影生产企业),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主导艺术生产,从而保障了1949以后几十年间电影革命化主题和题材主旋律政策的贯彻:而胜利者和主导者们的北方背景又极大地影响着1949以后大陆电影文化的审美品位和审美风格的形成与走向。另一方面,这种生产体制和政治背景也给中国自1930年代以来电影的传统、1949年后的电影事业和电影工作者(尤其是上海电影界出身的艺术家们)带来显性和隐性的销蚀和伤害。1956年,当时中央政府文化部主管戏曲电影的周扬、陈荒煤等曾专门就电影传统问题一再指出:“应该从上海算起,从延安、东北算起是不对的”。[7](P35) 然而1949年以后大陆电影在审美品位和审美风格上的农村化和北方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首先体现在农村题材(或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影片在全国总的电影制作中的比例上,如前所述,仅仅1949~1959这11年间就达到44%(275部当中有121部);而在这121部电影中,绝大部分又是以北方农村(或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为背景。与此相对应的是1949年以后城市题材或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影片数量不多。这样,以北方农村文化为主导的农业文明和1949年后的战争文化相融合,奠定了新中国几十年的主流文化的基础和走向。
这样,建立在农村文化或曰农业文明基础上、尤其是北方农村文化基础上的审美品位和审美风格决定了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审美模式,也是1949年以来几十年间大陆主流电影文化审美模式。其具体体现数不胜数,这里篇幅所限,仅以女性演员的选择标准为例,就可以明白其中奥妙:女演员一定是浓眉大眼,即民间所谓银盆大脸式的美人。但并不是说她的脸像银盆那么大,而是说她的皮肤洁白细腻,这里说的是北方化的美女标准脸型。《白毛女》中的喜儿扮演者(籍贯河北唐县)、《李双双》(海燕电影制片厂,1962)女主人公的扮演者(籍贯河北保定)就属于这一种。如果说《青春之歌》(北京电影制片厂,1959)的人物出身和故事背景因为在是北方(河北和北平),所以女主人公林道静的饰演者挑选了谢芳(籍贯湖北黄陂)这样靠谱的脸型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红色娘子军》(天马电影制片厂,1960)你怎么解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背景和人物局限在大陆最南端的海南岛岛内,女主人公吴琼花的饰演者的籍贯是江西赣州,但就是这么选的。表面上看是因为她们南人北相(即面像学上说的“富贵”之像),实际上,根源在于北方文化中的女性审美标准。而像周璇(籍贯江苏常州)、黄宗英(籍贯浙江瑞安)、上官云珠(籍贯江苏江阴)、王人美(籍贯湖南长沙)、黎莉莉(籍贯浙江吴兴)这样有着典型南方美人特征的女演员,在1949年后逐渐淡出大陆影坛,除了因为她们有上海电影界的“政治出身”背景外,新的审美标准的制约不能不是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力度不大,但“旧时王谢堂前燕”啊,新的庙堂显然没有“前燕”们合适的栖息空间。
(二)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及其定位上的成熟与示范
在1949年以后,大陆电影人物形象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脸谱化,有明确的“好人”与“坏人”之分,书面表述就是“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好人不仅政治品质、阶级出身可靠,而且外貌出众,还不仅是一般的好。男的一定是浓眉大眼,比如就是今天来看《白毛女》,大春哥哥也是一很酷的帅哥;喜儿漂亮到不仅是好人要娶她,而且让坏人也动了邪念。而且这种美是内外合一的、正反有定的。影片中的坏人,相貌丑陋,不仅阶级出身、政治品质、道德品质很差,男女关系方面尤其很差。比如黄世仁和穆仁智,在电影《白毛女》中,扮相都是很难看的,以突出其阴险、凶狠和淫荡。我推测这是从歌剧那里保留下来的演出妆。在大陆后来出品的电影,如果出现女性坏人,她一定长得很难看;如果她长得不难看,她的个人品质一定是很差的,俗称化装成美女的毒蛇,资本家太太、小姐、地主婆……尤其是女特务,淫荡不已。当然,这种建立在人物阶级属性上的形象塑造,源于电影主题思想的革命性,对它的追溯要跨越1940年代,回到1930年代初期兴盛一时的中国“左翼”电影。比如《野玫瑰》的女主人公阿凤,明显一个农村下层女子,但是她的阶级性、政治性、进步性、反抗性、斗争性、群众性、自由天性,性质优先,所以一让王人美出演,就“惊为天人”。《白毛女》不过是表现出“左翼”思想的继承性而已。
从演职员表上看,歌剧《白毛女》中的反面人物只有地主黄世仁母子,电影则增加了管家穆仁智,这是出于对阶级内部成员同一属性的意识形态考量。以后就演变为一个固定模式:地主必然有个经理型的“狗腿子”,譬如《红色娘子军》南霸天和老四(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1960年摄制)。而黄世仁他妈,作为地主阶级的女性成员(俗称地主婆),那就更坏。所以,在电影《白毛女》中,为了表现她的狠毒,设计了一个经典细节:喜儿给她捶背时打盹,地主婆就从发髻中拔出一根簪子恶狠狠地往喜儿脸上扎去。(所以,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北京电影制片厂,1997)特意安排让刘蓓演的地主婆重现当年景象,原因就在于,这个表现地主阶级狠毒残酷的细节给那个时代的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只不过,时过境迁,这个经典细节的阶级教育意义已经被喜剧化地消解和颠覆净尽)。
既然人物属性是其阶级本性所致,那么,农民阶级内部就是阶级意义上的兄弟姐妹一家亲。如果说在电影中,王大婶、王大春母子对喜儿好,那是因为喜儿和大春既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两家又是亲家;赵大叔对杨家父女好,那是因为他和杨白劳是老朋友,是看着喜儿长大的长辈——这些都属于人伦亲情,那么,村里人,包括在黄世仁家做佣人的张二婶,无亲无故的,为什么对他们也那么好?张二婶解答了喜儿的疑惑:你爹当年在我家躲过债。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穷人啊。对于阶级内部成员及其相互关系的成熟政治观,为后来绝大多数影片所遵循。1970年代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由于淡化了大春和喜儿的爱情,所以取消了王大婶这一人物,但强化了赵大叔和张二婶救助喜儿的阶级动机。即将人伦亲情上升到阶级感情的高度,达到模式化的顶峰。
(三)阶级性的双重纯洁模式、性回避模式和斗争模式(复仇模式)
与阶级属性相对应的,电影对人物阶级性的要求是两重标准,这种要求事实上通用于1949年后的所有文艺作品。对男主人公,要求他政治上的纯洁。在《白毛女》中体现在大春的阶级立场和反抗性是自始至终的;在经济上,虽然大春是黄世仁的佃户,但是,你没有看到大春从他们作为雇主和被雇佣者的经济关系中得到任何好处;作为被剥削者,大春种粮食也是为了糊口,绝不是为了给地主交租子。对女主人公的要求又多了一层,也就是除了政治上的纯洁性、经济上的被剥削性之外,还有对性的纯洁性的要求。影片的结尾定格很有象征性,喜儿抱着一捆麦子,幸福地跟在大春身后,原先的一头白发又变黑了。这绝不是一个头发颜色的改变的生理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高度的性归属的问题。事实上,我总在讲,1949年以后众多中国大陆电影如果从性的角度来看,表现的就是性权利的争夺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和性解放的问题。
但是,电影《白毛女》这样的处理,恰恰是后来电影性回避模式的拐点。在1950年代以后的大陆电影中,你会发现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实,如果涉及到女主人公的性权利的话,它是绝不能被拿走的东西。对立阶级(反动阶级、统治阶级、外国侵略者)可以拿走她的自由和生命,但绝对拿不走她的性的纯洁。性剥削及其场面处理被基本回避和删除。比如1960年代《红色娘子军》(天马电影制片厂,1960),可以非常清楚地明白女主人公吴琼花被地主南霸天夺去过贞洁,但影片却回避掉了。否则你不能解释她为什么对南霸天有那样深仇大恨、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影片显然是想用阶级仇恨来解释,但对一个年轻女人来说,对她所遭受的性剥削、性压迫、性暴力的反抗和复仇才是更主要和更重要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拍摄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八一电影制片厂,1974),主人公的母亲宁可被烧死在房子里也不能被抓住,就是这个模式在起作用。因此,1950年的电影《白毛女》在这一方面则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符合人性的真实。而让人悲哀的是,后来形成的回避模式,又激发和培养了来自观众建立在文化传统上的回避意识,使得人们习惯于仅仅从国家、民族、阶级、集团的高度和利益,却很少甚至没有从个体,尤其是女性自身去考虑和面对这种伤害和痛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拍不出《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Universal Pictures & Amblin Entertainment,1993)那样有震撼力影片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中国有日本军队实施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罪恶滔天。
斗争模式指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夺取胜利、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的正义行为在作品中的设定程序,这是意识形态在1949年后对所有影片的政治要求。但在电影《白毛女》中,它和性回避模式一样,存在但并不成熟和鲜明,影片前半部分的斗争处理应该说没有受这种模式的制约。无论是喜儿的反抗(哭泣、求助、逃跑)、杨白劳的悲愤(哀告、自杀)、还是大春的反抗(怒目而视、敢怒不敢言),可以说它还没有成为模式。这种模式在1950年代中后期趋于成熟,到1960年代则明确固定下来。电影《白毛女》和“文革”时期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最大的反差就体现在这方面。
在电影中,杨白劳的自杀是弱者的最大的和最后的反抗,而在芭蕾舞剧中,杨白劳拎起扁担奋起反抗的暴力行为,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这个设计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欠着债的老农民能拎起扁担跟东家打吗?这样看来,电影《白毛女》中对革命暴力场面的处理,只体现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但它是中国文艺作品中复仇模式的体现。随着音乐渐强,画面是灿烂的阳光照在山水之间,骑马跨枪的王大春回来了,有什么能比这个场景更让人有彻底释放和欢快的感觉呢?这种复仇模式的根源一方面是传统的,另一方面又是历史存在的。就像当时一首陕北民歌唱的那样:“骑白马,挎洋枪,当红军哥哥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而且还要报仇雪恨。譬如审判黄世仁的一场戏,电影给的场景是大量群众都涌上前去,但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镜头更多地给了女主人公,显然后者的这种处理更有感染力,效果更好。群情汹汹,但没有谁能比喜儿的仇恨更深。当初喜儿逃脱黄家的追杀后,面对滔滔河水,对天发誓:“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这种表述与仇人相见、又由恋人将仇人亲手杀死的结局相呼应,符合人物身份和情感,更符合观众的道德需求。1949年后电影模式的演进在这一点上并非一无可取,虽然它被限定在严苛的阶级话语体系里,但满足了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积蓄已久的正义渴望和暴力诉求。
三、电影《白毛女》的时代朴素性和艺术成就
不论白毛女这个个案有多么个别的极端性,有多么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多么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和多么深厚的党派政治教化传统,又是怎样影响和引领了大陆电影模式化和审美风尚的形成,1950年的电影《白毛女》还是在体现时代意识的同时,留有时代反映的朴素性。而这种朴素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陆生产的电影、实际上是所有的文艺作品中,色彩越来越淡薄,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发展到非人性化的地步。而在突出政治主题的同时,电影《白毛女》成熟的艺术成就也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一)艺术反映的朴素性例举
首先,不能否认,在影片中,对于一些历史真实给予尊重和反映。比如农民的落后和温顺。面对东家催讨债款和逼诱画押,杨白劳除了哭诉、哀求之外,只有自杀。当黄家拿着卖身契把喜儿从杨白劳的尸体旁带走的时候,村里那么多人也就是看着(围观),大婶还在劝喜儿:闺女,戴一条孝(布),跟人家走吧。这就是对历史的尊重。但是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当黄家去抢人的时候,那么多农民伯伯疯狂地扑上来大打出手,最后只不过人家拿出枪来,才没有抢回来,这恐怕是没有依据的虚构,如果当时的农民真有这么生猛的话,哪里会有杨白劳父女的悲剧?
其次,没有用模式化的回避模式处理喜儿这个性受害者形象。所谓的回避模式是说,1949年以后的大陆影片,对有些历史、人物、场景、话题、乃至有些字眼是采取回避态度的。回避最多的是牺牲场面,就是对生命剥夺、死亡场面的回避,当然是针对“我方”,所谓正义一方的死亡场面的回避,即使是大屠杀场面,镜头一转就没了(立刻转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悲剧力量,掩盖了历史真实。回避次数最多的是性场面,就是对性剥削、性压迫、性掠夺和性强暴场面的回避。在1950年的电影《白毛女》中,喜儿这么一个性受害者的形象基本了无遮拦,不仅有黄世仁强暴喜儿的指示性镜头,有张二婶回到村里向大春妈述说“孩子被糟蹋了”的情节,而且还有“有了”、“你大了身子在家活动不方便”等等观众一听就明白是喜儿怀孕的台词。后来竟然出现喜儿逃出去后把孩子生下来的场面,观众可以清楚地听到孩子的哭声,紧接着两个她用手挖坑压土的镜头,说明她把孩子给埋了。其实观众都知道是喜儿把孩子给弄死了。这些在以后的电影制作和表现中是绝对不可以想象的。(直到几十年后,作为所谓大陆第六代的新锐导演侯咏才在他的影片《茉莉花开》(金马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天津],2006)中借鉴了《白毛女》这组镜头的精华,而且成为片中不多的亮点之一。
(二)艺术表现的朴素性例举
首先,大量朴素的民歌和地方民谣的使用,是电影《白毛女》艺术朴素性的首要表现,而且更难得的是,它们更多地定位在个人感受层面和从个人感情出发。譬如杨白劳唱的《十里风雪》、杨白劳喜儿的二重唱《扎头绳》,都是纯粹的原生态民歌面貌,而且是从歌剧《白毛女》的诞生地陕北带来的(据歌剧《白毛女》作曲刘炽说,这两段是在陕北吴堡县收集、李林改编的。刘炽:《悲壮的旋律》,《光明日报》,1990年7月19日)。这种难得的评价是因为1949年后的大陆文艺作品中,伪民歌、伪民间音乐层出不穷,纯粹的男女情歌也掺入太多的意识形态话语冒充新民歌。所以到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歌词的改编已经上升到阶级感情的政治高度了。剥去种种历史的伪装,《白毛女》中能够流传至今的歌唱也就是那些注重人物个体感受和尊重人性最基本感受的表达的部分,比如《北风那个吹》和《扎头绳》。
其次,电影的音乐和画面结合以及叙述节奏非常到位。《白毛女》刚问世的时候是歌剧形式,因为在延安有很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也就是内地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这里面就包括上海来的一个三流演员,后来改名江青的人),他们接受过西方文化的完整教育和熏陶,有相当成熟的艺术观念,对歌剧和电影的欣赏创作并不陌生,所以1950年电影《白毛女》的创作起点和基础就很高。比如,村里一个老头儿对人们说我碰到了白毛仙姑了,镜头闪回,隐隐约约传来庙里的钟声,手法细腻传神。当大春带着本村的民兵大锁去山洞里追踪白毛女,也就是男女主人公相见的时候,这本来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环,如果渲染得音量强、节奏快,就会一塌糊涂,那就是过犹不及。然而电影《白毛女》处理的节奏把握非常到位:喜儿先是叫“大锁”,感到惊惧的大锁本能地叫了声“大春”,为什么呢?与其说他感到好奇,倒不如说他感到害怕。然后镜头对切,音乐慢慢地跟,这一点与其说它是舒缓有致,我倒认为不如叫它从容不迫。1949年以后,大陆影片在这方面充满了太多的暴戾之气,镜头语言处理得刚、直、硬,没有给男女主人公留有充分的情感释放空间。
当然,无论是歌剧还是电影,《白毛女》的艺术性不能离开其意识形态的创作背景、接受对象和政治传播方式来讨论。譬如就结构而言,以“喜儿与大春的‘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作为情节发展的副线,并由此展现了‘鸳鸯拆散’——‘绝处不死’——‘英雄还乡’——‘相逢奇遇’——‘善恶终有一报’等一系列情节线索,这都是农民观众所熟悉的,对它们是很有吸引力的”,从歌剧《白毛女》开始,这个故事无论在戏剧矛盾冲突、人物形象和性格都被充分地强化,从而“适应农民要求‘明确、强烈、有劲(力)’的审美趣味”[3](P623) 这种艺术上的成熟建立在政治成熟的前提条件之下,这还可以概括为革命文艺或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文艺作品在意识形态高度上的成熟表现。
感谢电影学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吕月华同学对本文相关统计资料的收集。
标签:白毛女论文; 黄世仁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