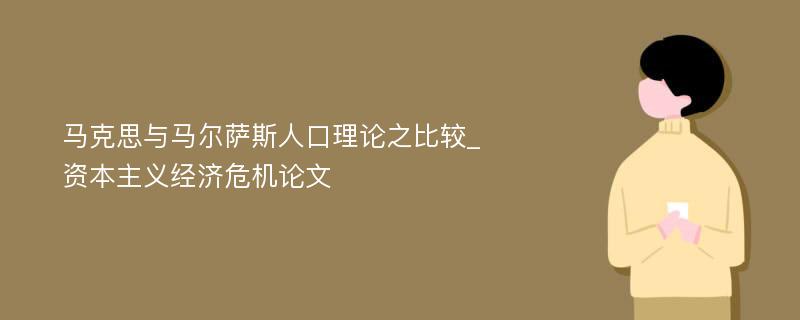
马克思与马尔萨斯人口论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尔萨斯论文,人口论论文,马克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资本积累会引起对两种商品需求的增加,一是普通商品,二是劳动力商品。对于普通商品来讲,当需求增加时,其价格会提高,从而引起价格偏离价值,在高额利润的引诱下资本竞相投入到该商品的生产中来,供给增加重新使该商品的价格降低,利润也回到正常水平。但是,劳动力不是普通商品,不存在这种价格回复机制。
如果考察简单再生产,那是可以假定劳动力按价值出卖的。因为这时不存在什么力量会迫使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价值发生背离。但是,一旦有了积累,情况就不同了。积累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引起工资上升。如果不存在某种回复机制,那么为什么工资不会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把利润侵蚀净尽?而如果没有利润,资本主义的存在岂不成了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意味着将建立不同的人口理论。
李嘉图把劳动力价值称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把工资称为“劳动的市场价格”,他还没有能够把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范畴区别开来。因此,在李嘉图那里,工资何以会趋向劳动力价值的问题就变成劳动的市场价格何以会趋向劳动的自然价格问题。李嘉图指出:“劳动正象其他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可以在数量上增加或减少的物品一样,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彼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中文2版,第1卷,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使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保持一致的力量是什么呢?李嘉图的回答是:“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论能和其自然价格有多大的背离,它也还是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当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时,劳动者的景况是繁荣而幸福的,能够得到更多生活必需品和享受品……但当高额工资刺激人口增加,使劳动者的人数增加时,工资又会降到其自然价格上去,有时的确还会由于一种反作用而降到这一价格以下。”(同上书,第78页。)在李嘉图看来,人口的作用之于劳动力商品,正如资本家的竞争之于普通商品,都是使价格趋向价值的回复机制。换言之,李嘉图把人口的自然增减作为调节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蓄水池。
2
马克思是完全察觉到工资在资本积累冲击下会趋于上升的。但是马克思确信,这样一种工资上涨,决不会涨到威胁这个制度本身的地步。所以,他势必要问:是什么力量压迫工资而使剩余价值和积累可以继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和本质特征呢?马克思是通过“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相对过剩人口也被称作劳动后备军,这个后备军由失业工人组成,他们通过自身在劳动市场上的积极竞争对工资水平起到一种抑制作用。“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7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也是运用“蓄水池原理”来解决问题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所指的不是自然人口,而是相对过剩人口。
相对过剩人口是由于随着积累增进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形成的,即主要是由那些被机器所取代的人口组成的。马克思认为,采用机器是资本家对工资上涨趋势的一种颇为直接的反应。
把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压迫工资上涨的力量,又把机器的采用作为相对过剩人口这个蓄水池的进水口,包含了这样一个思想:人口变动通过机器的采用而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之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基础之上。换句话说,马克思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而是在这个生产方式之内寻找它维持自身存在的条件的。这样一来,他的人口理论就获得了具体的历史规定,即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马克思不仅从逻辑上,而且从历史上以事实说明了这一特定规律:“1849年至1859年间……英国农业地区出现了……工资提高。……这是农业过剩人口空前外流的结果,而人口外流是由战争的需要和铁路工程、工厂、矿山等部门的大规模扩展引起的。……租地农场主大喊大叫起来,甚至伦敦《经济学家》在谈到这些饥饿工资时,也郑重其事地胡诌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租地农场主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会象教条的经济学的头脑所设想的那样,等待这种优厚的报酬促使农业工人繁殖,直到他们的工资不得不重新下降吗?不,租地农场主采用了更多的机器,工人转瞬间又‘过剩’了,过剩的比例连租地农场主也感到满意了”。(同上书,第699~70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了两个时间概念,“等待”和“转瞬间”。这两个时间概念准确地显现出马克思人口论与古典经济学和马尔萨斯人口论之间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本体论上区别了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由于形成的基础不同,有着不同的变化节律和生命活动周期。如果社会存在得以顺利运转的条件需要由自然存在来提供,那么,就会出现自然变化周期能否适应社会运转需要的问题。如果不能适应,社会存在将不得不“等待”。在农业生产中,播种之后社会还要等待自然起作用一段时间后才能得到劳动成果。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根本不能依赖自然人口增殖来满足它突然扩张或收宿时对人口的要求。经济周期和人口自然周期是不同步的。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硬要人口自然增长能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连续进行,在本体论上必然会有意无意地消除两种存在类型的界限。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正好镶嵌在人口自然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作为蓄水池,当资本突然扩张时,蓄水池的水可以流出;当资本突然收宿时,水又可以流入,而根本不需要什么“等待”。
如果资本突然扩张使相对过剩人口全部进入现役大军仍然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资本积累还能存在吗?马克思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说:“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扩张力也增长了”。(同上书,第693页。)资本积累的迅速扩张,有可能使后备军减少,从而使工资上涨的限制得以消除,剩余价值的确可能大为削减,“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一定点,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同上书,第681页。)毫无疑问,工资的上涨和利润缩减潜伏着积累动力的减弱和经济危机。因此,和机器代替劳动一道出现的,是危机和萧条。当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时,就业人员因后备军减少而有所扩大;而处于危机和萧条阶段时,就业人员收缩,后备军得以扩充。
3
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在该书第二章他指出:“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陷于贫困,使他们的境况永远也得不到明显的改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文1版,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马尔萨斯讲的“人口的不断增加”是指自然增殖,相对于食物来讲,这种自然增殖的人口过剩也是一种“相对过剩人口”。但与马克思相对于资本积累需要的相对过剩人口不同,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是建立在他的两条公理之上的:“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同上书,第6~7页。)这两条公理是“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由于以几何比率增加的人口总是超过以算术比率增加的生活资料,马尔萨斯就因此把过剩人口看作是“永远”存在的,换句话说,这种相对过剩人口是一切社会共有的人口规律。
马尔萨斯一经建立了永恒的人口规律,他也就很顺当地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的人口问题。“以前养活700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750万或800万人口之间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大大恶化,许多穷人必然陷于极为悲惨的境地”。(同上书,第14页。)到此他讲的是一切社会共有的人口规律,紧接着他就一步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者的人数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则趋于上升”。(同上书,第14页。)这一步跳跃使得马尔萨斯完全丧失了考察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性质的能力,他解释不了甚至也从未提出如下问题:除了因人口自然增殖带来的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以外,劳动市场供求是否就没有其他因素起作用呢?如果存在其他因素的作用,那这些因素和人口自然增殖对“劳动的价格”(即工资)的影响相比,哪一个更具有决定性呢?马尔萨斯的“相对”食物短缺的过剩人口是一种真正的绝对过剩,他用这种过剩人口既解释了劳动力价格何以低廉,又解释了食物价格何以高昂。
工资变动和食物价格波动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内在规律决定的,马尔萨斯却因袭古典经济学的错误,从人口自然增殖这一生产制度外的因素出发来加以说明,这在本体论上就是没有坚持社会存在的总体性原则,而只有坚持从一个统一的总体出发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坚持从总体出发去认识人口现象,就是坚持从社会存在的基础范畴——劳动出发去认识人口问题。对马克思来讲,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是机器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共同基础,正是这种等同性保证了资本家在劳动力价格超过劳动力价值从而造成使用机器更为有利时,就能够通过排斥工人,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的办法来渡过难关。试想如果不坚持劳动范畴的基础地位,机器和工人的价值就不能等同,不能替换。
马尔萨斯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总体以外去理解人口,就必然动摇劳动范畴的基础地位。马尔萨斯在劳动之外又找到了一个“生育”范畴与劳动范畴相并列,形成一个二元基础范畴。正是这种二元基础才使得作为劳动的“人手”和作为生育的“人口”在一个有机整体上被肢解了,工资基金和人口总量之间只存在机械的平衡关系,工资铁律终于形成。一般见解以为,马尔萨斯把“两种生产”作为社会历史的前提与恩格斯的下述观点是一致的:“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但是,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两种生产等量齐观,而是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总是决定人类自身生产的。而马尔萨斯的“两个前提”却是两个相互并行的固定不变的法则。需要指出的是,马尔萨斯的“食物”不是什么生产的产物,而是自然的恩赐。“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产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人类虽有理性,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88页。)
食物靠天赐予,劳动微不足道。在劳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性亦不能把人类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在有限的食物面前人类展开的生存竞争与动物界毫无二致。这一点深深影响了达尔文。后者的“生存竞争”概念源于马尔萨斯。达尔文所以能够在生物界成功借鉴社会存在的法则是由于马尔萨斯在本体论上错误地把社会存在等同于自然存在的缘故。马克思就此所作的批判同样是在本体论上的:“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
4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悲观的。“我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具有忧郁的色调,但我认为,我绘出这种暗淡的色彩,完全是因为现实中就有这种色彩,而不是因为我的眼光有偏见”。(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2页。)的确,如果人口增长总是有超过食物增长的趋势,人类的前景当然毫无希望。但这种悲观论调的依据是将通过劳动已经从自然界中把自己提升出来的人类重新发配到自然界。人类作为生物学存在永远是自然物,问题在于,在劳动的基础上人类不仅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存在,而且同时使自身的自然限制不断退缩,尽管这种自然限制只是不断退缩而不会消亡,但作为一种趋势是由劳动这种能够不断超越自己现有情境的力量保证了的。马尔萨斯以“生育”范畴取代了劳动范畴对人口的基础地位,社会发展和自然限制的退缩就都在他的视域中消失了。《人口原理》出版200年来,在两个事实击破了马尔萨斯的悲观论调:其一是以科技进步为标志的人类劳动生产能力的空前增强;其二是生育控制。这两个事实恰恰反映了社会进步和自然界限退缩这一不可逆的趋势在当今时代的新表现。今天,不仅两性关系社会化了,子女生育也社会化了,无论生育数量还是生育质量都不再是自然规律盲目起作用的领域。
马克思的人口论把人口看作是社会经济制度的一种内在因素,这就在本体论上坚持了劳动的基础地位,从而使他看到雇佣人口不过是雇佣劳动的产物,同样,相对过剩人口也不过是雇佣劳动所特有的人口现象。而雇佣劳动的发展虽然是以牺牲了无产阶级整个阶级为代价的,但毕竟是使人类自身的能力得到了发展。正是这种发展保证了人类自由时间的延长;也正是这种发展,单位商品中所包含的价值量不断下降,这就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灭亡和人类的史前史的结束准备了条件。人类的未来并非如马尔萨斯所言是暗淡无光的。
标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