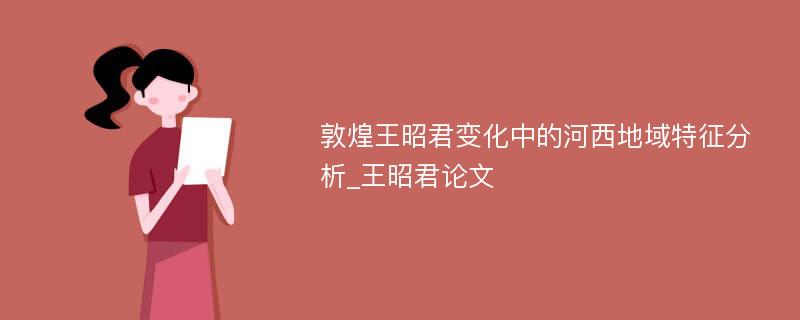
敦煌《王昭君变文》河西地域特征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西论文,敦煌论文,探析论文,地域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2)06—0159—04
敦煌《王昭君变文》与历史记载的王昭君故事及唐前诗文的相关内容比较,显示出了浓郁的河西敦煌地域特征。为了考察敦煌《王昭君变文》的地域特征,我们首先要研究清楚历史上王昭君的出塞方向、目的地等问题。
一、历史上昭君出塞的方向与目的地
虽然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昭君出塞的去向,但是,相关的记载还是能提供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史载呼韩邪单于四次入朝,第一、二次的路线比较明确。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二三年正月”[1]。《资治通鉴》载:“(公元前52年)诏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单于,发所过七郡二十千骑为陈道上。”此句后胡三省注曰:“七郡,谓过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后至长安也。”[2]第二次,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3],“二月,遣单于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幕南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4]。
顾炎武对呼韩邪单于来朝廷的路线的理解与胡三省相同,并进一步推出昭君出塞的路线:“《汉书》言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光禄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后单于竟北归庭。乃至汉与匈奴往来之道,大抵从云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5]顾氏所说甚是,历史上王昭君出塞的方向是去北方。
如同昭君出塞的方向一样,昭君出塞的目的地在历史文献中也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呼韩邪单于当年来朝的路线,我们知道历史上昭君出塞目的地在北方。史书中有呼韩邪单于几次归庭的记载,如(公元前58年)“呼韩邪单于归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6]、(公元前56年)“是时,李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单于捕斩之;遂复都单于庭”[7]、(公元前43年)“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8]。据黄文弼先生考证:“单于庭当在鄂尔浑河畔,杭爱山之东麓,哈喇巴尔噶逊附近也。”[9]这说明呼韩邪单于的重要活动都在单于庭,而单于庭在今外蒙古境内。另外,《汉书》载:“竟宁中,呼韩邪来朝,与秩訾相见,谢曰‘王为我计甚厚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复顾留,皆我过也。今欲白天子,请王归庭。’……单于固请不能得而归。”[10]“竟宁中,呼韩邪来朝”,“请王归庭”,最后,“固请不能得而归”,说明呼韩邪单于竟宁中入朝那次回去的地方是单于庭。竟宁只有元年(公元前33),昭君这年出塞,说明其出塞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单于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历史上昭君出塞的方向是北方,出塞的目的地是单于庭。然而,《王昭君变文》中昭君出塞的方向与历史上记载的不同——出塞的方向是西北,并且其中有明确的出塞目的地——敦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变文中关于昭君出塞路线及方向的描述。
二、变文中昭君出塞路线及其方向
变文中昭君出塞的路线是这样的:“□(酒)泉路远穿龙勒,石堡云山接雁门,蓦水频过及敕戍,□□□(望)见可岚屯。”也就是说昭君出塞的路线经过雁门、酒泉、龙勒、石堡、敕戍、可岚屯等地。这些地方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酒泉”,“唐代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酒泉市”[11];“龙勒”,一说是县名,“在敦煌县西南一百四十里”[12],一说是唐敦煌县又有龙勒乡[13],一说是山名,在沙州寿昌城南一百八十里。[14]总之,“龙勒”无论是县名、乡名还是山名,它都离敦煌不远;“石堡”,“即石堡城,在今青海省西宁市西南,为唐朝与吐蕃的交通要冲”[15];“雁门”,“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自古为戍守重地”[16]。“蓦水”、“敕戍”、“可岚屯”今不可考,但其应在河西地域之内。
“雁门”、“酒泉”、“龙勒”、“石堡”、“敕戍”、“可岚屯”这六个地方显示的路线是从“雁门”出发,过“酒泉”、“龙勒”到西北去,但是经历的地方却又涉及“石堡”这一去吐蕃的要冲。为什么会出现经过“石堡”的情形呢?笔者以为这是作者杂糅唐朝文城、金城等诸位和蕃公主经历的结果。
昭君出塞到西北的说法并不是《王昭君变文》作者的首创,它始于陈后主的诗“狼山聚云暗,龙沙飞雪轻。笳吟度陇咽,笛转出关明”(《昭君怨》)[17]。之后,一直至唐代,这一说法都很流行,如陈昭的诗“交河拥塞路,陇首暗沙尘”(《明君词》)[18]、上官仪的诗“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王昭君》)[19]、卢照邻的诗“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王昭君》)[20]、李白的诗“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王昭君》)[21]、令狐楚的诗“魏阙苍龙远,萧关赤雁哀”(《王昭君》)[22]等。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说法,笔者以为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西行出塞公主的影响,如汉代细君公主[23]等;二是河西曾经是匈奴的属地。《汉书·地理志》载:“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24]“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25]三是敦煌和呼韩邪单于有联系。《汉书·匈奴传》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26]可见,呼韩邪单于的势力当时可以影响到敦煌。
《王昭君变文》的作者借用了昭君出塞到西北去的说法,并且,对其有所发展。这一发展就体现在明确昭君出塞的目的地——敦煌。
三、变文中昭君出塞的目的地——敦煌
关于昭君出塞的目的地,历史的记载是模糊的,笔者分析应是单于庭,但《王昭君变文》的作者却把昭君的出塞地明确地写成敦煌,笔者认为这是作者主观创作的结果。
变文中王昭君的活动地点是以敦煌为中心来展开的,其他地方涉及金河、胭脂山等。昭君思念故乡时的唱词说:“妾家宫宛(苑)住奏(秦)川,南望长安路几千,不应玉塞朝云断,直为金河夜蒙连。胭脂山上愁今日……风光日色何处度,春色何时度酒泉?”“遂使望断黄沙,悲连紫塞,长辞赤县,永别神州”。变文最后的祭词中又有“不稼(嫁)昭军(君),紫塞难为运策定”句,由此可知,变文中昭君出塞后生活的地方是“紫塞”、“玉塞”,活动的地域包括“金河”、“胭脂山”等。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地方所指的具体地点:
“紫塞”指敦煌。敦煌其他文献“诏临紫塞,鸿泽虔熙”(P2913和P4640)、“乾符之政,以功再建节髦。时降皇华,亲临紫塞”(P2913)、“和尚俗姓陈氏……敦煌人也……义富宝山,法兰降临紫塞”(P3556)等句中,“紫塞”即指敦煌。
“玉塞”也指敦煌。由敦煌文献记载如“玉塞敦煌,镇神沙而白净”(P4640)、“名高凤阙,玉塞声飞”(P4660)、“名高玉塞,礼乐双全”(P4660)、“领袖敦煌……玉塞崇枝”(P3718)等可知。当然如果作关塞讲,“玉塞”指玉门关。
“金河”在肃州,即今甘肃的北大河。敦煌写卷中有提及,如“金河东岸阵云开”(P3633),史书也有记载:“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27]
并且,在敦煌卷子中,“金河”与“玉塞”常常对举,如“运张良之计,东静金河;立韩信之谋,北清玉塞”(P3556)、“金河路上,飞泽云奔,玉塞途中,忽承雷令”(P2613)等。
“胭脂山”即焉支山、燕支山、燕脂山。清人张驹贤考证说:“焉支山,一作燕支。”[28]《五代诗话》卷一:“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北人采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妇人妆时用此颜色,殊鲜明可爱,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胭脂也。”[29]由此可知,“焉支山”写作“胭脂山”也是自然的事情。另外,敦煌写卷中还有“燕脂山”的说法:“单枪匹马,舍躯命而张掖河边;仗剑轮刀,建功勋于燕脂山下。”(P3556)
变文在大量写敦煌及河西地名的同时,也提到塞北、阴山等北方地名,如“居塞北者……不知塞北有千日之雪”、“瀚海上由呜戛戛,阴山的是振危危”、“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等,关于文中的这一现象,笔者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状况在变文中的反映。
综合以上信息,笔者以为作者创作中王昭君出塞不是到北方去,而是到河西敦煌,敦煌这一出塞地是作者有意改造历史的结果,变文具有浓厚的河西敦煌地域特征。那么,为什么作者要让“王昭君”出塞到敦煌呢?原因只能是作者要借昭君的故事反映敦煌人的思唐归唐情结。
四、变文地域特点形成原因
《王昭君变文》地域特点的形成,首先是作者依据当时情形主观改造昭君故事的结果。变文作者把昭君故事移植到敦煌河西地区,并改变了变文的情节内容,显示了作者想通过对传统昭君故事细节的改写,反映敦煌乃至河西陷蕃百姓对唐朝强烈思念之情的创作倾向。变文作者对昭君故事发生地的改写上文已有论述,此不多言。下面我们来看看变文的情节主题。
《王昭君变文》不同于传统昭君故事,其变文情节很简单:昭君愁苦,单于一再讨其欢心,即使“既荣立,元来不称本情”,并“因此得病,渐加羸瘦”,最后在蕃地郁郁而终。昭君愁苦思乡的主题在变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文中有大量的写愁苦思乡的句子,如“愁肠百结虚成着,□□□行没处论,贱妾倘期蕃里死,远恨家人昭(招)取魂”、“单于见明妃不乐”、“边云忽然闻此曲,令妾愁肠每意归”、“莫怪适来频下泪,都为残云度岭西”[30]、“昭军(君)既登高岭,愁思便生,遂指天叹帝乡”、“远指白云呼且住,听奴一曲别乡关:‘妾家宫宛(苑)住奏(秦)川,南望长安路几千,不应玉塞朝云断,直为金河夜蒙连。胭脂山上愁今日,红粉楼前念昔年……风光日色何处度,春色何时度酒泉……’”、“昭军(君)一度登千山,千回下泪,慈母只今何在?君王不见追来”、“遂使望断黄沙,悲连紫塞,长辞赤县,永别神州。虞舜妻贤,涕能变竹,玘良(杞梁)妇圣,哭烈(裂)长城。乃可恨积如山,愁盈若海”等。
昭君为什么如此愁苦呢?原因是她嫁给了“蕃家”,生活在敦煌,她“长辞赤县,永别神州”。她归家的心愿特别强烈:“一朝愿妾为红□(鹳),万里高飞入紫烟。”以至于昭君亡故后单于哭也说:“早知死若埋沙里,悔不教君还帝乡。”这个“(入)国随国,入乡随乡,到蕃禀(里)还立蕃家之名”的昭君自始至终都不习惯单于的宠爱:“如今以暮(慕)单于德,昔日还录(承)汉帝恩”,“乍到未闲(娴)胡地法,初来且着汉家衣”,“蒲桃未必胜春酒,毡帐如何及彩帏”,“假使边庭突厥宠,终归不及汉帝怜。心惊恐怕牛羊吼,头痛生曾(憎)乳酪膻……”,“初来不信胡关险,久住方知虏塞□(寒)”。
变文中的女主人公是“长辞赤县,永别神州”,郁郁而终。她的侍从又是怎样的状况呢?作者这样形容她们:“侍从寂寞,如同丧孝之家,遣妾攒蚖,仗(状)似败兵之将。”把侍从与“丧孝之家”和“败兵之将”联系在一起,初看读者会觉得很奇怪,但仔细揣摩,这恰恰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他告诉我们,昭君及其侍从其实都是“丧孝之家”和“败兵之将”;昭君嫁给了“蕃家”,其实是敦煌陷入了吐蕃的统治。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设置的情节和反复渲染的主题了。总之,变文改写了传统昭君故事的故事发生地、丰富了昭君故事的情节内容,变文作者正是通过改写传统昭君故事,杂糅敦煌河西地区的历史状况,达到了反映敦煌乃至河西陷蕃百姓当时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的目的。
《王昭君变文》地域特点的形成,原因还在于这是敦煌乃至河西地区的历史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王昭君变文》反映了敦煌陷蕃(786年)后河西广大民众的心声,以“王昭君”为代表的河西民众身陷蕃中、心怀唐朝的情形文献资料中多有记载。
文献显示当时民众有死也不愿意辞国者,如《新唐书》载:“(贞元三年787年)虏又剽汧阳、华亭男女万人以畀羌、浑,将出塞,令东向辞国,众恸哭,投堑谷死者千数”[31];有身陷蕃中密计逃离者,如白居易《缚戎人》载:“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有李如暹者,蓬子将军之子也。尝没蕃中,自云蕃法唯正岁一日许唐人之没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胜,遂密定归记也。)暗思幸有残筋力,更恐年衰归不得。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32];并且陷蕃民众普遍有故国情结,思念唐朝,不忘唐服,如《新唐书》载“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33],《新唐书》载:“(822年)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34]。同样的情形《旧五代史》中也有载:“开成(836年—840年)时,朝廷尝遣使至西城,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35];
而且河西陷蕃地区沙州百姓的故国之思最深,它在陷蕃百年之后,仍然是“人物风华,一同内地”,此情形见于《张淮深变文》,文中说:“尚书授敕已讫,即引天使入开元寺,亲拜我玄宗圣容。天使睹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其于(余)四郡,悉莫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堞彫(凋)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袵;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以上资料显示了河西陷蕃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和他们思念唐朝的深挚感情,这样的历史生活在文学作品中再现,使得变文具有了鲜明的河西敦煌地域特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王昭君变文》作者改造了之前传统的昭君故事,其文本具有浓郁的河西敦煌地域特征,其地域特征的形成在于作者对传统昭君故事的改造以及历史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标签:王昭君论文; 呼韩邪单于论文; 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新唐书论文; 西汉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唐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