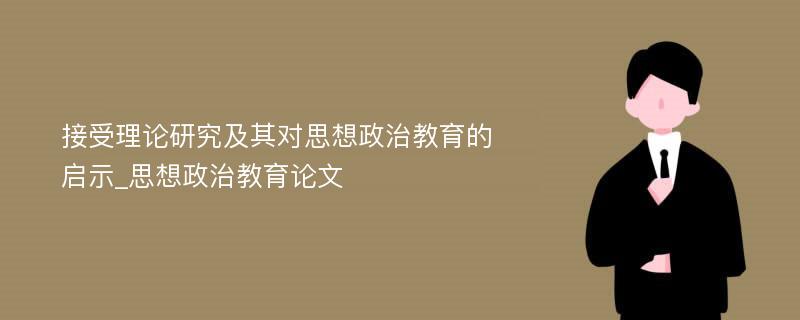
接受理论研究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接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而我军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的研究相对较薄弱,以致对思想政治教育特点与规律的研究难以深入。因此,关注学术界对接受理论的研究状况,借鉴人文及社会科学相关理论研究的成果,有利于对我军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特点与规律的深入认识和全面把握。
一、接受理论研究的主要观点
1.关于接受的定义
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姚斯创建了“接受理论与接受美学”体系,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新文学史概念:文学史就是文学作品的消费史,就是消费主体的历史。因此,必须更多地关注读者的阅读活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理解,构成了作品的现实存在。可见,他所说的接受主要指读者在文学欣赏中的“阅读活动”。姚斯指出:“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积极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1](P24)这是系统论述接受问题较早的理论,属于界定接受的“活动说”。
到了80年代,我国学者对西方的“接受理论”进行了翻译介绍,相关的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胡木贵等提出了接受的另一种定义,即“关系说”:“接受是指思想文化客体及其体认者相互关系的范畴”,[2](P42)具体讲,接受标志着接受者与思想文化客体之间的一种“认识和实践关系”。吴刚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将人的认识划分为理性认识之前的活动与理性认识之后的活动两大部分,认为理性认识之后的活动主要是从理论到实践的活动,“接受是一种后理性认识活动,包括理解、设计和加工”,简单地说,“研究如何从理论到实践的活动,就是接受活动”。而他主张的接受活动,主要指对理论的“应用活动”。[3](P4)
张琼从伦理学角度,认为“道德接受就是指发生在道德领域的特殊的接受活动,它是道德接受主体出自于道德需要而对道德文化信息的传递者利用各种媒介所传递的道德文化信息的反映与择取、理解与解释、整合与内化以及外化践行的求善过程。”[4](P58)这个定义比较全面地描述了接受的过程及其特征。邱柏生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角度,认为接受是“主体(即受教育者)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教育的控制下,选择和摄取思想教育信息的一种能动活动”,是“对社会有控影响的积极反应”。[5](P3)但是,仅仅把接受界定为一种“能动的”“积极反应”,而排除了“消极反应”,那么“被动接受”就不能纳入接受的范畴,显然这个定义过于狭窄。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学从一开始,就将接受与接收等同起来,认为接受指的是受众对传播符号及其意义的“接收”活动。[6](P6)
显然,与“活动说”相比较,“关系说”不足以揭示接受作为现实活动的实质,因而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接受的各种定义以“活动说”为主。在对接受的各种定义中,分歧和差异的要害不在于“活动说”或“关系说”,而在于由于研究角度和层面的差别,导致最终的落脚点不同:文学和哲学认识论接受的研究重在“期待视野”的契合与跃升(如姚斯),或观念的重新整合与辩证否定(如吴刚)等,而道德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接受者从理论、观念向行为、实践的转化结果,如道德、政治觉悟的提高、行为之迁善程度等,而是否能付诸实际行动,则是“活动说”与“关系说”从不同层面关注的不同点。
2.关于接受的基本矛盾
姚斯认为,作品在读者心中不断唤起读者先前的期待,构成读者新的审美感觉经验,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构成读者接受反应的矛盾运动。因此,读者的阅读与期待视野的发展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接受的基本矛盾。接照姚斯的接受理论,任何作品总是要通过预告、信号和暗示激发读者开放某种特定的接受趋向,唤醒读者以往的阅读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感情态度中,于是唤起一种期待。[7](P11)读者带着这种期待进入阅读过程,并在阅读中改正、修改或实现这些期待。这里,姚斯重点强调了读者在阅读前的记忆等构成的“前结构”,这是接受的前提条件。
胡木贵等认为:“接受主体与思想文化客体或对象文本是接受学的一对基本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接受认识活动的根本矛盾。”吴刚则认为,接受活动的矛盾主要是接受主体(即应用特定理论的主体)与被接受的理论(理性认识成果)之间的认识和实践关系的矛盾。张琼认为,接受的基本矛盾是社会道德规范与接受者的主观需要之间的矛盾、差别和对立。
综合各家之说,对接受基本矛盾的界定可以归纳为:接受者的主观思想、行为状况与外在(社会、军队等)要求之间差距的矛盾。而接受则主要是为缩短此差距的一种努力。这样,从内涵和外延上都能揭示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包容接受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矛盾运动。
研究接受的基本矛盾,重在揭示其内在本质。在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反应中,承认接受者的阅读记忆等“前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与官兵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情况既相似又不完全相同。相似的是,政治教育也必须承认接受者在接受前具备一定的思想、文化基础等,否则接受就缺乏起码的条件。不同的是,文学领域对读者接受的“前结构”的依赖性更强,“接受理论”也尽量夸大这些“前结构”对接受的决定性影响作用,并通过接受活动来主观地调整和修改其既有的“前结构”,使其与读者心目中的“期待视野”相融合;而思想政治教育则强调接受者需调整其既有的“前结构”,如受教育者的思想基础、道德觉悟、文化程度、接受能力、社会阅历等,使其思想和行为与党和军队的要求相一致。遗憾的是,我们对接受者“前结构”的深入研究和分析不够,因此影响了我们对接受者思想情况的全面了解和掌握。
3.关于接受的过程
这是构成任何接受理论的主体部分,也是个老大难问题。20世纪60年代,西方心理学出现了认知学习理论,集中研究人类学习问题,认为人类的学习是经验的重组,是认知结构获得和建构的过程。皮亚杰认为,儿童获得知识和道德价值观都不是从环境中直接将知识内化,而是将知识与已有知识(schema)联系起来,从内部通过各种活动及其创造、协调来建构知识,接受是接受者不断建构的过程。1974年,加拿大教育心理学家加涅(R.M.Gagne)提出了学习模式的8阶段论,[8](P93)即动机阶段、了解阶段、获得阶段、保持阶段、回忆阶段、概括阶段、作业阶段和反馈阶段。加涅对接受过程的认识,吸取了建构主义和行为主义两派的优点,同时也抛弃了两派的不足,比较辩证地揭示了接受过程的规定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姚斯在《文学与解释学》一书中认为,理解、解释和应用是解释学的三大重要范畴,相应地文学解释活动应该包括三个层次或阶段:第一是审美感觉的理解视野,属于初级阅读的阐释重建,与阐释学中的理解相对应;第二是意义的反思性视野,它与解释学三要素中的阐释相对应;第三是阅读历史视野,它最接近于历史哲学解释学。同时,在姚斯看来,文学解释学的三级视野不是一种绝对的分割或对立,而是相互包容和转换的。在理解、阐释和应用的三重组合中,审美感知的优先权要求的是其视野的优先,审美感知的理解视野在重读文本或在历史理解的帮助下也能获得。审美感觉不是无时间有效性的普遍密码,而是像所有的审美经验一样,交融着历史经验。它本身以历史变化为条件,又在审美理解之后拓宽了历史认识的可能,这说明三级视野之间是辩证地交互影响和转换的关系。
如果说在文学批评理论中,接受可以被描述为不断联想、体验和各种情绪情感的波动的话,那么接受中领悟过程本身却通过思辨的语言被淡化了。许多学者更愿意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接受的过程,而不愿意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详细的实证性考察,因为从研究模式的提出、主题的确定、理论的选择到材料的取舍上都有一定的难度。如果这项工作付诸实施,必然要取得相关的认识心理学和社会学习理论的支持,而这些理论本身也需要反思和确证。所以,研究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存在逻辑前提的再论证的任务。
4.关于接受的规律
经过对文学接受现象的研究,姚斯认为,审美交流过程中,具有审美自由的观察者(接受者)与他的非现实对象(作品中的主人公)之间的来回互动,这种互动构成了交流结构,可以归结为五种模式:第一层次是联想型认同,第二层次是敬慕型认同,第三层次是同情型认同,第四层次是净化型认同,第五层次是讽刺型认同。这五种模式,是研究接受的“理想类型”,是从文学接受史中概括出来的,又可以用于具体的文学阐释活动中,体现了对文学接受规律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哲学、文学还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中,模式的研究显然比规律的研究更受重视,因为模式可能更“实用”和具有“操作性”,更能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此外,研究的难点还有接受的评估、接受的机制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结合相关学科和方法,对接受进行通力合作的研究,否则,就很难有大的突破。
二、接受理论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接受”是人文社会科学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理应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视。当然,文学(美学)、哲学意义上的接受与道德、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之间,存在着层次和内容方面的差别,甚至教育心理学所关注的学习接受也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具体说,不同领域的接受,各自的理论支持不同,接受者接受的动机、接受的内容、接受的目标、接受的落脚点等都有较大的差异。同时,也必须看到,在将接受者的接受活动作为一种理解、认同活动和作为一种主体与客体关系、外在与内在转化的矛盾运动的意义上,许多领域的接受仍然具有相似和相通之处,需要打破各自的壁垒界限,进行分析比较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完善。
1.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现象的研究。目前,政治教育中“投入”大于“产出”,或只见“投入”不见“产出”的情况还在某些单位存在着;有的受教育者主观上不愿接受、拒绝接受,有的政治教育客观上令人难以接受;少数人身上存在“虚假接受”的现象。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现象缺乏研究。比如,思想教育中,接受者对理论的接受与对实践(事实)的接受之间出现的反差,思想接受与心理接受之间的不协调,情感接受与理性接受的不同步,观念接受与行为接受之间的冲突,利益追求与人格认同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是影响接受的重要因素,而教育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还远远不足以消除接受的障碍。为此,要求教育者要紧密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重视对各种接受现象的研究,探寻其不同的成因,把握其不同的特点,以便从整体上优化教育的可接受性,增强教育的有效性。
2.重视对接受特点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在研究文学接受现象时,姚斯提出了五种认同的模式,达到了一定的规律性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与文学艺术的接受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相同。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具有能动性、选择性、建构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有学者结合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将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规律概括为:利益认同律、理性认同律、情感认同律和价值认同律等,[9](P48-52)尤其强调了接受是一个从利益认同向价值观念认同的不断发展、深化的辩证过程。当前,在经济、技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随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往的发展,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会逐渐加剧,人们的认同危机成为接受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人们认同和接受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认同和接受有什么规律可循,更需要我们深入地去进行研究和思考。
3.注意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对接受问题的研究,除了前面提到接受美学等之外,还有一些较成熟的理论成果。例如教育心理学(以加涅为代表)、发生认识论(以皮亚杰为代表)、儿童道德发展理论(以柯尔伯格为代表)、社会学习理论(以班杜拉为代表)、当代欧洲大陆的解释学哲学(以伽达默尔为代表)、当代德国社会交往理论和商谈伦理学(以哈贝马斯为代表),以及传播心理学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理论都已经形成比较成熟和被人文社会科学认可的理论体系,并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方法,值得思想政治教育者认真学习借鉴。
4.接受理论的研究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相结合,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重视接受理论研究,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总体上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时刻将接受理论的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实践相结合,将接受理论的研究放在我军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建设的大局下予以定位,这样才能得出科学、全面而不是狭隘、片面的结论。同时,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接受理论,把对接受理论的研究作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步骤来进行,不能犯简单化、片面化的错误。例如,早期的传播学对传播活动自身的特点规律的认识有限,认为传播者对传播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传播者怎么传播,就能收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阶段属于传播中心模式。后来有人提出,受众才应该是传播研究的重点:受众有什么样的需要,只要传播能满足其需要,传播的接受效果就会大大提高,于是,出现了以受众为中心的“使用—满足”传播模式。[10](P102)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传播者—受众相互影响、作用的“交易”、“商谈”等新的模式,可以称之为交互主体性模式。许多学科对接受理论研究的轨迹已经证明,接受问题仅仅是一个必要的环节,绝不能代表全部。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的研究放在文化—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并努力遵循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才能使接受理论研究、使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