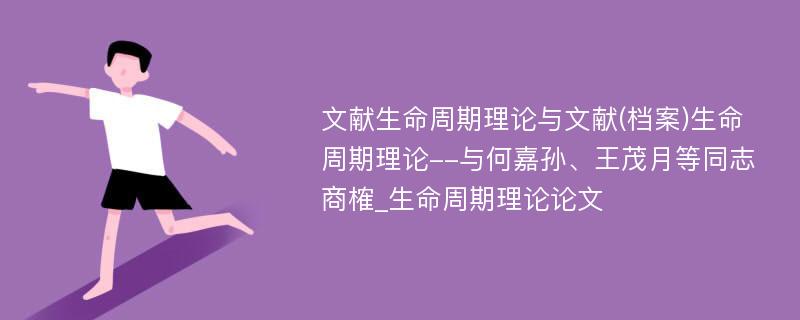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档案)生命周期理论——与何嘉荪、王茂跃等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命周期论文,理论论文,文件论文,同志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讨论又热烈起来。以何嘉荪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而以王茂跃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则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两方面的意见完全相反,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上述争议的核心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何嘉荪认为:“如果我们熟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具体内容就能判明,它所描述的,确实是文件运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王茂跃则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或者干脆说,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难以中国化。我国对中国化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应当采用什么名称加以概括至今仍不能达成共识,也就印证了这一点。当然,将这一理论介绍进来,以作借鉴、参考、比较研究之用,则是很必要的。不过,这又应当另作别论。”
显然,这里提出了一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世界性问题。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存在是否适宜中国化的问题
吴宝康教授在谈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时,曾多次指出,我国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殊途同归,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类似的结论”。1962年,曾三提出:“由文书部门或有关人员立卷归档形成档案开始,经过档案室,最后集中到档案馆,这就是档案形成与运动的过程。”曾老的这一观点把文件(档案)的运动过程依次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文书部门阶段、档案室阶段和档案馆阶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曾老在表述他的这一观点的时候,使用了“形成”、“运动”、“过程”这样一些词。这些词的使用给我们描绘的是一个动态的、完整的、阶段性的生命过程。因此,有理由说,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不完全是舶来品”。中国也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一理论与国外的文件生命理论,有类似的结论,但也有其不同点。
国外,从1950年的“三阶段论”到80年代发展形成的生命周期理论,用何嘉荪的观点可以总结、归纳为三点:
“(一)文件从产生形成到最后消亡(或臻于永恒)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即文件的运动具有完整性;(二)文件在其全部生命过程中,先后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和价值,使其整体生命周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运动阶段,即文件的运动又具有阶段性;(三)文件运动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有着特定的内在联系,因而在不同的运动阶段应根据其不同的特点,采用适宜的存放与管理方式。”
依此,国外的有关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将这个生命周期看成是文件的运动过程,文件运动到那一个阶段便可以称为档案,没有什么界定。而我国的文件(档案)生命周期理论则对此作出了规定。所以,笔者在这里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文件(档案)生命周期理论”。这是中国和国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大差异。这个差异涉及到对档案的不同认识。中国的文件(档案)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由文书部门或有关人员立卷归档形成档案。”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个“归档”的认识,把办理归档手续作为档案工作和文书工作的界限,区别开来。
档案工作实践的普遍性,决定了世界档案学具有共性,但各国档案工作的个性,又决定了它们的差异。所以站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否适宜中国化的角度去讨论问题,有无视自己之嫌。
二、文件(档案)生命周期理论的重要特色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文件的运动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这个生命过程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运动阶段;处在不同运动阶段的文件具有不同的价值形态。”而文件(档案)生命周期理论,则提出了一个“归档”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文件(档案)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乃是文件与档案的区别与联系的理论”。多年来,不少同志对“归档”的认识是不全面的,甚至是仅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的,把“归档”行为本身看成是一种人为的主观行为,并不深究这一行为的实际意义。如果笔者对曾老提出的“由文书部门或有关人员立卷归档形成档案”一说理解不错的话,“归档”反映着的是一个不同性质工作的界限划分。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大文件”的概念之下,把文书与档案的区别看成是处在不同运动阶段的文件所具有的不同的价值形态,所以档案又属于文件,它所形成的社会基础是文件档案统一管理的体制。文件(档案)生命周期理论在“归档”的概念下,把文件和档案区别开来,文件不是档案,档案也不是文件。它形成的社会基础是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分别管理的体制。
“归档”这一中国化的概念是具有实际内容的,它是指文件内容规定任务的完成或文书处理程序的结束。正因为有了“归档”这一概念,才使档案工作与文书工作处于一种离散的状态,这符合我国的文书工作、档案工作分属不同管理体系的国情。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共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国家管理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但变化了的形式,仍然是一个规律。
三、文件、档案与文件中心、档案室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档案)生命周期理论是一种理论思维,它是建立在不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不可能脱离实践而存在。因此,从广义上讲,无论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或文件(档案)生命周期理论,确实是反映了不同社会实践文件运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在这里要避免陷入一个误区,即并非所有承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国家都必须选择文件中心这种形式,来管理他们国家的档案或者文件,这之间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不可否认,1950年英国档案学者马勃斯在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提出的文件生命的三阶段论(即关于文件的现行、暂存和永久保存三个阶段的理论)与文件的保管场所——办公室、文件中心和档案馆相吻合,由最初的出于对文件中心的理论解释,而逐渐演变成今天的一种学术思想,一旦这种思想形成,那么它就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目前,文件中心已成为北美和欧洲许多国家的一种非常普及的文件管理机构,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也设有文件中心或类似的机构。文件中心是介于文件形成机关和终极性档案馆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的管理机构,而且其资金和人员也均由存放文件的机关提供。显然设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经济而有效地管理即将但尚未失去现行作用的文件,以缓解文件形成机关、档案馆的负担。
文件中心的建设,确实起到了经济有效地管理即将失去现行作用文件的目的,缓解了文件形成机关、档案馆的负担,但不是说,文件中心是唯一完美的选择,就是在国外也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少数档案工作者不赞成,认为有了文件中心会拖延对文件的鉴定和向档案馆的移交,不利于档案利用”。另外,对还没有完全失去现行作用的文件,使其脱离形成机关而交由文件中心来负责管理,绝不会比在本部门利用来得方便。
档案室的建设是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分别管理体制的产物。因此,很多同志认为,档案室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物,然后进一步推导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这是一种推理的错误。如果说,办公室、文件中心、档案馆称为一种模式,那么,文书部门、档案室、档案馆不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吗?如果排除对档案的不同认识,这两种模式似乎看不出什么本质的区别。
文书部门、档案室、档案馆前后衔接,分工明确,形成了一个文件(档案)实体管理机构体系。档案室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起着接收文件“归档”和向档案馆移交“档案”的责任。如果从管理的对象来看,文件中心和档案室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管理着具有半现行性的文件或者“档案”(这里的档案国外称之为半现行文件)。从管理的关系来看,一个是“不出屋”式的,一个是“脱离式”的,这就有了很大的区别。从所有关系来看,档案室的“档案”仍没有出原部门,而文件中心的“半现行文件”从某种意义来讲,已进入半社会状态。从管理方式来看,档案室按部门的方式进行管理,而文件中心则是一种社会式的管理。
档案室在对“档案”实施管理的过程中,由于仍具有浓厚的部门色彩,所以在向档案馆移交的过程中,就不如文件中心的社会式的管理来得直接和自然。在一个机关或者部门建设档案室,对于文件的收集和整理又是十分有利的。当然也有许多弊端,诸如:兼职多,水平低;不符合“精简、效能”的精神等。
笔者认为,如何正确地评价文件中心和档案室,还是用吴宝康的话来讲比较准确:“我们究竟是继续坚持档案室制度好呢还是改建为文件中心制度好呢?依我之见,一切应决定于国家和机关的具体情况以及历史传统和习惯,难以断定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可以说,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办公室、文件中心、档案馆相对应;文件(档案)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书部门、档案室、档案馆相吻合。
四、档案概念的再认识
各个国家的档案概念往往有不小的差距,这个差距源于每个国家的不同的体制。那么,什么样的“文件”可以转化为“档案”,何时应转化为“档案”或者应被视作“档案”,这些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谢伦伯格对此曾有过这样的意见:“‘档案’一词显然没有一个不可变动而必须优先采用的、最终的、最完备的定义。它的定义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作不同的修改,以适应不同的需要。被采纳的定义都应该提供一个基础,使档案工作者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有效地应付他们为之服务的政府所产生的各种材料,凡是有损于他们的工作效力的定义,就不应该接受。”因此,档案概念来源于档案工作者为之服务的政府的体制以及文化的影响。
“档案”与“文件”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的认识,在我国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而且同我国政府的现行体制相适应。“档案”与“文件”的区别在我国是以归档来划分的。文件向档案室移交之后,就进入了档案阶段。两个阶段的中间纽带——文书立卷归档,是文书阶段的起点,也是档案阶段的起点。而国外,在关于档案的认识上,从表面上看是按文件运动阶段来确定的,但实际上所考虑的仍然是如何有效地服务于政府和社会这样一个主题。
在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关于档案的认识不仅仅要考虑到如何有效地服务于政府和社会这样的问题,似乎还应当注意到文件形成方式的变革所带来的重大影响,这个影响是否大到需要修正我们的档案观念,还有待时日确定。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档案工作情况也是如此。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传统的档案室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建立联合档案室、寄存中心或者文件中心,我们应持欢迎的态度,鼓励探索。然而探索的原则是,要能够“有效地应付他们为之服务的政府所产生的各种材料”,而不是非要在档案室或文件中心这个问题上搞出个孰优孰劣来。档案学理论依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我们要学会从社会实践去看档案或者文件的运动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认识档案,认识文件运动的规律性。
(本文由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