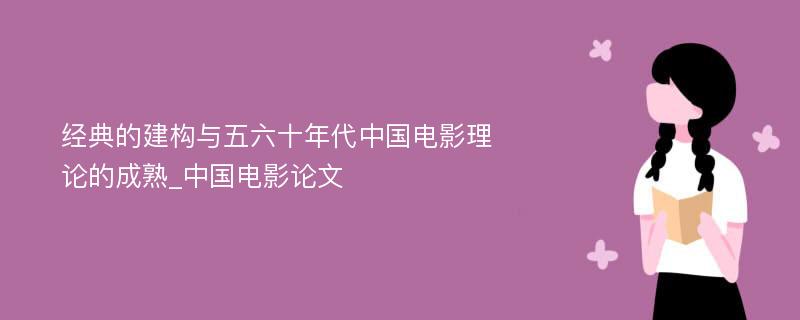
经典的建构,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的成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六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成熟论文,理论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六十年代,即1949至1966年的理论时代,中国大陆的电影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峰。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共出版了电影理论专著35部,出版了重要译著22部,比建国前所有电影理论专著、译著总数还多;未结集的有分量的论文则远远超出这个数目。从中国电影理论自身的发展形态考察,这一时期正是学术规范全面建立的时期: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研究已与电影批评划分为其畛域;电影语汇也已规范和统一;这一时期的理论文体已成为中国大陆电影理论操作的范式,至今仍以此作为“理论性”的准则而被认同。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由国家拨款的电影理论研究实体纷纷创设,带动了电影界内外普遍的理论风气。新政权对电影理论研究直接介入的同时,确也给这些生活于国家事业机构内的电影工作者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学术研究条件和写作生涯所必需的物质保障体系,使得他们有充分的余裕去从容地进行理论思考。这是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代充满激情的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新的社会理想的追求和被超越个体的社会价值观念所激发的敬业精神和朴素的学风,给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增添了为数可观的厚实的理论成果。然而,电影理论界此起彼伏的政治风浪和日甚一日的意识形态化倾向、电影艺术家自身对于电影市场的隔阂以及受前苏联理论界学院意识影响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使这一时期的电影理论界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图景。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论列五六十年代的电影理论成果,以期勾划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基本轮廓。
艺术的大总结:资深电影艺术家对古典电影的理论阐述
自本世纪初至40年代末是中国电影艺术的古典时期。这一时期辉煌灿烂的电影艺术成就,标志着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的创立。40年代是中国古典电影发展的顶峰阶段,电影创作领域层出不穷的宏制伟构和天韵独成的艺术精品将中国古典电影形态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令人至今叹为观止。然而,40年代剧烈震荡的现实环境和激越亢奋的社会心态,使得当时的电影艺术家们未能从容地对中国古典电影艺术进行深刻而完整的理论总结。这一历史任务便遗留到50年代,由中国大陆的资深电影艺术家全面完成,从而产生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理论成果。
史东山:中国古典电影形式美学的理论总结者
史东山是中国古典时期首屈一指的电影艺术大师,其艺术创作从20年代绵亘至50年代,是中国大陆权威的资深电影艺术家之一。建国后史东山出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委员兼技术委员会主任。为新的理想主义精神所激发,50年代初史东山着手修改他建国前夕所写的专著《如何处理电影的镜头组接》(1957年5月改名为《论电影镜头的组接》,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并撰写一系列长篇论文,从镜头语言方面总结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创作的历史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9 篇论文结集为《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问题》,1954年10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史东山从电影艺术的影像本体切入,探讨和总结了中国古典电影艺术一系列重要的形式美学问题。
史东山在他的理论研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电影虽称是综合艺术,但基本上应该是一种‘视觉艺术’,这就是说,这种艺术所表现的人物形象和一些事物现象或斗争发展情况,绝大部分或全部都应该是在人们视觉上所能看得见。”(注:史东山:《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中国电影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 )史东山的这段话在理论上完整而准确地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所持的根本的电影观念,即在强调以视觉形象为主的基础上的一种综合艺术观。史东山接着指出:电影的“这种特性,虽然含有一种艺术表现方法上的特殊规律所产生的约束性,但只要我们一掌握了这种规律,我们便可能得到为其他艺术所不可能有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独特的美。”(注:史东山:《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中国电影出版社1954年版第19页。)这就在50年代上半叶风云变幻的社会背景下,将电影艺术形式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大胆而明确地提了出来。
史东山认为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形式美学的核心问题是电影镜头的组接问题,这是打开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大门的一把钥匙。为此,他潜心撰写了专著《论电影镜头的组接》来集中探讨这一问题。史东山在其专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镜头的组接’应该就是‘蒙太奇’,而不单纯指影片的剪接。”(注:史东山:《论电影镜头的组接》,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也就是说,他是从影像美学的层面而不单从技术操作的层面来阐述镜头组接的问题的。史东山指出,中国古典电影艺术的镜头语言有两个相反相成、互为一体的基本审美取向:一是“力求其能发挥电影的基本特长”;二是“力求能使观众易于了解”。(注:史东山:《论电影镜头的组接》,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史东山所要揭示的是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从自身的主体意识与观众的审美接受心理两个方面全方位读解和把握影像的艺术思维方式。基于此,史东山提出了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分镜头的三个原则:第一,“要严格规范观众的注意力,使其在某一时间中必定集中在某一部分空间上或表现对象上。”;第二,“要随时弃掉除‘表现对象’以外的废料或累赘的东西,而使留存在画面上‘表现对象’特别显著起来”;第三,“要把许多‘表现对象’之间随时发生的变化,依据宾主轻重的比较,而呈现给观众以最适当的距离或角度”(注:史东山:《论电影镜头的组接》,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 年版第9—10页。)。这三个分镜头的原则,确实将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和观众的接受心理两个审美视角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史东山的电影理论体系,是以“电影镜头的组接”——即影像系统的结构方式为核心来系统地探讨中国古典电影艺术一系列形式美学课题的。史东山认为,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在“电影镜头的组接”方面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形式美学问题,也就是影像的整合问题。史东山指出,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在电影镜头的组接上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念:“只有相当差别的距离,或者相当差别的角度的两个镜头相联接,才能予观众以流畅或活泼的感觉。”(注:史东山:《论电影镜头的组接》,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因而在具体进行镜头的组接时,“对于观众已熟悉的动作一般不完整地保留在同一个镜头内,应将其切分,以利用它来增加上下两个镜头的联系性。”(注:史东山:《论电影镜头的组接》,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这是中国电影艺术家对于影像美学的重要命题——“前后关系”问题做出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探索,它成功地解决了影像结构方式的连贯性与不连贯性的辩证关系问题。
以“电影镜头的组接”这一命题为核心,史东山还探讨了其他形式美学问题。电影影像的节奏和韵律问题是史东山所要研究的另一重要理论课题。史东山明确指出:镜头组接的节奏和韵律问题是一种“形式的形式”,即“外形式”,它可以通过镜头的对比衬托、长短变化来体现。(注:史东山:《论电影镜头的组接》,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27—28页。)他认为,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在镜头组接的节奏和韵律方面“讲究表现方法的精炼,结构的紧凑和节奏的有力。”(注:史东山:《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中国电影出版社1954年版第30页。)从而在镜头语言上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民族风格。对于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的声音观念问题,史东山也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总结。他指出,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虽然要求电影本体中的声音元素由从属于“视觉”的关系上来处理,但同时认为“声音虽然是从一种物体上发出的,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也常常成为一种脱离它的物体而独立的东西被记忆着,所以它有可能让我们在电影上独立运用来表现,而不会破坏电影艺术表现的逼真性。”(注:史东山:《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中国电影出版社1954年版第34页。)因而,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既强调电影语言的视觉特性,又同时注重电影叙事体系中声音元素独特的艺术表现功能。早在声音技术传入中国影坛之初,中国电影人就接受爱森斯坦的声音观念,把声音作为艺术因素来看待。成功地运用声画对位等声音艺术表现方式,把“声音表现”从“物体表现”的附从地位上解放出来(注:史东山:《论电影镜头的组接》,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34—35页。),而未出现象好莱坞电影中的那种技术至上主义的创作倾向。此外,对于中国古典电影的情节结构方式和具体的镜头形态特征,史东山都作了详尽的理论总结。尤应指出的是,《中国电影》杂志1959年2 月号发表的史东山的遗作《在写导演剧本与拍摄时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刊载了史东山所总结的22条具体的拍片规则,这是他一生导演艺术经验的具体总结,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史东山在其论文《谈谈电影文学剧本艺术形式的要求》中说过:“电影在各种程度上汲取了各种艺术的有助于电影表现方法和艺术美的东西,而它自己又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注:见《论电影剧本创作的特征》,中国电影出版社1956年版,第75页。)这是他进行电影形式美学研究的一个理论依据,也是他同时代的电影艺术家对于电影作为艺术的一个基本认识。史东山曾经热情洋溢地赞美“电影无疑问应该是一种‘特长’最多的艺术。它的潜在艺术能力还没发掘净尽,有待于将来的努力。”(注:史东山:《论电影镜头的组接》,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其遗响至今振聋发聩。(注:史东山于1955年不幸去世,享年53岁。)
张骏祥:古典电影导演艺术理论的阐述者
与史东山一样,张骏祥是位善于进行理论总结的资深电影艺术家,他早在1943年至1944年领导重庆“中电”剧团期间,就写出《导演术基础》的专著,上卷《导演基本技术》在重庆《戏剧月报》1—5期上连载,中卷《导演的分析》发表于重庆《戏剧月报》1卷6期上,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惜未终篇。建国后,张骏祥就任上影厂和上海市电影局领导之职,于紧张繁忙的公务之余,仍孜孜矻矻,笔耕不止,辛勤总结中国古典电影的导演艺术。1958年7月, 其论文集《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还撰写了不少其它有质量的论文。
张骏祥的电影艺术理论的核心观念便是强调电影导演对电影本体内部影像性与文学性的全面把握,这是张骏祥在理论上潜心研究和总结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后所采取的基本艺术立场。张骏祥的理论起点是对电影影像的特殊表现潜力和它的局限性的揭示。张骏祥指出:电影影像“一方面享有时间空间的跳跃自由”;“另一方面,镜头功能的限制也迫使我们非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表现不可”、且“有画框、有焦点的限制”,因此,“优点和限制一起决定了电影的表现形式,也决定了这种形式的特殊的对生活作集中与概括地表现的原则”,“它要求在生活的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注:张骏祥:《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载《中国电影》1956年3期。)。 电影影像在直接诉诸观众的的视觉与听觉的同时,必须遵循“蒙太奇逻辑”——即电影思维的逻辑,它具有艺术直觉和艺术抽象的两面性。正是在影像的艺术抽象层面上,张骏祥引入了有关电影本体的文学性的观念。
张骏祥对电影本体的文学性研究,是从悬念技巧的研究开始的。法国著名电影艺术家特吕弗曾精辟地指出:电影情节结构中的悬念体现了电影影像中“那种与有节奏的或必要时突兀的剪辑相结合的相当随意地改变视点的能力”(注:参看(加)比尔·尼柯尔斯《从希区柯克谈阐释问题》,载《世界电影》1987年2期。), 它是电影艺术操作系统中意义层面与影像层面的结合点,而这正是张骏祥把握电影本体的文学性特征的基点。他在《谈悬念》一文中明确表示:“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在悬念技巧的运用上所提供的几乎是无穷的便利,我们更是还没有能够充分的体会和利用。由于电影形式所享有的时间空间的自由,由于表现生活可以从极广阔的天地到极其细微的地方,更由于是通过形象的表现手段,电影编导在悬念的运用上比起小说戏剧或其他文艺形式的创作者享有更便利更巧妙的工具。”(注:张骏祥:《谈悬念》,载《中国电影》1958年4月号。 )张骏祥在他的这段论述中所谓的“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便是指出电影操作系统中的影像层面;所谓的“悬念技巧”,便是指的电影操作系统中由影像层面指向具有文学性的意义层面的具体方式。在张骏祥的心目中,电影艺术家对于电影艺术的影像性与文学性的把握是决不可偏废的,否则是构不成完整的电影本体的。这一观念,导致他后来正式提出“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的电影观(注: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字》, 载《电影文化》1980年2期。)。
张骏祥电影导演艺术理论的核心便是强调导演艺术家必须兼具影像表现能力和文学表现能力。在漫长的中国古典电影艺术时期,不少电影艺术家都是集编导于一身的,“编导合一”是许多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观念。张骏祥的导演艺术理论便是对中国古典电影导演艺术的理论总结。他的导演艺术理论包括电影影像和电影文学研究两大部类,其重心在于探讨导演艺术中两者结合的具体途径及其理论依据。张骏祥是十分重视电影导演的影像表现能力的,他在《人物的动作和镜头的动作》一文中,精确地概括了电影导演艺术影像表现的四种方面:时空安排、造型表现、音响表现、人物动作和镜头动作的配合。他特别强调镜头性能对人物动作调度上所产生的影响,指出电影导演在人物动作调度外还得学会镜头动作的调度。(注:张骏祥:《人物的动作和镜头的动作》,载《电影艺术》1959年12月号。)张骏祥电影理论研究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导演艺术的文学性的阐述。1959年6 月他在安徽省文联电影编辑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谈电影剧本创作中的三个问题》,将电影艺术中的文学性归纳为电影形象(动作)、叙事结构和主题内涵三个方面。他还要求电影导演兼具造型能力与对电影对话把握的能力(注:张骏祥:《电影的对话》,载《中国电影》1957年7月号。)。 同时期撰写的长篇论文《电影剧本为什么太长》,文中将《渡江侦察记》等5部国产片与《列宁在十月》等6部前苏联故事片中的场景、群众场面和人物对话进行详尽的比较分析,来具体展示导演艺术中文学性和影像性密不可分的关系(注:张骏祥:《谈电影剧本创作中的三个问题》、《电影剧本为什么太长》,载《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与史东山的形式美学理论一样,张骏祥的导演艺术理论是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电影观念与电影创作实践丰硕成果的理论概括。他们的理论活动与同时期许多资深电影艺术家的重要论说——如柯灵的电影剧作研究、洪深和司徒慧敏的电影本体研究、叶明的导演艺术研究和苗振宇的电影声音研究——共同,在急风骤雨的年代,构筑起一座坚实的理论桥梁,将中国电影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保存和延续下来,汇入新时代的洪流中。他们的理论事业遗泽后世,至今仍显示其理论魅力。
时代高标:主流电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所说的主流电影理论,是指在五六十年代电影界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体系,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是这一时期电影理论的主体部分。建国初期,新政权的电影艺术家们的文化素养大多来自前苏联电影艺术,大量前苏联的理论与技术论著被翻译介绍进来。但即使在这一时期,新政权的电影理论家们就已经开始艰苦的独立的理论探索。早在建国前夕,东北书店就出版了阮潜(伊明)编著的新政权第一本理论专著《电影编导简论》。但在1957年前,年轻的主流电影理论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中。1956、57年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三本理论文集:蔡楚生等所著的《论电影剧本创作的特征》;冯雪峰等所著的《电影编导演随谈》;陈波儿等所著的《电影评论集》,大体反映了主流电影理论初期的概貌。1957年后,中国大陆主流电影理论进入了它的繁盛期。
应该指出,研究这一时期新中国影坛的领导者——夏衍、陈荒煤、袁文殊的艺术观念和电影理论对于把握中国大陆的主流电影理论形态是十分有意义的。建国后历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于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中主张:在“达到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目的”、“描写我们时代的劳动人民中间的先进分子、英雄人物”的前提下,“深刻地揭示生活中间的矛盾和冲突”、“描写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的人”、并着力“发掘正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写他们的感情、痛苦和欢乐”,(注:陈荒煤:《解放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60、94页;第361、94、370、374页。)实际上是在理论上提倡一种社会主义方向下的较为宽松的艺术氛围。钟惦棐《电影的锣鼓》和瞿白音《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中的电影革新思想的萌芽,也是在这一理论方向下产生的。
夏衍:经典电影编剧理论的集大成者
夏衍于五、六十年代进入了他的创作全盛期。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电影剧本《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故园春梦》《在烈火中永生》以及他参与创作的《早春二月》,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期,他以1958年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讲稿《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为核心撰写了一系列创见迭出的论文,对电影编剧理论作了全面的阐述。这些论文大部分收于1963年12月出版的《电影论文集》中。
夏衍在他的电影编剧理论中首先考察了电影编剧的艺术语言的特质问题。夏衍自谦“我历来所写的所谓电影剧本,都只是供导演写分镜头台本时‘使用’的提纲和概略,而并没有把它看作可供读者‘阅读’的‘文学剧本’”(注:夏衍:《杂谈改编》、《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227页。), 实际上显示了他对电影编剧艺术本质的基本看法。夏衍认为,电影编剧的艺术语言已不纯粹是文学语言,而具有电影语言的质素。夏衍强调电影编剧要以电影的而不是戏剧的艺术感知方式去进行艺术思维,其焦点集中在对时空的体验与表现的差异上。早在30年代,他就明确指出电影与戏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电影艺术在本质上已经克服了空间的限制。”(注:沈宁(夏衍):《〈权力与荣誉〉的叙述法及其他》,载《晨报》1934年1月21日。 )这一认识使得他在电影观念上超越了当时一般的中国古典电影艺术家,居于艺术探索的前沿。在五六十年代的电影编剧理论中,他进一步提出电影编剧的艺术语言要与“从易卜生以后成长起来的现代剧”的创作方式分道扬镳,而去借鉴“中国的戏曲”的表现方式,因为电影和话剧在艺术的感知方式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注: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99页。)电影与中国的戏曲一样,表现的是一种具有充分自由度的虚拟的时空,它们与话剧对于时空表现的严格限制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重要的电影美学命题——“维度”问题。电影艺术将现实的三维空间转化为具有深度感的二维的银幕空间,并且打破了第四维——时间的限制,展示了电影表现空间极大的艺术潜质。夏衍将电影艺术对时空的独特感知方式置于电影编剧艺术的核心,强调“电影编剧的方法和舞台剧不同”(注: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99页。),要求电影编剧的艺术语言突破文学语言的限制,确实抓住了电影编剧理论的要害。
夏衍电影编剧理论另一个要点就是电影编剧艺术的叙事方式问题。夏衍将“蒙太奇”这一电影镜头语言的结构方式引入电影编剧的叙事艺术中。他在编剧理论中一再主张要用蒙太奇的方式去结构电影剧本。他说:“中国人写戏曲、传奇很讲究‘脉络’和‘针线’,外国人写电影剧本很重视蒙太奇,这两者很有关系。”(注: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157页。 )夏衍的用意是要将蒙太奇方法转换为不同于戏剧和文学的独特的叙事结构方式。夏衍解释说:“说的简单一点,蒙太奇就是影片的连接法,整部片子有结构,每一章、每一大段、每一小段也要有结构,在电影上,把这种连接的方法叫做蒙太奇。”(注: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158—159页。)可见,夏衍在编剧理论中主要是把蒙太奇作为电影叙事的独特结构方式来体认的。在夏衍看来,电影编剧的叙事方式不是事件间的线性连缀,而是画面与场景的类似于蒙太奇方式的多元结构方式。在夏衍的叙事理论体系中,无论是叙事段落的设计、人物与事件内在脉络的把握、叙事效应的照应,都是以时空交叉的蒙太奇式的叙事结构为核心、并由它所决定的。
夏衍电影编剧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电影改编理论。建国后,夏衍先后成功地将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文学大师的经典之作改编为电影作品。五六十年代之交,夏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他的电影改编理论。夏衍认为:电影改编就是要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艺术样式改写成另一种艺术样式,所以就必须要在不伤害原作的主题思想和原有风格的原则之下,通过更多的动作、形象——有时还不得不加以扩大、稀释和填补,来使它成为主要通过形象和诉诸视觉、听觉的形式。”(注:夏衍:《杂谈改编》、《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221页。 )夏衍的电影改编理论所要集中解决的便是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这两种不同艺术语言的转换机制问题。夏衍围绕着媒介与素材、原著视点与改编者视点、影像表意与文字表意三个基本命题来全面揭示两种艺术语言的转换机制,并系统地探讨了诸如改编的三种方式(抓主线、舍其余;分段写;以个别人物为中心来写)、“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主客观视角的转换等具体课题,(注:参看《电影论文集》第266—267、244、268页。)从而在中国电影理论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电影改编理论的完整体系。
夏衍这一时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强调艺术语言的视觉化,标志他在观念上向中国现代电影的转向,并在理论上开了80年代影像本体论的先河。
《中国电影发展史》:电影史学的里程碑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理论界,对于中国电影史的史料收集与研究成为一个热点。50年代的大型电影理论刊物《中国电影》自1956年10月创刊起,特辟“昨日银幕”专栏,专刊中国电影史的回忆录;继起的《电影艺术》杂志仍坚持开辟这一专栏,直至60年代。在这个专栏中,发表了中国大陆早期电影人的一批珍贵的回忆资料。田汉、梅兰芳、欧阳予倩等艺术大师的长篇回忆录也在这一专栏连载。1962年起,中国电影出版社将“昨日银幕”专栏上的回忆录结集为《电影回忆录丛刊》出版,从而成为中国电影研究资料的大型文库。此外,《中国电影》和《电影艺术》还发表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电影史资料;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中国影协的有关部门,也开始征集和整理中国电影史研究资料。这一切都为大规模地开展中国电影史的理论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1963年2月,一部近百万字的中国电影史巨著——由程季华、 李少白、邢祖文三人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在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电影界的领导人直接关怀和亲自主持下由中国电影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套我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电影史”研究作为一门电影学学科的正式建立,因而在中国电影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电影发展史》创立了中国电影史学的一种范式,即电影思潮史的研究方式。这部电影史注重电影的意识形态研究,强调电影的社会文化形态,着力于电影艺术的价值判断,并以一种社会发展史观来观照电影艺术演进的轨迹。这样一种研究方式虽不免印上时代的痕迹,却使中国电影史研究具有了电影史学的理论形态,其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电影发展史》在理论上解决了新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即30年代左翼电影与延安电影的关系问题,确立了中国早期电影—30年代左翼电影—延安电影—新中国电影的史学框架。它还筚路褴褛地从浩瀚的史料中梳理了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至40年代末漫长的历史线索,清晰地描述了中国电影丰富复杂的历史生态面,在当时社会和学术环境所能允许的条件下,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延续了中国电影文化和艺术的命脉,其意义远远超出于理论领域。
《中国电影发展史》还保存了大量的中国电影史珍贵的文献资料。该书于编写过程中,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和中国影协的支持下,从全国各地收集了大量有关电影资料、报刊说明书以及剧照海报等图文资料,其中不少收录于这部电影史著作中。全书附图片八百余幅,书后并附1905年以来详尽的影片目录(除沦陷区电影外)。这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尤其具有抢救电影历史遗产的意义。
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中国主流电影理论呈现了一种迅速成熟、全面繁荣的态势,理论上的建树不胜枚举,前文未及提到的诸家学说:如陈西禾和张客的电影视听语言研究;冀志枫和周伟的蒙太奇理论;于敏和甘惜分的电影文学理论;羽山的类型电影研究;陈怀皑的电影剪辑研究;罗静予的电影技术理论;郑君里、成荫、谢晋的导演艺术理论;韦林玉的电影摄影理论;靳夕、姜今的电影美术理论;赵丹、白杨、孙道临的电影表演理论,都有厚实的理论成果。五六十年代的主流电影理论,不但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新型电影理论家群体,而且还树立了一种平实朴素的理论风气。他们注重自身的学术品格、提倡理论的实践意义、标榜平易近人的文风,这一切都作为这一时代理论风格的标志而存留于中国电影理论的史册中。
理想的冲突:东方电影美学的探索与影坛“洋务派”的崛起
五六十年代,以法国“新浪潮”运动为标志,世界各国电影正在全面地进行艺术革新。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具有远见卓识的电影艺术家正以自己的方式艰难地探索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路向。在理论思潮上,“对话”观与“接轨”观是中国电影艺术家对于中国电影艺术未来发展的两种不同的艺术理想。所谓“对话”观,就是以一种独立的现代民族电影美学的立场和世界现代电影艺术(实质上是西方现代电影艺术)对话与沟通;所谓“接轨”观,就是站在整体的现代“世界电影”的层面上,促使民族电影迅速转型而与之接轨。一种是多元艺术观,一种是整体艺术观,这是两种不同的中国现代电影的发展模式,也是对未来世界电影艺术图景的两种不同的理论预设。在这一理论背景下,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理论界,同时出现了对东方电影美学的探索和所谓影坛“洋务派”对现代电影理论开放的尝试。中国电影人这两种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思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了中国电影艺术家对于未来中国电影艺术改革的深刻的理论思索,也预示了8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创设中的一些根本命题。
从韩尚义到徐昌霖:建立东方电影美学的探索
对于建立东方电影美学的艺术尝试,早在三四十年代之交便开始了。当时一些有识见的中国电影艺术家打破古典进化论的传统/现代的线性思维模式,力图从中国古典艺术形式中发掘东方现代电影的艺术因素。他们精心地拍摄了一些舞台艺术片,探索“在写意与写实之间,别创一种风格”(注: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中所引费穆的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的艺术变革的路子。五六十年代,桑弧、石挥、陶金、徐苏灵、岑范、崔嵬等资深艺术家为深入把握东方电影的现代美学元素,相继创作了一系列优秀舞台艺术片,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受到法国“新浪潮”运动主将戈达尔的注目(注:《与实验艺术家的谈话》(外国部分第一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271页。)。与此同时,在电影理论界,当时的领导人茅盾和夏衍都曾提出过“创造民族形式的新电影”的口号;不少电影艺术家撰写了一些有份量的论文,从不同视角具体探讨东方电影的形式美学,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韩尚义和徐昌霖的理论成果。
著名电影美术艺术家韩尚义于1956年《中国电影》第2 期上发表《戏曲影片的布景形式》一文,提出了将“戏曲形式美的法则”转换为电影语言的命题。文章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我国古典戏曲是世界上独特的艺术,它用高超的写意手法,把艺术和自然区别开来,同时又是以生活作依据的现实主义艺术”。韩尚义理论上的出发点,就是要把握这种作为戏曲形式美学内核的“用主观融洽于客体”的写意手法,并将这一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有效地转换为电影语言,从而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电影形态的艺术变革路子。电影艺术家徐苏灵也在同一期《中国电影》杂志上发表论文《谈谈戏曲艺术片的一些问题》,与韩尚义的理论相呼应,具体探讨了戏曲写意手法电影化的途径。
1961年12月韩尚义再次和徐苏灵合作,在《电影艺术》1961年6 期上共同撰写了长篇论文《戏曲艺术片——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晶》,将他们对东方电影美学的理论探索推向了高峰。这篇论文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东方现代电影的美学原则,他们提出,理想的东方现代电影应是“它的艺术表现手段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风格上也不受写实与写意的局限”。而要实现这一审美理想,东方电影艺术就“要创造性地运用电影自己的艺术语言,而不是仅仅把电影作为单纯的纪录工具。”这是一种和巴赞纪实美学不同的现代电影观念。他们的这一美学原则的依据来自于对中国戏曲的写意形式电影化的信念。他们坚信“戏曲与电影在造型艺术的风格有了一定的通途”,并指出:“中国戏曲的表现形式,是努力不模仿自然,努力把艺术和自然区别开来”,“现在要把这种富有象征性和夸张性的戏曲语言和电影的这种写实性和分析性的形象语言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西方电影模式的带有鲜明的东方电影美学风格的艺术范式。他们在论文中,还探讨了中国戏曲的写意形式电影化的具体方式,如采取他们称之为“艺术的‘减法’”的手法,用简练的形象产生出“似与不似的意境”;运用非自然的装饰性的“布光”和音响效果,以造成“画面的单纯净朗和优美”等等。韩尚义和徐苏灵扎实厚重的理论成果为建立东方电影的美学体系打开了思路。
1962年,资深电影艺术家徐昌霖的专著《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连载于当年的《电影艺术》杂志1期、2期、4期、5期上,在当时影坛起着很大的影响,《新华月报》1962年第10、11期还专门予以转载。此书开门见山地提出:“怎样使我国有更多具有民族风格的影片屹立于世界影坛,研究和吸取我国丰富的古典遗产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课题。”这本专著以缜密的笔触从古典小说、戏曲以及民间说唱艺术等中国本土艺术样式的广袤领域,列举大量实例来阐述它们与电影艺术的姊妹关系。徐昌霖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他用大量不争的事实来阐明中国人固有的艺术思维与电影思维的近亲性。文中举例说:“民间说唱艺术跟电影最共同的特点是都最具有群众性,而且恰巧都是‘一次过’的艺术。同时评话和弹词的说表极为自由,忽东忽西,忽万马奔腾,忽空谷人静,在表现手段上,与电影艺术具有同样广阔的天地。”这一重要的艺术现象曾在五六十年代屡次为电影人所语及,如李玉华在《诗与电影——学习札记》一文中,将中国古诗与电影蒙太奇手法进行了比较和引喻,他甚至将韦应物诗《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的前四句切分成镜头,并把它构成一个蒙太奇片断(注:李玉华:《诗与电影——学习札记》、载《中国电影》1957年1月号。); 郑君里也在《画外音》一书中阐述了他在五六十年代将中国古典艺术具体引入电影导演艺术中的心得。但如此系统地提出将古代中国人的艺术思维与电影艺术思维“打通”的,徐昌霖应是第一人。70年代末,徐昌霖还继续与别人合作,撰写了《电影的蒙太奇与诗的赋、比、兴——吟诗观影随想录》一文,进一步解决“中国诗词的各种手法、技巧、意境可否运用到电影艺术中来”的课题。文章明确地将前人所概括的“赋”“比”“兴”这三种中国古代主要艺术思维方式与电影思维相比较,(注:徐昌霖、李长弓、吴天忍:《电影的蒙太奇与诗的赋、比、兴——吟诗观影随想录》,载《电影艺术》1981年1期。 )从而为东方电影美学的建立提供了新思路。
由于电影艺术是中国本土一种新兴的外来艺术形式,长期以来不少中国电影人习惯于以西方电影思潮与理论意识来参与和规范自身的理论体系与创作实践,形成了中西电影艺术和电影理论传通中的失衡现象。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中国电影艺术家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独辟蹊径地集中对东方电影美学作了初步的探索,产生了最初的一批理论成果,并开拓出不同的理论思路,在理论建树上显示出特异的独创性。
影坛“洋务派”的崛起及其对现代电影思潮的开放意识
影坛“洋务派”是电影理论家罗艺军在《中国电影理论与“洋务派”》一文(载1995年第3期《电影艺术》)中正式提出的概念。 文章说:“本文提出电影‘洋务派’这个概念,并不是基于已存在一个有共同电影美学纲领的理论流派,而是指一个长期从事电影理论翻译转而进行电影研究的群体。基于这个群体年龄、出身经历和知识结构比较相近,长期致力于外国电影理论翻译,在文化素养、文化视角,乃至理论方法和表述方式上,有近似的旨趣。在这个意义上,电影‘洋务派’又具有一定的理论流派的色彩。”这是一支50年代初组合起来,先是集结于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编译组,后转为中国电影出版社三编室(电影艺术编译室)的一批电影理论家。它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职业电影理论工作者群体,其兴盛期人数达40之多,形成号称仅次于中央编译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三支编译队伍”。
这个后来被称之为影坛“洋务派”的理论群体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影坛最具理论开放意识的一批文化人。他们以《电影艺术译丛》杂志为阵地,自建国初至“文革”前夕漫长岁月里,历经艰难坎坷,始终不渝地认真翻译、介绍、研究外国电影理论。他们从1952年3月20 日正式出版《电影艺术资料丛刊》起(1953年2月改名。《电影艺术译丛》), 到1964年6月停刊的近10年时间里(1959年10月至1962年3月曾中止出版),共出刊90期(包括1958年7月至1959年6月的《国际电影》),发表了约1500篇左右的译文。他们的理论活动带有比较严密的系统性和计划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往昔引进外国电影理论的那种零星的、即兴的、著译混杂的的状况。他们还以翻译原著的方式,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系统地原原本本地介绍世界上比较重要的电影思潮和理论,创立了一种在风云变幻的中国理论界引进世界现代艺术理论的具体操作方式。从他们起伏动荡的理论活动轨迹中,可以窥见五六十年代中国波谲云诡的理论风云。
建国初至1956年是其理论活动的创始阶段。这一阶段他们翻译活动,主要是介绍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理论和电影信息。这一时期的《电影艺术译丛》介绍了库里肖夫、普多夫金、爱森斯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罗姆、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杜甫仁科、邦达尔丘克、顿斯阔伊等前苏联经典电影艺术家的理论与创作,还翻译出版了《电影艺术丛书》(主要是前苏联电影理论)、《电影剧本丛书》(中苏电影剧本)、《演员小丛书》(前苏联电影演员介绍)和《电影技术丛书》等数十种书籍。
1957年1月至1958年6月是影坛“洋务派”的第一个理论活跃期。这一阶段的理论活动主要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对西方电影史上先锋电影理论——像雷纳·克莱尔、加·布努艾尔、贝拉·巴拉兹、布莱希特、 C·柴伐梯尼、伯格曼的电影理论和B·哥格兰、 保罗·茂尼等人的现代表现理论——的集中介绍。对于前苏联电影理论的译介,也转向维尔托夫、爱森斯坦等具有先锋意识的电影艺术家。《电影艺术译丛》还辟“电影特性问题”专栏,进行专题研究。乔治·萨杜尔《电影通史》也开始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至1957年,在中国电影理论界已形成一批“更多受到西方文化精神的熏陶”的电影理论家队伍(注:罗艺军:《中国电影理论与“洋务派”》,载《电影艺术》1995年3期。)。
1958年7月至1960年底是理论沉寂期。罗艺军说:在“反右派斗争”中,“影坛‘洋务派’队伍遭到严重清洗。这支队伍约近三分之一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个比例之大,即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文艺界,也是惊人的。”(注:罗艺军:《中国电影理论与“洋务派”》,载《电影艺术》1995年3期。)。1958年6月,《电影艺术译丛》停刊,改出较通俗化、大众化的《国际电影》杂志,但出刊至1959年6月也告终刊。 这一时期,电影界主要理论成果便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的翻译出版。
1961至1963年是影坛“洋务派”的第二个理论活跃期。1961年中国电影家协会宣告成立,其所辖中国电影出版社三编室(电影艺术编译室)专设以编译出版外国电影史论书籍为主兼搞理论研究的外国电影编译室。这一时期理论活动的重心由对早期先锋派理论的介绍,转向由法国“新浪潮”运动发轫的当代西方新电影运动理论的引入。当时,《电影艺术》杂志连续两期连载署名“习耐玛”所写的长篇资料《外国电影中的〈新浪潮〉》,标志60年代初(1961—1963)中国电影理论界对西方新电影运动及其理论的密切关注。1962年3月《电影艺术译丛》复刊, 将电影理论界对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的研究推向了高潮。该刊1—5辑全面介绍了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电影、美国“新一代的电影”,日本、波兰、古巴新电影运动至法国“真实电影”的大量原始资料,为中国影坛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现代电影的窗户,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一时期,《电影艺术译丛》还探讨了电影蒙太奇、电影改编、电影喜剧、“视点”问题等电影美学课题,其中绝大多数译文俱有前言、后记(大部分为邵牧君、郑雪来所写),这是影坛“洋务派”的理论活动由单纯翻译介绍向学术研究转折的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出版社编制了总字数达二千万字的外国电影史论选题计划,并组稿翻译,出版了鲁道夫·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艺术》、库里肖夫《电影导演基础》、《爱森斯坦选集》、《普多夫金论文选集》、亨·阿杰尔《电影美学概述》、岩崎昶《电影的理论》、卡·赖兹《电影剪辑技巧》等一批重要的电影理论经典著作;此外,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已译竣,马尔丹《电影语言》、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英国罗沙《电影史》、饭岛正《日本电影史》均已译校完毕,波兰托埃普立茨的多卷本《电影艺术史》以及世界各国其它有代表性的史论专著、大师文集等正在积极翻译中,这就为80年代大规模的电影理论研究打下了扎扎实实的理论资料基础,其理论贡献功不可没。
五六十年代所谓影坛“洋务派”的电影理论家群体为世界现代电影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最早的启蒙与研究工作。由于他们自身强烈的理论开放意识和深厚的理论积累,使之在“文革”结束后迅速跨越文化断桥,成为80年代中国新电影运动的理论先驱。他们与东方电影美学的探索者异趣的激进的艺术理想和西方的风格文体,直接影响了“文革”后的青年电影理论家们,因而扭转了一个时代的理论风气。
作为一个理论时代的标识,五六十代沉稳从容的理论品格、由深沉的理想主义情怀所驱动的忧患意识及其对超越个体的生命意义的追求,都体现着一种理论壮年期的成熟感。虽然作为一个理论时代已经过去,但它的某些质素将超越其自身的局限而对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起着长远的潜在的制衡作用。历史无法绕过这一时代,对于一个清醒的理论反思时期更是如此。
标签:中国电影论文; 蒙太奇论文; 电影语言论文; 中国电影发展史论文; 艺术论文; 电影理论论文; 电影艺术论文; 夏衍论文; 张骏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