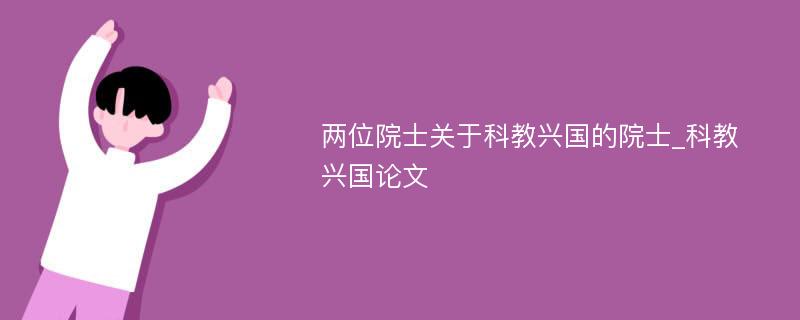
两院院士谈科教兴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教兴国论文,两院论文,院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卢强:《群言》杂志的同志最早动议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希望我能来主持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请来这些院士,他们每个人忙的程度一般人难以想象。
当得知诸位能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时,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在感谢和感动的同时,认真思考了原因,我想还是因为科教兴国这个主题牵动了大家的心,这是大家无时无刻不在关心考虑的问题。今天来参加会的各位院士都在本学科中极有代表性,希望大家能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和自己工作中的心得体会畅所欲言。
借鉴历史经验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赵忠贤:我是搞基础科学研究的,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有一种感受越来越强烈,就是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要尽量做到选题自由,对优秀的研究小组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这是不竭的科学创新思维和高层次人才来源的保证。
目前我国科学研究工作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资金和人才的分散。我们总在说投入不足,是的,我们的总量投入是有缺口,但只是一味强调美国投入了多少,日本投入了又是多少,这种单纯的比较是不够的。如果目前这种资金使用的分散状况不解决,投入增加多少也难抵因分散造成的不足。此外在人员配置上,我的感觉如同拍一部电影,有了好的构思、好的剧本和好的导演还不够,还要配齐能饰演各种角色的好演员。在完成科研项目时能配齐各种岗位所需的人往往成了我们的难题。我现在的课题组有9个博士,其中有5个是从国外回来的,力量很强了,但我仍不满意,觉得有些演员我还没找到。我是搞基础研究的,有此强烈感受,推及国防、产业研究更会如此。
我们可以借鉴当年集中力量完成国防任务的经验,尤其是搞“两弹一星”的经验,对于在国民经济和国防领域中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建议有关领导部门是否可以考虑部分恢复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调动、配备好队伍,在生活和工作条件上给予保证,这样做可以增强科研人员的责任感、荣誉感,也有利于集中优势突破、完成一些重大项目。
卢强:国家目标明确地立项,经调研后交给能够胜任的部门,然后集中配齐所需的人、财、物,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出成果。
赵忠贤:我认为还要复杂一些,即在产业、国防领域的一些重要项目,由专家和主管领导选定,不要采取招标的办法,而以指令性方式交给最有资质的部门,以某一部门为主,一些部门为辅,接受任务的单位可以自主调动资金、人员、设备。
如果这样,我认为可以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 为国家解决一些产业、国防中的重大课题。
张存浩:要找当前可与“两弹一星”比拟的主攻方向,对类似“两弹一星”这类大项目,这种用团队精神攻关的做法确实是需要的,同时要注意运用多种形式、恰当比例。千万不要一窝蜂,单打一。
赵忠贤:当然不能完全恢复,也不能冲击其他建设项目,不然我们又要吃亏了,只能是经过慎重研究、论证过的部分重大项目恢复,要两者结合起来。
卢强:不能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张存浩: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要给基础科学研究以一席之地。这一席之地有多大?美国是20%,欧洲是百分之十几。当然绝对数字是没法比的,但相对比例要恰当。我们过去定的指标是到2000年基础研究投入达到10%,这几年只有6%,达标有一定困难。
另外,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质量,包括一些产品的质量,都不能达到应有的最高度,总是差那么一点。这里边原因很多,但溯本追源常常还是基础研究的质量水平问题。往往我们的理解力并不差,但缺少原创性,有时和别人几乎同时起步,但逐渐就落后了,这与对基础研究在培养人才中所起作用的认识不够有很大关系。应该创造一个通过基础研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环境,同时在宣传和投入上给予适当的重视。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白春礼:科教兴国、知识经济、科技创新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达成共识的热门话题了。我赞成大家说的,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项目,要集中各部门的优势支持,应该是国家行为。一些关键技术问题,必须立足自主创新。如我国的大型交换机大都是进口的,如果对方做一点手脚,我们就完全被动了。
我赞成学习借鉴“两弹一星”的精神和经验,但现在我们抓的毕竟不是“两弹一星”了。如何凝练出具有前瞻性的有战略意义的与两弹一星可以比拟的大项目,比如在资源、信息、生物技术等方面的重大突破性项目,应是国家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共同论证确定的事。
就我国基础研究而言的创新,应该说情况并不是很好,这从自然科学一等奖的评选结果就可以看出。当然自然科学一等奖只是评价的一个侧面,但不可否认是代表了我们国家自然科学研究的标准、水平。一些带有基础性的,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凝聚力很大的项目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甘子钊: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灵魂,这种提法很鼓舞人,但实际上有一些现象却使人难以理解。如自然科学基金奖,80年代自然科学占一等奖的6%,90年代只占到了0.6%;国家发明奖,80年代自然科学占一等奖的1.5%,90年代则下滑到不足0.3%。
白春礼:1988年国家发明一等奖是4项,1991年只有2项,1992 、 1993年则为零。这说明重大科研成果水平下降,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在重大理论上的建树,或在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创新水平下降。
这种现象说明,在青年中提倡创新、培育创新很重要。科学院建立了“院长创新基金”,就是为了鼓励原始性创新。请年轻同志提出课题,不要你说国外或国内谁做了什么,就是鼓励创新尝试,鼓励那种风险极大、探索性极强的选题。成功不成功不是最终目的,10个人里有一个成功就不错了,但不能满足于小小的成功。现在的一些年轻科学家提出的新颖的想法不多,大部分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做一些延伸、补充。我们是要呼吁加大资金投入,但更重要的是要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思维的氛围,鼓励原始创新思想的萌芽。要从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着手。人的知识基础、视野、推理能力和思维方法,决定着他的创新能力。这就是科教兴国中教育所起的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源研究刻不容缓
刘光鼎:我在海上漂了30年,中国从南到北我都跑到了,我想多讲几句我国的资源问题。
现在我国年产石油和天然气达1.6亿吨,大庆占了5000万吨。 但是大庆已经是二次开发、三次开发,实际上回采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几,达不到30%,问题很严重。在“八五”期间我们曾申请立一个油储地球物理项目,就是想在摸清储集层的基础上把回采率提高10个百分点,使大庆年产5000万吨的水平还可以延续12年,这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贡献的提议。现在有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要“稳住东部开发西部”,我认为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从地球动力学的角度看,中国是三分的,东部的地壳减薄,西部的地壳增厚,鄂尔多斯、四川处于当中,从这一带到北部湾都是大气田,就不管了?只要石油,天然气就不管了?
赵忠贤:你应该明确指出,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提法,是宣传的语言,不是科学的语言。
张存浩:早就说要扭转这种看法,到现在也没有扭转过来。
刘光鼎:油田点天灯的现象不在少数。
张存浩:现在国际的趋势是天然气的产量要超过石油,份额达到能源总量的40%,石油只占20%,煤炭的比例更小。中国如果长久把煤炭的比重定在70%,是要吃亏的。
刘光鼎:问题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我国的主力油气田都存在于新生代陆相碎屑岩的地层之中,这样的油气田已经给国家作出重大贡献,但并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至少每年还要有3000~4000万吨原油进口。“两种(国内、国外)资源都要利用”的提法原则上大家都是赞同的,现在国际油价已经降到了每桶10元左右,当然要买。问题是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怎么办?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目前迫切的问题是抓紧研究、开发前新生代海相残留盆地的油气资源,实现中国油气资源的二次创业。中国并不是像以前人们认为的那样没有海相油田,在古生代时期中国有广泛的浅海分布,海相沉积地层中存在着巨大的油气潜力;中生代时期,虽经过印支、燕山及后来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强烈挤压、改造,但仍有一些海相沉积盆地残留下来,并未遭破坏。最近,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与胜利油田合作,应用叠前深度偏移技术重新处理了某地区的地震反射资料,进而查明海相古三千山内部结构。经钻探验证,可日产1059吨石油。
张存浩:在我们还不认识、没有想过的领域出了大成果。
刘光鼎:如果我们能继续扩大这样的战果,中国的油气资源还大有可为。陆相一口油井日产10吨左右,海相则是日产千吨,而且我们的技术完全可以达到。非常希望通过“973”能得到一些资金, 我们可以拿出一套地震层析成象技术,组织渤海和中国东部沿海的扩大开发,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路,我们嚷嚷了3年没有结果, 北朝鲜却在北黄海的白垩纪、侏罗纪找出了油气。
我们在塔里木投进了几百个亿,在那里打一口井要钻进6000米,钻杆在底下像面条一样软了。不是不可利用,但成本太高。
我国的矿产资源现状同样不容忽视,金属矿处于一种等米下锅的状态。总结国内外勘探经验,我国寻找金属矿床必须走“攻深找盲,寻找大矿富矿”的道路。我建议,对于金属矿床的调查研究,更应该采取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的综合研究,以求得比较接近实际的深刻认识。要分层次寻求规律性认识,以指导实践。
资源开发是立国的基础,人口、资源、环境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无论是油气能源还是金属矿床的研究都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培育、吸引、留住优秀创新人才是关键
张存浩:根据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的关键取决于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高层次人才要通过基础科学研究来培养,实践证明,通过大兵团作战,大规模生产的方式不是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正确途径。
人才培养不能只到博士生为止,应从博士后延续到成为中高级研究人员直至终生。人的进取和提高是没有限度的,甚至获得诺贝尔奖也不是极限。
赵忠贤:有这样的例子,博士论文就获得了诺贝尔奖,然后就止步不前了。
甘子钊:这就是过于功利,过于以成败论英雄的结果,是一种短期行为。
张存浩:在这一点上希望能与科技部、教育部的领导取得共识,不光要看人才成长的速度,还要注重他最终能达到的水平。
蒋丽金:成长的环境是不是也很重要?
张存浩:对,软、硬环境都很重要。
还有一点我认为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就是对拔尖人才不能够惯纵。前些年我到伯克利加州大学看到一种现象使我深有感触。该校的物理化学学科是世界知名的,李远哲在那里得了诺贝尔奖,应该说是登峰造极了。但他们还不断从校外找来不少同一小学科的优秀人才,鼓励他们与李远哲竞争,也鼓励他们相互竞争。那种刚刚小有成果就被捧得高高的做法,只会使人丧失危机感、紧迫感,浅尝辄止,出不了大成果。应该说我们的舆论和宣传媒介在这一点上常常作得过了头,一些部门的领导也没有正确地把握好鼓励与鞭策的度。
白春礼:去年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次青年科学家的前沿学科研讨会,双方各选了40位年轻的科学家参加。 每次会议所定的8个前沿领域的课题,由中美双方共同投票决定。每人讲半小时,答辩要一小时。不同学科的与会者可以自由提问,这种现场交流的方式对青年科学家的思维、表达应变能力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选议题的创新、前沿,决不能是国内一些人习惯了的大量引用、借鉴国外的文献,重新组织后再去讲,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创性。如美方前年自己先开了个会,初选了8个课题。其中两个提出时并没有获过奖,一个是激光制冷, 一个是疯牛蛋白,报告以后都获了奖。这说明他们在选择课题时就已经很前沿了。令我深有感触的是,在我国,这种对青年科学工作者成长很有好处的交流、研讨活动很少,青年科学家接受挑战的机会也太少。今年这个会在北京开,美国科学院的院长要来,我们在选择国内参加会议的青年科学家的问题上还有一定难处。所选的40个年轻科学家,一要英文好,二要研究的项目必须有创新的成果。这些人大部分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当然今年还可以选出来,但如以每年40个的数量选择替换,我担心以后是不是能接上。
去年6月9日国家批准了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这个工程应该讲是国家行为,是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希望能从国家层面上吸引最优秀的国内外人才投入这项工作。
甘子钊:在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留住优秀人才的任务变得特别尖锐。尽管近年来实施了各种吸引、留住人才的措施,但仅以北大物理系为例,保守的估计外出毕业生也有70%,实际上还超过这个比例,学业成绩位于前1/3的,100%走了。 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靠待遇的改变,应重新考虑我们的人才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尤其是尊重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要真正落实到行动上。要使那些下决心奋斗在国内第一线的同志感受到关切和温暖。
现在我们的一些做法就不够科学、合理。如以SCI 的数量评定一个人的能力,SCI对一段时期的科学学有统计的意义, 但如果对每个人和单位的评价都与SCI的数量联系起来,就很成问题。 另外一些青年科学工作者一旦被授予了杰出青年等称号,马上就给他安排许多职务,占去了他的大部分精力,这种使用人才的方法实际上是浪费了人才。
白春礼:现阶段留住和吸引人才在实际操作中常会碰到不少具体困难。如长江学者计划是因为有李嘉诚先生的捐款才开始启动的,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用于个人支出的部分只有500元和1000元这两个档。 我这几年带过的学生也都陆续走了,其中有一些我很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他们也有留下的愿望,但因住房等一些具体困难实在解决不了,最后还是没能留下。我很惋惜,但也很体谅他们的难处。
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为吸引人才专门留出了11套住房,但这也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要吸引100个人怎么办? 现在各所都在挤出一部分科研经费盖房子,但总不能这样无限期地盖,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这些微观具体的事情,应该从整个体制的运作上解决根本问题。
提倡追求科学、追求真理
甘子钊:鲁迅先生在30年AI写作了杂文《沉渣的泛起》,距今已六十余年了,可沉渣泛起的现象依旧很严重。一些人仍然对极端愚味无知封建迷信的东西津津乐道,而我们所看到的荒谬的现象还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这些现象的出现只是因为文化水平的低下还好理解,现在情况不是这样,一些大学生,甚至物理系的研究生也参加其中,这就要分析其中较为复杂的原因了。宋健同志曾经讲过: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时间还不长,科学的思想要在人们心里扎根还要做比较艰苦的努力。
现在我们谈的多是科学对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对科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一种手段,科学对于破除迷信、认识自然的作用,对于人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影响谈的太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的,但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力。现在是不是可以适当地倡导一点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尤其是基础科学,它本身的动力就是追求真理,而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人类的历史证明,这种非功利的追求从整体来说为人类带来了最大的功利。18世纪欧洲搞电学的都是一批莫名其妙的怪人,美国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房龙在他写的《人类的故事》中,称这些人是“一批可爱的疯了”。现在我们常能看到一些英雄的雕像,这些科学家却永远没有雕像,但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比这些英雄大得多。
我们在思想导向上还应该高举现代科学的旗帜。我认为现在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太大,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能持科学的态度,带头说了一些属于哲学上后现代主义的话,把当代社会的缺点问题归结到自然科学本身,这完全是错误的。如污染问题,被认为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实际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人类还没有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结果。另外在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也应注意到古代文化中确实有一些不利于近代科学发展的因素。现代科学强调分析的精神,过分强调“天人合一”、“主客观合一”会不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张存浩:中国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还没有最终完成。西方科学的发展主要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思想解放了,文学、艺术、医学的发展,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我们现在还是要大力宣传小平同志的理论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倡导崇尚科学,反对迷信。
为学科间的合作创造条件
蒋丽金:我是研究生物光化学的,我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跨学科的科学研究常会遇到障碍和阻力。如新生儿黄疸病的治疗,传统的办法是“全身换血”,使他在以后的生长过程中产生出所需要的一种酶。由于新生儿很多器官并不健全,这种办法风险很大。后经光化学等科学家证实,利用太阳光照射可以治疗小儿黄疸病。这就需要光学、化学、生物学、病理学等科学工作者的联手合作。还有我正在研究的利用第一代光疗药物“血卟啉”抑制癌症,这种疗法对健康组织损伤较小,无传统化疗的毒副作用,也是一个前景看好、探索性极强的课题,同样也需要医学、光学、药学、农学的跨学科协作。但在协作的过程中,因为涉及多学科,申请经费常会遇到困难,致使工作很难进行下去。
卢强:自然科学基金会专门设立有交叉重点学科基金,就是鼓励这种研究的。
张存浩:但在实际操作中常会因一些学科过于注重自己的利益,如每个学科都希望向本学科倾斜,使这项工作在执行中还有不少缺欠。
张启先:蒋先生讲的跨学科研究问题,我也深有感触。我原来是教授机械原理的,后来转到了机器人的研究领域。从单纯的理论研究转到应用研究,思想上有所拓宽。我们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和海军总医院联合研究的立体定向脑外科机器人系统,就需要脑外科、机器人、计算机等跨学科的交叉研究,现在也面临着经费的问题。希望自然科学基金会在基金的分配使用上,更加有利于开展多学科综合的创新研究。
蒋丽金:本世纪初以来,科学研究的过程逐步经历了一些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同程度地拓展了与之相关的多学科的合作。各个学科的学者除了致力于本学科的发展外,逐渐感觉到不能忽视学科的相互作用。他们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完全可以移植和借鉴到其它学科,共同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以推动各学科的快速发展。事实证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可以起到扬长避短、事半功倍的作用。
完善政策 狠抓落实
张存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震惊,我们原来说21世纪是和平发展的世纪,现在看来恐怕不完全如此。我们的国防过去比较薄弱,今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些政策要相应调整。
甘子钊:为了国家安全,应慎重研究开发一批实用技术产品,以启动内需。
赵忠贤:不要单纯追求指标,要开发实用的,我们自己能掌握的,不受别国制约的技术产品。
张启先:这就涉及到把一种研究成果转化成市场产品,要有人操作,要有经费。现在往往是有了创新思路,却要为申请经费经过相当复杂的论证过程,花费很长时间。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宁可与一些可以先承担风险投资的公司合作,出了成果优先给他们转化成经济效益。要想扭转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局面,学校科研人员也要有观念的转变、拓宽。
刚才大家讲了创新基金很重要,我认为转化基金也很重要。一般的高校没有条件像清华、北大那样成立开发研究院,直接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也没有科学院那样的创新工程体系。国家是否可以拨点钱协助在一些高校设立转化基金,因为非名牌大学也会有冒尖的创新人才,也应给他们以脱颖而出的条件和机会。
另外我国科技奖项过多过滥,这种情况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副作用。
张存浩:昨天公布了科技奖励法,减少了奖的等级,提高了档次。
刘光鼎:科技部目前对重点基础研究搞的招标的办法并不科学,往往是为了一个项目几个部门都来争,思路在这边,实力在那边,怎么办?申报、解答耗费了很多时间,最后两败俱伤。
甘子钊:我也认为项目招标提成的办法很不科学。科研成果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但科研成果本身并不是商品,宏观地讲,商品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而科研成果的价值和它所花的钱是不等值的。我们对前苏联科研体制的弊端体会比较深,但是也应该承认正是在那个时代苏联科学家对世界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许多领域有重大创新,始终站在当时科学的前沿。这种现象说明,要想出科研成果,除了体制的转换外,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思考。我们现在谈规划、想法、政策谈的特别多,而且过分把责任交给了领导。我认为现在的科技体制改革有些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成立了很多专家小组研究课题,但如果是人人都能认可都投赞成票的课题,原创性一定很小。市场经济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主要放在生产和进入市场的环节。而现在的科技体制改革越来越加大了机关的作用,具体的课题由领导定,对科学家的使用也是如此。
白春礼:我们目前面临着一个非常好的机遇,科教兴国被提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但要真正落实还要遵照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在整个软环境上提供一个有利于科教兴国的最佳氛围。有一些问题确实不是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如房改,人事制度、劳动保险等配套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不解决,科研单位要想做到队伍精干、人员流动,很难。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到目前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许多具体问题。
卢强:今天大家谈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但涉及各自研究和工作中的问题,还就科研体制改革、科研政策调整、科研环境改善及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和人才流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和建设性意见。相信这些意见发表后,一定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由于时间关系,大家仍觉得意犹未尽,《群言》杂志今后将以专题座谈、专题笔谈、专题访谈等多种方式长期关注“科教兴国”这一主题,希望各位能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
再一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叶稚珊 整理)
标签:科教兴国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两院院士论文; 科学论文; 甘子钊论文; 白春礼论文; 刘光鼎论文; 卢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