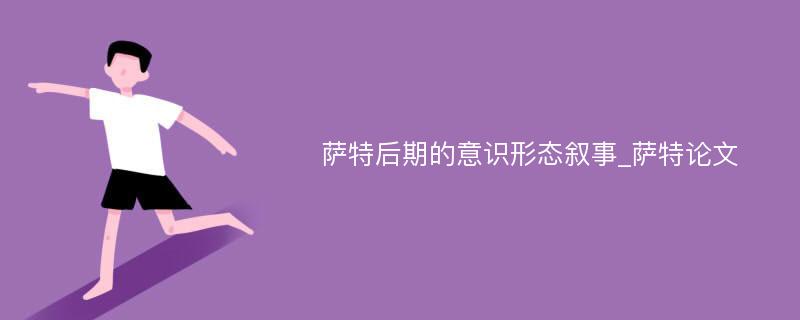
萨特后期的意识形态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特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8-0061-05
二战以后,萨特的叙事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果说在萨特前期,他主要运用一种表现个体伦理困境和生存悖论的伦理叙事,那么,在后期,他提倡“介入文学”,在文学中表现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倾向。与这种主张相一致,他在文学创作中使用了意识形态叙事的方法。萨特意识形态叙事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叙事方法和技巧上,也体现在文体风格的转变上。“处境小说”和“处境剧”的出现,便是这种叙事模式的文体显现。
一、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的叙事
“意识形态叙事”概念,来自于萨特研究专家、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著名学者詹姆逊。他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把叙事定义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将叙事看成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投射。他认为:“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做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1](P67-68)詹姆逊以研究萨特的文体风格作为自己的学术起点,并在研究中表现出来自萨特的强烈影响。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提出,一个作家要在风格、技巧和题材上进行变革。而风格的形成,不仅受到作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制约,而且和作品中的题材和叙述技巧密切相关。他认为:“一位作者的风格总是同一种世界观有关;句子、段落的结构,名词、动词等的使用,位置、段落的构成和叙述的特点……”[2](P114)詹姆逊也许就是从这里出发,分析文学风格和作品中语言的关联。
在詹姆逊看来,作品风格不仅是一种审美意蕴的外化,而且显示出文学价值的历史意义。因为,“在我们时代,自圆其说的形式或任何普遍认同的文学语言已然不在,作家作品的价值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或是否呈现与现存风格截然不同的一种风格。”[3](Pvii)詹姆逊是在萨特文学创作的整体成就上,确定其风格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义的。但我们可以参照他的思路,在区分萨特前后期文学创作风格的差异时,发现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在萨特个人的创作历程中,也存在着某种“危机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剧变,萨特由战前只为自己写作的状态,一下子发现了文学创作的社会性。他开始为别人写作,为所生活的时AI写作作。萨特在文学观念上实现了自我超越,改变了旧有的文学形式,表现出了一种更具时代精神的风格。
这种形式上的革新,非常明显地体现在语言这个微观世界中。具体到文学中的语言叙述层面,就是他由早期的自由主义伦理叙事向意识形态叙事的转变。与萨特介入社会的宗旨相合,意识形态的叙事展示的“不仅仅是人们在叙事中表达的欲望和幻想”,也是那些“暗含的对现实的逃避即意识形态的遏制”[4](P77)。
二、处境小说和处境剧——意识形态叙事的“新”文体
在萨特后期,“处境小说”和“处境剧”是他展示人们生活处境的主要文体样式。处境小说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它“是传统小说意识的回归,作为介入文学,揭露世人真诚作弊,描绘社会生活的种种处境,可称处境小说”[5](导言)。处境小说的核心在于“描绘社会生活的种种处境”,以达到揭露、批判和改变现实的目的。它的意图和后来萨特提倡的处境剧一样,鼓吹介入时代,改变人的处境,以至改变社会历史环境。如果说早期的处境是一种更具个人化的相对有限的时空环境,那么,处境小说和处境剧中的处境则是融入了社会历史维度的广阔时空环境。他明显地扩展了处境的内涵,将外在于自我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纳入进来。
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写道:1930年起,由于世界危机、纳粹主义上台、西班牙战争等,大部分法国人“不胜惊愕地发现了自己的历史性”[6](P248)。此时,萨特终于发现“自己处于处境之中”,意识到自己“被粗暴地重新纳入历史,被迫创作一种强调历史性的文学”[6](P251)。他已经逐渐从对抽象的个人存在处境的分析,转为对个人现实的、具体的、必须承担的社会处境的研究。在萨特那里,“处境”成为将文学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交汇点。在这个交汇点上,“文学在两个向度上表达着自己的政治内涵,一方面是它的社会群体特征,另一方面是它的阶级特征,这两方面如同一个坐标系的水平轴与垂直轴,共同构建起文学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对文学史的描述中最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阐释理论。”[7](P46)在萨特看来,作家的任务就是把握他的处境(即他的社会历史环境),然后鼓励读者采取行动,摆脱由处境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或阶级的局限性,最终改变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
如果说早期的萨特没有将处境放在意识形态环境中进行考虑,那么,后期的萨特则没有将处境和意识形态分开:“处境已经同意识形态的含义更为广泛地联系起来,也同这种差异相关联,即‘处境’是一种特殊的历时性和辨证性概念,从中我们可以读出那些包含了意识形态冲动及实践的信息。”[3](P224)在这种意识形态冲动之下,萨特的实践方式表现为——“惟一可能想到去写的小说是处境小说”[6](P258)。从萨特本人的发展来看,这表明他已从关注自我的个人化创作中超越出来,进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的洪流当中,为社会写作,为民众鼓与呼。这种胸怀和气概,对萨特来说,不可谓不新,不能不令人关注。
三、《自由之路》中多音齐鸣的复调叙事
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共分三部:《不惑之年》、《缓期执行》和《痛心疾首》。从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上看,《自由之路》是一个有着内在关联体系严密的整体,被视为是具有政治内涵的处境小说。
无论是从框架、社会生活容量、时空跨度还是人物形象的类型上,《自由之路》都大大超过他的早期小说。他借鉴了新闻报道的表达技巧,并使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来展现各种人物的不同意识。在那些类似文献纪录片性质的宏大的政治场面中,交叉的蒙太奇技巧所渗透出的象征意味,折射出丰富而又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自由之路》中,各种叙事声音同时说话,有时相互交叉,多重叙事话语汇成了万花筒般的景象。“作者转动万花筒,让不同的价值观念撞击,让复调音乐夹着噪音一起迸发,让人心的浮动通过乱哄哄的场景跃然纸上。”[5](P26)
特别是在后两部《缓期执行》和《痛心疾首》中,多音齐鸣的效果形成了一种叙事的狂欢。《痛心疾首》描述的是法国大溃败的情景,以布吕内为中心的一大群法国战俘被押往德国。萨特讲述了许多单个的小故事,并把它们加以归类组合,成为一部记录“人类崩溃”的编年史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文学作品成为狂欢的广场,不同的叙事话语打破了独白性话语的垄断性地位。众声喧哗形成了“一符多音”的荒诞气质。在列维看来,“萨特的作品仍然是将虚构和杂文混合在一起,将自传和传说,将对文明、对人类、对世界的疯狂指责和诗歌混合在一起。按照萨特的定义,小说是全面的文体,是一架机器,可以让视点旋转起来,使叙述变得不可名状、四分五裂。”[8](P148)
这种狂欢化的叙事,通过对单一视角的拒绝,让每一种叙述声音都具有独立的地位,代表一个绝对的价值。不同声音的出现,意味着代表不同价值和利益关系的并立。詹姆逊从这种具有对话性质的声音之中,看到了阶级话语的范畴。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把阶级理解为关系,并且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最终的(或理想的)形态总是二分的。体现这种关系的话语范畴,其结构在本质上是“对话”。在巴赫金的阶级话语之中,“即对话的常规形式本质上是一种‘对抗性’的,阶级斗争的对话是两种相反的话语在一个分享的符码之总的统一体内部斗争产生出来的话语。”[9](P75)
四、《自由之路》中意识形态叙事的方法与特点
在《自由之路》中,萨特的意识形态叙事具有以下方法和特点:
第一,从庸常世俗生活的描写到宏大社会历史画卷的刻画。在情节方面,《缓期执行》和《痛心疾首》不再像萨特早期的小说,局限在个别人物庸常生活的细节描写上,而是表现那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和场面。
主人公开始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走出来,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战争来临,他该怎么办?在《自由之路》中,当视角范畴由个人生活故事提升到集体故事的时候,萨特也由对个体主义的描述向新型的集体事业叙事过渡。于是,作品中矛盾冲突的设计,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小说中不仅出现了宏大社会政治场面的描写,还出现了富有政治意味的人物形象。此时,个人的生存状况开始与社会历史环境有了密切联系,萨特不再是站在伦理的角度观察问题,而是自觉地进行政治观察。
在《自由之路》的第三部《痛心疾首》中,有和《厄罗斯忒拉特》一样向着人群射击的情节。只不过,《痛心疾首》中的马蒂厄,不再是对着无辜的路人射击,而是对着德军射击。萨特是这样描写他的射击动机的:
这是一次极大的报复,每发子弹都是对他过去不敢有所作为的报复。“一枪射向洛拉,因为我不敢偷她的钱;一枪射向玛赛儿,因为我早该甩掉她;一枪射向奥黛特,因为我不敢吻她。这一枪射向我不敢写的书,还有一枪射向我所拒绝的旅行,再有一枪射向全体我原本憎恶却又竭力去理解的人们。”他还在射击,法律被打得漫天飞舞;你说爱你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砰”一枪打烂你的臭嘴;你说你永不杀生,“砰”一枪正中伪君子的嘴脸。他向大写的人开火,向德行开火,向世界开火:自由就是恐怖……[10](P242)
虽说马蒂厄的射击动机和厄罗斯忒拉特有相似之处,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获得自由,并且都以杀人这种方式来换取自由。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射击都是荒诞的、毫无价值的举动。罗杰·加洛蒂在《萨特的戏剧与小说是我们时代的见证》中认为:马蒂厄的“行为不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而是形而上学的、人格的事件:无非想使自己留下一个痕迹。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比厄罗斯忒拉特具有更多的历史意义”[11](P338)。
笔者认为,马蒂厄射击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厄罗斯忒拉特。首先,马蒂厄不像厄罗斯忒拉特那样由于憎恨人类,才有丧心病狂之举。马蒂厄的狂热,产生于对自己以往谨小慎微行为的痛恨。这种在马蒂厄身上出现的私人性事件,凝聚了当时战败后法国人的反省和自责。其次,通过射击这个行动,马提厄对自由有了全新的理解。这既是与过去沉陷于个人主义的旧我划清界限,也表明一个投入现实,在社会历史处境中寻求自由的新我即将产生。马蒂厄的狂热,不是厄罗斯忒拉特剥夺无辜生命的丧心病狂,而是想改变旧我获得新的存在价值。因此,马蒂厄的所作所为,要比厄罗斯忒拉特有着更多的历史意义。
第二,小说的叙述模式由个人模式向集体模式转变。从结构上来看,《自由之路》明显不同于萨特的早期小说,它已由其早期小说中的情绪结构模式向集体结构模式转换。法国学者塔迪埃认为:20世纪法国小说的封闭型结构分为三种类型:个人模式、家庭模式和集体模式。所谓“个人模式”,就是叙述个人的成长史、个人的历程及其主要危机的情节模式。所谓“集体模式”,就是以某一时代的集体命运代替了个人命运或家庭命运的叙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物的数量增加了,他们之间不再靠血缘维系,其中某些人代表着某一地域、某一阶级或国家,作者把他们放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画面上来展现,向历史借鉴了人物、事件和时间表。这类小说在结构上一般沿用历史年表,注明历史年代,具有坚实的参照系。当历史阶段结束时,作品也获得了完整的结构[12](P47-58)。笔者认为,《自由之路》明显地属于这一模式,它以宏大的架构,描述了以马蒂厄和布吕内为代表的一代法国青年的历史命运。
首先,与以往那种具有自传意味的个人独白式的小说不同,《自由之路》中人物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成了“群像小说”[4](P26)。其次,从人物性格来看,萨特由描写罗冈丹式的孤独的自由形象,过渡到有初步政治意识的“社会人”。人物也由一种焦虑人格,逐渐演变为一种比较明确的政治人格。马蒂厄和布吕内再也不是独来独往的个人主义者,而是在战争环境中集体组织中的一员。
从叙述的事件来看,意识形态叙事也比伦理叙事清晰了许多。萨特早期的伦理小说,不强调表现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环境,故事充满了象征意味。小说《恶心》里并没有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罗冈丹眼前那个一切令人恶心的布维尔城,在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地图上找不到,小说里也并没有出现某种反动社会势力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形象。人物就更加面目不清,虽然大部分有名有姓,但我们并不清楚他的五官相貌、家庭住址和职业爱好。罗冈丹就是一个没有家庭、没有朋友和工作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种类似于表现主义的手法,是萨特有意通过模糊事件、人物的现实真实感,而凸显人类存在处境的普遍性。然而在意识形态叙事中,为了突出叙事的现实指向,萨特像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叙述了时间与地点明确的社会事件。
《自由之路》中的中心人物,不再像萨特早期的伦理小说,是绝对、唯一的叙事主体。在他身边,总有一些并肩而立或截然对立的人物存在。在周围人物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这些人物逐渐疏离自我,并最终从自我中解脱出来。他们站在自己的外部审视自己的人格,思考自由的价值。在挣脱了个人主义的束缚以后,他们渴望将自己个人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群体、民族、阶级、国家甚至人类的命运和追求中去,由此克服个体生命的缺欠。这种理想主义的光芒,与萨特早期伦理小说中那种混沌和黯然的道德相对主义比较起来,更容易让人看到若干亮色。
第三,从道德情感的不干预立场转变为在社会政治价值的全面介入。如果说萨特早期的伦理叙事,是一个隐匿在作品背后的叙述者,对故事作“不动情”讲述的话;那么,萨特后期的意识形态叙事,就如同站在舞台中央的演员,向观众表白他的情感与立场。
在《缓期执行》中,我们看到,一个“阶级”的叙事者时隐时现。小说的一开始,叙事者描绘了一幅错综复杂的社会画卷。“开卷便采取了闪电般的跳跃方式,从一张报纸跳到另一张报纸,从一个专栏跳到另一个专栏,从气象跳到巴黎肮脏的市容,从圣彼得堡的霍乱跳到拉巴特的鼠疫或黄热病,从保加利亚的独立跳到奥地利的威胁,把读者引入10月5日这一历史性日期的真实之中。”[12](P309)如果把“10月5日”换成“9月30日”,《缓期执行》也有了和《善良的人们》一样开头。小说描述了在同一个时刻,从伦敦到柏林,从张伯伦到里宾特罗甫,从布吕内到泽泽特一些人的所作所为。
这样的叙述风格,看似颇具现实主义的风格,但叙事者并不是一个冷静超然的鸟瞰者,他似乎无意描绘社会或历史的全景图像,而旨在勾勒一幅线条分明的讽刺画。他们泾渭分明地属于各个阶级,如以雅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以布吕内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马蒂厄为代表的追求绝对自由的知识分子,另外还有一些历史人物。而且他们的性格特征、政治立场也是按照叙事者的设想确定的。这样的“脸谱”只有一个“阶级”的叙事者才能做到,只有他才具有这样的意识和权力。
同时,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更多的是依据叙事者的观念,而不是现实生活逻辑的必然性。叙事者的操控多于人物自身合乎情理的发展。同时,为了使小说有个积极的结局,萨特让他的主人公参加抵抗运动。布吕内在战前对纳粹德国采取观望态度,直到德国进攻苏联,他才参加抵抗运动。这与萨特本人的思想困惑息息相关:他对小说中的主人公定位充满犹豫,难以对他笔下的人物作出评价。这些主人公虽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创造历史。“这样,提出让良心重新肩负起历史的责任的《自由之路》便站不住脚,从而不得不停留在未完成的状态。”[13](P35)萨特的此举,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不符,却鲜明地表现了叙事者强烈的阶级意识。
五、结语:意识形态叙事的激情与幻灭
萨特的意识形态叙事,注重阐释叙事主体的意识形态立场,强调作品中的叙事与社会环境、文化规约之间的关系,叙事技巧的使用是为了强化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他由为自己写作的状态转到为他人写作,极力弘扬文学的社会功能,“政治萨特”逐渐取代了“文学萨特”的角色。他以文学实践积极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体现了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这是萨特文学观的一次质变,从早年对文学本体论的关注,演变为文学可以用来干什么的实用主义观。在文学创作中,叙事技巧的使用是为强化文学社会功能的目的服务。
从情节上来看,意识形态叙事贴近现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事件和政治危机,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感。在瞄准个体的选择和行动的同时,作品以宏大叙事将人物命运置于历史和政治事件之中,显示出不同于伦理叙事的强烈历史感和政治倾向。在叙事的情感和道德立场方面,意识形态叙事由原来的展示道德相对主义转变为政治现实主义,即把功利性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表达叙述者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在某种程度上,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关系被简化为一种启蒙/被启蒙、训导/被训导的模式。意识形态叙事不仅把叙事当作一种社会行为的象征,而且成为反映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舆论工具。它以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立场影响着民众。
萨特在后期也创作出许多颇有影响的作品,但与早期的文学创作相比,它们在艺术上就显得粗糙。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往往被先行注入某种价值观念,以至思想大于形象,有些人物被简单地图解为政治人格。特别是在戏剧文学中,在情节处理上有模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一些作品因多是对当时社会历史事件的迅速回应而成为急就章。因为过于靠近现实,它们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意识形态叙事相信它对社会具有改造力量,同时又过分地高估这种力量。这样,它不免陷入被各种功利主义控制的泥淖。随着时代的变化,一些功利性很强的作品难免有时过境迁之感。在中国纪念萨特百年诞辰的活动中,柳鸣九这样评价萨特:“萨特作为一个作家、哲学家,不仅非常社会化、政治化,热衷于卷入各种路线的文化争端与政治斗争,而且凭借自己的声望与才华、信仰与自信,在具体的事件与极左思潮中,投入得过于执著。他没有给自己留下缓冲的距离,没有保持一个思想家的高瞻远瞩和超然态度,而是把自己的阵营性、党派性表现得过于鲜明。一旦他所立足的阵营在历史发展中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萨特激昂慷慨所立足的基石和支点就坍塌了,他所投入的激情都变得意义不大。”[14](P77)柳鸣九虽然是从宏观角度分析萨特政治活动的得失,但这句话对我们理解萨特意识形态叙事的得失,也不无启示。
标签:萨特论文; 马蒂厄论文; 自由之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电影叙事结构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