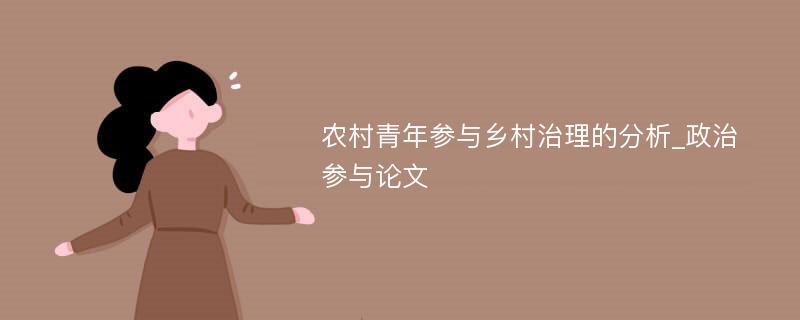
农村青年在村级治理中的参与状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级论文,状况论文,农村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4)06-0023-07
农村青年作为农村中文化水平较高、对外部情况比较熟悉、思想解放而有活力的群体 ,在农村中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社会的变迁,农村青年的参与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关 于农村青年的政治参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很不理想,与现实的农村政治生活还有 距离。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及二手资料,描述农村青年总体的政治参与状况,揭示影响 当代农村青年政治参与状况的因素。对中国农村青年的选择样本,年龄限定在18~35周 岁之间,根据经济发展的程度,地域分布在东、中、西部地区,选择浙江、山东、河北 、重庆、青海作为随机抽样的省(市)。本次调查于2003年7~8月间进行,收回有效样本 93份。由于经费、人力等方面的限制,抽样数目有限,但大体仍能反映出农村青年的政 治观念和政治参与行为的状况。关于农村青年的政治参与状况,主要通过测试被试者讨 论村干部和村选举等公共事务,考察登记成为选民、参与投票和竞选、拉票和助选、履 行公民责任的状况,观察农村青年的政治行为表现。
一、当代中国农村青年在村级治理中的参与状况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农村青年在村级治理中的参与状况有如下特点:
第一,参与形式的多样性。农村青年在村级治理中的参与既有直接的村委会选举,还 有讨论村庄政务、助选、接触村干部、上访、起诉等形式。在村民自治背景下,参与三 年一次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成为最主要的参与形式。由于法律的规定、行政的安排、政 治的动员以及村庄各种社会组织的介入,一般青年都会参与村庄的选举活动。但近年的 换届选举中,青年农民的消极态度也有抬头之势。正如许多青年所说的:“谁当干部还 不都是一样,都是为了自己捞取好处。”尤其是在一些村庄治理较差的地方,村干部的 腐败行为和管理混乱,使许多青年对换届选举失去了信心,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参与的 积极性。在村庄社区范围内,讨论村务也是一种重要的参与形式。在问及“您是否经常 和家人、同伴、朋友讨论村委会选举状况、现任村干部的品德和做法”时,11.96%的农 村青年选择了“经常”,41.3%选择“偶尔”,33.7%选择“极少”,13%选择“从未” 。一些比较活跃、积极的青年,或者积极竞选村委会职务,或者参与拉票助选活动。在 调查对象中,有7.6%的青年参与了为候选人做宣传、争取选票等方面的助选活动。当村 里做出了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直接侵害的决定时,49%的农村青年采取 “直接找村干部表达不满、要求撤销该决定”的方式,14%可能会采取“向上级领导反 映、上访”的形式,9.8%可能会采取“向媒体反映”的形式,4.35%可能会采取“到法 院起诉”的形式,9.8%会采取“在村内制造舆论、向村干部施加压力”的形式,还有13 %会采取任人宰割的消极态度。此外,对村庄事务的建议、关心也是重要的参与方式。 根据笔者的调查,在被访青年中,有31.5%的农村青年曾经就村内事务或决定向村干部 提出过建议,其中72%部分或完全得到采纳。
第二,参与内容的功利性。农村青年的参与大多是基于切身利益而进行的。相对来说 ,农村青年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关注,更甚于对政治利益的关注,关注经济活动中的民主 权利胜过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而对于和自身利益不太密切的公共事务,多持冷漠的态度 。在对农村青年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对于“村干部贪污腐败、侵害村民利益”的 行为,只有36.6%的人会以行动做出反应,如上访、举报、联合要求罢免村干部职务、 张贴大字报等,其他人则保持沉默。针对一项不公正的村内政策,由于并不是针对特定 个人,多数人也会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目:“假如村中的一项政 策和措施正在考虑中,而您认为这极不公正或有害,您会做些什么呢?”54%的青年不会 做出积极的行动反映。而对于村里侵害到自身利益的行为和决定,有超过77%的青年会 以接触、上访、媒体反映、诉讼等形式做出反应。这反映在农村个体经营的体制下,村 民有机联系的减少,原子化社会的现实,促使许多青年村民的自利意识增长。作为一个 理性的经济人,对于村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问题,农村青年自然具有“搭便车”的心 理,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
第三,自主性参与和被动性参与相互交织。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青年独立精神、利益意 识的萌生,刺激了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在村民自治体制下,人们主动地参与村委会换 届选举,已经成为主要的参与方式。根据一些学者对村民选举态度和选举程序的调查, 村民自愿投票的程度和村委会选举的民主程度已经大大提高[1](P220)。一些青年积极 参与竞选村庄职务。早在1992年底,湖南资兴市水口村团支部书记曹某和团支部组织委 员刘某,针对乡里内定村委会候选人的不民主做法,毛遂自荐,到处游说,争取群众, 竞争村委会职务,为广大农村青年树立了榜样[2]。在我们的调查中,近11%的农村青年 参与过村委会的竞选,还有7.6%的农村青年积极从事为候选人宣传、争取选票等助选活 动。
农村青年的自主性参与还表现在,为了捍卫和争取自身的权益,他们积极游说、接触 各级政府官员和媒体,进行上访。近年来农民上访告状的大量增加,反映了农村问题的 严重性,同时也是农民利益意识觉醒、自主性参与增加的明证。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一些农村青年的依赖性和被动性仍然十分严重。如问及“您投 票选举时是否与他人商量”时,27.2%选择“与家人商量后决定”,23.9%选择“听从大 多数人的意见”,还有15.2%选择“随便填写”。在问及农村青年参与选举的感受时, 约33.7%的被访者选择了“应付”。可见,农村青年在村庄选举中的从众心理和冷漠心 理仍很严重。
第四,合法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并存。制度化参与渠道的多少及其是否畅通,直接 影响到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在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及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为青年农民 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合法的途径。诸如选举、监督、罢免、上访、接触各级干部,成为农 村青年常规的参与渠道。但是,这些渠道又不是十分畅通的。选举中的违规行为很普遍 ,乡镇政府、现任村干部、宗族势力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就使得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受 到很大影响。部分农村青年参与冷漠,主要原因是:(1)“我只有一票,对选举结果没 有什么影响”(46%);(2)“即使我希望的人当选,他也不能真正起作用”(23%);(3)“ 选举与我没什么关系”(27%);(4)“不了解候选人”(4%)。很多农村青年感到自己在村 里讲话没有分量,没有通畅的意见表达渠道。如罢免村干部往往是极难成功的事情。在 一些农村,村民的政治冷漠又助长了乡村干部的腐败。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一些农民 便走上了非制度性的参与渠道,如张贴大字报、抗拒税费(甚至发展成与乡村干部的集 体暴力冲突)、越级上访等。[3]在这一过程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熟悉国家法律政策 、易于冲动的青年,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年人血气方刚、感情易于 冲动,较之中老年人,更容易采取激烈的方式进行参与。这是因为:“在孩提时代,自 我主张趋于压倒无私行为。经验还表明,我们在青少年中比在年长于他们的人当中更能 经常地发现反抗和不驯服的态度。用奥尔波特的话来说,随着个人的成熟,‘个人倾向 的侧重和强度都会渐趋减小,而尊重他人的情感则会不断增长和扩展’。”[4]实际上 ,正是制度性参与渠道的阻塞,才刺激了非制度性参与的增加。而这反过来又激化了农 村社会的冲突。
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政治参与状况,既有乐观的一面,也存在着诸多隐 忧。村民自治制度的引入,使更多的农村青年卷入到村庄公共事务中来,增加了参与村 级公共事务的渠道,部分农村青年的参与热情和强度也有所增加。但是,农村青年的政 治参与层次比较低,往往限于和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村庄范围。由于参与渠道不够畅通 而引起的群体上访行为,也主要是为了解决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从参与的效果 看也不太理想,往往劳而无功,偶尔在高层的行政干预下才能达到目的。极其高昂的参 与成本,也限制了农村青年的参与积极性。按照制度规定村民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尚 得依赖上级行政部门的干预才能解决,进一步破坏了制度的权威,强化了人们对权威的 依附性和“官本位”情结,这进而加剧了农村青年群体上访这种参与形式的发生。
二、影响农村青年政治参与状况的因素
第一,农村青年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影响。根据行为科学的研究,人类行为的发生 受到心理和意识的支配。农村青年的政治知识、政治功效感和政治意识,对其政治参与 有重要的影响。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青年的政治、法律知识明显提高,权利意识和 民主意识明显增强。如有58.1%的农村青年对事关农村政治经济生活的“村组法”比较 熟悉。而在1999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中,有56%的农村青年不知道“村组法” 的颁布。[5]有75.3%的农村青年知道村委会必须经过选举产生才合法。农村青年民主、 法治意识的提高,是自主性政治参与的观念基础。
然而,农村青年还具有浓重的权威意识和依附心理。在问及“村级管理的好坏主要靠 什么”时,有47.83%的被访者认为主要靠村干部的品德和能力,有35.87%的被访者认为 靠制度。可见,青年农民的“贤人”、“能人”情结很浓重。尽管如此,农村青年对村 干部的信任度却很低。在问及“村干部能否代表村民的利益和愿望”时,回答“完全能 够”者为0,回答“经常能够”者占26.9%,回答“很少能够”和“不能够”者高达73.1 2%。相关的调查资料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如曹卫秋等人对9个省的调查发现,“60%的人 认为‘乡村干部贪污腐化’,77.8%认为‘少数党团员损害了党团组织的形象’,41%的 认为基层党支部‘不按政策办事,还有少数违法’。”[6]对村干部的不信任感,影响 了农村青年对村级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却没有能够产生对制度的关注。
如果我们把农村青年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状况做一对照,就会发现具体的政治认知 、政治态度与政治实践存在一定的落差。尽管大多数农村青年对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持 肯定态度,但这些态度取向并没有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如71%的被访青年认为村委会应 “由村民选举产生”,67.74%认为村民大会应该具有村里重大事务的最终决定权,75.3 %的被访青年认为村里的事是大家的事。但是,针对村里的极不公正的政策和措施,却 有54%的被访青年不会做出积极的行动反映。农村青年的政治参与冷漠,与参与渠道的 狭窄、参与成本的高昂和参与效果的有限性密切相关。
第二,政治参与结构的限制。政治参与结构是指公民施加影响的各种机构、职位和程 序。在乡村层面,主要的参与结构包括村委会、党支部、乡镇人大、村民代表会议、妇 女组织、青年组织、乡村干部、乡村选举、各种关系网等方面。在村级权威组织中,村 支书一般享有最高的权威,村民选举只能影响村委会成员的当选。况且,在村庄选举的 各个环节,村支书可以施加各种限制。因而,村民选举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影 响。如有的村民说:“村里是书记说了算,选举是支部包办一切,换届实际上是假的。 ”“如果把所有村干部都让我们投票选举,我肯定去参加投票了。”[7]村民代表一般 由村干部指定,而且几乎不开会,也很难形成对村干部的制约。至于隶属于党支部的妇 联和青年团组织,往往处于瘫痪的地步,很难成为代表青年和妇女表达意愿的渠道。根 据一些学者的调查,40.7%的农村青年认为“基层党团组织瘫痪”,77.8%的农村青年认 为“少数党团员损害了党团组织的形象”[6]。此外,在许多村庄,除了换届选举会议 外,很少召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信息的封闭与控制妨碍了村民对村务的知情权 和监督权,加大了村干部与村民的心理距离,削弱了村民的参与欲望。可见,选举制度 的缺陷以及各种参与结构的问题,限制了青年在村级民主过程中参与和锻炼提高的机会 。
第三,农村青年社会经济地位状况的影响。青年是富有理想的群体,他们重视自我实 现,精力充沛,敢做敢为,渴望摆脱各种控制,获得独立的地位,具有较强的政治主体 意识和权利意识,因而具有明显的竞争意识。在农村,青年群体往往受过更多的教育, 或打工或经商或读书或参军,具有更多的外出经验,见多识广,具有改变个人处境和村 庄现实的抱负。
一些农村青年精英为了提高个人和家庭在村庄的声望和地位(当然也有不少青年是为了 捞取私利),为了对村庄的发展做点贡献,积极竞选村委会干部的职位。根据民政部的 有关统计资料,1998年前后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平均年龄约为37.84岁,农村青年日益成 为村干部队伍的主体[8]。许多农村青年步入村庄政治舞台,显然是青年地位提高的重 要标志。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村青年都具有这样的能力、愿望和机会。农村青年要进入村庄 政治精英队伍,既需要个人能力,更需要丰富的关系资源和强大的家族背景。在笔者的 调查中,只有约10%的青年参与过村委会成员的竞选。而绝大部分青年却因个人能力、 关系或者政治冷漠而没有参与村委会的竞选。如34%的被访青年认为“自己没有能力” ,24%认为“自己在乡镇没有后台”,11%认为“本家人不支持”,12%认为“村委会没 有什么权力”,还有18.7%认为自己年龄小、威望不高、不知道选举程序,因而不感兴 趣。如果我们把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合并,可见有半数以上的农村青年对参与竞选村干部 具有无力感。农村青年对于村干部行为和态度的影响能力,也呈现出大致类似的状况。 在问及“关于村中或个人的一些事情,您向村干部反映,您觉得您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 村干部的态度和做法”这一问题,6%表示“影响很大”,44%表示“有一点影响”,50% 表示“没有影响”。可见,多数农村青年的政治效能感很差。如果考虑到被访对象中, 党员占22.8%、民主党派占4.3%、共青团员占26%这样一个情况,可见整个农村青年群体 的政治无力感是多么严重,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对农村政治参与的冷漠态度。正是许多农 村青年对村庄公共事务和政治问题的无力感和淡漠态度,决定了其政治参与的消极性和 被动性。事实上,在乡村政治场域,动员型参与仍然是农村青年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
第四,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农村青年的政治参与深受农 村各种社会组织状况的影响。共青团本来是锻炼青年政治技巧、积累青年政治经验、动 员青年进行政治参与的理想场所和机制,但由于许多村庄团组织瘫痪,从来不组织青年 活动,也失去了组织青年、联系青年、动员青年的作用。这样,就很难适应农村青年对 科技文化知识、文娱活动以及互助的需要。同时,也失去了团组织作为凝聚农村青年群 体意识、培养青年领袖、表达青年群体利益的作用。由于凝聚青年利益的组织的缺失, 一些农村青年就通过各种媒介形成不同的团伙,其中不乏具有负面效应的非法组织,如 “赌友会”、偷盗团伙,甚至黑社会组织。党支部、村委会等村庄正式组织机构权威的 下降,刺激了宗族、教会等社会势力的兴起。在许多村庄,家长或族长基于对青年一代 的不放心,加强了对本家族青年的训导和影响。在一些宗教发展较快的地区,教会设立 了各种组织机构,加强对青年的影响。如设立“仁爱会”负责教会与青年教民的联系, 组织其学习教义。教会还设立各种机构,加强教民之间的沟通,如组建管乐队,学练宗 教乐曲等,也举办公益事业,具有教化青年的功能。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组 织,教会对农村青年的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组织动员功能,同时也发挥了与贪污腐败的 村干部进行斗争的作用。[1](P98-101)在笔者所调查的9名信教青年中,大多数对新闻 时事和村内公共事务比较感兴趣,8名知道村委会必须经过选举才合法,但对参与选举 比较冷漠。他们全都没有为候选人做过宣传、拉票等助选活动,也没有参与过村干部的 竞选。然而,信教青年大多具有公共责任感和维权意识。如对于村中极不公正或有害的 措施,67%的信教青年会以上访、直接抗议等形式施加影响,而所有被访青年(包括信教 青年)这一比例仅有46%。对于村干部贪污公款、进行腐败的反应,56%的信教青年会以 举报、上访等方式进行反应,而所有被访青年中这一比例仅为36.56%。对于村里做出的 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部分人利益直接侵害的决定,100%的信教青年都会以直接找村干部要 求撤销、举报或向媒体反映等形式做出行动反应,而所有被访青年(包括信教青年)这一 比例仅为77%,尚有23%的政治冷漠者。可见,教会组织对于农村青年的政治意识和政治 参与行为确实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五,人口流动与农村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大量的农村剩 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作为农民工主体成分的农村青年,不仅为农村带来了丰富的社会经 济信息和经济发展的资本,也对农村青年政治观念的民主化、法制化以及政治参与水平 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许多农村尤其是比较贫困的农村,由于大量农村 青年常年外出务工、经商,逐渐淡化了他们与本村的利益关系,也使得他们对本村事务 的热情下降。这不仅使农村的“精英”大量流失,村干部队伍质量下降,而且不利于农 村的政治发展。
2000年2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致国务院领导人的信中谈到,自当 年开春后的20多天中,全乡4万人(其中1.8万劳力)中的2.5万人(其中1.5万劳力)弃田撂 荒奔赴各个城市打工。据调查,外出务工人员多是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甚至还 有村委会干部。18~45岁的青壮年占92%以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0.2%。有一个乡 自1989年后的10年间,每年毕业的高中生300多人,除10%升入大中专外,其余几乎都外 出打工;某村统计,每年初中毕业生100人,除五六个升入高中外,其余全部外出打工 。大量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妇女外流,村里留下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1](P204-206 )大量农村青年为忙于生计而外出务工经商,削弱了与村庄的利益、信息甚至情感的联 系,因而对村庄政治失去了兴趣。这样,不仅村干部候选人的质量受到影响,而且由于 选举信息、选举成本的极其高昂,绝大多数外出青年或者放弃选择“当家人”的权利, 或者采取不一定反映其真实意愿的委托投票。至于对村干部日常工作的监督和村庄公共 事务的参与,更是付诸阙如。农村青年大量外出和村级组织的瘫痪,也严重影响了适龄 青年的计划生育管理、税费收缴和村庄公共事业的兴办,使村级治理难以走上“善治” 。
另一方面,青年村干部虽然有魄力、敢闯敢干,但浪费、贪污腐败的风险也很高。近 年来,由于农村经济的持续低迷,农民追求稳定的心理开始增长,因而对青年村干部的 信心也在下降。根据吴绍田对山东省莱西市牛溪埠镇的选举调查发现,1998年选举与19 90年选举比,35岁以下的村干部由33.04%下降为21.67%,减少11.37%,高中以上文化程 度的比例由38.7%下降为30%,减少了8.7%;但35~45岁的却由41.3%增加为45.56%,初 中文化程度的由41.7%增加为68.33%,小学文化程度由20%下降为1.67%。[9]农村青年较 低的政治成熟度和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冷漠态度,都限制了他们在村级治理中的地位和作 用。
可见,影响农村青年政治参与的因素,不仅有青年个体自身的原因,还与宏观的农村 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有关。提高农村青年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水平,是一个综合性 的系统工程。
三、结论
近年来,许多中外学者和官员高度关注和评价中国农村的民主选举。他们只是看到了 广大中国农村热闹的选举场面和远比西方发达民主国家高得多的投票率,但对选举背后 村民的诸多心理和行为因素缺乏深刻的了解。投票率经常被视为民主制度内公民投入的 程度,但选举次数、选举涉及的层次和范围、日常公共事务的参与、对干部的监督和制 约等方面,都影响了民主的程度。
本文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青年基于自身利益而萌发了初步的 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但由于传统文化和自身成熟程度的限制,还存在着明显的依附心 理和权威崇拜意识,对公共事务缺乏足够的热情,在政治上有无力感,这些都限制了其 政治参与的水平。由于参与机制的诸多问题,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人口流动等原因, 进一步影响了农村青年对村级治理的参与。从总体上看,由于农村青年作为参与主体在 从业领域、经济条件、社会经历、文化水平及涉入组织的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其政治参 与表现出多样性和层次性的特征,既有政治冷漠者,也有被动的参与者,还有积极的参 与者;既有按常规渠道进行的参与,也有通过越级上访、抗税、对抗等非制度性渠道进 行的参与。从参与内容上看,农村青年的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直接性、功利性的特征, 他们主要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务,而且对经济事务的关注明显高于对政治 性事务的关注,对于公共事务缺乏足够的热情。在参与层次上,农村青年主要关注村庄 范围的具体利益问题,而对事关农民利益的宏观政策等抽象性利益,缺乏施加影响的主 动性。只是在难以承受税费负担的情况下,会采取消极的对抗形式。即使向各级国家机 关的上访,也只是谋求借助上级官员的行政权力维护自己的具体利益。这就是说,农村 青年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在乡村层次。尽管越来越多的事关农民利益的政策出自中央和地 方国家机关,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政策的执行问题,而非国家政策的制定问题。“ 中央和国家的政策是好的,只是基层干部念歪了经”。他们对于国家政策和高层官员具 有较高的信任度,而只是不信任具体办事的基层干部。
可以说,农村青年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行为方面具有很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近年 来,农村青年的法律意识虽有所提高,但其依附性心理和权威崇拜意识仍很严重,都表 现出浓重的“清官”情结,这对于农村治理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具有很大的消极性影响。 要促进中国农村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加强对农村青年的公民教育、拓宽农村青年政 治参与的渠道,创造有利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经济环境。
收稿日期:2004-0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