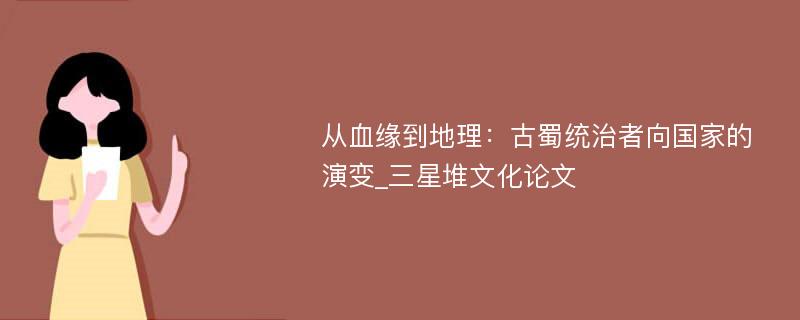
从血缘到地缘:古蜀酋邦向国家的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血缘论文,国家论文,古蜀酋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6)02-0005-05
《论语·先进》记载:“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1] 认为:此语作何解,汉宋诂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今俗用之以表不开化之人,此为甚后起之义。对照《诗经》、《左传》、《孟子》,可知野人指农夫,即殷人,君子指统治阶级,即周人。周灭殷,把一些殷人氏族分封给周贵族,殷人居野,故称野人,周人居城,故称君子。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泛指文明。野人先进入文明社会,而周人后进入文明社会。
傅斯年所做的阐释,基本符合商周时代的历史实际,故先秦史学者大多引以为是。
所谓君子与野人之分,实际上就是先秦史籍中多处提到的国、野之分,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国人是统治者族群,野人是被统治者族群。
国、野之分产生形成于殷、周革命和西周分封制,政治上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2],经济上是“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3],文化上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4]。王城和诸侯城均以族群划域,带有浓厚的血缘政治组织色彩,这种社会形态是与商、周时代村社组织与氏族组织并存的二重性相符合的。完全以地缘来划分国民,这种情形在夏、商、周三代还不存在,历史学家大多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之所在。
亨利·梅因(H.Maine)早就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说过,最早出现的国家可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以地缘为基础是在最早的国家形成以后不久出现的[5]。
亨利·梅因的论断是建立在对西方社会的材料分析基础之上所进行的归纳判断,确实具有相当说服力;但中国夏、商、周三代的情况与西方社会不尽相同,血缘关系及其组织和原则不仅在先秦夏、商、周三代尚不成熟的国家里没有丝毫消融,而且在秦、汉以后越来越成熟的国家里还继续长久地与地缘组织同时并存而且交织在一起,这就是宗族组织和农村公社的二重性表现之所在。
那么,在古蜀地区,是否同样存在着如同或类似于中原地区那样的国、野之分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提出来加以探讨的问题。
我们首先讨论古蜀史上所谓三代蜀王时期的社会组织的性质。
从历史文献方面看,根据《蜀王本纪》的记载,古蜀王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每一代都由名号相同的若干位王接续而成,也就是用一个固定不变的王名来表示一代。正如蒙文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三代蜀王均为“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6]。这种事例在中国古史尤其中国民族史上颇不鲜见,就是用共名作为私名。
进一步分析,这种所谓“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的怪诞现象,同古文献所记载的“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7] 的现象完全一致,它们所表达的,其实并不是君长寿命有数百岁之长,而是指君长这个角色及其地位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在每一代的政治组织中,都已形成了固定的权力机构即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已经达到了相当稳定化的程度,以致前后相继维持达数百年之久。这个机构的首领,即是所谓蜀王,亦即文献上所说的“君长”。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三代蜀王中的每一代,虽然是各自政治组织中的“王”、“君长”,但这里所说的“蜀王”和“君长”,仅仅是指其角色而言,并不是指王位一系相传的世袭制度。上古时代有所谓共名和私名之分,不论蚕丛、柏濩还是鱼凫,三个名称首先分别是三个族系的名称,所以一些文献在提到这三个族系时,分别称为蚕丛氏、柏濩氏和鱼凫氏,这就是所谓共名,即其族群的名称,其次才是各族内部成员的私名,它们则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君长的若干位蜀王,原本都有私名,但一旦出任君长角色后,就用共名取代了私名,每一位君长都是如此,世代相承同一共名。于是在古文献的记载中,我们所看到的三代蜀王,每一代都是一个单一的名称,因而造成“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那样的错觉,给人以实行王位世袭制度的错误印象。
其实,中国古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如黄帝、颛顼等,其年世之所以十分久长,就是因为同一族群酋长的私名都取用其族名即共名的缘故,所以当族群分化或扩张的时候,随着族群的流布,其族群的名称也同时传到四面八方,以致造成族群酋长的世系如此久长的错觉。
从古蜀史上“三代蜀王”均以一王之名表示一代,即以共名作为私名的情况看,三代均各别是一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单位,相互之间没有组织上或族群上的继承传递关系,它们都是自成系统,各自传承下来的。
其次,我们探讨三代蜀王时期的政治组织的性质。
从历史文献分析,三代蜀王时期已是原始社会的尾声。《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所称“王”,并不是君主时代的王,而是犹如“氐王”、“白虎夷王”一类族类的酋豪或首领,其性质如同鱼豢《魏略·西戎传》所记载的“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8],属于前国家社会的酋邦之长①。这种现象表明,蜀王蚕丛已经拥有超越部众和组织的权力,作石棺石椁而国人从之,又意味着蚕丛不但拥有对部众实施政治权力的力量,而且还拥有实施经济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力量。显然,这已经不是纯粹血缘组织那种平等社会的特征,而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酋邦组织的特征。蚕丛不但握有号令部众的权力,而且还在相当深广的程度和范围内表现自身的意志,王者的意志不再取决于全体部众的意志,无须再经全民会议或其代表批准通过,这正是酋邦组织中拥有决策权力的首领的特征。可以看出,所谓蚕丛“始称王”的实质,是酋邦的诞生。
鱼凫王的情形同样如此。《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直接反映了鱼凫王对部众所拥有的宗教权力,而宗教权力是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所赋予的。这同样意味着鱼凫王拥有超越部众之上的权力,表明鱼凫王时期已经突破了血缘社会的平等的组织原则,达到了酋邦政治组织的发展水平。而鱼凫所称的“王”,实质上也是酋邦组织中拥有决策权力的首领,即文献记载中所谓的“君长”。
再次,我们探讨三代蜀王的权力性质。
三代蜀王既是族群各别而分别达到了酋邦阶段的首脑,那么他们相互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三代蜀王之间是一种在有限空间内同时并存,为争夺成都平原这块膏腴之地而角逐争雄的酋邦关系,他们是文献和考古所见古蜀地区最早的酋邦社会[9]。
我们曾经指出,三代蜀王中的蚕丛和鱼凫分别是从川西高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南迁进入成都平原的[10];而柏濩的来源,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应是成都平原西北部地区今都江堰市(原四川灌县)“灌口”、“观坂”一带的土著[11],那里正是成都平原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这已经由近年以来成都平原的若干考古新发现所充分证实。三代蜀王虽然初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不一,但他们的相继南迁却使他们在成都平原先后相遇,终致因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而发生大规模的酋邦征服战争。
蚕丛氏从岷江上游南迁成都平原,其迁徙路线是沿岷江河谷而下,经灌口从成都平原西北角进入成都平原的。在岷江南入成都平原之地,古有蚕崖关、蚕崖市、蚕崖石等地名[12],正是蚕丛氏经由岷江河谷南出灌口进入成都平原的证据。蚕丛氏南出灌口,正与居息在这里的柏濩相遇,于是发生争夺土地和资源的战争。
鱼凫南下进入成都平原,也是经由岷江河谷南出灌口的,《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都记有“鱼凫王田于湔山”,湔山即今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之间的茶坪山,表明了鱼凫经湔山南下,走的是蚕丛氏南下的同一条路线。于是,在鱼凫王与蚕丛之间,引发了另一场酋邦大战。
三代之间酋邦战争的史迹,可以从文献中大致考见。《蜀王本纪》记载:“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意思是说,在征服战争中失败的酋邦,其一部分民众成为征服者酋邦的臣民,一部分则随其首领逃亡。《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说:“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反映的就是蚕丛氏酋邦在战争中失败后,其中一部分逃至姚(今云南姚安)、嶲(今四川凉山州西昌市)等处的史迹。此即“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的实质。
三星堆文化第2期始出现鱼凫王的标记——鸟头勺柄,同时此期也不乏蚕丛氏文化的石器、陶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1号祭祀坑所出青铜雕像中,有一跪坐人物像(K1∶293),发式似扁高髻,下身着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当是蚕丛氏后裔形象的塑造。据民族学调查,岷江上游戈基人被称为有尾人[13],实际上是“衣服制裁,皆有尾形”[14] 中的一种,即着犊鼻裤,因其一端下垂,似尾,故名。1号坑内所瘗埋的一自然梯形石块,也与理县佳山戈基人石棺葬中瘗埋自然石块一致[15]。而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代表文明高度发展的部分,即体现古蜀王国政权核心的物质文化遗存,却不能反映蚕丛氏的文化。这就意味着,蚕丛氏遗民中的绝大部分,已成为鱼凫王所建早期蜀王国中的治民。而鱼凫王作为早蜀王国的创建者,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第一代君主,也由此得到了证明。
征服战争扩大了征服者酋邦的王权,为维护王权并保证对被征服者的土地、人民进行统治,王权又得到进一步上升,转化为君权,并建立起相应的统治机器。此时,在这个王权的统治范围内,既有战胜者鱼凫王的族群,又有战败者蚕丛氏和柏濩氏的前朝遗民,于是形成了一个血缘关系多元化的社会,和在这个血缘关系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框架上所建立的统一的政治组织。这个统一的政治组织,就是古蜀王国。
最后,我们探讨古蜀王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政体演进水平。
鱼凫王朝的建立,使古蜀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原则同时发生了剧烈变化,从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演进为以血缘和地缘二重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由于古蜀王国内部血缘关系多元化局面的形成,鱼凫王朝就不再是一个由单一血缘组织所构成的社会单位,而演化为一个由不同血缘组织所构成的统一的政治单位,即以鱼凫氏为统治者集团的政治共同体或国家,这就是古蜀王国。
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这几段史料里,既有比较具体的历史事件,又包含着历史演化的比较明确的过程,十分具有典型性,应当引起我们的格外重视。
然而,对于三代蜀王之际政权的变换,化民的去留,以及鱼凫王朝政治社会中血缘与地缘结构的构成形态等,是否形成了殷、周革命以后所具有的那一类“先进”与“后进”、“国人”与“野人”之分的社会政治形态呢?对此,不论《蜀王本纪》或《华阳国志》还是其他史籍,都没有任何记载。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必须求诸考古资料。
大家知道,三星堆文化是以鱼凫氏为主体所创造的文化,三星堆古城是鱼凫王所缔造的古蜀王国的都城。因此,我们考察鱼凫王朝是否存在着如像中原那样的“国”、“野”之分,就得以三星堆古城为考察对象,这是不言而喻的。
考察的方法是,通过对三星堆古城城内外物质文化遗迹、遗存和遗物的比较,来分析其间的异同。这不外会出现下面几种可能性情况:
第一,如果城内外位于三星堆遗址二期(三星堆文化一期)同一文化层位的相同功能的遗存或遗物有别,那么就可以证明城内外居民的族群有别;
第二,如果城内下一文化层(三星堆遗址一期)与城外上一文化层(三星堆遗址二期,三星堆文化一期)相同或相近,则可以表明原来城内的居民(三星堆遗址一期)现已移居城外,他们应是“先进于礼乐者”,是被现居于城内的“后进于礼乐者”(三星堆遗址二期,三星堆文化一期)所强制性地迁居城外的。前者是蚕丛氏和柏濩氏等前朝遗民,后者则是当政者鱼凫王的部民;
第三,如果城内外同时分布有位于三星堆遗址二期(三星堆文化一期)同一文化层的相同遗迹、遗存或遗物,那么可以考虑统治者的族群与被统治者的族群之间是否具有交错分布即错居的关系,或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关系,这需要仔细分析材料才能加以断定。
由于目前有关三星堆遗址的全面材料还未能公开发布,所以我们的比较分析尚不能有效展开,这里仅仅能够论其大概。
三星堆文化是在成都平原宝墩文化(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剧烈变化而形成的。三星堆遗址二期(三星堆文化一期)形成了巨大的古城,我们已经讨论过它是一座早期城市,是古蜀王国的中心城市,即古蜀王都[16]。从城内遗存看,在三星堆遗址二期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一期之物,而城外遗存中也存在着大量的一期之物。这种情形意味着,三星堆文化时期并没有形成中原殷、周革命所形成的“国”、“野”之别,即“国人”城居、“野人”野居那样一种社会组织按族群的尊卑贵贱进行划分的空间分布和组织形态。换句话说,三星堆文化主要不是以“国”、“野”界线和血缘组织为单位来划分其国民的居住界域的。在三星堆古城内外,既居住有二期的主人,也居住有一期的主人。这就意味着,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国形成了主要以地缘来划分其国民的政治组织。
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王国以地缘为主的情形,既与殷、周之际中原由于剧烈的政治变化所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空间组织形态有所不同,也与夏代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夏代,根据《左传·定公元年》的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薛,任姓,东夷之国,《世本》及其他诸书并谓其先祖奚仲作车②,谯周《古史考》谓禹时奚仲驾车。奚仲为薛国的君长,与夏不同族,但他既然是夏王朝的“车正”,就表明薛国是夏王朝统一政治单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夏王朝分层的政治体系中的一个次级层次。而这种政治上的分层,是以族群为单位作为划分基础的。奚仲由自己的族群入为夏王朝的王官,清楚地表明两者不仅族体界域有别,而且政治地位也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夏、商、周三代不同血缘组织与统一政治单位的关系可以从平面和垂直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平面结构分析,三代的空间组织形态都是以族群来划分领地界域,即所谓聚族而居;从垂直结构分析,三代的政治统属关系都是以各个族群在统一政治单位即中央王朝中的尊卑贵贱地位来划分政治层级的。平面和垂直两种结构,使我们能够更加透彻地认识三代国家血缘组织与政治组织的结构关系和政体性质。
根据亨利·梅因、亨利·摩尔根、恩格斯、莫顿·弗雷德(M·H·Fried)等的观点[17],国家的最主要标志之一是以地缘而不是以血缘划分其国民。据此来看,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的政治组织必为国家无疑。
当然,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国还是一个早期的神权国家,它的血缘组织形式及其某些原则仍然长久地保存着,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倘若仅仅根据它的神权政体形式和血缘组织形式就匆忙地否认其国家与文明性质,那将是极不科学的。关于这个问题以及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国的常设武装力量等有关国家与文明形成的问题,将另文讨论③。
注释:
①殷卜辞中的“王”,林沄先生《说王》一文认为像斧钺之形。这种看法还可以再研究。有的学者用此分析史前考古现象,以为某些地区的史前大墓是“王陵”,是阶级和国家社会的产物。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②例如,《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君守》、《文选·演连珠》注引《尸子》、《淮南子·修务》等,均谓奚仲作车。
③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从三星堆文化看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