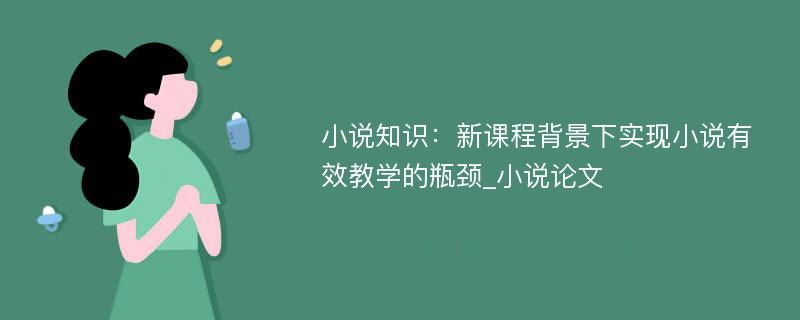
小说知识:新课程背景下小说有效教学实现的瓶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新课程论文,瓶颈论文,知识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初开始全面实施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至今已走过近10个年头了。但是,综观目前中学语文教学的整体状况,仍可说是“少慢差费”涛声依旧,小说教学也不例外。从与河南、广西、辽宁3个省区18所中学100多名中学生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中学生读小说,仍停留在道德判断的层面上,或是仅满足于从小说中得到一个故事,而很少能够进入到小说鉴赏的层面来体会小说的语感魅力和言语滋味。这种状况,充分显示出目前小说教学还非常缺乏有效性。
新课改之前,小说教学缺乏有效性,是因为我们的整个文学教育感兴趣的就是作品的思想性,作品的文学性成了传递思想性的工具,是外在的、附加的。教师在分析完主题思想之后,才会附加地分析一下它的艺术特征。但很不幸,这些分析,用薛毅的话来说,“那是陈年老调,千人一面的东西,什么地方都用得上,叫做语言流畅、结构严谨、刻画细腻、以情动人,还有夹叙夹议,比喻啦,排比啦,象征啦……”[1]这种做法,事实上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文学教育,小说教学当然也是低效甚至无效的。
新课改之后,文学教育逐渐走上正轨。如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准》就明确规定: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这也就是说,新课改背景下的小说教学可以堂堂正正地教学生如何从审美角度来鉴赏小说了。
郝德永教授指出:“从形式上看,课程表现为一种知识体系,课程研制的核心内容也就主要表现为对知识的选择与组织。因而,知识是课程的最直接的一级制约因素,而其他因素诸如社会或学生是通过赋予知识以某种价值取向及方法的方式来影响、制约课程的,是以知识为中介的二级制约因素,抛脱了知识,课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小说教学中,如何从审美角度鉴赏小说的知识,应该是极为重要的课程内容。正是这样的课程内容,在深层次上制约着小说教学的有效性。学生在课堂上掌握了这样的知识,就可以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小说鉴赏的基本图式,以指导他们对小说进行有效解读;反之,解读则只能依赖于每个学生对小说的整体感知,悟性好的学生会在整体感知过程中鉴赏到小说的美,而悟性较差的学生则会虽经艰难困苦而无所收获。
一方面是小说鉴赏的知识如此重要;另一方面,令人遗憾的是,从我们对3个省区18所中学30多节课的小说课堂教学的调查结果来看,语文课程好像并未与时俱进,没有及时吸纳足够的小说知识来支撑小说教学在新课改中的转型。正如王荣生教授所言:“小说,除了被拧干了的‘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概念,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知识可教了。”[3]不少教师在教小说时,正是靠这三个“被拧干了的”概念维持着教学的运转。这样,小说教学改革也就只能停留在理念层面上,技术层面上工具性知识的缺失,使得教学无法引领学生登堂入室,去领略小说的艺术奥妙,他们只好以道德判断解读小说,或仅满足于了解小说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因此,目前小说教学面临着的一个急迫的、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对学校语文知识中的小说知识进行除故纳新,将其中用处不大、肤浅笼统甚至是错误的内容及时剔除出去,将学术界相关的新鲜的研究成果及时吸纳进来。我们试从六个方面来展开这个问题。
一、小说人物方面的知识
这方面知识的科学性可能最需加以检视。如某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教学生读小说,曾说“小说还只需要说出主要人物是好是坏”。[4]这样的人物分析方法,反映出相当多的教师头脑中的人物形象还都是扁平人物,而缺乏圆形人物的概念,这导致不少教师对人物形象的分析经常流于肤浅化或片面化。如对都德《最后一课》中的韩麦尔先生这个人物形象,在我们的调查中,几乎没有一个教师能够将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小人物身上很明显的缺点(如教学方法陈旧、不善于班级管理、对学生的学习有时流于放任)指出来,更少有教师能够将都德为什么会把韩麦尔先生塑造成一个圆形人物这一点给学生讲清楚。其实,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都是圆形人物,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主要是一种审美价值,而非道德价值,是不适宜用“好”或“坏”这样的标准来考量的。
另外,小说教学中塑造人物形象的四种手段(外貌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和心理描写)的相关知识,错误的内容固然不多,但问题是太笼统了(太笼统的知识必然是缺乏实用性的),需要大力充实,将其精细化。
如关于心理描写,我们可以适当引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分析人物的心理结构。通常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心理结构中属于超我的显意识是凸显的,而属于本我的潜意识则处于休眠状态。小说家则经常在小说中将人物的潜意识揭露出来,以满足读者与生俱来的窥探欲。《水浒传》中林冲起初的温顺守法,体现出的是他的表层心理结构;后来的暴怒和决然反抗则体现出他深层的心理结构。在分析人物形象时,我们绝对不能通过林冲的前后表现,简单地说他的性格变了,这是不科学的。同样,对于《项链》中女主人公玛蒂尔德一开始爱慕虚荣和享乐,在丢项链后却能够吃苦耐劳、勇于承担责任的前后不同的表现,我们也不可轻言她的性格变了。另外,在分析人物的心理描写时,要指导学生抓住人物情感逻辑的起点(如分析茅盾《春蚕》中老通宝的形象),关注人物情感逻辑对理性逻辑的超越(如分析孙犁《芦花荡》中老头子的形象)。掌握作家运用的这些艺术手段,对学生深入体验人物形象是非常有利的。
人物描写中外貌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和心理描写四者的关系也需要我们认识清楚。在小说中,这四者有时统一,有时则错位。孙绍振教授认为:“人物语言、外部行为和内心活动,不一致时比一致时更有利于揭开人物情感深层结构的奥秘。”[5]如分析《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在和卡列宁一起观看伏隆斯基赛马时安娜的内心情感,这一理论是很有帮助的。
二、小说情节方面的知识
在分析小说情节时,由于经常混淆“故事”和“情节”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及不辨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差异,有不少教师总是用“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模式来套每一篇小说。其实,“故事”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所有事件,而“情节”则是指对这些素材进行的艺术处理或在形式上的加工,尤指在时间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故事更加生活化,情节则更加艺术化。传统小说喜欢讲故事,以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故事吸引人;现代小说却并不总是靠此取胜,相对而言更重情节,对传统的讲故事的模式力求加以突破。如鲁迅的小说《故乡》,为了突出“变化”,在情节上,只写了“我”同闰土交往的开头和结尾,并无发展和高潮;莫泊桑的《项链》,为了给读者留出一些空白,营造出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只设有“开端——发展——高潮”,而没有结局。但我们观察到的能够注意到这一点的课堂教学实例显然太少。
关于情节,还需注意的是:以往的小说家试着从生活陌生、混乱的材料中抽出一根清晰、理性的线索来。从他们的视野来看,理性可以把握的动机产生行动,这一行动又引出另一种行动。所谓经历就是一系列行动因果关系清晰的链接。实际上,这种普通的理性因果很难表现出人物的特殊情感。所以,小说要构成动人的情节,必须要求有不同于理性因果律的情感因果。对此,我们要学会深入分析。孙犁小说《芦花荡》中老头子的形象之所以生动有趣,和作家在普通的理性因果之外,发现了属于这个老人独有的情感因果有密切关系。这个老人精心设计圈套报复小鬼子,动机并非完全出于理性,而是要维护他过分的自尊;行动也非完全出于理性,而是一种冒险行为。
三、小说环境方面的知识
小说的教学,一般认为: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事实上,这样的分类虽然没有什么不对,但在教学上并无多大价值。将小说描写的环境分为第一环境和第二环境,则显示出了非凡的教学价值。所谓第一环境,就是人物生存的现实的、平凡的生活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情感结构非常稳定、波澜不惊,人物表现出来的是普通的、表层的情感结构。但是,读者读小说,是强烈地希望窥测到人物复杂的深层情感结构的。这时,就需要小说家将人物打入超越生活常轨的第二环境,以引起人物内心情感结构的变动,从而使人物表现出丰富的、深刻的深层情感,以达到揭示人物心灵奥秘的目的。按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就是要借此展现人的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小说具有游戏性质,它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范进中举》中胡屠户、范进的性格,《项链》中玛蒂尔德的性格,《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及其家人的性格,正是这样被揭示出来的,
另外,环境描写的作用也应予以反思。一般认为描写社会环境,可以交代时间背景、社会习俗、思想观念和人际关系;描写自然环境,是为了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表达人物的心情,渲染气氛。这些看法固然有道理,但随着现代小说越来越多地走进语文课堂,它们也急需得到修正和补充。现代小说中,不少作品具有诗化特色(如契诃夫的《草原》、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张承志的《黑骏马》)。徐岱教授认为:“在这些小说中,景物已经不仅是背景,已经不再是表现人物的附属之物,它们本身已经得到强调,获得了一种象征意蕴,事实上成了一位‘抒情主人公’,直接抒发着作者对人生的种种微妙感受,从而加强了小说的美的特质。”[6]如《老人与海》中神奇瑰丽的大海的形象本身,就给了读者无尽的悄然无声的冲击。
四、小说主题方面的知识
很多课堂仍喜欢用一句话来概括小说的主题思想,而不少接受了这样教育的中学生直到上了大学依然喜欢这样来读小说。北大一位著名教授曾举例说:他所接触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拿起小说,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老师,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什么”。这位教授认为,捧起一本小说,不是用自己的心去触摸它、感受它,而是习惯性地执意去“概括”,往往还是套用某种现成的公式去概括主题,那么这种人已经与文学无缘了。认为小说的主题可以用一句话、按某种公式概括出来,也是一种流行的错误认识。
米兰·昆德拉反复强调:“在小说的领地,人并不确证。这是一个游戏与假设的领地,所以小说中的思考从本质上来看是探询性的、假设性的。”“小说就是讽刺的艺术,它的‘真理’是隐藏起来的,不说出来的,而且不可以说出来的。”[7]这其实是告诉我们,小说教学中,正确的做法是:首先要指导学生以整体感知方式个体式地体验小说说了什么,而非对此作一个明确的规定。例如,我们不能说《药》的主题不是别的,就是怀念革命烈士,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脱离群众的错误,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更不能下定论说玛蒂尔德的虚荣心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里。从作品的只言片语出发胡乱加以阐释,贴上标签,都是不科学的。
五、小说细节方面的知识
在当代小说中,特别是当代短篇小说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是不可缺少的。现代短篇小说艺术的发展已经使短篇小说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整个文学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个细节都以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姿态出现。它对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的关系和情感事关重要,也给小说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使学生从阅读中获得无比的快感。小说评论界对此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在小说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到师生对细节描写的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小说教学中师生对细节描写作用认识的不足。
另外一种情形则是对细节描写的过分阐释,试图从每处细节中都挖掘出一些微言大义。但实际上,很多小说(典型的如李准的《铁木前传》)中的不少细节描写只是为了尊重生活自身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表现自然的生活图景,营造出一种浓郁的生活情趣,并非有什么思想意蕴在里头。
六、小说叙事方面的知识
从本质上看,小说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小说叙事学方面的知识,应该说也是急需“纳新”的知识。学术界近些年来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对指导读者鉴赏作品有着极高的价值,然而它们却很少进入到学校语文知识体系中去。语文教师有责任从中选择一部分作为小说教学的课程内容。
如叙事时间理论中关于时序、时距、频率方面的知识。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祥林嫂一次次地向他人毫无变化地重复她儿子阿毛的故事的行为,就可以用叙事频率中的“重复叙事”理论来解读在现代小说中,重复叙事常用来表现人物精神上的某种困扰。
又如叙事视角方面的知识。我们看到,课堂教学中不少教师将叙事视角和叙事人称两者混为一谈,这显然不科学。事实上,我们要给学生讲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让他们知道第一人称叙事有经验自我视角和叙述自我视角的不同,又有目击者视角和主人公视角的差异;第三人称叙事中全知视角、戏剧式视角和人物有限视角三者功能各异;叙事视角之间可灵活转换,但是不可越界。诸如此类的知识对学生解读作品应该是很有好处的。如孙犁的《芦花荡》,小说一开始用全知视角讲故事,但到最后讲老头子复仇这一段,全知叙事者却佯装不知情,转而用戏剧式视角来讲故事,从而制造了一种悬念,使得故事扣人心弦,饶有趣味。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以第一人称目击者视角叙事,这个目击者是一个有点“傻”、对孔乙己有点瞧不起、在酒店里地位不高但又可以凭工作之便旁观到很多东西的小伙计。正是这个精心选择的视角使得作品产生了一种不动声色、冷峻批判的效果。但有的课堂教学对此理论不甚了了,只会跟着教参肤浅地说“这样可以使故事更可信”。
另外,对叙事中小说人物话语的不同表达形式及功能的研究,为我们深层次地体验小说又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如申丹教授发现:“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相比,前者有一种响亮的音响效果,后者的好处是具有直接性、生动性和可混合性,可以使作品表达更加流畅,能够使作者自由地表现人物话语的内涵、风格和语气。”[8]这对我们分析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如分析《阿Q正传》中描写阿Q躺在土谷祠里睡前的一段心理活动),从而领略小说艺术的奥妙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性支撑。
我认为,在新课程理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只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做好小说知识的除故纳新工作,打破制约小说有效教学实现的瓶颈,小说教学就能够摆脱“少慢差费”,走上“多快好省”的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