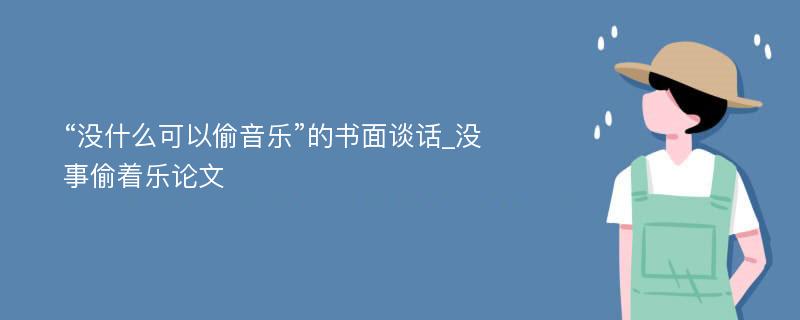
《没事偷着乐》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偷着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平民话语与表述真实
张建珍
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被称之为近年来少见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代表作品。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实际上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表述和提炼。在此,真实性非常重要,而表述本身则更为重要。它是叙事者对生活的一种关注和投射,它表明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这正是现实的特点。而导演杨亚洲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没事偷着乐》时,则运用影视语言的修辞手段,将这种人文立场的表述推向了极致。
《没事偷着乐》以张大民为中心,讲述了贫嘴张大民一家人的生活。问题的焦点是房子,即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因此影片阐述的是平民的生存空间和生存境遇的主题——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象喻性主题。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和不易,生活对他们的不平与不公,他们对生活的执著与希望,苦尽甘来的幸福,他们的欢聚离愁、内心情感等等,都是这类题材直接的表现内容,也是本片直接的表现内容。影片中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在于,由于贫穷导致的私人空间被侵占,私人生活被干预,因此人物的欲望诉求就是努力在公众空间中寻找出一片自己的私人空间,一个独立的生存之所。这在影片中表现为张大民长有大树的小屋、二民的出走、三民与邻居对男女共用厕所的争夺及床第欢娱对他人的干扰、四民那张不许别人坐的床、五民希望大学毕业后到内蒙放马新疆种树的梦想。于是,影片矛盾冲突的解决也就在于对这一欲求的满足。影片最后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它是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背着老人爬山的张大民的背影,整个画面色调明亮,阳光普照,这一象喻性的画面传达出的是“生活虽然充满苦难和沉重,但前方仍是一片美好光明”的朴素道理;它是登高远眺祖国山河时摆脱局促环境的开阔感和苦尽甘来的满足感;它是扶老背幼走在通往远方铁路上的一个核心家庭,前方是雾霭中如仙境般高耸的楼房。我们姑且不论这种梦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但它符合公众的梦想,并给我们以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当我们对张大民的生存状况有了深入的体察之后,这一结局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期望。在此,国家、集体所能给予个人的满足感和归属感成为人物的内心欲望,而不是一种被动的强加。
有关平民话语的言说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现实主义的典型性原则下对平民话语的想象性表述,有知识分子隐藏作者倾向努力还原现实生活原生态的纪实性表述,《没事偷着乐》似乎与两者都有所不同,它毫不隐蔽作者的主观立场,一反此类题材多使用长镜头的纪实风格,而是以频繁的淡出淡入、浓厚感情色彩的音乐、对某些生活场景的MTV式的画面美化、对生活事件的小品式的处理, 表达了创作者强烈的主观干预性。这种干预性是以一种冷静的注视、悲天悯人的关怀表现出来的。淡出这一暧昧的表达方式,似一双充满关怀的眼睛,伴随着沉闷悠长的管乐,或清亮悠扬的鸽哨,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含义。当张大民不得不面临两对夫妻一纸之隔的尴尬而坐在屋顶上沉思时,连续的淡出淡入不禁使我们对人物的生存困境有了更为深入的体察和更为冷静的思考;当四民患了白血病死去时,洁白的床单,飘动的窗帘,哭泣的儿童,不断的淡出切换形成一种MTV式的效果, 它把四民的死处理得凄美哀婉,它延缓了叙事的节奏,使我们的情感停留驻足,不禁为年轻美丽的生命的逝去而黯然神伤,即使她是一个普通人,这种美的破碎依然令人心碎;当大民为结婚征求全家人的意见时,影片运用淡出后较长时间的暂留形成的黑画面,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有时被屏蔽的事实,而且通过画面的遮蔽,使我们可以更真切地倾听他们的声音。
另外,影片在表现平民生活的艰难和苦涩时,还强调了苦涩中的温馨和幸福,如整部影片明亮的色调,大民新婚之夜红色背景下紧紧相握的两只手的特写,长有大树的小屋,浪漫的花墙,类似花墙的小院门,等等,所有这些,都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诗意的提升。也许这种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生活的矛盾冲突,美化了冷酷的现实,但是,它却更令人感动,发人深省,它将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的目光投向了生活。是生活更为真实呢?还是表述更为真实?实质上,这是一个难解的问题。所幸的是,《没事偷着乐》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范本。
安贫乐道——温情的港湾
谭政
正当国人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自己的栖居之所时,杨亚洲的《没事偷着乐》把镜头对准了当下驳杂的存在,他用诙谐而又凝滞的镜语为观众真切细腻地展示了一个纷扰噪杂的城市空间。虽然其中传递着几分苦涩,但那份真情与温馨却也透过镜语缓缓地弥漫了出来。
安居才能乐业,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家的概念可谓根深蒂固,虽然有不少作品发出了“家如樊笼、铁屋子”之类的诅咒,但“游子思乡”、“落叶归根”却一直是中国抒情作品中恒定演绎的母题。《没事偷着乐》正是关注了一个“家”的故事,在连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的居住空间里,张大民长兄为父,有如蜗牛一般,辛苦地支撑着这个庞大的家庭,空间越是拥挤,家庭的情感越是频起波澜。经过改编,电影已比小说温和多了,“矮胖得象个球”的张大民在银幕上已经变成了高大的冯巩,即使扮相刻意平民化,但已能轻易地被观众接纳。于是小说中的黑色幽默淡化了许多,虽然如此,但无论个体抑或家的生存苦涩在片中自始至终挥之不去。
一个时断时续的横摇镜头把一片嘈杂的平房院落展现给了观众,低矮拥挤却漫无边际的屋脊,以及那萦绕不去的音乐桎梏得人们几乎喘不过气来。片中两次出现的鸟笼隐喻着这个大杂院里的人群正象笼中的鸟一样,不可能在蓝天下自由翱翔。现实的场域中,要想得到超脱本是不可能。可张大民即使有了女朋友想结婚也要得到家庭各成员的首肯——喜事也不免带有点灰色的悲哀了。影片中的家庭会议是导演极力铺陈的一场戏,贫嘴的张大民在这时也是战战兢兢。迂回战术虽有收获,但到最后,自鸣得意的张大民却也只能哭丧着脸,不停地说着些气话了,原因有点滑稽——只是家里差点容不下一台电视机。此时影片中连续黑场的应用极好地表述了张大民的委屈、无奈与艰辛,让观众在品味张大民机智贫嘴的同时,更体会了小人物那份活着的酸涩。
嘈杂、拥挤的生存空间喻示了张大民这类平民苦涩的生存状态,从大民到五民谁都无奈地承受着那份沉重的压抑,乃至五民在兄长的婚宴上居然发出要到西藏去住的愤懑吼声,一句“我受够了”的哭腔让心软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那段长长的镜头也让观众为这份真切感动。当然除了居住的窘迫,影片中还有许多樊笼束缚了他们梦想酣畅的存在,家庭中的成员都有各自的辛酸。然而影片却没有完全沉湎于那份苦涩的营造中,“没事还得偷着乐”。贫嘴便是很好的注解,在无奈的生存中,它能很好地成为生活的融化剂,既能化解危机,又能因幽默而增添几分使人愉悦的情趣。贫嘴是幽默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影片中,它是张大民获得李云芳和在生活中化苦为乐的法宝,同时它更是影片进行叙事的一种有力的辅助因素,影片也因此在苦涩中融进了几分温情,让剧中主人公在读解艰辛的同时也得到温馨的抚慰。苦涩中的幽默本是一种无奈,可它能让压抑的情感得以宣泄,张大民以及他周围的人能从耍贫嘴中得到乐趣,而台下的观众也能从影片的诙谐中使情感得到释放,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因而幽默在本片的叙事中是努力为之的策略性情感抚慰。
“温馨”一直是中国叙述者对“家”刻骨铭心的注解,导演在渲染“幽默诙谐”之外,亲情的温馨也为片中生存的苦涩掩上了一层面纱。手足之情,夫妻之情,邻里之情,导演一直在银幕上自如地挥洒。尤其是四民和小树两人的设置。在五兄妹中,四民是导演极为同情而未加批判的一个人。小树则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儿童,天真可爱,透过他的眼睛看到的世界自然是美好无邪的。于是在四民即将告别这个世界时,导演让两个美好的心灵进行无邪的对话,虽然有几分凄凉,但影片中柔和的光影和小树稚纯的语气也呈给了观众纯真情感的温馨,影院中的空气也仿佛象病房中的空气一样给凝滞了许久。
因此,《没事偷着乐》在传递苦涩的时候,也营造着温馨。导演让剧中的人们在苦涩的无奈生存中,通过幽默和温馨的策略性抚慰,安心地停留在温情的港湾里,影片为此还在最后生硬地配上一段高昂的音乐。这也难怪,在许多尴尬的情况下,从《站直啰,别趴下》,到《红西服》,再到《没事偷着乐》,人们只有安贫乐道,机智地躲在温情的精神港湾里,让受伤的心灵在驳杂的存在中寻求一种替代性的慰藉,无论聪明与否。也许安贫乐道一直是人们温情的精神港湾。
平民活着
左衡
不知是否有意,《没事偷着乐》的主人公和他弟弟妹妹们的名字都被冠以“民”字。影片无意将他们表现成“人民”之“民”,于是“平民”及其生活空间就成了灰色叙述下的呈现物。
无论电影还是小说原作(《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题目都用了反义,而电影淡化了原作的反讽式幽默,现实平民的苦痛在这部都市电影中受到空前的重视和突出。杨亚洲不厌其烦地寻找着人物们的困窘,从满银幕灰色汹涌的瓦檐、两侧永远挤压过来的杂色砖墙与房屋,到一次次移至高空的鸟笼、叫人不得不仰视的电视机……无不明确地宣告了“人民”神话的破产;既而平民自觉意识苏醒:当平民的学子只能去房顶早读,当平民的妈妈只能睡箱子拼凑的床,当弟弟宣布要结婚的兴奋在哥哥耳中犹如雷鸣,当两对夫妻不得不忍受隔帘而眠的尴尬——简言之,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所在的阶层在今天注定处在社会的底层时,一种声音的发出也就不可避免。这种声音,可以是冰箱最不合时宜的轰鸣,可以是床头传来令人面红耳赤的隐私,更是家庭会议上的唇枪舌剑与喜酒宴间醉后的嚎啕和哽咽,从竭尽全力的克制到歇斯底里的爆发。如果说,镜头在迷宫般的窗、墙或甬道般的胡同之间长时间地摆动和逡巡是在细细地讲述着平民生活空间被严酷压缩的故事,那么,镜头之间反反复复出现的“黑场”以及时时回响的小号则在替他们不平地呐喊。
平民的精神人格与沉重生活水平相对抗并形成了影片的张力。为了活得稍微舒展,张大民艰难地耍着贫嘴,说服家人,折倒邻里。其目的已不仅是一张双人床的摆放或一间小房的立起,而是一方心灵乐土的建设,所以虽然形同画饼,张大民和兄弟床之间的墙上也会张贴一幅纵深感十足、画有林荫大路和明媚阳光的装饰画。这时,现实空间的谋求被赋予了人的合理欲求的意义,和人生存的价值紧密相连。与此相比,泾渭分明的社会规则在鲜活的生命个体面前显得那么没有人味:寻呼机的一声鸣叫,取消掉机主诉说贫困的权力;与家庭成员的死亡接踵而至的是在廉价同情下包藏的又一次打击——三居室减为两居室。然而主人公张大民并未被种种负荷压得渺小,他以一种朴素但是巨大的道德力量超越了琐碎的功利。张大民被邻居包子打伤,却决不肯报官,而选择“私了”,换来相濡以沫的情义;他用卖暖壶所得给母亲和妻子各买一只炸鸡腿,平衡了孝、爱在男人心中的地位;妹夫诚心诚意递上六枚金戒指,他只选一枚留给妻子,留给自己“不贪”的自得。当他和妻子退还了那个旧日情敌的美金,步出机场大厅时,善良和自尊使他们的背影可以表现得格外高大。道归市井,平民中间蕴藏的美德竟是如此感人。也正由于他的人格美好,贫嘴张大民的沉默更衬托出生活折磨的不公,贫嘴张大民的爆发则变得可以理解和原宥。
但是这些由于平民视点出发的表达都不应过分,否则又会损伤平民的形象。平民对那些急切地脱离平民阶层的人无疑会不以为然,但还不会象影片里那样对立。我们看到从外国归来的技术员,还有从外地大学毕业的五民(有意思的是,这两者的身份都定位成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不但改换了衣着发型,连乡音和质朴也一并丢失,可以明显地感到影片创作者的揶揄和挖苦。平民同知识分子的文化隔阂竟延续至今,这就未必完全是健康的了。此外,张大民对他农民身份的妹夫亲狎有余,尊重不足,而且不经意间流露出优越和高明之感,也让人隐隐不快:难道中国人的阶层观念竟如此根深蒂固吗?在这里,庸俗的市民意识——也许还有一丝小农意识,使影片出现了不和谐音。
无疑,上述心态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但由于张大民作为平民的化身愈来愈被塑造成一个智者的形象,他身上负载这样一些东西就有些遗憾了。而且,依我之见,将张大民这样的平民拔高到智者的地位也并不适宜。从贫嘴到懒得贫嘴,到大彻大悟则缺乏充分的理由。所以,影片结尾处,同是背着孩子,走在路上,张大民的哲理反不如福贵(《活着》的主人公)的童谣有力和有余味。
无论如何,《没事偷着乐》有一个出色的镜头作为结尾:男人背着孩子,女人搀扶了老人,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沿着草丛覆盖的铁轨向远方的巍峨楼群走去,镜头缓缓拉起,将关怀与温情的注视投到他们的背影上,以此完成对中国当代平民生活的观察和叙述,也借此传达一种对中国人未来的祝福,其境可玩,其情可感。
城市碎片下的平民真实
张燕
“文化的根就在现在,就在每个人身上……可能表现在非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导演黄建新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在席卷全球的都市工业化进程中,现代社会充满了喧嚣与躁动,我们这些现代人也身处于一种难以适从的尴尬处境——被动于工业化的快节奏,萎缩于传统的思维模式。我们犹如逡巡在传统寻根和现代侵袭的边缘地域,成长充满了难以名说的痛苦,我们的人生被割裂成一道道碎片,但这却是现代人生存状态的绝对真实。当然如何以影像画面再现出这种真实,却是一道较难跨越的门槛。
而《没事偷着乐》却敏锐地把握住了当前百姓最关注的住房困难问题,成功地以这一侧面扣住了时代的真实脉搏。也许是因为杨亚洲曾是黄建新多部影片的副导或联合导演,因此本片的风格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黄建新影片“平民生活化常态”的主旋律风格。他以一种原生态并极具独特艺术构思的影像,构筑出现代都市人真实的“鸽笼”空间和窒息的精神空间,以一种近乎冷观的创作心态去解剖现在,回响历史。
本片的英文名《A Tree In The House》意为屋中之树, 形象地描绘出百姓住房拥挤的真实状况。人的生存空间太狭窄了,为了不被窒息和多争取一些空间,只好把树困在屋里,一种多么朴实惨淡的影像表述。而本片的中文名《没事偷着乐》更有深意,现代人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双层夹缝,感受着现实和心灵双重空间的压抑,生存的现实与理想有着巨大的反差。他们无法把握生活的主动权,只能在现代都市的困境下挣扎着,所以只好以一种自嘲自娱的心态去调解生活,在心灵的压抑中有事没事地偷着乐一下,以阿Q式的精神学会解脱自身, 从而得以延续自己的生命。“没事偷着乐”巧妙地传递出这份深沉的文化内涵。
为了达到平民生活化常态的客观真实,影片中未加任何道德评判,导演以间离、静视的态度展示生活原生态的面貌。在场景上选择了天津拥挤的四合院居民区一角,采用原汁原味的方言。导演之所以选择天津,也许因为它是个历史悠久的古老的大都市,有着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因此在工业化轰炸式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冲突就越显激烈,从而深刻地反映出都市人艰难的生存状态。导演还在本片中静观复杂多面的人际关系,镜头冷峻甚或残忍地剖示出困境压抑下人与人之间细微却又尖锐的冲突,以及人性在物质束缚下的扭曲。片中张大民一家窝在两间狭小的平房中,以至于大民在为结婚而召开的家庭会议时,只有坐“冷板凳”吸“冷空气”的份,此外他买甲鱼引起二民的挑拨、母亲的牢骚等等,情感奠基于物质之上,在如此窒息的“鸽笼”空间里,所有的温情与人性都得变形。
另外,本片采用了一种独特的“不流畅”剪辑方式,在同一个场景甚或同一个镜头中多次强行以黑场来打断故事表述的连续,在视觉上造成一种情绪延宕的效果。画面的分割断裂代表着人物意识的流动与变化,也喻示着现代人心态的无奈与怅惘。人们面对艰难的现代生活体验,又经历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们无法逃逸,生命里间或会出现瞬间的窒息与突然的空白,而片中那频频出现的黑场恰恰就是最形象的寓示。这种自觉的剪辑形式,再加以画面自身冷峻客观的表述,平民原生态的处境就更加深刻、真实地显现于观众眼前。
本片作为一部优秀的现代平民状态的电影,其最出色的方面就是人物形象深刻的原生态塑造,尤其是贫嘴的张大民。可以说大民是个尴尬的现代都市人典型的代表,他身上集中体现着传统与现代冲突碰撞的都市心态。他善良,有爱心,尽孝子之责,对妻子百般呵护,工作任劳任怨,集合了中国传统的优秀品格;但同时他身上明显地体现出现代的变奏,具有典型的现代小市民的劣性,时时喷发出具有现代经典意味的都市话语,如“我说你别闹腾”、“你想打人,就抽自己嘴巴,别打老婆”,再加上有声有色的天津方言,精神萎缩的都市平民形象便跃然显现。张大民志向渺小,只有小家庭安逸生活的现实要求,对妻子与技术员的见面是表面的大方,背后却是心虚地跟踪,小市民的懦弱尽显无遗。我们难以简单地评价张大民的是与非、卑劣或高尚,反正他的性格有着许许多多的真实碎片,并且每一片都灌注着传统的压抑和现代的焦虑,每一片都是现代人真切体验的表述。影片以近乎调侃却又冷峻之至的镜头语言,深刻地剖析出现代人万般无奈的生存心绪。
冷峻中见客观,真实中现内蕴,一堆传统与现代冲撞的真实碎片,一幅白描的平民生活真实的展示,一份异常深刻的现代都市文化困境的呈现,这就是影片《没事偷着乐》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