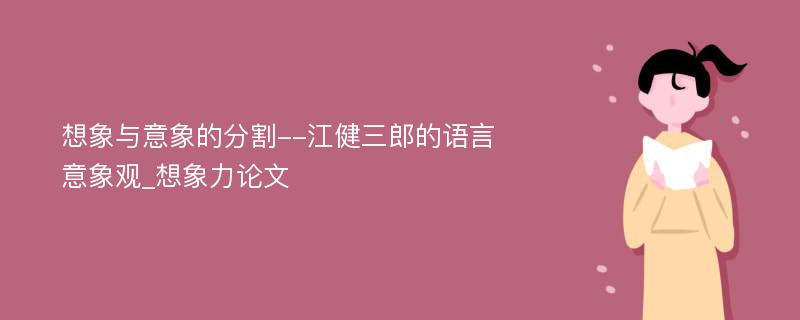
想象力与形象的分节化——大江健三郎的语言—形象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象论文,想象力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不仅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创作理论 上也进行了不懈的追求,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想象理论的不断探索上。大江健三郎对想象 力问题的关注,首先是萨特的“存在—虚无—自由”、“形象—想象—自由”,其次是 巴什拉的“想象力就是改变形象的能力”,最后是布莱克的“想象力就是人的生存本身 ”。也就是说,大江健三郎通过对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认识论大师巴什拉的想象理 论的反复确认,最后在英国浪漫主义先驱布莱克的想象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想象力就是改变形象的能力”(大江健三郎,《小说の方法》83),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提 出“形象的分节化”的课题,从而为想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尝试。这无论 对大江健三郎本人的创作,还是对普遍性的文学创作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主动自觉地 追随一种理论的指导,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加以发挥,应该是今天乃至今后文学发展的 必由之路。
一、语言结构与形象
关于形象,大江健三郎定义如下:
在小说中唤起读者想象力(imaginaire)的语言结构,在此我们称之为小说语言层面的 形象。就像我们对想象力进行探讨时所明确的那样,如果把一个形象再创造成一个新的 形象的根本能力称为想象力的话,那么作为这样被使用着的语言的形象,也就存在于我 们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中。为了便于在书写语言的层面上进行研究,我们把小说中唤 起读者想象力的语言结构称为形象。(大江健三郎,《小说の方法》98)(注:引用的日 本文献,皆为笔者试译,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形象,是小说中唤起读者想象力的语言结构,它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之中 。这是大江健三郎对于“文学的形象——语言层面的形象——语言的形象”的基本认识 ,是为了便于对文学文本中的形象在“书写语言的层面”上进行研究所创造的一个有实 践性意义的命题。语言结构,其关键在于与限定词“唤起读者想象力”相搭配。在这一 方面,日本传统文学观令大江健三郎极其愤慨:“国际上,对日语文学有形象丰富的定 评,被誉为多姿多彩的美的世界,那更多的是那些只能写出平静的、死去的形象的作者 的作品”(大江健三郎,《小说の方法》86-87)。并不是说所有的“语言结构”都是形 象,只有那些能够唤起读者想象力的语言结构才是形象(imager)。大江健三郎的“形象 论”,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形”是“主体理性与情感的复合体”,是“唤起读者 的想象力”;“象”是“外在的呈现”,是语言结构。可见大江健三郎从小说叙事的角 度,对形象理论进行了可操作性的理论阐释的尝试,使传统形象——想象理论得到了进 一步发展。
大江健三郎从果戈理的《死魂灵》中找到了“形象 = 语言结构”的例证,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形象分节化的问题。《死魂灵(МермвыеДуши)》作为果戈理的名作 ,可以阐释的空间比较大。作为一个固有名词,在俄语中“Души”以及它的单数形 式“Душa”与“灵魂”是相通的,而把这一词汇与另一个固有名词“农奴”联系起 来,则给这个词汇增加了新的意义。当乞乞科夫以收购死去农奴的名单的名义在小镇上 受到人们的欢迎时,读者们所感觉到的,这只是一个笑话的噱头,而无法唤起更为深刻 的想象力。但是,当他与女地主的交易公开化了之后,小镇上的所有人都开始呼应了“ 死去了的农奴——死魂灵”这一结构本身怪诞的唤起作用,从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因 此,乞乞科夫转瞬之间就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所以“死魂灵”这一语言结构,不止 可以唤起单纯的谐音,也可以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唤起读者的想象力。因此我们可以说 ,这种语言结构为想象力的活性化创造了契机。大江健三郎认为,《死魂灵》用了长达
几页纸的篇幅,为的就是表达这样一个形象:死去的 - 农奴 = 魂灵。这种能够唤起 读者想象力的语言结构,在小说的作者看来,就是小说的方法。当然在这种方法里,语 言 - 形象,是经过读者的分节化处理了。也就是说,对读者而言,这种对形象分节化 的处理方式就是小说的方法。对于读解某一部小说而言,这种分节化也是与作者相互理 解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从大江健三郎自己的创作看来,把形象分节化,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阅读方法。比如 ,《死者的奢侈》(1958)中的“死者”首先是现实世界中用于解剖的“尸体”,但是在 “我”所面对的现实中,“尸体”只是相对于我们的另一种“物”,相对于“我们”在 现实中所遭遇的“挫折”,“死者≠尸体”的待遇,确实可以称之为作为物的“奢侈” 。在日语中,“奢侈(おごり)”还可以有“款待”的词义。似此,则“死者的奢侈” = “死者的款待” = 我们的“现实挫折”,在这一不太复杂的过程中,形象已经有了三 次分节化的尝试,读者的想象力当然也要在这一方向上不断被唤起。《饲育》(1958)所 要“饲育”的对象,当然是被俘虏的美国黑人飞行员,但是当“我”理想中的“乌托邦 ”幻灭之后,残酷的战争所“饲育”的是“黑人兵”还是“我”?《万延元年的足球》( 1967)中的“万延元年”作为一个固有的历史名词,当然直接意指着“1860—万延元年 ”,但是时至“今日”的1960年,一百年前的“足球”的意义何在?一百年前的“足球 ”如何踢到当代人的心窝?《同时代游戏》(1979)所要限定的“同时代”,可以唤起多 少日本国内外的形象?你和我(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无可奈何的世界——同时代,我们也
就无可奈何地玩着这个游戏——规则无所谓,关键在于“玩”这一过程……
其实,在文学研究上,形象是通过语言—音声构图的能力。语言结构中的关键词汇, 就是这一“玩”的标志,它可以指示出一个条件、一个不完全推理、一个不完全序列。 作为“通过”标志的这个关键词,在读者想象力的作用下,产生词语联想,进而直指这 一词语所指事物的本身,以及与这一事物产生联系的生活、它对于生活的特殊意义。就 是说,凭借这一关键词所引发的想象,即有读者对过去的所知——关于过去的感觉的记 忆和经验,读者正是根据这种所知,继续完成不完全推理,把不完全序列还原或进行新 的排列组合,并由这一关键词给定的方位勾勒出一幅想象中的图画——如果读者有绘画 的技巧,可以把它描绘出来,这就是形象。在现代叙事文学中,对形象的认识越来越深 刻。小说家们越来越注意到形象——作为唤起读者想象力的语言结构的作用。在现代叙 事文学文本中,为描写景致而描写景致的大段大段的段落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对形象 以及形象体系的经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称为“破碎的景致”的描写打破了传统景致描 写的壁垒,使景致走向形象;普鲁斯特也曾经细致地描写感觉在个体身体上所唤起的形 象的过程……等等。
二、作为阅读方法的形象分节化
大江健三郎认为,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就是一部具有能够唤起读者想象力的 精彩的语言结构的中篇小说,最适合做形象分节化的研究。他在《读者与形象分节化》 一文中,用了很长篇幅分析了这部小说的形象,并讨论了形象分节化问题。他把作为欧 洲典型的主人公阿申巴赫称为形象a——是作者创作意识全部投入欧洲全体性的形象; 把具有多重含义的假青年 = 老头儿称为形象b,使其与形象a相互对峙;伪装成青年的 阿申巴赫是形象c,是托马斯·曼有意识地创作出的与形象a和形象b相互对比、带有固 定价值的形象。他进一步明确指出:
……即使像托马斯·曼这样真正的作家,也需要首先把形象a和形象b分节化,使各个 形象形成激烈的对抗关系,发挥互相作用的功能。如果没有这种互动的场合,形象c也 就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没法到达小说叙事核心的被分节化的形象c。小说只有通过 各种被分节化的形象的构成,只有依靠这些有意识的操作,才能成为包括超越作者意识 的浑然一体的结构体。(大江健三郎,《小说の方法》121)
分节化,是以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为根据的功能语言学理论的一种分析方法。叙事 文学的语言结构,往往可以看作是一个以唤起读者想象力为目的的大的形象群,这一形 象群有一个以上的形象体系,形象体系再由一个个形象构成。这仿佛某一语式为我们提 供的意义树一样,由一个个意义肢构成意义肢体系,进而构成意义群。对于形象作这样 分节化的处理,是读者自觉进入文学文本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形象分节化,使原来处 于混沌状态的全部形象清晰起来,使原来在叙事之流中缓缓流动的形象重新排排队,把 形象与形象间的关系凸现出来。
形象分节化,是读者接受理论的一个实践性较强的研究课题。形象是能够唤起读者想 象力的语言结构。对这一结构的分节化处理,一可以理清各个形象间的关系,二可以在 分节点上进行超越原作者的尝试。作为唤起读者想象力的语言结构,显然存在于分节点 上的可转换时空,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大江健三郎一直强调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接受是一 种能动的阅读活动,读者一定要意识到自己对文本中的文学形象的具体感受就是自己对 文学创作的主动参与,而在参与过程中的形象分节化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具体说来,《死于威尼斯》的开头部分就蕴涵了深刻的形象:“古斯塔夫?阿申巴赫或 者称冯·阿申巴赫——五十岁生日时被授予贵族称号——在历史数月带给欧洲严重危机 的一九……年春天的某一个下午,从位于慕尼黑摄政王朝大街的邸宅里独自一个人出来 散步。”从形象分节化的理论看来,这个句子使读者产生了消极的期待和不安的情绪。 正是这种形象上的准备,才为读者接踵而来的被唤起的想象力创造了契机。作为覆盖这 部中篇小说整体的形象—语言结构,作者所要关注的是籍此而被发动了的读者的想象力 。
同样,在大江健三郎自己的文本里,也有很多这种可以被分节化的形象。比如,在《 万延元年的足球》的开头部分:“在黎明的黑暗中醒来,寻求着热切‘期待’的感觉, 摸索着恶梦残留着的意识。仿佛咽下的威士忌使内脏燃烧起来的存在感,一边摸索着, 自己心里盼望着这热切‘期待’的感觉确实在体内恢复过来,但这永远只是枉然”(大 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7),就是能够唤起读者想象力的一组形象。对这些形 象的分节化,可以以几个动词为关键词来进行:“醒来—期待—摸索—枉然”。这就是 覆盖着这部长篇小说的全体性的形象。这两个句子给读者带来的是焦虑和不安的情绪, 接下来,作者的经营就在于对这种情绪的张驰有致的调动,对形象—唤起读者想象力的 语言结构的技术性调度。
对根所鹰四这个《万延元年的足球》的主人公,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形象来进行分节 化的操作。作为这一形象的分节点,形象a——“去国复归”,经过“安保运动”挫折 后的时代青年,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形象b——“组织足球队”并定名为“万延元年 ”,把今天面临的现实与一百年前的“农民暴动”结合起来;形象c——抢劫超市的“ 暴动”与失败的必然结局;形象d——“说出真相”后的“自杀行为”。经过这样的分 节化处理,一个清晰的“鹰四”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一个形象体系,形象a、b、c、d 以链条运转的方式,向这一形象的核心走进——“说出真相”。鹰四所要说出的“真相 ”——与自己的亲生的傻妹妹通奸,使其怀孕,最终导致其自杀,在表层结构上,是他 个人精神史上的巨大阴影,但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上,则对日本民族的精神史有巨大的暗 喻作用。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跨度在一百年间的独特文本,“万延元年”这一固有的历 史名词和一百年后的“安保运动”,在批判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现代性上找到了契合的焦 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百年的历史“真相”,正如大江健三郎在其他时事评论中所说 过的一样:明治维新的直接后果:一是形成一个隶属不明的天皇制,二是发动了一场对 亚洲周边国家的侵略战争,三是承受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共计两颗原子弹的轰炸…… 而把这一日本文化史上的“事件”,演绎成叙事文学的可以唤起读者想象力的语言结构 —形象:“傻妹妹”的不正常“受孕”和“自杀”以及“鹰四”的“疯狂—自杀”,都 更能够增加小说可读性空间。
《同时代游戏》中的“妹妹”的形象,也具有这种文化史上的意义。形象a——兄妹何 时产生近亲相奸的关系?形象b——父亲和妹妹在哪里发生的性关系?形象c——妹妹所怀 孩子的父亲是哥哥还是父亲?或者另有人在?形象d——妹妹为何要做“破坏者”的女巫? 形象e——妹妹与美国总统的性关系意义何在?从这些分节点看来,在《同时代游戏》里 ,“妹妹”是本真日本的一个隐喻(Metaphor)。表面上看来,围绕着“妹妹”的所有关 系都是有悖常理的,这种表面化的“有悖常理”也就是日本文化的根本病灶。由表及里 的“有悖常理”,是日本的父兄——家长制——天皇制的必然结果。依然是不正常的“ 受孕”,这次“妹妹”生下了“像狗那么大的一个东西”。作“破坏者”的女巫,其关 键在于谁是“破坏者”?在历史上,“破坏者”是领导人们创建山村的领袖,在历史延 伸到了今天,“破坏者”的使命是否有所改变?改变了历史使命的“破坏者”也需要有 同样追求的“女巫”,这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而“妹妹与美国总统的性关系”,则近乎 “明喻”地喻指当代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美日关系——当美国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他的 女王,当你妨碍了他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失踪”。可见,仅仅围绕这一形象,就有 这么大的能够唤起读者想象力的阐释空间,《同时代游戏》被认为是“最难懂”的小说 ,也在情理之中。也可以说,在这样的文学文本中,寻找与现实世界可以完全对应的“ 真实”是徒劳的,因为真实的世界只是这一被想象物的倒影。
三、唤起读者想象力的意义
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看来,言语理解的最初阶段是知觉分析,即将一些听觉的或视觉语 言结构加以识别,其实质也就是结构分析。言语理解以正确的言语知觉为基础,再进行 更高层次的句法和意义的加工。这是一个自觉主动的建构意义的过程,包括形成期望和 假设,进行推理,利用上下文等。这一切都依赖于人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包括语法和语 义的知识。相对而言,语言结构—形象的分节化,就是在这种言语理解过程中寻找文学 命题。言语理解(读者的接受)是从句子的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过程;言语产出(作者 的创作)则是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过程。言语产出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大致包括 :决定要表达的思想,确定句法结构,选择相应的词汇,实际说出话来等几个阶段。相 对而言,言语理解则是逆流而上,直到源头去寻找命题,经过语音知觉、单词识别、句 法分析和语义表征的判断等几种水平上的操作,才能从言语形式所传达的信息中,发现 思想是如何转换成言语形式,从而确定文学文本所要要表达的思想。由是观之,对有意 义的——能够唤起读者想象力的语言结构的分析,也就是形象的分节化。
大江健三郎“形象分节化”的理论依据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西方文论,这个问题的 提出,初衷是把想象理论与读者阅读和作者创作直接结合起来。从读者接受理论和小说 创作论而言,大江健三郎的理论尝试是有益的。如果把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技术来理解的 话,把作为能够唤起想象力的语言结构—形象的分节化,无疑是使读者更加透彻地理解 文学、走进艺术殿堂,进而更加热爱生活的一个捷径。正如萨特所说:在写作行动里, 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 动者。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 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从这个意义上看来, 大江健三郎的形象分节化理论,是对萨特的理论——作者与读者以及文学文本之间相互 关系的理论的自觉实践。
正确处理想象力和语言、形象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加具有实践意义的课题, 是大江健三郎对日本文学理论的一种突破。在日本,“想象 = 虚构 = 不真实 = 谎言 ”,是带有普遍性的推理逻辑。比如,日本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川端康成认为 ,如果仅只描写男性,则势必要写他的工作、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之类的主题,其 生命保持不了三五十年,这类主题几乎无法保留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一认识看成是川端 追求“脱政治”的最好理由。这仿佛《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所籍以“脱政治”的遁 词:“作者乃一介女流,不宜奢谈国事。”在“虚言(そらごと/谎言)”以及“真(真の こと)”和“伪(偽り驌れたゐこと)”的二元决定论的束缚下,日本文艺学丧失了想 象理论发育壮大的土壤。在这种理论的怪圈里,“想象 = 虚构 = 不真实 = 谎言”。 就连文笔生涯持续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的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寺田透,在这一问题上 也未能脱俗。他认为:“在小说创作上,由于某个作家的工作,使得他以前的某些作品 变得没有读的必要,也没有读的趣味了,可是诗却没有这种厄运,因为比起(容易)接受 时代倾向和特性的影响、多有夸张和歪曲的(叙事文学的)想象力来,’言志之诗’首先 是语言问题”(寺田透89)。寺田透“重诗轻文”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而更大的混乱 则在于“想象力”上——诗言志,述说的是诗人内心的真实,而(小说等叙事文学)“想 象力”,由于容易受到此时此地时代倾向和时代特性的影响,所以对这种“言志之诗” 的“真实”多有夸张和歪曲……并且,诗“首先是语言问题”,那么,小说等首先就不 是语言问题?诗,就不需要“夸张”甚至是“歪曲”的想象力吗?关于这样的设问,我们 已经没有延伸下去的必要。到了1998年,大江健三郎还要引述威尔士诗人托马斯的关于 想象力与语言关系的论述,即表明了他的担忧:“语言学领域有一种新的理论,即只有 通过语言,事实本身才会有秩序地发生变化。决定人生旅途的不一定是事实,而是语言 。语言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神话——比世上所有毫无特色可言的事实更能直接给 人传播真实,语言具有创造人类的形象和象征的力量。这种能力如何命名呢?对很多人 而言,这就是想象力。但是,最危险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想象力是并非真实的同义 词”(大江健三郎,《私という小说家の作り方》20)。
其实,至关重要的是,寺田所代表的是日本文坛根深蒂固的需要“活性化”的关于文 学虚构的本质主义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想象力,在更多情况下,是在承受着作 为“负数”的失衡状态中的重压。由是观之,大江健三郎从语言、形象进入想象力理论 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对这种“想象 = 虚构 = 不真实 = 谎言”的先入观的拨乱反正 。
语言,是作者和读者进入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文本、进入这一艺术世界的唯一方式; 形象,能够唤起读者想象力的语言结构,是联结作者和读者的唯一纽带。只有在这一意 义上,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大江健三郎所提出的语言、形象的分节化——想象力的活性 化;也只有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体会大江所说的:“语言把我从现实 中抛出去,放逐到想象的世界中……”(大江健三郎,《私という小说家の作り方》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