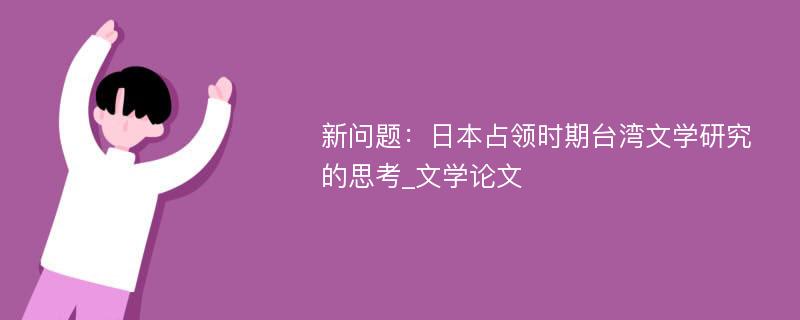
重临的问题: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时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如何,近10来年应该是两岸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自开展以来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一方面,研究观念和学术环境的变化,使台湾文学的研究得以不断推进;另一方面,以往未曾彻底解决的问题,也一再浮出水面,甚至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忽视这些一再重临的问题,那我们的研究将不可避免地不断重临研究的起点。有时我甚至怀疑,是否存在从一个固定的视点和高度进行这种评价的可能和必要?尽管如此,类似的尝试一直是我想进行的。因为它至少可以造成一种对话的氛围,而“对话”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研究和批评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不过,本文并不打算进行一般性的海峡两岸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的现象描述,而只是试图谈谈我们在研究中不得不一再重临的问题。
毋庸讳言,近十年的台湾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并不是在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上获得起点的,大部分研究者十几年前写下的东西今天有不少已不忍卒读。这也部分地解释了近十年来海峡彼岸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的发展何以如此迅捷、如此激烈的原因,当然,台湾文学研究之所以成为台湾当下的一门“显学”,与台湾当局竭力推进的“去中国化”和“渐进台独”的主张有着更为直接与密切的关系。
许多论者曾用多元化来把握近十年两岸台湾文学研究的主要特色。此一类说法大致不错。但是,假如这种把握不是基于对目前研究现状尽可能客观与公正的把握,而只是以卖弄个人才学或炫耀理论的新潮,那么,这样的研究存在的价值就需要斟酌。对于台湾文学,特别是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研究,说实在的,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界对此关注得还很不够,虽然也有一些大陆学者一再呼吁加强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研究,事实上却效果不彰。在台湾当局竭力推进“去中国化”和“渐进台独”主张的现实境遇中,在台湾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绑上了政治战车。然而,作为海峡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者来说,研究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不仅可以重新认识它的特殊文学意义和历史价值,而且可以帮助台湾人民摆脱殖民地的创伤。恰如台湾学者王晓波所言,虽然“今天台湾已不再是日本殖民地了,这种‘殖民地的伤痕’必须平复,而不能沉溺于嗜痂成癖之中,温习这段殖民时代的历史,应该是有利于我们走出殖民地的阴影才是”。①
海峡两岸半个多世纪的人为隔绝所造成的历史断裂、理想幻灭和价值混乱的危机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精神背景,因此新的研究意识的形成和确立不可能不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曲折和反复的过程。事实上,无论是标榜什么“主义”,都必须面临实践的检验和现实的制约。在这方面,近十年台湾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现象是意味深长的。譬如所谓的“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的论争”、关于“皇民文学”的论争以及台湾文学的本土化运动的倡导等,之所以引起了那么多的注意,不能不说是与海峡两岸的政治现实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考虑到这些不断重临的问题中所蕴藏着的重大历史真相,问题的严重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每当台湾文学的本土化叙述开始喧嚣尘甚的时候,文学中的“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就成了炒作的政治议题,如何公正、客观地诠释这一议题,就成了研究者需要直接面对的政治问题,而研究也无可避免地带上了“有色”的眼镜。为此我们不得不上溯至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界的几次文化与文学论争运动,只有尊重性地回归那一段历史,才能揭示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台湾文学的乡土主流
事实上,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界为了抵抗日本文化殖民的压力,确实曾掀起过关于“台湾话文运动”并进行过“乡土文学”的论争。而且不论是“台湾话文运动”,还是“乡土文学”口号的提出,都是台湾新文学动员期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和深入。他们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环,台湾和中国是永久不能脱离关系的,所以反对另立台湾特殊的地方性文化。这些意见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日据时期,“乡土”二字在台湾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强调乡土,本身就含有抵制外来奴役之意。事实上,不只日据时期,即便战后,乡土文学也依然是台湾文学的一股主要潮流。如果我们理清了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历史的真相,那么对于今天某些人企图利用“台湾文学本土化”做政治文章的用心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这些一再重临的问题,在今天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焦点之一,与某些研究者在现在时的政治意义上使用这些史料不无关系,尤为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某些台湾研究者甚至拒绝相信曾经有过的事实,故意将史料进行断章取义的引用。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现实层面来探讨这些问题,更需要从历史和学术独立的层面来进行思考。台湾历史上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成为受害者,故而某些台湾学者的本土叙述就充满了悲情的意味,甚至可以说积怨、迁怒于历史环境和某些个人(譬如蒋氏父子的威权统治)已经成了某些研究者的一条习惯思路。他们人为截断了大陆同一时期也遭受了苦难的情况,处处凸显出一种控诉的意味,企图利用所谓的“本土化”和“去中国化”方式,截断海峡两岸的民族文化联系,企图将台湾凭空打造成一个不存在的“民族国家想像的共同体”。
二、“为人生”的写实主义
毋庸讳言,海峡两岸分隔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浩劫确实给研究者造成了不少困扰。但历史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割断,民族文化传统也不会因为简单的“去中国化”而被截流。事实上,自1895年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时起,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台湾的这半个世纪,可谓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堪称“乱世”。台湾本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与闽、粤两省有着紧密关系,大多数的台湾居民本为这两地的移民。日本据台之初,即竭尽全力切断此关系,以使台湾人民彻底归附于他们。到了中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已经走上了轨道,其“统治力”遍及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可是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关系仍然无法被完全切断。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台湾地区亦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学运动。由于台湾新文学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遵循着“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原则,这是台湾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由于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严酷环境的限制,以及与祖国大陆一衣带水的深厚文化渊源,决定了台湾文化的另一种气质和氛围,表现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中的,便是对“原乡”的眷恋之情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屈坚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史,每一页都充满着血和泪。广大台湾作家,用自己的血和泪,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台湾同胞苦难生活,启蒙民众铲除封建桎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文学作品。
可以说,在1945年以前的“台湾作家的作品里,是充满着社会意识的,很少逃避现实,遁入虚妄的王国里。大多数的作品,所描写的是穷苦、朴实的农民,和他们在剥削下的生活,或者日本警察的暴虐嘴脸,御用绅士、走狗的面目等等殖民地现象。大多数的台湾作家都能将自我的价值归结到社会大众上,社会的灾难就是个人的灾难,周围人民的不幸就是个人的不幸,借着作品表达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抗议精神,或是对不可抗拒之外加灾祸的刚毅的隐忍精神。”② 譬如台湾文学的先驱者赖和、吴浊流等人,就在他们创作的小说中,表达了用本民族的文化来同异族殖民者的文化进行抗争的坚定意识。赖和的小说《一杆“称仔”》,通过对日本殖民当局颁布的“度量衡制度”和“警察制度”虚伪性的无情揭露,彻底瓦解与消泯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的所谓“现代国家”的神话。吴浊流在隐秘状态下创作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则倾诉了台湾人民没有家园,到处被放逐的“历史孤儿”心态,渗透着强烈的悲愤。“不但写尽了台湾社会的诸样相,道出了台湾人的悲欢离合、迂回曲折的命运,有瑰丽的乡土色彩,而且更进一步地指出了台湾人民的意愿、应走的路、未来的命运。”③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新文学创作与同一时期祖国大陆反帝反封建文学一脉相承,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神圣组成部分之一。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今某些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却成了一种效应研究,不再尊重历史,成了一种注定要在政治要求中不断变换的“研究”。
三、台湾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
首先涉及的就是关于研究中叙事方式的转化问题。那么,当下的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中的叙事方式又是如何转换的呢?它与过去的叙事方式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如果从文学研究记忆的视角来讲,研究性叙事应积极描述各种文学活动,诸如作家创作、作品阅读、思潮滚动以及流派争鸣之间所牵挂的解释、诠释与重新诠释,让史料始终处于研究者“当时”所赋予的“当下化”状态,从而具有现实般的“共时性”特色,并进而影响整个文学的内在结构,令史料呈现出研究者所需要的面目,或者撕开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或者隐藏,甚至扭曲历史的真相。
虽然在研究中,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历史流程必然要经过无数次地被还原和被阐释,每一种阐释都具有相对的真实性和历史性,只有拨开弥漫在其中的时代话语的笼罩,用特有的叙事去接近文学及历史的本真,这样才会帮助我们找到文学与历史的存在真相。为此,我想说的是,主体“叙述”的“零”度姿态应该成为一种努力追求的研究风气。换言之,研究者的叙事立场应该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要“关注这些类型的文学形态产生、演化的情境和条件,并提供显现这些情境和条件的材料,以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④ 如果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能够持有这种态度,也许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相当完整地重现了台湾民众历史的、社会的固有生活,因此这些作品中所闪烁的乡土色彩和多姿的风俗习惯,追求的绝非浪漫的异国情调;毋宁说,它从伦理的、民族性的立场上,试图去掌握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特殊的生存方式,揭橥了“被虐待者之解放,沉没者之向上,而自主独立者的和平的结合。”⑤ 这些文学作品从孜孜不倦地仔细描绘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日常生活情景中,清晰地浮现出了台湾人民顽强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鲜明意识,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施行的殖民统治予以了全盘否定,以活生生的事实指出:在台湾这一块曾经被日本帝国主义一度侵占的中国的土地上,日本殖民者永远只是异民族,永远只是陌生人,台湾人民是永远不会被他们征服的。也正由于此,这些作家在日据时期,以他们多姿多彩的创作成果,为台湾新文学奠定了写实为主流的反抗文学传统,以及具有人道特色的平民文学传统。然而,就目前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其研究过程中叙事者的声音在对研究对象阐释的过程中表露得异常激动,受意识形态干扰的意味异常浓厚。虽然说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通过日常生活批判视角,用热烈的乡土情怀和真挚悲悯的笔触,描写了勤劳而贫困的台湾农民及其他劳动者,呈现了台湾社会苦难与凋敝的历史景观。阅读这个时期的台湾小说,常使人联想起以鲁迅为代表的早期新文学作品中弥漫的那种整体性的悲凉情调。这说明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文学很相近,它们都是站在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审视当时现实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虽然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群台湾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在艰难的日据时期所奠定的新文学的血脉始终未断流过,然而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宝贵资料,却随着星移月换,在无情岁月流逝中,有些已散佚或湮灭,如果现在还不重视搜集和研究,恐怕这段台湾先辈作家们,以血泪和生命换来的纪录,势必将跟随着历史而一并消失。因此迫切需要更多的同仁以“尊重历史真相”、“复归历史真相”的严肃态度来共同关注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研究。
“尊重历史”必须成为目前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者强调的另一原则。这不仅是研究者独立学术品格的体现,更是衡量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尺。众所周知,在漫长的五十来年时间里,台湾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不仅顽强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抵抗斗争,而且始终在寻找着重建自己的家园与村庄的机会,锲而不舍地探索着一条彻底砸碎殖民主义枷锁的道路。恰如光复初期,台湾著名政治家林献堂所说的:“台湾沦陷五十一年,同胞饱尝亡国痛苦,痛定思痛,所以对国族倍感可爱,希望国家强盛民族繁荣的心情,比国内同胞或且有更来得深刻之处,六百五十万台胞,不但在敌人治下无时或忘祖国,对于祖国数十年来的内忧外患尤极关切,光复后已觉有可爱护的国家,可尽忠的民族,所以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莫不极度感奋,愿尽其所能以图报效,对于目前的军事统一,政治民主,确信其为建设新中国的对症良药,深愿与国内同胞同心协力,以促其成,永不愿再见有破碎的国家,分裂的民族,自行分割就是自取灭亡。”⑥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却出现了某些鼓吹“文学台独”的人,他们将“台湾本土化”无限上纲,并竭力推行“去中国化”与“妖魔化中国”等一系列阻挠祖国统一、分裂国家的政治主张与行动,他们这些倒行逆施的言行,若与台湾这百余年近现代历史中前仆后继拼死抗日,争取民族解放与回归祖国的先辈们相比较,是何等的数典忘祖。事实上,台湾新文学一向以来,就是跟随着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的发展而生长、茁壮起来的,反映了全体台湾民众的共同意愿——推翻日本人的殖民统治,重新获得民族的解放和自由,再次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因之,台湾新文学运动始终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离的一环,它蕴藏着强烈的民族精神,带着浓郁的乡土色彩,充分表达了在异族残暴统治下痛苦呻吟的台湾人民的心声。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说,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就是台湾人民反抗殖民暴政,追求祖国统一的文学见证。
当然,正是由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台湾文学发展历史流变的多重视角,为此,不能不花费一些篇幅来谈论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过程中对历史的宏观与微观把握方式,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中一再面临的问题。众所周知,从历史背景到具体作家作品和流派,从经济政治关联,到意识形态,恰如巴赫金所描述的四个环节:文学作品——文学环境——意识形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宏大叙事虽然可以使文学研究的编纂进入一种更加宏观的文化视野,但却常常冷落微小的、局部的历史叙事;宏大叙事虽可以勾勒出一个历史时段文学的总体面貌,但它也可能使许多复杂的史实及研究者独特的体悟从中消逝。正因如此,目前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的研究,特别是在大陆研究界常常流于相似或相近的背景分析和主潮描述,历史的独特性和叙事的独特视角被不经意地遮蔽了,以致个人的独特历史发现没有被预留下空间,故研究的雷同或趋同在所难免,低水平的重复之作汗牛充栋,鲜有深入之论。这从另一方面也喻示目前对于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研究者来说,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对那一段历史进行“补课”,只有真正客观、公正地“尊重”与“复归”那段历史的真相,才能在文学研究中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令人信服的观点或结论。
注释:
①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1985年8月版,第6页。
②林载爵:《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台北《中外文学》,1973年12月号。
③[日]尾崎秀树:《吴浊流的文学》,《台湾文艺》(第41期),1973年10月版。
④[日]矢内原忠雄著、周宪文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的“序言”,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年版。
⑤王晓波:《台湾抗日五十年》,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第285页。
⑥这段话是1946年林献堂率“台湾光复致敬团”赴南京时发表的谈话,见王晓波所著的《被颠倒的历史》一书,台北,帕米尔书店1986版,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