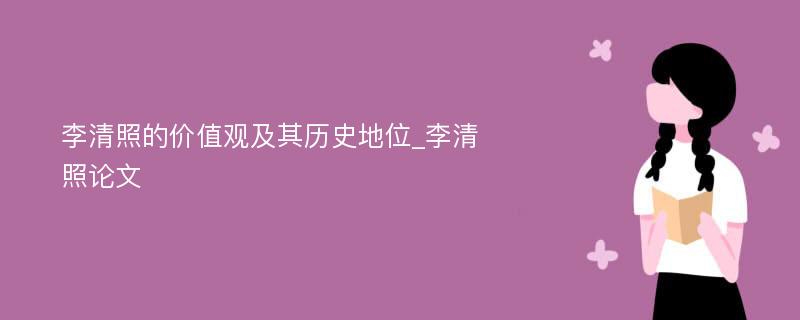
李清照的价值观念及其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念论文,李清照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词人,遗憾的是自宋至今,或褒或贬,率皆就人论人,就事考事,就词品词,有较多的随意性。本文从思想史和词史的角度来看李清照,给李清照其人其词作历史的定位。以为李清照是崇尚自我人生价值的勇士,是女性解放的先驱,是中国文学史上倡导平等的文学批评的旗手。兹略加陈述以就教于大家。
一
讲到思想发展的历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特别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且不说先秦的“百家争鸣”、西汉初的独崇黄老、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之际的玄学佛教道教的盛行、唐代的三教(儒、释、道)并重,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非本文范畴,姑置而不论)。就以宋代而论,学者咸以为有宋一代的意识形态是三教(儒、释、道)合一。就宏观而言,这个概括符合事实,倘细加分析,问题决不如此简单。
唐代的三教并重,并不是绝对的静止的势态,其中,儒学占有着特殊的优势:首先,儒学是小农封闭经济的产物,只要这个基础不变,它就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其次,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社会结构条件下,儒学是该结构各层面利益相对合理的粘结剂。其三,知识分子由于渴求仕进,极自然地成为儒学推行的中介。因此,尽管唐代帝王三教并重,但实际社会生活中却常常掀起儒学高潮,最著名的当是韩愈,他利用安史之乱以后的社会结构严重失调,奋起抵排佛老,尊崇儒学,做了许多令人瞩目的事。宋代的三教合一,也不是凝固式的静止。宋代的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与唐代大体相似,但是,细加比较,宋代又有几条特殊性。首先宋代的城市经济,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与唐代相比更为兴旺发达,读过《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诸书的人,都不难想象北宋、南宋的城市生活状况。《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开封的盛况,就中商业之繁荣令人咂舌。大相国寺原是开封的佛教胜地,但在《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中,大相国寺实为北宋京城大市场,更令人有兴味的是,“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等记载,则北宋的商业大潮将出家人裹挟在内,堪称叹为观止。至于城市功能,其服务项目之细,与今日之城市相较,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请参阅《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雇觅人力》《防火》《天晓诸人入市》《诸色杂卖》诸条)。提及这些琐事,意在说明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即在官员和农民之间,商人及其附属阶层的数量逐渐扩充,在宋代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这个阶层和上层官员的关系特别密切。其次,宋代官制十分特别,不仅官员的数量多,而且冗员亦多;不仅官员多,而且俸禄和赏赐还特别丰厚,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以《宋制禄之厚》、《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诸条标出,兹不赘。将这两个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看,不难理解,官员的消费享乐和商业及其相关的服务阶层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质言之,在这个特定的社会活动过程中,商人及其相关的阶层(包括手工业工人和从事服务业的市民)越来越发现其自身的价值,会越来越体认到他们自身的社会功能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其三,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受儒学和自身政治需求欲望的影响,很少重视对商人和市民阶层的研究,甚而至于常常流露对商人和市民阶层的轻视和鄙视。因
而,这个新兴阶层的思想愿望和情绪常常处于被抑制的状态。要想了解商人和市民阶层的思想情绪是相当困难的,有时只好从通俗故事中去寻找线索。被认为是宋代通俗话本小说《碾玉观音》和《快嘴李翠莲》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价值观念信息。《碾玉观音》中的主人公是崔宁和秀秀。前者是雕刻能手,尤以雕刻观音而出名;后者是刺绣专家。两人相爱,企图依仗自己的才能(雕刻、刺绣)过自由幸福的生活,虽然最终失败,但故事发展过程中的主人公相信个人才能而不依赖其他社会力量的信念是感人的。值得注意的是,男女两位主人公中的女主人公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动积极的地位,一反中国妇女在社会、家庭及至两性关系中的被动、依附、顺从的传统,一反传统婚姻制度依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事实,提出了崇尚自我,崇尚个人才能,女人和男人一样有同等的追求自身合理愿望和要求的社会价值观念问题。孔子说过“木讷近仁”的话,而《快嘴李翠莲》中李翠莲口齿锋利,言谈不让他人,凡事她都洋洋洒洒口若悬河般地演说一通。这种崇信自我,不让须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这个新的信息便是新的社会阶层提出的新价值观念思潮。这种新的思潮,在事隔千年之后,也许我们的感觉并不十分强烈,但在当时,却也许是十分震撼人心的。李清照在开封住了六七年,不能不受这个时代风潮的影响。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宋代的“三教合一”。其实,宋代的社会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基本相同,新的市民阶层的扩大还没有发展到产生对抗的地步。因此,儒学在唐代享有的三项优势在宋代也没有本质的变化,相反,在儒学看来,影响和威胁儒学生存地位的,不是佛道二教,而是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的价值观念和追求人自身利益的新思潮。这些新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儒学社会政治伦理是相悖的、对立的,有时是对抗的。敏锐的知识分子必须发展儒学,对抗新的价值观念。于是,儒学专家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存天理,灭人欲”。通俗地说,天理就是儒学社会政治伦理,人欲就是前边叙述的崔宁、秀秀、李翠莲诸人的要求和愿望。涉猎过宋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北宋的儒学,不管是邵雍的“象数”说,还是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说,抑或是程颢、程颐的“理学”,只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他们一无例外地以儒学的社会政治伦理为皈依的目标。且不说君臣父子,单就夫妇而言,他们都是封建性的夫妇关系的维护者。无需乎旁征博引,且看他们口头禅:“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唱随之礼,此常理也”,“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均程颐语)。在儒学社会政治论理中,社会的结构尊卑有序,虽然提倡尊要爱卑,但卑决不可以反尊,“犯上作乱”是万万不可以的。至于夫妇之间,夫尊妇卑,所以“夫唱妇随”是一条定则。孟子确实说过“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话,《礼记·礼运》中也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记载,但是这个“性”和“大欲”只属于人口的一半——男人,不属于人口的另一半——女人。质言之,男人可以娶妻、纳妾,还可以挟妓,而女人即使“孤孀贫穷无托”,也不可以改嫁,女人一讲“色”,一讲“大欲”那就是“失节”,和犯罪没有两样,因而是万万不可以的。搞清了这个思想背景,我们就能理解李清照的词所具有的思想意义和人格价值:
红酥肯放琼苞碎,探著南枝开遍未?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色藏无限意。
道人憔悴春窗底,闷损阑干愁不倚。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
(《玉楼春》)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
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樽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
(《渔家傲》)
李清照这类词的意识形态特征不外以下几点:一、写女性美,或借助于花作喻,或借助于白描手法。二、写女性的春情,或借助于怀人,或借助于暗示。三、写女性美或女性的春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展示或自我需要,并非以男性为中心,将自己放在从属的被动的地位。质言之,李清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前边提到的《碾玉观音》中的崔宁、秀秀的价值观念相似。李清照的性格和行为,和《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相似。虽然他们在形式与表象上有明显的区别,但其精神实质是感通的。我们注意到,前文提到的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恰好是李清照的前辈,他们的思想影响和价值观念从时序上正好涵盖李清照:
邵雍,一○一一——一○七七。周敦颐,一○一七——一○七三。
程颢,一○三二——一○八五。程颐,一○三三——一一○七。
李清照,一○八四——一一五六。
被北宋理学家的“光辉”照射的李清照却发射了强烈的反光,而且,是以一个大家闺秀的身分,其意义可想而知。应该指出的是,人的觉醒和对自我的认识常常从自身开始,原始人大概是从人自身的渔猎能力和生殖能力认识最早的人的价值的。魏晋时期玄学盛行,提倡率情率性,人们开始重视个人的才能、智慧和自身的形体美。唐代的考试制度使许多知识分子从政有望,人们将才能智慧纳入政治轨道,对形体美的追求有所淡化。其实,形体美和自然美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审美客体。人体和山川风景、花卉树木一样,只是审美的对象,将人体和两性关系拴在一起,虽然不无道理,但它却是伦理观念淡泊和文化素质低下的反映。众所周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首先是一种责任,一种社会的需要,即人类延续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个体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次才是生理和情欲的需要。因此,将形体美和性乃至和“淫”联系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宋人攻讦李清照“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是完全从儒学社会政治伦理看问题的缘故。王灼的话应该翻过来看,所谓“闾巷荒淫之语”正是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念新标志,是一种对旧历史的背叛,是一种对新历史的企求和开创。王灼提到缙绅之家的能文妇女,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东汉班彪的女儿班昭,赫赫有名,说缙绅之家的妇女也行,说是大家闺秀也行,不妨看看班昭的人生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观念: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容。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这就是班昭写的《女诫》中关于“妇行”的见解。毫无疑问,中国封建士大夫之家的女性大都遵循所谓“女诫”。无庸讳言,这些妇女实质上是不具备独立人格的,是男性的附庸,甚至是男性的工具。有一位伟人说过,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我们将李清照的词和《女诫》相较,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念显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检索一下李清照的家庭背景,就更能显示李清照人生价值观念的意义。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有文名,却属于“元祐党人”。所谓“元祐党人”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对抗的政治势力。元祐党人的是非曲直,与本文无关,姑置而不论。我们想说的是,李格非既然属于元祐党人,那么李格非在人生价值和伦理观念上必然有与元祐党首脑司马光相似的地方。司马光在哲学上相信天命,认为人的得失成败,咸由天决定。由此推理,人间等级贵贱由天命注定,不可改变,以为“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易说·履卦》)。其核心强调等级不可更易。虽未涉男女,其体系可知。李格非的思想体系想必与司马光大同小异。然而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却大量写作有背于封建观念的词,所以我们说,李清照对旧的价值观念是一次背叛,那么对新的价值观念说,则是在开创,至少也是一次启迪。
这当然不是说人的形体美、人的青春觉醒的追求,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人的价值观念的全部,更不是说她们是人的价值观念唯一的最高层次,但是,只要我们关注一下人类历史的进程,就不难发现人对自我价值的认识是从人自身的特点开始的。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对自身的价值认识越来越深刻,自我要求也越来越高,却是毫无疑问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初始意识常常就是最有革命意义的意识。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艺术家用人的形体美向冷酷的封建意识宣战,并成为一代最优秀的艺术遗产。中国历史上初始的自我意识后来逐渐形成深刻的哲学思想,成为近代的革命思想。因此,我们将李清照归入一个特定的历史思想环境,就能充分看出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历史地位。至于她的具体作品,人们已作了详尽的鉴赏,无需我再饶舌。
二
李清照填词、写诗、作文,但她最引人注目的是词。词是曲子词的简称,填词实际上是“依声填词”。所谓曲子词实际包含“曲子”和“词”两个范畴。所谓“依声填词”也包含“声”和“词”两个范畴。因此,一般说来,讲词,实际上要将“声”(曲子)和“词”合在一起,才能全面而正确地评价。“声”,或者称曲子,就是音乐旋律。众所周知,抛开文词,曲子的音乐旋律也能反映情,音乐家称反映感情的旋律为音乐语言,其意义和文词有同等的艺术价值。遗憾的是,词的“曲子”未被保存,留下来的几个曲谱我们又读不通。这对我们的研究是十分不便的。我们之所以先讲这个问题,是因为李清照有一篇《词论》,中心就是讲音乐和文词两个问题,其中音乐问题还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逮及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逗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声韵,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李清照的《词论》并未被学者们正确理解。宋代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中说,“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并以韩愈在《调张籍》中批评嘲笑李杜的人是“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为口实,言外之意,李清照亦“群儿”之辈。其实,胡仔根本不理解李清照,自然亦不理解《词论》。我们已经说过,曲子词是包含声情与词情两个因素,舍其一,不成为曲子词。学者们常以词情统盖全部,则难免失之偏颇。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对公正的,他说:词是文学,也是音乐,从文学的观点看来,词不殊于诗,所以苏轼说“词为诗裔”。而晁无咎、陈师道批评苏轼的词“不协音律”、“要非本色”,都是站在音乐的观点,说词应当异路。后来论词的虽有所见,但大体仍是这两种观点,如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女词人李易安《词论》,都是编于以音乐的观点立论,虽然也不忽视文学。(按,引用时作了删节,但不损原意)。罗先生很有学者风度,客观而委婉。其实,词论家特别是后世的词论家大都于音乐不甚了了,于宋词的音乐则更加茫然,但论起词来却咄咄逼人,虽然振振有词,细细想来,却难于首肯。既然音乐已难于搞清,我们就不想再从音乐本身的角度去评价李清照的《词论》。我想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从词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词论》中观点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或许有可取之处。
中国诗歌源于民歌。就《诗经》收录的情况看,不管是王畿的雅乐或者是郑卫之声,率皆入乐可唱。那就是说,现存《诗经》中的作品,在当时也是具备声情和词情两个因素的。现在有人说《诗经》大部分没有诗味,是离开了音乐单就文词而言的。若在当时,有个悦耳的曲调一配,也许还是流行一时的歌曲。君不见今日有些流行歌曲,尽管风靡一时,若单论其文词,不也令人哑然失笑么?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很难透彻地理解中国诗歌史。自从文人染指诗歌,或者确切地说,自从东汉文人写作五言诗开始,中国文人诗和音乐分离。但是诗不唱却是要诵读的,若要诵读其音节则有诘屈聱牙和琅琅上口之别。到南朝齐永明年间,以沈约为中心,创四声八病之说,在语言内部寻求音乐性,人称“永明体”。有的学者认为,四声八病之学和和尚诵经唱经有密切的关系,此说亦不无道理。理论的推导不必重复,听觉的直感确乎相似。记得儿时读私塾,老师吟旧体诗之声势和今日和尚之唱经相差无几。“永明体”的发展便是唐代的近体诗。近体诗音韵铿锵,对古代诗歌的创作起了良好的作用,例如唐人将律句引入乐府歌行,使歌行体面目一新,出现了一大批永世传诵的名作。有人说,唐诗皆可唱,虽不敢说篇篇皆可唱,但“旗亭画壁”也决不只是小说家言,换句话说,唐诗至少有一部分是可唱的。我们回顾这么多的历史事实,无非重在一点,即中国古代诗歌和音乐有极密切的关系(这里说的音乐,含意有二,一是曲子,二是语言内部的声韵平仄)。李清照在《词论》中重视音乐,反对忽视音乐的重要性是十分正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有一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民间的文学形式被文人染指,然后就发展演进成杰出的文学样式以流传后世。屈原的《离骚》是他学习楚地民歌创作而成的伟大著作;汉代乐府民歌被文人注意,最终创作了大量的文人乐府乐篇;词(曲子词)最初在民间,后来被文人改造,终于成为具有与诗有同等文学价值的作品;民间的说唱文学最后被文人将它演进成戏剧,等等。李清照的《词论》正是在词由民间而文人化过程中的一篇具有导向性的文章。众所周知,曲子词大约兴起于隋唐之际,是周边国家的民族音乐传入,与中原音乐交叉感染重新组合而成的一种流行音乐,或者用今天的名词——通俗音乐。我们今天从敦煌的抄本中能见到少量的歌词。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歌词可以使我们推想曲子词流行的情况。丝绸之路的边远城镇敦煌能保留抄本,那么在中原或经济相对繁荣的地区流行状况也可以想象。唐代的知识分子被考试制度吸引,读书作文做诗谋求仕进的劲头太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忽视了这个盛行一时的通俗歌曲。李白只写了《清平调》、《忆秦娥》、《菩萨蛮》等词,直到中唐之际,白居易、刘禹锡、王建、张志和等人才开始重视流行在民间的通俗歌曲。最有代表性的言论当推刘禹锡,他说: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
(《竹枝词序》)
不过,中唐文人的努力虽然业绩可观,但并未发展到替代通俗歌曲的程度。同时,晚唐政治腐败,外患频仍,李唐王朝处于奄奄待毙的状态。此时文人,逐渐对政治失去兴趣。为了排遣这种政治感冒病,他们投身于秦楼楚馆,在歌妓中依红偎翠,在温柔乡中医疗心灵的创伤。结果,他们不但没有改变、提升通俗歌曲的劲头,反而出现《花间集》那种“香而软”的风格作品,似乎在通俗歌曲中俯仰浮沉,难以自拔。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作了简明的概括: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调》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
骈体文说理自然含混,但是,大意是清晰的。就是说晚唐五代的词风依然香艳一路,所谓“迩来作者,无愧前人”,实际上是“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的延续。无须乎将晚唐五代词人的词一一列出,因为《花间集》的风格特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当然是就其主要倾向说的,并不意味任何一篇作品都不带有新气象。五代南唐的冯延已就是一位既在“花间”之内,又在“花间”之外的人物,就冯词的题材、主旨而言,依然在“花间”之内,就冯词的艺术由描述转向抒情而言,大概应在“花间”之外。李煜的前期词,应该在“花间”之内,而后期(被俘以后)的词,则当在“花间”之外。因此,王国维在《人间词活》中作过正确的描述: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筌》、《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在我看来,所谓“伶工之词”,就是通俗流行之间,就象今日之“流行音乐”、“通俗歌曲”。所谓“士大夫之词”,就是经过历史选择的高雅音乐或经过现实社会筛选的有深厚内涵的歌曲。王国维说李煜“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是单指李煜被赵匡胤俘获之后的作品。需要指出的是,李煜后期的这个变化,只是一个历史动向的开始,而不是历史局面的完成。其次,李煜后期的这个变化,是他政治生涯变化压出来的,并不是他文艺思想的觉醒而挥发出来的,因此,只是一个历史趋势的标志,不是历史终极的目的地。完成通俗词的提高、改造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宋代文人的身上。
北宋词人的写作,一以柳永为代表,在音乐上力求按照曲子词的规则,一方面依声填词,一方面自己另创新声,就是文学史上大家都说的“慢词”,或者称“长调”。在内容和语言上,他依然承袭五代的主要倾向,语言通俗,当时市井小民皆能歌柳词。不过,柳永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固然有“词语尘下”之作,但也不无“词语尘上”的佳构,象《雨霖霖》(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望海潮》(东南形胜)。但是,无论如何,柳永的“新声”是值得重视的。苏轼是公认的北宋文学大家,词坛上豪放派的大师,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文坛上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对“大家”只能研究其伟大成就,说毛病只能是缺点,且小而又小,微乎其微,假若妄加评述,就是唐突前贤,要受学人的非议。其实,“大家”成就固然大,有时候那毛病也不小。我想,只要不诽谤,出言有据,自圆其说,就应该允许。否则就不会有文艺批评和文学的进步,于“大家”也不利。苏轼的词从文学的角度说,确乎写得意蕴深厚,韵味深长。但他的不遵格律,也是前人多所评议的。不遵格律,突破格律,也许是另一种创造,也许是才华横溢的反映,但毕竟是事实,只要是事实,别人就可以评论。即使评论不妥也许可以将道理讲清楚。我以为,李清照意在保持曲子词的音乐风貌,在保持这个音乐风貌的前提下,对文词进行提高。这样的主张是否完全正确,且不必深究,至少是一家之言。另外,李清照自己精通音律,比较熟练地把握了曲子词的音乐规律,又能够以文人特有的文化层次来写作文词,自然是自身的长处,按照这个“长处”来进行文学批评,是极自然的。最后,在宋代,李清照作为一位大家闺秀,她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都和她所批评的人无法相比,但她却敢于进行评论,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此事本身,标志着李清照自我价值观念的觉醒。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政治上属“元祐党”,而她在文学上批评的也是政治上属于司马光倾向的欧阳修、苏轼、秦少游等人,这也充分说明她追求的是自己确信为正确的文学观念,因此,攻讦李清照“妄”、“狂”是没有道理的。李清照是中国文坛上以平等的身份与自以为高女人一头的男人进行文学上较量的第一个女评论家,令人敛衽以敬!
标签:李清照论文; 宋朝论文; 东京梦华录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碾玉观音论文; 词论论文; 通俗歌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