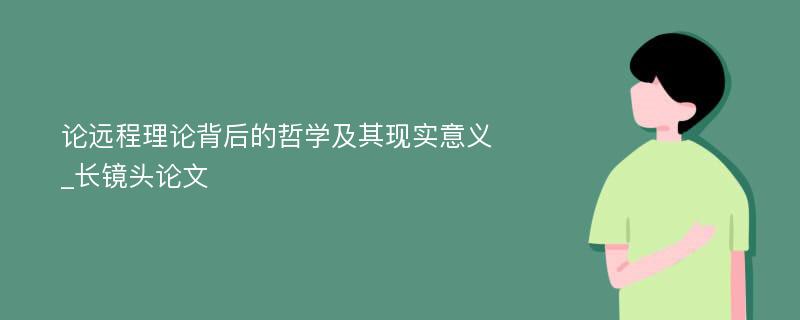
论“长镜头理论”背后的哲学及其当下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镜头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镜头理论”的出现,始于对巴赞电影理论的浓缩,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不确切的称谓。因为“长镜头理论”远非只是关于如何运用长镜头的论述,真正要在一个长镜头内展示一个行动或事件的完整段落,它至少应包括景深镜头、移动摄影和场面调度。而更重要的是,就理论而言,它首先是指巴赞的“影像本体论”。对此已有许多论述,恕不赘言。但“长镜头理论”后来成了一种与“蒙太奇理论”相对立的观念,尤其是其概念外延牵涉到诸多流派,实际上早已越出了“长镜头”的范围,所以,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潜藏在它背后的哲学观及其演变过程,且直至今日,其哲学基础仍在西方电影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下意义,而这正是笔者所要深究的原因所在。
一、从现象学到转向存在主义
最近,《当代电影》上刊发了刘云舟的《巴赞电影理论哲学观》,读后颇觉意犹未尽。作者认为巴赞的电影理论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具有不可否认的联系。(注:见《当代电影》2000年第3期。)这无疑有其合理之处。但应看到真正影响巴赞及其后学的哲学思想的,除了现象学外,更为重要的乃是存在主义思想。诚然,存在主义本身是从现象学演化而来的,现象学的前提,便是肯定世界存在于思考之先。但经由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之“现象”,并非实指客观事物的表象,而是一种“纯粹意识内的存有”。“现象的还原”是要人们从感觉经验返回所谓的“纯粹现象”,即先将现象“悬置”(epochě),或放进“括号”里(Einklammerang),视之为不存在的,以便能全身心专注于自身的经验和体验。而且现象学还要求去理解现象的“意向结构”,这与巴赞的用摄影机来再现现实的原义显然是不一样的。事实上,任何一部电影都不大可能使观众从电影的想象中“还原”出一种抽象的“意向结构”。电影毕竟不是纯哲学理论,它是以影像运动来刺激人,给人以审美享受的。其深含着的哲理,也须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图像经综合后,再加以领悟。而且,一旦影像不存在了,这种悟性也就无从开掘。不过,现象学所提出的“面向事物本身”却又与巴赞所言之“现实纪实”是一脉相承的。而梅洛—庞蒂的理论之所以可能为巴赞所吸纳,主要是因了他的“知觉现象学”美学。在他的《知觉现象学》(1945年)、《意义与无意义》(1948年)等著作中,首先强调了知觉的核心地位,他认为“哲学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深入到先于客观世界的生动世界,并重新发现现象,重新唤醒知觉……”。(注: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69页,人道出版社1962年版。)这个看法与巴赞倡导的电影“是表现”,而“不是证明”,的确是很近似的。但梅洛—庞蒂的哲学后来也明显转向存在主义,他的强调语义,实际上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的承袭。因为在他看来,“视觉是各式各样的存在的会合点”。(注: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第54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恰恰在这一点上与巴赞所强调的空间的整体性是相吻合的,而在《电影与新的心理学》一文中,梅洛—庞蒂为证明就知觉对象的整体性而言,电影是声画联系后的一个新的整体时,援引了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这显然又与巴赞的想法迥然有别。当然,众所周知,蒙太奇理论亦非完全排斥写实,长镜头理论也明知电影不可能只由单一镜头来完成。关键是双方所指的“写实”、“真实”是一种什么意义中的写实、真实。在两种理论的背后,实际上深藏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观,即蒙太奇派更强调电影的“假定性”及其幻觉和造梦功能。而前苏联蒙太奇派,则是通过蒙太奇技术来假定出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真实和梦境。长镜头理论的哲学,却是从现象学的现实主义到转向存在主义的现实主义。这在巴赞称赞雷诺阿偏爱深焦距和长镜头运用时已有明确的回答。他认为雷诺阿发现了电影形式的奥秘:“它能让人明白一切,而不必把世界劈成一堆碎片;它能揭示出隐藏在人和事物之内的含义,而不打乱人和事物所原有的统一性。”(注:见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第80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所谓“揭示出隐藏在人和事物之内的含义”,不就是人与事物间的存在关系,亦即海德格尔所言之“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敞开了存在者的存在”?(注: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第5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实际上真正与“现象学”贴得更近的是另一位“长镜头理论”的捍卫者克拉考尔,他曾明确提出电影应实现“物质现实的复原”,起到“拯救”的作用,在宗教意义上找到自我。这无疑与胡塞尔现象学提出的,从感性经验返回纯粹现象的“想象的还原”如出一辙。而且胡塞尔也认为,还原的意义在于要求一个个人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和宗教的皈依相提并论,而且甚至不止于如此,它具有期待人类的、最伟大的存在性皈依的意义”。(注: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第47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然而,克拉考尔虽与现象学有共同点,但真正影响他的更为直接的哲学观仍是存在主义,或者说象巴赞一样,都由受现象学的影响开始,而后又不知不觉地转向存在主义了。他的那句名言:“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往往被人们误解为他不承认电影是一种艺术。但实际上虽说克拉考尔似更显得比较极端,以致于因片面强调电影的写实属性,结果反造成按他的评价系统几乎不存在一部能称为“电影的”电影的悖论。但他认为电影的特性不仅是纪录,而且是揭示现实,指出电影与戏剧的根本不同是,戏剧要受到特定空间的束缚,而电影可以表现偶然的、含义模糊的生活流,这无疑是合理的。他认为《圣女贞德的受难》是非电影的,尽管此说明显偏颇,但他批评说:“《圣女贞德的受难》避开了历史片所难以摆脱的困难,那只是因为它抛掉了历史——利用特写的摄影美来抛开历史。它的情节是在一个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的无人地带展开的。”(注:《电影的本性》第100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尊重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它提醒人们不能为了追求猎奇和利润,将历史歪曲为非历史。在今天强调电影的娱乐性、商业性时,返观此说,不也有着一定的警示作用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极力推崇写实主义美学的背后,却隐伏着一种强烈的反异化情绪,在他的《电影的本性》的“尾声”部分,克拉考尔提到了电影的社会目的性,“不难看出,克拉考尔指出了西方精神文明的退化和衰败……特别是在个人与所在社会发生异化(alienation)的条件下宗教信仰的丧失”。而且,他争辩说:“西方精神文明衰败的主要原因是科学发展的结果。”(注:见[美]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第6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这与海德格尔、雅斯贝斯等存在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海德格尔就曾坦言道:“现代科学与极权国家都是技术的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技术的随从……归根到底是要把生命的本质本身交付给技术制造处理。”(注: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第5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而且,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带有一定反科学主义色彩的存在主义理论,在今天的电影艺术,乃至其他各种现代的、或后现代的艺术样式中也仍时有反映,而且,也绝非毫无道理。换言之,“长镜头理论”所倚重的写实主义,远非只是反对形式主义或技术主义,他们更反对的是逃避和歪曲现实,他们同存在主义者(也包括现象学哲学家)一样,认为艺术是存在和真理的一种表现模式,对于现实只有敞开,真理才能自行在作品中显现。它不需要分析,也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只要把存在者的存在从遮蔽状态中显示出来,真理也就“自行置入”于作品中了。正因为这样,巴赞在评论法国导演拉莫里斯的《白鬃野马》和《红色球》时才一再指出,《白鬃野马》中用特写镜头描写马,把脑袋转向那孩子以表示已经驯服于他,拉莫里斯必得在前一镜头中把两个主角拍摄在同一画格里,而在《红色球》里,摄影机也把一只会跑的汽球与小狗和小狗的主人拍摄在同一镜头里,如将这些分成几个镜头,那么观众就不会相信那是真实的。这看起来似乎有点死板,但其目的,正是为了表达通过一个长镜头来显示真理的“自行置入”。总之,长镜头理论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观念、一种理论,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长镜头”本身,如果没有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哲学转化,它也无法构成一种观念,以至为后来各种流派所重视。所以,长镜头理论绝非简单地等同于写实主义,它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和哲学背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镜头理论的出现,是西方哲学思潮由现象学向存在主义转变在电影上的具体反映。
二、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的互相渗透
人们在谈论20世纪40至50年代中叶的意大利优秀电影时,都称其为“新现实主义”,而在讨论法国“新浪潮”电影时,又称之为现代电影。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二者在许多观念与技术处理方面都是极为近似的。首先,二者都强调电影的纪录本性,都要求真实、自由和民主地反映现实,都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都反对弄虚作假,粉饰太平,而且都高度重视长镜头、景深镜头的运用,强调不能任意切割完整的时空,要“尊重感性的真实空间和时间”,并都对电影走出摄影棚,走出戏剧空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更有趣的是,“新现实主义”电影为巴赞电影理论继让·雷诺阿后,找到了更多的创作实证。而“新浪潮”的导演们客观上都将巴赞视作“精神之父”。它们的区别,除了国家的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外,从艺术上讲,大概可作如是分析:“新现实主义”注重内容上的更新,维斯康蒂就明确指出:“新现实主义首先是个内容问题。”(注:见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第8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这与战后意大利人强烈的反法西斯情绪和要求,以及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的不满和反抗有着直接联系。而法国“新浪潮”、“左岸派”,虽也要求真实地反映和揭露资本主义的痼疾,但实际上更强调个人化、个性化表现,“作者电影”观念的出现,即是最好的证明,特吕弗在那篇被看作“新浪潮”宣言的文章——《作家的政策》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在我看来,明天的电影较之小说更具有个性,像忏悔,像日记,是属于个人的和自传性质的。”(注:《弗·特吕弗其人其作》,《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表现形式上,“新现实主义”更倾向于真实的“反映”,而“新浪潮”则着力于“表现”真实。但就哲学基础分析,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将现实主义原则和创作方法与存在主义意识相互作用,并使之揉和在一起,但所取角度有所不同。
“新现实主义”电影无疑是“长镜头理论”的自觉实践者,它们的现实主义性是不言而喻的。柴伐梯尼早就说过,电影要更直接地注意各种社会现象,“把我们认为值得表现的事物,按照它们的日常状态(我们不妨称之为它们的‘日常性’),尽可能充分而真实地表现出来”,(注:《电影理论论文选》第120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年版。)并提出了“还我普通人”、“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等口号,而且的确也如此实践着。维斯康蒂在《大地在波动》中就率先拍摄了大量日常生活过程乃致细节,利用深焦距镜头的表现力,将男人们捕鱼、卖鱼、聊天、喝酒,女人们操持家务等画面真实地再现于银幕。而且片中没有一个专业演员,都是当地的普通渔民,对话也是即兴的随意的。人们往往因它的票房不高和气氛过于沉闷而指出该片的局限性。但许多人不理解维斯康蒂的用意,是想说出真实生活所深寓着的悲剧性。而这正是早期存在主义的一个主要论点:“悲剧的本质也就是展现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注: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第52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雅斯贝斯就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悲剧。所以首先是真实地展示,而不是粉饰它、遮掩它,因为“在人面临悲剧的时候,他同时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这是获得净化和救赎的一个方式。”(注: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第524-5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这不啻又使我们联想到巴赞理论中的人类文化学本体意义,他认为电影是以影像来捕捉生命,保存生命现象的,所以巴赞既反对爱森斯坦式的“理性蒙太奇”——思想意义是影像叠加后被抽象出来的;也反对好莱坞电影中的“分析性剪辑”,它同样把现实世界弄得面目全非。他欣赏让·雷诺阿的作品,让摄影机跟着生活转动,不仅不重视明星,而且要求直接在生活中挑选演员,并可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他的《母狗》、《幻灭》、《游戏规则》等作品都体现了这种风格。通过写实和讽刺,让影像自己对社会现象作出分析和揭示,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人生问题。所以“长镜头理论”主张借助摄影机将一定视野内的人物与景物关系,以及人的命运都如实地收入画框,以保持时空的客观真实性。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更是倡导不要人为的修饰、加工,强调采用实景和自然光,其主将罗西里尼、柴伐梯尼等,都公开表示最反感的正是好莱坞电影。“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罗马11时》都是根据真实新闻拍摄的,所以它们能以其绝对的真实性而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偷自行车的人》中安东的扮演者本身就是一名失业工人,影片中,自行车被偷就意味着重新失业,无奈之下,安东只有去偷别人的车,却不幸被抓住,又当着儿子的面蒙受羞辱。这固然是安东个人的悲剧,但其画面影像却点出了“穷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偷窃”这一社会悲剧主题。同样,《罗马11时》也是通过逼真的楼梯坍塌,反映了意大利严重的失业问题。那么谁是悲剧的罪魁祸首呢?这些引发人们思考的现实问题,恰恰实现了雅斯贝斯所讲的:“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事物;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注:转引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第52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浪潮”、“左岸派”所接受的是后来发展了的、更为个人化的存在主义思想,因为那时存在主义自身已发展到了萨特的时代。“新浪潮”电影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结构,以表现生活流、荒诞、非理性、反传统而闻名于世。特吕弗的《四百下》,通过一系列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桀骜不驯而又沉默寡言的少年安托万的种种经历,他逃学、游荡,无所事事地虚掷时光。从家里出走后,偷了一瓶牛奶,特吕弗不间断地拍摄饥饿的安托万喝奶的全过程。结尾时,安托万从教养院逃出来,穿过农舍、越过田野和空房子,最后奔向他从未见过的大海。在这里,长镜头显示了它潜在的表意性,一连串完整动作“自动”地揭示出“存在”其实是一种孤独,是一种孤独的体验,存在本身就是荒谬的。而人所追求的,正是萨特所言之“绝对自由”。这不由使人想起萨特自己的名作《作呕》,作品中的洛根丁无目的地进出图书馆、按字母顺序翻资料、跟老板娘调情、在公园里游荡,最后被一种“作呕”感所抓住,对人生的价值、人类的理性发生怀疑。安托万这个角色很大程度上带有特吕弗的自传色彩,他后来又以安托万为主角,拍摄了《二十岁的爱情》、《偷吻》、《夫妻之间》、《飞逝的爱情》,可见其对这一形象的重视。特吕弗是巴赞发现并一手培养起来的,也是巴赞“长镜头理论”的积极实践者。直至1975年,他在《阿黛尔·雨果的故事》中,仍注入了许多存在主义式的思考。影片力图再现法国著名文豪维克多·雨果小女儿的爱情故事——阿黛尔从欧洲前往加拿大找寻自己的情人,一个爱尔兰军官,本望能与他成婚,不料却遭到拒绝。她因此郁郁寡欢,以日记为伴,固守自己的一份挚爱,最后神经失常。这实际上也是用电影手段在阐释着萨特关于“自由”的论述:“一个人不能一会儿是奴隶,一会儿是自由人,因为他是完全地而且永远地自由了,要不然就根本没有他存在。”“我们被判处了自由这样一种徒刑”。(注:萨特《存在与虚无》见《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至于大名鼎鼎的戈达尔,则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存在主义迷。他实际上是一个以巴赞的理论来反映存在主义的革命性的电影语言大师。他的代表作《精疲力尽》可以说是对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化解说。影片中男主人公的冒险、我行我素、偷车、抢劫、打死警察、与女人厮混等,均无任何明确的动机,连与他同居的帕特丽夏,先把他出卖给警察,接着又催促他逃掉,也无任何动机可言,一切都似乎是心血来潮,随心所欲的结果。片中,戈达尔在充分运用“长镜头”的同时,又掺入了“跳接”,从思想内容到形式翻新都显示出他的探索性、前卫性。这里,既体现了萨特的“自由选择”,也在演绎着所谓“他人即地狱”的故事,这在《狂人彼埃罗》中也有相同的表现,所以,连萨特本人也对他赞赏有加:“戈达尔之所以对文化有着持久的号召力,原因就在于他自己没有号召——在戈达尔的影片里学问太多了,而表现在戈达尔身上却太少了。”(注:转引自《西方电影艺术史略》第19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而且,戈达尔时而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时而说自己是“存在主义者”,时而又对中国的“文革”十分感兴趣(1967年拍摄了《中国姑娘》)等,也与萨特本人观念的转化十分类似。“左岸派”电影无疑也是存在主义思潮的产物,同时它们又自我标榜为现实主义的,且在关于“存在”的思考中又加进了更多精神分析学因素。《广岛之恋》不断将回忆、幻觉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把性爱与战争串联起来,让人们在看着法国的景象时,听到的却是广岛的声音。整个片子既是“反战”的,又是对现代爱情的反思:从赤裸的身子到坦诚的交谈,一切都敞开着,肉体是赤裸裸的,灵魂也是赤裸裸的,没有任何遮蔽和掩饰。女主人公的讲述、回忆过程,看来是痛苦的,但敞开本身又是一种幸福。电影以长镜头、组接加闪切的手法,表现了人内心的矛盾,也表现了内心的诗意。让观众去思索,女主角究竟爱的是谁,抑或两个都爱?战争是不幸的,但过去无法摆脱,以显示人在“在”中的进退两难。《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同样借女郎A与一个从不相识的男子X,由拒绝承认他们曾相爱过,到最后抛弃自己的情人(或丈夫)M,而同X私奔,来对观众提问:“她究竟是谁?为什么来这里?她爱上了谁,她要的是什么?”言下之意,弦外之音,不也在暗示着每个观众都可以自问:“我是谁?我要的是什么?”从而反映了人的复杂性、偶然性,以及海德格尔讲的人的焦虑、烦、畏,人自一生出来就处于一种“被抛状态”。同样将现实与存在主义思考交织在一起的影片,还有诸如《长别离》、《印度之歌》、《远离越南》、《卡车》等等。其实,西方现代电影后来的发展和变异,也始终未完全脱离这一轨迹,只是注入了更多的精神分析法,如性、恋母情结、无意识等等。总之,在“长镜头理论”的背后,始终深藏着20世纪哲学演进的逻辑,其更深层次的思想,不仅仅只是现实主义,而是西方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思潮不断变化的互渗。所谓“新现实主义”,这个“新”尽管有各种注解,但《大英百科全书》却认为,“新现实主义运动”表现的是人类对生存的四个基本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即(1)反对战争及由此而生的政治混乱;(2)反饥饿;(3)反对贫困和失业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困境;(4)反对家庭的解体和堕落。而“新浪潮”和“左岸派”,则在反对的同时又告诉人们:这一切都无法避免,“存在的偶然性”是自在无法把握的,而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人存在的本质”就在于他的自由,“人注定是自由的”。(注:萨特《存在与虚无》见《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三、后存在主义、后精神分析与当下的西方电影
承前所言,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的互渗,始终维系着西方电影的发展史。然而,现代主义电影和当下的后现代电影又都不断掺入了各种精神分析模式。自有现代电影以来,从弗洛伊德到荣格,再到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就不断地影响着西方电影的叙事内容、结构形式和影像话语。正如有人已经说过的那样:“通过拉康,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已共同进入到存在主义阵地。”(注:王志敏:《电影美学分析原理》第6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但这样一来,给存在主义也打上了“后”的烙印。如“本我”、“力比多”、“转移”、“无意识”等,都成了后存在主义分析的当下话题,甚至源头。为此,连萨特也认为拉康的“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的论断是很深刻的。(注:王志敏:《电影美学分析原理》第60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而恰恰正是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在电影哲学倾向上的结合上,才进一步促成了“长镜头”与“蒙太奇”的相融,不仅使二者理论的对立得以消解,而且在以后的电影中,处处显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事实上,在60年代的电影中,这一现象就已经初露端倪。如在安东尼奥尼的《奇遇》中,错乱的人物关系和显得有点离奇的情节,形成了一个日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爱的沙漠”,实质是一种后存在主义式的追问——爱还存在吗?《蚀》片中,维多莉娅和彼埃罗等人的恋情,短如一次日蚀,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隔膜,这不正是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所言之“从我存在的时候起,我就在事实上对‘别人’的自由设定了界限”?(注:萨特《存在与虚无》见《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在《夜》中,女主人公莉迪娅离开丈夫的宴会后,在米兰市区、郊区缓慢地、无目的地徘徊,一个男人与她擦肩而过,两人互相望了眼……凡此等等,都在说明着莉迪娅内心的烦躁不安。在《红色沙漠》里,朱莉娅娜因一次车祸受到强刺激而失去了心理平衡,她对周围的一切产生了病态的恐惧感,神思恍惚,无法驾驭自己。丈夫、儿子、情人对她的爱都无济于事,她内心空虚孤独,尤如一片沙漠。这些都典型地体现着自海德格尔、萨特以来,存在主义一再强调的现代社会使人产生孤独感和空虚感,人失去了精神家园,一切都成了无根的浮萍!如是,我们还能从法斯宾德的《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中,看到他采用间离效果来提醒观众去专注于“读解”传统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在《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中,看到“灵”与“肉”的分离,既是一种当下的事实,又是一种必然的毫无出路,玛丽亚尽管一直自欺欺人,但她的精神支柱最终还是倒塌了。今天,在许多西方电影中,后存在主义与后精神分析紧紧扭结在一起,一如“长镜头”与“蒙太奇”一对冤家喜结良缘似地无法拆解。如在美国电影《骗子》中,罗伊和其母莉莉都是骗子,片中充斥着混乱的私生活,卖淫、乱伦、赌博,母亲为了钱愿与儿子作爱,儿子退缩了,无意中母亲杀死了儿子,这种精神陷于狂乱的状态,似乎正是萨特“存在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外形”(《作呕》)的演示。影片《不准掉头》里,失意的波比因汽车坏了,只得转入一个沙漠小镇去修理,结果却走进了一条充满着欺骗、性冲动、乱伦、凶手的不归路。波比的种种经历都与他本来的想法相冲突,一切都是偶然的,突发的,这也自然而然会令人想起《作呕》中的那句名言:“我的存在是偶然的”,“任何偶然性不是一种假象,不是一种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衣;它就是绝对,因而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萨特《存在与虚无》见《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在日本电影《失乐园》中,两个婚外恋的异性,既真诚地相爱,有着强烈的性要求,又无法面对现实,公开他们的隐情,最终双双服毒后,在作爱的高潮中死去。不也正是萨特“死亡哲学”的一种注脚嘛?同样,影片《西尔玛与路易丝》,讲述了一个关于性、酒、摇滚乐与公路的当代道德故事,这部女权主义公路片强调的是所谓两性之间的战争,但最终还是以选择死亡而告终。尽管尖锐地指出了女性的反抗,却仍无法回避存在主义所宣扬的苦闷、孤寂与绝望。就象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言:“只有死才排除任何偶然的和暂时的抉择,只有自由地就死,才能赋于存在以至上目标。”(注:萨特《存在与虚无》见《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当下电影中的后存在主义,无疑是后现代的产物。所以,后存在主义与过去的存在主义的最大差别在于,它在更加强调偶然性的同时,又强调它的“非真实化”(derealization)。“非真实化”的始作俑者也是萨特,只是它比存在主义的其他术语更贴近后现代社会。诚如弗·杰姆逊所言,萨特所发明的“非真实化”,在后现代社会中与“形象”直接联关:“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里,形象也是有着同样的非真实化的效果。尽管它很忠实地复制出现实,但也正是在这种复制中,形象将现实抽掉了,非真实化”了。(注:[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2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例如在《美国丽人》中,正经历着中年危机的男主人公厌烦了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与从事房产交易的妻子也渐渐疏离,却被女儿的好友、一中学女啦啦队员迷上,并对她产生了性幻觉。他辞去工作、健身,想能一亲少女之芳容,但到最后才发现他所追求的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影。阿尔莫多瓦电影中的人物,总是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和边缘化特征,剧中角色大多是同性恋者、变性者、精神病人、影视名星、斗牛士、妓女、吸毒者等。如果仅从影像表面看,似乎都是些“问题人物”,不道德的性生活,以及各种忌妒、报复、犯罪等现象,如在《欲望的法则》、《神经近于崩溃的女人》、《关于我的母亲》一类影片中,都可找到由那些后现代的“非真实化”影像所引出的多重伦理道德问题。他夸张地让同性恋现象在电影中暴光,正如他自己所言:“为了使讽刺性幽默的夸张在它原来的同性恋范畴外得以使用,你必须赞美它,无节制的应用它。”(注:[美]马莎·帕莉:《激情的政治:佩德罗·阿尔莫多瓦与讽刺性幽默美学》、《佩德罗·阿尔莫多瓦谈自己的创作》,《当代电影》2000年第3期,第63页。)而实际上,阿尔莫多瓦从小感兴趣的电影就几乎都与“长镜头理论”和存在主义哲学直接相关。他说:“我观看了法国‘新浪潮’电影崭露头角时的影片,有特吕弗的《四百下》,戈达尔的《精疲力尽》。我还看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伟大影片……这些影片令我记忆犹新。……我感到它们所揭示的世界与我是那么接近。”(注:[美]马莎·帕莉:《激情的政治:佩德罗·阿尔莫多瓦与讽刺性幽默美学》、《佩德罗·阿尔莫多瓦谈自己的创作》,《当代电影》2000年第3期,第57页。)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下西方会出现这么多揭示各类社会问题的探索片。当然,不仅仅只是后存在主义,还有后精神分析与之相互作用,而它们间的合流与一起进入后时代,正是后工业社会所引起的后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尽管“长镜头理论”作为一种力主写实的电影美学,其高峰期早已过去,但潜藏在它背后的哲学基础却并未随之而消歇。相反,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后存在主义与后精神分析结合得更为紧密。而且,这种结合本身已体现为现实主义的一种新的样式,也使长镜头的运用始终保持着它独特的魅力。实际上,这种影响在中国第五、第六代电影中也可寻见其端倪,如在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张扬的《洗澡》、张元的《过年回家》等电影里,一边用了不少长镜头来跟踪拍摄,一边又在提出关于人活着的意义、人的存在价值,以及爱与被爱等人生问题。而它们的指向又都是现实主义的。可以相信,这种由揭示现实与终极关怀,后存在主义与后精神分析的相互纠葛所形成的哲学思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后哲学的多元组合不会消失,且将长期作用着电影乃至其他各种艺术的发展轨迹。
标签:长镜头论文; 现象学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艺术论文; 蒙太奇论文; 萨特论文; 新现实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