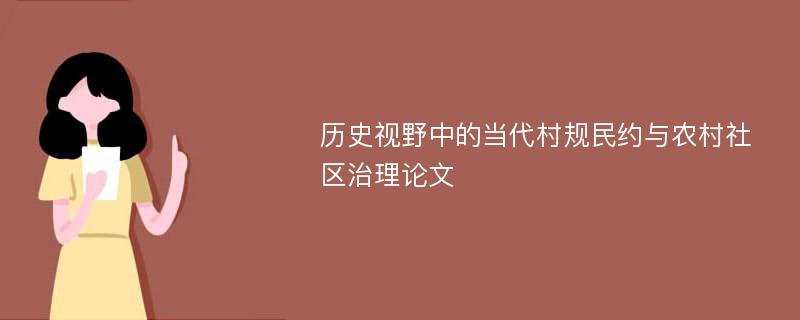
历史视野中的当代村规民约与农村社区治理
陈学金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村规民约肇始于传统社会乡民的一种自然传统,后经由开明士绅倡导,成为基层社会的自治制度,而在另一些时期内,则被皇权所吸纳、改造、强化推行,成为帝国治理乡村的重要手段之一。20世纪80年代之后,村规民约的缓慢复兴过程正好伴随着国家权力从乡村撤出而又重新介入农村建设和治理的过程。作为一种农村治理工具的当代村规民约表现出来的程式化和民主化的趋势实际上反映出当代农村社区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当代村规民约的有效性取决于村庄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民主协商治理,而非过分强调借助于物质上的村民福利作为激励。
关键词: 村规民约;文化;社区治理;人类学
近20年来,伴随着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家对村规民约社会治理积极作用的认定,全国各地探索运用村规民约推进社区治理的实践愈益丰富。与此同时,学界对村规民约的研究也逐渐升温。法学界侧重于讨论村规民约在制定和实施中的正当性、合法性,以及其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冲突与协调问题[1][2];政治学界关注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基层民主的关系;社会学者较多关注村规民约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过程与机制[3];人类学界秉持生物——文化整体观,关注民间社会不同类别规约的自然生态基础与社会文化适切性,着重探讨生态、仪式、权威、文化传统等问题[4-6]。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较多研究者将村规民约理解为农村社区居民共同制定与遵守的约定、规范[7]。譬如,有学者将村规民约界定为“依照法治精神,适应村民自治要求,由共居同一村落的村民在生产、生活中根据习俗和现实共同制定、共信共行的自我约束规范的总和”[8]。将村规民约仅理解为一种规范,显然无法理解其历史渊源,无法理解其作为一种基层自治手段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之间的关联,也无法理解其作为当代社区治理工具的社会文化意义。本文拟先简述村规民约发展演变的历史,论述其在传统中国双轨政治中的角色,然后重点审视20世纪以来村规民约的兴衰过程,阐释被纳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当代村规民约的特征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一、村规民约的历史演进
将村规民约置于中国长期的历史中考察就会发现,村规民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角色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若将成百上千年前的村落视作人们共同居住、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在帝国皇权不能直接到达的地方,那些处理各家户关系、维系某一群体或村落社会秩序的约定俗成的规则、风俗习惯、纠纷解决方式就构成了最初的“村规民约”。
图1中在设备维修更换周期L内,对其开展N次不完全预防性维护工作,以预先设定的可靠度下限R确定各弹性维修周期τi。在前N-1个维修周期内,当设备可靠度降至R时,对其采取不完全预防维修;在第N个维修周期内,当设备可靠度降至R时,进行完全预防更换;若设备在各预修周期内发生非预期故障,则采取应急事后小修。在保证设备高可靠工作的前提下,通过对事后小修、预防维修和预防更换做出合理选择与维修时机安排以优化设备维修费用。
村规民约经过成百上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在北宋年间形成了一套拥有较为完整的组织、管理体系的乡约制度[9]。北宋煕宁九年(1076年),当儒士吕氏兄弟在陕西蓝田推行乡约之时,这是一种典型的在县以下村落推行的地方自治制度。在民族学家胡庆钧看来,乡约是对当时施行的保甲制度的一个反动和补充[10]。它是开明绅士的一种具有乌托邦式的地方治理实践,也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约正的角色由士绅亲自来担任,负责讲解约文,感化约众。吕氏乡约的条款主要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以及罚式、聚会、主事等相关制度。乡约只有约正一至两人,由公认的刚正不阿的人来担任。吕氏乡约特点有四:以乡为单位,由人民公约,可自由参加,有成文法则[11]。但是吕氏乡约缺乏真正的底层基础,其前后维系的时间并不长。
简言之,村规民约是村落社会的产物,经过士绅的提炼,逐步成为地方自治的一种工具。明清之时,经朝廷提倡,逐步加入帝王的训谕内容而演化为御用的工具。也就是说,村规民约本肇始于乡民的一种自然传统,经由开明士绅倡导,在一定时期内,作为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在另一些时期内,则被皇权所吸纳、改造、强化推行,成为帝国治理乡村的重要手段之一。乡约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基层组织形式之一,与保甲、社仓、社学等联系在一起对于基层社会运行发生过重要作用。如学者所论,作为士绅推动的结果,乡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向上、向下两方面的积极效果。向上,经由地方官吏的关注和施政,引起皇权的重视并被纳入到国家制度之中;向下,走向民间和市场,成为民间社会自治的一种重要形式[15]。
自20世纪初开始,国家权力就开始了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改造。一百多年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各种政治运动及国家农村政策的深刻调整,乡村的社会秩序赖以运行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不断变化与发展。
每月朔望日,择宽洁公所,设香案。届时县中文武官俱至,衣蟒衣,礼生唱,序拜,行三跪九叩首礼。兴,退班,齐至讲所,军民人等,环立肃听。礼生唱,恭请开讲,司讲生诣香案前,跪,恭捧圣谕登台,木铎老人跪,宣读毕。礼生唱,请宣讲圣谕第一条,司讲生按至讲毕而退[14]。
从中可以看出,乡约活动只是官方的例行公事而已,早已远离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杨开道所著《中国乡约制度》描述与分析了乡约在中国历代农村社会组织中的发展、演变历程,费孝通则在中国传统双轨政治中进一步考察与分析了乡约制度的角色与功能。杨开道是费孝通最为敬仰的老师之一,费孝通也曾阅读过杨开道先生乡约制度的相关著作,因此费的论述也可以视作杨的论述的延续和深化[16]。
明嘉靖之后,乡约逐步成为正式的国家法令与规条,由官方主导,自上而下,强迫民众参加。后世的乡约逐步加入了圣训或圣谕,乡约逐步成为宣讲圣谕的御用工具。明朝末年,陆世仪(号桴亭,1611-1672年)所著之《治乡三约》一书的理论价值为社会学家杨开道所称道。依陆氏所论,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是一纲三目、一虚三实、相辅而行,相互为用的关系[12]。但是,这套理念并未真正付诸实践,而成了“空中楼阁”。
27 g混合粉→加50 mL水溶解、搅拌→倾注于糊化盘→沸水浴中糊化1 min→冷却→揭皮→切皮→烘箱(50 ℃)干燥4 h→成品
二、双轨政治中的乡约角色
村规民约在发展成为民间的一种自治制度之后,有两个关键问题显得愈发重要。一是如何让村规民约被村民认可并拥有较强的效力;二是如何协调村规民约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村民民约的倡导者们认识到规约公议、村民自愿加入是村规民约发挥作用的基础,一些规约文后还附列首倡者和参约者姓名。同时在条文中约定惩罚、奖赏的内容以提升村规民约的效力。此外,制定和宣讲约文以及实施惩罚、奖励的各种集会和仪式,也可以发挥村规民约的社会教化功能。对于第二个问题,古人已经注意到地方自治规约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区别,社区或族群内部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诉诸于村规民约或道德教化,而对于一些重大违法犯罪问题,则需借助国家的力量予以解决。一些规约中明确一些行为会被“送官究治”,一方面增强村规民约的惩戒性和震慑性,一方面也区分了自治规约与国家正式法律的区别。
萎缩性阴道炎作为常见妇科疾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卵巢功能衰退、阴道壁萎缩和雌激素降低等,同时患者局部的抵抗能力也会不断下降,一旦病菌侵入极容易引发炎症,如果不对其展开及时治疗,也会引起外阴溃疡[1]。基于此,对我院收治的60例萎缩性阴道炎患者采取雌激素联合甲硝唑进行治疗,并观察治疗效果,具体报道如下。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是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士绅阶层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层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表面上,我们只看见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但事实上,一到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在差人和乡约的特别结构中,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绅士可以把压力透到上层[17]。
费孝通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乡村的自治组织是因为某一地方社区的公共需要而自动组织起来的。地方的公共需要包括水利、自卫、调解、互助、娱乐、宗教等,当然也包括应付衙门。乡约就是地方自治的一种组织。同时,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面对面的社群”,乡土社会运行依靠一种文化的礼治秩序,追求息讼,村庄内部的矛盾纠纷往往不需要经过官府便能解决[18]。
事实上,在无为主义的地方政治中,县政府的命令只发到地方的自治单位,负责这些自治单位的董事和管事等地方领袖并不直接和衙门往来,由另一种被称为“乡约”的代表完成。乡约是个苦差,大多有人民轮流担任的,他并没有权势,只是充当自上而下那条轨道的终点。费孝通还生动描绘出乡约在上下勾连中的角色:“他接到了衙门里的公事,就得去请示自治组织的管事,管事如果认为不能接受的话就退回去。命令是违抗了,这乡约就被差人送入衙门,打屁股,甚至押了起来。这样,专制皇权的面子是顾全了。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政治活动也开始了。地方的管事用他绅士的地位去和地方官以私人的关系开始接头了。如果接头的结果达不到协议,地方的管事由自己或委托亲戚朋友,再往上行动,到地方官上司那里去打交涉,协议达到了,命令自动修改,乡约也就回乡。”[19]
一般来说,乡约的领袖称作“约正”或“乡约”,还有几人辅助约正工作,称作“直月”。约正和直月每年都会从公家领取一定的报酬。实际上,杨开道理想中的乡约形式只能在农村举行,要有具备高尚人格与满腔热忱的领袖人物,不需要政府强令举办[20]。起初,乡约的领导者由地方士绅或其他有威望的人担任,当其沦落为官方统治的工具之后,约正担当者的身份和地位都降低了,乡约效能也大大衰减。透过费孝通的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般化论述可知,村规民约这类民间组织机构要发挥作用,必须有地方权威人士出面主持或在背后支持,否则很难发挥效果。
2.2.1 实时监控。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对焊机进行参数设置只占操作工人很少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在焊机的工作状态,实时监控画面是操作人员观看时间最多的画面,因此将监控画面作为整个系统的主画面。
三、 20世纪以来村规民约的制度轨迹
明代的乡约制度完成了从民间性到官方性的转变,乡约由民间的自治组织演变为吏治的工具。清朝历代皇帝表面上都大力推行乡约,但变成了单纯的圣谕宣讲,缺少必要的物质生活基础,而沦为官治的工具[13]。杨开道曾引述同治五年(1866年)《仁寿县志》(四川眉山市)中有关乡约的仪式过程。其中,康熙十六条圣谕和雍正圣谕广训是仪式宣讲的主要内容。
20世纪以来,为加强对农村资源的汲取能力,以及在战争、革命、建设中形成对农民的动员能力,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都加强了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21]。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国家权力已经延伸到行政村,并形成村行政管理与生产合作社合一的“政社合一”的局面。在集体化时代,自然村落的许多传统社会组织由于被认为是封建的、落后的,而变的相对松散、甚至解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之后,为配合农村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改变农村国家权力撤出后的“弱社会”问题,一些地区开始恢复农村的传统社会组织,并制定乡规民约。譬如,1995年出版的《中国农业全书·贵州卷》的相关论述即表明了这种状况。兹作摘引如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加上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得早、来得猛,许多工作没有跟上去,因此,一些农村的基层组织曾一度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涣散;以致赌博偷盗、打架斗殴、买卖婚姻、乱砍滥伐山林等经常发生,严重影响了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广大农民对此很不满意。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各地农民群众纷纷建立自治组织,比如“议事会”“互助会”“寨老会”“议榔会”等;推选作风正派、热心公益事业、有能力有威望的人作为自治组织的负责人。这些群众自治组织调解民事纠纷,兴办公益事业,维护社会秩序,开展文化活动。为了规范大家的行动,这些群众自治组织沿用五六十年代曾在部分村寨采取过的措施——制订乡规民约[22]。
选取2016年12月~2018年1月本院收治的缺血性脑病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均表现偏瘫、失语、偏身感觉障碍等症状。其中,男41例,女19例,年龄52~73岁,平均年龄(62.5±2.5)岁,均行CTA检查,其中15例同时进行脑动脉血管造影(DSA)检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后,乡镇基层政权得以重建。随着国家政治权力从乡村退出,村规民约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重新走向前台。在健全基层党组织的基础上,全国各地逐步建立了具有村民自治性质的村委会。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实施,确定了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朝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方向发展。其第十六条规定,“村规民约由村民会议讨论制定”“不得与宪法、法律和法规相抵触”“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23]。以此为标志,村规民约被国家法律制度正式吸纳,成为农村自治的工具箱中工具之一。199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加了村规民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加注重国家法律政策的权威,规定“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遵守并组织实施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24]。
201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2018年12月,民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文明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全国妇联等7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推动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村规民约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意义不断得以凸显。上述政策文本是村规民约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中发挥功能的法理依据。可见,当代村规民约已经是当代中国乡村振兴和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部分了。
东海海鲜不是跟每一款油都对路,花生油、菜子油等香味较浓的油脂烹制海鲜会显得过于油腻。豆油的豆腥味明显,也不适合烹海鲜,清爽剔透的橄榄油最适合东海小海鲜。
四、作为社区治理工具的当代村规民约
近年来,村规民约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为“柔性的治理方式”,可以配合国家“硬法”,填补基层农村的法治洼地[25]。也有研究者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施行“法治双轨制”,灵活运用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民间智慧,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创新[26]。当代村规民约之所以能够被吸收、改造成为农村治理的工具,主要在于中国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社会学家张静认为,国家进入乡村秩序有“立法进入”和“仲裁进入”两种方式。在中国农村多属于第二种情况。国家对农村的特殊制度安排,使得基层组织在选择执行国家规则方面有相当程度的选择空间。基层组织对村民身份的确认,是村民获得选举权力、集体收益和福利的基础[27]。而村规民约正是确认村民资格的重要机制之一,而这也正是当代村规民约可以作为农村治理工具的制度性条件。从村民的角度而言,大多数村民遵从村规并在集体事业中履行自己的职责,是因为这些安排比外加的制度更能令他们受益[28]。村规民约作为一项书面签约的村庄正式制度,可以以其规范条例确定个体对村集体的归属关系,从而促进村庄的社会整合[29]。
当代村规民约已不能完全等同于传统的约定俗成的村落或民族的习惯法。当代村规民约是国家正式法律和政策所倡导的一种社区治理方式,它是在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针对集体公共事项民主讨论、协商,制定规范并实施的一系列组织和过程。作为社区治理工具的当代村规民约是一种建立在同意权力基础之上的契约,契约规定了个体应履行的责任和应获得的权利。其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基础在于村庄的每一家户的知情和同意。
笔者在2017-2018年对华北农村不同类型村庄进行田野工作时发现,村集体拥有资源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村规民约的风格。一种是强资源的管制型,另一种是弱资源的民主型。一般来说,村集体有较多资源(如拥有集体企业、有集体土地收益或厂房出租收益等)的村庄往往会导致一种管制型的村规民约,即相对硬性规定村民必须遵守某些规范,否则就不能享受福利待遇,甚至一些需要村委会盖章的事项都不能得到批准。一些相对贫困或者集体资源较少的村庄,在制定和实施中则会更加注意关注党员、村民代表、普通村民的意见,以获取大多数村民的支持。在很多村干部看来,村庄缺少物质资源,就没有办法调动老百姓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调研发现,凡是利用村规民约有效推进社区治理的村庄,也大都是上级政府眷顾的项目村或试点村,这些村庄往往能获得比其他村庄更多的项目资源。这种现象实质上反映出村规民约制定和施行中的一种物质化倾向,即认为,缺少物质资源,制定村规民约也没用;施行村规民约,必须要有物质激励。
与此同时,一些取得成功的村规民约呈现出一种民主化和程式化的特征。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规范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程序,提出了“三上三下”模式[30]、“三下三上”模式[31],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但是细心的研究者会发现,上述两种成功模式的内在精神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原有之义,只不过是按照其要求,民主、有序、法治性地展开而已。在笔者的调研中,并非每一个乡镇都要求各村庄制定村规民约,也并不是所有的乡镇要求各职能部门提出指导各村村规民约的意见。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村规民约要么是一种未成文的、非官方的形式在村庄发生作用,要么就根本没有被作为治理工具而使用。而在那些将村规民约应用得较好的村庄,则势必按照民主和一套明确的程序展开,以显示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当代村规民约呈现出的民主化和程式化的特征其实正好应和了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国家以及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的同时,一些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这种转型集中表现在农村人口生计方式多样化、人口的高流动性、居住格局的老龄化、传统社会组织解体、个体化的思想观念形成等方面。这是新时代农村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现实背景,同时也是村规民约发生功能的现实条件。可以说,正是农村社区发生的这种社会文化转型,使得当代村规民约若想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借助于程序正义、内容合规的法理权威。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一些地区强制性地在乡村推行村规民约时,村规民约成为基层政府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约束个体行为的工具。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表明,在普通村民那里,村规民约是“村干部写下来给上面的人看的,实际上没有什么作用”[32]。最近几年的农村实践中仍旧出现的村规民约“上了墙却落不了地”的尴尬[33],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村庄只是表面上应上级要求制定村规民约作为以法治村的依据,而实际上村庄干部并未将村庄民主自治作为一项重要目标,他们也不想借助村规民约的制定与实施而获得某种程度的“法理权威”,或许他们感到自身并不缺少合法性的权威。
五、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村规民约的再次兴盛,实质上起源于农村传统礼治秩序的衰落以及国家行政力量对于村规民约积极作用的大力倡导。村规民约作为一种民间社会的传统文化资源,已经被整合进国家治理策略中,从而作为一种社区治理工具而存在,为实现农村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服务。在此意义上,当代村规民约已不能完全等同于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的民间习俗或习惯法。村规民约是处理某一村庄集体公共事务的约定型规范,在这一点上,既不同于国家法也不同于私人契约。因此村规民约的正当性和效力,源自于村集体中每个家户在讨论、协商、谈判基础上做出的同意或合意允诺。因此,当代村规民约的有效性在于村庄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民主协商,而非过分强调借助于物质上的村民福利作为激励。
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农村地区范围广,自然生态与人们的生计方式多样,呈现出一种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相互交织的复杂多元局面。现代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建立,乡土社会身处一种急剧的转型过程之中,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层出不穷。此外,还要特别注意不同农村地区经济方式发生的转变,以及现代法律观念、城市矛盾纠纷解决方式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对农村社区居民思想观念及社会实践的影响。因此,在当代,惟有分析特定地域的社会文化土壤(包括生态基础、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及各种典章制度、包括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内容)[34],以具体的和棘手的问题为导向,充分尊重和调动村民的主体性,通过程序正义建立起村庄内部的“法理权威”,借助村规民约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才有可能。
在涉及的体育项目中,从观众的选择倾向来看,排序分别为足球(55.3%)、篮球(47.8%)、乒乓球(35.6%)、游泳(28.6%)、羽毛球(16.5%)。从观众的消费动机来看,位于前三的是“支持型”“兴趣型”和“娱乐型”(如表3所示)。从观众的消费行为来看,排序分别为与朋友一同观看(65.2%)、与家人一同观看(23.2%)、独自观看(11.6%)。
除了上述因素外,还要注意重量,透明度和净度等。天然宝石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购买时就必须要注意取舍。
参考文献:
[1] 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C]//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15-480.
[2] 戴小明,谭万霞.论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及整合[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12-18.
[3] 周家明.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4] 徐晓光.苗族习惯法的遗留、传承及其现代转型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5] 赵旭东,周恩宇.“榔规”运行的文化机制——以贵州雷山甘吾苗寨“咙当”仪式为例[J].民族研究,2014(1):71-77.
[6] 徐晓光,杜晋黔.华寨的“自治合约”与“劝和惯习”[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2):65-71.
[7] 马敬.村规民约在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J].学术交流,2017(3):126-130.
[8] 张广修,张景峰,等.村规民约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30.
[9] 董建辉.“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51-58.
[10]胡庆钧.从蓝田乡约到呈贡乡约[J].云南社会科学,2001(3):41-45.
[11]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68-86.
[12]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74-175.
[13]董建辉.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300-304.
[14]同治仁寿县志·卷4·礼教志[M]. 同治五年(1866)刻本.
[15]刘笃才,祖伟.民间规约与中国古代法律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00-101.
[16]费孝通.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67-68.
[17]费孝通.乡土重建[C]//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0.
[18]费孝通.乡土中国[C]//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08-188.
[19]费孝通.乡土重建[C]//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9-40.
[20]董建辉.中国乡村治理道路的历史探索——杨开道及其《中国乡约制度》//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52.
[21]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政治学研究,2000(3):61-69.
[22]《中国农业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全书·贵州卷[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319-320.
[23]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87-1988 第8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9.
[2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七号[EB/OL].(2010-10-28) [2018-08-29].http://www.gov.cn/flfg/2010-10/28/content_1732986.htm.
[25]袁日晨.以村规民约为抓手创新基层协同共治[J].前线,2016(9):77-78.
[26]杜鹏.“法治双轨制”:我国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惠机制——以侗族款约法为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2):79-85.
[27]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增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3-85.
[28]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M].岁有生,王士皓,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297.
[29]周怡.共同体整合的制度环境:惯习与村规民约——H村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6):40-72.
[30]中江县富强村:以村规民约为抓手 推进基层法治建设[EB/OL].(2014-03-18) [2018-08-29].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4/03/18/013926624.shtml.
[31]中国组织人事报.北京顺义区:“三下三上”完善村规民约[EB/OL].(2015-08-26) [2018-08-29].http://www.zuzhirenshi.com/dianzibao/2015-08-26/5/5b923364-1ac4-4011-bc4f-61550bca1699.htm.
[32]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308-310,322-323.
[33]李浩.村规民约上墙了,更要“落地”[N].安徽日报,2018-05-04(7).
[34]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86-87.
On the Contemporary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EN Xue-j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 100101, China )
Abstract : The village regulations started with a natural tradition of the villagers in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which were advocated by the enlightened gentries, and became the self-government system of the local societies. In other periods, it was absorbed, reformed and strengthened by the imperial power, and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the imperial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side. From the 1980s to the present, the slow revival process of village regulations coincided with the process of state power withdrawing from villages and re-intervening in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As a tool of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trend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contemporary village regulations reflect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rural communit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temporary village regulations depend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village achieves democratic governance rather than on the excessive emphasis on the material welfare of villagers.
Key words : village regulations; culture; community governance; anthropology
收稿日期: 2018-09-27
基金项目: 2017 年北京“高创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2017000020044ZS07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研究项目“传统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过程的人类学研究”(2018B503 )。
作者简介: 陈学金(1982- ),男,北京通州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1X(2019)02-0069-06
[责任编辑:吴才茂]
标签:村规民约论文; 文化论文; 社区治理论文; 人类学论文;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