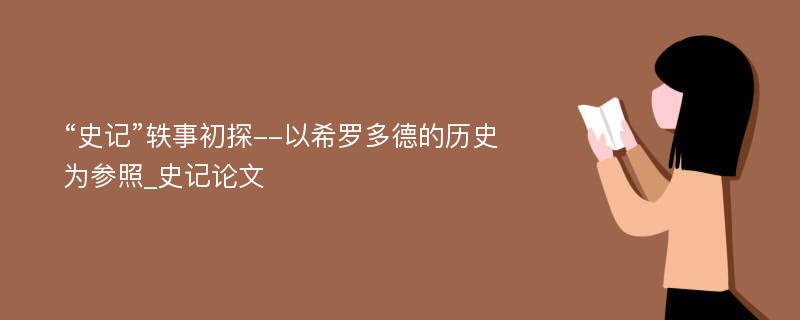
《史记》中的轶事初探: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轶事论文,多德论文,希罗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西方两位伟大的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前425)和司马迁,在过去常常被相提并论。① 毫无疑问,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希罗多德的《历史》所涉及的范围仅局限于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冲突上,而司马迁的《史记》却是对从上古至他所处时代所有已知历史的记录——但是其相似性也是惊人的。两人作品中的大量材料都是在广泛的游历中通过与他人的对话搜集而来,此外,他们的创作动机也极其类似。希罗多德在其作品的第一行就提到“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② 司马迁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在自序中承认“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并于第一篇列传里总结说:“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土,恶能施于后世哉?”
然而,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讨论哲学层面的创作动机,而是在于分析这两部伟大史书的具体结构,特别是它们对轶事的使用,因为轶事实际上在这两部书里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希罗多德向读者呈现的第一个人物是吕底亚的统治者克洛伊索斯,他注明这样的安排只是因为“据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克洛伊索斯在异邦人中间是第一个制伏了希腊人的人”。在寥寥数语的描述后,希罗多德又用几句话简单回顾了在克洛伊索斯之前的统治者——曾经统治吕底亚达505年之久的赫拉克列斯的后代。随后希罗多德放慢了叙述节奏,讲述了一个关于王位继承的奇怪的故事来娱乐读者。故事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第1年吕底亚的首都萨尔迪斯,③ 那时的国王是坎道列斯,他“宠爱上了自己的妻子”,这在古代西方的王室成员里并不常见。希罗多德接着写道:
(坎道列斯)把她宠爱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认为她比世界上任何妇女都要美丽得多。在他的侍卫当中有他特别宠信的一个人,这就是达斯库洛斯的儿子巨吉斯。坎道列斯把所有最机密的事情都向这个人讲。既然他对于自己妻子的美丽深信不疑,因此他就常常向这个巨吉斯拼命赞美自己妻子的美丽。在这以后不久的时候,终于有一天,命中注定要遭到不幸的坎道列斯向巨吉斯这样说:“巨吉斯,我看我单是向你说我的妻子美丽,那你是不会相信的(人们总不会像相信眼睛那样地相信耳朵的)。你想个什么办法来看看她裸体时的样子罢。”巨吉斯大叫着说:“主公,您要我看裸体时候的女主人么?您说的这话是多么荒唐啊。您知道,如果一个妇女脱掉衣服,那也就是把她应有的羞耻之心一齐脱掉了。过去我们的父祖们已经十分贤明地告诉了我们哪些是应当做的,哪些是不应当做的,而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古人的这些教诲。这里面有一句老话说,每个人都只应当管他自己的事情。我承认您的妻子是举世无双的丽人。只是我恳求您,不要叫我做这种越轨的事情。”
但是在坎道列斯坚持下,巨吉斯被安排藏在卧室门的后面,这样他就能看到坎道列斯的妻子脱掉衣服上床的情形。在巨吉斯偷窥成功以后:
他就从房中偷偷地溜出去了。可是,当他出去的时候,她是看见了他的,于是她立刻猜到了他丈夫所做的是怎么一件事,可是,由于害羞的缘故,她并没有叫了出来,甚至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样子,心里却在盘算着对她的丈夫坎道列斯进行报复了。……然而到早晨天刚亮的时候,她便从自己的仆从当中选出了一些她认为对她最忠诚的人来,对他们作了部署,然后派人把巨吉斯召到她面前来。……巨吉斯来到的时候,她就向他说:“巨吉斯,现在有两条道路摆在你跟前,随你选择。或者是你必须把坎道列斯杀死,这样就变成我的丈夫并取得吕底亚的王位,或者是现在就干脆死在这间屋子里。这样你今后就不会再盲从你主公的一切命令。去看那你不应当看的事情了。你们两个人中间一定要死一个:或者是他死,因为他怂恿你干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你死,因为你看见了我的裸体,这样就破坏了我们的惯例。”
毫无疑问,巨吉斯选择了弑君而不是自杀,他“随着王妃进入了寝室。她把一把匕首交给巨吉斯并把他藏在同一个门的后面。而过了一会儿,当坎道列斯睡着的时候,巨吉斯便偷偷地溜出来把坎道列斯杀死了,这样巨吉斯便夺得了坎道列斯的妃子和王国”。④
那位不知名的皇后和巨吉斯之间的对话仍然很程序化,因此几乎没有展现出暴力中任何一人的形象。希罗多德讲述这个故事似乎带着三个目的:第一,这是一个揭示事件起因的情节。他告诉读者,在坎道列斯被杀以后,吕底亚的人民对是否支持巨吉斯作为他们的统治者产生了分歧,最后决定根据戴尔波伊神殿的神谕来宣布巨吉斯是否能够称王。神谕确认了巨吉斯的地位,因此巨吉斯进献了很多金银给戴尔波伊神殿,同时也形成了一项向神殿进献贡品的传统;第二,这个故事取代了一系列描写如何诱拐已婚和未婚妇女的概述,成为了显然最为详细与吸引人的叙述;第三,安排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也许是出于吸引读者的目的,驱使他们带着热情去阅读接下来的八本冗长的《历史》。
《史记》的开篇在某种程度上也运用了与《历史》类似的手法。虽然司马迁在卷一《五帝本纪》里对传说中三位皇帝的叙述远远多于希罗多德对坎道列斯祖先的描写,但是他仅仅关注于黄帝、颛顼和尧作为伟大的教化者的公众形象,对其个人形象或者说个性并没有提供什么细节。而从对第四位皇帝舜的一系列轶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第一次偏离了那些神化远古统治者的创作模式。如同希罗多德在坎道列斯的故事之前列举其先祖一样,司马迁在记录舜的轶事之前也记载了舜的祖先的谱系。⑤
同时,这些轶事关注了舜家庭生活的艰难,这又再次与希罗多德关于坎道列斯私人生活的叙述相对应:
舜,冀州之人也。……舜父瞽叟盲,⑥ 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⑦
因为舜的孝行,皇帝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舜的妻子们对他的父母都很恭敬,舜本人也尽心尽力地服务于尧。于是,
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⑧
在这段记叙里,没有交代的内容可能与已经交代的内容同样意味深长,例如象在舜的居室里与舜的妻子究竟呆了多长时间。清代学者梁玉绳对这种隐含的不合礼仪的描述感到非常困扰并且质疑说:“象居宫,鼓琴,二女何以自安?且是时舜在何处而反往见象耶?”⑨ 而在《孟子·万章》里则记载了由孟子本人讲述的另一种不同版本的故事:当舜的弟弟象进入舜的房间时,舜正坐在房内弹琴。⑩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故事里卧室场景的安排与坎道列斯的故事的发生地点又一次不谋而合。通过展示一部分舜的私人生活,司马迁所塑造的舜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相比于以往传统刻板的人物刻画——仅仅只是描写舜模范般地服务于尧及其人民,这种方法显然更进了一步。在把舜描写成为农民、渔夫,以及自己妻子的榜样的同时,司马迁将若干轶事穿插其中,产生的整体效果是把舜塑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圣人,既展示了他作为公众人物行事无不尽善尽美的一面,也展示了他在私人生活中恪尽孝道的一面,但是这样舜的形象因此也就不够逼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司马迁所创造的弟弟象的形象也许更为逼真。他先让读者偷听到象以为舜被杀死以后的狂喜之言“本谋者象”。接着,读者又听到象对舜说“我思舜正郁陶”来表明自己的沮丧以及对舜的想念,从而试图使舜相信自己。在这个场景中,司马迁进一步地贴近象,让读者去体会象的内心那种局促不安的情绪状态“鄂不怿”(这里再次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吻合:巨吉斯比他的主人坎道列斯的形象更为完善)。
如果说司马迁将孝行等同于统治者对其所统治的人民的尊重和关怀,对舜模范般的个人行为的描写暗示了舜潜在的统治能力,那么他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关于宽恕的次要情节:尽管舜的父亲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屡次把他们邪恶的想法付诸行动,舜仍然对他们非常慷慨大方。
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11)
从这句话看来,《史记》与《历史》里故事情节的对应在这里貌似告一段落——舜采取了完全宽容的态度,而坎道列斯的妻子只追求最残忍的报复。然而,在其他文献关于舜的记载中也可以找到与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复仇情节相类似的内容。《孟子·万章》中万章向孟子询问了一系列关于舜的问题。万章对“象日以杀舜为事”(12) 而舜并没有流放象感到疑惑。尽管孟子以“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13) 作为解释,但万章似乎对接受这一说法显得非常迟疑。虽然认为舜应该严惩象这一想法与司马迁把舜刻画成一个行为温和的圣人的主题相悖,但是却呼应了《太平御览》引用的《尚书》逸篇中的说法“尧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14)(对比《五帝本纪》里的记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史记》卷一,第30页)。所以,“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并不高尚的行为,即舜不过是想要在他父亲面前炫耀他新获得的权力。
不管读者怎样理解原文,这两个关于舜的父亲和异母弟弟如何谋害他的故事给后来的读者所造成的影响,似乎比舜服务民众的圣人事迹更为持久。然而,梁玉绳却认为这两个故事是由战国时期的说客捏造出来的。他评论说:“焚廪,掩井之事,有无未可知,疑战国人妄造也。”(15) 在许多《史记》的“节选本”里,比如吕祖谦的《史记详解》(16),这些故事都被删除掉了。梁玉绳的论点使读者对司马迁所使用的数据的来源产生了疑问。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样,希罗多德和司马迁两人都依赖于广泛游历搜集得来的口头资料。(17) 希罗多德作品的整体结构所采用的蓝本,常常被认为是荷马史诗,即口头诗歌。他将“据雅典人”“据古科林斯人”或者“据埃及祭司”等所说的内容作为对事件或者主题的描述,这种做法一直以来被认为不够严谨而遭到批评。从字面意义看,这样的表达也许暗示希罗多德曾经和“雅典人”或者很可能是雅典的上层人士交谈过,他们之间的对话随之成为希罗多德的直接材料来源……更为可信的理解是,希罗多德通常表示的不过是“这是雅典人的传说”,或者“这是雅典人对事情最普遍的说法”,或者“这个说法来自雅典人”,因此他指向的是社会记忆,即集体意识,他的读者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虽然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过程看起来要比希罗多德复杂得多,但是他同样也是在把各种各样不同传说的片段拼接起来,这些片段既有来自书面的(有时记载于独立的单篇文章中,有时记载于一整部文献里),也有来自口头的(某些是司马迁通过旅行在当地发现的,某些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基础),正如他在《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所说: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18)
这段文字值得仔细阅读。第一处难以理解的表达是“风教”,这个词在《史记》里只出现了一次,它常常被解释为风俗教化。但是,在这里把“风教”理解为风俗教化似乎不太恰当。无论“风教”指什么,司马迁注明“风教”中最可信的是接近经典的那部分。《五帝本纪》涉及的经典大概是指《尚书》,因为一些关于舜的公众行为的记载似乎节选自《尚书》。司马迁接着称“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这里的“说”究竟指代什么?这些“说”是否就是梁玉绳所怀疑的由战国时期某人或者某些人“妄造”出来的内容?“说”无疑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它的所指也许就是口头表述,即司马迁在旅行中所听到的表述。不可否认的是,把“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理解为“我把它们集中起来并排序,选择那些特别文雅的口头表述”只是一种尝试。考虑到《五帝本纪》里重复地告诉读者舜的父亲渴望杀死他这种拙劣的写法,如何理解这句评论还需要深思熟虑。这种重复的安排虽然貌似是将若干书面材料拼凑起来的结果,但是同样也可能说明这些数据本身就是对各种传说的口头表述的记录。
我们在《历史》和《史记》两者开篇所见到的都是作者对轶事的强调。希罗多德把他的作品称为“调查”,收集以前不为人知的事情(轶事的一个定义就是秘密的或者未发表过的事情)。司马迁同样也从他的旅途中收集了很多当地的传说。但是,他不仅对所听到的不同的口头表述进行了权衡甄选,而且也尝试着根据那些在长安他能够支配的档案来核实这些材料。此外,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采用了那些更为使人兴奋的故事来使自己的叙述富有生气,并且尽了最大努力把口头和书面的传说结合起来。
关于《史记》中使用口头资料的问题,可以通过对《殷本纪》篇首几行文字的研究进一步加以探讨。《殷本纪》说: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19)
司马迁笔下的舜的传记大部分来源于《尚书》(除了两则描写谋杀的故事),但是存《尚书》里几乎没有关于契的信息,更没有任何有关他冲话般出生的记载。在《殷本纪》结尾处“太史公曰”的部分里,司马迁再次提及他的资料来源:“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20) 这里,司马迁表明他按照《颂》撰写了契的故事。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现在的《颂》里只有《玄鸟》这一首诗提供了极少的关于契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以最简单的形式出现在《玄鸟》头两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1) 里。因为司马迁只提到他使用了《颂》,所以在他的时代里是否还存在其他关于商朝建立和契出生的书面记录都变得无关紧要。《毛传》提供了一些与《史记》的记录类似的材料:“春分,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22) 因此,对“余以颂次契之事”一种可能的理解是:司马迁根据依附于《颂》的口头传说——可能与《毛传》相似,但不是完全一样——创作了契的故事。这种假设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太史公声称他根据《颂》撰写了契出生的故事,但是在现存的《颂》中却找不到对应的材料这一难题,(23) 同时也在希罗多德和司马迁之间建立起了另一个联系。如同希罗多德从荷马的伟大史诗中汲取了部分材料一样,司马迁也有可能把依附于中国诗歌源泉《诗经》的各种口头传说当做一种重要的资源来使用。
另一种可能则是司马迁所依据的献给契的诗歌,在现存的《颂》里已经不存在了。《宋世家》里提到:“太史公曰:‘……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24) 正如《商颂》里《那》用来祭祀成汤,《殷武》用来祭祀高宗,因此《商颂》里本来也应该有关于祭祀契的诗歌。
通过这几页的论述,笔者希望能将司马迁对轶事的各种不同的使用方式(包括把轶事作为预言,作为整章的起源,以及作为传播名人所不为人知的故事的一种手段)进行一个更彻底和全面的研究。当然,这些看法仅仅只能算是一种初步假设,笔者对任何意见和建议都表示欢迎。
注释:
① 参阅邓嗣禹著《司马迁与希罗多德(Herodotus)之比较》,《历史语言所集刊》第28本上册,1956年,第445—463页;Siep Stuurman,“Herodotus and Sima Qian:History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Turn in Ancient Greece and Han,China,”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1(2008):1—40.
② 本文引用的《历史》章节来自王以铸中译本《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③ The Landmark Herodotus,The Histories (hereafter The Histories).Robert B.Strassler,ed.Andrea L.Purvis,translator.(New York:Pantheon,2007):1.8—12(pp.8—9).
④ 这则轶事,尤其是其中对谋害坎道列斯方法的记载,使人联想起唐传奇《冯燕传》中的张婴。参阅汪辟疆著《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5页。
⑤ 谱系如下:“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史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页)。
⑥ 孔安周《史记正义》云:“无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别好恶,故时人谓之瞽,配字曰‘叟’。叟,无目之称电。”(《史记》,第32页)据此,“瞽”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比喻,表示人不能分辨是非。因此“舜父瞽叟盲”有可能是指舜的父亲从修辞意义上的失明变成了真正的失明。参阅《庄子·逍遥游》:“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清郭庆藩编《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页。
⑦ 《史记》,第32页。
⑧ 同上书,第34页。
⑨ 梁玉绳著《史记志疑》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页。
⑩ “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张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女其于予治。’”《孟子·万章》,焦循(1703—1760),《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19—620页。
(11) 《史记》,第44页。
(12) 《孟子·万章》,《孟子正义》,第628页。
(13) 同上书,第631页。
(14) 《太平御览》(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卷六十三,3上。
(15) 《史记志疑》卷一,第18页。
(16) 参阅吕祖谦著《史记详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3页。
(17) Rosalind Thomas,“Introduction”in The Histories,p.xxii.
(18) 《史记》,第46页。
(19) 《史记》,第91页。
(20) 同上书,第109页。
(21)(22) 《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册,第1444页。
(23) 关于契出生的故事至少还有另一种说法,即《天问》里的诗句“简狄在台喾何宜,鸟致贻书女何喜”所蕴涵的内容。甚至《离骚》“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可能也有所暗示。
(24) 《史记》,第1633页。
标签:史记论文; 希罗多德论文; 司马迁论文; 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尚书论文; 读书论文; 五帝本纪论文; 殷本纪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