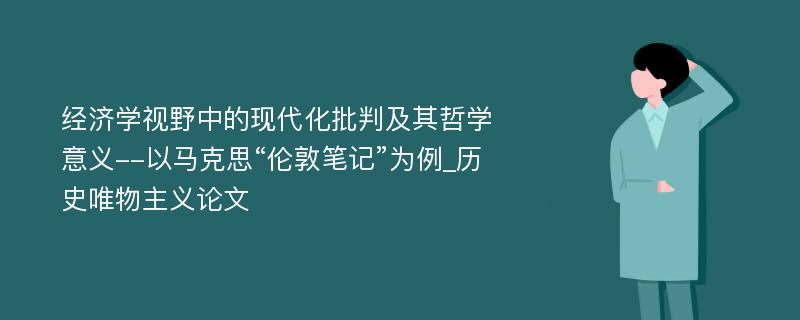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哲学意义——以马克思的“伦敦笔记”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伦敦论文,现代性论文,为例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伦敦笔记”是马克思1850-1853年在伦敦期间写下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及其他问题的研究笔记,它共由24本篇幅各异的笔记本组成。从马克思的研究笔记系列来看,它是接着1843年的“巴黎笔记”、1845年的“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之后的一个新的研究笔记。准确地理解“伦敦笔记”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桥梁”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完整内容是至关重要的。“伦敦笔记”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是怎样通过深化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的理解,来凸显其思想中所固有的主体批判维度的内容的。把握住了“伦敦笔记”的意义,我们就可以从一种内在统一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反之,如果忽视了“伦敦笔记”的意义,那么,为了接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论的线索来“重新”谈论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辩证法的思想,就只能在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线索之外,另起炉灶地从“存在的意义”的角度来“建构”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线索。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伦敦笔记”在三个经济学维度上的思想进步,来凸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双重线索(即主体维度和客体维度的线索)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获得共同推进的。
一、货币理论的阶段性突破及其哲学意义
马克思首先实现的是货币理论方面的突破。
货币理论尽管从直接的层面上来说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学理论,但就深层内涵而言,它又是跟关于社会历史过程的理解水平直接相关的。譬如,如果仅仅从流通手段的角度来界定货币,那么,作为货币之完成形式的资本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就必然会处于不在场的状态,而从这种理论层面来理解的社会历史过程也必然只是经验性的历史事实的连接而已。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有较大缺陷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货币形式或货币职能方面,马克思只区分了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和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而没有考虑到作为交换或流通手段的货币与其他货币职能如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之间的区别。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把金银视为构成价值的最初应用的观点时,提出了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区别的。通过对作为流通或交换手段的货币的职能的强调,马克思是想凸显货币的现实社会关系本质。应该说,就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来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已经足够了。但如果就货币的丰富内涵或者说就阐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深层本质而言,上述观点则是不够的。货币本身还有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以及世界货币等形式,如果不对这些形式进行研究,就不可能揭示出与它们直接相关的、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深层本质。客观地说,就马克思在1847年的经济学水平而言,他还无法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等概念的理解止步于交换或流通的层面,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此时还无法理解资本的独特的社会关系本质(这必须要进入到生产的领域才能理解),还只能从积累劳动与直接劳动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只能从“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的角度来理解“阶级对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5页),并进而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同上,第104页)。用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观点来说,他此时所理解的只是一般生产过程,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其二,在货币的价值问题上,马克思此时还认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因而在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李嘉图把货币的所有职能都理解成纯粹的交换手段,而无法理解作为资本的货币所独有的历史性社会关系本质,因而,在面对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而出现的商品价格普遍下降的现象时,只能把原因归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减少,而看不到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必然现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想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但其经济学水平的限制使他无法从生产过程内在矛盾的角度,而只能从分配不公平的角度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性,他此时对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认同就是这种局限性的一种表现。在批判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货币观时,马克思说:“在一切商品中,只有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的商品;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因为金银在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只要流通的需要和发行货币(无论纸币、金币、白金币或铜币)的数量之间保持着一定的比例,那就不可能产生保持货币的内在价值(由生产费用所确定)和名义价值之间的比例问题。”(同上,第125页)这种经济学观点说明了或者说决定了,马克思此时在哲学上还不可能完整地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内涵,因为他对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认同,说明他在面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时,其基本思路只是停留在交换或流通的领域,还没有深入到生产的领域来理解危机的本质,并由此来理解社会发展的真实过程。如果说,李嘉图把无论是国内的货币还是国际上的货币都理解成纯粹的交换手段,这使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犯了一个基本的方向性错误,那么,马克思只从交换或流通的层面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则表明他离彻底科学地剖析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尚存一段距离。
如果要准确地界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的理论成就的话,那么,应该说马克思在这两部著作中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建构,也即全面地证明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本质上是由经济运动的规律所决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经济运动的主要内容。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上述两部著作中对生产关系或交往形式概念的理解还不是很深刻的,他是在一般生产过程(他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这种一般生产过程放在“抽象”的层面上加以界定,以区别于“具体”层面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层面上来理解上述两个概念的,这是因为受到了斯密和李嘉图观点的影响。斯密和李嘉图囿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般生产过程来理解,进而论证了资本的永恒性。但由此带来的一个局限是:所谓的生产关系在他们的视域中其实只是各经济主体根据劳动资料的投入比例而分配或交换劳动产品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生产关系更多的是从分配或交换关系的层面上体现出来的。由于受到上述两人观点的影响,马克思直到《哲学的贫困》时期事实上还无法运用已经建构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去完整地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他还不能严格地从生产领域内部去解读经济运动的矛盾规律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还只能借助于人的异化的线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私有制只能带来人的片面化和异化的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性)或由分配不公平带来的政治对抗的线索(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用这一线索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来解读经济的矛盾运动规律。我们知道,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完整理解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有机内容之一,这说明,马克思的哲学在《哲学的贫困》之后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马克思“伦敦笔记”时期新的货币理论的关键内容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角度,去理解货币危机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流通领域内的表现形式。在面对自1825年以来的屡次经济危机时,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尽管来自不同的学派,但都从流通领域的层面来解读这种经济危机并试图找出解决的办法,其思想实质在于: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特定的生产形式当成了一般性的生产过程,因而他们都脱离物质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仅从其物质形式的角度来看待货币、信用的危机问题。“通货原理”派的思想基础是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这其实只是李嘉图未能在其思路中彻底贯彻劳动价值论而导致的一个有缺陷的观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线索的,他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与一般劳动过程之间的区别,因而当他面对一国流通中的货币量与相应的商品价格量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一流通领域的表面现象时,不是去找出劳动价值论在“具体”层面的转化形式,而是从劳动价值论的层面退出去,退到货币数量论的水平上。同时,历史性生产关系线索的缺乏也使他无法从质的层面把作为信用货币(它由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发展而来)的可兑现的银行券的流通与作为纯粹流通手段的货币(国家纸币)的流通区别开来,因此,即使在面对银行券的流通这一新的话题时,李嘉图也未能从货币数量论返回到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轨道上来。“通货原理”派接过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并致力于更为详细地论证作为信用货币的银行券的流通就像纯粹金属货币的流通一样,也是从属于货币数量论这一规律的。这一学派在同样不考虑货币的不同职能的前提下,得出了银行券的发行必须与银行中金的贮藏量的变动相适应的结论。也就是说,当金被输出的时候,就意味着流通中的银行券已经过剩了。这一观点在1847年的经济危机中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对“通货原理”派的批判中,马克思除了偶尔发表一点评论外,并没有太多地阐发自己的观点,这也许是因为马克思自1850年开始已经发现了存在于“通货原理”派观点中的明显错误。相比之下,马克思此时对“银行理论”派的观点倒是给以很大的关注,并通过对其观点的批判使自己的货币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图克、富拉顿等“银行理论”派经济学家通过对货币的不同职能(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及其发展形式——信用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世界货币等)的区分,得出了与“通货原理”派不同的观点:不是货币的流通量决定价格,而是价格的提高决定货币的量。应该说,“银行理论”派对货币不同职能的区分是正确的,但这是仅就量的层面而言。这一学派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不能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货币职能从单纯的流通手段向信用货币的转变的社会历史本质。也就是说,看不到信用货币作为一种商业资本,它的出现与实现恰恰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信用货币才可能真正地实现其自身。而“银行理论”派只把货币的不同职能理解为货币形式的不同,这就使他们得出了如下的错误结论: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与信用货币之间的区别是货币与资本之间的区别;资本是能够生息的货币,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是缺乏货币,而是缺乏资本。
在摘录与评述“银行理论”派著作的过程中,马克思显然产生了比“银行理论”更为深刻的货币观点。在“伦敦笔记”的第4个笔记本中,马克思对威廉·雅可比的《历史研究》一书继续进行了摘录。正是在这个摘录中,马克思写下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只有劳动可以自由交换货币,也就是说,只有同雇佣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货币制度本身才是纯粹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5期,第27页)。很显然,马克思此时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信用货币决不是自身能生息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与信用货币之间的区别也决不能被看成货币与资本之间的区别;信用货币之所以能实现自身,其根本原因在于现实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因此,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危机的本质原因既不是缺乏货币,也不是缺乏资本,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出现了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矛盾具体地说就是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第7个笔记本中的《反思》一文中,马克思在谈到经济危机时说:“商品不再是货币,它们不能再换成货币。当然,这种缺乏被归咎于货币制度,归咎于货币制度的某种特殊形式。这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58-159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在社会历史观的基础性思路上的确已经完成了从交换、流通关系向生产关系的转换,这对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的完善是非常关键的。
二、再生产理论、危机理论的阶段性突破及其哲学意义
马克思其次实现的是再生产理论及危机理论方面的阶段性突破。
再生产理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危机理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拓展具有如下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那么就物质生产实践这一认识对象来说,马克思就只能看到其物质形式的一面,而看不到其历史性的社会形式的一面,因为只有上升到再生产的层面,资本的积累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层面才能凸显出来,而只有站到这一理论高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形式的本质内涵才能显现出来,进而物质生产过程才可能从物质形式和社会形式这两个层面显现自身,即物质生产过程才可能不仅显现为物质生存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而且显现为生产这些物质生存资料的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惟其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不仅从客体维度即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维度上表现出来,而且从主体批判性的维度上表现出来。从历史唯物主义深层内涵的角度来看,再生产理论与危机理论之间是一种前因后果的关系。如果没有再生产理论,物质生产过程就只能在一般生产过程和简单流通过程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而根据马克思后来的思路,这种生产、流通过程只不过是一种“抽象”。在这种“抽象”中,不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会被掩盖起来,而且还会造成某种自由、平等交换的假象。如果在这样的思路中硬要加进一条批判的线索,那么,这条批判线索的理论支点就只可能在生产过程之外:要么是生产过程之外的人道的支点,专注于从私有制使人片面化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要么是生产过程之外的、单纯的交换和分配关系的理论支点,专注于从资本家和工人在劳动产品分配上的不平等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应该说,上述这两条批判的思路都没有完全进入到物质生产过程的内部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最深层内涵的揭示。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时期尽管在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方面的突破只是阶段性的,因而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深层内涵的把握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已经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下一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相比而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由于没有再生产理论,因而他在对资本主义危机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丰富内涵的把握上,与“伦敦笔记”时期的思想相比是有一段明显的距离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蒲鲁东提出了“构成价值论”,马克思的任务是针锋相对地阐明价值、货币等“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9页)。《哲学的贫困》很好地完成了批判蒲鲁东的任务,这是必须十分明确地加以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哲学的贫困》还不足以把马克思引向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危机理论的研究中去,因而它还存在着以下的局限性:马克思虽然在不少地方使用了“生产关系”的概念,但严格地说,他此时还没有完全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的视域之中。如果真的进入了上述视域,那么,马克思就应该从生产过程内部去寻找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灭亡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必须从严格的生产过程内部来理解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而《哲学的贫困》中的马克思还没有做到这一点:马克思此时恰恰是从交换、分配的层面来理解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的,这和他此时仅从流通领域的层次来理解货币的职能是相呼应的。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此时的确已经进入到了生产过程及生产关系的理论层面,正像他在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时所说的:“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7页)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马克思在上述这段话中的“生产的形式”、“生产方式”概念所指认的,实际上就是“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形式”,而不是他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指认的那种负载着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此书中所一再强调的“积累的劳动”与“直接的劳动”,于是,这两种劳动之间的交换就成了马克思此时所说的生产方式概念的内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尽管在多处指出了生产方式与阶级对抗之间的直接联系,但他对这种直接联系的理解仍然是相当薄弱的。他把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对抗仅仅理解为供工人消费的产品的生产与供资本家消费的产品的生产之间的不合比例(同上,第104-105页)。我们知道,仅仅这种“不合比例”似乎还无法说明“阶级对抗”,那么马克思是怎样推进他的批判思路的呢?马克思的思路最后还是落脚到了“人”上面——工人所处的社会条件使他们只能消费马铃薯、棉花、烧酒等工业品,而这些工业品所满足的恰恰只是工人作为工人的需要,而不是作为人的需要:马铃薯会引起瘰疬,棉花与羊毛、亚麻相比太不卫生,烧酒是一种有害的食品。(同上)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尚未真正地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找到内在矛盾的理论支点的前提下,马克思要想把分配领域的不平等的理论思路推进到生产过程的领域,把自己的资本主义批判思路奠基在生产过程的层面上,事实上是不可能贯彻到底的。
下面对马克思“伦敦笔记”时期在再生产理论及危机理论方面的思想水平作具体的分析。
1847年的经济危机(商品卖不出去,无法转化成货币)使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聚焦点从以前的劳动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不公,转向了生产与消费这两大领域之间的关系上面。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从货币、信用危机等角度解释1847年经济危机的观点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不同职能的了解,使他对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与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这两种不同的贸易活动的内涵有了更深的了解。应该说,这是马克思此时能初步建构起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的直接原因。马克思的这部分思想主要体现“伦敦笔记”的第7个笔记本中的《反思》一文中。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必然受到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但在理解这一点的时候决不能走向单纯的消费不足引起经济危机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由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为它所设立的界限而引起的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不合比例,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或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货币制度的特殊形式下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的独特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54-159页)。马克思此时所论及的“生产方式”和“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当然已经不同于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他已经把分配领域糅进了生产领域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在一个更广的领域即再生产领域的层面来理解“生产方式”、“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等范畴的内涵了。以这种再生产理论为基础,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他此时已不再像在《哲学的贫困》中那样从分配不公的层面来理解阶级对抗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了,而是从资本制度的内部来解读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正像他所说的:“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同上,第159页)
严格地说,再生产理论是必须要等到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建构起来之后才可能被真正建构出来的,但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此时的确已经建构起了再生产理论的初步形态(并非完成形态),他是在建立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前建构起再生产理论的这种初步形态的。马克思此时关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的思想大体上是后来关于第Ⅰ部类生产的思想的原型,而关于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思想大体上是后来关于第Ⅱ部类生产的思想的原型(请注意“大体上”这一限定词, 因为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局部的区别的。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杨对此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参见其论文《关于马克思1851年的〈反思〉手稿》[《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1-2合期,第78页])。马克思确实是从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扩大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危机的,只不过他对这一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本质还缺乏深层的了解。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方面的这种阶段性突破所蕴含的哲学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它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彻底地拉进了生产过程的领域,而且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领域,因为马克思此时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才可能出现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所设定的界限的现象。马克思一旦站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高度(而不是站在一般生产过程的层面上)来审视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有可能在以下两个思想层面上获得进展:(1)从严格的生产过程的角度深化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的经济运动发展规律的理解;(2)从不断拓展的拜物教分析的角度深化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的、主体批判性线索的理解。尽管这两种思想的彻底达成出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反思》一文中,马克思已经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端倪。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把从“生产方式”出发的经济矛盾分析与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货币交换所具有的“假象”出发的拜物教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货币制度和缺乏货币制度时比较起来,和货币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比较起来,其前提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和更大的阶级划分和分离……在这种交换行为中,转化成货币的收入的特性消失了,一切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61、162页)
三、价值理论的部分要素的构建及其哲学意义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价值理论的构建,与其在货币理论、再生产理论及危机理论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突破而言,是相对滞后的,因此,我们只能说马克思此时构建了价值理论的部分要素。但尽管如此,如果与《哲学的贫困》中的相关思想对比的话,那么马克思此时在价值理论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对其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在《哲学的贫困》中,应该说马克思还没有进入价值理论的视域。马克思此时所达及的是从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所有的经济范畴譬如劳动、分工等,因此,对于批判蒲鲁东从形而上学的、超社会历史的角度所界定的经济范畴而言,马克思此时的知识储备或者说经济学水平已经足够了。但同时也必须看到,马克思此时尽管意识到了要从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解读经济范畴或经济现象,但他尚未深刻地理解现实社会关系的本质,也即他还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内在关系的角度,还只是停留在分配或流通领域中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解读现实社会关系的内涵。这就导致他在批判蒲鲁东的“劳动的剩余”的观点时,尽管谈到了交换价值的剩余与财富的剩余之间的不同,但却并没有真正立足于价值的角度来批判蒲鲁东的上述观点,而是仍然立足于分配关系中的不公平的层次。例如,他说:“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须有阶级存在,其中一些阶级日益富裕,另一些则死于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35页)仅仅停留在分配关系的层面来理解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的内涵,这不但会使马克思由于无法准确地理解物质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从而无法完整地解读社会历史过程的全部内涵,而且还会妨碍马克思凸显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主体向度的内涵,因为惟有从历史性的生产过程的内部关系出发,才能不仅清晰地解读社会历史过程的客体向度的完整内容,而且揭示随着私有制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断地、越来越深刻的拜物教化的过程,从而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的内涵。这一项工作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时期开始做的。
马克思的这部分思想主要集中在“伦敦笔记”的第8个笔记本中。他在这一笔记本中断断续续地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多次进行了摘要,其价值理论方面的思想进展就是体现在这些“李嘉图笔记”中的。概括起来,马克思此时主要从两个方面构建起价值理论的部分要素:
其一,在一个较为深刻的层面上分清了价值与财富之间的区别。李嘉图尽管也看到了价值与财富之间的不同,但根据马克思此时的观点,李嘉图只是在概念上区分了价值与财富,而没有从本质上对这两个范畴作出区分。其具体表现是:李嘉图尽管认识到通过提高同量劳动的生产率而不追加劳动量,只会增加商品的数量,而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但他依然坚持认为,整个社会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富裕。这说明,李嘉图从根本上无法区分一般生产过程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间的不同,他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具体的、历史的生产过程形式的目的不是增加财富,而是增加价值。如果无法在这一点上获得突破,就必然无法把握住私有制的初级形态不断走向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私有制高级形态的历史过程的真实本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实际上就处在李嘉图此时的思想水平上,但在“李嘉图笔记”中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此时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同上,第109-110页)这说明,在马克思此时的思路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一般生产过程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区分,这种区分恰恰是马克思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就不再是分配不公平的理论线索了,而是朝着生产过程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理论层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目的与手段之间是存在着必然的对立关系的:资本家要想增加交换价值就必须扩大产品的生产量,而要增加生产就得提高生产力,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因此,“价值增长在自己的运动中扬弃自己,转变为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等等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经常在这样的矛盾中打转的。”(同上,第110页)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初步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增长与以价值增长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应该说,这一理论层面比单纯从分配不公平的角度所展开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线索要深刻得多。
其二,在一个更为清晰的层面上界定了“价值的余额”的出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是从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和积累的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分配的角度来说明“劳动的剩余”的,但在“李嘉图笔记”中马克思的观点就有了很大的不同。随着对价值与财富之间的更为清楚的界划,马克思此时已经明确地从生产过程中来寻找价值余额的来源。在他看来,在分配或流通领域之所以有余额出现,那只是因为这一余额早在生产过程中就已经被创造出来了:“由此可见,他能在商业中得到100镑之外的10镑,只是因为他或另一个工厂主当初在生产中已经创造了这10镑。这是十分清楚的……为了做到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在补偿总资本之后,手里还留下一些余额,这个余额本身必须存在。他们以欺诈的办法弄到的相对利润,只不过是全部余额的不平等的分配罢了。但要进行分配,就必须存在着待分配的东西:有了利润本身的存在,才可能有利润的不平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39-140页)更进一步,马克思还指出了这种价值余额的出处。单看上面这段引文,可能会认为马克思此时是把工厂主当成价值余额的创造者,其实不然。马克思清晰地看到:“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价值,而价值是相对的:它不是量,而是量对第三者的关系。这第三者只能是工人阶级。”(同上,第140页)也就是说,马克思已清晰地认识到,是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才创造了价值的余额。如果把马克思的这种观点与他在“李嘉图笔记”中得出的以下观点结合起来,那就很容易看出,马克思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维度(即客体和主体的维度)来完整地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远了:“在李嘉图那里重要的是,虽然甚至亚·斯密和萨伊也还把劳动的某种一定产品看作(价值的)调节者,但他却到处把劳动、活动即生产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把产品,而是把生产即创造的行为(当作调节者)。由此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时代。在亚·斯密那里,活动还没有解放,还不是自由的,还没有摆脱自然的束缚,还没有摆脱物。”(同上,第115页)
当然,应该承认,马克思此时的确还没有形成劳动二重性的理论,没有清晰地区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而这是形成价值理论的必要前提),因而离科学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尚有一步之遥。但同时也必须看到,马克思此时在价值理论局部要素的构建方面所作的努力,为他以后完成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旦完成了上述这两种经济学理论的构建,马克思对私有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就会变得十分充实与丰满:在马克思的脑海中,这段历史就不仅会浮现出严谨的经济矛盾运动规律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同时也会清晰地浮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伴随着上述这段历史而出现的不断拜物教化的内容,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批判维度能够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完整地凸显出来。
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再生产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