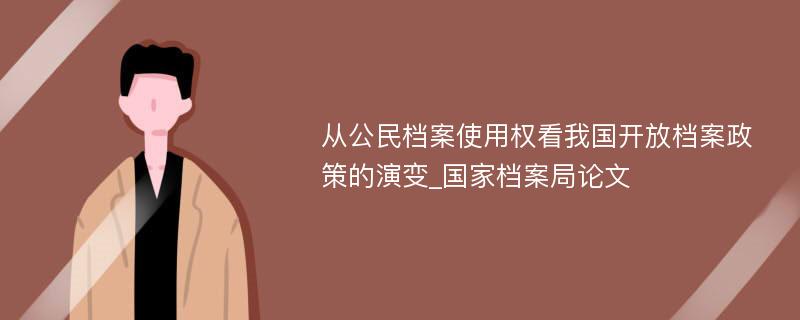
从公民的档案利用权考察我国开放档案政策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论文,公民论文,政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我国档案开放政策,曾经给保守封闭的档案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档案管理部门在开放档案方面的积极努力和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站在档案管理部门的立场,可以说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视角,从公民权利的角度重新考察我国开放档案政策的产生与嬗变,其中的缺失与疏漏就凸现出来,而这些恰恰是开放档案工作所不能回避的。
一、缘起
我国的开放档案政策是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满足文化研究的需要,从开放历史档案开始的。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迫切需要大量、系统地利用历史档案。在1979年6月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学术界的委员们提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提案。他们认为:档案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记录材料,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材料。科研人员只有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才可能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新的发现,才能开辟新的领域。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集中在档案保管部门,有的由于不必要的保密限制无法使用,有的由于缺乏整理,不便利用。这种状况应当尽快改变(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66页,第455页。)。1979年10月,国家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历史档案工作座谈会,就历史档案的利用和开放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历史研究人员强烈呼吁开放档案。为此,党中央“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根据目前历史研究高潮的到来,也看到了历史档案机密程度的变化,”(注:国家档案局:《曾三档案工作文集》,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326页。) 提出要开放历史档案。
除了国内的客观需求,国际档案界的促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979年,国家档案局恢复以后,在着力进行国内档案工作的恢复、整顿的同时,加强了国际交流。1980年1月,国家档案局和外交部给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联合发出关于中国1980年正式加入国际档案理事会的信件,并准备参加同年9月份在伦敦召开的以“档案的利用”为主题的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为此,我国档案界着手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开放历史档案政策的出台。当时代表中国参加大会的国家档案局局长张中同志,就向国外同行简要介绍了我国在学术研究方面利用档案以及开放历史档案的情况(注:张中:《在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上的发言》,《档案工作》1980年第6期,第1页。)。
在研究人员的强烈呼声中,在国际档案界的影响下,威严、神秘的档案馆大门终于向人们徐徐开启。由于时代的局限,起初开放档案的动机仅是满足知识界的需求,尚未提升到保障公民权利的高度,至少决策者主观上未达到这样的认识。
二、我国开放档案政策的历史演进
1.1980~1983年,首次提出开放历史档案——利用对象局限于研究人员,且只有利用权没有公布权。
1980年3月17日,国家档案局拟制了《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明清档案以及1949年以前的民国档案、日伪政权档案”,“1949年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实行对外开放。同时强调,历史档案向全国史学界和有关部门开放,“凡中国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持正式介绍信,证明其身份与使用档案的目的,经档案馆同意后均可在馆利用档案”;革命历史档案向搞党史研究的部门开放,“凡是中央或省级党委领导下的党史研究部门,党校和大专院校的党史教研室,由党委介绍,证明其身份和使用档案的目的,经档案馆同意后,均可利用已宣布开放的革命历史档案,并可摘抄其部分内容”。《意见》还对档案的公布问题作了限制性规定,“利用档案的单位或个人,允许在写作时摘引档案内容,但未经批准无权公布档案文件。”(注:国家档案局办公室:《档案工作文件汇编》第二辑,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206~207页,第209~212页。) 1980年5月19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21次会议,讨论了《关于中央档案馆开展利用工作的请示报告》,并就历史档案的开放问题做出决定(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66页,第455页。),这个决定对我国开放档案工作影响较大,权威性较强,所以后来的学者们撰文时,常以1980年的中央决定作为我国开放档案的起始。实际上在此前,国家档案局就曾拟制并颁发了《意见》。1980年5月27日至6月6日,国家档案局召开全国省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并讨论了《国家档案局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几点意见》(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66页,第455页。)。会后,各级综合档案馆正式启动了开放历史档案工作。
自1980年提出开放历史档案以后,各级档案馆为党政机关和学术研究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但由于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把握开放与控制界限,历史档案的复制、公布与出版等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对此,1982年11月20日,国办、中办转发国家档案局《关于开放历史档案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就开放历史档案的范围进行划定,重申了档案公布权的问题。《报告》指出,包括涉及到国家军事、外事机密,与邻国的领土、边界、产权等问题,以及党内有争议的问题、对领导人的评价材料等档案,属于免于开放、控制使用的范围,原则上不能提供借阅。在档案的公布与出版方面,《报告》首次明确档案的“公布权属于党和国家,由党和国家授权档案馆执行,特定档案由党和国家授权有关部门执行,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均无权公布和出版档案。”(注:国家档案局办公室:《档案工作文件汇编》第二辑,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206~207页,第209~212页。) 与《意见》相比,《报告》的内容更加详细具体,对利用范围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限制,以期在学术利用与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利益平衡。同时重申了限制性规定,并对档案馆在历史档案的公布和出版方面的工作任务作了一些要求。
1983年《档案馆工作通则》第18条规定,“档案馆应积极主动地开展利用工作,并根据党和国家有关规定开放历史档案。”首次以行政规章的方式规范历史档案的开放问题,标志着这项工作开始从行政命令走向法治。
在开放历史档案之初,尽管利用档案还只是一部分人的权利,而且利用范围、内容和手续均受到严格的限制,但这项政策毕竟首开我国档案事业的先河,对此后的档案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986年,确定进一步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明确了档案封闭期限为30年,利用档案成为我国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界要求进一步开放档案。1985年11月19日,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全体人员,以“请求进一步开放档案的报告”书呈胡乔木、王兆国。1986年1月16日,胡乔木就此问题批示:“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包括对国外的开放)势在必行,这是繁荣我国学术事业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要求,各国的通例我国不能例外。”(注:国家档案局办公室:《档案工作文件汇编》第三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44页,第229页,第237~239页。) 1985年8月,国家档案局召开全国省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明确了开放历史档案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解放思想,加快步伐,积极创造条件,开放一切应该开放的历史档案。即全国县以上各级国家档案馆不仅要继续开放解放前的历史档案,而且对于解放后的档案也要准备分期分批地开放;不仅要向机关、团体、大专院校、研究部门开放,也要向社会开放,允许公民利用某些档案;同时,在不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外国学者利用我国开放的历史档案,以开展对外文化学术交流工作。”(注:国家档案局办公室:《档案工作文件汇编》第三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44页,第229页,第237~239页。) 会后,国家档案局印发《档案馆开放历史档案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提出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除了未解密和控制使用的外,向社会开放。该《办法》的重大进步是利用对象的扩大和利用手续的简化。档案馆从面向研究界到面向我国的每一个公民,利用时从必须有单位证明到只须持个人的合法证明(介绍信、工作证)即可利用(注:国家档案局办公室:《档案工作文件汇编》第三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44页,第229页,第237~239页。)。
利用对象范围的扩大,标志着在我国档案利用不再仅仅是研究人员的需要和偏好,而成为普通公民的一项权利,它表明了档案利用向公民个人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尽管直到1987年的《档案法》中才明确这一点,尽管这种权利依然受到许多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办法》关于档案公布的政策有所宽松,如对于开放的档案,利用者依然可以在著述中引用,如果征得档案馆同意并签定出版合同,利用者还有权全文公布或汇编出版。
3.1987年以后,公民的档案利用权得到法律确认,成为一项法定权利,但将档案开放与档案公布分离、档案利用权与档案公布权分离。
1987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正式宣布了公民按照规定利用国家档案是一项法定权利。并就开放档案的范围和手续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并且“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有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下面简称《实施办法》),对各类档案开放的具体时间作了规定,在保障公民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方面作了一些积极的努力。《实施办法》首次对档案的利用、档案的公布作了界定,并对档案的利用权、档案的公布权限进行了限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由国家授权的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公布;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这个规定将档案的利用权与公布权相分离,这意味着公民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但不得公布国有档案。
1991年12月26日,国家档案局发布《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档案的公布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利用者摘抄、复制的档案,如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研究著述中引用,但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公布。”1999年颁布的《实施办法》,重新定义了档案的公布,将通过各种传播渠道首次向社会公开“档案的全部或者部分原文,或者档案记载的特定内容”,均纳入公布的范围。《实施办法》在重申国家享有档案公布权的同时,对档案馆的义务也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要求档案“分期分批地向社会开放,并同时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
三、从公民的档案利用权分析我国开放档案政策
1.我国开放档案政策变迁的实质是公民档案利用权利的逐步回归,具体体现在开放范围与利用对象逐步扩大、利用手续日益简便。
综观我国开放档案政策的演进,不难发现,80年代初期,它是作为档案利用工作的一种新方式提出的,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催生的一个副产品。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思想的解放,开放档案就不再“仅仅是对以往档案利用范围的一种扩大,而是对我国公民利用档案这一权利的承认和实现”(注:国家档案局办公室:《档案工作文件汇编》第四辑,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146~147页。),实际上,我国开放档案政策演进历程也正是公民档案利用权利逐步回归的过程。
这主要体现为开放范围与利用对象逐步扩大、利用手续日益简便。开放档案的范围从解放前的历史档案,到固定的30年封闭期限,再到个别门类随时开放。像涉及到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的,虽自形成之日起已满30年,仍应延期向社会开放;而对于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可以随时向社会开放。利用对象也逐步扩大,起初档案仅供学术界研究利用,后来面向每个公民开放。利用手续愈来愈简便,从必须有单位的介绍信,到使用个人合法证件即可利用档案,反映了在利用档案方面,公民逐步摆脱对单位的依附,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
2.档案开放与档案公布分离、档案利用权与档案公布权的不一致性,显现了档案开放政策在制度设计方面的缺失。
在档案开放政策的演进中,档案利用权利逐步回归于民,但档案公布政策却呈现了相反的势头。1982年我国首次明确提出档案的公布权“属于党和国家,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均无权公布和出版档案。”1986年档案公布出版权依然“属于档案馆、档案形成机关以及党和国家授权的有关部门。”不过,利用者虽然无公布权,但如果征得档案馆同意并“签定出版合同,可以全文公布或汇编出版。”1987年,法律按照所有权的不同划定了档案的公布权限,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档案的原文或复制件。”1991年“利用者摘抄、复制的档案,如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研究著述中引用,但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公布。”1999年,利用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档案馆、档案保存单位同意,或主管机关的授权和批准,均无权公布档案的全部或者部分原文,或者档案记载的特定内容”。这里档案的公布,不仅仅是1987年的“原文或复制件”了,“档案记载的特定内容”也包括在内。
这种将档案开放与档案公布分离,将档案利用权与档案的公布权相分离的规定,使得开放档案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层面出现了偏差。档案开放与档案公布原本指的是同一事物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二者的指向均是“档案首次向社会公开”,区别仅在于,档案开放解决的是哪些档案可以公开,档案公布解决的是如何公开的问题。如果说档案开放是一项任务,完成任务可以有多种途径,那么,档案公布只是实现目标的途径之一。
上述档案开放政策与档案公布政策相背离的发展趋势,给档案开放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惑。国家一方面积极地扩大开放范围,鼓励社会公众利用档案;另一方面又在制度上牢牢把持着档案的公布权,这既违反了法律制定的同一性、协调性原则,也使得利用者进退维艰、无所适从,陷入到可以查阅档案内容但又不得传播档案信息的两难境地。
3.开放档案是政府为确保公民的档案利用权利实现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
由于开放档案与公民的档案利用权利之间的关系尚未厘清,导致了迄今为止,档案管理部门对于应该开放多少档案缺乏足够的关注,而是沾沾自喜于已经开放了多少档案,开放档案工作的进展依然主要取决于档案管理部门的自觉自醒,而不是作为保障公民利用档案权利的根本途径来看待。尽管《档案法》将开放档案视作“对我国公民利用档案这一权利的承认和实现”,但也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法律宣言。
根据权利与义务关系理论,在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是主,义务是从,权利具有受外界强制力保障的优势。(注:魏再龙:《法学权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7~68页。) 如果认为利用档案是公民的一种权利,那么开放档案就不再仅仅是利用工作的新方式,而是有了制约国家、政府公权力的意义。作为义务主体——档案管理部门悉数公开到期应开放的档案,不是依据馆内情况“量力而行”、可为可不为的单方面决策,更不是对公众的“恩赐”,而是为了确保公民档案利用权的实现,代表政府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和职责。开放档案的宗旨,不仅仅在于改善政府作风、满足学术研究的需求,更是实现公民利用档案权利的根本途径。
感谢前国家档案局局长冯子直先生对本文在资料方面的协助
标签:国家档案局论文; 企业档案工作规范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档案法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