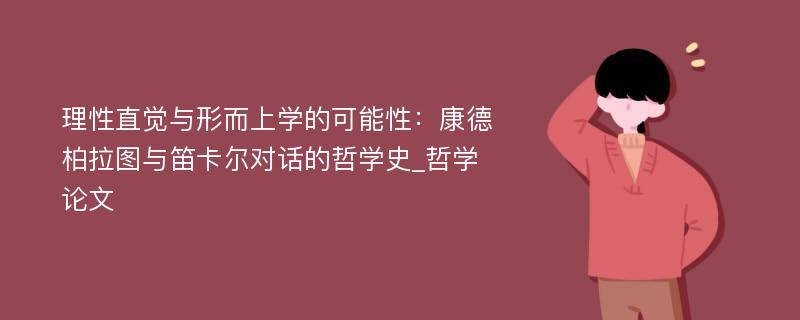
理性的直观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种展开在康德与柏拉图及笛卡儿之间的对话性的哲学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柏拉图论文,哲学史论文,形而上学论文,直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0)05—0026—08
对于形而上学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阐明。一般认为康德之所以否定了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是因为康德彻底论证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亦即在康德看来人类的认识能力根本不可能达到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当然,这种看法并非错误,但也太过笼统而不够具体。事实上,康德之所以能够判定形而上学的不可能,只是由于康德取消了此前作为人类认识能力之一部分、且被认为是具有最高确定性认识的理性的直观,具体来说就是,康德只承认人类有感性的直观,不承认有除此以外的别种直观可作为人类认识能力的一部分或构成要素。因此,对于形而上学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回答最终应落实于对理性的直观的考察:(1)人类有无理性的直观;(2)理性的直观能否普遍地作为人类认识能力中具有最高确定性认识的部分。如果人类根本没有理性的直观,那么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就可以成立;如果不能肯定但也不能排除人类可能有理性的直观,而且也不能排除它可能是人类认识能力中具有最高确定性认识的部分,那么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否定也不无可能是康德狭窄化人类认识能力的结果,这一结果本身并不能表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换句话说,形而上学恰如同宗教修行者所希望要达到的“见地”一样,在某种超越感性世界的意义上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如此一来也引发了如何界定哲学的性质的大问题。
一、柏拉图理性的直观与形而上学的理念论
康德之前的大多数理性主义哲学家都主张存在理性的直观,认为理性的直观是人类认识能力中最具有确定性认识的部分。如果我们上溯到古希腊哲学,那么柏拉图无疑是坚持这种观点的最重要的早期代表人物。在著名的“线段比喻”的论证中,柏拉图全面而概括地阐明了人类认识能力。在柏拉图看来,通过感觉我们只能获得“意见”而不能获得“知识”,因为感觉的对象是处在流变之中的可感事物,因此,要获得“知识”就要运用理智,因为理智是一种推理的能力。于是,柏拉图就把算术和几何学看成是运用理智推理的典型。不过,由于在算术和几何学中,不仅理智推理的前提是假设,而且理智推理的过程也涉及感性的因素(例如几何学中的图形、图解之类),所以运用理智推理所获得的知识,一方面是从前提下降到结论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是夹杂着感性因素的知识,因此只能当作低级知识,而不是“纯粹知识”。为了获得“纯粹知识”,柏拉图主张超越理智而诉诸理性。因为理性与理智不同,不是从假设的前提出发下降到结论,而是把假设的前提当作起点或梯子从而上升到原理(理念),直至达到最终的原理(最高的理念),然后以此为根据考察假设提出的事物,并下降到结论。由于在此过程中,理性决不使用任何可见事物,而只是从理念到理念并归结于理念的认识,所以运用理性认识所获得的知识是不含感性的“纯粹知识”(真理)。正因为如此,所以柏拉图就把理性认识的这一条道路称作“逻格斯”或“辩证法”。然而问题在于,理性如何超越理智也就是理性如何把理智假设的前提当作起点或梯子从而上升到理念?简言之,理性如何认识理念?虽然柏拉图并未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问题的答案,但仔细解读《理想国》(Republic)中苏格拉底和格劳孔(Glaucon)的对话,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通过理性的直观超越理智从而直接地认识理念的。下列引文是我们得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
所以你也必须知道尽管事实上他们(几何学家,引者注)对看得见的形式自身不感兴趣而对看得见的形式是其相像者的事物感兴趣,但是他们在讨论中仍使用看得见的形式:也就是,他们在讨论中所感兴趣的不是出现在他们的图解中的正方形、对角线等等,而是正方形本身、对角线本身等等。他们所作的图形以及图解作为实物事实上有自己的影子(即阴影和水中的影像),但他们却把图形及图解当作影像看待;他们实际上要努力看见的,是只有思想才能看见(which only thought can see)的正方形本身、对角线本身等等。[1]238
这里,苏格拉底对格劳孔的答问表明,几何学家之所以使用假设是因为他们通过对可见事物的推理试图要达到对可知领域中的理念的认识,也就是说,几何学家使用假设不是为了推论可见的图形而是为了认识别的东西—数学的理念。正因为如此,所以数学才是一门“知识”,才区别于“意见”。但尽管这样,几何学家却只能看见可见领域中的图形而看不见可知领域中的理念,因为可知领域中的理念“只有思想才能看见”。因此,根据柏拉图的论证,我们把前者看作是感性的直观,而把后者看成是理性的直观。当然,我们如此解读柏拉图的哲学著作也许会招来严重的非议,因为众所周知柏拉图的哲学著作极具文学的风格,所以“只有思想才能看见”的表述只是比喻抽象的理性认识,不能因此就把它落实为理性的直观,否则也太过拘泥于文字本身了。然而实际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固然,在柏拉图的哲学著作中充满了大量的文学性的比喻,但是,在这里与其把“只有思想才能看见”的表述看作是比喻,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与前者进行的对比要更加准确和妥当。因为在感觉中,柏拉图最重视“视觉”(俗语: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正是通过对“视觉”的分析,柏拉图得出了太阳使视觉的能力成为可能而使“视觉”的对象得以被看见的结论;然而恰恰是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柏拉图又进一步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对比推理:
太阳在可见领域中与视觉及我们看见的事物的关系,正如同善在可知领域中与智力及我们认识的事物的关系一样。[1]235
显然,柏拉图在此运用对比推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说明“善给予我们要认识它们的真理的事物且使我们有能力获得知识。”[2]236因此,根据柏拉图的这一对比推理,我们可以发现“视觉”的感知与理性的认识之类似性的两点:(1)如果“视觉”的感知依靠“太阳”,那么理性的认识依靠“善”(最高的理念);(2)如果前者是感性的直观,那么后者就是理性的直观。当然不可否认,在柏拉图看来,感性的直观与理性的直观也有下列三点的不同:(1)如果感性的直观使用肉体的官能,那么理性的直观使用心灵的能力或“心灵的眼睛”(the mind's eye);(2)如果感性的直观的对象是流变的可感事物,那么理性的直观的对象则是不变的或永恒的理念;(3)如果感性的直观作为感知只能得到“意见”,那么理性的直观作为认识则获得“纯粹知识”。
当然,从“视觉”出发,通过把感觉与理性的直观进行对比从而凸显理性的直观的确定性或理性的直观认识理念的论证方式,无疑是柏拉图特别予以突出而反复强调的基本内容。因此,这种论证方式不仅出现在《理想国》中,而且也同样地出现在《裴洞篇》(phaidon或phaedo)中,不过《裴洞篇》把这种对比引向了更趋激进的立场,以至于达到了为了认识真理而贬低感官而要求与肉体分离的极端程度。苏格拉底对辛弥亚的不厌其烦的忠告可佐以为证:
实际上我们深信:如果我们想要对某事某物得到纯粹的知识,那就必须摆脱肉体,单独用灵魂观照对象本身。看来根据我们的论证可见,我们所希求的、我们信誓旦旦地从事追索的智慧,只有在死后才能获得,生前根本不行。如果我们以血肉之躯不可能取得任何纯粹的知识,那就要末根本不可能求得知识,要末只有在死后才可能,因为只有那时灵魂才会与肉体分离,独立于肉体。看来我们在有生之年只能尽量接近知识,其办法是尽可能避免与肉体接触往来,非绝对必须时不碰,不受肉体本性的影响,使自己纯粹独处,直到最后神使我们解脱。像这样,我们摆脱肉体的愚昧,保持纯粹,我想就大概可以与我们的侪辈相通,对纯粹的东西获得直接的知识,这也许就是认识真理了。[2]
毫无疑问,无论是上面所引“单独用灵魂观照对象本身”的表述,还是前面所引“只有思想才能看见”的表述都表达同样的观点,即都是对理性的直观的肯定,都是对理性的直观作为最具确定性认识的肯定。不过,在柏拉图看来,理性的直观得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前提是使心灵摆脱肉体感官的影响。为此,柏拉图甚至希望通过死亡的方式使心灵彻底从肉体感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当然,这样的思想亦可在《理想国》中发现,“洞穴”比喻就是揭示肉体感官的欺骗性,或肉体感官蒙蔽心灵之眼睛的极为生动的例子。只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主张通过教育促使心灵逐渐地摆脱肉体感官的影响,其重点放在了对于心灵的训练上而不是对肉体感官的贬低上。教育的首要课程是学习数学,因为数学主要运用理智推理而非感官,可以引导心灵逐步地远离可见的事物,亦即走出“洞穴”。但由于理智推理运用假设,所以理智推理只能思维理念而不能认识理念。换言之,理智推理,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思维只是达到认识的必需的阶段而非认识。通过格劳孔之口说出而被苏格拉底同意了的下面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认为你把几何学家以及研究这类学问的人们的工作称为思维(thinking)而不是认识(knowing),因为思维是位于信念(believing)与认识之间的中间状态。[1]240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思维看作认识,但在柏拉图那里,思维与认识是有区别的。因为思维进行在信念(意见)与认识的中途,所以思维具有中间性或者说思维只是达成认识的中介环节。如果我们把思维的中间性与知识的“回忆说”联系起来,那么思维与认识的区别就可以清楚地被理解了。按照柏拉图在《枚农篇》(meno或menon)中的记述,苏格拉底只提问就能让从未学过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小奴隶成功地从“自己心里浮现出”几何学的知识,由于在此过程中苏格拉底并没有教给小奴隶什么,所以知识的“回忆说”也就因此而得到了确立。尽管知识的“回忆说”证明了知识与生俱来的本质以及灵魂不朽的本性,但是仔细考察小奴隶解证几何学知识的实际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苏格拉底的提问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刺激了小奴隶的思维,小奴隶事实上是通过自己的思维才获得了几何学的知识的。然而,知识的“回忆说”却把通过思维获得的知识理解为回忆到从来就寓于灵魂之中的知识,因此,知识的“回忆说”在此把思维等同于回忆的观点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不可否认,柏拉图在《裴洞篇》中重申知识的“回忆说”时也同样地把由可见领域中的感觉作用而想到可知领域中的理念的心理过程看成是回忆。不过,虽然《枚农篇》中提出的知识的“回忆说”与《裴洞篇》中重申的知识的“回忆说”确有不同,但我们也没有根据表明后者就是对前者的否定或修正。这样,合理的解释也许就是由于小奴隶解证几何学知识的实践或学习是知识的“回忆说”由以得出的原始根据,所以后来的重申可以看成是在此基础上对知识的“回忆说”的丰富或进一步的发挥。只不过,即便知识的“回忆说”能为彼此严格划分的可见领域与可知领域搭建起由此达彼的“桥梁”或联系,但是通过思维获得的或由可见领域中的感觉作用而想到的知识都属于回忆到的知识,都是间接的知识。因此,思维与认识的区别就在于通过思维我们获得间接的知识而认识则是指获得直接的知识。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认识无疑是通过理性的直观最后达成的。由于理智推理或者思维作为达成认识的上升过程中的梯子只能“回忆”知识或者“尽量接近知识”而不能达到“纯粹知识”或知识本身,所以理性的直观是作为对理智推理或思维的超越而出现的最高的认识能力。不过,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最高的认识能力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是天赋的,但也不是自发地呈现的而是在理智推理或者思维的基础上促使心灵彻底出离可见领域(“心灵的转向”)之后实现出来的。因此,在柏拉图那里,理性的直观是形而上学的理念论由以得到确立的认识论基础,因为理性的直观直接把握理念是理性的思辨(不是理智推理或思维而是纯粹理性的思维)之所以能够进一步揭示理念之间关系的实在的或客观的出发点。柏拉图正是通过理性的直观和理性的思辨试图建立起以“善”作为统辖且具有等级秩序的形而上学的理念体系。
二、笛卡儿理性的直观与形而上学的“我思故我是”命题①
理性的直观是人类先天的认识能力,只是由于心灵在为感官知觉或“意见”所遮蔽的同时也使它一道被遮蔽了。因此,思维就是引导心灵摆脱感官知觉、走出可见领域从而使它定向于可知领域,以便于理性的直观能够把握理念的一种道路或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儿是柏拉图主义在近代的真正的复活者。笛卡儿也是借助于思维试图清除充斥于心灵中的感官知觉的,不过,笛卡儿比柏拉图更彻底,因为笛卡儿运用普遍怀疑的方法,不但要清除充斥于心灵中的感官知觉,而且也要破除心灵中的种种成见,甚至要排除为心灵所认知的数学知识,等等。总之,笛卡儿的目标是要使心灵得到彻底的净化。“我思故我是”的命题就是在这种净化的完成中被确立的。于是,如同前述对于柏拉图的提问一样,我们的问题是:“我思故我是”的命题是如何被确立的?
事实上,围绕“我思故我是”的命题的提出,与笛卡儿同时代的神学家、哲学家就已经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反驳意见,不过,我们的兴趣在于笛卡儿的答辩,因为正是在答辩中笛卡儿才交待出了“我思故我是”的命题由以得出的方法。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笛卡儿似乎提出了两种并不一致的观点。
(1)当有人说“我思维,所以我是,或我存在”时,他不能通过三段论从他的思维中推论出他的存在,而只能通过心灵的单纯的直观(a simple intuition of the mind)把它认作自明的事情。从以下的事实看,这是很清楚的,如果他通过三段论推论它,他就必须首先要认识大前提“任何思维的东西是,或存在”;然而事实上,他是在他经验的实例中认识到如果他不存在他就不能思维。它是根据我们对具体实例的认识在我们心灵的本质中建构的一般命题。[3]68
(2)我们不能直接由实体来认识实体,而是从我们对某些形式或属性的知觉上领会实体,这些形式或属性应该依附于什么东西而存在,我们就把它们所依附的这个东西叫做实体。[4]225
引文(1)是笛卡儿直接针对对于“我思故我是”的命题的反驳而进行的答辩,由此答辩我们可以看出笛卡儿明确地肯定“我思故我是”的命题不是通过推论而是通过“心灵的单纯的直观”得出的。引文(2)是笛卡儿针对对于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的实在性区分的反驳而给予的答辩中所提出的另一种观点,虽然这种观点没有直接针对“我思故我是”的命题,但“我们不能直接由实体来认识实体,而是从我们对某些形式或属性的知觉上领会实体”的表述也暗示“我思故我是”的命题可能是通过推论得来。这样,在对于“我思故我是”的命题究竟是如何得出的问题上,笛卡儿自己似乎陷入了两种认识的矛盾中。我们暂且不去解决这个矛盾而是首先考察后来的哲学家在看待“我思故我是”的命题上的一些持论,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在近代哲学史上,无论是休谟还是康德都认为“我思故我是”的命题的得出是一个推论。只不过,休谟从“实验的推理方法”出发,对“我思故我是”的命题作了经验的分析,认为“我思故我是”的命题的得出缺乏经验或事实上的根据。因为我们对于自我的知觉是接连不断且变动不居的印象或经验,从中无法推出同一不变的自我或自我实体。而康德则从理性的先验批判出发,对“我思故我是”的命题作了逻辑的分析,认为“我思故我是”的命题是理性的“一个谬误推理”(a paralogism)。因为在康德看来,“我思”中的“我”只是思维的逻辑意义上的不变主体(the constant logical subject of thought),仅仅是思维的自我意识,可笛卡儿却把它看成了是对思维所依存的实在主体的认识(as being knowledge of the real subject in which the thought inheres)。[5]334因此,混淆思维的逻辑主体与思维所依存的实在主体的区别是导致笛卡儿作出谬误推理的认识论根源。于是,康德认为要获得对于实在主体的认识,仅有“我思”或思维的自我意识是不够的,还必须配合以相应的内直观(inner intuition)或内感(inner sense)才有可能。然而内直观仅限于提供关于实在主体的内在状态的经验而莫能及其它,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只能认识实在主体的现象而不能认识实在主体自身(the real subject in itself)。和休谟一样,康德也认为自我实体是不可知的,所不同的是,康德肯定了“我思”的认识论意义,因为“我思”是一切范畴所从属的最高条件。总之,休谟和康德都主张“我思故我是”的命题得自于不正确的推论,不能成立。继休谟和康德之后,虽然黑格尔坚持了与其前辈们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我思故我是”的命题的得出并不是一个推论,但是黑格尔也不认为“我思故我是”的命题是得自于“心灵的单纯的直观”。黑格尔只是从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的原则出发肯定了“我思故我是”的命题。[6]不过,在当代哲学家中,胡塞尔倒是从笛卡儿普遍怀疑的方法中充分地发掘出了“纯粹直观的或明见性的原则”,然而胡塞尔所谓的纯粹直观“只承认我们在通过悬搁向我们开启的我思领域中现实地并且首先是完全直接地给予出来的东西,因而不去陈述任何我们没有亲自‘看见’的东西”。[7]因此,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儿把自我把握为是一个思维的实体的认识是一种完全不合法的超越。这样,胡塞尔也同样拒绝承认笛卡儿“心灵的单纯的直观”。
综上所述,尽管上述哲学家分别从各自的哲学原则出发,对“我思故我是”的命题作了不同的分析,或否定或肯定或批判性地继承,莫衷一是,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他们所共同忽略了的,那就是笛卡儿指出的“心灵的单纯的直观”。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忽略的背后所可能隐藏着的派别之见,我们最好还是返回到笛卡儿的文本以便厘清究竟。
因此,既然我们的感官有时欺骗我们,我宁愿假定并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地象感官呈现给我们的那样;因为有人推理时即便在最简单的几何问题上也会弄错,我相信我和别人一样易于犯错,我就把我曾经用于作证明的全部理由统统当作假的而予以抛弃;最后,当我考虑到我们在醒着所经验到的种种思想(所与物)也同样会在我们的睡梦中被经验到,而那时没有一样是真的,我就假定在我醒着而进入到我的心灵中的全部对象(所与物)本身并不比梦境中的幻见更真实。然而我立刻注意到:当我这样想要认为一切都是假的的时候,这样认为的我必然应当是某个东西;我发现我思故我是这条真理是那么确实、那么可靠,以至于无论多么狂妄的怀疑派都不能使它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把它接受为我所寻求的哲学的第一条原理。[8]
该段落摘自《谈谈方法》,是笛卡儿首次提出“我思故我是”的命题的地方。它可划分为两层:第一层“因此,……,……真实。”叙述怀疑的具体事项;第二层“然而……,……,……原理。”指出在怀疑的情境中发现了“我必然应当是某个东西”或“我思故我是”。从逻辑上看,这两层并不构成一个推论。因为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的过渡不是下降而是上升,是从具体的怀疑或思维(经验)中上升到普遍认识(理性)的一个飞跃,而这个飞跃只有通过突然间发生“心灵的单纯的直观”才能完成。因为在怀疑中,意识本来指向思维的内容或对象,可是长期无法确定思维的内容或对象之可靠性的绝望突然使意识回头指向了思维的来源处,直接把握住了能产生思维的心灵本身,“心灵的单纯的直观”就在此瞬间发生。心灵能直观自己是心灵之为心灵的本质,“能看到自己的既不是眼睛,也不是镜子,而是精神,只有精神既能认识镜子,又能认识眼睛,又能认识自己。”[4]368不过,由于意识的突然转向同时也意味着思维进程的中断,所以和柏拉图一样,“心灵的单纯的直观”同样也是作为对思维的超越而出现的最高的认识能力。笛卡儿所谓“心灵的单纯的直观”也就是理性的直观。
可是,我怎么知道除了我刚才列举的那些不可靠的东西以外就没有别的丝毫也不能怀疑的东西呢?难道就没有上帝或无论我叫他什么的某种存在,把这些想法放在我心灵中吗?然而我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呢?因为也许我自己就能产生这些想法。这样,难道我至少不就是某个东西吗?但是我刚才说过我没有感官和身体。这倒是一个很难摆脱的观点:从这个观点中能得出什么呢?难道我不是与一个身体和感官联系的那么紧密以至于没有它们我就不能存在吗?但是我刚才使我确信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天,没有地,没有心灵,没有形体。难道由此就能推出我也不存在吗?不:如果我曾经使我自己相信什么东西,那么我肯定存在。但是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骗子,极其强大和狡猾,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欺骗我。即使这样,我也毫无疑问地存在,如果他欺骗我,就让他尽其所能地欺骗,只要我认为我是某种东西,他将永远也不会使我什么都不是。因此,经过全面和彻底的思考之后,我必然最后得到这个命题我是,我存在,每当我说出它或者在心中想到它的时候,它必然是真的。[3]16
这段篇幅完整的自然段落,摘自《第一哲学沉思集》。在这里,笛卡儿充分地展开和深化了对“我思故我是”命题的论证。如果我们把摘自《谈谈方法》中的前述段落与摘自《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该自然段落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前者只是断言“我思故我是”的命题不会为任何怀疑论所动摇,而后者则对此进行了公开的怀疑论的考察。这种怀疑论的考察按照认识论的怀疑和假设的怀疑的逻辑顺序展开[9]。就认识论的怀疑考察来看,如果“我”怀疑我是“某个东西”,那么单就“我”怀疑本身即已揭示出“我肯定存在”。这一认识完全是通过理性的直观直接完成的,无须考虑作为怀疑主体的“我”和被怀疑的“我”之间的逻辑同一性的问题。因此,对“我思故我是”的命题进行逻辑的分析只能被看成是否定了理性的直观之后所能开展的工作。就假设的怀疑考察来看,如果“我”设想上帝(恶魔)欺骗我,也就是说我设想上帝尽其一切所能地使我作出不正确的判断,那么不正确的判断也属于思维,因此,即使上帝欺骗我,“我也毫无疑问地存在”。总之,不管是通过认识论的怀疑考察,还是通过假设的怀疑考察“我思故我是”的命题能经受得住任何怀疑论的检验而必然成立。因为无论从“我思”中,还是从外在于我的上帝力量介入的“我思”中都可以通过理性的直观直接确证思维者的绝对存在,或者说都可以确证“我是,我存在”的命题。因此,倘若我们的分析确实符合笛卡儿哲学的原旨,那么“我思故我是”命题则正如笛卡儿所指出的那样是通过理性的直观确立的。可是问题在于,我们又如何解释笛卡儿提出的另一种观点,即“我们不能直接由实体来认识实体,而是从我们对某些形式或属性的知觉上领会实体”的观点呢?显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得涉及对笛卡儿哲学体系的认识。因此,我们打算把这个问题留在下文中适当的地方加以解决,现在我们首先着手探讨理性的直观由以提出的现实根据及其可能与否的问题。
三、康德与柏拉图及笛卡儿的对话:理性的直观与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以及怎样可能?
理性的直观这个概念肇始于柏拉图对数学知识(几何和算术)的哲学反思。但是如前所述,柏拉图对数学知识的哲学反思是本体论的,因为柏拉图肯定超越思维而出现的理性的直观直接通达形而上学的数学理念。然而与柏拉图不同,笛卡儿对数学知识的哲学反思是方法论的。只不过,虽然笛卡儿从数学知识中抽象出了理性的直观-演绎的普遍方法,但是这一普遍方法只有同普遍怀疑的方法相结合才能使它得以被提高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因此,尽管诸如“两点决定一条直线”的命题或“正方形有四条边”的判断都是通过理性的直观确立的,但是这类命题或判断一旦被加之于普遍怀疑的方法的检验则数学知识摹仿形而上学的数学理念的信念就会被瓦解。因为在笛卡儿看来,假如上帝欺骗我们,那么即使是建立在理性的直观基础上的数学知识或自明的数学知识也势必不能免于错误,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肯定它们揭示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因此,只有建立在理性的直观基础上的“我思故我是”的命题才能揭示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因为惟独这一命题才是通过彻底怀疑论的检验而被证明是确定不移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所以笛卡儿在《哲学原理》的序中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是想象的本原,并非是清楚明白的真理。[10]因此,对于理性的直观,柏拉图与笛卡儿的不同之处在于:柏拉图认为理性的直观可以直通形而上学的全部存在,而笛卡儿则认为理性的直观只可直通形而上学的自我存在(“唯我论”),形而上学的其他存在只可据此为逻辑起点,通过理性的演绎揭示出来。因此,在笛卡儿看来,只有从“我思”出发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之后,我们的清楚明白的观念才能被肯定为具有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的意义。这样,在笛卡儿哲学体系中,自我实体是由理性的直观直接提供出来的,而物质实体则是推论出来的。也就是说笛卡儿认为,我们不能直接认识物质实体,我们只能从“广延”观念(属性)中推论出物质实体,因为证明了其存在的上帝并不是恶魔或骗子,所以上帝能够按照我们“清楚明白”的“广延”观念把物质实体现实地创造出来。因此,笛卡儿“我们不能直接由实体来认识实体,而是从我们对某些形式或属性的知觉上领会实体”的观点仅指我们对于物质实体的认识,并不涉及我们对于自我实体或心灵的认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笛卡儿的断言:“认识我们的心灵要比认识别的东西更容易,也更清楚”。[3]23总之,尽管柏拉图与笛卡儿对于理性的直观是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分歧的,但是肯定理性的直观直接把握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全部抑或部分)则是他们的共识。然而,这一共识却被后来者康德彻底地推翻了。
如上所述,对于理性的直观的确立涉及对数学知识的哲学反思,因此,康德对于理性的直观的否定也开始于对数学知识的哲学反思。与柏拉图对数学知识本体论的哲学反思不同,也与笛卡儿对数学知识方法论的哲学反思不同,康德对数学知识的哲学反思是先天条件论的。康德认为数学知识诚然是先天的知识,但数学知识之为先天的知识并不是说数学知识的产生只通过理智或理性而不涉及感性的因素,恰恰相反,感性的因素,也就是感性直观的形式(时间和空间)是构成数学知识的先天条件。因此,数学知识中的直观不是理性的直观而是感性的直观,数学知识虽然与感性直观的内容无关但是离不开感性直观的形式或“纯粹直观”。正是如此,所以康德才说:“数学知识是得自概念构造(construction)的理性知识。”[5]77由于数学的概念可以通过“纯粹直观”先验地被展示出来,所以例如我们画在纸上的三角形图形就不是对于客观存在的三角形或三角形的理念的一个表象(representation),而是我们根据三角形的概念所构造出来的对象。因此,数学知识归根结底是人类理性的构造物,是属于现象界的知识。这样,康德就宣告了柏拉图对数学知识本体论的哲学反思的破产。当然,不仅如此,康德也同样宣告了笛卡儿对数学知识方法论的哲学反思的失败,因为笛卡儿把“普遍数学”的方法论运用于哲学领域只会产生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总而言之,在康德看来,通过对于数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的哲学反思,我们只发现构成数学知识的感性直观的形式是使数学知识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因此,理性的直观实不能从对数学知识的哲学反思中抽象出来,换言之,数学知识并不是理性的直观之所以被提出的现实根据。既然如此,那么理性的直观这个概念从何而来呢?
对于理性的直观(康德又名之为智性的直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分别提出了两种意义不同的观点。当然,这两种观点也并不构成矛盾。
(1)如果我们把“本体”(noumenon)理解为一个这样的物,就它不是我们感性直观的客体而言,可以抽掉我们直观它的方式,那么这就是一个消极地理解的本体。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非感性的直观的客体,那么我们由此就假定了一种特殊的直观方式,即智性的直观方式,但它不是我们所具有的,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它的可能性。而这将会是积极地理解的“本体”。[5]268
(2)一个本体的概念,即一个完全不应被思考为一个感官的对象、而应(只通过纯粹知性)被思考为一个自在之物,是完全不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不能断言感性就是唯一可能的直观的种类(wo cannot assert of sensibility that it is the sole possible kind of intuition)。此外,为了不使感性的直观扩展到自在之物本身上去,从而限制感性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本体的概念又是必要的。[5]271
根据以上引文,我们发现康德把理性的直观与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或本体直接相对应,认为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或本体是否可知决定于理性的直观之有无。但是引文(1)表明康德只承认人类有感性的直观而不承认有理性的或智性的直观,因此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或本体的概念只能是消极意义上的而不能是积极意义上的,换言之,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或本体是不可知的。于是,我们不得不发问康德否定智性的直观的依据究竟何在呢?事实上,康德之所以否定了智性的直观是因为康德把人类认识能力分析为感性的和知性的两种不同的构成要素。概括地说,康德认为:感性是接受性的能力而知性是自发性的能力,感性只能直观而不能思维且知性只能思维而不能直观,感性与知性必须联合才能产生知识。在康德看来,如果我们假定存在智性的直观,那么就等于说我们承认主体思维中的一切杂多表象是通过知性的自发性活动(“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自动地被给予的,然而康德认为这是根本可能的。因为知性思维的自发性活动只产生“‘我思’表象”(the representation I zhink),所以尽管“‘我思’表象”必然伴随着主体思维中的其余所有的杂多表象,但是主体思维中的其余所有的杂多表象只能在知性思维前由知性之外的直观方式被给予,也就是通过感性的直观被给予。[5]153因此,知性不具有直观对象的能力而只具有思维对象的能力,是康德之所以要否定智性的直观的根本依据。然而,虽然我们只拥有感性的直观,但我们不能据此断定感性的直观就是唯一可能的直观方式;虽然我们不拥有智性的直观,但我们也不能据此断定智性的直观就没有可能为别的存在者所具有。因此,引文(2)暗示康德设想智性的直观可能为“原始存在者”(primorial being)或上帝所具有,当然,康德的这种设想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康德认为感性的直观是派生的(derivative),“我们的直观方式依赖于客体的存在,所以它只有在主体的表象能力为客体所刺激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5]90正是从此出发,康德才推论智性的直观是本源的(original),即智性的直观无须外在客体的刺激,而“本身就能给予我们它的客体的存在。”于是,康德认为智性的直观看来只能属于“原始存在者”(intellectual intuition seems to belong solely to the primorial being)或上帝。[5]90在康德看来,智性的直观只能来源于我们并不违反逻辑的合理构想。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拥有智性的直观,但是我们可以推想上帝拥有智性的直观,以便表明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或本体也许只能为创造了世界的上帝所知晓,从而把人类知识限定在现象界的范围以内。
通常认为以柏拉图和笛卡儿为典型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抬高了人类理性,而康德批判哲学则限制了人类理性。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这种认识尚属泛泛之论,不够具体。事实上,理性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抬高人类理性,是因为理性主义哲学肯定人类拥有理性的直观,批判哲学之所以能够限制人类理性,是因为批判哲学不承认人类拥有理性的直观。在康德看来,肯定人类拥有理性的直观就等于把人提高到了上帝的位置,是属于无理的僭越行为。那么,理性的直观对人类而言到底能否存在呢?
根据柏拉图和笛卡儿的论述,我们发现理性的直观不是在心灵的自然状态下自发地呈现出来的,因此,改变心灵的自然状态的实践或训练是使理性的直观得以可能的先决条件。如前所述,改变心灵的自然状态的实践或训练在柏拉图那里是通过教育和学习,而在笛卡儿那里则是通过普遍怀疑和宗教修行般的哲学沉思。尽管在改变心灵的自然状态的实践或训练上,柏拉图与笛卡儿分别采取了各自的方式或方法,但是他们借此所要达到的目标则是相同的,即无非是要使心灵的自然状态得到彻底地净化。正是在这种心灵的自然状态被彻底地净化中,柏拉图用“心灵的眼睛”看见了“理念”,笛卡儿用“心灵的单纯的直观”发现了“我是,我存在”。因此,柏拉图和笛卡儿以自身的哲学实践证明,理性的直观只有在心灵的自然状态被彻底地净化之后才是可能的。那么,什么是心灵的自然状态?彻底净化心灵的自然状态将意味着什么?显然,所谓心灵的自然状态,或者是心灵为感官知觉所禁锢的状态(柏拉图),或者是心灵不仅为感官知觉而且也为种种成见所蒙蔽的状态(笛卡儿)。因此,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所谓心灵的自然状态,至少是指心灵为感性的直观所拘限的状态。这样,彻底净化心灵的自然状态的实践或训练必然包括对于感性的直观的超越。因此,理性的直观也许在超越感性的直观的意义上是可能的,是能够通达感性世界之外的彼岸世界的。但是这一切也只有通过投身于柏拉图和笛卡儿所倡导的那种哲学实践才可能得以亲知,否则只作为一个局外人或旁观者就对此加以彻底地否定是缺乏正当的理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康德否定理性的直观恰恰表现出了康德自己的“独断”,这一“独断”也许真的狭窄化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正如禅宗的修行者通过修习“禅定”是有可能会“见性成佛”的一样,通过彻底净化心灵的自然状从而开发出最高认识能力的理性的直观,从而认识到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或本体也并不是绝无可能的事。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说,理性的直观又不是普遍地可能的。因为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处在心灵的自然状态之下的,所以对于形而上学的真理也并非人人都可以认识。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笛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序中的声明才更加耐人寻味,他说:“除了能够而且也愿意与我一起进行严肃的沉思并使他们的心灵完全从感官知觉和各种先入之见中摆脱出来的那些人以外,我不鼓励任何其他人读我的书。”[3]8可是如果对于形而上学的真理的发现就像柏拉图和笛卡儿所陈述的那样,必须通过心灵的自然状态的彻底净化,那么柏拉图和笛卡儿的哲学实践势必模糊了哲学探索与宗教修行的区别,以至于使理性的直观也不可避免地蒙上了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或许有鉴于此,所以康德批判哲学才取缔了此前备受理性主义哲学家所推崇的理性的直观,以便划清知识与信仰的界限,从而把哲学知识与宗教启示严格地区分开来。因为哲学要达到普遍性的思考,就必须拒绝一切神秘主义的诱惑,以免误入歧途。这样,在康德那里,哲学是批判,哲学无法提供可窥视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或本体的“心灵之窗户”。总之,对于理性的直观能否为人类所拥有这一问题的或肯定或否定的不同回答不仅关乎形而上学的命运,而且也折射哲学观的分歧。
我们之所以要对理性的直观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作出如此不厌其烦的甚至冗长的哲学考察,是因为我们最终想要借此表明柏拉图、笛卡儿与康德之间所存在着的哲学观的分歧,以及由此分歧所彰明柏拉图和笛卡儿哲学中所充斥着的宗教神秘主义的倾向,康德批判哲学(至少认识论)中所充盈着的科学主义的精神。考虑到柏拉图哲学产生的古希腊奥尔弗斯教的背景、笛卡儿哲学产生的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的背景,以及康德批判哲学产生的牛顿物理学的背景,这两种哲学观的分歧及其哲学思想的本质差异或许本不难理解。但是康德批判哲学确实变革了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开启了哲学的现代性。可是,我们站在哲学的传统与哲学的现代性之间徘徊不定,仿佛找不到了方向。因为我们面临着如何界定哲学的性质的大问题。哲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哲学是趋近于宗教呢?还是趋近于科学。如果哲学趋近于宗教,那么哲学必然要回答形而上学的问题;如果哲学趋近于科学,那么哲学必然要拒斥形而上学的问题。从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其主流方向仍然是接续康德所开启的哲学的现代性,使哲学与科学更加紧密地结合,更彻底地质疑或批判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然而,这样做也就使得哲学好像只能研究逻辑、语言分析或现象学的描述、解构等等,不一而足。因此,面对如此复杂的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哲学的性质呢?
收稿日期:2010—03—26
注释:
① 王太庆、王路、吴童立等学者主张将笛卡儿“Ego cogito,ergosum”译为“我思故我是”较妥,我同意以上学者的看法,故将旧译“我思故我在”更改为“我思故我是”。
标签:哲学论文; 柏拉图论文; 康德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笛卡儿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数学论文; 理想国论文; 推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