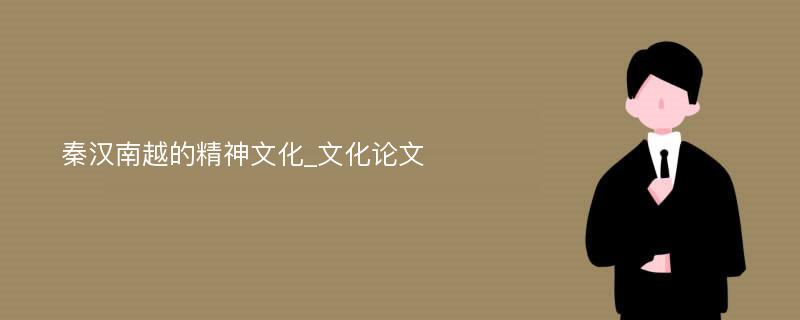
秦漢時期南越國的精神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越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秦漢時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紀80至90年代以來,廣州考古新發現推動了南越國史研究的持續熱潮,人們將目光聚焦於南越國相當成熟的制度文化和燦爛的物質文化,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相形之下,對其精神文化的研究卻較爲薄弱。究其原委,這與研究取向以及史料的匱乏都有關係。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復原和揭示南越國百年史的精神文化傳統,無疑是當前研究工作的重要課題之一。
如所周知,精神文化是文化結構中的深層内涵,相對於物質和制度層面而言,它是一個相當寬泛的領域,根據文化學者的研究,通常將其定義爲宗教信仰、道德規範、政治意識、價值觀念、審美趣味等層面。① 精神文化又“是一個複雜的多層次的能動體系,它們緊密交錯在一起,結果產生一種特點,這個特點構成每個時代、每個歷史時期文化本質特徵”。② 由此可見,探討南越國時期的精神文化,對於加深對南越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具有重要意義。筆者參加秦漢史年會時曾考察遇相關墓葬和遺址,對充滿南國風情的漢墓漢文物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因此不揣淺陋,在徵信於傳世文獻的同時,也注重從墓葬、遺址和出土文物中提取信息,並充分吸收學界已有成果,擬從宗教意識、政治意識、儒家倫理、建築審美、開放精神等方面作粗略考察。
一、事死如生的社會宗教意識與信仰
南越國是一個“在南越族分布地區、以南越人爲基礎,由中原漢族人割據中央而又臣服中央建立起來的封建王國”。③ 在這樣一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南越國的宗教信仰,既與中原相似,又有嶺南地域文化的烙印,形成了自身特色。
在古代中國,靈魂不減說淵源久遠,先秦到秦漢時期人們幾乎都相信靈魂的存在和死後世界,戰國墨家將鬼神觀念講得最明確,“天志”、“明鬼”說法代表了世俗對於死後世界的看法。儒家經典《禮記·郊特牲》云,人死後“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即便著名的無神論者荀子也承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④,反映出對喪葬祭祀之文化意義的尊重。出土的秦簡《日書》,則記錄了周秦之際西部地域的民俗信仰中光怪陸離的鬼世界。司馬遷在《史記》中百餘次說到鬼,五十五次說到鬼神,兩次說到“地下”世界。⑤ 秦漢時期宗教文化發達,鬼神迷信相當活躍,當時喪葬的禮制規範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這種宗教情緒制定的。立足於上述語境,我們以南越王趙眛陵墓爲個案來解析當地富有特色的宗教意識。⑥
南越王陵墓是迄今發掘的嶺南地區規模最大、随葬品最豐富的一座漢墓。該墓具有“前朝後寢”結構,其設計就是爲了死者冥間的王侯生活而備。其前室象徵墓主人生前的朝堂,東耳室爲燕樂場所,西耳室爲庫藏之所,墓主安放在中部的主室。東側室中殉葬夫人,模擬生前的後宮。⑦ 該墓雖然不是很大,但設計的布局模仿其生前宮室,體現墓主在冥間享受王者至尊待遇的意識。
南越王陵中使用了罕見的人殉,數量達十五人之多,被殉葬的有越王趙眛的四位嬪妃,另有庖丁、厨役、門亭長、宦者和樂伎等十一人。廣西出土的羅泊灣1號和2號漢墓,墓主人是受到南越國封爵的西甌君夫婦,在墓槨室下也分別發現了七名和一名殉葬的家奴。⑧ 這種現象的根源來自淵源久遠的死亡觀,人們對於死後魂靈的存在篤信不疑,認爲其生活如人間一樣,有著七情六欲乃至日常起居的種種需要,爲了滿足越王和貴族在地下世界的淫侈生活,所以要從人間帶去殉死的嬪妃宮人和侍者。據《漢書·趙敬肅王傳》,漢律不許殺人殉葬,所以當時中原地區人殉已基本絕迹,僅個別王侯墓葬殘存但數量甚少。相比之下,南越國不受漢法約束,這種蒙昧的靈魂信仰更帶有較强的原始性和血腥性,反映其社會文明發展程度明顯低於中原。
該墓出土的車馬儀仗圖帛畫殘片,同樣也蕴含了深層的葬俗觀念。據披露,該墓西耳室中發現的帛畫殘片是用紅黑白三色繪成,能看到類似車輪輻條等圖像。⑨ 這是唯一見於石室墓的漢代帛畫,也是漢代所有帛畫墓中墓主級別最高者,反映了嶺南文化與楚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聯想到該墓中西耳室随葬仕宦器物,東耳室随葬生活用品,再聯繫到馬王堆3號漢墓西壁帛畫爲《車馬儀仗圖》,估計此畫原來也類似車馬儀仗圖。帛畫內容表明,它與內地諸侯墓葬使用兵馬俑陪葬的用意殊途同歸,不僅爲了滿足王者靈魂在冥間出行的排場,並且保護南越王國及陵寢免遭外來侵犯。⑩
墓中隨葬的各種玉器蔚爲大觀,數量多達二百餘件,格外重要的有玉衣、玉璧等類型,均包含重要的象徵意義,投射了當時葬俗文化中對死後世界的複雜認識和矛盾態度。
先說其中的隨葬禮器——玉璧。據出土報告,墓主身穿絲綴玉衣,玉衣上下和棺槨內外隨葬玉璧達四十七件之多,上面刻有夔龍紋飾和穀紋等。在古代,人們將玉器視爲通天的靈物,《說文解字》:“巫以玉事神。”《越絕書》:“夫玉者,亦神物也。”因玉璧“外圓象天”(11),這成爲古代先民將其與天相關聯的心理基礎。按照周制,在祭祀天地的儀式場合中使用玉璧,《周禮·春官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至於喪葬文化習俗中的用玉,《周禮·天官冢宰》云:“大喪,共含玉。”《周禮·春官宗伯》:“疏璧琮以斂尸。”東漢鄭康成注曰:“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劉氏注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故其斂也,以禮天地四方之玉器爲之。”上述注文是說明漢代人觀念最有權威性的表白,可知以玉璧随葬殮尸是爲了用它來“通於天地”。
怎樣認識斂尸儀式中溝通天人之目的呢?這可以從漢代葬俗將上述功能具象化,衍化出所謂天門、璧門的現象中來得到解答。在四川省巫山等地發掘的漢墓中,曾經出土有石棺、銅璧等器物,這些器物上用漢隸鎸刻有“天門”二字,其形制被研究者認定爲是所謂“升龍護璧門”之象徵。(12) 由此推理,漢墓中随葬玉璧的確可能被賦予象徵天門的意義。换言之,即希冀死者靈魂沿著玉璧的天門或璧門升入天國。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七十一件玉璧,雖然没有見到類似字樣,但璧面所镌刻雙身夔龍紋飾圖形,也是大有深意的。我們知道,按照古人觀念,龍是引導人類升天成仙的吉祥神獸,鄭玄注《尚書·大傳》云:“龍,蟲之生於淵,行於無形,游於天者也。”《史記·封禪書》記載了黄帝乘龍升天的傳說。《大戴禮記·五帝德》說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山海經·大荒西經》稱夏后啓在“大樂之野”中“乘兩龍”。特別是馬王堆漢墓帛畫非衣圖中繪有天界、人間和地下世界,畫面上就繪有二龍穿壁圖像(13),寓意是墓主在二龍引導下穿越璧門進入地下世界,並憑藉此力量來升入天界。據此,便不難揭櫫越王墓中夔龍紋飾的玉璧所寄托的象徵意義。
在出土的玉器中,引人注目的還有使用了兩千兩百九十一塊玉片編綴而成的絲縷玉衣,做工相當考究,這是迄今漢墓中出土玉衣年代較早也是唯一的絲縷玉衣。以玉衣爲葬服用意何在?根據漢代道家說法,金玉斂尸可使軀體不腐,“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臘,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後漢書·劉盆子傳》稱,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據李賢注引《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爲札,長尺,廣一寸半,爲匣,下至足,綴以黄金縷,謂之爲玉匣。”今天看來固然是無稽的訛傳,但反映了古人對玉衣神奇作用的篤信。稍晚的葛洪《抱樸子·內篇卷三·對俗》亦云:“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上述漢晋典籍表明,當時流行的玉衣斂尸乃是企圖保護尸骨不朽。(14) 那麽,爲何要追求尸骨不朽呢?筆者認爲,這並不僅僅是出於愛護死者的情感,而是基於一種復生意識。因爲在秦漢時代的觀念中,只有同時具有靈魂和肉體的人纔能得道復生,如果肉體腐敗,靈魂就無法與肉體結合,使死者無法得以復生。後起的道教經典說:“死者尸體如生,爪髮潜長,蓋默練於地下,久之則道成矣。”(15) 這裏引申出的練形之說,可能比西漢人觀念來的更複雜,但它强調以原有的軀體爲基礎,强調“死而更生”是原有生命的延續,則可以爲上面分析做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當時佛教尚未傳入中土,人們尚無輪回轉世觀念,對死後世界的安排,或是追求升仙到昆侖山仙界,或將天國視爲靈魂升仙的歸宿。前者最早見諸戰國的《莊子》,後來主要發展於齊地;而後者則流行於同時期的楚地。我們在《史記》、馬王堆漢墓帛畫以及後來的漢畫像石中,不難找到這類觀念的直接記錄。反觀南越國墓葬遺存中,則未見到升仙到昆侖或天國的直接表白,給予更多關懷的是亡靈在幽冥中的起居享樂,可見其意識中的死亡歸宿主要停留在傳統的“黄泉”、“幽都”的地下世界。但追索玉璧殮尸習俗流露的宗教意識,也幫助我們揭示出南越葬俗文化中相形隱晦的升天觀念。
一方面期望死者在陰間享受奢侈生活,並且藉助玉衣保護尸骨不朽,期待其復生於陰間;另一方面,又希冀死者靈魂在玉璧和神龍引導之下早日升仙,進入天國——南越王墓葬蕴含的升天追求與陰間復生的矛盾,在兩漢社會葬俗文化中看來也帶有相當普遍性。這種具有內在矛盾的宗教意識,反映了本土高級宗教形成之前民俗死亡觀的不盡成熟。
至於如何避免死亡,也是當時宗教文化所普遍關注的問題。如秦始皇、漢武帝等都曾熱衷追求長生不死之藥。流風所及,遠在嶺南的南越王趙眛也樂此不疲,其墓中随葬的五色藥石和製藥工具就是明證。據研究,用五石入藥開始於戰國,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就講到齊王服五石治病之事。應是中原的方術之士將煉丹術和五石帶到了嶺南。根據鑒定,趙眛的卒年爲四十至五十歲,其早逝很可能與服用了五石有關。(16) 這從一個側面透露了南越國貴族對宗教養生文化和神秘文化的篤信態度,也可以窺見方士文化南播帶來的廣泛影響。
二、以倫理爲核心的儒家禮教精神
儒家禮教精神是中原文化觀念的核心成分,其內容主要包含等級制、禮儀制和以忠孝倫理爲核心觀念的充分內化的價值觀等。考察儒家禮教文化的南播,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秦朝文字統一措施的推廣和收效問題。秦統一之初,朝廷詔書至桂林,一般人都不認識。(17) 但曾幾何時,羅泊灣漢墓出土的南越國時期木牘《從器志》表明,“簡牘上的文字書體,與雲夢秦簡、馬王堆簡牘帛書文字相似”(18),其中漢字三百七十二個,標點符號十九個,文字書寫工整,筆法流暢,書法藝術水準不低,說明漢字文化在嶺南的統一是成功的,這成爲儒家禮教文化南播的傳媒平臺。
由此帶來制度文化的相對統一,如南越國官僚制度和禮儀制度的完善,證明了這一點。在官制方面,出土官印業已證明南越國官署和宮廷設官,幾乎完全是模仿中央朝廷和皇宮官制;在等級秩序爲主導的喪葬制度上,南越王陵墓的形制和埋葬方式基本符合中原諸侯王墓葬規格和形制。這透露出南越國對華夏政制文化的仰慕和模仿心態,也說明中原禮教文化精神所具有的强大涵攝力。
那麽,南越國文化成就當中是否存在儒家人士的直接貢獻呢?回答是肯定的。比如可以從其官僚制度和禮儀制度的完善來推測,如没有精通皇朝典制和儒家禮制的儒家人士随之南遷,則這些政治設施的設置是難以想象的。但另一方面,儒家精緻的典籍文化在這裏的流傳情形卻不容樂觀,我們知道,大量的考古發現揭示,漢初諸侯王陵墓普遍流行以簡帛典籍随葬的文化習俗,但南越王陵墓卻是一個例外,墓中未曾出土任何典籍,究竟是因爲該墓不具備保存書籍的條件,抑或是這種習俗的缺席呢?從該墓中能够保存有漆器和羅泊灣漢墓中存有木牘《從器志》來推斷,後者可能性更大一些。(19) 這足以證明,典籍文化在南越國貴族社會中的流行程度大約遠低於中原。《後漢書·循吏傳》中所記東漢儒臣在嶺南傳播儒學、移風易俗的事迹也反證了這一點。
再來看禮教核心精神的傳播問題。在邊遠的南越王國文化中,禮教精神究竟有多少和多大程度上滲透到這裏,則需要從史料線索中仔細鑒別加以判定之。首先,儒家孝道倫理在這裏屬於普遍認同的基本文化價值。據《史記·南越列傳》載,在呂后執政時期造成了與南越國交惡的情形下,漢文帝采取了非常措施,“初鎮撫天下……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招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後陸賈奉使南越以此相告,並恩威並施,越王趙佗大受感動,“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越佗願意“北面而臣事漢”的動機,也是稱“不敢背先人之故”。朝廷的感化方式能够奏效,說明孝道觀在南越國是被認同的。
厚葬文化在這裏的流行也是有力證明。南越國貴族普遍厚葬之風氣甚濃厚,南越王陵墓的厚葬情况已如前述;又如1976年發掘的羅泊灣1號漢墓,整個墓制模仿了商周以來中原貴族墓制度,隨葬器物一千多件。部份銅器如鼎、壺、鈁、匜等與中原出土者相同,另一部份如銅鼓、銅鐘、越式鼎等富有地方特色。再如廣州柳園崗漢墓11號,墓室較小,卻出土了一百零一件銅器玉器和陶器等。(20) 可見舉國上下,只要有能力者就實行“厚資多藏”的做法。厚葬文化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上古中國人慎終追遠的祖宗崇拜觀念,儒家興起後强調宗法人倫,將孝道思想貫徹到厚葬模式當中,對死去祖先特別是父母的厚葬,被看作最主要的孝行,造成爲中古社會喪葬文化的精神宗旨,也是西漢厚葬風潮泛濫的驅動力。厚葬事實說明,孝道觀念對這裏同樣有深遠的影響。
女性婚姻倫理觀念和忠君觀念,在南越國史傳亦有絕索可尋。南越王嬰齊死後,王后與漢使私通,爲當地臣民所不耻,史稱“國人不附”,並成爲激化內部矛盾的導火綫之一,表明中原婚姻的貞節觀念在這裏同樣深入人心。呂嘉的叛亂固然非一日之寒,但其策略卻是打著維護南越王趙佗威信、懲罰嬰齊王后之背叛越王的“淫行”的旗號,所以司馬遷評論道:“呂嘉小忠,令佗無後。”(21) 他使用“忠君”的尺度評騭史事,頗值得注意。可以說,這些倫理觀念與呂嘉之亂有多重聯繫,對該地區歷史變局起到很重要的影響。
三、王權至上和向心與離心兼存的政治意識
政治意識是人們在從事政治活動的指導思想和價值目標,它透過思想家的言說和政治家的實踐進而與政治發生互動,影響到歷史的發展。南越國時期的政治意識,集中反映在統治階層對待君民關係、朝藩關係和民族關係諸方面。
如所周知,在漢初以來的分封制度下,諸侯王獨霸各地,具有君臨一方的威權和勢力。反映在政治觀念上,就是無條件的尊王意識,這是南越國文化中十分突出的政治精神。南越王趙眛之墓采用了多達五百塊巨石依山建成,形制的宏偉,陪葬物的極其豐富,無不襯托王權的至高無上,反映南越王的政治權威,包含著彰顯、尊崇王權的專制意識。
歸順和割據傾向並存、離心與向心兼容的政治取向和立國意識,這在南越國統治者處理與中央皇朝關係時均表現得十分突出。
南越國是在中原秦皇朝土崩瓦解的特殊情勢下創建的,就趙佗的心態而言,並没有打算與繼起的中央政權長期對峙,所以劉邦派遣陸賈出使南越,趙佗馬上表示了歸順的意向。呂后時期轉而采取封銷和打壓措施,激化了雙方之間的矛盾。後來陸賈奉命出使南越修補,取得了成功。正如張榮芳先生所指出,“縱觀南越國九十三年歷史,除呂后時期趙佗一度稱帝之外,大部份時間是以諸侯王國的面目出現”。(22) 除了皇朝主動調整對藩政策外,趙佗對故土切不斷的親情聯繫和文化情結,同樣是推動南越國歸屬中原的重要因素。後來閩越王攻打南越邊境,繼位王趙胡没有擅自興兵反擊,而是請中央派兵,被認爲是“守職約”的表現。趙胡又派太子嬰齊去長安宿衛天子。嬰齊死後,子興即位,“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23) 趙佗子孫對中央皇朝的態度也反映了一種歸順心態。
但另一方面,割據情結也是客觀存在的。據史載,趙佗在漢初和高后時兩度“自尊號爲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孝景時趙佗稱臣,“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24) 第三代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似乎放棄了帝號。但其墓葬中發現了南越文帝的龍紐金印。南越國在國內還使用自己的帝制年號,該墓中出土的八件銅鐃上均有“文帝九年樂府工造”銘文(25),文帝九年相當漢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另外,在南越國宮署遺址中,曾出土了形式多樣的“萬歲”吉語紋飾瓦當。“萬歲”一詞在西漢時已逐漸被限定爲皇權政治用語,用來傳達尊君的政治情緒,如劉邦命陸賈著《新語》,“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26) 再如漢九年,劉邦爲太上皇祝壽,“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27) 長安考古表明,文字瓦當大約出現於漢景帝時期,“萬歲”瓦當是西漢京畿地區皇家建築的组成部份。(28) 南越國宮署建築中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越國制度僭越和妄自尊大心態。事實上,即便在兩漢同姓諸侯王中,覬覦皇權進而發動反叛者也所在多有,南越國統治集團的確存在明顯的離心傾向。由於地理環境和歷史原因形成的差距,導致嶺南與中原之間的政治關係不盡穩固,整個中古時期,許多漢族强力者在邊緣地域中常常窺伺獨立的時機,例如五代時廣州一度也出現過割據政權。
需要强調的,還有南越國“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所體現出來的寬容胸襟和政治氣度。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依靠“中國人相輔”,實行郡縣制的同時,大膽吸收越族首領參加統治,如任用有威望的南越首領呂嘉爲丞相,封呂嘉之弟爲將軍,呂氏宗族中爲長吏者七十餘人。(29) 還采取“以財物賂遺閔越、西甌、駱,役屬焉”(30),“懷服百越之君”(31),與之友好相處。二是趙佗本人带頭采取一些越人習俗,自稱“蠻夷大長”;三是提倡漢越通婚,如第三代越王嬰齊就娶越女爲妻。這些政治措施所蕴涵的兼容精神,推動和加速了漢越民族的文化融合,是南越國政治意識的精華所在。
四、審美意識和建築文化精神
如果說盛行於中原的漢墓壁畫或帛畫在南越國較爲罕見,那麽藝術考古的缺憾則在新的地下發現中得到補償。2000年,人們在重現人間的南越國宮署遺址中領略到了頗有創意的建築審美意識,這也是迄今發掘的唯一的兩漢地方宮署遺址。
據發掘簡報,該遺址主體是石砌的方形蓄水池和曲流水渠組成的園林水景、迴廊散水和磚砌水井等。石陂池的整體面積可達四千平方米,與之相連的石砌曲渠長逾一百八十米,這兩處結構聯成一體的人工水景,規模較大,各種相關建築設施也頗具氣勢。(32)
上述園林水景所展現出來的審美意識,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景觀布局上追求曲徑通幽的曲綫美和深邃美感。南越宮苑中的彎月形石室,平立面均呈彎月形,凹下如水池,兩個開口處與曲渠連接,東西壁的石墻都砌成圓弧形。曲流石渠的盡頭建有曲折的迴廊,從殘存的大型石件如礎石、八棱石柱等可推知迴廊建築的規模較大。南北走向的蜿蜒石砌曲渠,將石池水景和南面的彎月形的石室和曲廊連接起來。曲渠西端鋪設的石板平橋,橋頭的九塊步石,也作彎月形排列,而曲廊又將宮殿建築群相連接,給人一種曲折迴環、不可窮盡的感覺,在迂回映帶之間形成深遠意境。
二是追求水景的動感和静感互補之美。據實測數據顯示,曲渠水平高度東高西低,溪水與渠底密鋪的灰黑色河卵石相映襯,形成粼粼碧波的人工水景。與曲渠相連的彎月形石室,放養了大量觀賞用的龜鱉,水流引進石室凹池後得到緩衝,平静的水面與曲渠潺潺水流相映成趣,兩者之間動静的結合恰到好處。
三是在藉景中營造人工與天然相映成趣的複合美感。山與水是古代造園中最重要的元素,該宮苑遺址在越秀山之南,從苑中極目北望,層疊的崗巒與宮苑中人工水景交融,遠山近水,開拓了園林中的視野(32),將人造景觀和自然山水融爲一體,體現了古代文化中對“天人合一”藝術境界的追求。(33)
淺見以爲,還可以將其與都城長安的園林稍作比較,以領略其异同。在漢人所撰的《三輔黄圖》中辟有“園囿”、“池沼”等篇,記載了都城長安大量的皇家園林水景,如“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的“宜春苑”,三百餘頃“清淵洋洋”的昆明池,“周迴十頃,有采蓮女嗚鶴之舟”的太液池和“宮人乘舟弄月影”的“影娥池”等,這些園林池沼的造景,多带有宏大開闊的皇家氣派,具有向往彼岸神山聖水的宗教意味;(34) 而南越王宮御苑園林則以静致迴環之美取勝。正如學者所指出,“這種園林的設計專長,在於利用有限的隙地營造出寬廣無窮的自然風光,達到以小見大、以短見長的效果”(35),從而開創了明清時期造園的藝術濫觴。南越園林與長安宮苑各有千秋,對於揭示漢代建築文化的審美意識來說,具有明顯的互補價值。
南越國宮署遺址高水平的建築文化內涵和豐富的審美意識,無疑爲南越國的精神文化平添了神來之筆,令今人仍舊可以領略到其文化中靈動秀逸的一面。
五、商業意識和開放精神
根據世界範圍內的地域文化類型研究,人們早就發現,沿海文化(但非海洋文化)與內陸型文化有很大不同,一般來說,前者富於冒險精神和商業精神,具有較强的文化開拓性等。循此來觀察南越國文化,大體上可以得出近似的結論。
擁有“負陸面海”優勢的南越國,與周邊東南亞國家的交通有著舟楫之利,因之其航海造船技術起步早,並且達到相當水平,如史籍記載“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36),近年在當地漢墓中發現的陶質、木質航船冥器很多。據介紹,廣州漢墓中出土的這兩類船模多達十五件,爲全國之冠。1975年在廣州發現的秦漢造船廠址,估計可造長二十米左右的大船,河海交通的興盛可見一斑。(37)
沿海的便利條件,使這裏與外域經貿往來較多。《漢書·地理志》:“番禺,亦其一都會也。”“處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其中的果布,據研究,應即“果布婆律”,是馬來語龍腦香kapar barus的音譯。這種香料盛產於蘇門答臘、馬來半島等地。(38) 南越王陵墓中出土有未加工的象牙、象牙器、玻璃器以及瑪瑙、水晶等多種質料的裝飾品,還有罕見的金銀器,據研究,部份器物是從中亞或南亞輸入的。(39)
南越國對外來物態的接受,轉化爲地域性習俗,有些很快又影響到內地,這方面的典型例證就是燃香之俗。中國本來没有燃香的習俗,燃香習慣首先從這裏開始。南越王陵墓出土有香料和香爐。據統計,廣州地區漢墓出土物中,已發現熏香爐二百餘件,其中珍品有南越王墓中的“四連體銅熏爐”。漢代考古發現,出土的漢代熏香爐式樣有南北之分,就時間先後而言,南越蓋豆式熏爐在先,中原博山式熏爐在後,這不僅說明香料由海外輸入的路綫是先至番禺再轉運到中原,而且該習俗是由這裏傳播開來的。
另一方面,南越國在對外交往中又輸出哪些物產呢?根據南越王陵墓的發掘報告,該墓出土的絲織物品,其數量和種類都不亞於馬王堆漢墓的成批絲織物。就出土實物統計,西耳室內共出土絹、羅、紗、組帶、錦、綺六大類織物,每一類中又分別有不同的品種,還有爲數不少的整匹絲絹,但均已碳化。同時,該墓中還出土了印花凸版,是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一套織物印花工具,反映了南越國絲織業的相當水準。在廣西羅泊灣七號墓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實用織機的部件,如紡錘棒、繞綫句”板、吊杆等,被專家鑒定爲較原始的斜織機。上述現象表明,嶺南地區出産的絲製品很可能已經成爲對外輸出物品中的大宗。
上述可見,南越國的中外文化交流較爲活躍,沿海文化特質較爲明顯,這些成爲釀就其開放精神的温床。限於史料,本文描述其開放意識的信息來源主要局限在墓葬出土的物態文化上,但這些來自海外的器物,固然是反映了貴族統治者不惜代價,遠距離獲取海外的奇物异珍滿足其奢侈消費和貪欲,但可以窺見南越國廣泛地開通對外交往,與周邊國家互通有無的積極姿態,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有限的開放精神的物化證據。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漢廷平定南越實行郡縣制後,這裏仍舊是漢帝國對外開放的海上絲路的重要起點,南越國文化中的開放精神得以綿延久遠。
六、南越國土著的精神傳統
據考證,南越國領土南抵今天的海南省和越南,西抵今廣西,北抵五嶺與長沙國爲界,縱橫數千里,民衆百萬。在西漢初年的中華大地上,它是一個疆域遼闊、民族衆多的邊地諸侯國,號稱百越的少數民族長期生長於斯,創造了自身燦爛的文化。秦朝統一後,土著文化與數十萬秦軍隊移民爲載體的漢族文化之間產生了積極的融合,既是南越國精神文化的重要淵源,也是這個時期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
我們不宜過高估計當地社會文明水準,到了東漢時漢族循吏還在推進文化傳播和改變當地的落後狀况,反證南越國民間的土著文化可能還停留在較欠開化的層次上。三國時呂岱回顧說,秦漢之初該地“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异,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甚至到三國之初習俗還是“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40)
根據廣東多年考古發掘,迄今還没有發現越人單獨埋葬的墓地。(41) 這個事實足以說明,當地土著越人已經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漢族文化,或者說漢越文化的融合已經初見成效,由此又可以窺見越人土著對外來高级文化的寬容和接納心態。
值得關注的,是當地少數族墓葬中的民族傳統問題。儘管在廣東没有發現越人單獨埋葬的墓地,但在其首領墓葬中仍舊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傳統的痕迹。如廣東發現當時的木槨墓,“隨葬的銅、陶器物全爲地方的器形,没有漢文化的器物共存”(42),據判斷,這些墓主人也許就是越人首領而當了南越國高官的。
南越國土著文化的習俗在廣西漢墓中更爲典型,例如1972年發掘的廣西西林縣普馱墓,該墓隨葬有石寨山式的銅鼓,骨骸以綠松石、玉管和瑪瑙串珠編綴的絹布“珠襦”裹殮,銅鼓裹外随葬器物四百多件。其中帶筘和珠襦玉石飾品的造型與石寨山所出也極爲近似。(43) 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墓底腰坑設置和人殉的習俗,以及采用獨特的民族樂器隨葬。這方面如廣西羅泊灣一號墓中,發現有七個殉葬者尸骸;墓中出土有羊角鈕鐘、筒形鐘等就是例證。(44) 上述墓葬的文化內涵在於,它們鮮明反映了南越國西甌地區句町上層强烈的民族意識。在楚漢文化大舉推進並整合土著文化的情勢下,他們並未丟棄自身的民族文化,起碼在習俗層面仍頑强的保持著某些上古舊傳統。從不同時段墓葬看,大約到了南越國後期,尤其是到西漢中期這類現象就愈趨淡弱了。另外,墓中銅鍋、耳杯、騎俑等則與內地幾乎完全相同,這類隨葬器物提供了漢越文化逐漸融合的生動象徵。
土著人士中的離心傾向和割據意識,在呂嘉事件中充分地顯示出來。其實,當年越人頑强抵抗秦軍的事件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民族主義情緒在秦漢之際也是帶有相當普遍性的問題,呂嘉家族反叛事件的深層本質,反映了當地土著貴族對於中央皇權統一的抵制心態。儘管這在當時可能是民族關係中的一種支流,但的確也是一種客觀存在,後來土著與漢族統治者之間的衝突也並未終結,到了東漢時轉化爲駱越族上層對漢朝的反抗。邊緣地區的統一與反統一的鬥争是中古歷史上的重要主題。
本文開篇曾援引文化史家貢恰連科的意見,指出了精神文化是一個複雜的多層次的能動體系,它們緊密交錯在一起,所產生的特點構成每個歷史時期文化的本質特徵。那麼,南越國精神文化的特色是什麽呢?綜上所論,筆者初步認爲,一是漢族文化的主導性。遠在嶺南地區的諸侯王埋葬制度和其中所透露的宗教意識,表明漢族文化觀念和意識在當地上層中的主導性;冥間世界的安排表明,西漢時期嶺南諸侯國的世俗文化觀念與中原幾乎没有大的差异,世俗觀念的傳播和整合之廣泛程度較高,這無疑成爲後來漢武帝構想並實施“六合同風”文治理想的社會前提。二是同時又保持了較多的落後性,越王墓和貴族墓的人殉現象以及典籍文化流傳綫索的闕如,就說明了這個問題。三是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開放性,前者反映在政治意識上的割據傾向,以及風俗層面上對當地土著民族之精神文化的保留上;後者則反映在對楚漢文化的兼容並蓄,乃至對海外習俗的接納等現象上。南越國統治時期結束後,中原獨尊的儒家文化和其他相對發達的社會文明形態以較快的速度傳播到嶺南地區,這裏迎來了一個精神文化飛躍發展的新時期。
注釋:
① 參見郭齊勇:《文化學概論》第六章《文化的系統、結構和功能》,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 [蘇聯]尼·瓦·貢恰連科著,戴世吉等譯:《精神文化:進步的源泉和動力》,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年,第182頁。
③ 黄崇岳等:《華南古越族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歷史貢獻》,《文博》1998年第3期。
④ 《荀子集解·禮論》,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78頁。
⑤ 參見王子今:《史記的文化發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7頁。
⑥ 依漢制,諸侯王墓稱陵,這在《後漢書》中直接記載,例如《明帝紀》提到漢明帝前往祠祭“東海恭王陵”、“定陶恭王陵”和“沛獻王陵”等可證。徑稱爲“某某墓”則是通俗的泛稱,並不符合漢代禮制。因此,爲尊重歷史起見,兩漢諸侯王墓宜沿用其原始名稱,如近年發掘的西漢獅子山楚王墓葬已正式命名爲“楚王陵”。南越王同樣是被中央皇朝肯定其合法性的諸侯王,故其墓應予以正名,當稱陵爲是。
⑦ 參見廣州文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⑧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38~439頁。
⑨ 參見林力子:《西漢南越王國美術略論》,《美術史論》1991年第4期。
⑩ 參見劉曉路:《中國帛畫》,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4年,第81頁。
(11) 《白虎通疏證》卷八《瑞贄》,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51頁。
(12) 參見趙殿增:《天門考》,《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
(13) 參見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编:《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
(14) 前述玉璧等玉器的隨葬,除了所謂“通於天地”的宗教意識外,也同樣有保護死者肉身不壞的用意。
(15) 轉引自傅勤家:《中國道教史》第八章,上海:上海書店重印本,1990年。
(16) 參見黄淼章:《談談五色藥石與南越王趙眛之死因》,《秦漢史論叢》第七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7) 參見朱紹侯等:《中國古代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1頁。
(18) 《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438頁。
(19)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漆器雖然多已腐朽,但器形可辨者有耳杯、盤、案、盒、卮、奩等,又有漆博局、漆屏風等,許多種類花紋尚可辯識,由此推斷,倘若墓中随葬大量典籍簡牘的話,應該有可能被辨識。
(20) 《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439頁。
(21) 《史記·南越列傳》太史公曰,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977頁。
(22) 張榮芳:《略論漢初的南越國》,《秦漢史論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38頁。
(23) 《史記·南越列傳》,第2972頁。
(24) 同上,第2970頁。
(25) 《西漢南越王墓發掘初步報告》,《考古》1984年第3期,第229頁。
(26) 《史記·陸賈列傳》,第2699頁。
(27) 《史記·高祖本紀》,第387頁。王春瑜先生認爲漢武帝時該詞纔轉化爲皇權政治用語,似欠妥,因爲自西漢初年起“萬歲”就專用於宮廷場合了。王文僅使用文獻史料而忽略了萬歲瓦當等考古資料。見王春瑜:《萬歲考》,《歷史研究》1979年第9期。
(28) 西漢考古發現的萬歲瓦當,主要出土於西漢長安宮殿區。但在漢代京畿之外的遼寧、臨淄等地也有發現,具體出土地點當屬地方官府的建築遺址。參見陳根遠等:《屋簷上的藝術——中國古代瓦當》,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
(29) 呂嘉政變時下令國中,强調“太后中國人”來煽動反叛情緒,這足以反證呂嘉是當地土著人。
(30) 《史記·南越列傳》,第2969頁。
(31) 《三國志·吳書·薛綜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251頁。
(32) 廣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1期。簡報稱“規模宏大”,拙文以爲用“較大”爲妥,因爲倘若與長安園林相比,似不宜用“宏大”來描述。
(33) 麥英豪等先生已做宏觀研究,對筆者深有啓發。參見上引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簡報》;馮永驅、麥英豪等:《南越宮苑,中華瑰寶》,秦漢史研究會第八届年會論文。
(34) 參見王復振:《中國建築的文化歷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7頁。
(35) 《南越宮苑,中華瑰寶》。
(36) 沈懷遠:《南越志》,載《南越叢錄》卷二。
(37) 參見上海交大造船史話組:《秦漢時期的船舶》,《文物》1977年第4期。
(38) 參見韓槐準:《龍腦香考》,《南洋學報》第2卷第1輯。
(39) 《西漢南越王墓發掘初步報告》,第230頁。
(40) 《三國志·吳書·薛綜傳》,第1252頁。
(41) 麥英豪:《廣州地區秦漢考古的發現與收穫》,《秦漢史論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42) 同上。
(44) 《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439頁。
(44) 蔣廷瑜:《廣西貴縣羅泊灣出土的樂器》,《中國音樂》198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