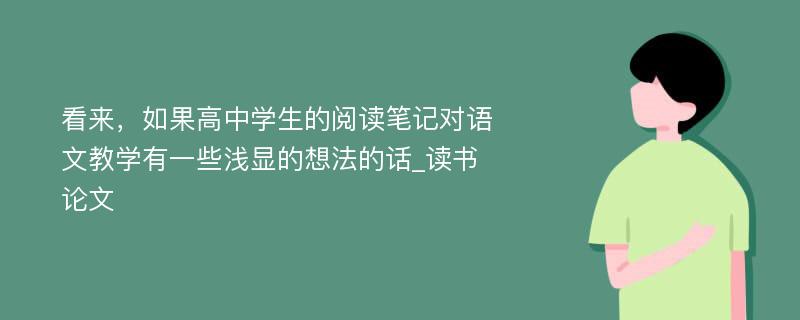
仿佛若有光——由一位高中生的阅读笔记思考语文教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有论文,语文教学论文,笔记论文,高中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直忘不了35年前的那个“吕叔湘之问”——
何以两千七百多课时的中小学语文课程,学生的本国语文还是多数不过关?而少数学得好的学生,却无不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
经吕老这么一问,长期以来,人们几乎都把检讨的心思放在了课内,于是有了种种课堂教学的改革与探索,蔚为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语文教改的热闹景观。改革也确实部分回答了吕老的质疑。然而疑问依然没有真正解开,后来甚至还出现越解越糊涂、越改越复杂的景况。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实有一个可穷究本然、揭示规律的研究方向,有可能长期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吕老所说的“少数学得好的学生”那一头,他们所“异口同声”说出的普遍经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对它研究清楚了吗?做过哪怕是起码的事实调查了吗?
多年来,专家们对语文课程的性质任务做了反复深入的研究,课程标准越写越长,空间想象越来越丰富,解说越来越详密。我说过,关于语文教学的“原理”,怎么说都不嫌过分;可是语文学习的“机理”,却一直沉睡在“黑箱”里,还没有人去认真研究如何打开它。只要“箱子”未打开,随便胡猜瞎说都是容易的。似乎“原理”也就是“机理”,只要明白了语文课程的一大套“原理”、“通则”,“箱子”里的东西就一目了然了。然而事实很无情,它一次又一次嘲弄了这样的痴想与神话,语文的课程改革,至今仍是举步维艰。
几乎近半年,我断断续续都在读一位名叫白杏珏的高中学生的读书笔记。之所以断续,并不是没有完整的时间,而是我不得不边读边思考。这思考也时断时续,因为很艰难,难在它总是逼着我一再思索而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位中学生读者,在高中课程负担不轻的状态下,能够如此自觉地坚持自我书写?是什么心理动因在支持着她几乎不间断地完成私人作业?尤其是,她所读过的那些书,是如何孕育成她那健康而活跃的文字生命的?
粗略统计一下,白杏珏笔记里所涉猎的作家当不下60位,而实际所读肯定还不止此数。在她的同龄人特别是女生中,喜欢读小说散文和写景言情的作品的,可能是大多数,甚至还可能集中于几个青春偶像甚而成为他们的粉丝。白杏珏所读则大异其趣,而是偏重于抒写内心体验和表现智性思考的文字,也就是说,其目光已开始从外部世界的纵览,转向了内部世界的审视;从欣赏他人情感经历的描述,返回对自身经验世界的体察。很多教师都曾发觉,高中生不同于初中生的一大心理特点,是少年人相对开放的心扉明显开始走向封闭,尤其是与教育者和成年人的交流变得内敛和警惕。当高中班主任的,会因此感到德育工作比起初中显得艰难。我认为,这正是中学生心理成长趋向成熟的阶段特征和客观规律。“封闭”恰是内在的需要,是一种自我窥视的表现,也可以称之为“关门思考”。白杏珏的读书取向,正是切合了她的精神发育的自觉心理选择;而她则显得特别自觉,也更为成熟,因此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意义就在于提醒,提醒我们:说教型的德育工作和指令性的语文教学,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一厢情愿,不再隔靴搔痒?教与学失之交臂的状况,可有根本改变的途径?
白杏珏的读书笔记,留下的成长足印之所以深刻,原因之一,首先是她对“谈话”对手的高位选择。无论是周国平、史铁生、张承志、简媜、梁文道,还是梭罗、纪德、尼采、卡夫卡、乔布斯,莫不来自古今中外杰出的智者、思想家和作家的群落。她还有幸“遇见”了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的历史学家、陈之蕃这样的科学家,开始感觉到文化在历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知道在文学中可以寻找历史的痕迹。同时,她还发现写作在情感与理性、文学与科学之间会有“一个最适宜的位置”。但正如她自己所说,与这些思想者的遇合,乃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是需要“谋划”的。我十分惊奇于她所使用的“谋划”这个词儿。如此强烈的心理期待和主观抉择的姿态,在当今的中学生中是罕见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我们得先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读一读白杏珏笔记里对20位作家的推介,不难看出她正是先有了与潜藏在自身内部的“另一个自我相遇、相知、相惜”,才有了对那些杰作价值的精准“发现”。其次一个原因,便是她对笔记写作的恒久坚持。日复一日、年深月久地留下“对话”的记录,需要何等的毅力!勤动笔墨,是她自觉完成的日常功课,但却不是刻苦的修炼。我并且相信,这样对读书心得的记录乃是即时性的,是由于随时适意的交谈和注意瞬间的捕捉,故显得十分真实而鲜活。我在持续阅读那些笔记的过程中,常能够感觉她好像每天都在和那些思想者促膝而谈、謦欬相接,反应是如此的机敏而准确,感觉又是那么的轻松而愉悦。由阅读对话而思想碰撞,因碰撞而激起思想的火花,照亮了平时未曾觉察的心灵角落,从而拓展了思想的宽度,掘进到思想的深度。这样的例子在她的笔记里可谓俯拾皆是。这里,且允许我采用较为机械的方式,大体把它归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体验型。所读的内容与自己的经历类似、经验相近,遂将此经历、经验写下来加以储存。例如:
(一)
其实,只有安静下来,人的心灵和感官才是真正开放的,从而变得敏锐,与对象处在一种最佳关系之中。
——周国平《品味平凡生活》
总觉得夜深了写文章是件很美妙的事,如果不困倦不疲乏,在极度安静的环境下,放一首歌,写一段文字,应该是心最舒缓的时刻。而那些夜半书写下的文字在日后看来,总有一份难得的从容沉静。夜深,心静,我也就逐渐放纵自己沉入那个美妙的文字世界。在喧闹的环境下写作至多是一种证明。
——白杏珏
(二)
独处,为了重新勘察距离,使自己与人情世事、锱铢生计及逝日苦多的生命悄悄地对谈。
独处的时候,可怜身是眼中人,过往的人生故事一幕幕地放给自己看,挚爱过的,挣扎过的,怨恨过的情节,都可以追溯其必然。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那些结局,也不管我们曾经为那些故事付出多少徒然的心血,重要的是,它们的的确确是生命史册里的篇章,应该毫不羞愧、毫不逃避地予以收藏——在记忆的地下室,让它们一一陈列着,一一守口如瓶。
独处,也是一种短暂的自我放逐,不是真的为了摒弃什么,也许只是在一盏茶时间,回到童年某一刻,再次欢喜;也许在一段路的行进中,揣测自己的未来;也许在独自进餐时,居然对自己小小地审判着;也许,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只有一片空白,安安静静地若有所悟。
——简媜《独处》
记得从前有一次,英语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慎独。谨慎地独处,小心地面对自己。而后读周国平的书,也提到了独处。似乎独处是人生必修的一门功课,却绝没有老师教授,亦没有同学陪伴,只能在静默中,靠自己,一步一步行到成熟的彼岸。挚爱的、挣扎的、怨恨的情节,在独处时回放给自己看。观众只有一人,但因为有了过去的自己的陪伴,而不会觉得孤单。人必须有一些时间独处,自己与自己交谈,如此这般,才不会遗忘了心内的自我。毕竟生活太忙碌,我们为了物质而奔忙,若再不抽出点时间给自己,我们必将成为人潮中模糊到没有面目的那一个人。
——白杏珏
从亲身经历的夜半书写、英语课上教师的板书,发现与所读文字的彼此关联而得以印证,这也许是阅读最常见的交流状态。事实的联想,是其他形式的联想与触悟的感性前提。茅盾先生说过,阅读者“应当一边读一边回到他所经验的人生,或者一边读一边到现实的活人中去看”。笔记中有这样一则:读到周国平说起“喜欢讲自己的人多半是在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白杏珏认为所谓“酒后吐真言”很是可疑,那不是在“讲自己”而是在讲述“自己的角色”,世上没有多少人发现自己是在舞台上——这就是书写间接观察体验的一个好例子。
第二种,体认型。这是指在阅读中发现自己的认识理解,正与所读对象的观点相同或相近,在认知上找到了吻合与认可。其中,有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达方式去复述的;也有做出诠释和解说的,从而使得某一话题有了更为清晰的展现,某一观点有了更为醒豁的阐释与证明。从内容上看,这种体认型的书写,由于融入了作者的思考,比起体验型的书写有着更多的理性色彩。例如:
(三)
我们不一定能够在计算好的时间抵达我们的港口,但我们会保持正确的航线。
——梭罗
我们的聪明应用于目标的精确定位上,方向一旦确定,剩余的便是为之努力了。把太多的时间精力耗费在寻求捷径上,不仅不是节约精力的方法,反而容易迷途。我们也许会误期,但我们至少胜利地抵达了港口。
——白杏珏
(四)
诗歌,那不过是渲染着情感的真理;音乐,是无字的情感;宗教,是幻象中表现的智慧。……宗教衰落是由于推理过多。如果使我们的信仰变成愈加正当合理的东西,一定以为我们是对的,那么我们将愈加变得不敬虔了。……这种宗教造成了个人的自私,不但卑视其他的宗教,并且使宗教的信仰变成了他自己和上帝的私人契约。
——林语堂《心灵快乐吗》
宗教是幻象中表现的智慧。是的,宗教原本就只是虚幻的空中殿堂,是建立于精神,而不是物质之上的。只是一旦宗教的影响力膨胀,人们总难免开始希冀着以宗教之名谋取实利。要谋取利益,必须使这个幻象变得如金币一样真实。于是种种为了自圆其说而不断循环衍生的学说理论层出不穷,神父在看似一砖一瓦地加固宗教基石,实则在动摇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最珍贵的本源——源自心灵的虔诚。宗教之所以神圣,便在于追随者是毫无所求地信仰——若真有所求,也只是求一片心灵乐土,而不是所谓财富、健康、死后进入天堂。宗教本是幻象,只为心灵而生。
——白杏珏
(五)
用成批的方法是不能培养出儿童的。那样做会使所有的儿童成为弃儿。他们将失去母子之间微妙的同情心。
——赫兹勒《论柏拉图的教育》
集体……一个以荣誉之名困住无数自由灵魂的名词。我们自小便尽己所能融入到不同的集体中,这种以共性为至高准则的传统从遥远的古代一直延续至今。而我们的孩子是否真的具有了所谓的集体意识与集体荣誉感?至少,目前已成人和未成人的孩子大部分仍是自私的,虚荣的,区别只是在于是否懂得给自己苍白的内在镀金。我们所期待的那种雷锋式的、拥有普照众生的能力的太阳之子哪儿去了?事实是,不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的人不可能成为太阳,不懂得何为爱、何为温情的人不可能具有炽热的内里。
——白杏珏
以上三则,或以“目标的精确定位”进一步诠释“保持正确的航线”;或针对宗教衰落是由于“推理过多”而导致人的自私的观点,分别从“以宗教之名谋取实利”的世俗存在,和“宗教本是幻象,只为心灵而生”的神圣本质这两个方面,对林语堂的观点作出个人解说与简约论证。赫兹勒论柏拉图的教育一段文字,尤为精彩。“用成批的方法是不能培养出儿童的”,是个十分通俗的说法,如果不作明确解释和适当演绎,可能失之简单肤浅,笔记则联系切身经历和体验,对当下仍以“集体”名义采取“成批培养儿童”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方式加以剖析,直陈弊害,具有相当强烈的批判精神。其深刻的体认,往往因注入主观的情感而更富说服力和感染力。
第三种,体悟型。体认与体悟,本也不必严加区分,甚至在体验中也会带出感悟,例如前面讲到“在喧闹的环境下写作至多是一种证明”就有相当深刻的悟性。但我还是从她上百则的笔记中发现,比起所读的对象,大多数笔记更有着阅读者的自由思考与独特感悟。其中,有对所读作辩证思考或拓展延伸,这种更饱满、更深入地与作者展开对话的巅峰体验,是阅读的更高境界,会给人更多启示,更具有学习借鉴的价值。例如:
(六)
哲学和诗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神话是永恒的化身,她死了,留下了一双儿女。直到今天,哲学一醒来就谈论死去的母亲,诗一睡着就梦见死去的母亲。
——周国平《人与永恒》
相当喜欢这个比喻。哲学是醒着思考,诗是梦着想象。清晰的、精确的、冷静的,是哲学的眼界;模糊的、游离的、热切的,是诗的心灵。哲学在认真剖析神话,以求把我们的世界向天堂靠近;诗只是不断呼唤着神话,梦里流着泪,企求着回到母亲身旁。
——白杏珏
(七)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史铁生
命运,是既定的角色与脚本。在人间的舞台上,许多人的台词都是被规定好了的。可那又何妨呢,这是个舞台,而不是个牢狱,如何表演,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白杏珏
(八)
石头是材料,神殿才是意义。
——圣埃克苏佩里
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以前看到的一个采访摄影师的报道,那个闻名世界的摄影师以其独特的画面构思出彩。记者问道,你觉得摄影最重要的是什么,光影或是景深?他答道,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想法。想法才是意义。神殿是形式,信仰是本质。
——白杏珏
周国平说神话孕育哲学与诗,只含蓄地点出其一醒一睡的状态;而白杏珏则将其状态更往内里本质去探寻,虽同样用了“向天堂靠近”和“回到母亲身旁”这样感性的句子,但其智性的思考与揭示,表明她确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与深入。史铁生指出命运指的是一个人在世上的角色“不可以随意调换”,语气多少带些无奈;而白杏珏却认为即使角色固定,表演仍可“取决于你自己”,其感悟则明显趋于积极乐观。“石头是材料,神殿才是意义”,圣埃克苏佩里的这句话已经说出精神高于物质的存在,但作为精神象征的神殿也仍然可以成为崇奉或迷信的形式外壳;那么,究竟什么是神殿的真正意义?白杏珏进一步道破:最具本质的,最能体现宗教意义的,乃是人的信仰,信仰才高于一切。就像前面评点史铁生的话那样,一旦与文字碰撞,她总是能很快扼住事物或问题的要害,迅即作出准确的反应,读来让人倍感犀利而醒豁。
无论是体验、体认还是体悟,笔记里所写下的与那些思想者的文字一旦对接,就有一种非常鲜明的现时感、在场感,常常让人分不清说话的谁是谁,是两人对话还是个人独白——读者与被读者之间已达至神交心契、声气相嘘的地步,这一种阅读的高级精神享受,是令人欣羡的。它因此也更使我们认识到,阅读既是一种“物我回响”,也是自我发现、自我觉解的过程。
倡导阅读笔记写作的最大理由与好处,正如余秋雨所说,“概括全书的神采和脉络,记述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种读书笔记,既在描述书,又在描述自己”。我们通常把读书仅仅简单理解为获取知识,看重的是“让我了解你”(“描述书”);而不知道也是在创造知识,更要看重是否“你也因此了解我”(“描述自己”),是否也把我心中的东西说了出来。白杏珏说得好:“从前也看书,却从来是看过了就忘,没有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什么叫做“自己的东西”,又怎样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她的笔记已经给了我们难能可贵的最佳答案。
于是我们可以说,“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仿佛那是在“写”我所要说的一段话;“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读”,仿佛是在“读”着我心中早已存着的一段文字。这和海德格尔所说的“讲本身就是听”“讲是对我们所讲的语言的听”正是同一个道理。而我所谓“以心契心”的物我交融、谐振共鸣的心灵遇合,在白杏珏的笔下也终于找到了知音。
现在不少教师指导作文,总是要求学生多多积累语言素材,牢牢记住人物事例,到时再想方设法往作文里套,而并不教会学生如何分析那些素材——因为一旦分析,你的主体就要“契入”;不能契入,就只能堆砌。从白杏珏的笔记里,几乎没有看到她单纯摘抄别人的“事例”,她更看重的是别人的“思想”。从阅读中积累作文素材,必须分为两种:一种是语言材料,类似好词好句之类;一种是思想质料,是语句所表达的思想观点,亦即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对高中生来说,尤其需要积累后者。只重“材”不重“质”,可能是当前作文教学在储材、用材方面的一大失误。白杏珏的笔记之所以能让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就因为她有自觉的对“质”的追求,她的阅读视界,比起同龄人,的确既高且宽。
我还主张阅读要达到能够“以言传言”的程度。白杏珏的“传言”是相当出彩的,但在这里我不想细加评说,只想指出一点:经常阅读那些富含思想养分的上乘的文章作品,日久还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在文风和语式上受其熏陶感染。因为真正深入的对话,似乎也需要在表达水平上尽可能接近与对等。在白杏珏的笔记中,洗练的文辞、晓畅的表述随处可见,与那些智者透彻的哲思、精警的格言,形成彼此呼应,自然对接。这是长期接受濡染的结果,并不是任何刻意求工所能达到的。
当然,阅读既然是对话,话不投机、言不搭界的情况容或有之。例如,梭罗在其名言“每一根枕木底下,都有一个爱尔兰人”的最后,有一句话特别发人警醒:“我保证,他们都是沉睡着的。”白杏珏读后怦然心动,但结语却归之“哭泣”,对“沉睡”二字似乎视而未见。又如,周国平说美是骚动不安和稍纵即逝的,笔记却认为周国平所说的乃是“跳脱的美”,理解大相径庭。更突出的例子是,第欧根尼认为“精神需求相对于物质需求所占比例越大,他就离神越近”,而白杏珏竞误读成“这确乎是一个评定人之好坏的标准”。当然,这只是其中极其个别的例子,我倒不想说什么瑕不掩瑜,而是将之视为阅读的常态和生态,与阅读者的水平未必有什么相关。我读我写,自说自话,全然是读给和写给自己的东西,只对自己负责,自然允许有偏离和错失,而作者与编者保留了这样带有微疵的文字,则是明智的。也正因为做到“有真意,去粉饰”(鲁迅),会让我们感觉更亲切随意,更自然本色。
我曾向编者建议在笔记中收录白杏珏的几篇精彩随笔。从采集点滴的感悟到放纵奔涌的思绪,由只言片语的记录到完整形制的抒写,我感觉白杏珏的笔记已形成很好的书写格局,只待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敷衍成文并不见有多么困难。这是否可以看成是“读”与“写”之间的一座无形的“桥梁”?语文教学提倡学生做读书笔记由来久矣,但做笔记好像也仅仅是为了养成阅读的好习惯。白杏珏的笔记,让我们看到,原来还有一个更宽阔的出口,可以通向自由写作,使得理解与表达形成有机的良性循环。是的,刚开始做读书笔记,会感觉吃力,会不耐烦,久之则会逐步觉得有了收获积累的满足感。如果能够坚持下去,积以时日,一旦形成习惯,非仅满足而已,还会顿然发现,自己恍若走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语文世界,犹如陶渊明所说的“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但关键是,是否已发现那“仿佛若有光”?今天,我从白杏珏的笔记中,分明看到了这一线希望之光,我因此相信,让我们的学生通过经典和精品的自主阅读,走向个性化的自由写作,完全存在现实的可能。同时我也相信,在我们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红杏珏”、“蓝杏珏”、“绿杏珏”……值得我们去发现、珍视、研究、总结。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读书笔记也有可能取代单一的命题作文,成为语文写作主修的日常课目,学生在课外都会自觉养成做读书笔记的习惯,从而享受一份自我书写的快乐。
最后,我还想引用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一段话,将我最初读到白杏珏笔记的第一印象做个补述。黑塞是这样说的——
真正的修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出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对于“教养”也即精神和心灵完善的追求,并非朝向某些狭隘目标的艰难跋涉,而是我们自我意识的增强和扩展,它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享受更多更大的幸福。……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是的,我没有在白杏珏的笔记中发现任何一点艰难跋涉的足迹,她只是那么幸福而自在地独自前行,这本身便有意义。她的自由快乐的行走姿态,既带给我阅读的愉悦,也将启引我继续谛视她的足迹而行行复行行,不管需要数十步、数百步还是更长,总希冀在探讨“读”与“写”之间微妙的“阡陌交通”中,对语文教学前景会有豁然开朗的新发现。
原标题:仿佛若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