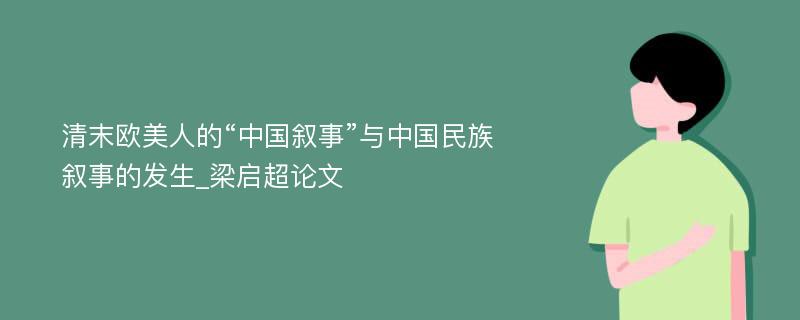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晚清论文,人士论文,民族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以来,出于观察中国、了解中国的用心,来华的欧日人士通过办报和著述,写下了大量讲述中国的文字。这些人既包括商人、传教士、官员,也包括学者、思想家和文人墨客,其笔触广涉中国的政事、商情、思想、民风以及学术文化,“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来说均远非同时期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①,形成规模宏大的“中国讲述”热潮,亦促成西方和日本向来之“中国学”的转变。影响所及,不仅触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根基,也提供了关于中国文学的新的“想象”源泉。从文学影响的层面来看,这些中国讲述所展开的中国图景,尤其是它们对中国国民性“杂树生花”般的描写,其学理的“实”和想象的“虚”相胶合,都给中国作家在文学意识、想象方法和对象审视方面以新鲜的刺激。受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所塑造的中国国民性启发,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文学民族叙事的发生。目前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一般的还只是侧重于对二者在思想联系方面的抽象观察,对“史实”的描述和细节勾连尚留有不少空间,对于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也还未来得及进行郑重申明。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欧日人士中国讲述的实际情形,指出受其影响,在中国形成了以国民性为中心的写作意识,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又存在着一般文士和思想型作家的区别。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
一、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热潮
1815年4月17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带领中国雕刻印刷工人从广州抵达马六甲,筹建英华书院及其印刷所,同年8月创办了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为中国近代报刊的肇始。1827年,来华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在广州创办《广州纪事报》,随后《中国信使报》、《广州周报》、《广州杂文报》、《中国丛报》、《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国教会新报》(后更名为《万国公报》)、《申报》等报刊杂志相继出版发行,它们立足于“西方立场”的中国讲述,虽然明显地带有“贬抑中国”的色彩,但对中国社会的形象化描写和学术性研究,作为一面镜子,无疑会促使先觉的中国人揽镜自鉴。据历史学者吴义雄考察,上述报刊所载文章,已涉及对中国“民族性格”的研究。这些研究指出,由于满足于天朝帝国的乌托邦信念而与世界历史相隔绝,导致了中国文明和历史演进的停滞,从而得出了中国仍属于“半文明民族”和“民风迷信”、“民性恶劣”的结论②。对民族性格的描述催生了近代意义的“国民”概念,例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出现了“国民”一词,其“并非单纯外国人的贡献,往往是来华外国人为了翻译上的用途,而和他们身后的中国助手一起逐渐发明出来”③,已可见出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表达,最初并非由日本传入,而实是中国人主动参与同西方人对话的结果。1889年复刊的中文周刊《万国公报》发表了主编林乐知的《治安新策》,就针对“民族群体形象”,指出中国国民性格“骄傲、愚蠢、恇怯、欺骗、暴虐、贪私、因循、游惰”八大积习,以其38,000余份的发行量和立足于影响中国普通士人的办刊立场,对在中国“养成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气氛”④,影响力之大是显而易见的。谭嗣同即认为,“西方所谓中国人不虚心,不自反,不知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至目为不痛不痒、顽钝无耻之国,……令人愧怍,无地自容”⑤,从而进一步发出了“奈何读书明理之人,曾不知变计一雪此谤耶”⑥的追问。这种追问表明,由西方人所办报刊提供的中国讲述平台,在中西文化风云际会之时,逐渐刺激了中国人的“对话”欲望,使中国人产生了用近代理念进行“认识自我”、“改造自我”的冲动。
在报章杂志的短篇报道之外,来华西方人关于中国的长篇著述更为生动地描写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其中尤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的《开放的中国》、英国汉学家德庇时(1795-1890)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45-1932)的《中国人的素质》(又译《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特性》)等最有代表性。它们的作者长期居留中国,对中国的社会民风有切身的感受和了解,其发言的姿态,就不是致力于“异国情调”的搜神猎奇,而是刻意发掘中国的具体国情与民性。1831年,郭士立来到中国,除1833年8月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外,还出版了《中国简史》,成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在其名著《开放的中国》上卷部分,郭士立通过对中国文化风俗的观感,用力于中国民族性的研究,总结出中国人存在着迷信、守旧、贿赂、谎言、在精神上受到奴役、对女性进行野蛮压制等等恶习,锋芒所指,就是中国种族的劣根性。1816年,德庇时以“汉文正使”的身份随英国外交使团来华,1844-1848年间升任英国驻华公使、商务正监督,同时兼任香港总督及总司令,总揽英国在华事务大权。他曾著有《中国诗歌论》、《中国见闻录》、《中国杂录》等书,对中国的文事人情和政经风习多有著录,特别是《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一书,涉及中国国民性较多,虽然仍不能免于西方的优越感,但由于“对中国政治、文化、民族性采取了理性评论的立场”,所以持论比较客观。对其他西方人描写的中国人愚昧、残忍等恶习,德庇时很不以为然,认为“其程度和数量被多数作者夸大了”⑦。这种中立的姿态,与其他西方人“讲述中国”的立场大异其趣,纠偏矫正的用意,昭然若揭,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自省,也在“反方”的观照之外,提供了“正方”的视野。
然而观察最细、用力最深的无疑是明恩溥描写中国国民性的专书《中国人的素质》。由于它系统性地“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而被称引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⑧。明恩溥1872年受公理会差遣来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山东农村庞家庄传教,由于与乡土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使他对中国国民性的讲述更加显得“持之有故”,“立言有本”。明恩溥认为,通过描画乡土社会来认识中国的国民性,是在“对小说、民谣、戏曲的研究”之外更有效的一种渠道,因为“外国人如果想详细了解中国国民的生活内容,住在城市十年也比不上住在农村一年”,假若作者能够集合个人与他人的经验,并把“村落当作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进行描写,就能准确传达出中国人的特性。该书分26个专题,就中国人的“面子”、“节俭”、“勤奋”、“装糊涂”、“拐弯抹角”、“神经麻痹”、“保守”、“缺乏真诚”、“猜疑”等问题进行了亦褒亦贬的描写,其力图穷形尽相的文笔,颇能传达出中国国民性的众生相,且由于作者既非政治也非纯粹基督教的发言立场,也使这部著述更带有一种文化人类学的特征。这些专题文章最初是明恩溥受上海《字林西报》的约请而写的,由于“有些话题令人激动并且感兴趣”,结果不胫而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⑨。为了满足读者的兴趣,明恩溥把文章编纂成书,于1890年以《中国人的素质》为名在上海出版,此书传至日本,马上以《支那人气质》为名翻译成日文出版,引起在日华人,特别是留日学生的争相传阅,对后来中国文学国民性主题的形成,影响巨大。
从1862年开始,由于观察中国的目的已经转变为“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⑩和中日两国之间在近代历史环境下存在的竞争关系,来华的日本人不再抱有“学生取经”的态度,其讲述中国的视角,也就有了不少俯瞰的批评。他们来华的方式多是游历,但由于深具“汉学”的知识背景,其走马观花的发言议论,并不影响他们对中国作出认真的国民性观察。据1997年日本学者小岛晋治《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期的统计显示,见闻录的数量已达16种之多(11)。考虑到这只是初次统计,未被收录的应该还有很多。这些见闻录包括: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草稿、日比野辉宽《赘疣录》、曾根虎雄《清国漫游记》和《北中国纪行》、尾崎行雄《游清记》、高桥谦《中国时事》、中村作次郎《中国漫游谈》、内藤湖南《中国漫游·燕山楚水》、村木正宪《清韩纪行》、木村粂市《北清见闻录》、小林爱野《中国印象记》、山川早水《巴蜀》、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米山庸夫《四川云南踏查记》以及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编写的《满韩修学旅行纪念录》。它们“多在现地作成”,广涉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土、风俗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12),不乏田野调查的生动与切实,对中国国民性的描写也不吝笔墨。比如内藤湖南即指称中国人“无法无序”,并用日本人的“勇于进,拙于守”反照中国人的“勇于守,拙于进”和“惯于久安”的保守性。宇野哲人在他的《中国文明记》中更是特立了《论中国国民性》专章,论说中国国民性的民主性、家族主义、利己性、迷信、夸张性、附和雷同、社交性、同化作用、保守性、服从性、和平性、社会性、从容不迫之性格(13),些微赞词之外,尤多讽刺性的蔑视判断。这些言论还与日本境内汉学家的中国研究构成呼应之势,如福泽谕吉即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是贫乏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丰富复杂的人,迷信就易消除”(14)。此褒彼贬,一扬一抑的态度十分明显。考虑到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宇野哲人、内藤湖南也是日本名重一时的教授、记者,其大家出场,讲述中国国民性的林林总总,自然会产生掀动时潮的效果。虽然其中存在着种族优越感和对中国的歧视偏见,但对于催生在日华人的民族意识,唤醒他们对国民性进行反思,无疑起到了引导舆论、提供材料和呈现视角的作用。
二、“中国讲述”提供的文学新变契机
来华欧日人士关于中国的讲述,并非始于19世纪,也非终于19世纪。前此来华的日本僧人空海、园仁所著《文镜秘府编》、《入唐求法巡礼行纪》,意大利马可·波罗所著《马可·波罗行纪》以及后此来华的大哲学家罗素所著《中国问题》,由于它们所表露的对中国的“好感”和正面评价,均未能在中国造成巨大的舆论影响,同晚清中国讲述得以在中国引起舆论的方向性转换和文学氛围的整体性突变相比,它们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其“文化利用”的价值也未能得到明显的伸张。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晚清的中国讲述会在中国知识界造成“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成为引领时代的风向,并连带造成中国文学主题的新变以及变革文学的冲动?究其原因,不外如下:
——在文学主题形成方面,晚清中国讲述强化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由于切合中国人的“民族焦虑”而突出了时代的“问题意识”。它使中国人从文化利用角度,引发“重塑自我”的内在要求。在这种主体诉求之下,中国人对这些讲述进行了一种有选择性的阅读,即在“问题意识”的导引下形成统一的方向感,把复杂的观感引向一个中心意识——国民性思考和民族性批判,从而使“国民”、“民族”成为流行一时的“关键词”,亦促成讨论“国民性”、“民族性”的时尚。面对《中国人的素质》,李景汉即认为在“民族受到严酷自然淘汰的今日,我们实在有急于认清我们自身的需要”,其方法除在“自己研究自己之外”,“对于外人论断我们的话,尤其是依据精密观察的结果,我们不但不应当忽视,尤当加以重视,引以为鉴才是”(15)。其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即是深究“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而通过连篇累牍地发布《新民说》,鼓吹对国民进行“德育”和“智育”的培植,“先维新吾民”,然后“维新吾国”(16)。在《新民丛报》的理论著述之外,梁启超接着创办了《新小说》,利用“说部”便于传播、易于感人的力量,“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时旷达人士,翼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17)。对此,梁启超非常自信:“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则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18)风流自赏,却是由来有自,颇能传达当时文学思想的一个转变痕迹。对中国国民性的反复申说,梁启超采取说理文字与形象传达双翼齐飞的方式,以他在舆论界引领风骚的地位,其致力于发布“新民说”和实践“新小说”的举措,对于思想风习的“定篇”和文学主题的“定调”以及推进以国民性为想象中心的民族叙事的展开,作用自然不容忽视。
——从启蒙意识的培育来看,晚清中国讲述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晚清中国讲述产生于19世纪近代西学普世化和现代民族国家纷纷创建的历史进程中,其强势话语虽然带有种种霸权意识,但它启迪民智的述说立场却能满足先觉中国人的期待视野,符合他们振奋自强的民族心理。由西方传教士所设“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孩提报》、《训蒙画报》、《女铎报》、《成童画报》、《大同报》等报刊,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大众传媒,通过揭露中国民性拥堵的时弊,传递有利于维新的启蒙观念,并因此“成为刺激近代知识分子维新思想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19)。这种欲使中国“绝地逢生”的用心显然影响到明恩溥讲述中国的立场,通过与中国社会的广泛接触,明恩溥认识到中国人能“十分坦率地承认民族性格的弱点”,因而主张改良中国不靠其他,只需改良国民素质,推进人格重建的启蒙行动即可(20)。虽然受限于宗教视野,明恩溥有意贬低文艺启蒙的效果,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人利用文学作为启蒙工具的联想和冲动。沈惟贤即认为:“养蒙正俗,兴起感其心,通达其智力者,莫捷于小说。”(21)梁启超则从总体论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气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22)。梁启超明确提出用文学美术锻造国民独具之气质,以培育独立之国民精神,并把它作为收揽民心、构建崭新民族国家的名山事业,对激活中国作家采取启蒙立场,无疑影响巨大。
——从文学自身的角度看,晚清中国讲述传递了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虽然文学不是中国讲述的重心,但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表征符号,文学并没有离开讲述的现场。不过与此前“东方学”、“汉学”对中国文学大加褒赏的情况不一样,它们对中国文学从观感到功能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德庇时认为中国文学作品不过是“文学名义下的垃圾”(23)。从文学是否“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和自由的发展”的角度,裨治文批评中国人“读史不足以明世,做诗不足以砺德”,对中国的“诗文策论”殊无好感(24)。宇野哲人则把中国文学与国民性讨论联系起来,认为中国人性格中的“夸张性”使文学流于幻觉而背离现实:“读中国人之文章,让人错觉世上真有如此之仙境,而往而观之,只不过是鄙俗俚境。……吾人读中国人之文章时,必须大打折扣。”(25)面对中国文学的不足,他们有意识地希图施加影响,以为改进。如广学会曾拟定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准备出版包括“文学史”在内的《世界历史》,用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2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10-11月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与中国留学生杨度之间有一场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往复讨论,嘉纳治五郎明确提出,如要改造中国人的“恶根性”以鼓舞民族意识,在开办报纸、教会、设立图书馆和翻译图书之外,尤需创作推进新思想的小说,以使中国文学与世界近代文学有相当之价值:“其中小说效用最为迅速,诸国与日本兴学,盖始于此,皆因其教人浸心入深之故。”当时鲁迅正在弘文学院学习,又与杨度曾有过从,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应不难猜测。更有意味的是,在这次讨论中,嘉纳治五郎在谈到中国于“百亡之中而求一存”时提出了“烧毁旧屋”的意象:“在烧毁旧屋、建造新屋的过程中,不一举烧毁是没有效果的,烧掉一半,留下一半是不行的。”(27)联想到鲁迅《呐喊·自叙》中著名的“铁屋子”意象,其思想启迪和意象传递有明显的痕迹;再联系到鲁迅始终坚持文学革命,其推倒重来、不留余地的信念,应与此有莫大的关系。从这个经典个案可以看出,晚清中国讲述实为中国文学变革不可或缺的外缘助力,对于推动中国文学告别古典,实现观念、性质、功能方面的突破,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以国民性为中心的民族叙事的展开
对晚清叙事作品的形态变化,文学史家多有论及。但由于目的不同或视野所限,他们的论述都有特定的个人指向,或不免于时代意识的左右。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特别注意对晚清小说的类型归纳,但其中“公案”、“狭邪”、“人情”、“讽刺”、“谴责”的分类,重点是在题材与风格的疏理,对晚清小说的修辞和趣味则多有懑意。其实鲁迅也注意到这些小说涉及了“风俗”的描写(28),却是点到为止,未及提升而一笔带过。后来胡适著《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虽然对晚清小说不吝赞词,但其论述中心显然是针对这些小说的“白话”形式,认为“这一段小说发达史,乃是中国‘活的文学’的一个自然趋势”(29),对其中的内容新质则未作重点申说。事实上,鲁迅和胡适都是站在新文学史家的立场进行历史叙述的,这种立场不免使他们的发言于深刻处含有偏颇,特别是胡适还要表彰他所提出的白话文学史观,一叶障目,尤使其中的一部分价值不得彰显。抗战期间(1941年)阿英编写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已经注意到了晚清文学丰富的民族意识,但其致力于收罗“民族主义之伟著”的目的,却是树立“政治剧曲之丰碑”,以“有助于今日方兴未艾之民族意识”(30)。这种联系时事、“以古鉴今”的著录心态,在爱国主义的宜教之际,不免会“窄化”文学史家的历史视野,使对晚清文学以国民性为中心的民族叙事形态及其实质的观察,仍不能得到一种恰当的方式;对于中国文学从“世情叙事”转向“民族叙事”的关节,或有史料的存放,殊无激活与展开,对二者间的嬗变轨迹,仍未能作出应有的文学史描述。
宋明以来,以描写世态人情为内容、以劝善惩恶为主旨的世情小说非常发达。它专力于道学心肠的发掘,而独无意于民族意识的传达,直到晚清初期仍居于中国文学的主流。1848年邗上蒙人撰《风月梦》,即意在“警愚醒世,以意稍赎前衍,并留戒余,后人勿蹈覆辙”;1849年珠湖渔隐序《云中雁三闹太平庄》亦云:“古人著书以相劝戒,正言之而不能行,则微言之;微言之而不能行者,则创为传奇小说以告诫于世。……庶己广为传观,且可见福善祸淫之理,尚扶冀于宇宙间也。”诚如《红楼梦影》序所言,“善善恶恶,教忠作孝,不失为诗人温柔敦厚本旨,洵有味乎言之”仍然是此类小说的旨趣所在。但是到了光绪年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国民性为描写中心的民族叙事已初具规模,其与晚清中国讲述的映射关系也痕迹明显。如公开宣讲“革命何尝不是堂堂正正的旗,但民智不开,民力不足,民德不修,这三样没有,决不能革命”(31)的小说《轰天雷》,作者明明是中国人孙景贤,却署名“藤谷古香”,托为日文小说译出。这种不考虑版权意识、一心追求宣传效果的“另类”做法,显然是为了借重日本人中国讲述的“权威性”。由此也可看出,晚清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之间的“互文”关系,并非出于偶然和臆测,而实是有现实的关联。
其时一般文士已注意到办刊撰述之于民族意识传达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他们与广学会所办报刊及其中国讲述的对话意识甚为明显。1903年李伯元创办《绣像小说》,取法“欧美化民,多由小说”,开宗明义即是:“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益民。”(32)1904年中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也“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其惟一之目的”(33)。1907年在香港创刊的《新小说丛》,其编撰意识已注意到文体变化与新兴主题的关系:“小说之作,体兼雅俗,义统正变,意存规诫,笔有褒贬,所以变民俗,开民智,莫善于此。”(34)与之相随,竞言民性、表达民族忧患意识的作品在竞相刊发。如陆士谔的《新孽海花》,即因其塑造人物“人格之高”,“读之令人精神勃发”,而被李友琴序称为可以“鼓舞国民”(35)。吴趼人所著《痛史》、《情变》等,也被称为“无论章回杂记,皆能摩绘社会之状态,针砭国民之性质,积理既富,而笔之恢奇雄肆,又足以达之,……一纸风行,啧啧于众人之口,洵可有目共赏,非可幸而致也”(36)。足见影响之大。程佑甫所著《天足引》,事缘“普劝中国女人脱缠足之苦,享天足之乐”,其立意却重在“敦孝友,贱势利,贵自立,革旧俗,启新机”的国民性启蒙(37)。由此可见,此类小说虽仍以演义世情为表相,然而它们“藉思开化于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的用意,自然可使“爱国君子”,“畅此宗风”,以“引为同调”(38)。启蒙之心昭然若揭,文学形态的变化亦内蕴其中。
与一般文士的撰述相比,梁启超虽然也通过国民性描写传递“新民”的信息,但其形式已完全脱去演义世情的外衣而呈现欧化的痕迹。梁启超立足于“政治”变革立场,尤其重视西式“政治小说”革新国民性的力量,在《译印政治小说叙》中,他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以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学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各国政治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某名士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39)不过梁氏所针对的对象虽然犹在“民间”,但由于他“自上而下”的维新策略,其民族叙事实际上已向精英阶层的国民性描写靠拢。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梁启超有意构造中西比照的视野,其《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所述意大利建国民族英雄故事,就是要利用英雄传奇,“借为箴膏肓,起废疾”,达到启蒙民性、鼓励志士、重铸国魂的目的。取“他山之石”的用意相当明显。在这种中西比照的用意之下,其《李鸿章传》所述传主行事,“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而惟弥缝,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要挟小智小术”(40),与西方俾斯麦、伊藤博文等政治家相比,则明显遭到贬斥。在传记结束部分,梁启超大段引用日本报人德富苏峰对李鸿章的评述: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脸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烩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41)
作者借此传达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度批判,尤其是这种批判以能左右中国政局国事的潮流人物为对象,就更能见出批判的力度。在这里,梁启超立足于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发布民族忧思的情怀,借重于日本人中国讲述的痕迹也至为明显。
在民族叙事渐次上扬之际,作为后起之秀的鲁迅也置身其中。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除受前述明恩溥、嘉纳治五郎的中国讲述启发外,还得助于当时活跃于日本的梁启超、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如鲁迅在1902年12月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即告之已购得《新小说》杂志,可见他与梁启超的精神联系。到日本的第2个月,鲁迅就积极参加章太炎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活动。此事虽然未果,但无疑收到了增进亡国记忆,促发民族反思的效果。据许寿裳回忆,此时鲁迅已形成了如下三个问题意识:(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42)其时鲁迅的思想活动虽然还未以具体的文学创作为主,但就他当时的文学思考来看,显然是以国民性为中心的,其论述也是围绕着“民性之力”之于“文学之力”两者双向互动的链条展开:“降及种人失力,而文事亦共零夷,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民之灵府,流转异域,如亡人也。”(43)而要革除国人“安弱守雌,笃于旧习”的劣根性,必须有精神界之战士出现,作真诚忏悔之书:“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洵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众皆曰维新,此即自白其历来罪恶之声也,尤云改悔焉尔。”(44)由此出发,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列举欧洲浪漫主义诸诗人,就无不在意于这些诗人通过“美化育人”的创作,在唤醒国民、建构民族国家方面起到的巨大作用。鲁迅既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又格外推崇文学的审美品质,与前述作家相比,在文学认识上显然更为本色和深入,也更具现代性,对推动中国民族叙事由近代向现代转型,其作用不容忽视。
四、民族叙事的两条进路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为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但作为民族叙事的源头,它又隐伏着不同的历史走向。学界讨论晚清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不外乎“断裂”与“接续”两种。前一种认为五四超越晚清,是为旧说;后一种认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论断二者关系多有钩沉索隐、启潜发微之功。如果我们把民族叙事当作近现代文学的一个潮流,则其发展并非简单递进,其流向也非铁板一块。个中关节值得讨论。
就民族叙事发展来看,它发生于同一源头,却呈双水并流的走向。其一流入通俗小说,另一个则通往精英叙事。其原因在于作为一般文士如黄摩西、东海觉我等人与作为思想型作家如梁启超、鲁迅在文学观念上的分野。一般文士似乎更看重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故倾向于考虑作品的实际接受程度,对传统小说表现出相当的好感;思想型作家则更看重所传递思想之价值,且多彰显个性,故而虽力图张扬文学启蒙的功能,但在形式上却不予读者以过多的考虑,反而专力于文学的“西化”和“现代”。不过二者虽分道而行,却又能相互对话,从而使现代民族叙事呈现出丰富的发展形态。
对民族叙事发展的思考,一般文士同思想型作家的对话欲望非常明显。1907年《小说林》创刊,黄摩西所作《发刊词》即言“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也太重”,直接把梁启超所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摆上了对话平台:
昔之视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是鸩毒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今之反是也,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虽稗贩短章,苇茆恶扎,靡不上之佳谥,弁以美词。一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课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无一不赐于小说者。其然,岂其然乎?(45)
不过从《小说林》刊发文章不乏民族叙事的情况来看,黄摩西所言并非否定小说的“国民进化之功”,而是认为文学如无“高格可循”,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46)。这种倾向还由东海觉我在《小说林·缘起》中指出:“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最上乘者。”(47)两人的论述虽然同时援引了黑格尔的美学观念,却决不可视为呈义高明,亦不可妄作“现代”之联想。因为它不过是论者抵抗“西化”,以“偷梁换柱”的包装重振传统小说的借词:
西国小说,多述一人一事;中国小说,多述数人数事,论者谓为文野之别。余独谓不然。事迹繁,格局变,人物则忠奸贤愚并列,事迹则巧绌奇正杂呈。其首尾联络,映带起伏,非有大手笔、大结构、雄于文者不能为此。盖深明乎具象理想之道,能使人一读再读即十读百读亦不厌也。(48)
由此可见,对于民族叙事的走向,黄、东二氏一是反对“惟主题”的论调,一是主张复归传统形式。这种姿态既反映了他们的文学意识,也与他们卖文为生的生计考虑相关,所以不得不顾及发行量,以通俗而传统的文体形式追求“能使人一读再读即十读百读亦不厌”的效果。但对于梁启超而言,文学专为发布思想而存在,于其身家行世则并无多大关系,所以他的作品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虽被称为“才笔纵横,感人尤切。欲教少年子弟以为文学者,最宜以此等书为读本,甚于寻常教科书万万”(49),不过是广告词而已,也只能引起中上层知识精英的追捧欣赏,于普通民众应殊少感觉。即使梁启超也说他“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50),不过从他所赋予文学的历史使命及自身的创作实践来看,并非如此。从他“诗界革命”的目的乃是呼唤中国的“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51),即可看出梁启超借助文学之力,所欲辐射的领域不在普遍的“民间”,而在特指的“上层”,其民族叙事的精英意识不难辨析。
从梁启超到鲁迅,二者民族叙事借重西方文学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从鲁迅《摩罗诗力说》极力伸张近代欧洲诗人的创作看,二者通过文学输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以唤起国内民族意识的用心有内在的一致性。不过鲁迅虽然追随梁启超的精英叙事和欧化作风,但对梁启超专务于上层民族精英的描写显然不以为然,对这种“崇强国”的偏执习气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和冷静。所以鲁迅转而推崇“平民文学”,其民族叙事虽不免于“自上而下”的俯瞰式眼光,但他通过普遍之“立人”,达到最后之“立国”的意图相当明显。他的译著多选择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品,此后他的小说创作多以普通民众与下层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为对象,都反映了中国民族叙事局面的打开和成长。
晚清民族叙事通俗写作和精英写作的并存,对开启现代民族叙事的作用非常巨大。李涵秋、包天笑、平江不肖生、张恨水等人的现代社会言情小说,借世运人情的变化,演义国事的发展,不乏对国民性的批判暴露,显然是继承了晚清通俗民族叙事的风格;通过五四文学革命崛起的乡土派等新文学作家,其民族叙事则显然是受到了鲁迅的直接启发。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老舍、沈从文的出现,他们描写“老中国儿女”、重铸“民族道德”的写作姿态,又使民族叙事出现雅俗合流的倾向。这种情况表明,从晚清到现代,中国民族叙事在深化重构民族意识的过程中,已经体悟到刻意经营叙事文体的重要性。个中关节如何,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讨论。
注释:
①见黄兴涛、杨念群为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所作的“主编前言”,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6页。
②吴义雄:《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③桑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解说》,见赵立彬:《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4页。
④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26页。
⑤谭嗣同:《报贝元征》,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5页。
⑥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65页。
⑦吴义雄:《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⑧见为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所作的“出版前言”,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⑨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引言”,第3-5页。
⑩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96页。
(11)张学锋:《幕末明治时期的中国见闻录及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见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12)张学锋:《幕末明治时期的中国见闻录及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见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第207页。
(13)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95-209页。
(14)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页。
(15)引文出自李景汉1930年代为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所作之“序”,回忆他25年前阅读日文本《中国人的素质》时的观感想。参见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300页。
(16)梁启超:《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17)梁启超:《三十自述》,李兴华、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8页。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7页。
(19)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9页。
(20)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第283页.
(21)引自沈惟贤为《万国演义》(上海:作新社,1903年)所作“序”,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22)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丛报》1905年第1期。
(23)吴义雄:《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4)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50-252页。
(25)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26)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92页。
(27)嘉纳治五郎与杨度的谈话后被杨度以《之那教育问题》写出。参见杨度:《旷代逸才》,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45、151页。
(2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第329页。
(29)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30)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叙记》,《阿英全集》第6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31)以上文献转引自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第7、16-17、114页。
(32)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第1期,1903年。
(33)转引自《阿英全集》第6卷,第248页。
(34)转引自《阿英全集》第6卷,第262页。
(35)李友琴为《新孽海花》所作之“序”,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第252页。
(36)此为1910年9月《舆论时事报》编者为吴趼人未完遗稿《情变》所作按语。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第269页。
(37)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第173页。
(38)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第1期,1903年。
(39)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叙》,《清议报》第1册,1898年。
(40)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7-28页。
(41)梁启超:《李鸿章传》,第183页。
(42)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19页。
(4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44)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100页。
(45)黄摩西:《发刊词》,《小说林》第1期,1907年。
(46)黄摩西:《发刊词》,《小说林》第1期,1907年。
(47)东海觉我:《缘起》,《小说林》第1期,1907年。
(48)东海觉我:《缘起》,《小说林》第1期,1907年。
(49)广智书局:《出版书目介绍》,《新民丛报》第25期,1903年。
(50)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李兴华、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171页。
(51)梁启超:《汗漫录》,《清议报》第36册,1900年。
标签:梁启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晚清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中国人的素质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鲁迅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万国公报论文; 新小说论文; 明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