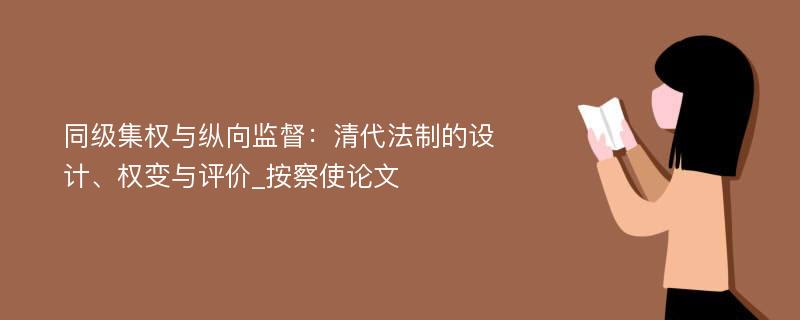
同级集权与纵向监督:清代法制体系的设计、权变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纵向论文,清代论文,法制论文,体系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15)01-067-10 以往对于清代法制体系的研究,往往以现代法学理论为研究工具,以现代法学价值观为评价标准,以自下而上的“诉讼”或自上而下的“审判”等具体制度为入手点,①且多将地方与中央两部进行分割研究。②本文拟抛开以现代法学理论和价值观研究中国传统问题的窠臼,使用政治史、法制史、行政史相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寓政治思想于制度设计之中,寓制度设计于行政运作之中。另外,拟将清代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制体系作为一个上下贯通的整体,侧重探究清代统治者和政策执行者对王朝法制体系的设计理念及权变应对,并对该体制的执行效果与历史意义提出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在方法论层面,全世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现代法学的体系为标准,套在中国传统的法律和法律制度上,衡量中国的传统社会到底有法还是无法、制度成熟还是不成熟。在这个阶段,学者们的立足点是西方的,中国只是作为一个比较对象出现。第二阶段,研究者承认了中国传统法律与法律制度相对于西方的特殊性,且意识到不能因为其与西方不同,就认为其是不文明、不发达的。因此,有必要运用中国的史料,对中国本身的问题其进行单独的、系统的研究。但在这个阶段,研究者思考模式、切入点,仍然是现代法学的。在这两个阶段的基础之上,我们应该把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层次,即: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传统中国的问题,不单要使用中国的史料,还要将一条条孤立的史料置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当中,用中国传统的制度框架和解释体系构建研究的基础。中国传统的观念制度,与现代的、西方的观念制度,可以并谈却不能混谈。研究的视野可以是开放的,但史实必须是清楚的,立足点必须是明确的,解释体系必须是专一的。以上,也是本文所要追求的目标。 一、减少冤案抑或节约成本:直省地方法制体系的设计与调整 清代的政府行政,以钱粮、刑名两项为至重,贯穿于从州县到中央之间的所有环节。前者让国家从民众手里获得运作政治的资源,后者维护政权的存在与社会秩序。二者构成王朝赖以存在的基础,也与一般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前者的数目大小,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同时受到国家税收制度与执行力的直接影响。而后者依赖于前者成行,其运作方式、规模、能力则受到前者的高度限制。有清二百多年,财赋主要仰赖于小农经济的状况未发生根本改变,然而人口急速增长,实际控制地区大范围扩张,社会流动加大、人与资源的矛盾日趋尖锐,社会治安压力空前。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代刑名体制的设计,要尽量找到两个原则之间的平衡点,即:慎重人命、维持社会秩序稳定。与尽量加强刑名案件办理效率、减少运行成本之间的平衡。 基于此,清王朝为广大汉族地区设计了一个自认为齐整而高效的理想型的刑名体系,即:对于户婚田土方面的小事,主要通过乡党宗族调解解决,即便一定要诉诸官府,也由州县官员依照情理调和劝谕了结,不要占用过多的行政资源;至于徒流以上特别是危害到社会治安、名教伦常,甚至国家统治的命盗重案,则从县到府再到按察司,由各级正印官依次审转驳查,但其均无定谳权,最终经督抚达部上奏,定谳处决。此外,死刑案由刑部主稿后定谳后需经三法司会议上奏,经皇帝本人亲自批准。总而言之,清代法律体系的最大特点是集权,这里不仅仅是指通常所说的中央集权,而且在每个行政层级上都进行集权。对于每一个审理层级的监督,主要采取上级监督下级,中央监督地方,皇帝监督刑部并全面协调中央与地方衙门关系的方式。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使整个系统权责分明,以上级制衡下级而避免同级内多部门扯皮。制度以“慎刑”为最高追求,在防弊与追求效率、节约成本之间不断权变,寻找平衡。 清王朝疆域广大,统治民族众多。清王朝各地方的刑名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地域是在郡县统制下直省地区,对象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第二类是实行军府统治的边疆地区,如新疆各城、蒙古各旗盟等,对象是生活在当地的各族人民;第三类是驻防在各地的八旗官兵及其家属。本文研究中涉及的是清代地方刑名体制中最基本、最复杂、涉及的刑案数量最大的直省地区。 在清代,一件起于州县的重案,最基本的审转程序是这样的:如果是一般徒罪案件,经知县或知州初审后,将人犯解往所在府或直隶州(厅),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覆审,详按察司,详督抚(有抚省分详抚,无抚省分详总督),督抚二十日内批结。结案后按季汇齐,咨报刑部备查。涉及人命的徒罪案件与军、流、遣案件,由州县初审后,人犯解往府或直隶州(厅),知府等覆审后,再行解往按察司,按察司详报督抚,专案咨部核覆,年终汇题。至于斩绞重案及由斩绞减等的军流遣案,则人犯需由按察司审转后再经督抚亲审具题,同时揭报三法司。乾隆以后又有依案情轻重,将凌迟、斩枭、斩决之案专折具奏之例。[1] 在这样一套审转制度中,最严重的斩绞大案在未经驳审的情况下,州县人犯要经过至少四次审讯。而对于直隶州(厅)本州(厅)的百姓来说,因为初审是在直隶州知州,所以,死刑的审转路径只有三级,比其他州县少了一级,冤假错案被驳正的机会就少了一次。[2]如果是徒刑,唯一的一次覆审就要直接解往省城,两造证人的负担又比只需解往本府、直隶州(厅)其他州县的百姓更重。[3]因此,在雍正末年,朝廷经督抚奏准,将直隶州(厅)本州(厅)初审的徒罪以上案件分两种情况办理,大部分直隶州(厅)的案件在送按察司之前,先由本管分巡道覆审一次,但如果该州(厅)离巡道驻地过远,而离省城较近,则遵照旧制。仍送按察司审转。[4]到乾隆中期,各地直隶州(厅)案件的审转归属已基本得以明确。 清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迅速膨胀,各地治安压力越来越大,地方非常有限的公费存留银两愈发不足以支付高昂的审转成本。为节约开支,督抚们开始在维持足够的覆审次数以慎重刑狱与尽量减少审转次数、拉近审转路途之间大搞权变与平衡。因此,刑案审转由“道”还是由“司”以距离远近论这样的想法,从嘉道年间起,开始突破直隶州(厅)的范畴,用于传统的第二审级“府”。如江苏省位于江北的淮安、徐州二府地瘠民穷、骠悍好讼,因为距离省城苏州一千里以上,且有黄河、淮河、长江相隔,犯人在苏州臬司衙门审转,多有拖累。道光三年在江苏巡抚韩文绮、按察使林则徐的建议下,凡军流遣罪人犯及涉及人命的徒罪人犯,徐州府及淮安府的阜宁、安东二县归淮海道审勘,淮安府山阳、盐城、桃源、清河四县归淮扬道审勘。此外,直隶州海州原属解司之州,亦归淮海道审勘。审后仍将审转情由送按察司备案,并详巡抚咨部。[5]除江苏外,如江西之南赣,广东之雷潮、安徽之凤阳、颖州、泗州三府也如此办理。[6] 地方审刑案的转层级问题是法制史研究中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专门探讨,分别有三级、四级、五级之说。三级说认为,案件由州县到府到省,一个行政等级,即为一级。四级说是目前的主流观点,如郑秦、寺田浩明等都持此种观点。他们将按察司与督抚分开来算,认为清代存在散州与县、直隶州(厅)两条审转线,各分四级审转。五级说出自那思陆的《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他并没有把一般州县和直隶州(厅)的情况进行区分,而是将州县、府、道、司、督抚统算为五级。[7]三个结论中,三级说和五级说问题都比较明显,相对而言,四级说更贴近清代文献对于地方审级的概括性描述,但与实际的运作情况还有一些差距。 首先,三种说法总结的都是刑案中的最极端情况,即斩绞死罪的审转,而不计军流遣徒等罪;其次,都忽略了清廷在确定各地审级时较为灵活权变的态度,尤其平衡审转次数和解送成本关系的考量;第三,过分追求对“道”是否作为一级行政单位的看法。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强调一下“审”的概念。在清代的语境中,只有面对面问讯犯证的情况才被称为“审”。如果只是根据文书定拟罪名,提出本级的“判”的建议,则称为“核”。事实上,清代地方刑案需要审转的是三种情况:其中无关人命的徒罪不管是散州和县,还是直隶州(厅)所审,都只有一次审转,经过两级衙门,再向上呈报只用详文,不用递解人犯。军、流、遣罪和涉及人命的徒罪。由散州和县初审的。大多经州县、府与直隶州(厅)、按察司三级审转。嘉道以后离省会较远的则经州县、府与直隶州(厅)、邻近巡道三级审转。而有直隶州(厅)初审的,则操作较为复杂,一类是经直隶州(厅)、巡道、按察司三级;一类是因为本州离省城较近,在雍、乾时期奏定的,经直隶州(厅)、按察司两级;一类是本州离省城很远,在嘉道年间奏定的,经直隶州(厅)、巡道两级。这类案件不用督抚亲自提讯,是以不作为审转环节。至于斩绞大案,散州与县初审的,经府与直隶州(厅)、按察司、督抚四级;直隶州(厅)初审的多经道、按察司、督抚四级,也有少部分距省城较近的,则经司、督抚三级审转。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当时对“道”一级的使用完全出于实际行政运作的考量。在雍乾时期考虑直隶州(厅)初审案件审级不足时加入巡道,是用巡道履行府的作用,所以,道员在审转过程中的奖惩考绩,也依照知府处理。[8]而在嘉道年间,考虑到部分府离省城太远,改由邻近巡道审转军流遣徒案件时,则是以巡道履行按察司的职责,道员相关的奖惩考绩也参照按察使处理。[9] 学者在对审级问题的研究中容易出现僵化的问题,主要是预设了清代“有一级政权就有一级司法审判”,要借此论证“行政与司法不分”的观点,[10]而非从清代的实际情况入手,观察他们到底是怎样处理刑名政务的。从审级的设置与变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办理地方刑名案件这个问题上,政府常常纠缠在慎重谳狱与降低行政成本的两难之中。按照最初的设想,从州县初审到最终的皇帝勾决,如此层级繁复的审转方式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给嫌疑犯提供更多次接受讯问的机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二是充分利用官僚体系中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保证后一审级的官员级别一定比前一审级高,避免官僚们因碍于情面、回护同僚而不肯驳正揭发。但在清代地方行政中,有两个致命的问题制约了这一设计的施行。第一,省一级行政区的面积过大,省内地形复杂,很多地方交通不便。不但云贵、四川这样的省份,就是面积最小交通最发达的江苏,北部徐、淮二府距离按察司所在的苏州也有一千里以上,且要渡过黄河、淮河、长江三条江河,对涉案的两造、人证来说也十分困难。第二,清代没有专门的地方财政,凡是解往府、省的徒流死刑犯人,每案所用费用多则四五百金,少也要一二百金。[11]这些费用没有固定的出处,多系官员捐俸,或是补役、解差垫补。是以,州县中不论官、吏,出于经济的考虑,也很不乐意生事,命案常嘱贿和,大盗改为偷窃。且既然需要衙役补贴公费,州县官对衙役的管理监督就要大大松懈,甚至纵容他们勒索事主,以致地方积案累累。乾隆中期以后,刑名案件中的腐败问题趋于严重。 很显然,受国家的财政规模和僵化的财政体制制约,增加财政投入的可能性显然比减少审级或是缩短解送距离的可能性更小。因此,从乾隆年间开始,尽量以直隶州(厅)、府一级治所到巡道还是按察司所驻的地方更近为依据,调整审转程序,成为督抚们愿意采用的一种做法。但即便如此,新问题又产生了。那就是原本刑名体系设计的第二个原则:在审转过程中由高级官员监督低级官员,避免同僚回护的原则受到了冲击。根据清代官制,巡道与知府都是正四品,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相对于“臬司分尊,一经亲审,假其案有出入,府县即不敢以私语行其禀牍,欲假公上省面求则缓不及事”[12]的制度初衷而言,道对于府所产生的制约是很小的,同僚之间难免照顾情面。③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中央的刑部始终非常慎重,在乾隆年间,经常以“政贵有定”的原则,对各地督抚、按察使的这类意见给与否定的回复。到了道光初年,审转成本问题越发严重,朝廷的尺度就放得比较宽了,各省都出现了类似江苏徐、淮二府这样军流遣徒罪审转不经臬司的情况。他们甚至把淮安府六个县分成两拨,东北部不临运河临黄河的阜宁、东安归驻扎徐州的淮海盗审勘;临近运河的桃源、清河四县归驻扎清江浦的淮扬道审勘。这与学界已成定论的“一级行政对应一级司法”正好相悖。刑名程序甚至不以“府”这样一级标准的地方行政等级为依托,只关照实际运作中的便利度。当然,清廷在照顾审转成本过于审级数量与上下监督的转变过程中,死刑犯还是必须递解省城,经过作为“一省刑名之总汇”的按察司审转、督抚覆核。这是帝国慎重刑狱、保护人命的底线,是不能因为经济原因而突破的。 在地方徒刑以上案件的审转程序链上,每个环节的官员都是同级层面内理论上素质最高、权力最大、名分最正的人物,同级层面内无所掣肘、不能推卸,可以保证效率。特别是州县一级,一定要正印官亲自审理,不能假手佐贰。如果正印官因公出差,或由临州县正印官兼理,或从省城派出候补官署理。一旦被查出有佐贰官代审刑案的情况,处分是非常严格的。府一级在清初还有推官负责审理刑案,推官裁撤后,这项工作也全由知府承担。斩绞大案,特别是经皇帝过问的钦案以及被参审办的官犯到省后,在臬司衙门由按察使主审,但布政使也要会稿列名。一般来说,布政使虽然列名,出现问题也会有轻微的处分,但绝大多数的布政使是不对刑名案件提出意见的。除非他是刑部司官出身的著名法律专家,才会在皇帝的特别要求下对本省的某件重案留心,并向按察使提出谨慎建议。④至于督抚层面,清代的内地各省分为有抚无督,如河南、山东、山西;有督无抚,如直隶、四川;督抚兼有而同城,如云南、广东、福建等;督抚兼有而不同城。如贵州、广西、浙江等。在只有总督或巡抚的省分,刑名问题都由这位巡抚或总督负总责。在兼有总督或巡抚的省分,刑名案件大体是由巡抚负责,如果涉及绿营武弁,则与总督会稿题、咨。⑤总督通常情况下不会对刑名案件的审转进行干涉,但由于命盗大案州县在通详上司时要向总督报告,总督又有兼管军民二政之责。是以一旦总督对案件的审理提出质疑,从抚到县,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如果督抚异议,或者府县官员对总督的意见置若罔闻,那么总督可以向皇帝单衔奏报。⑥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很容易产生督抚不合的问题,这在督抚同城的模式里是比较多见的。虽然督抚一级在一些省分稍有制衡,但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内地省分刑名制度设计的基本判断,即:不论一个地方刑名案件所经历的审转衙门怎样应时而变,这些衙门的正印官都是该层面内唯一对这些刑案的审、核负有责任的人。正印官权力之集中,是前所未有的。 二、驳审与开参:对案与对人的双重监督 既然同级层面内没有相应的制衡力量,那么,由州县—道府—按察司—督抚—刑部—皇帝这样的纵向次序而形成的上对下的监督,就成了清代刑名系统中最重要的监督形式。监督的对象有两个,一是刑案本身,二是参与办理刑案的相关官吏。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监督并不是按照行政层级的顺序依次进行的,而是根据案件发展的具体需要进行监督。上级衙门对刑案的监督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第一是案件已经审转到本层级;第二是案件尚在下级衙门审理的过程当中;第三是两造双方不满下级的审理进而控诉到上级衙门。 第一种情况最为常见,是完全随着审转程序运作的。滋贺秀三在《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一文中,将清代这样的审转方式称为“必要的覆审制”,将其视为“官僚机构内部的互相牵制”以达到正确解释、适用法律的目的。[13]审转中监督的重要表现是“驳审”。一件刑案由县达部,层层可驳,谓之“府驳”、“司驳”、“抚驳”、“部驳”之类。案子被驳,是当时十分常见的现象,特别是负责初审的州县,碰到斩绞大案,则“上司未有不驳”[14]。因此,那些精于此道的刑名幕友们纷纷告诫州县官员、幕友,不要惧怕、抱怨上司驳案,要认真研究上司所驳的情理所在,因为“果合情理,事出公论,府司不驳,而部院必驳。”[15] 驳审的层级越高,承受压力的官员就越多,如果预测到会有“部驳”的风险,就连督抚也要十分小心。军流咨部案件,刑部本身就有驳回重审的权力。而事涉斩绞,一旦刑部对督抚的题本提出异议,内阁就要票拟“依议”和“著照该(督)抚所拟”双签。如果刑部驳词严厉中肯,还要再加“部驳甚是”一签,刑部司员可以据此议叙,[16]或干脆撤去“照该督抚所拟”之签,[17]只票“依议”“部驳甚是”二签,意味着督抚等地方官处分在即。事实上,即便还留有“照该(督)抚所拟行”的票签,根据清代“重内轻外”的传统,[18]皇帝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做出依部议的选择,将督抚驳回。如果碰上雍、乾这样严厉的君主刻意为难,督抚遭受到的处分可能会比条例所载严重得多。 慎重谳狱固然不错,但往返驳审也有很多问题。对于官吏来说有审限和经费的问题。清代一般命、盗案件初限都是六个月,州县将犯人捉拿归案、审问成招,算上解府及在府城逗留,时间已不充裕,如果再经驳审,甚至多次驳审,那么逾限是不可避免的。以嘉道年间的情形看,一件案子从初审成招至最终到省,往往要“以百日为期”[19],如果再遭“部驳”,整个案件很可能要推翻重来。⑦地方官员只好挪移迁就,以各种名目“扣限”“展限”,规避逾限处分。至于路途上和在府城、省城居住的花费,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支出,都靠官员捐俸、差役垫付,时间过长也难以支应。此外,两造及人证等受往返拖累之苦。等到地方上一系列审转程序完成,咨、题到部,奉部文发落时,往往出现笞杖轻犯甚至无辜邻证瘐死狱中,凌迟斩枭的大盗被同伙劫囚或是日久稽诛的事情,连督抚也要受到处分。因此,面对一些疑难大案,督抚或按察使等高官经常选择在州县接案通禀,或初审通详之后,就将犯证等人直接提到省城审讯,不必依既定审级挨次审转,这就是上级衙门对刑案的第二种监督方式。 第二种监督方式的形式表现为两种,比较常见的是基于“文书流程和审转流程的非同步性”。地方官向上汇报刑名案件,有用“禀”,有用“详”。一般来说,碰到州县内出现命盗大案,有司官员在初步了解案情后,就要先“通禀”从督抚到府道的所有本省上司,如同现在“通报情况”的意思。等审明事实,叙招供、作看语之后,再将本案所有文卷整理作一“详文”,“通详”各上司,再将犯证人等解送上级审转衙门。如果案情复杂,在上达详文的同时最好也要附以禀文,达详文未尽之意。所谓“如事有可疑者,需从其疑处反复辩论,俾阅者恍然觉悟而释疑;事关重大者,必将其根由曲折详陈无疑,或系现在作何办理,或俟请示后而遵行也。”[20]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接到通禀或通详的上司,在人犯审转到本层级之前,就对案情有了初步的了解,并对初审官的态度有了基本的判断。于是,每个被“通禀”的上司虽然还没等到犯人审转到本级,也可以做出三种选择:(1)同意州县官的看法,静待审转继续进行;(2)不同意州县官的看法,不待审转到本级,仅就禀文或详文立即提出驳斥意见;(3)督抚或按察使这样的高官如果认为案情重大疑难,或是对初审的意见强烈不满,可以下令本案停止正常的审转程序,迅速将犯证押解省城,由按察使亲审,或指派首府及其他得力官员在省城审理。⑧雍、乾以后,这样的做法被视作加强监督、提高效率、节约成本之法,在大案、重案上被使用得越来越多。 乾隆二十二年,有御史建议令州县官在命案在验报之初,除了通禀本省上司外,还要报刑部备案,以免本省官员官官相护,在审转过程中“删改原招、回护初审”。[21]不过,这样的建议没有被刑部认可。[22]首先,刑部作为“天下刑名总汇”,事务繁冗已是六部之最,没有足够的人力再从案件的初始阶段就对大量的地方刑案进行监督指导。更重要的是,“隐程序”的过分放大颇有弊端,即:上司衙门容易对初审官在发案时的“通禀”内容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如果最终审理的结果并非如“通禀”所说,上司难免对初审官产生“舞弊”“改供”之类的怀疑,在“通详”或是正式审转时形成意见对立。蓝鼎元在《鹿洲公案》记载的他在担任广东潮阳知县时审理的“云落店私刑”一案,就因为“从前验报如彼,今日详审如此”,同深信“初禀”的本省按察使发生了激烈冲突,换成一个畏惧上司不敢坚持己见的官员,恐怕就要办出一件冤案。[23]以刑部之权威,更非一省臬司可比,所以,他们选择拒绝在过程中对地方刑案进行监督。当然,如果碰到律例不清晰、适用拿不准的疑难问题,督抚可以预先向刑部咨询,请求帮助。 除了以文书为载体之外,这种监督方式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即督抚主动派遣亲信到各州县“密防行牌坐名擒拿”,批发州县官审理,称为“访犯”。这原本是明代巡按御史巡视地方时惯用的方式,清代裁撤巡按后,督抚引为己用,借以立威。[24]上司密令访拿的犯人送到州县衙门后,州县官往往要根据上司的意旨行事,“未审之先,要请教口气,以便迟速宽严。既审之后,要请教口气,以便轻重定拟。”[25]如果案情重大,上司特别是督抚还要将访犯直接提到省城审问。⑨这种将督抚的意志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虽然比前者更有效率,但弊端也更大。如乾隆年间担任过两江总督的黄廷桂惯用此法,引起江南官民的极大反感。黄总督对自己主政一方兢兢业业、勤政廉洁,却不能得到官民的支持深感困惑,问计于首县袁枚。袁枚在《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一文中为他分析了个中原因。袁枚说: “明公侦事委之武弁,武弁受委,托之兵丁。此辈不知是非,实固有赏,虚亦无罪,朝匦一投,暮符立下,东驰西突,所在驿骚。在公以为仍付有司鞫讯,然后裁之以法,当无颇戾。不知督抚之威有雷霆万钧之势,从空而下,讯详拘解,逐层核转,或深明无罪,立释拘系,而被访之人已弃产破家无可救。万一委讯之官人本倾危,以有事为荣,以深文为技,望控揣公意,张口辄曰:大人洞察。宁有误哉?其幕客亦曰:纵十事九虚,亦须坐实一二,为制府光颜。在公澄剔之苦心,为小人迎合之捷径,岂不可惜?”[26] 可见,这种由督抚秘密派遣带有特务性质的武官介入刑名系统,侦查民间生活的做法,是对地方文官系统极不信任的表现,不但扰民,且容易引发州县官员逢迎长官、诬陷良善的问题。清代为督抚者,偶然一用此法,可以收到监督震慑地方官的良好效果,得到能臣的美誉。⑩经常采用则多被官场中人视为“好事者”,是不能获得舆论支持的。 第三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上控案件当中。尽管在制度设计以及应变方面颇为用心,且长于变通,但清代的刑名体制终究不能摆脱官僚体制的弊端,到乾隆末年以后,州县基层政府经费紧张、因循拖延,腐败现象多见,对社会的控制力和公信力大大减弱。许多屡拖不决的案件积小成大,两造双方矛盾激化,越诉、上控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甚至有大量对地方官不满意的控告者涌入京师,向督察院、步军统领递状。根据清代的实际情况,上控到按察司、督抚的案件,按察使、督抚等人几乎不会亲自审理的,而是“辗转发交属员,属员又层层递委,以致结案无时,任情枉纵。”而京控的案件,在乾隆末嘉庆初,皇帝通常会钦差刑部堂官或者其他在京大臣带领刑部司官前往审理。但这样做的成本很高,嘉庆十二年,嘉庆帝派军机大臣英和等人外出审案,英和回京后向皇帝缴旨,嘉庆帝说:“汝之自爱,朕稔知之,此次地方供顿当不致过费。”英和回答说: “虽侨居两月,地方所费恐不免盈千累万。”“臣之仆御及马夫不过八人,蒋予蒲亦同,司员四人又各递减,然公馆中不能无应役者,加以巡捕、兵丁、书役等人逐日听候,所有饭食皆地方供应,其费安得不多?恳求嗣后除督抚被揭被控不能不用钦差,此外悉交督抚审办,若不能办,朝廷安用此大吏?倘审办不公,难免复控,自有共刑在,谁能适之?”[27] 嘉庆帝对英和所奏“深以为然”,遂转变处理方式,京控案件,先由接受呈状的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分类,事情比较重大的上奏,由皇帝下旨交该省督抚题审,是为“钦件”,必须督抚亲自提审;情节较轻的则由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直接咨交本省督抚,批交两司处置。[28] 案件由督抚审理,在对地方官吏不满的百姓眼中,虽然不及钦差大臣那样权威、公正,也总比发交本府本县要超脱很多。且事情一旦变成“钦案”,对案件的监督权就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督抚起码在姿态上要予以高度重视,随时向皇帝奏报案件的审理进程。如嘉庆二十年直隶宁津县民妇迟孙氏京控贾克行等强奸其女二姐一案,发交直隶总督那彦成审理。因为皇帝批词严厉,那彦成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先后上了八道奏折,极为慎重。[29]在这种情况下,京控的数量在嘉道年间越来越多,特别是离京师较近、交通较便利的直隶、河南、山东、江苏等省,如道光初年的江苏巡抚韩文绮,任期不到两年,就审理京控案二十三件,均用奏折上达。(11)京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刑名体系的传统生态,成为了民众对抗地方官的重要办法,一些冤假错案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申雪的。 除了对案件审断的正误进行监督外,对办理刑名事务相关官员的监督与对案件的监督是同步进行的。《钦定吏部处分则例》中,与刑名事务相关的处分条款是最多的,贯穿于刑名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如一个地方出现盗案,地方文官和绿营武弁有“疏防”处分;命盗大案人犯在逃,缉捕超过期限,文武官员有缉捕处分;捕役诬良为盗、滥用非刑,正印官有失察处分;徒留以上案件审理各有时限,各级承审官员都有逾限处分;犯证人等在监病故或是反狱劫囚,正印官及管狱官也都有相应的处分。这些名目繁多的处分轻则罚俸降级,重则丢官论罪。在办理刑名事务中,一旦触犯相应条例,各级印官及与其相配合的佐贰、首领等官、受上级委派的会审官,以及有相关防御、缉捕责任的绿营武官就要有上级衙门“开报职名”,由督抚在具题案件的同时附带“开参”。如果督抚有意或是无意将应该“开参”的官员漏参,那么,刑部核拟上报的案件时,要将这些官员“补参”。 在这些“开参”项目中,与案件审断正确与否关系最直接、措施最严厉的是出入处分。所谓出,是将重罪拟轻;入,即将轻罪拟重。承审官出入人罪,又以是否有主观故意分为故出、故人与失出、失入两类。根据《处分则例》的规定,承审官的处分以犯人的实际罪行以及错判的程度论,总的来说入罪重于出罪,故意重于过失。 如果初审、覆审的官员出现的出入错误,是在本省的审转程序中就被发现了,那么,拥有参劾属官权力的督抚是有自行权衡余地的,常因为一些私人关系的原因,免参或者从轻参奏。如道光末年四川遂宁知县蒋某被入室抢劫的强盗杀害,知县徐钧为回避处分而讳盗,诬陷蒋某的妻子与小妹合谋杀死蒋某。案件由潼川府转解到四川按察使张集馨手中,张集馨提齐人犯亲审,揭露了蒋妻、蒋妹刑讯诬服,知县徐钧因避盗案处分,故入人凌迟重罪的恶行。事发后,徐钧料到自己要被参劾,开始四处打点。果然,很快他的亲友:本省学政彭某、山东巡抚陈某先后致书四川总督琦善,央求免参。琦善在道光年间还算得一个强势能吏,对此也只能碍于情面不予追究,徐钧平安乞病而去。[30] 不过案子一旦送到刑部,事情就不容易蒙混了。刑部官员的考绩、声名,很大程度上基于纠正错案的数量。一旦平反大案,更可能获得“天语褒奖”“明允之名闻天下”的荣誉和京察一等、记名道府的实际利益。[31]错案一经部驳,承审中出入人罪的地方官,下到州县,上到督抚,都难免于参劾治罪。 三、“依律”与“有权”:刑部与皇帝的权力性质与作用 与地方上不论名、实都是同级集权的问刑体制相比,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名义上是相对分权,即众所周知的三法司会议制度。但是,和明代相比,清代中央刑名体系中的分权色彩被大大削弱了,趋向于以皇帝——刑部为中心的纵向集权。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要三法司会议的事项范围被缩小,二是三法司的合作模式发生了变化。 与明代直省只上报死刑案件的制度相比,清代中央对刑名的控制权大大增加,各地涉及人命的徒罪及以上案件都要报刑部覆核,但需要三法司会核的案件则仍然延续明代旧制,仅限于死刑案。在乾嘉以后,立决、枭首、凌迟大案上报开始改题本为奏折,为了加急保密,这些案子的处理是不必“会法”的,只由刑部单独核议上奏。(12)至于发生在京师内外的案件,根据明代制度,从笞杖到斩绞的所有案件,都必须经过先由刑部或都察院先审,再将犯、证人等移送大理寺覆审。清代则不然。京师内外笞杖小事,五城御史和步军统领衙门即可裁决发落,而徒流以上案件送往刑部后,则由刑部签分某司,由司官审理成招,只有死刑案件才知会寺、院。除了单件刑名案件的覆核、审理外,诸如热审、大赦、减等这些在某一时间段内集中处理已决案件的工作,以及根据内外大臣官员的提议对一些具体刑名政策进行修改完善的工作,在清初还经常交给“三法司会议具奏”,但在雍、乾以后,则多由刑部独立完成。 会议范围大大缩小的同时,在仅存的会议事项中,刑部的主导性也越来越强。在明代,都察院与刑部并称“问刑衙门”,地方上由按察司系统上报的案件由刑部核拟,而巡按御史上报的,以涉及官吏为主的案件则由都察院核拟。部、院核拟后,将全案移送,大理寺遇“不合律者,驳回再拟。招词事情含糊不明者,驳回再问”[32],称为“审录衙门”。顺治末年裁撤巡按之后,都察院在地方上的“触角”不复存在,“问刑”衙门的地位不复存在,三法司的合作模式改为“主稿—会议”式。 “主稿—会议”模式的制度安排和实际操作有很大不同。根据原本的制度设计,会议的程序应该是:各省督抚将一件斩绞死刑案具题的同时,向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送题本的副本“揭帖”各一份。三法司在收到揭帖后,分别由各自的该管官员独立对案件进行覆核,写稿说堂。刑部作为主稿衙门,将本部堂官批准的奏稿送到大理寺、都察院,寺、院官员将己稿与刑部之稿核对,意见相同则列名会奏,意见不同则与刑部“签商”。“签商”不果,“两议”上奏,听皇帝裁决。但实际的情况是:大理寺和都察院并不根据揭帖提出覆核意见,而是专等刑部奏稿送来后,根据刑部的意见或依或驳,未经独立核查。[33]而三法司会核案件定有期限,主稿的刑部通常将期限用到最后,才将奏稿交送院、寺,寺、院宥于时间局促,除非碰到极为认真的官员,更多情况下是随手列名,应付了事。[34] 这一格局的形成原因很多,如清代中期以后审断用案多于用例、刑部专业化程度提高、皇帝对言官系统的刻意压制等等,此处不予赘述。总之,在清代,特别是雍、乾以后,刑部在三法司中已成一枝独秀。在明中期就已渐式微的大理寺至此已经沦落为闲散衙门,“居此职者视若赘旒,头仰屋粱,手批大诺,相夸为识时务”[35]。都察院境遇稍好,但每有签商、两议之事,也十有八九被刑部和皇帝以“不谙律例”为由予以驳回。 在中央层面,刑名大权集中到刑部后,官僚体系内部的监督也就告一段落,但仅仅如此,并不能体现一个专制国家的根本属性。在刑部之上,皇帝在刑名体系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在雍正以前,清代皇帝参与刑名活动主要在最后阶段。即每一件死刑案件的具题环节、军流案件的汇题环节、秋审案件的勾决环节以及一切重大刑名政策经刑部议覆后的决策环节。雍正以后,奏折文书的使用逐渐普及起来。起初,奏折更多用于军国大政、人事任用,及地方文武大员与皇帝联络私人感情等事,刑名案件作为日常基本政务,仍用题本程序处理。然而面对雍、乾这样权力欲望极强的君主,不论督抚还是部院大臣,无不战战兢兢唯恐有失。到乾隆初年,一些谋逆反叛、江洋大盗、弑亲逆伦等大案,虽无具体规定,但各地已多改为密折陈奏,下部议后,刑部也用密折议覆。此风日长,到乾隆中期,已有督抚将普通谋故杀、吏胥作弊等案改题为奏。[36]不但定拟结果,其他如侦查、缉捕、审理过程,及经部驳后的改拟情由也随时上奏。[37]这样做,既可以满足皇帝的控制欲,出现问题又便于卸责。特别是乾隆末年以后,京控案件日益增多,负责接收京控呈状的都察院与步军统领衙门先将案情上报皇帝,再奉旨发督抚审理,形成钦案。因为皇帝对这类案件已有先入为主的印象,是以承接审理的官员更要随时上奏,报告审案进度。皇帝从拍板决策转为参与过程,对刑案控制力大大加强。 除了对案件本身的影响外,强大的皇权在刑名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对其下全体法司官僚的监督。在一个没有民主监督的政体下,皇权对庞大官僚集团的抑制是最为有力且有效的。从理论上讲,皇帝作为家天下政权的拥有者,他的利益与政权的利益是一致的。相对于拿俸禄、有任期、有各种个人或小团体利益诉求的官僚,其地位和视野都是比较超脱的。特别是对于作为“天下刑名总汇”的刑部,在这个逐层集权、上级监督下级、刑部监督地方的刑名体制下,因为都察院系统被严重打压,刑部的权力被格外放大。既然刑部官员的考绩、名誉都来源于平反纠正错案的情况,那么,“苛驳”地方官的倾向也就会自然而然出现。且清代并无司法独立的制度,刑部官员亦是官僚系统中的一分子,其入仕、升转都与其他官员大体一致,虽然身居中央与地方上的利益关系相隔较远,但仍然无法摆脱官场中人的爱憎、偏倚。另外,各地督抚作为地方官,固然要遵循“内重外轻”的行政惯例对部院的意见小心翼翼。但督抚身为封疆大吏,身份上可以与部院堂官匹敌,如果部院的意见实在令督抚难堪,督抚坚持己见与之僵持,皇帝就成了他们之间唯一的裁决者与平衡力量。 康熙末年朝廷党争严重,刑部核拟各地刑案,也不能秉公办事,“遇督抚之素相亲厚者则有意顺从之,遇督抚之素不相契者则故意驳诘之”。[38]是以督抚也常常不服部驳,每每固执原题具奏。根据当时的制度,“大凡督抚题奏本章必勅部议覆而后施行”,所以“内重外轻,乃事势之固然”。在这种情况下,督抚一旦对部议不满,就要经过上督抚题本、下部议、刑部议驳上题本、驳回,督抚不满再上题本这一系列循环过程。二者互不相让,以致“一经驳回,往返迟误数月,干连人等多至受累”[39],效率和成本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也非常突出。雍正帝即位之初,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将立场先站在刑部一边,规定日后反经部驳之命盗案件,如果该督抚固执原题,部内可将督抚议处具奏。[40]但一年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因为自己针对部驳事件连续几次批复“部驳甚是”,就开刑部揽权妄驳之端,甚至因为部堂与督抚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漫行搜驳。[41]雍正五年六月,刑部有驳河南巡抚田文镜题胡大保强行鸡奸曹柱儿未遂,将其勒死一案。田文镜将胡大保原拟斩立决,三法司改拟监候。是时,田文镜因为科举朋党一案,正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此时将田氏议驳,突显部臣故意为难他的意思。为此,对田文镜采取坚决保护态度的雍正帝大发议论,批评内重外轻的行政格局,并准许日后督抚到部之文,再有被部臣非理驳诘者,准督抚密折奏闻。[42]此后,刑部与督抚之间在理论上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制衡关系。一旦督抚与刑部之间就个案产生矛盾,就会同时将问题提交到皇帝面前,既不至于像康熙年间那样互相扯皮,经久不能结案,又不会使刑部一手遮天,任性苛驳。皇帝则居于其中,充当仲裁的角色,对刑名大案的影响力被大大加强了。 州县等地方官有上级监督,督抚有刑部监督,刑部有皇帝监督,那么,是否意味着高居九重、独掌生杀大权的皇帝毫无制约,可以为所欲为呢?理论上固然存在这种可能,但从实际情况看,清代皇帝作为唯一对死刑案有“自由心证”权力的人,虽然没有人或机构可以对他进行硬性制约,但处在由官僚士大夫主导的舆论环境之中以及置身于以内外法司,特别是刑部的审断为直接基础的法律体系当中,他究竟有多大的勇气和余地可以使用这种权力,虽然难以量化,但也不应过高估计。在清代的法制体系中,皇帝这个角色的优点是利益超脱,理论上是“道”的天然代表,现实中又受到时代价值观和官僚制度的软制约。这一制度的缺点是法律专业素养不足、拥有生杀大权的君主如果一意孤行,是无法被硬性制约的。因为同时具备这样的优、缺点,在帝国的刑名体系中会存在三种极端状态:(1)一个明君,勤勉、自控、明察,在一个超脱的位置上,利用手中生杀大权和比成文例案更接近“天道”的朴素正义观,有力驳正法司官吏在审断中因为各种各样原因产生的错误,最大限度除暴安良,打击贪官墨吏,平衡中央、地方法司之间的矛盾;(2)一个暴君,一意孤行,毫不顾忌“天道”与制度的约束,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滥杀无辜;(3)一个庸君,没有承担君主责任的能力,听凭官僚系统自行运转。清代在政局比较稳定、君主比较强势的时期,大部分皇帝面对一般刑名案件,多有向第一种情况靠拢的追求,至于接近到何种程度,需视具体人、具体情况而定。(13)到同、光君主衰微之际,一般刑名案件的处理更接近第三种情况。 四、结语 对于清代这一同层高度集权上级监督下级的法制体系,法学背景的学者大多评价不高,其中日本学者岛田正郎的评价很有代表性。他说:“郑重反复之覆审制度,对百姓而言,仅系增加被剥削的机会而已,毫无公平正义之情形,是以百姓宁屈死不讼,多选择屈死一途。[43]与之相反的是,尽管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这一制度的负面影响,如成本过高、效率低下、官官相护、犯证拖累等等,且毫不讳言、百般应对,但清人对本朝这一制度的总体评价非常之高。道光年间的名幕管同就认为:“国家慎重人命,旷古未闻。盖古者富侠酷吏操生杀之权,今虽宰相不能妄杀一人。古者人命系乎刑官而已,今自州县府司督抚以内达刑部而奏请勾决,一人而文书至于尺许。民之感激也深,天之垂佑也至。社稷延长,端赖于此。”[44]太平天国爆发以后,迫于战事压力,清廷订立“就地正法章程”,将生杀大权部分付与地方官。犯谋反、强盗等罪处以死刑者,不必像过去那样层层审转上报中央,只要有州县官录供详报,督抚查核案情,批饬道府官员提审或前往督审,认定无误后,报督抚后即可就地正法,不必经过“郑重反复之覆审”。[45]可就在这一阶段,各地频频揭出冤案,如四川东乡抗粮案、江宁三牌楼顶凶案、河南邓州王树汶案、杨乃武小白菜案,都给朝野舆论带来很大震动。东乡案审理期间,张之洞正在四川担任学政,他亲眼目睹地方官借“就地正法”之便滥杀无辜,遂作《四川东乡县案是非未明疏》上奏。奏疏开头称:“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狱平。”赞美清代固有法制体系,不论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特别慎重人命的特点。进而话锋一转,谈到自从将权力下放,改行“就地正法”后,封疆、牧令“心粗手滑”,杀戮太重。“朝廷若再不遏其流,以后肆贪虐,必致殴民为盗而后已。”[46]光绪七、八年前后,随着全国各地相对恢复稳定,多位科道官先后奏请恢复原有体制,将死刑大权部分收回中央。 “就地正法”简便高效,成本低廉,一下就解决了旧制中无论怎样弥缝,也难以解决的问题。何以时人如此反对,极力要求恢复旧制呢?《申报》关于杨乃武小白菜案的一篇评论揭示了此时中央不能下放死刑权的问题所在。评论说:“余初疑,国家既已信任督抚,何必诸事必须部覆,未免有信任不专之嫌。由今观之,则始知国家之用意深而立法密也。外省离京较远,而官民犯罪每由地方官上下其手……”[47]换言之,就中国传统人情社会而言,一方面,地理范围越小,范围内的人与范围内事情的利益关系就越大。以州县为例,虽然官员是外来的流官,但衙门内的书吏、衙役,与两造双方容易产生利益关系,从而干涉、左右案情。而地理范围越大,这种影响就越淡。另一方面,品级相近、关系相熟的官员问容易通融枉法,而品级较殊、交往较少的官员间则坚持原则的可能性更大。再就清代的官僚制度而言,道府以下官员大多在本省内部调动,督抚对于本省官员、政务负有全责,下级官员出现问题,督抚等上级官员也要负有连带责任。而京官在制度上与他们两不相干,皇帝就更加超脱自由。这就是清王朝一定要使用逐层集权、上级监督下级的方式达到“慎重人命”的效果,而不惜大费周章、层层审转。 清人多有凡事有无相生、利弊相乘的思想。在讨论王朝的法制体系时,他们的态度是:以慎重人命、减少冤案为根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对同时产生的效率、成本等问题采取因地制宜,因时而变的微调策略。相对而言,受现代法律思想影响的法学家在讨论清代问题时,往往以工业社会下的价值判断为标准,忽略了清代社会和整体政治制度下的实际运行情况。这是我们在阅读现代学者研究著作时,应该特别慎重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4-09-23 注释: ①以诉讼为研究视角者如朱一泓:《清代地方刑事诉讼程序浅论》,湘潭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黄文斌:《清代诉讼制度几个问题的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等等。以审判为视角的研究如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等。 ②清代法律制度史研究的学者通常将中央制度与地方制度作分割研究。侧重地方法制研究的如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等。侧重中央法制研究的如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郑秦先生在《清代司法审判制度》一书中,虽然兼有地方与中央两方面的内容,但分散在不同篇章中,并未述及其内在理路。 ③道光六年,道光皇帝在上谕中称:乃近年以来从未有道、府、直隶州于所属之案平反得情,经督抚题达、部臣查明奏闻者。总由积习既深,官官相护。平时因循疲玩,置民瘼于不问。遇有案件,又务博宽厚之名,扶同徇隐。参见《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九十八,道光六年五月甲午。 ④乾隆年间的这类情况是比较多的。如乾隆四十一年河南有错审案件,乾隆帝责备河南布致使荣柱说:“荣柱向系刑部出色司员,律例素所谙习。虽现署藩司,谳狱非其专责,然于审拟此等重案,亦应留心商办,何得视同膜外,听该抚桌率拟若此。荣柱并著传旨申饬。(卷一千六,乾隆四十一年四月辛亥)乾隆五十九年又因陕西邪教问题严重,下旨陕西布政使穆精阿”该员系删部司员出身,谙习审案。现在该省有邪教重案,臬司姚学瑛不过照常供职之员,未必能办理得当。此案即著阿精阿在彼帮同秦承恩严切审讯。参见《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百五十九,乾隆五十九年八月甲戌。 ⑤如果碰到涉及官员的案子,题参审问文职由巡抚主稿,总督会稿;题参审问武职有总督主稿、巡抚会稿。 ⑥如雍正六年湖广总督参奏湖北按察使王肃章等讳盗。王肃章在接到知县上报的窃案后,没有发觉这是一起讳强为窃的案子,在同时上转督、抚二人后,总督驳斥而巡抚照覆,王即照窃案办理。总督按照程序题参了按察使以下审案的官员,并向雍正帝密折奏报。参见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潮广总督迈柱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三册,第36页。 ⑦部驳有三种情况:督抚等拟罪过轻,而部议应从重者,应驳令再审。如督抚拟罪过重,而部议从轻者,若情节显然,该部所见既确,即改拟题覆,不必驳审。如果情节不清,则仍发回本省重审。参见《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百十二,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乙巳。 ⑧如那彦成道光十年担任直隶总督时,平山县有民人要自新被勒挂身死一案,平山知县先以要自信图奸寡妇赵氏被拒后自缢身死通禀。总督认为知县所禀情节支离驳回,臬司委派子牙河通判去与知县会审,以原审回禀。臬司仍予驳回,并将相关人员提省,交保定府知府督同委员审明,系要自新酒醉强奸赵氏,被赵氏与其母轫死移尸。平山县知县被总督摘印交吏部议处。参见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十,《二任直隶总督奏议》,《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049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37页。 ⑨道光十年那彦成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有新雄营都司奉命在境内访查邪教敛财惑众情形,访获新城县民胡犄角立会治病敛财一案,报知总督。邢彦成一面上奏,一面命新城知县将犯证解省,饬保定府审理。《那文毅公奏议》卷七十,《二任直隶总督奏议》,影印本续售四库全书,第0497册,第5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⑩如嘉庆年间的两江总督长麟就流传有“微行摘印”的故事,甚至被改变为戏曲。参见梁恭辰《东北园笔录》续录卷三,《微行摘印》。昭琏《啸亭杂录》卷二,《牧庵相国》。 (11)韩文绮担任江苏巡抚时间为道光二年九月到四年闰七月,其在江苏巡抚任内审理京控案件的情况见《韩大中丞奏议》卷一至卷七,影印本续四库全书,第04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2)“会法”是清代的行政术语,即三法司会议、会核之意。参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四卷抄本《通本签式》卷一,凡例,第9页。 (13)而在面对政治色彩浓重的案件时,则着力在第一种与第二种情况间平衡捏合,寓私意诛杀政治反对派于正常的刑名体制之内,尽量不留下破坏体制的恶名。如雍正帝费尽心机、步步为营地处理年羹尧、隆科多等案,使之必须符合法律程序,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标签:按察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