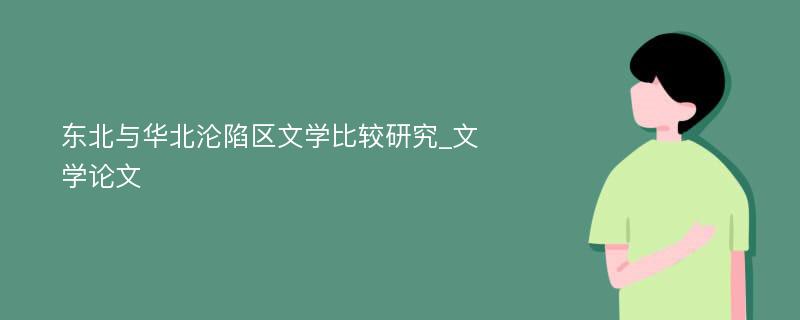
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沦陷区论文,华北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北沦陷区文学大体是在1939年后进入中兴期,1941年华北沦陷区文学开始崛起,1944年以后,两个沦陷区文坛都逐渐显露出萎缩的态势。(注:黄万华:《沦陷区文学鸟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这一得到学术界认可的研究结论, 向人们表明这样一个史实: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其发展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但却承担了极其艰巨的民族重任。置身于法西斯专制之下,新文学作家们在“不聋而哑”的时代无畏地“不言而言”,成为延续和发展中华文学的中坚。同时,基于政治格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呈现出迥异的风貌。从文体的运用、题材的选择到创作格局的调整,从形式结构到美感特征、地域特色等方面,都可以梳理出两个沦陷区文学各具特色又相互影响的创作走向。本文试图从两个沦陷区文学中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的各自特征的比较分析中,揭示出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价值。
一、小说创作态势的一元与多元
在东北沦陷初期,以萧军、萧红、金剑啸、罗烽、舒群等为核心的“夜哨”作家群构筑了抗争黑暗现实的文学前哨阵地。这一作家群体以其鲜活的作品文本、富有生气的精神跋涉者的人物形象和雄犷、明快的创作风格,奠定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异族高压统治和民族意识潜行的政治环境下,“夜哨”作家群整体上呈现出较为自觉的审美追求。小说题材往往落笔于东北故土的突变与民众的苦难和觉醒,显示出贴近现实的创作倾向。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东北生民身上所体现出的强悍、野性、豪爽、互助等品格及由其组成的关东精神,成为作家群体共同的追求。作品自然环境的设置和风俗语言的运用,充满着北国文化韵味,明丽刚健、朴实粗放,具有鲜明的关东风情。“夜哨”作家群的创作表现出东北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和民族意识相融合的特征。
在白山黑水之间息息运行的民族正气,对优秀文学传统的有意识的、充满热情的继承,特别是东北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强悍和豪爽的民风民俗,使东北现代小说在题材的选择和审美风格上表现出相应的特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东北的乡土小说。东北、华北沦陷区作家在对新文学主流传统的坚持中,都有过对“乡土文学”的提倡,其含义不限于提倡描写乡村题材的作品,而是有着更深远的追求。东北乡土文学的倡导者山丁就将乡土文学归结为“描写真实”与“暴露真实”,评论家楚天阔则明确指出乡土文学至少含有“民族”、“国民”、“现实”、“时代”这些意义在内。所以说,乡土文学突现的正是张扬文学的民族性、国民性与现实性的文学观念。东北的乡土文学在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和时代的特征:一是国难与乡愁的交融,二是民风乡俗的剖析同国民品格挖掘的结合,三是美学品位的追求同高扬民族精神的统一。东北乡土文学源起于山丁的乡土小说,一开始便以社会批判的目光揭露现实,表现农民经济与精神的重负和农村的灾难,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称其为苦难小说,因为它指示给我们的是完全失去了欢乐的人生悲剧,让人目睹的是沦丧的国土上的东北乡民无边的灾苦。作为东北乡土文学的倡导者和成功实践者之一的王秋萤,其小说的人物画廊中,以都市生活中的工人和知识青年居多。工人家庭的血淋淋遭遇、知识青年的苦闷与彷徨,都通过作品独特的结构与切入点,在晦暗社会背景上得到鲜明、完整的展现。疑迟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同情下层劳苦者的倾向,往往被“寒气”所笼罩。这里不仅有东北荒原的酷寒,更有社会现实的刺冷,而作家又将其同东北乡民们在生死场上的挣扎与抗争相揉合,使其所叙述的故事,显示了复仇这样一个最基本和重要的主题;“寒气”中又融入了如同火山爆发时所掀起的一股股冲天热流,生命意识得到更为深入的开掘,显示出有着独特内涵的关东人文精神与悲怆粗犷的艺术魅力。疑迟的笔触在涉及纷乱繁杂的都市生活时往往显得流畅不足,而每有乡野文化的融入方呈生气。其创作乡土小说自有其独特的美学追求:“不铺张,不渲染,常常是利用不华丽的题材,用无颜色的笔……选择着自己所寻求的纯朴的故事,而剔除一切华丽的浪费。”(注:小松:《夷驰及其小说》,《新青年》(沈阳)第98期。)疑迟“以强有力的笔调、粗犷的线条、简单的轮廓”,为我们“构成一幅荒原的流民图”。(注:小松:《夷驰及其小说》,《新青年》(沈阳)第98期。)
不论是追随“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遗韵,或是以“为艺术而艺术”为标榜,或是师法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东北沦陷区作家在共同的审美追求中,显示着鲜明的个性。爵青小说集《群像》,受某些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哲学观念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爵青的小说对现实的批判自有其特殊的力度,但这种批判大多是建立在精神废墟之上的。其作品更多是表现“一个哲学思维患者”的世纪末情绪,被一种神秘气氛所包围。作者旨在以“非俗的故事”表现“超乎常人以上的独奇的性格”(注:姚远:《东北十四年小说和小说人》,《东北文学》1946年。),其中常常映现出作家自我的生活面影。艺文志派作家古丁的小说集《奋飞》,执意描绘各类乡间人物的命运,真实地揭露阶级压迫下的人们吞食荒土、争吃死尸的悲惨现实,给人以沉重的艺术感染力。《奋飞》之名取自《国风》中“静夜思之,不能奋飞”之句。顾名思义,作品主旨在于展示小知识分子“欲奋飞而不能”的困苦、愤懑心态,作者对生活的哀叹,使人闻之多生幻灭之感。
相对于主题鲜明的东北沦陷区小说,作为文学革命肇兴之地的华北,承续着新文学发展的路向,以现实主义为依托,表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小说创作格局。
华北沦陷区文学发端于1939年兴起的校园文学热潮中,它同时也标志了华北沦陷区小说的产生。校园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张秀亚,其中篇小说《皈依》和《幸福的源泉》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作者试图以其作为自我与社会的对话,进行某种心灵的沟通,结果却未获成功;在“梦的国度安排自己”,但“梦又无法继续做”(注:张秀亚:《大龙河畔·自序》,天津海风社1936年版。),梦境的轻幻与现实的沉重形成强烈反差;面对民族命运的巨大转变,在前行无路的困境中而皈依宗教。她轻曼、静秀、圆美的创作个性,柔和、轻灵的笔致,和谐、圆润的格局,将纯情人物的描写同铺叙环境、渲染气氛揉和在近乎古典诗词曲赋所特有的意境中,表现出作家醇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和富有特色的文学追求,由此提供了华北沦陷区不多见的诗体小说。校园文学的另一代表作家赵宗濂的创作也颇引人注目,他这一时期的小说结集为《在草原上》,大多篇什以抒情的笔致描摹下层民众的苦难而又透出顽强的生命力的生存状态,展示“柔和而刚毅的中国人的灵魂”(注:南星:《在草原上·序》,北平辅仁文苑社1940年版。)。他的创作以充沛而真挚的激情和对社会现象的渐趋深刻犀利的透视,成为华北沦陷区乡土文学的先声。
继校园文学勃兴的余势,华北沦陷区小说进一步展开了全方位的、多元的开拓,走出以往单纯的农村题材、爱情题材的狭小天地,作家的笔触更为关注城市中各阶级、阶层的人们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于是出现了擅长工厂题材的张金寿,熟稔京城风俗人情的萧艾,描绘青年艰难成长的心路历程的王石子,辛辣嘲讽贪官污吏的田秀峰等。
特别应提到的是,来自东北的黄军和范紫的乡土小说的创作则弥漫着浓郁的北国气息,黄军粗劲的笔触几乎都循着山野乡村的平民百姓挣扎于战乱中的悲苦命运而游动。他的作品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善于从人物活动和细节来表现东北特有的世态风情;范紫入关后的创作题材迅速地从恋爱故事转向对阶级压迫与复仇的揭示。尤其是《黎明前》中王三嫂的形象所体现的质朴而坚韧的反压迫意识,足以让阶级的压迫者以及民族的压迫者胆寒,具有特殊历史境况下的曲笔意味。与此相呼应,毕基初等文学新人形成了华北沦陷区独特的山林小说创作,刻画了形象各异的山林草莽人物,在为正常社会秩序所不容的极端状态中开掘民族意识。借“绿林传奇”来弘扬民族正气,将清纯、雄旷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青龙剑、酒旗等人文之物交织在一起,在一个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身上写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文笔强悍刚健。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引发了华北乡土文学的勃兴。华北的乡土文学在时间上显然是继东北乡土文学之后而起,但是其理论主张要比东北乡土文学显得更为成熟和完整,其创作也较多地带有鲜明的理性色彩。关永吉是华北文学最早倡导乡土文学者。他说:乡土文学要“把握写实主义的本质,认识现实的存在,强调‘乡土’——家、国、民族的观念。”这一主张,表明了其乡土文学创作理论的民族意识,同样,他的小说便绵延着同“我乡我土”——“生长教养我们的作家的整个社会”——的血缘般的深情,《牛》、《苗是怎样长成的》等小说表明作者对中国农民命运深切的人文关怀。
华北沦陷区小说创作中,通俗文学创作的风行成为一种非常醒目的文学现象,或许是其文体特征中蕴含的与现实的疏离和浓郁的传统色彩决定了它为特殊时期的深怀国恨家仇的沦陷人民所倾心接纳,其中白羽的武侠小说创作甚丰,并表现出对现实主义创作意识的追求,昭示着传统的文学体裁与现代文学意识的融会;王度庐擅写“侠情”,揉刚、柔、侠、爱于一体,创造了言情武侠小说的完美形式;刘云若的社会言情小说人物生动,描写酣畅淋漓;耿小的滑稽小说于谐谑中寓褒贬,独辟针砭时弊的蹊径。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于多元中透露出成熟,体现出非常时期的文学的美学追求与社会道义、责任感的融会。如果说文学是人学,是社会发展进程的生动写照,那么,它必定不只体现为单纯的美的想象、塑造和追求,更要表现出于人类社会的意义所在。
二、散文创作题材的庞杂与闲适性主潮的崛起
沦陷初期的东北文坛,杂文因长于议论而兴盛一时,古丁的《一知半解》和季疯的《杂感之感》便是其中的代表。古丁所写的杂文不屑于空洞的人生杂谈,社会批评的成分较多,往往侧重于针对现实文坛有感而发,激情洋溢,犀利泼辣,既有“肉搏社会”的斗士风范,又不乏讥讽、幽默与趣味,表现出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季疯把杂文锋芒指向了敌伪文化统治,著名的《言与不言》篇就有如铁屋中振聋发聩的疾喊。其行文朴实,刚劲中显露深沉,于对时弊的针砭、社会人生的分析和古今中外史籍与作家的论评中,营构对人生世态的独特感悟。
题材庞杂,是东北沦陷区散文的一个基本特征。源远流长、底蕴丰富的种种文化风俗,流连于山水自然中引发的奇思遐想,翻拣古今历史时涌现的人生感喟,品鉴艺苑珍玩时纷至沓来的审美遐思,种种人生况味麇集于作家笔下,由此抒发的情思,有热情的呼号,也有消极的避世。也丽的散文多记写生活琐事,表达个人悲欢,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不平之气常常溢于笔端,处处隐现着作者深重的忧患和对时势的关切。成弦的散文集《奈何草》抒发的是哀莫大于心死的人生感受,唐景阳也写日常琐事,但他将弥漫于沦陷区的压抑、悲愤和孤独情绪铺排得近乎到了极致。他的《乡居散记》、《再见到母亲》等篇什将浓浓的思乡情化作一片深郁的咏叹,又令人深切地体验到作者对祖国的无限眷恋之情和对民族解放的企盼。就各自的特色而言,关沫南、萧戈等“说梦者”的杂文时露锋芒;爵青的议论性散文富有思辨性的创作特色,充满了洞悟人生的理趣,也包含着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评判。抒情散文在东北沦陷时期的散文创作中数量居多,由于殖民统治的严酷,散文抒情当然是打了折扣的。作家们对时代的感叹、民族情愫的传达以及自我心灵的告白,都是以迂曲的方式折射出来。但娣(田琳)是优秀的抒情散文作家,她的《望乡》、《天涯寂寞》、《樱花的季节》等均受何其芳《画梦录》的影响,抒发孤寂、苦闷、抑郁的情怀,尤其难得的是作家表现出敏锐的感受力和准确而精致的表现才能,其写意式的叙事手法也独具艺术魅力。
日伪殖民统治后期的东北,时势更加险恶,这就迫使有良知的作家们不得不更曲折地表达自己思乡爱国的情思。寓意梦幻、曲笔象征,成为此时散文创作的特有手法。
华北沦陷区的散文作家以随笔写作为突破口,因其涉写范围由“宇宙之大”而至“苍蝇之微”,故“个人性”、“闲适性”的随笔小品成为华北沦陷区散文创作的主潮,其取得的成就在其他形式之上。
沦陷初期华北文坛的知识小品随笔创作形成强势。较资深作家多热衷于创作抒情状物小品和知识小品,周作人《谈鬼怪》、沈启无《无意庵谈事》、永明《听雨庵随笔》等,是这类散文中的代表性篇章,杂文则寥若晨星。华北沦陷前期散文创作的走向,整体地笼罩在随笔和小品两种形式之下。
华北沦陷后期散文依旧呈现出以何其芳与周作人各自所代表的两种创作趋势,虽然个人性、闲适性的随笔小品仍是散文创作的主流,但创作态势发生了些许变化。个人性散文中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其与反抗奴役的时代主旋律相融会,显示出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这种创作格局的形成,亦与外来文学的影响相关。西方文学中以作家个人为本位的散文观很容易与华北散文作者创作心态发生契合,推动着散文创作潮流的发展。林榕《远人集》中收散文30篇,多为写景之作,作者热心于对细致景物的描画,恬淡平和的诗意中又契入对人生的思考,表现出作者内心对现实的关切。
华北沦陷区的小品随笔创作队伍,随着张秀亚、毕基初、林榕等一批年轻诗人的加入而更显壮盛,同时新人加盟对这一文体的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作品虽也偏重于知识理趣的叙写,但青年期的压抑与苦楚,却是时时可以令人感受得到的。林榕的《远方的梦》,所传达出的正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年轻作者共有的苦闷的心绪,并构成了其散文创作的基本意象。同时,华北沦陷区散文于所笼罩着的青春苦闷的气息之外,又多了一种书卷气。俞平伯、商鸿逵、毕树棠等一些资深作家的随笔,以及麦静、张秀亚的作品都属此类。
当然,华北沦陷区散文作家的创作是严肃的,他们在进行小品随笔创作的同时,又尝试着诗化散文的创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生命精神得到了升华,尤其在民族战争处于重要时刻,这种生命精神在其作品中得以弘扬,传扬开去,对于唤起民众的觉醒和民族意识的增强,具有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三、贴近泥土的现实诗篇与诗歌形式的多方探索
沦陷区诗歌在继承了抗战前的新诗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诗学质素,华北沦陷区诗歌的重要价值在于其在诗歌形式上的多方探索,而东北则以贴近泥土与现实的诗篇,展示出一种地域特色鲜明的粗放、悲凉的审美风范。
东北文学作为中国沦陷区文学最初时期的实践,首先在反帝抗日文学先导上显示了其历史存在和价值。
面对乡邦沦丧、生灵涂炭的严酷现实,“夜哨”作家群以“原野的呼喊”奠定了东北沦陷区诗歌创作的基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金剑啸,他的《兴安岭的风寻》,真实描摹出东北抗日武装可歌可泣的斗争画面,是东北新诗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其他如萧军、罗烽、萧红、舒群等,也取贴近现实的文学道路,反映现实苦难,揭露种种社会罪恶的根源,将一己的情怀心绪揉入民众的喜怒哀乐之中,显示出较为宏阔的视野和积极的文学追求。日寇对东北地区的高压、严控和封锁使东北新诗整体笼罩在冷郁沉重的阴霾之中,尤其是与关内新文学的关联近乎中断,使其背负了又一重生长的艰难,“精神上失去外界滋养,在大饥渴和窒息中,又看不到前景和出路,都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彷徨”(注:王秋萤:《东北日伪统治时期文艺社团的发展》,《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到30年代末,古丁等人的诗集相继出版, 冷寂的诗坛生机渐复。古丁的散文诗集《浮沉》以集名摹写出作者的心境,充斥其作品中是种种矛盾的心态,砰然有声的心灵的撞击,阴郁悲苦的意象,传达出焦虑苦闷的情绪。小松的诗歌风格受19世纪英国抒情诗的影响较深,在内容上,小松从不讳言他的诗作是“痛苦的歌讴”,毕竟是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放飞的“心灵最深处的声音”,其沉重与真挚并在,而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出“清淡中含有快乐”,具体体现为对想象、节奏、词藻等的协调配置,从而构筑了一种雅致轻灵的艺术风格。冷雾社成弦的诗歌创作也颇为引人注目,在《青色诗钞》和《焚桐集》中,诗人在焦灼的叩问中表达了对诗艺的痴迷和现实中的幻灭,这使得他的诗作总是弥漫着无法消散的寒寂的“冷雾”。如果说前期的诗作虽不失真诚却有偏向个人心灵一隅、诗风晦涩朦胧之嫌,那么,随着40年代初诗季社的出现,东北诗坛明朗清新之作渐出,主题取向更贴近于现实生活,艺术形式、手法的取向则由前一段的晦涩朦胧转向明白晓畅,整体上呈现出更为成熟的走向。40年代,山丁、冷歌、金音、徐放等人的诗风渐趋成熟,东北沦陷区的新诗创作渐入佳境,小说等文体集中体现的“乡土文学”思潮也影响了新诗的现实取向,诗坛普遍地摆脱了歧曲幽晦的表述形态,转以清朗甚至强悍粗犷的诗句抒写乡土情怀。山丁的诗作激情充沛又不乏深刻的透视与体验,二者叠合成生动的厚重,他似乎对这片蛮荒之地上的拓荒者更加情有独钟,先后创作了《拓荒者之歌》和《拓荒者》,将颇具区域特色的人文现象和当下的社会现实融为一体,透出东北生民强健不屈的磅礴之气。冷歌的笔致显得清疏而舒缓,善于铺排故土故事,从中咀嚼乡思乡情;一些作品中方言口语的介入,为诗作别添了生动和活力,是有益的尝试。金音的诗作意境奇丽,别有一番幽美,但涉笔却表现为近乎明快的淡远,使人感动于其举重若轻的艺术表现力。但娣、蓝苓、朱媞等女作家的诗歌创作,也脱却了“闺怨”的色彩、将视野和心灵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且为东北诗坛奉献了从思想题材到艺术成就都可圈可点的作品,如蓝苓的叙事诗,杨絮、但娣诗中的某些苍凉劲健的意象也是女性诗歌中很少出现的,从中不难看出地域文化与社会现实对文学的双重雕塑。总观这一时期的东北新诗可以发现,现实的和唯美的两种倾向交错前行,相对普泛的农耕文化和在异族侵略和掠夺下凸显的乡土的内涵,使得抒写乡土情结的现实主义新诗是其主流和基本方向,同时艺术上的成熟和丰满又有赖于不懈的唯美追求,更具独特性的当是社会历史、现实及文学三重因素在短暂的时空中汇集碰撞,催动东北新诗的超常速生长。
相比于散文、小说,华北诗坛在沦陷初的数年间较为沉寂,但小说、散文多元的创作格局也影响了华北诗坛。沦陷初期的为数甚少的诗作中,由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幼稚模仿和源于剧变了的社会现实的苦闷迷茫,导致了大多数诗风表现为晦涩郁暗,被称为是“看不懂的新诗”,华北文坛对此进行了探讨。40年代初,华北诗歌开始复兴,一批青年诗人率先打破沉寂,出现了以校园诗歌为先声的明朗晓畅的新诗,成就较为突出的有南星、李曼茵、何漫、吴兴华、查显琳等人,随后形成了各以艺术和生活社、《中国文艺》及高校为中心的三大诗人群,构筑了华北沦陷前期诗坛的基本格局。总体说来,华北青年诗人诗作中的意象仍多凄清、悲凉的况味,但诗风有所转变,由晦涩转为清新显豁,同时也在这种技巧的调整中又出现了直白的偏向,于是诗作中抑郁、愁苦的具体内容往往触手可及,过于裸露。有人将这一阶段的诗风总结为“有大地与温室两种相异的气息,有原野的呼喊,也有诗人的吟哦”(注:楚天阔:《三十二年的北方文艺界》,《中国公论》4卷10期。)。 面向大地的呼喊与徘徊斗室的吟哦表现了华北新诗的两大基本取向,前者指向外部世界,种种有关历史、现实社会的问询与求索在此找到了宣泄的渠道;后者指向内心,种种富于个性的人生况味和艺术探索成为湎思的内容。在华北诗坛一派青春风采闪烁的映衬下,刘荣恩“私人藏版”诗的创作颇为醒目,他在沦陷期间创作的近400首诗大多秘而不宣, 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语”,中年人的沉郁、旷达与犀利表现了相对厚重深刻的生命体验,其揉合新诗与古诗的艺术个性探索与后文述及的吴兴华的诗歌创作形成华北诗坛一脉特色鲜明的支流。
华北的沦陷区后期的诗歌创作延续了前期已现端倪的倾向,侧重诗歌形式的多方探索,报刊上刊载的诗作普遍地表现出对诗歌艺术形式如韵律、格式的探求。其中成就最为醒目的是吴兴华。从1937年发表成名作《森林的沉默》时起,吴兴华即表现出对诗歌艺术独特的感受力和创造力。他善于将沧桑的历史和人生融到特定的具体的情境中进行诠释。在理性与感性的双重追索中完成艺术创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化古入今、化洋入中的艺术探索。就前者而言,他善于在超越历史时空的中国古典诗词歌赋领域内寻求现实思想情感的承载体,铺排古今相通的深刻的人生体验,如《刘裕》、《秋日的女皇》、《柳毅和洞庭龙女》等诗作,使得他的作品既有充分的现实感又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他还致力于寻求并融会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诗歌的特点,尝试过十四行体、十一音节体、六音步体等数种西方诗歌样式,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总体看来,他的诗作既传统文化底蕴浓郁,又具有充分的现代文学气息,视野开阔,形式多样,技巧娴熟,是华北沦陷区诗歌中的上乘之作。这种跨越古今中外时空而进行的诗歌形式探索的尝试,无疑要建基于丰厚的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修养和对西方诗歌艺术的相当程度的认知之上,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华北沦陷区文学秉承并得益于相对更为深厚的古典文化的滋养以及相对更为迅捷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是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生长进程中所欠缺的,就新体诗创作而言,尤其如此。由此也不难理解早在华北沦陷初期,诗坛就涌现出大量的长诗,出现了张秀亚的《水上琴声》、毕基初的《幸福的灯》、高深的《奴隶之爱》等一批作品,这些作品有叙事、有抒情,借古讽今,抒情写意,形式上虽未臻成熟,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结构、韵脚、节奏、排列等方面都较为协调。
四、结语
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环境中历史基因和现实因素,特别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借鉴的侧重点的不同,导致了两个沦陷区呈现出迥异的文学风貌。在主题的选择上,东北沦陷区文学,无论小说、散文、诗歌始终贯穿着“描写真实”、“暴露真实”这样一种明朗、坚决的创作走势,或明或暗地流涌着反帝爱国战斗的旋律,并在此基础上作着文学上的艺术追求,使满洲作品整体上流溢着一股雄浑、豪迈、粗犷的关东地域色彩。相较于粗线条的满洲作品,华北沦陷区文学讲究艺术手法上的细腻、入微,追求冲淡雅闲的美学风范,论古道今、谈天说地、品茶饮酒的人生情趣的“小摆设”散文在华北的泛滥正体现了华北沦陷区文学对纯的文学艺术气息的追求,从诚实、青春的校园文艺到有感于东北沦陷区文坛而兴盛的华北乡土文学,这股始终潜行的爱国意识相较于东北,暴露了华北沦陷区文坛与现实和时代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这种差异正体现了两地不同的现实政治重压,其中也联系着华北自身对北平市民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受“五四”以后“京派”创作的影响等因素。
相比于散文、小说,华北诗坛在沦陷初的数年间较为沉寂,但小说、散文多元的创作格局也影响了华北的诗坛,一批有影响的青年诗人显露了创作个性。真诚、朴实的校园诗歌可算是吹进华北沦陷区诗坛的第一阵清风,众多的青年诗人的涌现使华北诗坛的复苏带上一股浓重的青春气息。较有影响的青年诗人有南星、李曼茵、何漫、吴兴华、查显琳等。“诗人的吟哦”包括诗人抒写“自我”,吟唱“斗室”的“沉重的独语”,也包括诗人对诗形式的个性探索。
“沉重的独语”可以代表华北沦陷区现代派诗人的“心灵的咏叹”。同时,“独语”又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表征着诗人向心灵深处追索,向幻想与回忆的世界中沉溺的情感方式与思维方式,并借此营建一个堪与外部世界进行对抗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心城池。与这种“独语”的个体话语方式相关联的,是“现代派”诗作中具有普泛性的哲理化的趋向。借助于这种深思的力度和深度,沦陷区的现代派诗人试图突破由于经历的有限所带来的题材和视野的狭隘,并试图超越温室中的独语者而代之以潜思人性、生命以及历史、现实的哲人的形象。
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环境中历史基因和现实因素两个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两个沦陷区呈现出迥异的文学风貌。华北无论小说、散文均充满了冲淡雅闲的作风,细腻的描绘、入微的刻画,绝非以粗线条见长的满洲作品所可以比拟的。同样,满洲作品的雄浑豪迈,在华北方面却很难找到的。由于各沦陷区文化背景的差异,其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借鉴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异。东北沦陷区文学始终把“描写真实”、“暴露真实”当作冲破“笼罩文坛”的“粉饰堆砌的氛围”的主要课题来实践,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东北皆显示出了鲜明的关东地域色彩,以一种明朗、坚决的文学走势,或明或暗地流涌着东北沦陷地区这个特写历史时空中“特定文学”的主旋律,并在此基础上作着文学上的艺术探索。华北沦陷区文学以诚实、执着并潜行着爱国意识的校园文艺开始其复苏,以寓有民族意识的“乡土文学”迎来其中兴,并始终注重于文学“自身的觉醒”,这种对纯文学艺术气息的追求,使华北文学相较于东北,发生与现实和时代有一定程度的疏离。这些固然同现实环境的政治重压下,作者不得不寻求自我保护之计有关,也联系着北平市民文化的传统,“五四”以后“京派”创作的影响等因素。这些论古道今、谈天说地、品茶饮酒的人生情趣的“小摆设”散文,在华北最为泛滥,这不仅同“北平文化”的士大夫趣味吻合,而且同日伪当局企图实现心理征服的现实有关。
标签:文学论文; 乡土文学论文; 散文论文; 东北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作家论文; 张秀亚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