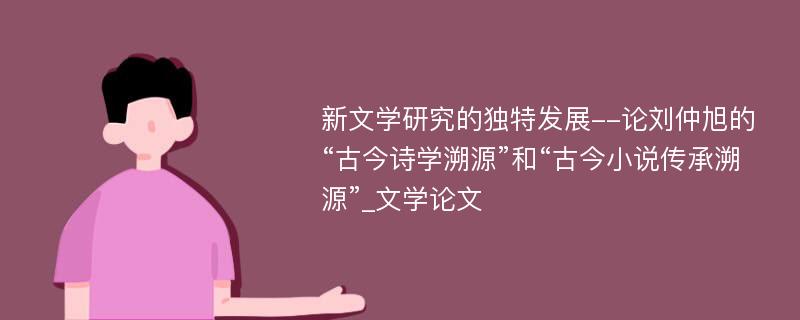
新文学研究的独特拓进——评刘中顼的《古今诗歌传承溯探》和《古今小说传承溯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今论文,新文学论文,诗歌论文,独特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新文学自“五四”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新文学主要是学习外国文学的经验创造与发展起来的。刘中顼先生在《古今诗歌传承溯探》中谈到:“一些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由欧美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移植过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也曾认为:‘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典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朱自清先生在谈到新诗的初创时曾说:‘小说、散文、戏剧的语言虽然需要创造,却还有些旧白话文,多少可以借鉴;只有诗的语言得整个儿从头创造起来。’”40年代胡风则认为“五四”时代的新文学,主要来自外国文学的影响,“和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划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对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理解》)。解放后,欧外鸥、傅东华等人也曾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革命,就是越革越没有民族风格”(参见《古今诗歌传承溯探》第8页引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认识依然存在。如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我国的古典文学之间是“断裂”的,他们认为“戊戌变法”至“五四”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古代中国文学全面的深刻的‘断裂’开始了”,“这是一次艰难而又漫长的(将近历时五分之一个世纪)的‘阵痛’。一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最终完成了这一‘断裂’”(《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任洪渊在《当代诗潮:对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古典诗学的双重超越》中也说:“当中国诗人与自己的古典传统断裂,目不转睛地盯着西方浪漫派和现代派的时候,从西方,例如庞德的意象派却正神往于中国的古典诗学,甚至把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他们现代主义的一个传统。”(《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此外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理论完全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在现代中国已经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如陈洪、沈立岩说:“我们曾经拥有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完整而统一的传统,拥有自己的话题、术语和言说方式。遗憾的是,这个传统在‘五四’的反传统浪潮中断裂了,失落了,而且溺而不返,从此我们就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失语’的状态……”(《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曹顺庆、李思屈说:“意识到中国文学理论界处于传统中断、创造乏力的困难局面中,应该说是中国学术界认真地面对现实、在国际文化背景下清醒地反思自己的一个开始。”(《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因为这样,于是在文学理论界与文学创作界,关于新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的“断裂论”、“移植论”、“失语论”等观点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新文学的传统问题本来是一个应当大力研究,深入探清其历史源流的大问题,但长期未得到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理论界的重视。近20多年来,我们研究中国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各种“关系”的文章连篇累牍,刊物与著作济济众多。这种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也带来了某些负作用,好像中国新文学完全是“外国母亲”的产儿,至少也是与外国文学血脉相联的“近亲”,与中国的“老祖宗”倒没有血缘关系。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理论界轻忽了一个本应重视,然而至今仍未引起充分重视的问题——中国新文学躯体中汩汩流淌的血液,究竟脉归何处?中国古今文学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当然,对于中国新文学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一般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或多或少也是承认的,并且有些学者也在他们的研究中有所涉及。然而集中的、系统的、比较深入地论述中国新文学受到了我国古典文学哪些影响;从文学理论到文学创作,中国新文学又是如何具体地继承、发展和超越了古典文学的传统,这样的系统性研究实在太少。刘中顼先生却在这一被忽视的冷境中长期不懈地探讨,近年来连续出版了他计划写作的“古今文学传承研究”系列中的头两部著作——《古今诗歌传承溯探》《古今小说传承溯探》。他这些可喜的研究成果和这种不趋潮流的探讨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在著作中对古今文学发展的传承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溯探,充分论述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对现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思想和艺术产生的深刻影响,后者对前者在诸多方面的充分继承与突出发展。作者以客观科学的研究雄辩地说明了中国新文学之根源,主要是深植于中国文学传统的沃土之中,而非主要继承西方洋邦的炫目衣钵。他的研究成果,在回答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方面作出了值得重视的成绩。正因为这样,我才深觉这两本研究著作在新文学研究方面的独特拓进及其所具有特殊的意义。
《古今诗歌传承溯探》和《古今小说传承溯探》的特色,还在其研究的角度、研究的全面、细致、深入等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这两本著作有着独特的研究角度。它们不像一般的文学研究著作那样,或研究新文学,或研究古典文学;而是在时间的“纵轴”上古今贯通,在研究领域的“横轴”上从文学理论、文学题材、文学创作艺术、作家作品,全面地进行古今文学发展流脉的溯探。这是一种尚不多见的研究角度。正是这种研究角度的独特性,构成了这两部著作一种与众不同的学术个性与价值。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从宏观到微观来研究我国古今诗歌和小说在创作发展中各方面的历史传承关系的,宏观上要突出研究古今诗歌、古今小说发展中创作艺术的普遍规律性,微观上要研究古今诗人、小说家艺术实践中丰富多采的鲜明个性。这样复杂的问题要分别在两本二十几万、三十多万字的著作中,进行较为全面的传承关系的描述与论说,并不容易处理。但是,由于作者在每部著作的第一章中,分别系统的论述了我国古今诗歌理论和古今小说理论的传承关系,并强调说明了这些基本理论对我国古今诗歌、小说创作艺术实践的重大指导意义,从而也就为后面展开关于古今诗歌和小说其它方面具象多姿的艺术实践的论述,提供了“万变不离其宗”的民族性在文学发展中古今贯通的基本依据。这正如武汉大学的陈美兰教授在《古今诗歌传承溯探·序》中指出的,著作的第一章“为全书的论述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石”。后面几章关于诗歌和小说的题材、艺术、作家风格等传承的研究又为前面的理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具象说明。二者紧密配合,相得益彰。
其次,刘中顼先生在这两本著作中,对我国新诗歌与新小说所受的古典诗歌与小说的深刻影响,前者对后者的继承、发展与突破的传承关系进行了流脉分明的描述。例如《古今诗歌传承溯探》的第一章第三节中对诗歌的“赋比兴”理论在我国古今诗歌理论中的传承就作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述。书中说:“‘赋比兴’说是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理论中最有特色,影响最深远的重要理论之一。自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前提出‘赋比兴’说以来,这一诗歌艺术理论不仅非常实际地指导了我国古往今来的诗歌创作;而且也成为我国诗歌理论界品评诗歌高下的重要艺术标准,而为历代诗歌理论家所继承。”接着作者分列了自“赋比兴”理论产生之后,从东汉郑玄、晋代挚虞、南朝刘勰、钟嵘,经唐宋元明清历代理论家的发展、丰富,一直到现当代毛泽东、刘大白、臧克家、郭小川等,都对诗歌的赋比兴理论有着充分的继承与精深的现代阐释。同时,刘中顼先生在论述赋比兴理论的古今继承中,还突出地说明了现当代诗人对我国古代诗歌艺术中逐渐消落的“赋”的传统来了一次大发扬,创作出了许多长达数千行、上万行乃至几万行的叙事诗,以叙事诗的辉煌特立于古代诗歌之上。这些论述,生动具体地阐明了我国诗学理论中赋比兴理论的历史传承性和赋比兴艺术在现当代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发展。
第三,这两部著作在研究的深入细致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特色。作者研究诗歌与小说的古今传承,不是仅仅从表象出发,去寻找现当代新诗和小说与古典诗歌和小说表象方面的某些“相同”或“相似”,而是着重深入从古今诗歌与小说创作中所贯通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与心理特点,创作与欣赏的民族思维习惯,诗歌与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种种艺术追求等深层次的方面,对中国诗歌和小说发展中古今传承的关系进行细致的论证。如书中的对古今诗歌创作中对意境、诗句、字词的“炼冶”追求,古今诗人向民歌学习的心理情结,古今诗歌创作中的画境追求,古今诗人崇尚田园、山水自然的创作情结;古今小说家对小说通俗化的重视与追求,对小说创作“传奇”性的强烈兴趣与自觉追求,对历史题材、家庭题材情有独钟的热爱,在小说情节艺术方面古今作家一脉相承的讲究“巧合之妙”、“曲折之美”、“团圆之趣”的审美心理等等。作者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艺术的宝库中,将最具有民族特色的重要理论和艺术方法择取出来,深入阐明这些理论和艺术方法在中国古今诗歌和小说发展中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和强劲的历史穿透力,它们对于型铸中国古今诗歌和小说“中华面貌”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书中重点论述的这些理论,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最有特色、最能充分显示“中华”特征的理论,同时也是现当代文学理论家继承最充分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古今一贯地指导了我国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同时它们也真正是决定我国文学民族特征最有影响力的因素。著者的这种择取与论述,不仅表现了高明的识见,也更有力地论证了古典文学理论和创作艺术方法,在现当代诗歌和小说创作中的历史传承性。作者对这种“历史传承”的描述,充分地说明了古今文学发展中这种内在的、深层次的传承关系。这样的论证不仅使这两本著作的论述具有了更强的科学性,同时也具有了更大的说服力。
当然,这两本著作和任何著作一样,也有它们的不足。其中对某些方面的传承关系的描述还不够清晰,某些论述不够深入,有些举例还不够精确、典型。这些都有待于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努力。尽管如此,刘中顼先生的《古今诗歌传承溯探》《古今小说传承溯探》在研究我国新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的关系方面,其独特的价值是明显的,不失为两部独辟蹊径、很有新意的学术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