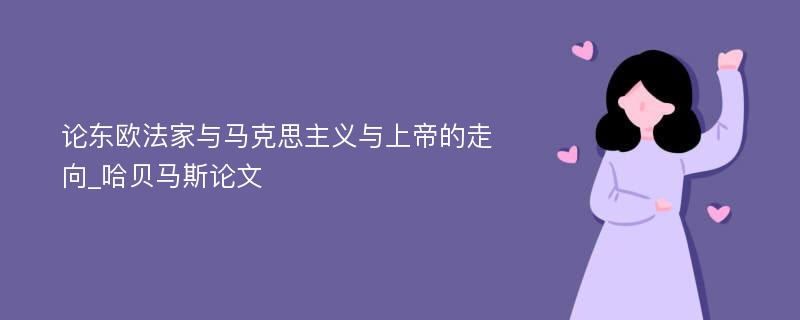
论东欧的法团主义与马克思主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马克思论文,走向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8)04-0015-06
什么是法团主义(corporatism)? Philippe C.Schmitter“把法团主义看作是这样一个体系,它是利益和(或)态度(attitude)的表达,是有组织地联结市民社会利益和政府决定性结构的、独特的或理想的制度模式。”① 法团主义强调政府、劳动(工会)、资本(雇主联盟)三方的利益协调与共谋,是一种新的市民社会理论。它试图用一种结构主义的架构取消阶级政治,用劳动和资本的共同利益取消劳动与资本的对抗。这种思想对于正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东中欧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劳动与资本的共谋意味着什么?面对这一新的社会现象,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了何处?
一、法团主义在东欧的出场
作为一种新的市民社会理论,法团主义是当代东欧的产物。
根据Ivelin Sardamov的研究,东欧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统治之下,市民社会表现为对抗极权主义的政府统治。“在早期理论家的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的’和‘经济的’社会是不可分割的。尽管‘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试图拓殖到所有的政治领域和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② 这种在与极权主义政府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得到了西方社会的同情。这种状况持续到1989年的剧变。第二阶段,东欧剧变后的最初几年,市民社会范畴得到了极大的扩大,它被看作是获得民主的良方,此阶段甚至出现了“全球市民社会”的伟大畅想。“20世纪90年代早期,‘市民社会’经常被等同于自愿的协会生活。”③ 这种理论得到Robert Putnam的宣扬。“他(Robert Putnam—引者注)认为,由积极的协会生活创造出来的相互信任的‘社会资本’和团结很可能具有额外的效果,即不仅促进民主制度的发展,而且润滑商业关系并因此刺激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应,一些学者甚至预言了新的‘全球市民社会’的到来,它能够扩大市民影响重要的政府事务的范围。尽管在几年之内,多数学者以及西方政府和制度将‘市民社会’的概念实际上压缩为追求具体事务的非政府组织。”④这段话已经包含了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三个阶段,即经过剧变的最初几年之后,市民社会范畴被压缩为追求解决具体事务的非政府组织。而法团主义正是在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被提出来的。Terry Cox也指出,“或许,对后共产主义的东中欧地区国家-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性理解的最大胆尝试就是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种新的法团主义就已经在这一地区发展。这一方法强调正式的组织;通过这些组织,政府与有组织的利益团体进行协商。”⑤
那么,法团主义的具体功能何在?Dorothee Bohle和Bela Greskovits在《新自由主义、嵌入式自由主义和新法团主义:中东欧国家通往跨国资本主义之路》中提出了构成法团主义参照系的四个因素,即市场化、工业转型、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和宏观经济稳定,这其实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既要追求经济的发展与安全,也要追求社会福利的提高。通过分析,Bohle和 Bela Greskovits认为,在东中欧地区,只有实行法团主义的斯洛文尼亚“取得了平衡各种因素的。胜利。竞争性工业和较好的社会指标的出现并没有以失去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为代价”⑥,斯洛文尼亚是“唯一在商业与劳动,以及在社会福利、工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方面都比较好地实现制度化的国家”⑦
斯洛文尼亚的例子表明,法团主义在东欧的出现与东欧学术界和政界精英渴望通过制度化的机制解决剧变后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
二、法团主义的体现及其特征
在东欧,法团主义具体表现为一种三方机制(tripartism)。
三方机制即政府、劳动和资本的三方合作关系,其中,劳动和资本作为市民社会一方与政府达成互动。后共产主义的东中欧国家均建立起了三方机制的组织形式。“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吸收了这一方法:在匈牙利,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的最后几年,建立了‘国家利益协调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rest Reconciliation Council),随后,在1990年又成立了‘利益协调委员会’(the Interest Reconciliation Council);在捷克斯洛伐克,1990年在联邦和共和国的层面上成立了‘社会经济协商委员会’ (Council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Agreement),联邦破裂之后,两个国家各自保留了这一委员会;在波兰,1994年成立了‘社会经济事务三方委员会’ (the Tripartite Commission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斯洛文尼亚则也于1994年成立了‘经济社会委员会’(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在每一个事例中,这些委员会均由三“方”组成:工会、雇主组织和政府代表。”⑧ 它们合作的方式就是一方面政府向重要的社会利益团体进行咨询;另一方面为社会团体在议会通过立法之前影响政策制定者提供机会。
在Terry Cox看来,有的学者,例如:Elena Iankova肯定三方机制的作用,认为它巩固了民主,并且使市民社会获得了更多的参与社会决策的机会和权利,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三方机制只是勾画出了一副虚假的法团主义幻象。例如, David Ost认为,三方机制只是政府的一种策略:通过三方机制,政府可以获得以下好处:一是讨好欧盟,给欧盟留下重视公共讨论平台的良好印象;二是部分地推卸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有助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和平。0st认为,工会的作用只是息事宁人,在劳动边缘化和社会福利下降的情况下,安抚社会的反抗因素。Bela Greskovits也看到,政府接受三方委员会的模式,只是为了平息转型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Greskovits提出可靠的论证,即在决定建立起工会、雇主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政策协商时,后共产主义的政治精英却同时能够排斥其他利益团体的激进要求发挥有效的影响。……在工会和雇主协会能够作为协商的可能伙伴的同时,事实上,他们在动员大众抗议方面却相对软弱。20世纪90年代早期,雇主协会处于建立的过程中,需要政府的有力支持来组建团体和吸收成员。同时,当工会经历大量草根成员(grassroots membership)的流失时,它也感受到了日益增长的脆弱性。这两个组织因此都必须建立起与政府的合作,并且在政策性事务上不想冒险站在对抗性的立场上。”⑨
不论学者如何对待三方机制,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在东欧实现真正的法团主义,并由此提高市民社会对政府的影响力。Terry Cox也认为,虽然三方机制未能完善地处理市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但是,它仍然是一种新型的、正在成长的新的法团主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东中欧地区的法团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希望通过法团主义来提高市民社会对政府的影响力,并进而将市民社会与法团主义的兴起看作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其二,将三方机制看作是通往法团主义的途径,或者说,三方机制就是法团主义形成与完善的中介。其三,在三方机制中,将劳动和资本看作是与政府相对的“一方”,并没有进一步揭示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核心矛盾和区别。其四,“三方”并不能包含除政府以外的所有的社会组织或团体,或者说,“三方”中的“劳动”一方已经发生了分化。正如Terry Cox在文章中引用 Greskovits的观点所指出的,工会本身也大量地失去了它的草根成员。其原因应该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当工会受制于政府时,它很难真正地代表其草根成员的利益;另一方面,草根成员本身作为失去话语权的群体,他们也失去了加入工会的积极性和热情。
由此可见,三方机制或者说法团主义暗含着这样两个政治预设:其一,对市民社会的重视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法团主义渴望通过市民社会的兴起来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其二,取消阶级政治,通过将劳动与资本划归为与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市民社会一方,从而模糊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差异。
三、市民社会理论:从马克思经由葛兰西到哈贝马斯
市民社会理论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课题之一。从马克思到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从来都没有排斥阶级理论,尽管阶级由显现走向了隐蔽。因此,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葛兰西以及哈贝马斯那里都不是一种法团主义,不是劳动与资本为了某一共同利益所达成的共谋。
在马克思那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关系;市民社会的出现意味着经济人的形成与发展。市民社会包括劳动与资本两个环节。在古代社会,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并未在哲学上被提出来,人主要就是政治人。经济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黑格尔第一次系统地将市民社会与国家作了划分,但是,黑格尔强调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真理,要求市民社会服从国家,为王权服务,这样一来,作为经济人的个体成了国家的奴仆。马克思肯定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的做法,但是,他却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并非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前提,国家应该服从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应该为新兴阶级服务。这里的新兴阶级是指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与封建主义的抗争中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力,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他的掘墓人,那就是无产阶级。所以,市民社会的兴起同时就伴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萌芽。
在马克思之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以文化革命的方式提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夺取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胜利的唯一途径;领导权就是指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统治阶级不仅要运用统治(政权)统治国家,而且要用文化的意识形态掌握市民社会,使被统治者和其他集团能认可统治集团的文化体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领导权具有独立性,既可为统治集团也能为非统治集团把握。若统治集团无法把握领导权,只有以国家机器实施强权,这样便脱离了群众,出现了权威危机。同样,如果非统治集团能掌握领导权,进而便可获取统治权。所以,是否拥有领导权是判断一个社会集团是否有广泛社会基础,所选择的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由此可见,葛兰西所理解的市民社会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中介和途径。
哈贝马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这突出体现在他的公共领域理论中。哈贝马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具有虚构性。“公共领域由于实际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因而其虚构也就变得比较容易:因为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从一开始就能使政治公共领域的客观功能与其从文学公共领域中获得的自我理解一致起来,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⑩ 这里包含着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两个层面。政治解放在封建社会是指资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利的解放,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解放则不再是资产阶级的解放,而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但是,人的解放则始终包含着资产阶级的解放。因此,资产阶级便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资本家的人,即作为“物主”的人,二是作为“人”的人。“作为‘物主’的公众和作为‘人’的公众的统一过程集中说明了资产阶级私人的社会地位本来就是具有财产和教育双重特征。”(11) 并且,“只要拥有一定的财产和受过良好的教育就能占领讨论对象的市场。”(12)
于是,公共领域暗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公共领域的主体是谁?哈贝马斯已经指出,主体需要具有两方面的能力,即财产和教育。因此,在这层意义上,公共领域只属于资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在这两方面能力的获得上无疑不具有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优势。由此可见,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种幻象。
从马克思经过葛兰西到哈贝马斯,他们的市民社会理论发生着变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由显现到隐蔽,革命的途径由激烈到温和,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却从来没有被取消,不同的只是对待二者矛盾的方式: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解放了经济人,同时又将经济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对立作为主要思考对象。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将经济人的斗争转化到了文化领域。从经济领域到文化领域,既是斗争策略的转变,同时也说明了,面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由经济斗争直接转换到政治革命不具有现实性,运动战必须转化为“阵地战”。到了哈贝马斯那里,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则更具有隐蔽性,二者的对立在公共领域的虚假性中得以显现。
四、东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转型
东欧马克思主义比哈贝马斯走得更远。
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主义制度下,市民社会理论表现为对极权政府的反抗。在这一阶段,市民社会理论伴随着对“阶级”范畴的新理解。第二阶段是苏东剧变之后到当前。这一阶段的东欧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或者转向了后现代理论,离开了对市民社会的思考,也谈不上对法团主义的积极回应。在我看来,这种忽视和缺乏回应正体现了当代东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阿拉托(Andrew Arato)就指出东欧马克思主义具有一个后马克思主义阶段,而判断这一“后”马克思主义阶段的标准就在于: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思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在解决国家—市民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异化问题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不可避免的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式,即反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民主统一。相反,他们寻求保护或重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中介(Vajida):法规、二元化、公共性。”(13) 但是,阿拉托同时也指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解决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时忽视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在凸显市民社会的重要性时却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市民社会的批判。“从哲学层面而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马克思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方式,无论这一事实如何得到确认,也未能澄清他们与黑格尔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市民社会的批判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这一批判只是简单地被抛弃(Kolakowski),那么,这些理论家就冒着近似为资本主义社会做辩护的危险。如果这一批判至少部分地被接受(Vajda),那么,这些理论家仍然必须为一种可能的市民社会规划——它不仅从极权主义国家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从它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中走出来——作出概念化的理论说明,这些问题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在1980—1981年波兰社会运动中已经凸显出来,但甚至此时的理论反思也没有跟上现实的实践。”(14)
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在东欧马克思主义最具影响力的阶段,他们的市民社会理论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缺陷:一方面,他们渴望通过重新发扬市民社会的作用来抵制极权主义政府的压制,渴望形成一种民主的社会模式;另一方面,他们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同时,也试图脱离马克思思想本身。但是,脱离的结果却是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无批判态度,即使具有一定的批判意识,却也无法建立起一种新的市民社会模式。具体而言,东欧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缺陷与他们对“阶级”范畴的新理解息息相关。
东欧后马克思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设,即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相应地,他们也反对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存的社会,认为这样的社会只是乌托邦。“希望现代社会能被缩减为只剩下两个阶级的社会整体,这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这也是一个相当消极的乌托邦。……因为它将会取消围绕在两个阶级周围的自由的社会空间,由此,两个开放的阶级就变成了两个封闭的阶级。”(15) 离开了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东欧马克思主义是无法建构起制度化的、理想的市民社会模式的,因为,这两个阶级构成了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研究思路却为后来东欧马克思主义走向非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并最终抛弃对市民社会的思考,抛弃对法团主义的回应埋下了伏笔。
肯利迪(Michael D.Kennedy)和格茨(Naomi Galtz)在1996年曾经撰文写道:“在今天东欧知识界的讨论中,很难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验的或积极的指导,或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仍然存活的理论传统。有时候东欧学者讨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为了说明它的意识形态僵化和顽固性(例如Mokrzycki1992,Zybertowicz 1994)。更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被忽视了。”(16) 毫无疑问,肯利迪和格茨为我们指出了一种存在于剧变后的东欧的现象。例如,作为东欧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赫勒(Agnes Heller)从20世纪末到今天的关注点转向了后现代。2007年6月,当赫勒来复旦大学做报告时,重申了她的后现代思想。她反复强调“去总体化”,似乎在做脱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最后努力。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总体化,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并且预设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总体远景。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新变化只是说明,“东欧的思想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或者因为他们自身并未为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17)
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构成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阶级范畴在市民社会理论中越来越淡出的时候,东欧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走向了背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道路,并且无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建构起理想的市民社会模式。面对法团主义这一新的市民社会理论,他们也无力作出回应。
注释:
① Philippe C.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36,No.1,The New Corporatism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Iberian World ( Jan.,1974) ,p.86.
② Ivelin Sardamov:‘ Civil Society’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tic Assistance,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ume 40,Issue 3,Jun 2005,p.381.
③ 同上,p.382.
④ 同上,p.382.
⑤ Terry Cox:Democratization and State - Society Relations in East Central Europe:The Case of Hungary,in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01.23,No.2,June 2007,p.277.
⑥ Dorothee Bohle & Bela Greskovits:Neoliberalism,embedded neoliberalism and neocorporatism :Towards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in Central - Eastern Europe 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 30,No. 3,May 2007,p.462.
⑦ 同上,p.448.
⑧ Terry Cox:Democratization and State - Society Relations in East Central Europe:The Case of Hungary,in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23,No.2,June 2007,p.277.
⑨ 同上,p.280-281.
⑩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0页。
(1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12) 同上,第42页。
(13) Tom Bottomore,Laurence Harris,V.G.Kiernan,Ralph Miliband (ed.),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Oxford: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1983,P.319.
(14) Tom Bottomore,Laurence Harris,V.G.Kiernan,Ralph Miliband (ed.),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Oxford: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1953,P.319-320.
(15) Ferenc Feher ,Agnes Heller:Eastern Left,Western Left,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p.214-215.
(16) Michael D.Kennedy,Naomi Galtz:From Marxism to Postcommunism:Socialist Desires and East European Rejections,in Annu.Rev.Sociol.1996,22,P.448.
(17) 同上,P.449.
标签:哈贝马斯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公共领域论文; 社会资本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