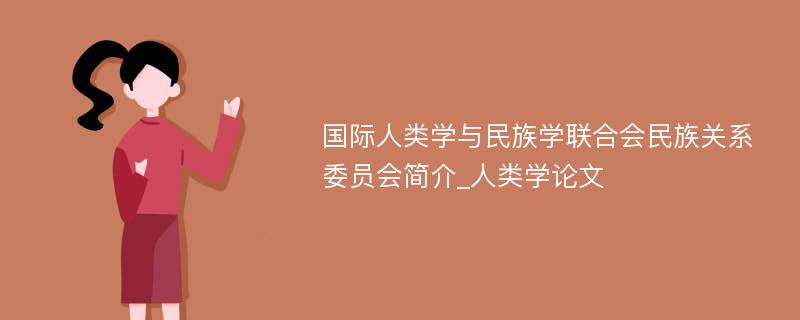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族群关系委员会简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人类学论文,族群论文,联合会论文,委员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8179(2007)06—0080—03
一、委员会简史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族群性一直在民族分离运动、公民自由抗争及群体冲突中日益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因此,对于族群关系的分析已逐步成为那些感兴趣于“直接影响世界和平与基本人权保护的进程”的社会科学家的一个主要关注事项。
在1999年墨西哥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ICAES)上,首次召开了一个以族群性为主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与会的学者们强烈地感到,为了凸显对于族群性的人类学研究的日渐兴盛,很有必要组建一个族群关系委员会(COER)。这一计划在1988年的萨格勒布ICAES上初具轮廓。到了墨西哥城会议之时,一个组织委员会已然形成,并敲定了国际支持团队的人选。此后,组委会主席向IUAES执委会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新委员会组建建议书”。在1995年佛罗伦萨举行的中期会议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COER的成立。这一计划的组织者E.L.(Liza)Cerroni-Long被委任为主席,最初的组委会中的一些成员则组成了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他们分别代表了广泛的地理区域(非洲的Berhane-Selassie教授、美洲的Barretto与Dossa教授、亚洲的Choi与Danda教授、欧洲的Kielstra教授)。在委员会的5年开创期中,这一群体对委员会组织的活动贡献良多,并扩展为日益壮大的地区代表团队,此后其成员构成了COER的编辑集体。
最初,委员会主席自其所属的学术机构(东密歇根大学)获得的支持以及由IUAES提供的启动资金,使得委员会能够出版与发行两份年度业务通讯,名为“COER报告”。此后,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元部获得的一笔小额资金则被用于对世界十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度、俄罗斯、希腊、以色列、尼日利亚、阿根廷、加勒比地区及加拿大等地)的多元文化教育的调查报告的编纂。这一项目的部分参与者在1998年于威廉斯堡召开的第十四届ICAES上提交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的报告由委员会主席编纂成为一个题为“人类学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角色”的综合性的项目报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发行。然后在2001年,委员会自意大利中央文化研究所(委员会主席也是该机构的成员)获得另一笔小额资助,使得委员会能够成立COER出版机构,并出版用于教学与培训的一系列概念性初级读本的“COER蓝图”的第一种出版物《多样性问题:人类学视角》。题为《种族与族群性》的第二卷也正在准备之中。
2000年时,COER通过开设网站的方式庆祝其成立五周年。通过网络主管Adrienne Haywood女士的卓有成效的工作,COER的网站(www.emich.edu/coer)在当年年底设立,其更新网页包含了最新的业务通讯。网站的设立使网上出版得以实现并扩大了影响范围,由委员会主办的名为《族群文化》的电子杂志的第一期已定于2007年初出版。
除了在常规的由IUAES主办的会议上组织各种小组讨论会与专题会议以外,COER还自己组织了一个国际座谈会项目,2006年7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了第一次会议,主题为“关于族群性:理论、实践与政策”,座谈会的成果将在第一期网络杂志上出版。
COER的标志,及用于由COER主持出版的或电子形式的书刊的徽标,是由挑选出的几个变形字体构成的,以凸显与族群性有关的议题的界定与分析的困难性。
二、族群研究的国际对话
在西方社会,社会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衍生于由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所催生的文化接触的经验,以及将跨文化差异与假想的主观界定的“文明阶梯”中的不同进程相联系的进化论知识范式。尽管这种开端相当不利,但这一相对年轻的学科一路发展,并通过对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社会组织分析概念的引进与理论提炼,通过促进丰富的民族志资料的收集,从而对我们了解人类行为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无论人们将社会文化人类学视为比较社会学还是文化科学,毫无疑问的是,对一个以人类学研究为目标的学科的终极价值的检验是其全球相关性。倘若认真地考虑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就必须承认我们的文化背景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过程,这就意味着任何知识上的努力,包括人类学的理论概括或民族志描述,会受到我们的特定文化感知的影响。因此,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科实践应当参与到一种持续不断的国际(跨结构)对话之中。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是唯一的旨在促进世界范围的人类学知识交流的机构。IUAES各委员会则将其国际主义的抱负付诸实施。因此,她们的使命相当微妙:尽可能广泛的为具有共同的特定学科兴趣的学者提供互动的渠道,同时也包容那些时常在国家学术界内部出现的知识分歧。要完成这种充满挑战的任务对于我们学科卷入的特定领域显得特别重要,关于族群性的研究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三、族群研究的使命
对于族群的人类学研究道路坎坷起伏。直到20世纪中期,这一主题鲜受关注,涉及的一般都是关于同化/涵化及现代化的研究。直到1960年代后期,人类学方法受到心理学的强烈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族群性被总体地加以讨论,其中心议题是“认同”,在探讨“涵化”过程及这一过程在少数民族移民中可能产生的精神紧张时更是如此。换而言之,其模式就是视族群性为一主要具有心理学表现的过渡性现象。因而,它与那种将文化视为一个整合的整体并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观点紧密相连。从这一观点来看,族群认同被视为在“由移民或侵略所引起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少数民族群体被强势文化所涵化”等的文化接触的情形下由对于“原始的忠诚”的不稳定的依附衍生而来。
然而,1960年代,殖民地放放运动达到了高潮,不少多民族社会中的少数民族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也不断高涨。其结果是族群性成为众多关注的焦点并吸引了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因此,这一年代的后期,许多人类学家转向了一种借自政治科学的模型,将族群性视为一种“情境化的”策略,旨在处理被认为有文化差异的群体间的关系。学术界一般将1969年视为理论思潮的转折点,这一年出版了由 Fredrik Barth主编的《族群与边界》这一战后最具影响的人类学著作,该著作最为清楚地说明了“情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人类学家如Edmund Leach的早期著作中已经提及了这一观点,但世界范围的政治分离趋势为其快速的建立提供了适宜的历史环境。
广义来讲,情境主义模式仍颇具影响,但由于两方面的原因,近年来它已经历了微妙的转变。首先,与族群有关的政治冲突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对跨文化多样性的社会——经济关联的注意。其次,跨国界的移民潮(它们常常由特定地区的族群冲突引起,并被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所加剧)的稳定增长使得许多人类学家确信,那种对于文化的传统学科定义已经失去了有效性。就如Barth本人听说的:“我们现存认识到,全球文化的实际变化是连续的,它并没有截然分割为独立的、整合的整体。在我们选定做为观察对象的任一人群中,我们也能发现它处在变动之中,它充满矛盾,亦非前后一致,它在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当中也有差别”(Fredrik Barth.Enduring and Emerging Issues in the A nalysis of Ethnicity.in The Anthropology of Ethnicity,H.Vermeulen and C.Govers eds.,Amsterdam:Het Spin huis,1994)。
视文化为社会分裂与纷争的不稳定的、不连贯的场所的观点主要由活跃在世界资本主义扩散之核心的欧洲与北美的学者们提出,这一事实使得其他人类学家对理论建构的文化与历史特定性加以关注。确实,这种“新历史主义”或许是人类学中最为有趣的一种当代潮流以及一种对后现代主义的有效应对。
无论人们是否视后现代社会科学为一种深受消费资本主义影响的知识范式的产物,就如同以前的进化主义范式受到工业资本主义影响的那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将族群性的文化成分琐碎化具有深远的影响。蕴涵其中的是对于做为西方殖民主义受害者的原著人群的权利的不尊重,这些人群的自我确认的渴望特别地植根于文化自主的要求。关于族群性的理论观点与文化的理论模式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并不可避免地与对于诸如国家建构与地区分离主义之类的变动无常的政治议题的应对有关。这使得“确保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对话具有真正的多元文化性与国际性”具有特别的紧迫性。
四、族群议题的全球影响
自族群关系委员会的创始委员进行初次探讨以来,我们都强调了明确的研究焦点的至关重要性。有几个主题被视为关注中心,因而应当被分别阐明,以便为我们提供总体的研究框架。这些相关的议题包括:
族群性的内在与外在表征;原著人群的自决;族群冲突的地域背景;族群进化与族群发展;民族分离主义与国家建构;语言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族群关系的宗教维度;族群流散与跨国主义;族群性与移民政策;族群性的政治维度;族群多样性与法律;多族群社会中的教育;族群认同与多元效忠;族群性的商品化;族群性研究中的种族概念;文化霸权与族群歧视;族群关系中的表现型及表达型因素;社会分层中性别与族群因素的相互作用;NGO及国际组织在应对族群性中的角色。
我们也认识到对研究中用到的概念加以澄清仍是一大优先事项。诸如族群进化或族群发展之类的术语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具有不同的含义,而且事实上甚至像文化、族群性这样的基础概念在人类学界也没有获得一致的理解。
然而,为了委员会各种活动的目的,有必要至少提出一个关于我们的核心研究主题的工作定义。因此,COER的成员同意将“族群”界定为“任何视其为与其他在社会政治层面密切相关的群体具有文化区别的社群”。这些社群可大可小,可为强势的或边缘性的;它们可能存在于单一国家之内,也可能跨越多个国家;它们间的关系可能是对称或非对称的、和谐或冲突的、合作或剥削的。我们也认识到族群认同是社会性建构的,因此,群体成员的辨别因素可能因时而变或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感知,个人可能在不同的时空选择认同不同的社群,他们特定的群体认同也可能被局外人及局内人所接受或辩驳。
最后,由于COER并没有提出任何关于族群关系研究的特定理论立场,我们也认识到社会文化背景及政治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影响对族群性的界定及族群研究的实践。因此,委员会在协调关于族群关系互动信息的交流的同时,也鼓励对收集、分析及解释这些信息所运用的认识论框架进行自我反省式的评估。
五、委员会的目标
委员会的成立,旨在探讨这样一种议题。它在这个世界上日益重要,但人类学家对他的理论思考却参差不齐并往往针锋相对。然而,COER吸引了国际上的广泛参与这一事实表明,一般意义上的族群性议题及特定意义上的族群关系深深地吸引着学科的实践者,并往往成为研究的中心事项。COER即着手通过“促进关于族群关系的信息交流与研究合作以及为这一领域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的发表与传播创造机会”来协调这方面的努力。
COER组织的研讨会所选的初始议题“民族分离主义”、“种族与族群性”、“多元文化教育”仍是族群关系研究中的核心领域。第一届COER国际研讨会即以理论、实践与政策的关系为主题,探讨了如何“在避免使我们的分析政治化的同时将人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的两难问题。COER所倡导的合作的另一个主题聚焦于族群性研究中所用术语的理论澄清,这将为我们提供编纂一种新型的术语表的机会。该表将根据概念加以组织,这将大大有利于族群关系领域的人类学研究的国际化。这一术语表以及关于种族与族群性的第二本小册子(属于“COER蓝图”系列)的出版,构成了我们准备在近期完成的主要出版计划。此外,我们也将保持业务通讯及我会期刊的电子出版的正常,并积极参加IUAES主办的各种会议。COER将在昆明召开的2008年ICAES上组织的各种专题讨论会的总的主题是“表述族群性”,旨在唤起对“澄清我们的理论与方法论观点,同时强调视角在界定与分析族群关系中的重要角色”的需要的注意。
尽管历史主义的当代影响是一个受欢迎的针对过渡后现代主义的学科矫正物,它也让人们感到,如果研究者局限于探讨太过具体化的个案研究,将难以从族群性研究中产生对人类学理论有贡献的成果。但那些聚焦于族群现象以更好地理解其如何与文化相联系,以及希望通过这种理解发展出更好的人类行为理论的学者们的努力,事实上驳斥了这种观点。我们学科最近已遭受了一种关于其有效性的彻底的内部批评,这包括对其产生的产品——民族志及其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参与观察与访谈的诟病。当将人类学方法应用于社会边缘人群——其族群性往往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研究时,剥削的议题就出现在前台。这反过来让人们注意到在我们与所研究的社群的往来中,很有必要建立起一种更为平衡的交互关系。
发展一种不是聚焦于族群认同“怎样”及“为何”被运用,而是努力代之以考察有“什么”蕴涵其中的人类学族群性理论的时机或许已然成熟。换句话说,现在已是建构关于族群性的社会文化理论的时候了。希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达到一种对文化为何物、它如何长期存在、如何传递、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如何处理等的更好理解。
慨而言之,关于族群性的研究能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论发展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我们在族群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具有政策应用的巨大潜力。COER将一如既往地促进关于这一主题的人类学研究的传播与交流,并热忱鼓励国际学者踊跃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
校/秦红增
秦红增(1967~),陕西合阳人,人类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收稿日期2007—0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