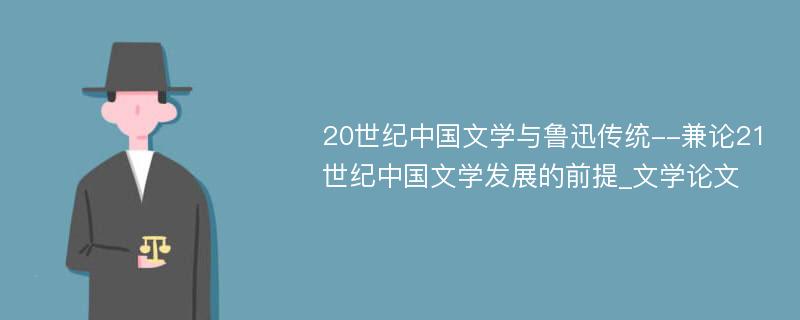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鲁迅传统——兼论中国二十一世纪文学发展的一个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二十一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此新旧世纪之交,我们讨论中国20世纪文学与鲁迅传统的关系,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阶段性和延续性的统一。这种统一,集中体现在对传统的继承和革新上。继承是根须,革新是花果。没有继承,革新将失去基础;没有革新,继承也将失去存在的价值。今天,我们站在20世纪的末叶,展望21世纪文学的未来,一个不可缺少的逻辑起点和思考前提,即是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对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的文学产生着怎样的影响,或者说,怎样制约着,规定着一个世纪文学的发展。
所谓传统,是指由历史沿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因此,文学传统,即是指由历史沿传下来的一种艺术习俗。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若进一步思考,文学传统是凭借什么力量才得以在历史上沿传不衰的呢?那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威性和规范性。也即是说,只有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历史上,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的文学现象,才能称得上传统,才能被后代所发扬和继承。
从这个观点出发,回首20世纪中国文学,在其流变、衍生的历史上,最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的人物,莫过于鲁迅。鲁迅,是中国20世纪文学所造就的一位最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文学巨匠和伟人,同时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最富权威性和规范性的一种传统。
从理论上说,确立这样一个观点的基本依据和重要标志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两段话。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转引自袁良骏《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毛泽东又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转引自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3—84页)这是我们至今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一位中国现代作家的最高评价,也是唯一评价。这个评价,肯定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肯定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实质上就是肯定了鲁迅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权威性和规范性。我认为,这样理解和认识,在理论上应该没有疑义。
从实践上看,鲁迅文学传统的权威性和规范性的形成,历经了以下三个阶段:
初始期(1918—1930):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影响的一个结果。它是伴随着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生而发生,伴随着中国现代革命的发展而发展。而我们愈是研究它的初始阶段,便愈会发现,它事实上对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生,是起到了某种催生的作用的。这即是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初始阶段,即“五四”时期,一批文化先驱首先带有思想先驱的特点。因此,“五四”文化革命也首先带有社会革命的特点。作家出山为文,首先是肩负着改造社会的神圣使命的。这构成了影响了一个世纪的“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作品的生命基因。
鲁迅从1918年5月发表他的旷世名作《狂人日记》开始,就出手不凡地使他成为这批作家中的一员骁将,把自己摆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祖师的地位。借用西方人的习惯,我们或者可以把鲁迅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
鲁迅从1918年起就最早参予了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的编务活动。历史地看,《新青年》杂志在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诸方面,都当之无愧地起到了新时代启蒙向导的伟大作用。鲁迅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一批论文、杂感和《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批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象集束手榴弹一样,“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极大地激动了青年读者,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引自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77页)。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对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适应时代潮流,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同上)。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说:“鲁迅是‘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同上)。
在二十年代中期,虽然鲁迅陷入“五四”退潮时期苦闷彷徨的境地,但是他不仅一刻没有停止过自己思想、社会、文化革命的求索,而且适时地写出了《祝福》、《孤独者》、《伤逝》等一批小说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命运,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成为映射这一时代社会生活的一面真实镜子。除此以外,鲁迅还出版了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华盖集》正续篇,发起组织了“语丝社”,“未名社”,编辑出版《语丝》、《莽原》、《未名》、《国民新报》等刊物。在他的麾下,团结、集中了一群进步的作家。1925年,当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蜂起,“三·一八”惨案最为激烈的关口,鲁迅义无反顾了站在支持、声援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并果敢地写出了《纪念刘和珍君》等尖锐犀利的篇章。在北洋军阀政府制造的黑暗、寂寞、无声地中国中,鲁迅的行动、作品和言论,无疑是一声震聋发聩的绝响,警世骇俗的春雷。鲁迅的声名、地位和影响,在愈演愈烈地斗争中日显光辉。
20年代后期,鲁迅南下广州。在北伐革命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和共产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机会更多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这加速了他世界观的转变。特别是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以后,严酷的阶级斗争,使他原先的“进化论”思想深受震动,轰坍倒坏,认识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二心集·序言》)。在这以后,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997页),实现了世界观的彻底换位。这标志着鲁迅的思想,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够达到的峰巅。而在这以后,富于戏剧性的插曲是,“创造社”、“太阳社”的一群年轻的共产党员作家,挑起了与鲁迅之间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这里,值得我们深思并特别加以强调的是,这场论争本来对刚刚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的鲁迅来说无疑具有挑战性,但历史已经结论并且证明,鲁迅在这场论争的过程中,出于应战的需要,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正确地回击了这群共产党员作家带有“左派”幼稚病的错误观点,显示了鲁迅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空前成熟,显示了鲁迅作为“一代大儒”和宗师的威力和风范。鲁迅的地位,不仅没有丝毫的动摇,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这事实进一步证明,鲁迅不仅在同外部敌人的斗争中是一员骁将,而且在同革命阵营内部错误观点的斗争中,也是一位正确的天才。
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酝酿筹备过程中,中共中央委派冯雪峰作为特派员,找到鲁迅请他领衔列名发起,并亲自领导“左联”。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又请鲁迅发表了《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这些事实,都雄辩地证明了鲁迅在革命文学阵营中具有不可忽视、举足轻重的地位,都是对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权威性、规范性的最鲜明的确认。据此,我们可以说,“左联”的成立,对鲁迅来说,是一个标志,到“左联”成立,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权威性和规范性的地位,大体已形成并奠定了。
发展期(1930—1940):
进入30年代以后,鲁迅作为左翼文坛领袖的名声大噪。声名的显赫,地位的重要,使鲁迅的社会活动日益增多。这个时期的鲁迅,留给世人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四面出击,多方参予,频频亮相,显示出十分活跃的战斗姿态。
他先后加入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
他多次和进步的文化人一起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暴行。他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到德国驻沪领事绾,递交反对法西斯暴政的抗议书。
他和进步文化界同仁发表《为团结御侮和言论自由的宣言》。
他先后参予领导并编辑了“左联”公开或秘密出版的革命刊物《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文》、《文学》、《太白》等,亲自倡导了革命的新木刻运动。
他与共产党人的陈赓、瞿秋白有了亲密的交往,建立了同志式的友谊,并就革命文化运动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时候,他与茅盾联名发出贺电,热情洋溢地赞扬中国共产党人,“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当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主张的时候,他专函表示热烈拥护,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凡此种种,可以说,从1930年“左联”成立一直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革命文化运动的各项活动、斗争、事件,都与鲁迅有关,都有鲁迅的直接领导和参予。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已经成为举世周知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自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以后,鲁迅的这种权威性和规范性,又由事实发展到狂热的遵奉和崇拜。上海左翼作家和人民群众数万人,自发地悼念鲁迅逝世的游行行列前,第一次亮出“民族魂”的大旗,首开了这种遵奉和崇拜的先河。随后,身受鲁迅影响的青年作家巴人(王任叔)首次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撰写理论专著《论鲁迅的杂文》,并创办弘扬鲁迅思想、精神和文风的刊物《鲁迅风》,同时又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起、展开关于“鲁迅风”杂文的大讨论。巴人因此而在鲁迅过世以后有“活鲁迅”的美誉。巴人上述的种种作法和努力,在基本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弘扬鲁迅文学传统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这次尝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全社会,同时也向未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宣告:鲁迅的思想、精神和文风犹存,而且作为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极富权威性和规范性的一种文学传统,必将发扬光大。
确认期(1940—1943):
所谓鲁迅文学传统的确认,即是我们要寻找鲁迅思想、精神、文风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的理论依据。即是在什么样的具有指导性的理论著述中,说明过、总结过、论证过鲁迅文学传统,这是全部问题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鉴于此,我们可以说,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3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验证鲁迅文学传统的两个最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关于《新民主主义论》,上文已经引证,这里不再重述。这里,我想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重要文献中的诸多观点来验证鲁迅文学传统,如何被党的最高领袖从理论上加以确认。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指导革命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献,至今仍然是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指导方针。它为革命文艺及随后的社会主义文艺规定了若干重要的准则。而现在,在本文中,我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这些准则和鲁迅文学传统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者进一步明确地说,坚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向,在本质内涵上,就是坚持鲁迅文学传统的方向。只不过在此以前,人们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全面、深入理解和领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明的观点,我想,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也同样应该没有疑义。
具体说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重要文献,在以下一些重大原则观点上和鲁迅文学传统毫无二致。
①在关于作家应有的人格风范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要以鲁迅为榜样,为楷模,毛泽东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这里,实际上毛泽东在整体人格上,是把鲁迅作为培养和造就革命作家的一个必要的尺度和标准。检验是否是革命作家,要以这个标准定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才把鲁迅的两句诗看作是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甚至是一切革命家的座右铭。由此,便形成了作为鲁迅文学传统基本内核的人格传统。所谓鲁迅文学传统,首先就是这样一种人格传统。毛泽东要求一切革命的作家要遵循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
②在关于我们的文艺应该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毛泽东论述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是鲁迅在1930年“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同上,第857页)接着,他具体论述了宗派主义的根源在于彼此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的不一致。他说:“比如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同上,第857——858)毛泽东在这里援引鲁迅的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他把为什么人的问题看作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把文艺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作克服宗派主义的先决条件,在理论上,是以鲁迅的“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为依据的。而在指导革命作家统一思想、统一战线的口号上,则是完全和鲁迅“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观点一脉相承的。这从一个侧面,也使我们看到了鲁迅的远见卓识,看到了鲁迅在30年代岁首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看到了作为我们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对鲁迅观点的重视、首肯和褒扬,以及在事实上,把鲁迅的上述思想当作革命文化的一种传统予以进一步确认。从那时起,我们的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始终紧紧地环绕着这样一个目的,牢牢地恪守着这样一个方向。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鲁迅的无量功德。
③关于作家,尤其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思想感情转变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一些人轻视工农,脱离群众的倾向,针锋相对地提出:“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转引自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等要求。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根据当时“左联”内部作家的思想状况,也对革命作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以下三个方面向革命作家敲响了警钟:“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第二,倘若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转引自袁良骏《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70页)这三个方面,鲁迅用否定句,从反面强调了革命作家与社会斗争接触,明了革命的实际情形,放下架子,和劳苦大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性,而且把这种重要性上升到若解决不好就可能滑向右翼的原则性的高度,提请每一个左翼作家注意和警觉。这里,鲁迅在实质上所涉及的,也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上海国统区的左翼作家多属于这类人)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毛泽东和鲁迅,虽然是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虽然语言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但问题的针对性和实质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鲁迅作为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在30年代初“左联”的成立大会上,就能有此番见解,更显难能可贵。
④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转引自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同上,第56页),“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同上,第57页)。鲁迅在这方面的见解,更是表现出和毛泽东惊人的一致。他指出:超现实,超政治的文艺作品是没有的。“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引自袁良骏《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鲁迅从早年开始,就和中国的早期共产党人如李大钊等有了密切的交往,崇敬地称他们为“革命的前驱者”,称自己所遵奉的正是这些“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并旗帜鲜明地将自己的创作称之为“遵命文学”(同上,第28页),断言“文学是战斗的”(同上第89页),而且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宣告:“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同上,第70页)。鲁迅这里的“一翼”说,和毛泽东的“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说,和列宁“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说,其内涵是完全相同的。鲁迅天才的思考力,还表现在他较早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正确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他说:“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同上,第62页)这里,鲁迅在肯定文艺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宣传手段之一的基础上,又十分强调要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其思考的缜密和论述的天衣无缝,可以说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论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⑤关于对中外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论述是:“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60页)鲁迅对这个问题的见解,集中体现在他1934年写的《拿来主义》的著名篇章里。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对于如何正确对待文化遗产,作了精辟的理论的概括,提出了一系列和后来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的观点。首先,他主张对于中外文化遗产要敢于“拿来”。敢于吸收,是有自信心的表现,要求革命作家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转引自《鲁迅研究》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其次,“拿来”之后,要进行“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同上),这即是要求革命作家要用革命的批判精神对待之。第三,“占有”和“挑选”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借鉴,为了推陈出新,为了新文艺的建设,为了发展和繁荣新文艺的创作。他的结论是:“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同上,第84页)“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同上,第85页)尤为可贵的是,鲁迅不仅是“拿来主义”的理论倡导者,而且也是批判继承中外文化遗产的实践上的身体力行者。他自己全部的创作道路,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精神。他自己全部的写作成果,则是在批判继承中外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新的结晶。鲁迅以自己卷帙浩繁的著作,为革命作家树立了一个在批判继承中外文化遗产中创新的光辉榜样。
限于篇幅,兹不赘述。从以上五个方面,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都是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都是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确认和弘扬。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实质和鲁迅文学传统的渊源联系上,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也应该没有疑义。只不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鲁迅文学传统提炼到,上升到指导革命文艺工作的方针和路线的高度,以党中央的名义号召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去贯彻执行,使之更具有代表性、普遍性和号召力。
几乎无人否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面鲜明的旗帜。它指引着在这以后的一代解放区文学,一代由1949年开国至今仍然在继续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前进方向。这已经变成半个多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一个基本的事实。依据上面的论述,随之而表的结论是,这样一个文学发展的过程,也同样可以现解为是鲁迅文学传统不断被继承和发扬的过程。谈到这里,不由使人想起郁达夫1937年,在《鲁迅的伟大》一文中所说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看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
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明确这一点,意义十分重大和深远。眼下,观念的碰撞,文学的困顿,物欲的诱惑,使人们淡忘了历史,消解了传统,冷漠了鲁迅,以至在20世纪新文学的出发点和发展方向上,出现了一些糊涂或模糊不清的认识。因此,回首20世纪的新文学大有正本清源的必要。其实,即便在讨论21世纪未来文学的趋向上,勾画21世纪未来文学的蓝图上,我们也完全可以大胆地说,鲁迅文学传统也仍然不失其指导、借鉴价值。鲁迅文学传统,不仅深刻地影响,或决定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历史,而且,也必将深刻影响,或决定着中国21世纪文学的未来。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历史不容割断。未来文学一定是历史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鲁迅文学传统,作为20世纪文学一项宝贵的历史经验,当永远为未来所记取。依愚之见,这在当前,大有提醒世人特别加以注意的必要。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引自《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1936年,鲁迅逝世前,在重病中诉说自己心境时,曾经这样自慰地说。6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这新旧世纪之交的关口,展望着中国文学的未来,重温这句话,不是可以从中悟出一些真谛和要义来吗?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读书论文; 毛泽东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二十一世纪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文艺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