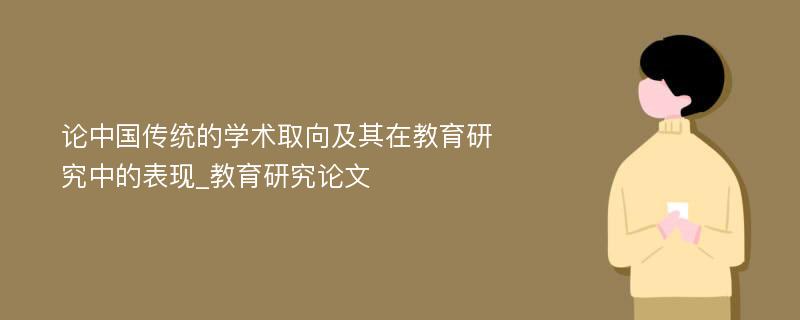
论中国传统学术取向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学术取向作为一种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色”,仍然浸染在当前的教育研究中。本文着重于讨论传统的政治与伦理、功用性、无为、泥古等价值取向,并分析它们在教育研究中的现实影响。
一、政治与伦理取向及其在教育研究的表现
(一)传统学术中的政治与伦理取向
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刘勰的“原道宗经”,到韩愈的“文统”,白居易的“为时为事”,以及宋明理学的“文以载道”,关心国事、政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入世态度在学理思想中的反映;反过来,积极寻求政治认同也被视为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正当的途途和最高的伦理,“学而优则仕”是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的和最终的归宿。这种追求被固定为一种习惯化的学术取向逐渐由显意识渗入潜意识之中,成为不动声色地支配读书、求学、研究的内在控制力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大一统国家。政治大一统或政治专制与意识形态的专制、思想的专制、文化的专制往往相为表里。因此,最高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就成为“正确”或“真理”的拥有者和相应标准的制定者、解释者以及社会思想、观念合法与否的最终裁决者,质疑、批判或争论、论证不仅不重要,而且,也没有可能。接受和传承既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也就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发展和创新倒成为次要的事情。
另外,传统知识分子的伦理理想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方面反映了积极的“救世”倾向,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在“兼善”与“独善”,即在社会与个体、至上与至下、入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之间极大的情绪和责任的两极跳跃,一旦不能获得“兼善”的机会和成功,便由第一种状态向第二种状态不经过任何中介地急遽滑落。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一旦有实现社会价值的机会,又可以很快从“自我”主体状态转换成“社会”主体状态,“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1]。
学理上的政治和伦理追求,与大一统政治和文化高度契合在一起,形成中国学术史上极其牢固的以“政治”口味和伦理原则作为首要标准衡量学术价值的思维倾向,这与“宁愿获得一个因果关系,而不要波斯王位”的西方知识分子传统十分不同。
(二)在教育研究中的表现
1.形成了以“方针、政策阐释”、“某某思想、理论注释”代“思想创造”的中国式的学术研究范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学术研究中“救世济穷”的精神并不总是处于充盈状态,但以政治思想、政策注解为定向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却一直绵延不绝。
2.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国式的”的理论命题,如,“教育为......服务”,“教育是生产力还是上层建筑”等,为中国的教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问题域和问题,并且产生了面向这些独特问题域和独特问题的独特的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
3.以政治为定向的思维方式导致的思想和思维控制必然引起“反控制”力量的对抗,控制与反控制、政治依附与追求自由和独立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如以个体、群体和社会,以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为轴心的一系列命题或隐或显地贯穿整个文化发展历程,虽然个体对自由和独立追求的力量强度没有壮大到可以与主流思想相对抗,但却成为后世新理想追求赖以汲取营养的一种珍贵的思想理论和精神资源。在较近的历史时期,专制与自由两股对抗力量的“缝隙”中产生的一些针对这种“紧张”的教育命题和论域,即反映出这样的追求,如: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等,教育的社会发展价值和个体的发展价值的统一,教育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的统一或教育社会价值实现的“中介”等,这些都是对单一政治取向的反动,也可以算做其产生的“副产品”。
二、功用性取向及其在教育研究的表现
(一)传统学术中的功用性取向
“子罕言利。”[2]而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故而,中国自古有“超功利”的文化传统,“正其谊不谋其利,明义道不计其功。”[4]但是,在相反的一方面,古代中国人在追求伦理、社会知识或者学说时,虽然没有“个人的”、“物质的”功利色彩,却含有强烈的“社会的”、“伦理的”功用倾向,“知以致用”,追求“知”的结果的“有效性”——或“治国平天下”、或“修身养性”,或“利国”、或“利人”。中国夏书上说:“正德、利用、厚生”,知和德、利是连在一起的。墨子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5]一切是否可实施即在于视其是否有利有用,有利则行,无利则止。韩非说:“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前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6]判断一个人、判断一种学说,唯以实效定是非;客体的知识和对主体的功用紧密关联,追求知识时首先考虑是否有应用价值,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几乎是不存在的。
功“用”性追求向两个纬度上发展,一是在时间上的无限延伸,虽经万世而价值不减——陆世仪有一段很典型的话:“天下后世公共之物不以兴废存亡而有异也”,所谓“天下后世公共之物”,就是永恒的圣学或其理。[7]也就是说,虽然天下有兴废存亡,但还是有一种经世致用的“圣学”或“真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是空间上的无限拓展,天下万物同出于“一理”,变化是表象的,而决定变化的“理”或“道”是同一的,因此,在此一领域的“道”与“理”放到其他领域也一样通用,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无论是天启神授的(如客观的绝对理念)“道”与“理”,还是人为的“道”与“理”(在经验之中抽象的真理性的认识),都必须通过人为的语言范式表达或描述,即从观念中观察、归纳或演绎出来;表达或描述的过程就是逐步摆脱具体、特殊、个别特点与条件的限制逐步抽象上升到一般的过程,目的是以期“经”万世且“致”万用。凡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命题,必然有笼统性、模糊性的特征(如拿破仑授意法典的制定要“短而含糊”),因为各种概念经过层层抽象以至于剥离了具体的内容时,就仅仅剩下一些符号或框架;这种符号或框架本身具有很强的可解释性和可填充性。这样,这些符号或框架的用途就极为广泛:
之一,可以极大地涵盖包容新思想。当人们想表征某一新鲜事物,或表达自己思想中某一新观念时,可以不用通过建构新的概念的方法来完成,而是从原有的概念中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沿袭古老的模糊度很大的术语,用意会的方法赋予旧的术语以新的涵义。例如:道、理、气等。符号是唯一的,然其具体表现形态却有千千万万。如朱熹所说,“月映万川,一理万殊”,“理一分殊”的观念深入人心。
之二,虽然抽象的理论或观念符号不能具体到行为与实践,但它被赋予了弹性地解释行为与实践的功能。
(二)在教育研究中的表现
1.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通用一种规则。清代第一个被朝廷认可的儒者陆陇其说,“九州万国,而统于一王,千流百派,而归于一海,千红万紫,而合于一太极”,[8]这个“一”是不需证明的既同一又唯一的普遍真理,而在集权一统的社会里,这个占有真理制高点的“一”只能是维护社会秩序合理性的政治伦理原则。这种真理被引进社会生活,成为评定、处置、规范行为、理论、实践的标准。所以,知识、思想、文化的发展受到钳制,教育同样不能幸免,以前有政治斗争原则代替教育规律,在“发展生产力”成为最大的政治时,教育的最大需要也是生产力的发展,教育也可以“产业化”。
2.在教育研究中,也希望能寻找到“握一管键而执万殊”的通则,把寻求普遍适用的“规律”或构建无所不包的理论框架本身作为最高和最后的旨归,反而忘记了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如孜孜以求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但却不感兴趣如何在日常的教育生活中为学生的创造意识的养成和创造能力的提高创造起码的条件。
3.高度抽象的通则其实只存在于理论和想象之中,虽然这些被绝对权威化的“符号”被赋予了解释、评价真理和行为的工具性作用,但它无论如何不能降临人间成为“条理”实践的规则。不能“用”的通则非要它发挥“用”的功效,只能导致一种常见的形式主义,即理论落实到“口号”上。
4.符号的含糊性有极大的理论包容度,但也往往出现“xx理论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现象”。似乎无所不包,其实什么也不能包容;似乎无所不能,其实什么也不能。
三、“无为”取向及其在教育研究的表现
(一)传统学术中的无为取向
“无为”在先秦时期不只是某家某派某个人物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一种个别的思想主张,它贯穿于儒、道、法等各家学说对天道观、人生观、政治观、认识论等多个领域的讨论之中,因此,“无为”思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天道观方面,“无为”表现为一种崇尚自然的倾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由于道、天、地都是自然“无为”的,而人应当以自然为法,所以人事也应该以“无为”为最高追求,“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天道与人道也,相支远矣,不可不察也。”[10]
在“事人”方面,也即在政治伦理观上,儒、道、法各家皆以“无为而治”作为理想状态。孔子认为古代圣王舜就是无为而治的典范;老子亦云:“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11]韩非子则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12]而这种对“无为”而治的推崇是建立在“天道”与“人道”统一、人性为“善”(如孟子)的前提性认识之上的。因此,道德准则和道德修养只要顺因了人之本性,就无需人为的强迫,只需顺其自然则可“直养而无害”。道家的道德修养学说更是强调因顺自然天性,主张“贵天法真”,“与天为一”,返朴归真,反对一切人为的举措。儒家的孝悌仁义在道家看来,仍然属于人为的勉强,“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13]虚静无为才是最高的道德,“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14]
在“事物”方面,即在认识论上,“无为”思维方式则表现为要求人们以虚静之心,不带“固执心”去认识事物。如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5]道家在认识论上的“无为”,几乎到了实际上否定认识活动本身的地步。如“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多知为败。”[16]也就是说只有不识不知,不进行任何人为的认识活动,才能得到真知,所以老子要:“绝圣弃智。”[17]“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18]
“无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社会强烈依附自然的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的生存形态有关。但无为的价值取向逐渐内化成一种普遍的“事人”与“事物”的思维习惯与态度,自然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主体的开拓性、创造性、进取性、建设性等精神为代价的。
(二)在教育研究中的表现
1.在“事人”方面,过于强调人的“自觉心”而缺少必要的外在的规范的制定和建设,如对制度建设的轻视。一般只有用制度实现的行为,以为可以用“圣人”的无为、“不言之教”以及自身的道德示范就可以启发人的自觉心得以实现。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多是把诸如“民主的管理方式和行为”、“实现教师的角色转换”等落实在理论探讨和观念中,在向实践迈步时,其保障“系统”是教师的“观念”、“耐心”、“爱心”等“软性”品质而不是“硬性”制度;同样,一般可以用制度规范和评价的行为,在无制度的情况下,也只有靠特殊的“人”来进行;因“人”本身具有的较大主观性、差异性,所以,所采用的评判标准和最终的评价结果也具有较大的“弹性”和随意性。
“无为”而治还孕含着另一种理论上不太可能但实践中却极容易转化成现实的可能性,即由无为而治转化为专制。在事实上不能人人自觉的情况下,又要达到“治”的目的,只能依靠人治来实现。“敬天”演变为“法祖”,“法祖”演变为“集权”,“集权”演变为“人治”,“无为”而治最终表现为“人治”,“治人者”虽不都是“圣人”,但由于是“代圣人言”,外加强权,因而,其权威性不可置疑、更不能抗拒。教师对教育行政权、学生对教师,被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服从与被服从的绝对关系,虽然在理论上已经有认识,但在实践中,仍然不能冲出旧的习惯化认识和行为的“围城”。
2.在教育中的“事物”方面,无为的思维方式一般表现为缺少对知识、尤其是对认识客观事物的知识的执着追求。自先秦时期,我们从来不缺少建立在体悟、直觉、经验之上的教育思想,但在教育的科学性追求方面却显得过于薄弱,建立在实证、实验基础上的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教育著作更是罕有。
四、好古、泥古取向及其在教育研究的表现
(一)传统学术中的好古取向
“好古”与“泥古”取向集中体现在学术发展中是“述—信”或“经学”式的思维习惯。它既是政治伦理取向的产物,又是“无为”价值取向的一种体现。
“述—信”式的思维方式,最早可以说源于孔子,也即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9],其根本特征是“泥古”,以经典的是非为是非,以经典内容的范围为学术应当固守的范围,不仅对待同一领域思想上不创新,而且在学术领域上不拓展。
这种注经方式在孔子时期可能是作为“私人”爱好,但从汉代开始,逐步的发展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传统方法,它的表现形式是通过经、传、注、笺、义疏、正义、疏证、集注、训诂等手段或技术,发掘前世圣贤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所遵循的原则是“注不破经”、“疏不破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清代的“考据”之风,除了外在思想的钳制,考据之风的兴起还是对宋明空谈心性之学的反动,提倡“行己有耻”的实践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工夫,以及“博学于文”的讲究确凿知识和博学主义的学风,使宋明之学过度强调的“内在自由”转向道德实践,因此,考据之风兴起之初,有着很强的“问题自觉意识”和“经世”取向。只是到了后来,这一取向越来越没有实现的可能,考据学逐渐由“征实”的行风、学风沦落成一种“技术”,成为知识分子表现智力和学养的一种纯粹的形式,“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20]明清以后,虽然经学注解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作为一种治学传统和研究方式,却根深蒂固地被继承下来。从发端上来看,注解式的思维方式应该是隶从于政治和无为取向,是一种衍生物,但就形式和发展过程看,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
(二)在教育研究中的表现
“述—信”或经学取向反应的是一种凝固的、保守的文化发展观,它至少遗留下来以下影响:
1.失去了问题意识,考据变成梳理既有知识的手段,导致知识和思想分离;尤其对经典、权威思想,基本上是让经典和权威代自己思考,阻碍了自我思想的发展和创造,进而造成整个思想系统的停滞和僵化。曾经有一个时期,教育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硬套搬就属于这种情况。
2.形成了依靠注解经典来寻求“真理”的传统,无论是瓦解既有的“真理”还是重建新的理论体系。过去以“尧舜周公孔孟之道”作为思想来源和最终的评判依据,现在仍不能完全摆脱这种思维窠臼。一些考据和注释的原则仍然通行,如时间原则、文本原则,“以时代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以时间的早晚、文本的原始为评判真理的标准,[21]今不如古,旁系不如直系,所以,一种理论如果血统不纯、出身不正,其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而不管它是不是对当下的事实是否有价值。每当有一种新的思想产生时,习惯于先给它找一个冠冕的“族系”,标明它是那种权威思想或权威人物的第若干代“后裔”;实在找不到“贵族血统”,也至少要想法让“贵族”给予承认。
3.如果说在思想钳制严厉时,“经学”注解式的研究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逃遁的方式(逃避对思想的审查和监督),但有时它也能演变成一种逃避社会责任的途径或为自己“偷懒”寻找的一种借口,“炒冷饭”总比重新启灶作饭来得容易。而且,不仅是炒自己理论领域的“冷饭”,而且炒其他学科领域的冷饭;不仅炒国内的冷饭,而且炒国外的冷饭,如教育学科缺少自己的独立性,对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简单移植;教育研究缺少本土特征,简单搬用西方理论等这些问题,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些研究方式的局限和弊端(当然,合理的“述”和必要的“考据”是绝对提倡的——它体现了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应遵循的基本学术道德;也是清理思想秩序和体系的基本方法和学术发展创新的奠基性工作)。
五、结束语
关于传统学术取向:中国传统价值系统是非常融通的一个有机系统,以政治伦理取向为本,功用性是一个具体表现,因为“功用”多是表现为对社会政治伦理的功用,主要不向物质的功利方面取向;“无为”是高度政治文化专制的必然结果,又是对积极入世受挫的极度反弹,而好古、泥古又是无为的一种具体表现。所以,这样就不难理解诸如“积极入世”和“清静无为”、“社会”与“个体”之类看似两极对立而实则相互转换和统一的独特文化现象。
关于传统学术取向对教育研究的影响:一种学术取向一旦形成传统,它对后继研究者的思考和行为过程都具有导向作用,而且,具有相当的弥散性、辐射性和时空穿透性,所以,当研究主体面对新的事物、解决新的问题时,它也能以内在的思维方式的形式发挥作用。如泥古式的“注经”,现在虽然不对“四书五经”本身进行注解,但却可以撇开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在对当代的中国和西方的“权威”思想注解中“大显身手”。本文在谈及传统学术取向对当前教育研究的影响时,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