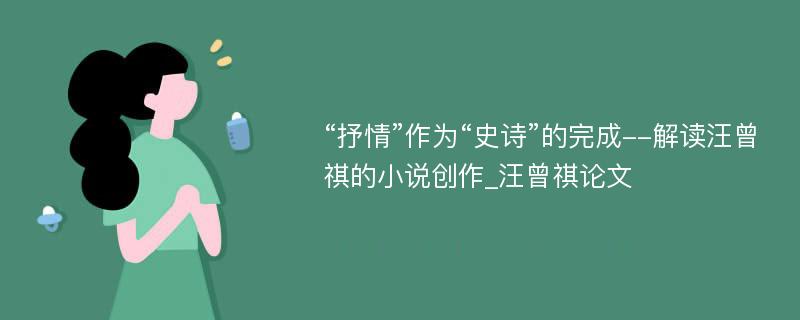
“抒情”作为“史诗”的完成——关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种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诗论文,抒情论文,汪曾祺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者而言,汪曾祺是个复杂而又难处理的作家,这或多或少是有些共识的。一方面,汪曾祺的写作很难被完全纳入某个宏大的文学史叙事,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早期现代派或者寻根文学,种种文学运动都与他若即若离;另一方面,他诗意的写作风格又增加了文本细读的难度。且不说别的,关于他到底是一个大作家呢,还是一个格局较小的作家,仅此一项就能引发无休止的争论。如果汪曾祺是一个大作家,那么他“大”在哪里?这恐怕又会导致层出不穷的辩论。一些耳熟能详、已成常识的指认,比如“京派传人”“最后一个士大夫”“继承了30年代文学”“恢复现代文学传统”等等,虽然是把汪曾祺往“大”了说,可总是有些“肢解”了汪曾祺、取其局部来探讨的嫌疑,并且往往是将汪曾祺从他自身所处的历史条件、脉络和环境中抽离出来,做一种“置身事外”的文本解读。
往“大”了讲汪曾祺,又能把他放在“毛文体”的终结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李陀先生大概是较早的一位。①无论今天他对于“毛文体”的评价是否有所改变,这篇论文都已占据了汪曾祺研究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罗岗先生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②,则正确地指出汪曾祺的语言风格所展现出的与延安文艺、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关系,从而试图填补汪曾祺研究“长达三十年的空白”,通过勾勒一个长时段历史中的汪曾祺,将汪曾祺的意义置于新中国文艺的价值判断之中,认为他写出了“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本文所做的无非是接续着这些经典论述来探讨汪曾祺80年代初的创作。一方面,我也确信汪曾祺并非一个“小”格局的作家,问题在于他“大”在哪里;另一方面,我将进一步把汪曾祺放置回他写作的更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汪曾祺的写作从来不置外于他所身处的时代,毋宁说,他比谁都对时代环境更敏感一些,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此外,罗岗先生在他的文中说到,他“并没有花更多的篇幅来讨论汪曾祺的作品”,而我则会尝试挑选一篇作品来具体剖析。
让我们先离汪曾祺的文本略远一点。
1978年第2期的《新华月报》,刊载了一篇名为《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③的文章,在当时的语境下,从多个方面反驳了“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这样一种激进理论,重新确立了“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地位。“按劳分配”的要义在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人们合法地占有他们的劳动所得,因而一方面,“按劳分配”能够激活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限制,“按劳分配”又不会带来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存在的差别只是由于劳动能力的不同而造成的“富裕程度的差别”。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不存在“剥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于“占有”的合法性仅被允许来自“劳动”,在私有产权并不是绝对至高无上的情况下,“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以至于“一部分社会成员无偿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的情况,并不会发生。
简而言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着“按劳分配”这一概念所建立起来的改革逻辑,并不纯粹是一种激活经济发展的经济手段,而更是一种涉及公正、平等等理念的整体性政治构想。这一政治构想在农村落实为“联产责任承包制”,在城市则是“计件工资制”,奖金制度的重新确立,其核心在于,当时的人们确实普遍认为,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限制,“劳动”将成为唯一合法的“占有”方式,这就限制了现代“私有产权”的自我理解,使得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下的财产权形式成为一种“有限度的财产权”,因而更接近于某种古典的财产权理解:“作为法权的财产”——“能够归功于罗马法学家的,是客观权利概念,它取自于希腊哲学,取自于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也就是说,罗马的法学家认为,存在着一种正义的客观标准,一种何谓权利的客观标准,每一个被分配给适合于他的东西。”④朴素地说,“按劳分配”同时提供了一种政治的正当性,公正、平等的政治理念与激发经济活力同等重要,或者说,恰恰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限制,才更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因为这可以避免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式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防止劳动的异化。
由于存在合法的“占有”形式,紧接着,“市场”“交易”的出现似乎是特别自然的事情,“按劳分配”原则下确立的“有限度的财产权”,使人们在“占有”之后很自然地可以交换他们的所属物,仿佛斯密所言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乃是人类的自然天性。在区分了资本主义“按劳分配”(虚假的)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区分按照逻辑也应当顺理成章,因为每个人用以交换和获取的,都是自己的劳动所得,由于不存在大的资本行为,以及并不是以资本增值为最终目的,在这个最简单的“市场”中不会存在剥削和不平等,只存在各取所需,选择的自由以及生活的极大便利,从而证明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巨大成功。这也是针对那个僵化的、只允许计划经济存在的社会主义而言的。
虽然在下文中也会谈到,但需要注意一点,这里的“市场”跟今天所讲的市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回到80年代初的语境中,我们姑且借用小说家何士光在《赶场即事》一文的概念,管它叫作“集市”,以区分于今天的市场。对于“集市”的描写,在80年代早期的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但我在此要做出一个简单的区分,限于篇幅,仅以何士光自己的创作为例。如果说“集市”的出场是“按劳分配”原则逻辑的自然延续,那么我们却能发现,《乡场上》(何士光的成名作,很好地诠释了“按劳分配”是如何落实下来的)与《赶场即事》有两点重要的不同。首先,前者的写作更理论化一些,着重点明显偏向诠释清楚“按劳分配”,而后者则因为“集市”的出场,立刻渗透进了人们的各个不同的日常生活领域,从而丰富起来。举例来说,“集市”不仅是交易场所,还是老百姓嫁娶办红事的必须场所,人们所有的日常生活都融于其间;其次,与之相对应的,《乡场上》的写作手法更传统一些,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些,而《赶场即事》则感情充沛,出现了大段大段的抒情性写作。
本文不是要做何士光的研究,因为接下去还会谈及“集市”,就不再赘言。这里仅需指出如下意思就够了:“按劳分配”是一种整体性政治理念,而“集市”在80年代初期文学中的出现,却绝不仅仅是在经济、政治的层面上继续证明“按劳分配”的正当性,它带来了某种新的东西,而这种新的东西,又促使80年代文学写作的风格产生了某种转变。倘若我们看一下汪曾祺在80年代早期的创作,就会惊讶于“集市”,或者小商小贩,或者做小买卖、小生意的人,在他所有当时的创作中所占比例之高。《异秉》《岁寒三友》《晚饭后的故事》《七里茶坊》《晚饭花》《故乡人》《徙》《鉴赏家》《八千岁》,包括《大淖纪事》,简直离不开此。于是我想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说,汪曾祺置身于他的时代之外,也许与我们惯常的认识正相反,汪曾祺比那些现实主义作家更现实主义一些,问题在于,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他小说所叙述的内容未必是80年代,有时甚至模糊了小说的时代背景,但既然作家写作的时代总要比他所写的时代更重要,不妨就把他的创作——内容、题材、风格、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回时代之中来理解。
借助波兰尼⑤的概念,我们不妨说,“集市”与市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集市”并不脱嵌于我们的其他(政治、社会)生活,反而是嵌入其中的,它不以“理性经济人”作为逻辑起点。我们来看看汪曾祺是怎么描写这些做小买卖的人物的。
在小说《鉴赏家》⑥中,汪曾祺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叶三是个卖果子的。”实际上,之所以选择这个文本,是因为它更完整地展现了汪曾祺对这些做小生意、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看法,当然也可以选择别的文本,比如《岁寒三友》,有意思的,季匋民这个角色,也在《岁寒三友》中出现过。
在开篇,汪曾祺首先交代了叶三的劳动及其收入,“叶三卖果子从不说价。买果子的人家也总不会亏待他。有的人家当时就给钱,大多数是到节下(端午、中秋、新年)再说”。小说创作于1982年,人们以自己的劳动换取个人财富的合法性已经成为共识,于是,与汪曾祺一贯的写作风格相符,他在此处对叶三的生意状况仅作简洁的交代,就将叙述转向了别处,他通过叶三之口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一点,这里的“生意”不是出于盈利为目的的经济行为,叶三做买卖完全是他整个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汪曾祺在交代了叶三以做买卖为生之后,有意识地立刻澄清了这种商业活动的性质,当叶三的两个儿子立业成家,叶三五十大寿之后,“老大和老二都提出爹不要走宅门卖果子了,他们养得起他。”但叶三应答道:“我跑惯了。我给这些人家送惯了果子。就为了季四太爷一个人,我也得卖果子。”在这里,汪曾祺通过叶三之口说出的恰恰是,做买卖这一行为固然为了谋生,但自己却并不将之看作简单的盈利活动,也不能仅仅在经济的层面上得到充分理解,虽然汪曾祺并不置外于自己的时代,显然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小商小贩在促进经济繁荣和便利生活层面上的赞美,但归根结底,叶三与季匋民的关系才是汪曾祺关注的重点,在其中,真正地来说,反而是叶三的劳动、“挣钱”嵌入了叶三的日常生活,是他在熟人社会中人情交往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给这些人家送惯了果子”,“这些人家他走得很熟,看门的和狗都认识他”。
至于季匋民,则更是如此,“他给季匋民送果子是为了爱他的画。”汪曾祺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叶三和季匋民之间的非同一般的“交情”,在这里,平等的“交易”、“交换”完全是次要的,叶三与季匋民是彼此互视对方为知己,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理解两人对于彼此的优待,“叶三搜罗到最好的水果,总是首先给季匋民送去”;“季匋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倘若在这里把两者的关系仅理解为平等的交易,则故事显然会出现严重的逻辑漏洞,因为“季匋民最讨厌别人谈画。他很少到亲戚家应酬。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喝半盏茶就道别。因为席间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谈阔论”。季匋民自视清高,显然不会按照平等交易的原则,因为叶三给搜罗到最好的水果,先给他送去,他便“对叶三另眼相看”。季匋民的“另眼相看”和叶三的“赏画”不是一种可以以金钱衡量的平等交易。也许既是作为某种证据,又是再次的强调,汪曾祺在小说的结尾再一次地明确地拒绝了这种交易原则,“有时季匋民给叶三画了画”,刻意“不提上款”,方便叶三拿去卖画,因为“有上款不好卖”,叶三则明确拒绝,“您的画我不卖”,“一张也不卖!”“季匋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日本有人专门收藏他的画。大家知道叶三手里很多季匋民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叶三的藏画”,并且是“要多少钱都行”,叶三从未动心,只管“不卖”。叶三死后,“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埋了。”
人的经济行为嵌入在他的整体生活世界之中,汪曾祺这样来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正如上文所说,关于“集市”的想象,并不单纯是处于“按劳分配”在经济和政治正当性的逻辑延长线上,它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整体性的政治构想能够完成的最后一步,是要确保这一理念能落实和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到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形式。80年代早期,许多敏感的作家们都发现“集市”是“按劳分配”这一政治理念在生活世界中的落实和展开,“落实”的意思当然很清楚,说“展开”,是因为“集市”不仅秉承了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的想象,还确立自身作为一种生活形式——“集市”始终是与婚嫁、节日、人际往来、熟人社会等等紧密扭结在一起——来承载这一理念。
进一步的,汪曾祺的写作不仅是改革早期的总体性政治世界构想的完成——让理念找到现实生活中的形式——而且赋予了这种形式美学上的合法性,他动用了各种传统文化资源来支撑起这一形式,让“按劳分配”的理念不仅是正当的,可行的,更是可欲的。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一过的、是美好的,这恰恰是政治最终需要回答和应对的问题。我们都习惯于说,汪曾祺的小说很抒情、很美,在汪曾祺的写作中,抒情不是那个有深度的现代个人对于现代性的审美对抗,抒情恰恰是对于“史诗”(整体性政治构想)的完成,表达着“按劳分配”世界最终可以带给人们的家园感。与此同时,人的工作、劳动、交往也浸润在美与善的理想意义和价值中,叶三的劳动没有丝毫的枯燥或者异化,很难想象今天一个卖水果的生意人能够通过他的劳动和他的顾客形成各种熟人社会的人情交往,并且同时能作为一个艺术鉴赏家。
汪曾祺写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都不可能建立在纯粹谋取利润和利益的基础上,它必然涉及如何安排人的生活,以及如何使这种生活呈现出“自然”的面貌,即便这种“自然”是人为的。人无法单独地赤裸裸地暴露在纯粹追求利益的经济关系中。于是,当我说汪曾祺是一个“大”作家的时候,我所指的是,汪曾祺也许比别的作家对于自身的时代都更敏感一些,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完成他的时代,并赋予它文化与美学上的合法性支持。
如果汪曾祺是一个“大”作家,那么他今天又为何常常被误认为一个“小”作家呢?我想,忘记了汪曾祺的意义,或者将他置于某种审美趣味的小格局中来阅读,也并非完全是读者的错,更合理的一种解释是,汪曾祺试图通过自身写作去完成的那个时代,已经终结了。
虽然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汪曾祺是一个“大”作家,并且从阅读和阐释他的作品的过程中洞悉更多,但仍然有必要简要地来说明,汪曾祺为何迅速地被读“小”了。这里大致上存在着两方面的因素,均与汪曾祺笔下人物的劳动形态——他们都是小生产者——有关系。
首先,在商品社会中,我们理解劳动产品的唯一形式,是它的“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如果说“按劳分配”的内在要求,即不存在贫富差距,只存在“富裕程度的差别”,在农业、小生产者这样更能自给自足的领域内还是可能的,因为此时“使用价值”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上还能实现和理解其自身,那么在发达的商品社会中,即便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保障,“多劳多得”也从来不是有保障的。在大约1983年开始的“城市改革”中,这一点体现得特别明显,在我们惯常的历史叙事中,“城市改革”是改革开放在农村地区取得成功后,在城市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仿佛这里存在着某种延续性。但事实上,改革一开始就是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展开的,在农村是“联产责任承包制”,在城市是“计件工资制”和奖金制度,但是,“按劳分配”在城市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反而出现了产品滞销,货物大量积压的情况。于是,1983年的“城市改革”与其说是原先改革逻辑的延续,不如说是一种断裂。其中最关键的两点,一是开始以效益、效率为中心;二是在沿海大城市,“按资分配”的逻辑开始逐渐取代“按劳分配”,也就是说,光有“按劳分配”,单纯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已经不够了。
于是,作为一种总体性构想的“按劳分配”在哲学上的失败,在之后几十年的中国社会迅速变为现实,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差别,一部分人的劳动比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更有“价值”,这并不因为取消一个外在的剥削阶级就能消除。“按劳分配”内在地缺陷可能在于,它将中国的现代性构想建立在小生产者的基础上了。但是,更有意思的一点是,早在这种差别在经济层面成为现实之前,在美学层面上,汪曾祺的想象就已经失效了。在此我仅举一例,在张承志《北方的河》中,主人公“我”有三种职业选择,本身是计划生育宣传科的职员,同时又在考研,事情发展不顺利的时候,同伴又提出开个小酒铺的打算。在“按劳取酬”的经济意义上,三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我”却无论如何要考研究生,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意味着,在经济差距拉开之前,不同的劳动在价值和美学意义上已经有所区分。考虑到“知识”通过8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写作所取得的霸权地位,这里直接就区分出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的差别甚至发生在实际的经济学层面上的差距之前。换句话说,“我”在研究生的考试和学习的劳动中才真正实现了全部的自己,而其他的体力劳动对于我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异化劳动。想想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选择走出农村的行为,他是一个不顾一切要走出农村奔向城市的青年,但想想马栓给巧珍的承诺,马栓是个能赚钱的农村人,这个安排显示了在当时,农村与城市在经济上的差距还没有完全拉开,但高加林仍然把在大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由汪曾祺来写作张承志的题材,让汪曾祺来描绘计划生育宣传科的一个卑微的工作人员,他同样可以把这种日常生活处理得诗情画意,值得一活。如果我们预先考虑一下新写实小说,诸如《烦恼人生》或者《一地鸡毛》在将来不可避免的出现,我们就能理解张承志的理想主义了。某种程度上说,汪曾祺展现了80年代早期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他以抒情的方式完成了关于自由和美丽生活的想象,唯一的问题在于,这种想象仍然奠基在小生产者的基础上,而终结了汪曾祺的抒情和美学的,恰恰是张承志。
汪曾祺所努力经营的日常生活想象最终失败了,但汪曾祺以这种奋力的写作表明了自己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格局小气的作家,汪曾祺的写作确实动用了某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因而常常容易被误认为一个士大夫,或者隐士的形象,然而他的这种寻求传统文化,比如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却绝不能做复古的理解,毋宁说是在完成自身所处的时代。他的写作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他指明了一点,我们所期许的并不是一个单纯追求公正分配和获利的世界,并且同时是一个能让我们的心灵安逸地存在于其中的伦理家园,汪曾祺通过写作提醒我们,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性世界的构想中,这一点都绝不可或缺。
注释:
①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载《花城》1998年第5期。
②罗岗:《“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③严实之:《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载《新华月报》1978年第2期。
④彼得·甘西:《反思财产从古代到革命时代》,“第七章作为法权的财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⑤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⑥汪曾祺:《鉴赏家》,见《汪曾祺全集》(二),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