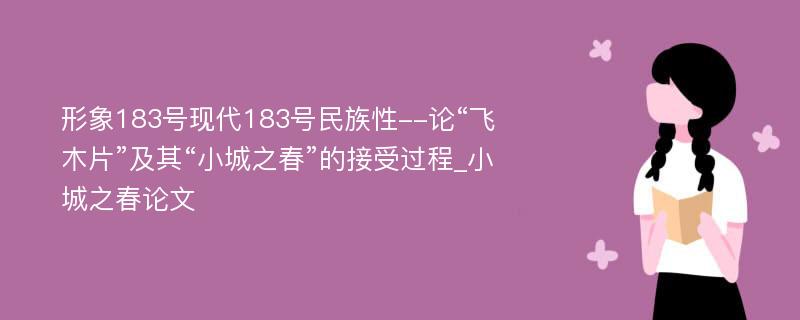
影像#183;现代#183;民族——论费穆电影及其《小城之春》的接受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城论文,之春论文,历程论文,影像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4)01—0079—04
新世纪初,原“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田壮壮重拍民国时期著名导演费穆的代表作《小城之春》,使得关于费穆及其《小城之春》的影像记忆再次被电影界召回。费穆电影被接受历程本身就是中国电影观念和电影观看情境的嬗变历程,它自成一条影像中国的历史脉络。对于费穆电影的观看、评论,生发了电影的中国情境的诸多想象,其中涉及电影本体与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的象征体系建构与知识分子身份与处境的影像呈现、电影与都市市民空间的关系、中国电影诗学的形成及其与世界电影的对话等等太多可阐释的空间。对于费穆电影的观看、评议与阐释的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49年以前,是“被看”并众说纷纭的时期;第二阶段,是1949年以后“不看”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重看”并深入阐释的时期。
一 第一阶段:“观看”的芜杂与喧哗、意识形态话语、都市空间话语与电影美学话语
费穆在1933年完成联华公司出品的导演处女作《城市之夜》,一时一鸣惊人,好评如潮,左翼电影评论家凌鹤在《费穆论》中称赞道:“大家都不会忘怀从《城市之夜》中所得来得深刻印象:贫民窟与高大的洋房,大富翁与赤贫的奴隶,悲苦与荒淫,天堂与地狱。……严肃的处理了这社会悲剧。”[1]黄子布(夏衍)、席耐芳(郑伯奇)、柯灵、姚苏凤四位批评家也联名推荐说:《城市之夜》“的题材之‘接触现实’与‘暴露的有力’,是……一张前进的有意义的新作品”[2]。《城市之夜》不仅在思想性、意识形态上获得好评,左翼评论家也不吝笔墨对其“电影性”作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夏衍写道:“现在的电影已经到达独立成年的时期,它应该尽力发展自己的特长,不必再为戏剧的隶属。……这样非戏剧的故事,若没有好导演一定会失败的,然而费穆先生的导演却异常成功”。[2]
出乎左翼影评家意料,费穆这之后执导的《人生》、《香雪海》、《天伦》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不断的“倒退”,使他们相当失望。但是,他们依然不吝在电影艺术上对费穆作出好评,认为《天伦》在艺术水准上“是达到了中国默片的最高峰的作品”,“费穆懂得用蒙太奇,这使他和中国所有的导演们有着不同,而独自在他的作品中放射着光芒”[3],“而《人生》……是代表了知识分子的风格的划时代的成功。……尤其是细腻的内心描写,差不多成为他的特长”[4]1936年费穆执导的“国防影片”《狼山喋血记》由于“政治上正确”,鲁思、凌鹤、尤兢、尘无等33位影评者联名隆重推荐:“费穆先生的《狼山喋血记》在中国电影史上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宣传已久的国防电影在这张有力的影片中巩固地确立了。对于许多软弱无力的作品是一个极烈地示威,对于一切向上有为的艺人又是一个强烈的号召。”[5]
至于1948年公映的《小城之春》,其反响就更复杂了,它有一些知音,并得到某一类知识阶层观众的共鸣和捧场。当时就有赞誉——“《小城之春》的作者用东方色彩的笔致——冲淡的笔致来描写一则美丽的东方人的故事”[6],“费穆严谨的制作态度,使《小城之春》达到国片前所未有的艺术的高峰”[7]。可是,终究对于“大时代”来言,《小城之春》真可谓是“生不逢时”。它“总不是顶坚实的作品……春光局促于颓域的一隅,带着一些狭窄、保守、陈旧、隐逸的气味。”[7]这还是最温和的批评。激烈的电影评论批评它“根本忘了时代”,“那么苍白,那么病态”,并规劝费穆“不要太自我欣赏,自我陶醉”[9]。更有甚者,说《小城之春》“没有时代性,没有民族性,完全是神经病者幻想的产物”;“没有思想,也没有感情,纯形式主义的东西……是不可宽恕的罪恶”![10]
总的来看,在30、40年代,对于费穆电影的接受应置于一个特别芜杂的语境或话语场中,其中有关键性影响的主要有三个因素。首先是电影如何参与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象征体系的想象和建构,这决定了电影应该产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意义,以及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当时民国政府文化官僚,都将电影视为建构主导性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一旦费穆的电影不能直接有效地纳入这种主导型意识形态时,就会面临被接受者的责问甚至否定。
其次,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电影如何参与形成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都市市民生活情境,从而形成关于都市民间或都市市民空间的想象。尽管费穆的电影后来一直只是电影界“圈内人”关注的对象,具有彻底的学院色彩,但是在30、40年代,它事实上是都市大众市民精神生活的参与者。当时的《申报》《晨报》等的副刊、电影评论、电影专刊经常有费穆的名字。就连《狼山喋血记》在苏州外景拍摄时“劈狼两头,猎犬10条”的消息也见诸于《申报》电影专刊的“联华花絮”[11],费穆电影的海报与众多的好莱坞电影的海报拥挤在同一报纸版面。他先后所在的联华、文华电影公司向来在由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职员等人群构成的“新派市民”中有较多的观众缘,而与阮玲玉、金焰等明星的密切合作也说明他是认同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的特性。
其三,费穆是如何参与对电影艺术的探索和完善的,即他对于电影这种独特的艺术样式的发展做过那些尝试,并有些什么成果。在此基础上,费穆电影又是如何寄寓个人化艺术风格和情愫,并得到一部分知识分子(或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共鸣和认同的。
事实上,从大量民国时期与电影有关的报刊杂志上看,费穆的电影在30、40年代的被接受与被评议中,以上三个因素是同时推进的,越是在社会心理和文化多元的“无名”时代,对他的接受就越是众说纷纭,而越是在“时代主题”压倒一切的“共名”时代,如全国性的内战时,对于费穆电影的接受时就会由一种声音压盖其它的声音,即意识形态的声音压盖都市空间、电影本体、个人风格与情愫的声音(注:关于“无名”、“共名”的提法,见于陈思和《共名和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一文,《上海文学》,1996年第10期。)。在费穆活跃着的这样一个大时代,拯救、再造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成为“中心任务”和时代主潮,所采取的方式和所运用的话语又是激烈对抗的、暴力性的,其它的不合时宜的声音自然是越来越微弱。无论是一个健全的都市市民空间的想象性建构,还是对电影艺术本体的探索,抑或对某种个人性心灵空间与艺术空间的追寻,相形之下都显得纤弱而在时代风暴中楚楚可怜。
二 第二阶段:“不看”的偏狭与晦暗、“修史”中的异类、小资产阶级
新中国成立之后,费穆基本上处于被遗忘、埋没的状态。只有在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它尴尬地存在着。思想上,该书认为“在民族斗争方面,费穆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一贯的,而在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斗争尖锐的时期,他则摇摇摆摆,并且基本上摇摆到消极颓废的方面”,至于《小城之春》,“它的消极影响就尤其不能忽视,在当时它实际上起了麻痹人们斗争意志的作用……再次反映了费穆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艺术家的两重性及其软弱的性格,反映了他在解放战争的伟大时代中心情的苦闷、矛盾、灰暗和消沉。”在导演艺术上,《中国电影发展史》承认费穆“是有相当高的成就和自己的独特色彩”,但是“这些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处理,在这样一部灰色消极的影片里,除了加深片中没落阶级颓废感情的渲染,扩大它的不良作用和影响外,决不会有任何别的效果。”[12]当年左翼评论即算在批评费穆“思想性”的同时,还能承认其对于电影艺术探索的价值,而《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导演艺术和电影艺术根本就没有独立的意义。
程季华等在1962年完成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史料的完整性和叙述构架的宏大性上依然难以超越。新的国家成立伊始,普遍开展的修史工程都真诚而急切地用一种通用的话语体系来叙述历史,而《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叙述和诠释历史时的纯粹性上做得更彻底。后人所知晓的大多数经典电影似乎都是左翼的功劳,也许正是这种历史叙述的结果。芜杂的多元的影像中国被叙述为左翼而且是尽量剥离“杂质”的左翼电影发展史,是一部现代性的新的民族国家在影像世界的起源和发展的史诗,其背景是连续不断的漫长的残酷的战争和惨烈的阶级斗争,而电影也构成了其中一条“战线”。与此同时,现代性中市民空间、都市民间的因素,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大众传媒和电影艺术本体的因素,以及电影工作者自身的独特创造空间,都因为进入不了“史诗”而被遗忘或招批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费穆自然成为一个暧昧的被叙述和阐释的对象:“由于费穆在政治思想上的动摇和软弱,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走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因此,在他一生的创作活动中,没有能使他的优异的导演才华更好地为中国的进步电影运动服务,这是十分可惜的。”[12]对于费穆电影的论述,《中国电影发展史》所使用的关键词是“小资产阶级”。在整套关于“史诗”的话语系统中,“小资产阶级”是一个晦暗并具贬义的词语,它与动摇、软弱、没落、颓废、灰色、消极、幻想联系起来,他们构成史诗叙述中的灰色幽暗模糊的地带。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小城之春》上映后,由于它所宣泄的颓废感情投合了当时一部分落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苦闷心情,从而赢得了一些观众,受到了某些人的赞扬。”“从费穆电影艺术创作的一生里,我们看见了一个爱国的、有才能的,但政治思想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艺术家的特征”[12]。这些含含糊糊的话语中,有着太多遮掩、遗漏,正是它们给后人留下巨大的可重新回味阐释的空间。
三 第三阶段:“重看”的赞誉与焦虑、学院话语体系、中国电影诗学
80年代是开始重看、重评费穆及《小城之春》的时代。汪俊绪认为,“就影片的思想价值而言,我们既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又无须给予过多的溢美,而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倒是它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该片在艺术上对中国电影所作出的贡献”[13]。进入90年代,对于费穆特别是《小城之春》的赞誉达到顶峰,几乎确立了该片在中国电影史上的至尊地位。《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李少白发表长文《中国现代电影的前驱——论费穆和<小城之春>的历史意义》,对费穆电影及其代表作《小城之春》的民族性、与儒学的关系、现代性、电影手段进行了彻底的重新分析和评价。香港的刘成汉为法国蓬皮杜中心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撰文称:“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是中国电影艺术上的一个里程碑,该片可谓集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优点之大成”[14]。
《小城之春》沉寂了数十年,总算获得了几乎至高无上的评价。我们需要了解的则是:这种重看和重评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进行,谁在看,谁在说话,以什么样的方式说出何种话,这一切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决定着。徐峰在《越界之行》一文对《小城之春》在80、90年代的接受情境有很准确的论述,“不同于《一江春水向东流》一类‘主流电影’(这些影片几十年来不断在影院或电视中重映,它们存在于广大观众的观片经验和记忆中),1948年短暂的公映之后,它便被束之高阁,从而失去了通过常规方式在影院中与观众对话的可能;然而,这部风格独到、形式完美的影片却又不能象那些平庸之作一般在电影史淹没无名,于是《小》成为一部依赖种种电影批评而存在的影片,这不仅长久以来,我们只能通过批评(普通评论、影片精读、电影史写作)窥见其雪泥鸿爪;同时还因为,今天这部影片的观众大多数是电影业内人士,或是中国电影回顾展的被感召者,而种种批评话语往往以其学术性和权威性,先入为主并强有力地引导着他们的反映。”[15]的确,对于费穆及其《小城之春》的重新接受背后有浓厚的学院因素在掌控,它将此转化为电影本体的学院知识体系和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心灵的深入解读,并付诸其以浓厚的影像中国的现代性和民族性色彩。
电影学术界对费穆电影的电影性、现代性、民族性的阐释中,其意义应该远不止“发掘”其电影意义和价值那么简单,这种话语实际上体现了接受者阐释者自身的某种文化焦虑和学术焦虑。这种焦虑首先体现于影像中国如何从自己的影像历史中打捞资源,并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叙述中给自己的当下和未来定位。一直以来,影像中国从早先的“左翼电影”中获得历史前提,而现实是,左翼电影已经不再提供影像中国未来主流的可能性。这是由左翼电影本身的叙事悖论决定的。真正的“左翼”永远将自己的位置确立在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批判性立场上而使自身取得永恒存在的价值,而民国时期的左翼电影在叙事上的“悲情”是不彻底的,它们在“暴露”“批判”“万恶的旧社会”的同时,在叙事上预设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如《万家灯火》中的“走向工农大众”,《乌鸦与麻雀》中“光明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三毛流浪记》结尾时举城扭秧歌的欢庆场景,左翼电影在叙事上埋伏了自我消亡的机制。早先左翼电影的最根本特性,即对小人物的悲情叙事和对社会结构不公的暴露,基本不可能进入新时代的主流电影叙事。
既然左翼的影像传统已事实上不可能为当下主流电影界包括学术界提供生长资源,“主旋律”电影又难以为学院空间提供有意义的话题,游离于左翼之外的费穆的电影,恰逢其时地替补了空白,成为学院话语中最“得体”的阐释对象,以释放其对于电影性、现代性、民族性的倾诉欲望。电影学科、电影史学界也藉此尽量驱除偏狭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于学院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的笼罩和遮蔽,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自说自话”的话语权力和自信心。于是以前“修史”中灰色暧昧的小资产阶级电影的贬义性定评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知识分子(或文人、作者)电影的正面论述,费穆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能保持自身精神独立性,既不“媚政治”也不“媚俗”的电影界内文化英雄般的人物。在关于《小城之春》的重新叙述中,都在强调这种情景:他置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时局世事于不顾,聚焦于一个抽离了党派政治的侵袭滋扰的小城一隅,对巨变前夕的若干中国人进行工笔细描,痴心不悔地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展示电影艺术的魅力。陈墨称,《小城之春》“在表现形式上熔中国古典诗词、绘画、戏曲的精华于一炉,在电影的艺术技巧和风格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试验,建立了一套耐人品味的民族电影叙事手法和技巧规则,并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从而使该片情节简单但寓意丰富,借‘闺怨’以寄托作者对家国兴衰和文化危机的忧思,寄意深远,充满弦外之音,创造了巨大的可阐释艺术空间。”[10]这些想象和赞语分明寄寓了说话者借费穆的《小城之春》来“浇心中块垒”,以省思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角色和际遇。
80年代以来对于费穆及其《小城之春》的重看、重评还有一个更大的语境和接受者更深的焦虑,即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身份焦虑。在好莱坞娱乐大片对大众影像世界的占领的同时,费穆的电影成为影像中国民族性的话题源泉,包括中国电影诗学、民族经验、东方电影、古典电影、先锋电影、银幕诗学、中国文化、古典诗词之类的现代性“民族主义”话语浸润着关于费穆电影的文章。例如应雄称它为“东方电影”的经典,“体现了我们东方人对感伤经验、感伤文化的态度……迷而不乱,恨而不惘”。[16]倪震也指出,“诗情电影”是中国的先锋电影,而这种“细腻而诗话的心理片传统”正是由费穆开创的。[17]评论者普遍认为,《小城之春》中,导演费穆将中国的诗、画、戏曲的古典美学神韵与电影的现代技艺作了圆浑的嫁接,创造出一种富于东方神韵的银幕诗学。这种论述分明隐藏着电影学术界藉此确立自身独特民族身份以参与“同世界对话”的诉求。
标签:小城之春论文; 费穆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艺术论文; 狼山喋血记论文; 城市之夜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